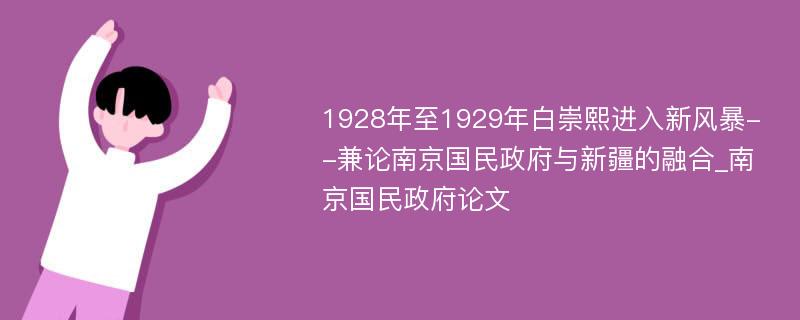
1928-1929年白崇禧入新风波——兼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之统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新疆论文,南京论文,风波论文,白崇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0)06-0022-09
一、引言
1928年7月7日,新疆军阀杨增新被戕,引发新疆乱局。杨增新被刺的消息初传至内地时,引起朝野震动,舆论哗然。事实上,新疆“三七事变”的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可谓始料未及,直到事隔半月之后,才采取了一些比较模糊的举动,对新疆政局的处理显得捉襟见肘。此间,中央和地方报纸均对此做了大量报道。震惊之余,人们对于新疆政局未来之运行给予了积极关注。与此同时,对中央政府统合新疆之举措亦有相关报道见诸于媒体。
是时,南京国民政府、新疆地方政府、社会舆论就新疆局势之演变及化解新疆政治之危机展开了宣传与公关,并进而引发一场关于白崇禧入新的风波。此间,白崇禧入新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热烈欢迎、翘首以盼者有之,如此时社会媒体;忌恨者有之,如西北军阀;恐惧观望者有之,如新疆地方既得利益者;心不在焉、瞻顾者有之,如白崇禧本人及其所在的桂系军阀;有心无力、拟强干弱枝者有之,如中央政府执权柄者蒋介石等。真可谓刻画了一幅幅精彩生动的浮世绘。
关于白崇禧入新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央政府对新疆统合之决心的研究,据笔者检阅,关注者不多。其中,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①、吴绍璘《新疆概观》②的相关章节对这一事件有较多叙述,但多是史料的罗列,未得其事后之精髓。此外,事件亲历者本人白崇禧在其个人回忆录③中对此事有所提及,其部下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系列文章④对此事件亦有相当反映。但总体来说,或浮光掠影,或语焉不详,终不得事件之要领。
基于对上述先行性成果之分析,笔者认为,有关此期白崇禧入新事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它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背后反映出的中央政府对新疆之统合,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拟将依靠相关文献、档案及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由白崇禧入新事件着手,叙述这次风波背后的故事,进而通过这个风波所反映出来的三方力量的博弈,分析中央政府统合新疆之决心及其实效。
二、契机:中央政府物色入新人选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接受授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清新疆巡抚袁大化第一时间给予承认,并通电拥护。为统一全国各省职官名称,新疆巡抚被改为新疆都督,袁大化就任新疆第一任都督。新、伊和谈⑤后,杨增新就任新疆都督,主持新疆军政大局。总体来说,鉴于袁世凯在前清时期继承下来的崇高政治权威,杨增新对于袁世凯甚为膜拜,并对其所领导的北京政府保持了高度认同。或可言之,从1912-1916年间,新疆地方与中央政府大致保持了实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联系。如果说袁世凯因为基于正统的地位及其政权来源的合法性而得到了杨增新的认同,那么对于1916-1928年间历届昙花一现的中央政府而言,无论是其正统性、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难以得到杨增新的承认。与此相对应,此间杨氏领导的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精神纽带亦相当疏离。至1928年北伐成功,蒋介石接管南京国民政府,杨增新尽管采用了“认庙不认神”的故伎通电拥护,但实际上新疆仍处于游离国民政府之外的半割据状态。
新疆地方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离心倾向,这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在新疆的外国人亦有所察觉。美国人巴敦指出:“新疆在表面上仍然属于中国,而实际上则与中国其余各部分显然分离,成了独立的状态。”⑥瑞典人斯文·赫定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在新疆当局的眼里显然形同虚设。”⑦此间关心西北者,大多意识到新疆表面尚称无事,而隐患已预伏渐深,苟不急图,屏藩立可倾覆。南京国民政府当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亦曾多次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表达了统合新疆之愿景。尽管如此,终杨增新主政之期,新疆地方与国民政府之游离关系一直未有变化。
直至1928年,新疆发生的一场事变,总算为中央政府统合新疆提供了一个契机。是年7月7日,杨增新参加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席间被戕身亡。杨增新被刺的消息传至南京,朝野惊异,徒以邈远,真相莫名。中央政府接到金树仁关于新疆事变的报告后,一面去电抚慰金树仁暂时代理新疆省主席,妥为维持地方治安;一面致电距离新疆较近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嘱咐其派员前往新疆调查军队情形和政治情况,为国民政府控制新疆做足准备。随后,国民政府于7月29日、30日先后收到刘郁芬的两封电报。电文报告了新疆事变的大致经过,强调新疆比邻苏俄,民族复杂,金树仁才智远逊杨氏,恐新疆从此多事,国防亦要吃紧。建议若要统合新疆,“必须中央派遣才学兼优、声望素著之大员前往,方有建设新疆之可能。如此种人选一时不易,以目前情形论,似不如派一老成稳练与负清望之人物前往收拾较觉相宜。”⑧
此间,新疆实际为金树仁所控制,由中央政府派员接管新疆无异于与虎谋皮,金氏必定竭力拒之。当时就有人观察到了这一点,并撰文指出:“我以为永久的治理与最近的收拾,绝非派一个什么大员,带几个随从如内地走马上任就可以的。第一是不谙新疆内情,处理不周,即可以断送新疆,糜烂新疆;第二是现在维持现状的杨氏僚属,正在用杨氏老把戏来拒绝派人,若以不相熟识或与本地素无关系的人去,足以酿成最近的第二次政变,也许因此引起全省的大混乱;第三是邻近两大帝国主义,正在想吞并新疆为己有,而我们又不慎重的处理,给他们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何乐而不为?”⑨其中前述两个问题正是国民政府统合新疆面临的现实困境,即中央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的博弈,派遣大员与新疆地方政府的博弈,而第三个问题则是因与新疆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不当,可能带来的远景威胁。
事实的确如此,新疆局势异常复杂,远非孱弱的中央政府所能把握。是时,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疆问题上颇费踌躇,武力控制新疆力有不逮,听任金树仁割据西陲亦情非所愿。综合多方面因素,中央政府为表明统合新疆之坚决立场,遂决定选遣赴新大吏,徐图处理之。而新疆民族杂处,人选不可不慎。当时情形下,中央政府内部有两位人选呼声颇高:其一是冯玉祥,其二是白崇禧。
冯玉祥应声而出不难理解。早在1919年之时,北京政府就曾有移兵新疆屯垦之议,冯玉祥因之欲西进,但杨增新绝对不允许冯玉祥染指新疆。是时,杨氏笼络新疆各族王公、头人,让他们联名通电中央阻止冯玉祥入新。由于措辞激烈,冯玉祥畏难而止。⑩1923年以还,冯玉祥兼西北边防督办,他非常清楚新疆是个地广物丰的地方,而且离自己的地盘又近,若能控制新疆,将其作为今后屯兵养兵的基地,那么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亦有保障。随后,冯玉祥的部下刘郁芬进驻兰州,担任甘肃省主席;宋哲元亦担任了陕西省主席。这为冯氏进驻新疆奠定了基础。杨增新被刺身亡之后,伸足新疆仍是冯玉祥的目标。据1928年8月8日《中央日报》报道,冯玉祥在豫,极注意新疆,并有回族代表马廷襄、马超群、定希程先后至河南、南京,分头请愿整理新疆政治及政府垦荒,国民政府亦曾批令开封政治分会就近办理。前后各代表又继续请愿,希望冯总司令以革命手段改革新政。冯玉祥决定先派员赴新疆调查,以备改制划区。
然而,站在南京国民政府之立场,它万难容忍冯玉祥入主新疆,其动机可谓了然,即不希望冯玉祥在西北一人独大,对中央统合地方之可能性构成挑战。显然,从民族国家之构建和中央政府之权威的视角来看,这具有合理性。故而,作为应对,南京国民政府必须物色一个较为合适的人选,一方面要给舆论公众一个交代,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形成冯玉祥指斥中央之口实。基于此,中央政府积极物色入新的中意人选。而最终,这个人选被圈定为白崇禧。
三、风波:白氏入新故事的演绎
白崇禧是一位自青年时期就对新疆充满兴趣和情感的政治家。1915年6月间,白崇禧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在校两年,毕业时,白崇禧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多个同学,自愿分配到新班担任见习官。大家均想训练一支边疆新军,为巩固边防、增强国防之用。青年白崇禧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回教徒,如去西北地区工作,极易与当地人民亲密合作,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关于这一段历史,据白氏回忆称:
我动身之前,书禀先妣,并与诸兄弟辞别,言此行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之壮志。比及北京,向训练总监部,按章领取旅费国币交通银票五百元。原定由京奉路经东北,转乘西伯利亚火车,沿土西铁路至阿里木铎,然后换公路至迪化报到。恰巧此时苏俄红军于列宁领导下,推翻尼古拉政权,白党谢米诺夫退据西伯利亚,我们无法经过西伯利亚,因而打算由陕甘出玉门关入星星峡。不料陈树藩盘踞陕西与北京政府为敌,不准我们通行。训练总监见无路可至新疆,改分发我们回广西原籍见习。我回广西被派至陆军第一师第三团。此我回广西之始,也是我第一次未实现去新疆之志愿。(11)
通过白氏之回忆录以及相关文献的佐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青年时代的白崇禧出于一颗赤诚之心和一个革命军人的责任感,对新疆之行充满期待,也真心希望在新疆创造出一番事业。但颇为无奈的是,兵燹之灾让白氏无功而返。
到1928年,年仅33岁的白崇禧已成长为一方诸侯。如果说,1915年之行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客观因素让白氏难偿所愿的话,那么,际会于历史的风云,新疆“三七政变”则再次为白氏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前往曾经向往的新疆成为可能。
此间即北伐军光复北平后,蒋、桂之间表面上似乎还算平静,彼此礼尚往来,但由于曾经有逼蒋下野故事,暗中内讧之象不断,矛盾日益加深。坊间亦传出了种种秘闻,声称白氏功高恃力,欲长留北方,经营北平。(12)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予以体察,在消除奉系张作霖之患后,如何安排白崇禧,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恰逢新疆政变之际,从阎锡山的天津卫戍司令部里吹出一股冷风:蒋介石欲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要求白崇禧做出抉择,要么到新疆做官,要么出国到欧美视察,总之就是要削去白崇禧的兵权。基于当时情形,这一传言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可以想见,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若能将白崇禧从北平礼送出境,转赴新疆,一则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收北平,起到“强干弱枝”之功效;二则可以利用白崇禧牵制西北独大的冯玉祥部(13);三则对于新疆混乱局势的控制又不啻是一个转机;再则倘若白崇禧不愿服从中央政府之安排,拒绝入新,则至少可将白氏入新事作为一个棋子,表明了中央政府统合边疆之决心,亦可对新疆地方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此可谓一举数得。
就白崇禧个人而言,一方面,其本人是回族,而新疆少数民族多信仰伊斯兰教,这使得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他,认为惟白氏能当此重任。(14)比如,10月13日,胡汉民致信白崇禧:“与任潮(李济深)、真如(陈铭枢)等深谈,以为吾党军人,宜以目光远瞩,中国国防在北而不在南,满蒙已成为俎上之肉,新疆广漠,乃复无人置念。赤俄垂涎已久,若我遽失其控驭,则英必起而取藏,尔时屏藩尽失,所谓五族共和国者,满蒙回藏俱非我有,中华民族何以发展,何由巩固?惟此仔肩,谁能任之?我环顾武装领袖同志,以为惟有健生足胜任愉快。”(15)随后,谭延闿亦致信劝告白崇禧入新疆:“经营新疆为极关紧要。非急起直追,恐落人后。静江、石曾、任潮、德邻诸公,皆然其说。环顾同志中人选,惟公可膺此艰巨,介石亦有同情,特托真如兄来北平,期公同意。……闻不得千里马,好奇之心,尤为欣动,公想已实验,能以其骨象意态告我否?”(16)
另一方面,通过相关材料可知,白崇禧是时处境相当尴尬,亟须解脱之法,故对新疆局势之演变亦颇为关注。1928年北伐完成后,全国舆论有裁兵建国、裁兵救国之呼吁。此间,白崇禧尽管头顶北伐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的光环,且在北伐胜利后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表面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实际上驻北平的军队,不是桂系部队,而是收编的唐生智旧部。国民政府亦打算于次年1月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商讨裁军及相关将领之安排事宜。白崇禧对裁兵一事着力反对。对此,他做如下解释:当前形势不重在裁兵而重在实边。实施总理之兵工政策是本建议之主要精神所在。边疆地区有许多宝藏,只因为交通不发达未有开发,如果成立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不但解决了国家财政之困难,也安置了北伐期间有功勋之将领;不仅给他们以地位,而付以建设之重任。随后他又提出,当前边境未靖,如新疆7月7日发生政变,此一事件表示出新疆从此多事。边疆未固,何能轻言“裁兵”?(17)
显然,就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所处政治地位而言,白崇禧入新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可能正是基于上述诸种考虑,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冯氏入新事,尽可能地降低论调,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对“白崇禧入新事”则可谓“用心”,在不同场合予以高调宣传,同时还派与白氏有同志之谊、兄弟之情的中央委员陈铭枢专程前往北平予以劝导。
从上述讨论,可大致了解到:新疆政变发生后,无论是出于中央政府统合地方之愿望,还是白崇禧本人所拥有之身份及所陷之困境,似乎白崇禧入新已是众望所归,让白崇禧入新呼声日益高涨。事情的发展果真是如此吗?
白崇禧收到胡汉民和谭延闿的劝慰信后,及时做了回复。在回函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入新一事的强烈愿望。内中声称:“真如兄(陈铭枢)北来,赉赐诸公手教,辱承关注,期许过殷,良用惭感。训政开始,党务政治,幸赖老成硕望主持中枢,党国前途,为无量颂。中国国防重在西北,诚为不刊之论。……辱以不才,缪承推许,苟利党国,岂敢推辞。禧束发受书,置身军旅,捍内御外,不敢后人。”(18)
随后的信文中,白崇禧在献身党国、驰驱边陲的豪言壮语下,就经略新疆之计划提出一大堆近似于先决条件的要求:中央应设立国防会议机关,讨论整个国防计划,统筹国防军队、经费、交通诸问题;先完成包宁铁路,再延至迪化;即刻筹划设立西北航空站及修筑西北公路,以为目下利军运、便交通的应急之需。并请胡汉民、谭延闿等人代为转陈中央政府。信文的最后,他再次表示:“边患日亟,今古异势,若不妥定实边之策,远树百年之计,轻率从事,恐蹈徐树铮之覆辙。区区愚忱,非敢过虑也。诸公伟划尽筹,远瞻高瞩,必有老谋深算,示我周行,辱在不弃,敢献芻荛,尚乞鼎力主持,妥定国防大计,禧献身党国生死以之,边陲驰驱,不敢告劳也。”(19)
与此同时,白崇禧还就入新一事高调地接受了相关报纸的采访。在访谈中,他亦表达了乐意接受入新使命的愿望。《申报》11月4日载:3日,白崇禧在北京语记者,表示“甚愿去新疆”,“如中央下令,余即前往”。6日,《申报》又披露《白崇禧赴新之条例》。14日,《申报》发表白崇禧与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来往函件,意谓其愿赴新疆。20日,又载白崇禧于19日发表对新疆问题处置的意见,陈说苏俄侵略新疆之野心。21日再载北京20日消息说,新疆问题,中央征求白意,白表示“愿负艰难”。(20)《民国日报》于11月5日,亦以《白健生关心边事:促奉放还平奉车辆,愿往新疆改良回教》为标题作了更为详细的报道。关于白崇禧本人对入新一事究竟抱何种态度,《民国日报》猜测,“至白如何表示,自是秘不得闻,惟有人晤白谈及时局。白之谈话,有足与上述相发明者”。随后,该报又追寻相关蛛丝马迹,对上述猜测予以佐证:“据白信语人:有人更以新疆之行,意思如何。白答覆大意:谓中国军队,本应全任国防,内地各省区,只要有警察防盗患已足,原不必鏖集大军,而本人对于新疆尤所愿往,盖本人乃回教中人,惟志欲改良回教,故与普通回人又有区别。……今后如果中央有办法,则一纸命令,立当率所部健儿,躬赴天山,决不辞此一行也云。”(21)
事实上,此间白崇禧亦在相关场合向中央政府表示忠心,“我是一个回民,对西北人地相宜,深愿统率第四集团军五万人赴新疆从事殖边工作,如总司令准我所请,今后中央将永无西顾之忧。”(22)
从白崇禧对诸位同仁之表态,以及对相关报纸发表之宣言来看,白氏入新一事,就其主观因素来说似乎非常确切了,现在要等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纸批令。但随后事态的演变,似乎并没有朝着此间报纸媒体报道和社会公众期望的进路向前发展。
四、博弈:中央政府对新疆之统合
尽管白崇禧及其相关同仁对入新一事颇为急切,社会舆论亦是异常关注,但终究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进一步认定和详细的后续政策安排。可能的情况是,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白崇禧暂时答应出走新疆,仅仅是个自保的战略,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试探中央政府如何安排自己的态度,以求应变之策。由是,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政府对于白崇禧入新事保持了沉默。
这一时期,关于白崇禧入新的传言,引起了新疆地方政府官僚如金树仁等的强烈反应。
金树仁自掌控新疆以来,效颦杨增新,一方面表示服从中央,但同时又婉拒客军入新,且加强新疆东路边禁。新疆“三七事变”发生后,金树仁随即打着为“辩诬阴谋刺杨事”和服从中央的旗帜,自行设立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这实为金树仁为迎合中央、确保中央承认他为新疆合法的统治者之举动。7月16日,金树仁即授意新疆省参议员联名上书南京政府,要求正式任金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9月12日,金树仁又以新疆省党部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等有关部门和军政要员,高调宣扬金为杨增新的高足,“学通古今,才兼文武”,“历任要缺,久著贤声,于政治极有经验,于边情最称熟悉”,“尚望当局诸公加以考虑,勿为奸人谰言所摇惑,则边局幸甚,党国幸甚”。(23)可以说,新疆局势的演绎,虽有甘肃省主席刘郁芬等人的陈报,南京国民政府终不能了然于怀,更谈不上驾驭和掌控。
此期中央政府尽管实力很弱,但从未放弃新疆,转利用宣示、实践的手段试图控制新疆,国家权力的渗透不断深入。一方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设立的省党部,中央政府认为“新疆省党部人员未经过中央正式委派,决议不理”(24)。另一方面,南京政府由于一时没有武力控制新疆的能力,而长期空悬主席一职实非良策,只得考虑改组新疆省政府的问题。此间金树仁曾奉令依据省政府组织法呈报委员人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批示通过。10月31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任命金树仁、王之佐、徐谦、刘文龙、张正地、陈继善、阎毓善、屠文沛、李溶为新疆省政府委员,指定金树仁为主席,并任命王之佐兼民政厅长,徐谦兼财政厅长,刘文龙兼教育厅长。(25)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留了后手,并没有同意金树仁提出任命其为边防督办的请求。
金树仁在被正式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半个月后的1928年11月15日,即派遣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为全权代表赴北平拜会白崇禧。就当时情形而言,这次会晤对双方来说,都可称得上是一个“测试水温的场合”。对于金树仁而言,他需要自己的亲信当面向白崇禧求证,确证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白氏入新一事是否属实,然后计划应对中央政府统合之措施;而对于白崇禧来说,他可能需要进一步明晰新疆地方既得利益者对其入新的态度,并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预测。这次会谈中,鲁效祖先入为主,甫一开始即表示:闻白将入新,致欢迎意。但随即又历陈入新之不利,实有阻白入新之意。眼见新疆方面态度如此坚决,白崇禧明白,入新一事实不可能。遂当场向鲁效祖表白,赴新系胡汉民等与之函商,并非本人主动。(26)
此番接触后,鲁效祖于11月25日携新疆驻京办事处主任钱桐即在南京宴请报界,介绍新疆近况,大谈新疆交通之极不便利。并说“近报传某方将派兵入新(27),某方(28)有整饬新疆之预备,此种宣传,不但足以激起新疆人民之反感,且亦非中央政府对于新疆之主旨,亦与事实不符”。还说“新疆人民自杨增新主持省政府17年来,完全养成人民之一种自决性质,凡与我好者,不论其为友邦、为官吏,皆为我们亲善”,新疆“对于外来纸币,全不适用,此是人民有自决能力之一端”。鲁效祖最后表示:“此次效祖经西伯利亚铁道来京,俄人开盛大之欢迎会,非为效祖个人,实对新疆之人民,可见新疆之内政外交,均皆妥善。盖新疆一省,与西北之关系极大,此则可以告慰舆论界之诸者。”(29)这一番演讲,至少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金树仁决心继杨坐镇新疆,同时亦有能力管理好新疆,无须中央政府过问;二是新疆无论对内对外,以好报好,以恶报恶,暗示倘若中央政府有进一步统合新疆之举措,新疆地方政府可能会利用苏俄正欲结好新疆之机会,以对抗中央。
新疆地方政府在公开场合表明对中央政府统合新疆之举措的强硬立场的同时,还及时与中央政府就新疆局势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以求得中央政府对金树仁领导的新疆地方政府的谅解和承认。12月16日,京沪各报均载金树仁致蒋介石电文。该电文中,金树仁对蒋介石极尽其奉承巴结之能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氏极赞蒋氏度量之宽容,说蒋“乃以泰山之高而不遗土壤;以河海之大而不择细流”,还说新疆“已如伤弓之鸟,稍闻谣诼,辄起惊疑”,“外蒙野心未戴,时时乘机思逞;苏俄处处接壤,头头是道,尤应特别注意”等等,是以外蒙和苏俄隐作威胁。随后,金树仁又派广禄到南京献金,向各政要馈赠大量新疆名贵特产。金氏还寻找各种借口,通过函电与中央政府大员通好。然而,关内码头甚多,显非新疆地方所能周旋,所以,此间关于中央政府拟进兵新疆、以安国防的谣言依然层出不穷。
显然,对于上述情形,新疆地方政府感到异常紧张。1929年春,金树仁再次发动新疆省政府全体委员,采取各种通电、通函形式,尽袭杨增新若干年前所持之理由,婉拒客军入新和屯垦殖边。(30)与此同时,金树仁与驻南京新疆办事处的钱桐、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就时下局势进行沟通,并私授机宜。他在通电中声称:
顷接获孟村(钱桐)来函称,新疆军事方面,中央特派人来新负责等语。查新疆孤悬塞外,幅员辽阔。又以接壤英俄,国御本极重要,巩固国防,不得不厚积兵力。然徒恃兵力犹非根本要图。民国成立十有余载,当宇内鼎沸之际,而新疆四境安然,七区不惊,无非由于内政修明,外交胜利,人心团结,始获保此太平之局。否则,外患相迫,宁自今日始耶?中央近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为惟一不二之政策,而新疆于领事裁判权以及英侨商货免税恶例,数年以来,已完全取消,是中央与各国几经榷商,未易就绪者,以区区新疆一省,居然获占优胜于两大强邻,此岂尽恃武力耶?要亦以公理战胜强权耳。兹使河山再造,百端待理,庶政革新,大有蒸蒸日上之势,英俄两国与我国益敦睦谊,不但无侵略之心,抑且不敢轻视,事实俱在,并非虚语。上年七七之变,我方于沿边一带扼要设防,时因发生内乱,全境戒严,抽调军队,分别驻扎,尚不致彼方猜疑,所以数年以来相安无事,无形之间已将国防布置周密。我现无隙可乘,彼亦绝不甘冒不韪,此以省防为国防,而国防即可保其有备无患,并拟实行寓兵于农办法,凡守边之兵,每三年即令退任屯垦以资休养,而以新疆训练者调补一兵换防一次。如此轮派,将见十年以后,全疆皆兵矣。此种计划,要在因地制宜行之以渐,而非急切所能图功。现在新疆军队业经切实改编,扼要分布,若劳师糜饷,万里间关,以无数客军猝临边地,设使彼方发生误会,边釁一开,谁尸其咎。外蒙被陷,何尝不因徐树铮以重兵压境,激之使然,前事之复,可以殷鉴。想我国府诸公,为维持边局治安计,谅必不至出此,树仁不敏,既荷倚之重,誓当为国宣力,对于新疆国防自应担此全责,决不致贻政府西顾之忧。倘祈详加考虑,幸勿轻信谣传,则新疆幸甚,大局幸甚!(31)
随后,新疆省建设厅厅长阎毓善等人又以省政府委员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发电,声称客军入境必不予赞同,移民屯垦亦不相宜。其电文内称:
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钧鉴:行政院、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参谋本部钧鉴,南京驻京办事处钱代表桐、鲁代表效祖、张代表凤九鉴,近接钱君来函,内有新省军事一方面,政府意有另派人来新主持等语。又报纸多载新疆国防问题,拟派某人赴新云云。查新省当七七之变事出非常,人心惶惑,谣言甚剧。彼时固十分危险,金主席以国防关系为重,负责于危乱之际,协心同力多方维持,近数月来地方安宁,邻邦和睦,窃盗各案亦鲜发生,方拟将各项要政已办者力行扩充,未办者设法指导。人心既定,政治可日渐修明,乃局外弗察,发生疑虑。若由内地派军队来新,孤军深入,转输困难,万里遥远,交通梗阻,恐未便轻率从事,而边防军心不免因之浮动,各界闻之,亦怀疑惧,以为无事自扰。窃恐无聊政客,视为投机事业,不知新疆痛苦无所希冀,而于边境前途影响甚巨。(32)
该电文还对新疆的外交、军事、内政、国防最近情形作了详细陈述,并表示新疆省政府有能力处理好各端问题,毋庸中央政府顾虑。电文的最后还就新疆不宜屯垦一事作出解释:东南人满,西北土满,移民固为当务之急,然新疆垦辟一事有特别困难情形,盖由荒地虽多,水源甚少,雨泽自稀,全恃灌溉,无水之地等于石田,开辟之地反多荒芜。春夏之交,急于用水,气候甚寒,雪难融化,盛夏秋初,山水暴发,又每冲毁渠工。因此,“移民屯垦一事,有未敢轻谈者也”。
新疆地方政府软硬兼施的种种举动并未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正面回应,但让金树仁等稍稍感到安心的是,此间关于中央政府统合新疆的呼声亦逐渐归于沉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放弃统合边疆地区之决心。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议决案中,其中关于“政府组织与地方自治”之条目即强调:“过去十七年间,国人既无此种国家组织之观念,而军阀官僚,复将前清帝政时代所遗传之统治权裂而分之,以致政府与人民之权力,两受其害。投机之政客,从而各倡集权之分权之谬说,以济其恶。于是国民对于国家权力之正当组织,益无从获得明确之观念。殊不知治权属于中央政府,政权属之地方人民,治权与政权各有所属,则窃取中央政府权力以归于各省者,固为国家所不容,即倡分权集权之说者,亦为无病而呻者也。”(33)并且,政治报告第七项议决案中关于新疆的条目明确申明:“吾人今后,必力矫满清、军阀两时代愚弄……及漠视新疆人民利益之恶政,诚心扶植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之发达,务期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造成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34)
也就在此时,即1929年3月下旬,蒋桂战起,李宗仁、白崇禧南逃广西。随后,1929年4月4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整饬党纪之通令严正指出:“关于目前之时局者,某某(此处系指李宗仁、白崇禧,笔者注)等称兵谋叛党国,全国代表大会为伸国法,以立党纪,全场一致议决讨伐,而一切反动分子及失意之军人政客,又认此为捣乱之机会,造谣滋事,挑拨离间,中央对于此种坏法乱纪之徒,唯有与叛逆同科,绳之以法。”(35)至此,白崇禧入新事遂寝。
五、结语
昔有“盲人摸象”之故事。若借喻“白崇禧入新事”为一象,本文权当是“各明一义,俱有所当”,期能增进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综观此期围绕“白崇禧入新事”展开的中央政府对新疆之统合过程,以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中央政府与白崇禧、中央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白崇禧等三者的博弈,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端认识:
1.此期中央政府尽管实力很弱,但从未放弃新疆,利用宣示、实践的手段试图控制新疆,国家权力的渗透不断深入。
在正史、地方志等古代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地方之统合,往往呈现出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的图景。这一类论述与概念无疑是建立在大量经验事实基础上的,并且与我们通常的观察相符合,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可能还会面临地方因素的挑战。此期南京国民政府肇建,中央政府对于新疆的地方势力还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把新疆建成“独立王国”,因为制度的缺陷而成为可能,“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尽管如此,追求主权的真正统一和完整仍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原则,并且在具体实践中,通过一系列举措予以展现。
此间,中央政府大肆宣传白崇禧入新事,一度导致以金树仁为首的新疆地方当权者十分紧张。在此过程中,金树仁苦心孤诣地追求,且极为乐意地接受了中央政府对其职务的任命,并先后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总体来说,在本身力量虚弱的情形下,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和一个被构建出来的故事,在对新疆实施统合的过程中把握住了方向性的主动,并为以后实现对新疆的根本控制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此期中央政府在没有明显的介入的情况下,形成一种“未出场的扩张”。在这样一种“未出场的扩张”中,中央政府所获得的,主要不是更有效地控驭新疆地方的制度,而是金树仁等当权者对自己的权威、象征的认同。
可以这样认为,此间围绕着白崇禧入新风波所展开的中央政府对新疆之统合历程及其结果,如果撇开军阀争夺地盘之固有观念及其背后利益的追逐,它应当符合“国家构建”的程序,无论是出于完善国家职能管理范围,还是修复其管理能力,都有其合法性,亦具有其合理性。
2.“白崇禧入新事”的两种叙述文本凸显出白崇禧在这一事件中的主动性。
通过前述考察,我们发现,若以事件的一般经历者的视角审视白崇禧入新事的前前后后,白崇禧与胡、谭的来往书信,以及接受相关媒体采访发出的豪言壮语,无不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新疆局势的热切关注,同时也能体察到他对中央政府表达出的拳拳之心。一方面我们惊讶于白崇禧对新疆之热爱,另一方面,更对其表现出来的经营新疆之决心钦佩不已。
然而,当我们以历史的后来者反向上溯历史,进而裁决白崇禧当年的心迹——在搜集了相关白氏入新事的文献并加以分析后,会呈现出另一幕历史场景:由于白崇禧本人的回族身份,加之其窘迫的政治处境,再就是中央政府“安抚”(抑或“安排”)白氏的需要,故一时白氏入新之说甚嚣尘上。而对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白崇禧而言,入主新疆似乎只是其是摆脱暂时的尴尬政治处境的一个进路,所谓“愿负艰难”、“躬赴天山”、“志欲改良回教”等慷慨之词,更多的时候像是一个政治家的话语宣传。也就是说,入主新疆可能并非白崇禧之初衷,跳出当前政治困境才是其根本要图。白崇禧参与这场博弈所获实利的前景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怎样,白氏第一时间表示愿赴新疆,为其摆脱政治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也为其赢得了舆论上的主动。关于这一点,时人在《白崇禧辞职之内幕》一文中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白氏在国府治下,虽参与北伐大役,每次必与,然其名义固为一总指挥也。近虽有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及北平政治分会委员之衔名,然政治分会之寿命,至久不得过三月十五日。光阴如箭,转瞬即届。是白氏在政治上徘徊瞻顾,终觉有顾影自慨之感。最近全国编遣会议开会,又议决蒋总司令、总指挥等名称取销。白氏又受此打击。盖总司令、总指挥之如蒋介石、冯玉祥、陈调元等,固均已先期取得主席、院长或师长之实缺也。白氏之总指挥取消后,尚无下文。此若驻防新疆国防等之下不能成为事实,在白氏眼光观之,仅可作为枝叶问题,又岂白氏辞职之本心哉?(36)
3.新疆地方政府通过白崇禧入新事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承认及由此带来的合法性地位。
此期,新疆地方因杨增新被戕引发乱局,从而使得金树仁走上新疆政治前台,并逐步控制新疆政局。随后,从中央政府传出的种种谣言让金树仁感到非常紧张。显而易见,中央政府的虚弱力量决定了它不足以采取武力的方式控制新疆,但这仍然不能使金树仁放松警惕。在金树仁看来,当下最为要紧的是,中央政府是其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为维护自身在新疆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并最好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为此,金树仁在不同场合强调了新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认同。
事实上,围绕白崇禧入新事,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获得了统辖新疆权力的合法性:此间中央政府对新疆地方政府持认同态度,同意新疆省政府提请改组省政府的要求,并按照金树仁的提名任命相关省政府委员,同时还任命金氏为省政府主席。
上述历史图景让我们不得不对中央政府统合边疆地区的动机和方式进行再思考。以往,我们在考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方的治理的事件时,似乎总习惯于站在中央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强调中央政府治理经营边疆的坚强决心。显然,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边疆地方存在的一股很强的力量促使中央政府在边疆彰显自身的力量。(37)事实上,一个看似统一的边疆地方政府,其内部往往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呈现出内部竞争的状态。当与中央政府发生接触之后,某些团体或领袖人物可能会积极因应新的政治情势,借助国家的力量介入本地方的事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和中央政府或多或少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些新秩序甚至可能就此产生。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大体可以这样认为,围绕白崇禧入新风波的演绎,南京国民政府、新疆地方政府、白崇禧等三方力量展开了一场博弈。从过程来看,中央政府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将白崇禧入新纳入统合新疆的日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此事作为一颗棋子,用以宣扬和阐释统合新疆之决心;而白崇禧亦对中央政府之用心有诸多理会,故而仅仅是周旋其中,积极应对,从而获得舆论上的主动;新疆地方政府作为制度上的弱势方,被动地加入到这场博弈中,穷于应付。但从结果来看,显然这是一场多赢的对局:中央政府获得了新疆地方的高度认同;新疆地方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授权,维护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白崇禧则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
注释:
①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69年。
②吴绍璘:《新疆概观》,仁声印书局,民国22年版。
③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④可参阅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载《学术论坛》1985年第7期、1985年第12期、1986年第1期。
⑤所谓新、伊和谈,系指新疆辛亥革命以来,以杨增新为代表的原新疆旧政府与革命党人掌控的伊犁临时革命政府,宣布于1912年4月在塔城展开的停战议和。双方围绕两个重要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其一,“分治”还是“合治”的问题。伊犁代表主张新疆分而治之,划天山为界,天山以北归伊犁临时政府管辖,天山以南归原新疆政府管辖,杨增新的代表主张“统一治理”,不但原伊犁地区和原新疆政府管辖地区合治,而且塔城、阿尔泰亦统一由新疆政府管辖。其二,在省议会未成立之前,由谁主持行使军政职权的问题。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双方最终于1912年7月8日达成和议条件11款。在和议条款中,双方确定迪化为新疆首府,公举杨增新为都督,主持新疆军政;撤销新伊大都督府,“以归统一”;设立伊犁镇边使署,以取代新伊大都督府行使伊犁管辖权。
⑥(美)巴敦:《美人眼中之新疆》,吴伟英译,《边疆》半月刊第1卷第4期。
⑦(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⑧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所藏外交部档案抄件。
⑨寄萍:《新疆之过去与未来》,《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第二卷第十五期,民国17年8月30日版。
⑩详情见1919年10月东日(1日)《新疆蒙哈回缠王公及各族联络会通函》。可参阅罗绍文:《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
(11)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12)据《民国日报》17年8月17日报道,是年8月15日,白崇禧对美记者谈话中,就外界的质疑做出了回应和辩解:“外界传彼将于北方开一新地盘,非事实;彼奉命而来,任务倘了,即当回去。”
(13)1929年3月4日,冯玉祥在其日记中借时为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的话提及:“日本田中有言,新疆宜归西北军,而蒋派白崇禧前往,意在分散桂系势力,且以牵制冯氏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冯玉祥日记,1929年3月4日条。)
(14)据白氏族谱记载,白家的始祖是伯笃鲁丁。又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松亭所述,伯笃鲁丁是阿拉伯人的名字,所以白崇禧的始祖是一个来自中东的穆斯林。
(15)吴绍璘:《新疆概观》,第307~308页。
(16)吴绍璘:《新疆概观》,第307~308页。
(17)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学术论坛》,1985年第12期,第65页。
(18)吴绍璘:《新疆概观》,第305~306页。
(19)吴绍璘:《新疆概观》,第306页。
(20)以上所引《申报》文亦可见于《白崇禧之国防意见》(《民国日报》,民国17年11月7日)、《白崇禧愿赴新疆为免新疆成库伦第二》(《民国日报》,民国17年12月11日)。
(21)《白健生关心边事:促奉放还平奉车辆,愿往新疆改良回教》,《民国日报》,民国17年11月5日第2版。
(22)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学术论坛》,1985年第12期,第65页。
(23)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所藏外交部档案抄件。
(2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5),第2718页。
(25)中央政治会议第161次会议记录,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28年10月31日条。
(26)《申报》,民国17年11月16日,第7版。
(27)本处系指蒋介石派遣白崇禧入新事。
(28)从当时情形看,此处应系指冯玉祥。
(29)《申报》,民国17年11月26日第4版、27日第6版。
(30)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29年3月4日条。
(31)上海《时事新报》,民国18年3月3日。
(32)上海《时事新报》,民国18年3月5日。
(33)《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页。
(34)《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84~85页。
(3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120页。
(36)此件选自国民党查扣的上海朝日书局印行《看不得》一书,原载1929年9月1日《福尔摩斯》小报。另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99页。
(37)李文良:《清代台湾岸里社熟蕃的地权主张》,(台湾)《历史人类学学刊》,第3卷第1期,2005年4月。
标签: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新疆省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白崇禧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冯玉祥论文; 杨增新论文; 申报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