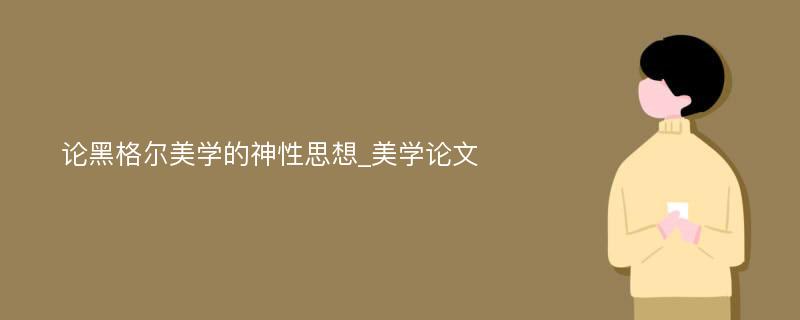
论黑格尔《美学》中的神性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美学论文,思想论文,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神性”(或“神圣性”)一语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的《美学》一书中频频出现,“神性”在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黑格尔在书中明确写道:“只有靠这种自由性,美的艺术才成为真正的艺术,只有在它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1](P10)(着重号为原文所加)“艺术首先要把神性的东西当作它的表现中心。”[1](P223)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国内诸多《美学》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到目前为止,从这一角度来立论的著作并不多见。个中原因或可归结如下:马克思、恩格斯虽曾明确指出但并不过多提及黑格尔哲学的宗教、神学内涵,主要考虑的是吸收其合理内涵以建立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而原苏联与中国学界大概误解进而延伸了这一做法,在解读黑格尔学说本身的内容时,也将它固有的宗教、神学内涵排除出去了。这种做法当然不够妥当,有失学术研究客观与公正的立场。
一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P142)这是黑格尔给美所下的著名定义。在黑格尔的哲学、美学思想中,“理念”无疑是一个核心概念,只有理念才是最高的真实,是世界真正的本体。而“理念”在实质上便等同于“上帝”、“神”、“普遍精神”、“绝对心灵”等用语,有着深厚的宗教与神学的内涵。
黑格尔的“理念”实则等同于“上帝”,这还要从有关基督教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谈起。上帝是否存在及可否认识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非同小可,自中世纪以来无数思想家都试图给予回答。黑格尔也并不例外。但他不满意于之前有关这一命题的种种理论,尤其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以及直觉主义的观点(即认为上帝只能依靠直觉来信仰,而不能靠理性来证明)。他十分明确地说:“哲学的对象与宗教的对象诚然大体上是相同的。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唯有上帝才是真理。”[2](P37) “哲学除神以外也没有别的对象,所以其实也就是理性的神学,并且就它对真理服务来说,它也就是永远对神的服务。”[1](P129)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安瑟伦把“上帝是最完善的东西”作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出发点,但是他却最终把上帝视为一个抽象的、静态的纯粹概念,从而导致一种片面性和不完善性。黑格尔批判继承了这种旧形而上学,把它改造成了自己思辨的、即辩证法的哲学。既然上帝是最完善的,那么必然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关键便是思维与存在是如何达到具体的统一的,也就是说概念如何扬弃自己的主观性而走向客观性或现实的。这样一来,上帝便只能被理解成自为的精神,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在自我否定和自我复归的发展过程中实现自身——即完善性和无限性。这种能够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概念就是上帝,就是理念。他说:“至于上帝之形而上学概念,就此说来,被理解为:我们应只讲纯粹的概念,这一概念通过自身成为实在的。因此,上帝(神)的规定在于:他是绝对的理念,亦即他是精神。而精神,绝对的理念,是概念与实在的统一;于是,概念在自身内则是总体,从而亦是实在。”[3](P413)
可以看出,黑格尔的上帝作为绝对理念已经被思辨化、理性化了,这不同于基督教信仰中的人格神(如《旧约》中的耶和华)。但是,上帝/理念并非与此无关。国内有学者指出,基督教“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蒙难”及“复活”等教义内容不过是黑格尔哲学概念的譬喻和表象;在其早期的神学思想中,理念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个体性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通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表象形式来表达的。圣父被看作普遍概念那原始的合一;圣子耶稣降临人世则为“道成肉身”,通过变形成为特殊的、有限的存在;圣灵又是对于圣子的否定,通过圣子耶稣的蒙难和复活,一切对立都最终被扬弃了,一切分离都在团体精神即圣灵中实现了真正的统一。[4](P105)这样,黑格尔一方面对基督教教义和表象进行了合理化阐释,完成了对神学的哲学化改造;另一方面又把理念、精神提高到绝对,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的、无限的)上帝,从而使哲学成为更为精致的神学。[4](P117)
应当注意的是,黑格尔《美学》中大量使用的“神”“神性”等语汇,其含义更加宽泛,并不局限于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包括所有异教神在内,特别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这种泛神学观的谈论方式,体现了黑格尔思想中非基督教的一面。
理念是富于神学内涵的最高真实,而艺术则是对于这最高真实的一种把握,对于理念的一种认识形式。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这种认识的第一种形式是直接的也就是感性的认识,第二种形式是想象(或表象)的意识,最后第三种形式是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这三种形式分别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它们作为理念精神实现自身的三种方式,构成了人类认识最高真理的三个阶段。[1](P129~133)这里,黑格尔所赋予艺术的神学及宗教内涵显而易见:艺术和宗教、哲学拥有共同的本质内容(即理念/神),只是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绝对理念的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地位低于宗教,并终将被宗教及哲学所超越。而在《精神现象学》中,古希腊艺术更曾被黑格尔直接称之为“艺术宗教”,构成了所谓宗教精神从自然宗教向艺术宗教再向天启宗教运动发展的过程。
二
《美学》一书开篇即指出,美学的对象“就是广大的美的领域,说得更精确一点,它的范围就是艺术,或则毋宁说,就是美的艺术”[1](P3)。可见,在黑格尔看来,美就是指美的艺术,或者说就是艺术美。他明确说道,“艺术即绝对理念的表现”,“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1](P87)。当具体的理念显现于适合的具体形象,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妥帖统一,就构成为艺术美或美的艺术,黑格尔称之为“理想”。“理念和它的表现,即它的具体现实,应该配合得彼此完全符合。按照这样理解,理念就是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这种理念就是理想。”[1](P92)有时黑格尔将“艺术美”直接称之为“理想”。
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在黑格尔看来,后者是有缺陷的,不是真正的美。因为艺术美是由人的心灵创造的,是人的心灵的表现;而只有人的心灵才是理念,才是神性的承担者。“从心灵所创造的东西,比从自然所产生和形成的东西,神还能得到更高的光荣。因为不仅人有神性,而且神性在人身上比在自然中所取的活动形式也更高,更符合神的本质。神就是心灵,只有在人身上,神性所由运行的媒介才具有自生自发的有意识的心灵形式。”[1](P37~38)心灵之所以比自然高贵,就是因为心灵的自由自觉性,即心灵能够在思想和实践中认识和反观自身。理念或神是完善、无限的,必定是自由自觉的,所以理念就是心灵。但是,理念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主观的、有限的心灵,而是普遍精神,是“绝对心灵”。“绝对理念……它就是心灵,当然不是有限的受约制受局限的心灵,而是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心灵,这绝对的心灵根据它本身去确定真实之所以为真实。”(着重号为原文所加)[1](P118)在黑格尔哲学中,理念或绝对心灵作为最高的真实,把自身分化为人的有限心灵和自然两个方面,最终又通过心灵的认识与反观达到自身的统一。如前所述,艺术就是这种认识得以实现的一种形式。
艺术美因其心灵性而高于自然美;不仅如此,美的艺术或艺术理想最恰当的题材,最适宜的表现领域也就是人体以及人的心灵本身。美的理想是理念内容与感性形式的统一,就是心灵与其形象存在的具体的妥帖性,而人体则是心灵的自然居所。黑格尔写道:“生命在他的演进中必然要达到人的形象,因为人的形象才是唯一的符合心灵的感性现象。”[1](P98)国外有人注解说:“上帝或宇宙发明了人作为心灵的表现;艺术找到了人,使他的形状适应个别心灵的艺术体现。”[1](P97)因此,以古希腊的人体雕塑为代表的古典型艺术,便成为黑格尔心中艺术理想的典范,而以古埃及建筑为代表的象征型艺术并非真正的艺术。以古希腊史诗、悲剧及中世纪基督教题材的绘画为代表的浪漫型艺术,是艺术理念发展的最高阶段,则直接以人的心灵生活或内心世界为表现对象。“就是这种内心世界组成了浪漫型艺术的内容,所以必须作为这种内心生活,而且通过这种内心生活的显现,才能得到表现。”[1](P101)
不难发现,黑格尔所推崇的理想艺术,主要就是以诸神、英雄、基督及圣徒等等的形象和事迹为题材的,从这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艺术首先要把神性的东西当作它的表现中心”[1](P223)这句话的实际含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神性”,什么是“神性的东西”呢?这些语汇在《美学》一书中频频出现,但其内涵并没有得到作者明确的界定和解说。综合全书来看,“神性”当指种种普遍的精神力量或内化的心灵实体,如智慧、勇敢、忠贞等等;而通过具体的人的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精神意蕴就是“神性的东西”。黑格尔写道:“人类心胸中一般所谓高贵、卓越、完善的品质都不过是心灵的实体——即道德性和神性——在主体(人心)中显现为有威力的东西,而人因此把他的生命活动、意志力、旨趣、情欲等等都只浸润在这有实体性的东西里面,从而在这里面使他的真实的内在需要得到满足。”[1](P226)如果说“神性”更侧重于精神力量的普遍性的话,那么,“神性的东西”则是普遍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无论神性的东西怎样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它在本质上也是具有定性的;它既然不只是一种抽象概念,也就应具有形状可以供人观照。”[1](P224)同时,这种可供人观照的具体形象只能是人而非动物或其他自然事物,因为只有人的形象才能以感性的方式把精神性的东西表现出来,也只有通过人的心灵,神性精神才可以自由自觉地反观自身。这样,“神性的东西,作为诸个别的神”才会走进理想艺术的世界之中,实现那静穆、和悦、严肃、高贵、福慧、自由等等沐浴神恩般的艺术理想。
神性必须借助于人的形象才能够得到艺术的表现,这就在神和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神性和人性统一了起来。黑格尔使用了“情致”一语,来说明神性和人性在艺术中具体的统一。“我们不能说神们有情致。神们只是推动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那种力量的普遍内容(意蕴)。神们本身却处在静穆和不动情的状态……所以我们应该把‘情致’只限用于人的行动,把它了解为存在于人的自我中心而充塞渗透到全部心情的那种基本的理性的内容(意蕴)。”[1](P296)“神们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1](P300)并且,“人不只具有一个神来形成他的情致;人的心胸是广大的,一个真正的人同时具有许多神,许多神只各代表一种力量,而人却把这些力量全部包罗在他的心里。”[1](P301)这样,由爱情、名誉、光荣、英雄气质、友谊、母爱等等构成的艺术情致,或者由种种神性力量所造就的人的丰富的、鲜明的、坚定的性格,就成为理想艺术的适当领域和真正的表现中心。
三
只有以神性及神性的东西为表现中心,艺术理想才会通过各门艺术及其作品展开为一个实现了的美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内容就是美的东西,而真正的美的东西,我们已经见到,就是具有具体形象的心灵性的东西,就是理想,说得确切一点,就是绝对心灵,也就是真实本身。这种为着观照和感受而用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神圣真实的境界就是整个艺术世界的中心,就是独立的自由的神圣的形象,这种形象完全掌握了形式与材料的外在因素,把它们作为显现自己的手段。”[1](P104)一切与真正的艺术理想相异的现象,一切与神性追求相悖的创作观念和实践,都受到了黑格尔毫不客气排斥和批评。他尤其反对在艺术表现中以如下三种因素为中心:
首先是抽象概念。“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因此黑格尔强调理念与其感性形式的统一,反对按照抽象的观念和理论进行艺术创造。他说:“美本身应该理解为一种确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1](P135)“概念不容许在美的领域里的外在存在独立地服从外在存在所特有的规律,而是要由它自己确定它所赖以显现的组织和形状。正是概念在它的客观存在里与它本身的这种协调一致才形成美的本质。”[1](P143)黑格尔深刻理解和把握到了艺术的具体性、形象性特征,进而强调艺术想象的重要性。“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种活动具有心灵性的内容(意蕴),但是却把这种内容放在感性形式里,因为这种内容(意蕴)只有放在感性形式里,才可以被人认识。”[1](P50)总之,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应该只是以它的普遍性出现,不应该作为抽象的议论、枯燥的感想、普泛的教条直接明说出来,而是必须化成个别的感性的东西,间接地暗寓于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当然,如上所述,最适宜的具体形象还是浑身灌注有神性精神的人的形象。
其次是有限现实。“有限现实”指客观自在的自然界以及枯燥乏味的人类现实社会。黑格尔认为只有理念才是世界最高的真实,有限现实不过是理念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异化的、特殊的、外在的存在形式。自然界没有自为的意识,不能认识和反观自身;现实社会中的成员和团体则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必须服从各种法律规范,所以是有限的,不自由的。与神性精神相疏离、相对立的单纯有限现实绝不能够作为艺术表现中心,进入美的领域。黑格尔不但贬低自然美,更加反对把模仿自然作为艺术的目的。在他看来,这种模仿是多余的、费力的,总是要落在自然的后面,“它实际给人的就不是真实生活的情况而是生活的冒充。”[1](P53)更重要的是,以模仿为目的,让人仅仅专注于艺术形式,却忽略了更为关键的美的神性对象和精神内容。同时,理想的艺术应以过去的、属于记忆范围之内的神话时代为社会背景,应以自由的神和英雄的性格为中心,而不是着力表现现实人物受到局限的凡俗人生。
最后是有限心灵。作为理念精神自身异化的另一种形式,有限心灵同有限现实相对应,不同于普遍无限的“绝对心灵”。它是现实社会中人的个体的、主观的心灵世界,往往受制于一时的感受、负面的情绪和无羁的欲望,不能自由地反观自身,所以同样是易逝的、狭隘的、混乱的、有局限的。心灵只有认识到它的有限性,实现对自身的否定,才能达到无限和普遍的绝对心灵,即神性精神。黑格尔不赞同把艺术的目的视为“激发情绪”,因为“依这样看,艺术拿来感动心灵的东西就可有好有坏,既可以强化心灵,把人引到高尚的方向,也可以弱化心灵,把人引到最淫荡最自私的情欲”。[1](P58)所以黑格尔把“情致”和“情欲”相区分,情致是由神进入人的心灵形成的,富于较高尚较普遍的意义,而情欲则带有低劣的、私心的意味。理想艺术的表现中心只能是前者而非后者。同样,黑格尔要求主人公的性格应该是自主的、坚定的、正义的,体现出普遍的神性力量,而不能被写成为被动的、软弱的和邪恶的。
总之,通过人的具体形象去表现普遍的神性精神是黑格尔心目中最高的艺术理想,诸神、英雄、圣徒等等这些神性的东西成为理想艺术的表现中心,而古希腊雕塑、史诗、悲剧以及中世纪的宗教绘画与骑士传奇则成为理想艺术的典范。马克思曾经感慨:“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5](P114)看来以神性理想为中心的黑格尔《美学》已经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这深刻地启发我们:伟大的艺术作品,总会以某些方式显现出一种无限性、超越性亦即神性的光辉。神性的失落便意味着艺术的式微。黑格尔断言,希腊艺术的辉煌时代以及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时代都已一去不复返,艺术终将为哲学所取代。但是,今天我们似乎不必过于悲观,因为黑格尔所理解的“神性”未免有些狭隘,表现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以及艺术思想中的题材与文体偏见。我们完全可以把“神性”理解得更加宽泛,文学艺术对于“神性精神”的承担方式也更为多种多样。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因神性的复归而取得的辉煌成就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还是一个值得日后深入探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