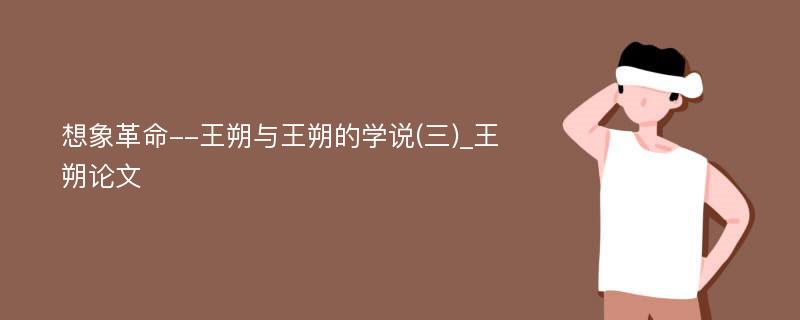
想像的革命——王朔与王朔主义(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之三论文,想像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脏话及其氛围。王朔笔下的主人公有个鲜明特色:说脏话。脏话就是夹带“脏词”的言语。脏词是或明或暗地带有侮辱女性意味或与性器官、性行为、排泄相关的词语。脏话属于粗俗语,其目的通常不在交际而在发泄情绪。而嬉游者经常使用的脏词,主要有“他妈的”、“妈的”、“他妈”、“操”、“混蛋”等。他们说这类脏话,目的并非简单地发泄情绪,而就是在实践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具体讲,他们通过说脏话是要显示一种反叛性生活态度,向传统规范宣战,并由此获取个体的狂欢。这样,脏话成了嬉游者的日常言语行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不过,应当看到,在当代文学中,这一点并不是王朔笔下的嬉游者首先“发明”的。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1984)里,那位充满“诗情”的精英人物“研究生”就免不了要以“狗杂种”、“狗东西”、“妈的”之类脏话诅咒从小抛弃了自己和母亲的罪恶的“父亲”,以致连他的崇拜者“女摄影师”也禁不住责备他“太粗野了”。对他而言,似乎说脏话是宣泄郁积于心的“弑父”冲动的绝好办法。不过,骂归骂,张承志没有因此而走上王朔式调侃道路,他的写作的主干部分还是庄正的叙述与独白。随后到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城市的故事》里,“他妈的”或“他妈”之类“国骂”竟页页不断,被主人公和叙述人分别重复了多达二十余次和三十余次。在《无为在歧路》中,徐星甚至让名叫A的病人(建筑工人)如此说道:“我他妈是个人,可谁也不知道,要是有一天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不就他妈白活了?所以我不干活儿,我一上脚手架就他妈浑身筛糠……”这里竟然每句都带脏话。最极端的例子似乎就数《帮忙》了。小说写小饭馆里两个满嘴“他妈”的粗俗青年秃头和瘦子,外恶内善,见义勇为地巧妙把一位纯情姑娘从伪君子“长发男人”的欺骗下解救出来。在这篇仅11页的小说中,“他妈”这一国骂竟被秃头和瘦子重复说了23次,达到创记录的平均每页2次。就笔者的阅历而言,在说脏话的数量和频率上,徐星的小说都创造了为其他当代作品所难以企及的极端记录,堪称文学中脏话的“超级标本”。由于秃头和瘦子都是正面人物,因此脏话在表现上就代表着作家所倡导的正面价值规范。显然,脏话在徐星成了一种积极的语言。另外,与此同时,陈建功在《鬈毛》里也频频让主人公卢森说脏话(“他娘的”或“他妈的”)。
在脏话方面,王朔很可能接受了徐星的某些启示,或者不如说,徐星的这些早出几年的“超级标本”对这位后来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影响。人们在研究王朔的“脏话”时,是不应忽略这种承续关系的。在王朔这里,单就脏话的数量和频率而论,嬉游者似远远不及上述标本。但问题在于,嬉游者为什么却在我们眼里总显得满嘴脏话而“痞子”气十足呢?问题并不在具体脏话的数量和频率上,而在脏话行为与其整个生活方式的特殊关系上。在《一点正经没有》里,主人公方言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无端被一群大学生强拉去作报告。他在台上大谈“玩文学”,引起台下哄声一片:
“谁他妈关心你们呀!”几条嗓子在喊。
“骂吧,我让你们骂够了。骂人谁不会?我要骂起来比你们可花式多了。有理讲理,不讲理咱们就都不讲理。”
“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绑架我的学生头儿跳上台,对我说,“你走吧,你还是挺真诚的。”
“我他妈当然够真诚了!”我瞪眼,“我要不是真诚我早跟你们谈理想了。”
“操你妈!”一帮男学生挤到台前指着我骂。
“操你们的妈!”我一摔杯子破口大骂,“你们他妈有本事打死我!”
“算啦算啦,别跟他们逗气儿。”一群温和派学生上台劝我,拉着我。
“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
我甩开众人,拂袖而去。
这里,不仅擅长说脏话的嬉游者在台上大骂,而台下大学生竟也敢于与他对骂,共同形成说脏话的总体氛围。对这些把生存当做嬉戏的嬉游者来说,竞相讲脏话、骂人,并不是他们的生存嬉戏中偶尔外加的“剩余精力发泄”或什么即兴表演之类,而就是这种生存嬉戏本身。说脏话以获取狂欢,已深深地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了这种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嬉游者之所以显得特别喜好说脏话而“痞子”气十足,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整个革命化生活方式都离不开说脏话,或者说,说脏话已成为他们的整个革命化生活的集中而鲜明的言语表征。上述两幕说脏话的场景突出表明,嬉游者的说脏话行为是取决于其整个革命化生活方式的特点的: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于自由地反抗一切现成权威,因而就要敢于说脏话。而只有说脏话才表明自己的生活是革命的。所以,说脏话与其整个想像的革命生活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以至成为他们的革命化生活方式的总体氛围和标志性特征。换言之,具体地说脏话属于直接呈现的“小本文”,而要理解这一本文就需触及那并未直接呈现却在深层起着实际支配作用的“大本文”——嬉游者的以说脏话为标志的整个革命化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以全部想像的革命化生活方式来无言地说脏话,正是据以读解嬉游者的说脏话行为的总体语境。
而就王朔与徐星的关系而言,不妨这样说:说脏话在徐星那里还只是“多余人”不时地发泄其生存无奈和不满的出气口,而到王朔的嬉游者这里,已进而发展成为挑战现成社会秩序并由此获取个体狂欢式生存的“开道”方式。
四、王朔主义
从以上对王朔小说的语言和人物特性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渐次来到这样的问题面前:王朔小说靠什么能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生过如此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
1.王朔的社会影响。在回答靠什么能之前,不妨先来看看王朔的社会影响的具体表现。确实,王朔的社会影响是广泛而又巨大的,这不仅在于他的小说在文学界一度销售火爆、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以及他直接参与创作和策划的电影和电视受到亿万观众瞩目,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他在一系列文学、电影和电视作品中虚构的“一点正经没有”的人物形象“顽主”,竟一再受到现实中人们的喜爱和模仿,并迅速摇身一变而成为90年代社会新潮的弄潮儿的集中表征,成为不拘一格地叛逆陈规陋习、改变个人命运、转动历史车轮的一类新生代人物典范。第二,在他的作品中本来属于想像、虚构或虚拟的未来生活事件,甚至是一些荒诞不经的离奇念头,竟然很快轻易地演绎成为现实生活中如潮水般滔滔涌现的新生事件。“三T公司”、“好梦一日游”公司、“人间指南编辑部”等王朔式(妄说式)构想,难道不正是准确地预示了与新公司、新服务、个人新活法等相连的新的社会变革风潮?第三,与上面的进程相伴随,无论是王朔小说、电影和电视,还是王朔的个人媒体作秀,都引发了中国社会公众与专家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论战,涉及语言、美学、哲学、历史、心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媒介学、新闻学等许多方面,可以说引发了一场涵盖文化的各个领域的前沿大讨论。
在当代中国,能够做到上述一方面的文艺界人物本已属罕见,能够以一人之力而一举涵摄全部三方面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按我的个人观察,当今中国大陆两人而已:一是引发了“张艺谋神话”的大名鼎鼎的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二就是令国人如雷贯耳的这位王朔了。张艺谋凭借其从下乡知青到城市成功者、从西北边缘到京城中心、从出奇制胜到成为电影主流、从中国到国际舞台、从高雅文化到大众文化等骄人奇迹,在急切地要完成“走向世界”大业的文化语境催生下,创造了当代中国人的丑小鸭自我实现神话(注:有关张艺谋,见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朔则不同:张艺谋拥有的这些神话资本他几乎都不曾有。
不过,王朔所拥有的恰恰是张艺谋所没有的:无需像张艺谋那样制造令人震惊的丑小鸭奇迹,而是本来就生长在红色中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心脏,从小饱受“红色”革命话语的熏陶。引人注目的是,王朔的文艺出场姿态却对他的上述生存语境构成断裂性或逆反性关系——他的调侃的锋芒所向正是那孕育他的红色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断裂与20世纪80年代位居主流的高雅文化潮流也构成令人惊异的另类话语、有时甚至就成为顶撞的力量。那么,王朔的断裂之举意味着什么?对此的回答正等于进入下面的问题:王朔靠什么能制造如此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
2.王朔主义。可以简单地说,王朔的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的造成,靠的就是一种不得不用王朔主义来概括的东西(注:这个词是王一川在2003年初次提出来的,见《中国电影的后情感时代——〈英雄〉启示录》,《当代电影》2003年第2期。)。所谓王朔主义,是指通过王朔的作品和其他媒介行为呈现出来的以调侃去想像地反叛又缅怀权威、破坏规矩又自我扯平、标举又消解个人主义的精神。属于王朔主义的并非王朔一人,而是可以包括若干相关人物,如刘恒、冯小刚、刘震云、王小波、李晓明、赵宝刚、姜文、夏钢、刘一达等。
王朔主义包含三要素:对于现成权威的反叛与缅怀、京味调侃、个人主义。说得形象点就是,王朔主义大体等于红小兵加京油子再加商人眼光,是这三类要素的混合体。第一,红小兵与现成权威的想像式反叛和缅怀。如前面讨论已指出的那样,像红小兵时代那样在想像中革命,构成王朔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第二,京油子与调侃。王朔在想像中反叛和缅怀“文革”的方式,正是来自京油子的具有时代烙印的调侃。京油子是人们对北京人中能言善辩或油腔滑调者的一种称谓,直言之,这是指那种善于以地道的北京话去圆通地待人接物的人。当王朔试图找到一条“红小兵”式的想像的革命的合适话语时,他所耳濡目染于其中的大院式北京话——调侃就成为他的最恰当的选择了。正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王朔由此创造了“顽主”的调侃式语言、并制造出言语的狂欢及其与行为的狂欢的关联体。而这种成熟的调侃式语言的产生过程的起始,应当上溯到红小兵时代的街头想像或模拟式革命游戏。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最终追寻的是言语的狂欢与行为的狂欢的关联体,因而王朔所代表的是一种破坏规矩(破矩)与自我扯平(扯平)相混合的圆通的人生态度。破矩,代表破坏正统秩序或规矩的反叛力量;扯平,代表个人在心理上实现自我平衡、自我安慰的圆通力量。调侃正体现了这样两种力量的交汇——通过语言调侃去寻求自我平衡,可以简称侃平。侃平就是指运用调侃而实现的自我平衡。正像《顽主》里马青在大街上与中年绅士和铁塔大汉所发生的两组三角关系那样,他在街头无端冲撞行人之举,固然显示了对于正统秩序的破坏力(破矩),但当铁塔大汉看穿把戏而挥拳回应时,他只能选择以调侃把戏去自救——侃平。在这场想像的激烈对决中,顽主最终取胜了,但他的所谓取胜靠的不是实力而就是调侃,即侃平。
第三,商人眼光与个人主义。前面引用过王朔的如下自述:“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了什么好卖。”确实,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少有的不依靠单位或作协支持而单纯以写作为生计的人,他在写作和媒体秀方面的空前成功,靠的正是商人才有的精明和独立性。换言之,商人理念及相应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正是由于没有单位可依靠,适逢中国社会那时(1984年)正发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举国单一的计划经济开始积极培育市场经济的萌芽,王朔才得以开始萌发独立的商人理念和个人主义;也正是靠了这种新兴的商人理念和个人主义的推动,他才可能大胆地反叛当时的主流写作信条而我行我素,例如不守文学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这类规矩而为赚取稿费写作,并且公然借小说人物的宣言和行动明确标举“玩文学”。
如果说,这里的商人眼光指的是在私有财产值得尊重的前提下和在社会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合法赚取利润的理念,那么,个人主义词语本身则要复杂得多,它在这里一般地是指包含初步的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等理念在内的以平等和自由为核心的一套人生观。王朔本人的商业成功以及他笔下的一系列顽主人物的商业成功,大大增添了王朔的商人眼光和个人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艺界、并且通过公众波及全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从王朔主义中当然还可以剖析出若干其他要素来,但必不可少的应是上述三种。红小兵与反叛和缅怀权威、京油子与调侃、商人眼光与个人主义编织成王朔主义这一奇特的混合体。
3.王朔主义的功能。按上面的方式去理解的王朔主义,是不可能具有改天换地的能量的,而只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一种心理催化剂或助推器作用。王朔主义的功能集中表现为,它构成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系统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想像性催化剂或助推器。
王朔主义所针对的社会转型,涉及从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到大众文化、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等领域。正是伴随着王朔作品的畅销和走红、以及王朔的媒介秀的红火,中国社会进入或正在进入大众文化占主流、个人主义上升、市场经济为主体、市民社会具雏形的时代。而王朔主义在此过程中的想像性催化剂或助推器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只要再次提及王朔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形象“顽主”、公司形象“三T公司”、服务形象“好梦一日游”、编辑部形象“人间指南编辑部”等,以及他个人的媒介秀模式等对中国社会的启迪和预示作用就行了。
王朔主义的想像性功能是指,王朔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毕竟不可能是直接地实现的,即不可能具有直接触动历史车轮的力量,而只能是通过影响那些观赏他的作品及媒介秀的公众的心理而间接地实现的。王朔主义携带其特有的情感与理智糅合的力量,化作一种感觉、一团气息或一股氛围深潜入公众的心理世界,转而化合成流注他们机体全身并诱发其行为的动力源。
究其实质,王朔主义的这种想像性功能的生成,还是导源于红小兵时代的想像的革命精神。在想像中从事革命,远比现实的革命来得纯粹、抽象、理想和完美,当然可以纵情驰骋浪漫的革命豪情。但是,当革命者想像的革命转而以不同于原初想像的方式令人惊诧地到来时,也就是当革命果真演化为变形的现实时,这位想像的革命者还会继续充当革命者吗?这只要提及如下事实就够了:王朔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么热烈地搅动起中国的大众文化浪潮,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化弄潮儿。但当这种热潮果真迅猛地席卷全国时,他迅速地转换成陌生人模样,把枪口对准了这股浪潮,怒加声讨,仿佛它与自己完全无关似的(见下文有关王朔与冯小刚关系的分析)。这不是由于王朔患了健忘症,而主要还是由于他内心深处那想像的革命情结在作祟。在想像中革命时,王朔大可以理直气壮;而换到现实中革命时,他八成会掉转枪口,转而以革命本身为革命的对象。这就是翻脸不认人的想像的革命者王朔。
4.王朔主义的二重性。承认王朔主义的功能,并不意味着把它的能量夸大、甚或直到无限。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王朔主义带有既反叛又缅怀“文革”、既破矩又侃平的两面。可以说,王朔主义具有一种二重性:既反叛又守旧、既激进又保守、既自我又无我。《动物凶猛》里一方面承认生活在社会秩序混乱、商品短缺、人力资源错置、纪律废弛的反文化、反法治等环境下,国家、社会和自我的发展都受到严重桎梏:“70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但另一方面却又深深“感激”那个年代:“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这个“我”根据个人亲身体验而产生的上述相互矛盾的感受、或者甚至多少带有某种辩证意味的分析,原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但是,小说叙述人没能超出“我”的个人视野的局限而上升到更宽广的层面去看问题。如果做了这样的上升,他就必定能更加全面地看到,当像“我”那样的少数红小兵在享受并且事后感激那个年代的“空前的解放”时,我们民族的大多数如工农兵、“走资派”、“反动权威”、“孝子贤孙”、下乡知青等却相反挣扎在反常态的甚至非人的贫穷境遇下,生活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不断折腾中。一方面是亲身体验社会的非合理化状况,另一方面是对这种非合理化怀有真诚的感激。在这里可见出“小我”对“大我”的遮蔽:来自“小我”的偏狭视野阻挡了“大我”的宏阔视野,“小我”的生存合理性代替了“大我”的生存的非理性。由于如此,王朔主义显示了固有的二重性:既反叛又缅怀,既激进又保守。
还可以就王朔主义在中国社会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特定功能来考察。如前所述,从行为的狂欢到言语的狂欢,王朔笔下的“顽主”或嬉游者确实显示了反叛政治国家传统的战斗姿态。他们的反叛行为诚然直接地都是为着实现个体“狂欢”的,但确实由此而显露出对于衰落的政治国家传统的消解意义来。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嬉游者是衰落的政治国家传统的掘墓人。那么,进而言之,他们是否称得上生长中的市民社会的成员呢?他们的嬉戏、游荡、做替补者、成立个体“作协”等行为,与过去政治国家体制下的集体化、统一化、平均主义等旧习相比,体现了长期沉睡的个体意识、市民意识的觉醒,确实带有市民社会的某些因素。但是,当这些行为总是与“无赖”或“流氓”方式紧紧相连、并以个体“狂欢”为最高满足时,他们与真正的市民社会境界就相距遥远了。市民社会需要的民主、平等、自主或法治意识等,在他们那里是很难立足的。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政治国家体制的“遗少”,在“文革”时期作为红小兵曾独享一份想像的革命的“阳光”。而当政治国家体制解体、新的市民社会时代来临时,他们必然在这个新社会中难以找到与过去相称的合适位置。但他们毕竟不甘做没落的革命“遗少”,于是,趁此新旧交替良机,就利用自己从“文革”红小兵时代承袭来的想像的革命意识和反叛权威的本领而向社会宣战,以便夺取属于自己的新东西,为自己寻找新的合适位置。这样,他们实际上是以正在被遗弃的想像的革命这一旧方式去叩响新时代之门,这自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也就是说,以属于政治国家体制的想像的革命方式去叩敲市民社会之门,显然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同时,当他们不是以切实的建设行动、而是仅仅以言语的狂欢为最大满足时,他们更多地不过是在为自己营造一种虚幻的想像的革命共同体罢了。
所以,与作为政治国家体制的掘墓人形象相比,嬉游者是无法向人们呈现真正完整而具体的市民社会形象的。不如说,他们体现了往昔政治国家正统的维护者与市民社会的拓荒者之见相重叠的二重形象。他们或许已一只脚跨入市民社会门槛,但另一只脚却还留在它之外,即留在过去的政治国家传统中。相比之下,更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只是他们留在门外而又传入门内的红小兵式的不守规矩的粗野敲门声。
5.冯氏贺岁片——王朔主义的演化、裂变与终结。王朔当然是王朔主义的合法诠释者,但却不是惟一诠释者,因为这个主义的合法诠释者可以由若干人分担。由于如此,当王朔在20世纪末年活动日趋减少、直到最近几年几乎隐居起来时,王朔主义并没有终结,而是悄然发生了演化,并在中国社会中继续扮演其特定角色。进入21世纪,当王朔在媒介江湖的频繁活动和辉煌影响渐趋式微之时,正是他的老朋友冯小刚渐入佳境之日。冯小刚接过王朔主义的大旗,勇敢地冲锋在媒介一线,继续演绎着消失了王朔身影的王朔主义。
冯小刚与王朔之间本来就关系紧密、渊源甚深。他俩除了是哥们儿、合伙人、同道等外,还有不少相似处:同生于1958年,长在北京大院,当过兵。这表明,他们两人对自己的红小兵时代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可谓心意相通。自从两人于1986年首度会面以来,冯小刚跟随或伴随王朔冲锋陷阵,成果累累。不过,两人尽管在《编辑部的故事》里有过成功的编剧合作,又在合股开办“好梦公司”的过程中有过共同奋斗的难忘经历,而且根据王朔小说改编、冯小刚执导的影片《永失我爱》也反响不赖,但毕竟冯小刚多年来总是生活在“朔爷”的影子中,成了王朔主义的不大有名的诠释者之一。即使是多年后,冯小刚自己也还是坦率地承认这一点:“《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个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注: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第105页,第42页。)。其实,直到90年代后期成功拍摄贺岁片《甲方乙方》(1997),冯小刚作为电影导演的独家风格才终于脱颖而出,名扬天下,初显与王朔分道扬镳的姿态;随后至今的《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和《天下无贼》等系列影片,更是组成了独步当今华语影坛的无可替代的“冯氏贺岁片”金字招牌。
尽管这些影片无可否认地已经打上冯小刚个人的鲜明印记,形成了当今中国电影类型片和大众文化的一种具有鲜明本土品格的品牌,但是,从作品体现的审美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看,仍能依稀辨析出王朔主义的气息。堪称冯氏贺岁片的筚路蓝缕之作的《甲方乙方》(1997),其实就改编自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影片当时“为了便于剧本通过”而没有注明王朔小说的原著身份,直到冯小刚6年后的回忆录《我把青春献给你》才“郑重申明”了这种原著与改编的亲缘关系。(注: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第105页,第42页。)冯小刚还不无得意地说:“……王朔实在不忍心看着他们这种人在和平环境里忍气吞声,挥笔写下一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我把它拍成了电影《甲方乙方》。影片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也起到了麻醉有志青年,维护安定团结的作用。”(注: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第105页,第42页。)这部贺岁片的“好梦一日游”框架和主要人和事都来自小说原著,其主要人物仍是由葛优扮演的,这个角色处处透露出王朔笔下的北京大院“顽主”身影。由此,冯小刚的这一作品仍然可以一般地被称为王朔主义制作,确切点说,可以构成王朔主义的一种新的演化形态。在王朔隐退的最初年月里,冯小刚扮演了王朔主义的新的权威诠释者角色,成功地使得本已风雨飘摇的王朔主义在新世纪延续了下来。
然而,冯小刚的演化性角色却扮演得别有用心:实际上,他从王朔主义进入而又很快地从这个主义系统中演化而出,迫使其在新语境中发生了裂变。冯小刚在随即而来的几部贺岁片实践中,不断根据市场经验和公众需求而寻求创新,逐渐地体现了比王朔更独特的优势——比王朔更懂得影视媒介的实际制作技巧与消费市场的公众需求,从而可以不仅以“比王朔更王朔”的姿态去在影视中实现王朔无法充分实现的大众文化表现意图,而且逐渐地摆脱王朔的影子而注入新东西,如市民娱乐因子。这样,冯小刚从王朔主义进入而又穿越了它,抵达一个为王朔主义已无法完全概括的新领域了。
返观王朔,他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型人物:一方面以其文学才能堪称开90年代北京影视制作新风气及大众文化潮的领袖性人物,但另一方面自己又缺少实际的影视制作才能,而只能听凭冯小刚们在领悟了他的原创性策划后,根据新的市场导向而做出比他本人更成功的影视实绩。例如,王朔自己于1992年参与《爱你没商量》编剧,事先吹嘘自己属“码字高手”,“稍不注意就写出一部《红楼梦》”,但实际播映时却遭受公众的剧烈责难,成了王朔自己后来不敢再提的“滑铁卢”。而相比之下,冯小刚、姜文等分别根据他的小说原著改编的电影作品却接连成功。平心而论,王朔在大众文化制作方面实属一种开拓型而非大成型、策划型而非操作型人物。“但开风气不为师”。当众人还不识水性的时候,他以红小兵式的英勇在水流湍急的大众文化小溪里第一个下水搏击风浪并成为冯小刚们的榜样,勇气可嘉,后人之范;然而,当这条小溪迅速扩展成波涛汹涌的大江长河时,这位弄潮儿却已丧失掉继续冲浪的余勇,而只能听凭一股股新浪潮把自己冲刷到岸边,冷眼旁观一江春水向东流。王朔无论如何奋斗,似乎仍走不出红小兵时代的想像的革命的边界。于是,冯小刚既是王朔主义的演化者又是它的裂变者,既是它的末世拯救者又是它的掘墓人。在冯小刚手上,王朔主义似乎起死回生、但同时又在回光返照中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
今天,王朔主义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性任务。在成功地促成中国社会和文化在世纪转折期实现转型后,这件催化剂或助推器必然会自动终结其使命。也就是说,到冯小刚这里,王朔主义实际上已经终结。王朔当然还可能会继续其文学或影视生涯,甚至也可能会重新握笔伸张一息尚存的王朔主义,但却已不大可能让它如幽灵般地在中国大地再度游荡开来了。不过,有趣的是,王朔与冯小刚这师徒兼哥们儿之间的口水仗有些耐人寻味。在冯小刚开心之日而王朔难受之时,愈发不顺、充满愤怒的王朔对娱乐圈与大众文化的态度发生了逆转,激烈地指责说:“现在的大众文化扮演的是一种戏子帮闲的角色”。(注:王朔、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第64页,第12、127页。)在他看来,时下娱乐产业“弄出来的东西中规中矩,一点真东西也没有。圆滑的东西,八面玲珑的东西,极尽媚态非把人往死里俗的东西,全成了好东西。”(注:王朔、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第64页,第12、127页。)更有甚者,他把调侃的锋芒直指刚刚时来运转并春风得意的昔日好友冯小刚身上:“我承认我下流过,但我不承认与冯小刚一样”。不过,他又不忘记显得颇为理解地说:“冯小刚当时就比较可怜,他没有退出来,他就得吃这碗饭。做导演的就是可怜,你要想适应这个社会,有饭吃,弄点儿钱花,那你就要投其所好,搞个贺岁片,票房成功,市场成功,也给咱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添几分喜庆。”(注:王朔、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第64页,第12、127页。)
应当讲,王朔对于大众文化的这种看似突兀的逆转,固然与其在影视制作上的不如意命运有关,但究其实质,还是导源于王朔主义的逻辑内部,即使不是在其时也会在稍后的时候、即便不是以这种方式也会以那种方式表露出来。这就是王朔主义中包含的红小兵式想像的革命情结。面对当年自己亲手点燃、如今已成燎原之势的大众文化火焰,王朔显出了格格不入、感受到了真心的愤怒,内心中原本已深潜的红小兵式反叛冲动复苏了,于是发出了上述激烈的声讨。在当年那位调侃“文革”的王朔与此时调侃冯氏贺岁片的王朔之间,不难见出同一种富于想像的革命精神的红小兵姿态。这位想像的革命者到头来并没有真正跨越他的红小兵时代。当“阳光灿烂的日子”淹没在“没完没了”的贺岁喜剧大潮中时,红小兵身份及其姿态会始终伴随他么?如何在今天这个文化消费时代继续扮演想像的革命者角色?
注释:
(26)[英]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