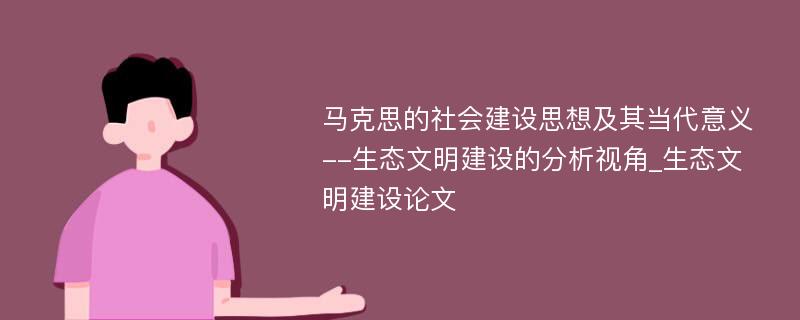
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种生态文明建设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角论文,文明建设论文,当代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如何加强“社会建设”始终是问题的核心。而社会建设的前提之一是深刻理解“社会”的内涵,把握社会理论中人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本质,从而开展关于社会建设的思考、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生成性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必然涉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包括人的本质与自然界的意义问题。
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与人的本质相关联,换句话说,社会的生成与人的本质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他指出:“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马克思,第170页)在此,马克思把人的本质与社会本质、社会联系相勾连,其核心思想是:(1)社会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是人的社会关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出社会的本质。(2)社会也是人的本质生成与展现的一个场域,人自己的活动、生活、享受和财富只能在自己创造和生成的社会中实现。(3)社会的本质是与每个人的活动相联系的,而这里的每个人是现实的生活中的个人,也就是说,社会的本质是每个人本质的展现,是每个人实现其本质的地方。社会也因成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关系的展现而摆脱了抽象,成为一种现实或实在。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社会与人的本质是相互生成的,“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同上,第83页)
其次,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与自然相关联的。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也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但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必须在社会中实践,并在社会中实现,这就是说,个体之人无法与自然界相对应,这样的自然界不属于人的本质属性。“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同上)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是个人从生物人转为社会人的场所。自然界也是在社会中成为人的无机身体,并在社会中得到复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同上,第89页)换言之,自然界的“现实性”就是在它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它被纳入到人的生存和人类历史之中,其中的相互关系首先就是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后来指出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社会的本质与自然界的意义处于相互生成之中。
可见,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人的生存发展相联系,与自然界的意义生成相关联。马克思的这一社会理论包含着当今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对此海德格尔给予了高度赞同。他说:“马克思主张要认识并承认‘合人性的人’。他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在‘社会’里,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说‘自然需要’(食、衣、繁殖、经济生活)的整体都同样地得到保证。”(海德格尔,1996年,第364页)但海德格尔却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误认为与尼采的“权力意志”同命运的形而上学之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连同它的由马克思与尼采所作的倒转一起都归属于存在的真理的历史之中。”(同上,第379页)在此,海德格尔一方面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也过高地估计了他所谓的“存在的真理”。其实,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蕴含着其唯物史观思想的精髓。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第89页)由此可见,社会的生成就是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自然界的生成,是自然界意义的真正的复活。社会不单是现存的既成样态,它更是动态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它需要建设;社会也不纯粹是一个空间概念,不是一个空洞的场所,它是与人的活动以及把自然界纳入人类生活之改造实践密不可分的关系域。这种社会的动态性和历史性特征,表明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视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误解。马克思的社会就是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活动和实践关系,其中主要是生产关系。由人在社会中的活动所构成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同上,第92页)历史与人的本质生成、与自然界的意义生成的这种直接关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所在。据此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上是社会(发展)理论,其实质之一就是展示如何正确处理人、社会、自然界三者在历史视野和现实生存的生产生活中的关系;其中,在社会中如何正确处理人的本质的展现与自然界的复活问题,是马克思社会理论和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诞生”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一思想的当代意义,突出地表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中;换句话说,它包含着如何对待生态文明与科技发展这两个现实问题。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核心
生态文明被认为是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在反思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后,人类共同自发地提出并力图建构的一种新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其核心是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自觉地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业已破坏。然而,何为“自然”?何为“生态”?自然是一个解决生态问题后的复归状态、一个标准,还是使生态问题成为人类必须面对和解决之“问题”的原因所在?
在古希腊文献中,自然一词主要指本质、本源、本性,具有使事物按其内在本性存在的含义。海德格尔对“自然”一词有着专门的考察,他认为,自然“指称着历史性的西方人与存在者的本质性关联,即西方人与他所不是的和他本身所是的那个存在者的本质性关联”。(海德格尔,2000年,第275页)它不是任何火、水、土、光等自然物“元素”。其实,自然的内涵应该是“自然物集合”与“自然物是其所是”这两层含义的综合,即自然物依其所是地本质地生长。
上述关于“自然”的双重含义,使我们对生态形成了一种新认识:生态问题即关于人、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它是人以自然(Physis)为基础,依据自然(Nature)规律,处理人、生物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当我们普遍地使用“自然”概念,并使之与“生态”相关联时,“自然”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作为Physis,自然是一个我们产生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没有对它的破坏和过度开发,生态文明不会成为“问题”而产生;作为Nature,自然又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力图“复归”的标准和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复归Nature,按Nature的内在规定性去实现人类夙愿。因此,贝克指出:“自然本身并非自然:它是一个概念,一项标准,一种记忆,一个乌托邦,一项供选择的计划。”(贝克,第27页)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在于:它不是一种“自然物的集合”的翻版或重现,不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纯粹“看护”或主客对峙上的“静观”,而是人类在自然之本质规律(Nature)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界之统一的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是人类在社会中依据自己的时代性“文明”,而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建设”和“构造”的活动。这个时代性“文明”意指不同时代对文明的不同理解,而文明的时代性也预示着文明具有历史的不确定性风险。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当马克思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种自然界的复活和生成过程置于“社会”活动的视野中时,生态文明建设就应该是社会建设之一种,应该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直接体现。在当前,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所体现出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等种种现代性危机时,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为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当今社会建设之核心要义。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建设?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就是一个人的实践活动问题。而价值实践成为回答该问题的关键。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这一价值实践的具体表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经常与劳动、生产概念相联系,彼此交替使用,相互意指,因此当劳动是人的本质体现时,往往也体现了实践是人的存在本质的含义。在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和当代的汉娜·阿伦特那里,实践与制作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即实践的目的在于自身,制作的目的在于外界的产品(制作品)。甚至在阿伦特那里,这种制作活动具有对自然材料的破坏和暴力,“这种破坏与暴力因素存在于所有制作活动之中,作为人类技能的创造者,技艺者同样也总是大自然的毁坏者。”(阿伦特,第138页)阿伦特对制作的批判其实是对工业社会中人类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在包容了制作、生产和劳动的内涵之后,摆脱了其中漫无目的的特性,成为人的一种根本的生存(存在)方式。在马克思那里,由于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实践必然具有生产性的历史内涵,只有这种生产性实践才能“生产作为人的人”,“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马克思,第58页)。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实践一方面从人的生存论意义上展开,强调了生产是维系人之生存的首要和必需,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的艺术气质与自由追求,说明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的生存依靠,而且是人类发展自身、艺术地生存的“作品”,人类艺术地生存就是自由地发展,就是按“美的规律”来构造世界,也是人类的解放过程。生态文明的“建设”作为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性实践,应该是包含直接的生存性目的和在该目的之上的自由生存和解放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即是说,生态文明建设首先是对人类当下生存危机的反思和对基本生存之需要的建设,同时也包含更高意义上的审美的和自由的实践追求。
当然,这种打上人的“美的规律”烙印的自然界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界了,而是我们说的“生态”,它是人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价值实践的成果。“美的规律”本身包含着不同时期人类的文明精神和文明实践的诉求。可见,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统一建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确切地说是建立在实践得以展开的社会建设的基础上,这种统一在当今的现实表现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内涵。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反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工业社会背景下,自然科学是以工业的方式进入人类的实践和生活的。因此,自然科学成为自然界复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式,科学技术成为实现“美的规律”等价值创造的主要实践方式。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费雷所说:“由于现代科学的影响,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欧洲的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技术转而又使我们世界的大部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我们将之称为现代科学文明。”(见格里芬编,第199页)无论统称为“现代科学文明”是否合理,它所要体现的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关键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科技既是当代“文明”的象征,也是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式。
生态与人类活动相关联,是依据人类历史地理解“文明”而展开的“改造”、“构造”和“建设”等实践活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是体现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统一,是力图体现人类“美的规律”,这也是生态之“文明”的实质。至于文明,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却难以界定的概念,人类在不同时期对文明的具体理解和把握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时期对文明的理解也很难达成一致。但是,无论思想家们对文明持批判还是褒扬态度,我们都可以肯定,近代以来的文明是伴随并借助于科技而发展的。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文明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文明的进程与人的自由发展程度相一致,是人的解放的过程,而这是与科技发展相关联的。
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否真的意味着文明的发展?科技是否推动文明进程的唯一动力?科技的社会功能是直接的,但也是双面的,因此,对于借助科技来推动的社会发展的文明特征,是需要辩证看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双方全面地考察了科技与文明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十分关注科技的社会推动力作用的。当然,在科技的正面而积极的作用普遍被认可的今天,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在马克思的科技思想中,同样具有对科技的辩证批判态度和警惕倾向。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工人成为机器大工业的附庸:“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87页)在此,马克思说明了科学技术及其表现(机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蜕变成一种统治和剥削的方式;原本用以解放工人、实现人之自由价值的科学技术,同样可以成为促使工人异化地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促使工人的异化走向极端。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延续着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异化理论的批判路径而展开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反思。马尔库塞认为,在极权主义笼罩着的后期工业文明,技术被纳入统治者的社会控制之中,“文明不得不抵御自由世界的幽灵。如果社会不能用它日益提高的生产来减少压抑,那么生产就必然会与个体相对抗;它本身成了一种普遍的控制工具。”(马尔库塞,第65-66页)这说明,如果社会出现异化,则人与自然的生产关系就会使生产成为控制人的工具,从而造成科技与人相对抗的局面。因此,科技进步并非文明的直接发展,并非人的自由度的自然扩大;科技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其本身不等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变革和革命。
除了在理论上对科技与文明之关系的批判和反思外,我们也可以从现实的实例中进一步探讨这一关系。在上个世纪60年代,印度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研究机构引进了美国农学家培育出的“高产”小麦和水稻,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机械化灌溉技术等新的农业形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迅速实现了粮食自足,甚至成为粮食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在墨西哥培育出高产小麦的美国植物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还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30年后,严重的后果出现了:土地板结,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作物物种日趋单一,农田周边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传统农作物与本地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昆虫、鸟、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坏。此案例表明,曾被标识为先进农业技术的“绿色革命”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技事件,就科技进程而言确实是进步的,表现为粮食产量的增长,局部解决了印度、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类生存问题,一时成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象征;但随着土地和环境问题的暴露,30年后它却成了反文明的例证。在科技史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说明:科技是人类文明的推动力量,但也是不文明的制造者。文明在根本上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种对世界的根本理解和对人在世界中之存在方式的根本看法。
生态文明重在建设,其建设的重要手段是科技实践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有风险的,因为它面对着未知领域,在创造着不确定性。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世界”的活动,其本质特性就是价值活动和价值创造,是去构造一个新的价值领地。这种面对未知领域的活动就是一种探索和创新。科技的风险性是以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当今风险社会理论家所关注的焦点,他们的核心概念之一“技术风险”说明,当今风险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我们自己创造的技术,即它是人为的风险。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我们可以为之贴上“绿色”等种种标签,带上“高新技术”等种种花冠,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多数人却始终无法消除心中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因此,我们必然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保证当今正在建设的生态文明不至于事与愿违地导致另一种不文明,陷入与生态危机相似或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危机?我们的技术建构和技术创新是否在制造着新的技术风险,或者,在技术地解决生态危机时是否带来了新型风险的技术升级?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这句话具有双层含义:其表层是说,人类利用技术手段来无度地征服自然环境是要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的;其深层则是说,初次胜利并非真正的胜利,每一次胜利都可能被后来的胜利所消除。因此,我们应该对技术发展的责任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其核心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责任
人类在拥有科技之时,就拥有了与自然界抗争的权力,就是在扩展自身的自由度。但是,权力和自由的实践过程是与责任相联系的,是履行实践责任的过程。谁拥有权力,谁就拥有责任。责任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但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与职责不同:“职责完全可能存在于一个行为本身之内,而责任指向行为之外,有一个外部关联。”(约纳斯,第54页)换句话说,科学家探索真理、发现真理,这是他的职责;而将该真理运用于社会时,考虑其在社会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这是他的责任。因此,科学家掌握了发现真理的权力,就应该对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则,人类拥有技术的权力有多大?人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技术来改造自然而前行的,这种“改造”我们有时满怀信心地称之为“创新”。但即便我们善意地发展技术,也难免产生技术的风险,造成“恶”的后果,因此,技术改造的权力大小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对自然的改造程度有多大、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能够容忍人类多大程度的改造的问题。这同样是生态文明的建设“度”问题。正如约纳斯所言:“技术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纯粹的范围本身。”(约纳斯,第223页)这指的是技术的涉猎范围和权力的活动范围。人类需要永久地栖居在这块大地上,人类是这块大地的看护者——这就是人类树立责任感和道德实践的根据。但是,人类的这种责任感和道德实践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它必须对技术的后果和自然改造的程度有所意识和警觉,对其风险的可能性保持一种高度的审视和慎重的评价,因为人类在根本上是受制于自然规律的。在技术时代,人类已经不必担心还有什么不能被制造,还有哪些自然领域不能被涉猎而原始地独自存在;人类应该共同考虑的是,在技术权力的推动下,“在可制造的东西的范围内,究竟什么是该被制造的?”(同上,第231页)这是问题的关键。它说明,人类应该知道自己制造的东西的界限,应该明白自己的技术权限。这是人类道德实践的一种自我约束,更是人类道德实践的自我意识和人类责任感的提升。
由于技术进步的专业化和微观化趋势日益显著,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考究的关键对象是科学共同体,因为他们是技术社会的引领者,是技术研发的实践者,同时还是技术进步的鉴定者和评估者。因此,文明建设和规避社会风险的社会责任就集中在科学共同体身上,人类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重建,首先应该聚焦于科学共同体的实践道德体系的重构。
总之,社会建设已成为时代的发展主题,是当今经济社会转型之际所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而就人类的总体性生存而言,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建设必须关注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关注这一建设所依赖的科学技术。技术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固然可以尽其所能地展示人类的自由意志,但也必须警惕“文明”导引下的不确定性风险。技术时代是科学家成为引路人的时代,他们的社会责任必然关乎全人类的生存,也必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标签:生态文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