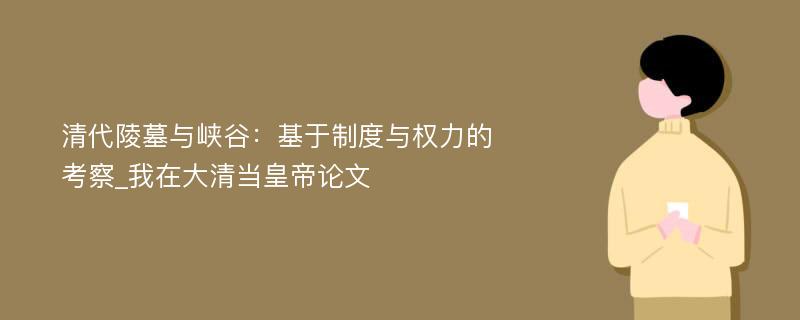
清代陵寝与堪舆:基于制度与权力层面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堪舆论文,陵寝论文,清代论文,层面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11-0105-07
近二十年来,随着民间风水活动的复兴和堪舆研究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对中国传统堪舆给予了关注。其中,陈进国博士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视,其《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以福建堪舆为重点,发掘堪舆的“行规”、“仪式”、“程序”等,对揭示这一事物的内在特质和各种面相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将我们带入到基层社会的场景,体验堪舆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①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②、胡汉生《明代帝陵风水说》③,以明代帝陵为例,描绘堪舆在其中的作用,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关。不少中国台湾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清代堪舆与台湾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上述研究无疑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从国家制度和权力博弈的层面展开讨论,得出堪舆既对国家权力具有依附性,但也具有自身独立性的结论,应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一、大工营建,皆用堪舆
堪舆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国家层面又是一种制度的体现,即礼制。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皇帝刚即位,就颁布了一条对于清代丧葬具有深远意义的诏谕: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所以变通宜民而达其仁孝之心也。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靡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接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奉持,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者,狃于沿习之旧,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之故也。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痛自猛省乎?嗣后如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朕又闻汉人多惑于堪舆之说,购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至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葬埋,以妥幽灵,以尽子职。此厚人伦、美风俗之要务也。钦此。④
这条诏谕同时收入《清高宗实录》和《大清会典》,可以视为规范有清一代丧葬的基本法令。它包含着三层意思:其一,要求所有的满人及归附的蒙古人,除了仍然保持游牧习惯者外,遇父母之丧,均改火葬为土葬。其二,要求所有臣民,无论满汉,按期葬埋,不得停柩延葬。其三,对于汉人之中流行的为了谋求风水坟地而推迟葬期,乃至累年累月、数世不得举葬者,各地官员要进行劝谕。但是,对于堪舆风水并不禁止。此时距清朝定鼎中原已近百年,随着清政权迁入关内的满人已经改变了过去“以师兵为营卫”的生活习惯,成为定居的编户齐民。而关外的满人,也在由游牧逐渐改变为农牧。安土定居成为绝大多数满人和东北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活人生活生产习惯的变化,也影响到死人安葬习惯的变化,由火葬而改为土葬,讲究入土为安。
满人的这个变化,其实也在演绎着几千年前汉人曾经发生过的变化。这个变化被“后世圣人”以“礼”的方式制度化和程序化,并且成为“孝道”的表现方式。用武力征服了汉民族的满族,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正在被汉民族的这个“礼”和“孝道”所征服。所以乾隆皇帝的这条诏谕开宗明义便提出“圣人”的教化,教诲满人和汉人一样,通过棺葬父母而达其“仁孝之心”。
但是,汉族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任何一个习俗都有其相关的附加物,而这个附加物甚至会发展到反客为主的地步。土葬本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不让尸体暴露即可,但此后竟然发展到棺葬,乃至要制作多重棺椁、要建造规模宏大的坟墓乃至陵寝,坟墓、陵寝不仅要构筑精美,而且要有诸多的殉葬品乃至殉葬者。与此同时,又要选择背阴向阳、依山环水、视野开阔、土层厚实且地下水位低、空气流畅并且能形成小气候的棺葬环境。也就是说,凡是活人所需要、所追求的,也要满足死人。因为只有死人得到满足、得到长久,活人才更安定、更有发展的机会。这就需要择地择葬,需要有精通堪舆、谙熟风水之人,相地相墓。
满人既然学习了汉人的棺葬,自然也就同时接受了汉人的堪舆风水。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中央有钦天监的“漏刻科”,有“博士”和“阴阳生”;地方有阴阳学,府设正术,州有典术,县为训术。他们实为官方法定的堪舆家、风水师,职掌是“相阴阳以卜营建”⑤。作为制度和法律,《清会典》载:“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⑥即大工营建,皆用堪舆。此营建既包括一切土木工程,从城池、宫殿、陵寝到贡院、文庙,以及水利、道路、桥梁,等等。
二、陵寝选址,皆用堪舆
清代在“大工营建”中所遵循的堪舆原则,首先即表现在陵寝的择址与规划上。《皇朝文献通考》不无夸张地炫耀:
我朝尊祖敬宗之典,超逸往古,而于山陵大礼,尤为隆备。兴京永陵,敬奉肇祖衣冠之所,而兴祖卜兆正中,景祖、显祖,昭穆序列,天锺福地,允为发祥所自。盛京则福陵在东北、昭陵在西,远拱长白山,近带辽水,郁郁葱葱,佳气所聚。世祖定鼎燕京,预定山陵于遵化州之昌瑞山,是为孝陵,而景陵在其东。重峦叠嶂,四面环抱,用启佑我万年有道之长焉。泰陵在易州之永宁山,脉厚力丰,堪与昌瑞并峙。遵化在京东,故称东陵,易州在京西,故称西陵云。⑦
所谓“佳气所聚”、“脉厚力丰”、“用启佑我万年有道之长”,全为堪舆家的语言。而“兴祖卜兆正中”,说明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汉人的风水已经开始为女真至少是女真的上层社会所接受。但从“景祖”、“显祖”的“梓宫”迁移,仍然可以看出在入主中原之前,女真——满族的丧葬遗风。
清太祖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以为“东京”,并在位于太子河滨的辽阳新城东北四里的杨鲁山营建山陵。天命九年四月,将祖景祖、父显祖之“梓宫”,由兴京赫图阿拉移葬于东京辽阳。⑧
顺治八年,在清代的陵寝规划及修缮上具有重要地位。这年十月,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遍封历代祖先之陵:位于兴京赫图阿拉的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的陵山封为“启运山”,位于东京辽阳的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的陵山封为“积庆山”,位于盛京沈阳的太祖努尔哈赤的陵山福陵山改名为“天柱山”、太宗皇太极的陵山昭陵山改名为“隆业山”。⑨
顺治十五年九月,顺治帝将在辽阳积庆山的“景祖”、“显祖”陵迁回兴京,与“原祖”、“兴祖”陵并称“四祖陵”。次年九月,称“四祖陵”为“永陵”,遣官告祭。⑩
努尔哈赤把景、显二陵从兴京迁往东京,理由是便于祭祀。但是,这个便于祭祀,正反映出当时的满族将祖先骨灰“随身奉持”的遗风。清朝定鼎北京之后,不仅没有将努尔哈赤及皇太极之陵移葬北京,以便祭祀,却将景、显二祖之陵迁回兴京,虽然标榜的是“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即主要考虑的是风水。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看重兴京的表面风水,而是将二祖的回迁看成是稳定清朝根基的风水,正有汉人入土为安、叶落归根的深意。这个变化,恰恰是清朝的入主中原、女真——满人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其间仅三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无论是关外的永陵、福陵、昭陵,还是入关以后的第一陵孝陵,据记载都是钦天监的风水师们选择的陵址。这个事情在康熙四年的一次偶然事件中被揭示出来。
康熙初年,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呈送了自己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摘谬论》,另一篇为《选择议》,都是针对当时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前者指责汤若望制定历法之“十谬”,后者指摘汤若望为荣亲王选择安葬日期之误。“议政王”会议对杨、汤二人进行了鞫问,二人各言己是。由满族贵族组成的“议政王”会议的外行们自然无法判断杨、汤关于历法和堪舆在科学上的是是非非,只好以“历代旧法”为依据,说汤若望等人所进新历只管二百年,而大清江山应该是“历祚无疆”。于是,认定汤若望等人“事犯重大”,均拟极刑: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但是,这一串姓名恰恰是当时清朝官方最著名的天文家和堪舆家,以及他们的“家传绝技”的继承人。而其中的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更是兴京永陵、盛京福陵和昭陵,以及东陵第一陵孝陵的择址人,故得旨:
汤若望系掌印之官,于选择事情,不加详慎,辄尔准行,本当依拟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著免死。杜如预、杨弘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11)
可见,无论关内、关外,清朝最早的一批陵寝,都是由钦天监的堪舆家们察看风水并选定陵址的。《清圣祖实录》又载:“康熙元年正月己丑,礼部等衙门遵旨会议:孝陵兴工动土,应遣武职大臣一员、内院大学士一员,礼部、工部堂官各一员,总管内务府官一员,科、道官各一员,率领钦天监看风水官同往详视。”(12)杜如预、杨弘量应该是这批风水官中的重要人物。
若干年后,乾隆皇帝由于没有留意到康熙初年已经将孝陵风水的堪舆师公布于众,遂在《御制文》中把孝陵风水的堪定说成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
夫此山陵,乃我世祖行狩于田,亲临所相度也。雅颂所称,高山天作,陟巘胥原,盖扶舆清淑之气,锺灵毓粹,用兆丕基,以建万国声灵之极,以贻我子孙奕禩无疆之庥。非若前代陵寝,委之将作、听之堪舆者比。(13)
当然,并不排除顺治皇帝由于“行狩”而对孝陵一带的环境情有独钟,或者是在他的带同下,和堪舆家一样选定。而真正对陵址进行勘测、“点穴”、规划的,自然只能是堪舆家。而据梁份《帝陵图说》,这个孝陵实为明崇祯皇帝曾经选择的“吉壤”:崇祯皇帝继位后,营山陵,因天寿山没有合适的位置,故“有别营通比之议”,只是因为“国家多事”,不仅没有营造山陵,且死无葬身之地。而其所选“吉壤”遂为后来的清东陵。(14)
顺治帝孝陵之后,太宗孝庄文皇后之昭东陵、康熙帝之景陵,雍正帝之泰陵、乾隆帝之裕陵、嘉庆帝之昌陵、道光帝之慕陵、咸丰帝之定陵、同治帝之惠陵、光绪帝之崇陵,以及皇后、嫔妃之墓地,无不由礼部、工部会同钦天监,与精通堪舆风水之人共同选址、规划。礼部主要从礼制上把握,工部负责营建,而选择、测量、规划,大抵是听取钦天监“谙悉地理”之员即风水师的意见。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因“云南底定、海宇荡平”,于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启程,“躬诣”在“兴京”的永陵和在“盛京”的福陵、昭陵告祭。三月初四日,先诣福陵、昭陵行礼,后驻跸盛京。初六、初七,分别往福陵、昭陵祭告。随后往兴京祭告永陵。在三月十三日给太皇太后和太后的呈中说:“臣初九日自盛京启行,十一日诣永陵告祭。环视地形,山回水绕,佳气郁葱,真是兴王基业也。兹因大典已毕,敬想祖宗开疆非易,臣至此甚难,故欲躬率诸王、贝勒、大臣、蒙古等,周行边境,亲加抚绥,兼以畋猎讲武。”(15)
这是清朝定鼎中原后,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第一次往关外祭祀祖陵。同时也揭开了修缮祖陵的序幕,但大规模的修缮,却是在乾隆时期。乾隆元年正月,拜谒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顺治帝的孝陵、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和康熙帝的景陵之余,乾隆下了一道诏谕说:
朕恭谒祖陵,敬瞻殿宇,规模崇整,妥侑攸昭。惟是榱题丹雘,多阅年所,似应重加藻饰,以肃观瞻。但陵寝关系重大,宜详稽典制,敬谨酌议,方可举行。朕思祖宗福祚绵长,万年垂裕,山陵庙貌,灵爽式凭,为子孙者,以时修葺,庶足以展孝思。如典制应行,则追远崇先,谊当均切,永陵、福陵、昭陵殿宇,并应一体修缮。著总理事务王大臣敬谨定议具奏。(16)根据这道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决定选择谙习地理之员缮修祖陵。乾隆帝批准了王大臣会议根据自己的意旨所拟的请求,开始对祖陵进行统一规划、统一修缮。而乾隆帝自己的陵寝,也早已开始选址。乾隆三年二月,议政内大臣兵部尚书果毅公讷亲疏请:“万年吉地事关重大,相度宜先,恭请命通晓风水之员,敬择吉壤。”(17)此后,嘉庆、道光、咸丰诸帝即位之始,也都派遣大臣会同精通堪舆之人,选择“万年吉地”,(18)而这个规矩,也是乾隆时期明确的。咸丰帝不仅在即位不久即面谕定郡王载铨、工部右侍郎彭蕴章、内务府大臣基溥等相度“万年吉地”。并命精通地理之学的江西巡抚陆应谷延访江西绅民中“精晓堪舆者一二人,带同进京”,共同选址。(19)
如果结合前文所说的雍正十三年十月有关禁止火葬、改用棺葬的诏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清朝丧葬制度的改革,始于乾隆即位之初。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改火葬为棺葬,二是陵寝的选址规划均用堪舆。这就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给予早已在民间形成惯例的相宅相墓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陵寝防护,皆用堪舆
选址及修缮用堪舆,陵寝的保护也用堪舆,兹以雍正、乾隆两代对福陵的防护为例进行说明。
福陵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位于盛京沈阳东北的天柱山。努尔哈赤死于“天命”十一年即明熹宗天启六年,火化后,骨灰葬于沈阳城西北角,皇太极继位后,选址葬于沈阳东北的石嘴头山,称“太祖陵”、“先汗陵”。明思宗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金”为“清”,年号“崇德”,定太祖陵号为“福陵”。而所葬之山,也在顺治八年改名为“天柱山”。
署名曾文辿的《青囊序》开篇即云:“先看金龙动不动,次察血脉认来龙。”(20)以这个标准来看福陵,自然是“福壤”。福陵所在的天柱山背靠辉山及兴隆岭,用堪舆的术语,是“后有靠”。而且所“靠”的这个辉山,是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的余脉,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靠”。而在天柱山之南,浑河自东北蜿蜒而来,流向西南,在辽阳西北与经过景祖、显祖陵山“积庆山”的太子河汇合,再向西南而去,在牛庄与辽河汇合,注入渤海。用堪舆的术语,这是“前有泊”,而这个泊又源远流长,源于长白山的余脉、尽于与大海相连的渤海。
清廷对于福陵的风水极其重视,雍正八年三月初三日谕内阁:
向来朕闻福陵前面水法,稍更故道。祇以未得精通地理之人,未敢轻议。上年福建总督高其倬陛见来京,伊素精堪舆之学,特命率同主事管志宁等,前往奉天,敬谨相度。据奏陵前水法,因夏日溢口而流,太近左畔山脚,弓抱之势,微觉外张。应即行修理石工,俾循故道。则水抱沙圆,益增吉庆等语。朕览高其倬等奏摺及所绘图样,甚为明晰。惟是祖陵工程,关系重大。著将奏摺图样,发与满汉文武大臣等,公同阅看。将应否修理之处,敬谨定议奏闻。(21)
雍正帝深于城府,这道“上谕”的缘起已非一日。早在雍正六年十一月,高其倬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就已经说到与“户部主事管志宁”议事。雍正在七年正月的“朱批谕旨”中告诉高其倬:“朕看刘世明若于闽抚一任,犹属妥协,地方无事,意欲召尔同管志宁来京。俟到时再面加训诲。但尚在未定,临期候旨行。”(22)当年四月,高其倬就已经带同管志宁进京,“陛见”雍正帝,专议福陵水法事。也就在同一天,即有吏部左侍郎史贻直署福建总督、代高其倬之命。(23)而史贻直其实在高其倬进京之前已经到了福建,可见雍正帝处事之精细。
雍正帝在八年三月初三给内阁的“上谕”坦率地说,早就知道福陵前面水法出了问题,但由于“未得精通地理之人”,所以没有敢轻举妄动。高其倬为铁岭人,属汉军镶黄旗,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翰林院检讨,后为内阁学士。康熙五十九年为广西巡抚,雍正帝即位后擢云贵总督,雍正三年以兵部尚书衔为闽浙总督。应该说,高其倬的“精通堪舆之学”,雍正帝早有所知,但光有高其倬还不行,他还应该有助手,甚至应该有真正的“操盘手”。而这个“操盘手”应该就是管志宁。
管志宁本为江西瑞金县学生员,因为精通堪舆,于雍正五年特召为“户部主事”。(24)所谓“户部主事”,只是给一个职衔而已,真正的职责,是协助高其倬查勘福陵风水及修缮工程,于雍正七年四月陪同高其倬进京。
经过几个月的查勘,高其倬呈上了治理福陵“水法”的奏折,并且附上工程图样。这个奏折既是一个工程报告,也是一个风水解说:
恭阅福陵形势,其龙与永陵共祖同源,分宗抽干,高山天作,瑞气特钟。发自长岭之西,行于浑河之北,万峰拱照,毓秀钟灵,群水潆洄,流辉裕庆。惟是陵前左畔水法,因夏日溢口流衍,以致稍更故道,弓抱之势,微觉外张。必须顺导河流,方称尽善。(25)
作为精通堪舆之人,高其倬和管志宁的工作是提出方案,而具体的施工并不是他们。雍正帝另外派遣了平郡王福彭,会同盛京五部尚书尚崇廙,以及奉天府尹黎致远、将军那苏图,办理福陵水法的修缮工程。这个工程属“大工营建”,所以“诹吉”事项,也由钦天监承担。(26)
雍正九年十二月,主持福陵水法修缮的平郡王福彭疏报,修理福陵工程告竣,得到雍正帝的嘉奖,但这个嘉奖令的最后,却是有关“风水”:“福陵红门前大路,与宝城甚近,车马俱由山根左畔行走,有关风水。著行文奉天将军、府尹,嗣后于浑河东南西南无关风水之处,设立船厂,以渡行人。红门前大路及山根左畔,严行禁止行走。浑河以北,凡系风水之地,所有草木不许擅动。至迁移房屋,禁止耕种地亩,著赏给房价,补还地亩。”(27)
福陵水法的修缮,严格地说应该是一项水利工程。但在雍正帝的处理中,却是从修复风水开始,以维护风水告终。当然,雍正帝诏谕中所说的“浑河以北,凡系风水之地,所以草木不许擅动”,却无疑对于植被的保护、避免水土的流失起着重要作用。风水与工程,竟然在不经意间得以统一。
但是,仅仅过去四年,就是雍正帝去世、乾隆帝即位不久,署盛京工部侍郎七克新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说是当年六月十三日,山洪暴发,洪水漫过福陵的石堤。因为石堤修筑得坚固,没有受到损害,但石堤前的平地、石堤后的培土都被冲刷。此外,前次工程为了疏导浑河水势所开挖的引河河坝,也有一段被冲塌。
山洪暴发,冲塌部分堤岸,乃至使得河道发生变化,这本来是每年汛期都要遇到的事情。但由于事情发生在福陵,也就被视为严重事件。刚刚即位的乾隆帝立即诏谕:“福陵工程,风水攸关,甚为重大。”派出以多罗淳郡王弘暻为首的京中要员,同样“带善看风水之人,前往相度形势”。只是这一次的“善看风水之人”,却不是管志宁,而是换成了洪文澜。弘暻称其“精于风水”(28)。洪文澜等人提出了和当年高其倬、管志宁类似的整治意见,并加宽了引河,以期“风水工程,两有裨益”。(29)
但这一次的“风水工程,两有裨益”,也只维持了四年,乾隆三年夏天的洪水,不仅冲刷了福陵的土坝,也冲刷了福陵的石堤,乾隆帝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此处石堤土坝,建筑于雍正八年,告成于雍正九年。屈指至今,七八年之间,两次被冲,从前未改筑堤坝之时,亦并无此冲刷之事。此或因水势难容,或系堤工不固?
乾隆帝的这些疑问,与当年即雍正十三年主持查勘的淳郡王弘暻在得知福陵堤坝受到更大洪水的冲刷之后,所提出的看法类似:
臣于雍正十三年奉旨派往沈阳,修理福陵。查浑河与苏子河合流,并汇纳诸山之水,来源远大,上流甚高,势若建瓴。水小则安澜循轨,水大则溢岸冲堤。从前高其倬不谙水性,议于水口建筑石堤,旋经冲刷。嗣据洪文澜议奏,于虎皮石岸前东西加筑石岸,培垫圆唇。今年夏水陡溢,堤坝仍被冲刷,而虎皮石岸前之圆唇,则凝然不动。可见两番修筑之石堤,徒费国帑。若恐弓势外张,则所砌圆唇,水势自已环抱。前奉天将军额尔图所奏一一修理,则今岁甫修,明岁复冲;明岁加工,后岁又决。此断非人力之所能为也。至工程处所,应作如何经久之计,俟臣到沈后,同侍郎张廷瑑,详酌确议,再行奏闻。(30)
当然,提出上述意见的并非淳郡王弘暻本人,而是另有他人。有意思的是,此人正是雍正八年随同高其倬前往辽东的管志宁。此时的管志宁已经升为“礼部员外郎”,经历了两次洪水的冲刷,管志宁显然对自己和洪文澜过去的工作有了反思。在随同淳郡王弘暻至福陵重新相度之后,管志宁确信自己判断的正确,遂提出:福陵乃“旺方水城,当顺其安澜之性”。所以提议将雍正八年所建的部分石堤拆除,·以便于泄洪。这个主张得到“议政大臣”会议的赞同,但人们把雍正八年在福陵筑堤修缮的责任推都给了一年前即乾隆三年病逝的高其倬。(31)
这里其实遗留下来一个谜案,雍正八年高其倬带同管志宁前往福陵查勘,并且提出筑堤防水的方案。这到底是高其倬的主张还是管志宁的主张?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福陵的风水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水利问题。但是,出于对风水的关注,更强化了对于水利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说,风水和水利,在当时其实是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的事情。而所谓的堪舆家、风水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最杰出的一批水利专家。但他们对于水利的思考,却是建立在堪舆的思路、风水的理论之上。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模式。
同样出于对风水的重视,故而从最高统治者的雍正帝、乾隆帝,到主持工程的亲王、郡王,都强调一个基本理念:“未得精通地理之人,未敢轻议”;(32)“非经熟悉风水之员斟酌指定,未可擅动”。(33)其后嘉庆十五年修复乾隆帝裕陵之东山口井座、十七年修补兴京祖先永陵之明堂迤西河岸,也皆以“陵寝重地,未可轻率从事”,“陵前河道,风水攸关,理应倍加慎重”,命钦天监“遴选精晓地理”、“熟诸堪舆”之员,前往相度。(34)
这是对堪舆、风水的敬畏和认同,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陵寝工程选址、规划、设计、施工的科学性。包括堪舆在内的中国古代术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敬畏”和“认同”之下得以传承。
上文所言雍正时期对福陵的防护,严格意义其实是水利问题。对于祖陵,浑河是其水法所在,福陵之“福远祚长”,是因为浑河的源远流长。但正是这条浑河,又在不断改变着福陵左侧即东南一带的地貌。从雍正八年开始,高其倬、管志宁等人持续不断地进行防护工程的建设。虽然是水利工作,但指导思想却是风水,让浑河绵延清朝的国祚,又不对福陵吉地产生危害。这种对于水利的态度,并不产生于清朝,却在清朝表现得极为突出。凡有水利城防,均与风水相关联,故多由堪舆家提出解决方案。
不仅皇陵如此,各地水利工程也如此。乾隆时期以论水利著名的苏州举人沈联芳在其《邦畿水利集说》中,论天津形势:“天津为畿南众水朝宗之所,地势既低,海潮复来荡激,故前人起建七星以镇之。内镇水者五、镇火者一、镇煞者一。实为水口吉星,有关通省风水,非只天津一郡。”(35)京畿之水多汇天津,由海河入海,加之海潮荡激,天津水利形势得到准确的概括。但当时的人们习惯以风水的角度理解,故有“水口吉星”之称,又建七星以镇之,镇水、镇火、镇灾害邪恶。以风水的角度理解,自然得从风水的角度进行治理。其实,当时发生的所有和自然乃至人类相关的事情,大体上都是需要从风水堪舆的立场进行理解。
四、陵寝风水与择址博弈
陵寝既寄托着清代皇室、满族贵族和满汉统治者维系现存政治体制和经济利益的希望,同时也成为皇室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舞台,而支撑这个舞台的,仍然是堪舆。
第一场斗争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这年六月,议政大臣鳌拜等议奏:
兴京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陵,自克取辽东后,迁至东京,原以便展谒、伸祭享也。今据钦天监地理官奏称,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请仍迁景祖、显祖陵于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陵傍,庶与风水有合等语。夫果旺气所钟、福祥攸萃,宜如所请,将各陵界内坟墓、房屋,俱应迁移;被圈地亩,应交户部拨补。
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之陵寝,是在天命九年即公元1624年从兴京赫图阿拉迁至东京辽阳的。顺治八年,将所在山封为“积庆山”。至顺治十三年,这两个祖坟已经迁至辽阳三十多年,如果说入土为安,则早已为安了。所以,早已亲政的顺治皇帝对于鳌拜等人提议,表现出大不以为然,立即予以驳回:
东京二陵,自太祖太宗时择吉恭迁,安奉已久,展谒致祭,孝慕可伸。今以地理之言,又议迁移,恐未合理。况本朝诞膺天眷,国运昌隆,移陵东京之后,肇基一统,垂裕万年,言乎福地,允推至善。至于周围界内臣民坟墓,安集多年,议令改迁,亦属未协。
鳌拜等人迁葬的主要理由是风水,这个风水是由钦天监的堪舆家提出的。顺治皇帝的批驳意见,理由也是风水。而这个风水是清朝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由关外到关内,到统治中国,“国运昌隆”。这个历程说明,迁到东京的祖陵,是肇基一统的根本保证,这个积庆山,无疑就是大清朝的福地。《清世祖实录》对于这场争议的记载仅此一条,以顺治皇帝的决定而结束争议。(36)
但鳌拜等人仍然不依不饶地再次提出了迁陵的主张,并在顺治十五年,将二祖之陵迁回兴京。《皇朝文献通考》载:“十五年九月壬寅,奉移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陵于兴京,罢积庆山祀典。”同时记载了发生变化的原因,“诸大臣等复言陵寝风水所在。今议将东京二祖陵迁祔兴京,于理为协。”年轻的皇帝拗不过固执的议政大臣,被迫同意搬迁。(37)
这一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入关不久的满族上层权力结构的特征。顺治少年即位,先是由摄政王多尔衮理政。多尔衮死后,由议政王大臣集体理政,但鳌拜的强势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鳌拜理政。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顺治也开始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康熙的幼年继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持续。但在康熙八年铲除鳌拜之后,特别是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不断提升皇帝的权威,及至南书房、军机处先后出现,从政体体制上完成了君主专制的权力构成,这一类的事情就难以发生了。康熙皇帝顺从祖母的意愿,将孝庄文皇后的陵寝建在父亲顺治皇帝的孝陵附近,称“昭西陵”,而不是葬在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附近。正是这种权威的建立在陵寝制度上的表现。此后,雍正帝另择西陵、乾隆帝返择东陵,都表现出皇帝的强势。但道光帝陵寝选址的先东后西,在某种意义上却反映出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祖制”之间的博弈。而此时堪舆的作用,也主要是帮助最高统治者愿望的更好实现。
围绕着雍正继位的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传说,被雍正帝的择址西陵进一步强化。雍正七年十二月,皇帝的一道谕旨,令不知内情的大臣们目瞪口呆:
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
此时的雍正帝已经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怡亲王、高其倬早已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前文曾经论及雍正六年至八年之间,雍正帝为福陵的风水维护事项,破格选拔了江西瑞金县生员管志宁,其与高其倬的反复讨论,以及将史贻直事前安置到福建。高其倬一北上,即令史贻直任福建总督。但雍正帝此时给史贻直的“朱批”,揭示了一个前文一直存在的疑点:雍正帝真是为了修复福陵水法而下如此大的功夫?“朱批”相关文字如下:
去岁冬初即闻汝不服闽中水土,深为系念。后阿尔赛到京,备询情形,为之少慰。今览所奏,殊觉不能释然于怀。高其倬素谙堪舆,命其择地,已得上吉之方。因又命往盛京,瞻视三陵,谕其便道审观关外风水,所以稽迟时日,大约四月尽五月初间方可旋闽,卿其勉力支撑此数月可也。(38)
原来,自从雍正五年开始选拔管志宁开始,到雍正七年高其倬往关外治理福陵水法的这段时间里,怡亲王、高其倬及管志宁等人,已经为雍正皇帝选定了易州太平峪“吉地”,并在此后多次确认,只是没有对外公开而已。史贻直在福建的贡献,更主要地是为了能够把精通风水的高其倬置换出来。
皇帝的意志和堪舆的结果达成了高度的统一,内阁、六部及都察院等衙门的会议能够做的事情是为这个决定提供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谨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又泰宁山雄高群巘,抽脉自管涔恒岳而来,襟带百川,分水以拒马滹沱为界。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伏乞钦派大臣,遵照定制,敬谨办理。
这个会议结果,也是雍正帝所预期的,所以当即下旨:“大学士九卿等引据史册典礼陈奏,朕心始安。一应所需工料等项,俱著动用内库银两办理。规模制度,务从俭朴。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不必建设。著该部遵行。”(39)
得到朝廷内阁六部大臣的支持还不够,雍正帝继续做满族八旗贵族的工作。雍正八年十月的“上谕”说:
从前吾弟怡贤亲王为太平峪吉地事宜,殚心竭力,区画经营,曾与高其倬等定为癸山丁向。今年高其倬来京,又复细加相度,观朝案之确情、察砂水之深蕴,应立为壬山丙向。又吾弟怡贤亲王在日,曾有于金圈后面酌留气土之说。今据高其倬等再三计议,若留气上一股,旁镶砖石,与土不能合一,其界缝之间,阳水渗入,转为未协。夫气之所至,金石莫间。阳燧取火,方诸取水,水在盘而外津,薪隔釜而内熟。或由虚而达,或隔物而通,乃其明验。龙吉气旺,无所不彻,无庸又留气土,应循规制建造等语。览高其倬等所奏,于形势理气,计度周详,研求精细,讲论之处,甚为明晰。吾弟当日之经理此事,惟期合理合局,并无成见成心,且逊志虚公,谦怀受益,其生平之令德如此。高其倬等今日之议,既较前议更为加善,吾弟若亲身办理,自必欣然乐从。即今日仙灵闻之,亦必大为喜慰也。着于月祭之时,将此情节告于仙灵知之。特谕。(40)
怡亲王允祥是雍正皇帝同母弟,对雍正帝忠心耿耿,为其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又是选择泰陵的主持人。所以雍正帝需要通过他的声望,来说服满族八旗首领。
从上述的安排可以看出,对于雍正陵寝的选址,在大臣之中,特别是满族贵族之中,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只是因为此时的雍正帝不但彻底粉碎了他在皇位竞争中的对手,而且通过他的铁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且卓有成效,所以将选择陵址问题上的反对意见进行了化解。而给予他最大支持的,则是怡亲王允祥和高其倬、管志宁等人。
虽然有人怀疑雍正帝离弃东陵另辟西陵,是因为在建储的问题对其父康熙帝有所不满,或者说是不甘心委屈于孝陵、景陵之下,但不能排除确实是在东陵未能选到令其满意的陵址。
尽管明朝从成祖开始,帝陵均在昌平,但清朝顺治、康熙的陵址却并没有和太祖、太宗建在一起,而东陵也仅有孝陵和景陵。至少到雍正时期,清代对于皇帝陵墓的选址范围还没有明确的限制。但不管什么理由,雍正帝本人的态度,却决定了这次陵址选择的大方向,那就是不必将陵寝建在一起。在这个大方向下,堪舆家们才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可以相信,内阁六部大臣们给雍正另建西陵所寻找到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依据,高其倬、管志宁等堪舆家们早已为雍正想到过,但只有通过大臣讨论并提出才更加具有说服力。
从此,清朝皇帝的陵寝除了在关外永陵、福陵、昭陵外,北京的东边和西边,分别有了东陵和西陵。
泰陵建成之后,成为清朝在易州开辟西陵的开始。但对于陵址选择问题上的分歧其实还在延续。虽然反对派无法说服乾隆皇帝将其陵寝迁往东陵,却挑出了泰陵设计中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因为人们发现,泰陵与其他帝陵相比,尽管极其宏伟,却没有其他帝陵前的石像生。根据上述《清世祖实录》的记载,因为雍正帝自己说过,石像生所用石料和工时都十分浩繁,本着节俭的原则,所以“不必建设”。但在《清高宗实录》的记载中,却通过高其倬、洪文澜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泰陵前之所以不设石像生,既不是雍正皇帝宣称的需要节俭,也不是体制的问题,比起泰陵的巨大工程,一些石像生所花的钱其实微不足道,而雍正皇帝也不是在体制上不经意的皇帝,真正的原因是风水问题:“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转旋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议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制之未备。”
虽然乾隆帝一再表示陵前石像生“系典礼之一节”,并提出将大红门、龙凤门向外拓展,使地势更加宽敞,则石像生的建立就不存在山势盘旋或甬路转旋的问题,但洪文澜等人经过再次查勘后坚持己见:“大红门正在龙蟠虎踞之间,搪北面随龙生旺之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实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41)尽管此后乾隆帝还是想方设法在泰陵前添置了五对石像生,但从这一段君臣之间的讨论和辩难,可以看出堪舆家们对自己判断的自信和对职业的忠诚。
其实,在陵址问题上的分歧在此后一直持续,所以才有乾隆帝的一道“祖训”。这道祖训决定自己葬在东陵,却把儿子嘉庆皇帝留在西陵。嘉庆二年三月,嘉庆皇帝向已经是“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问安。乾隆皇帝重申:“前经降旨,以嗣后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不必另卜他处。”
乾隆帝的聪明,在于能够因势利导,不仅用承认西陵的既成事实,掩盖他对父亲开辟西陵的不满,而且用昭穆之制,来成全父亲的既定决策。虽然在这道敕谕中严厉斥责堪舆术士,声称“所言最不可信”,但他自己的裕陵的选择和规划,同样是堪舆家在其中发挥作用。笔者将另文讨论。
注释:
①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胡汉生:《明代帝陵风水说》,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④《大清会典则例》卷179《步军统领》。
⑤《清会典》卷86《钦天监》、《清史稿》卷116《职官三·阴阳学》。
⑥《清会典》卷86《钦天监》。
⑦(37)《皇朝文献通考》卷150《王礼考二十六·山陵》。
⑧《清太祖实录》卷9天命九年夏四月甲申。《清史稿》卷1《本纪一·太祖》记:“(天命)九年四月,营山陵于东京城东北阳鲁山,奉景祖、显祖迁葬焉,是曰永陵。”
⑨《清世祖实录》卷61顺治八年十月乙丑。
⑩《清世祖实录》卷128顺治十六年九月辛巳。
(11)《清圣祖实录》卷14康熙四年正月壬寅。
(12)《清圣祖实录》卷7康熙元年正月己丑。
(13)乾隆《御制文》(三集)卷11《碑文·重修葛山隆福寺碑记》。
(14)梁份:《帝陵图说》卷4。
(15)《清圣祖实录》卷101康熙二十一年二月癸巳,三月壬子、甲寅、乙卯、辛酉。
(16)《清高宗实录》卷11乾隆元年正月辛酉。
(17)《清高宗实录》卷63乾隆三年二月壬寅。
(18)《清文宗实录》卷53咸丰二年二月壬午。
(19)《清文宗实录》卷43咸丰元年九月丙辰。
(20)曾文辿:《青囊序》。
(21)《清世宗实录》卷92雍正八年三月辛未。
(22)《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6之9《朱批高其倬奏折》。
(23)《清世宗实录》卷80雍正七年四月己亥。
(24)雍正《江西通志》卷56《选举七·国朝》。
(25)《清世宗实录》卷93雍正八年四月庚戌。
(26)《清世宗实录》卷98雍正八年四月庚戌;卷97雍正八年八月己亥。
(27)《清世宗实录》卷113雍正九年十二月庚戌。
(28)《清高宗实录》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癸巳、卷13乾隆元年二月癸未。
(29)《清高宗实录》卷13乾隆元年二月癸未。
(30)《清高宗实录》卷81乾隆三年十一月丁卯。
(31)《清高宗实录》卷86乾隆四年二月己丑。
(32)《世宗显皇帝上谕内阁》卷92雍正八年三月初三日。
(33)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129《国朝艺文十五·福陵前隄工议乾隆丙辰(庄亲王允禄)》。
(34)《清仁宗实录》卷232嘉庆十五年七月乙巳;卷256嘉庆十七年四月丙寅。
(35)沈联芳:《邦畿水利事宜》,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09《工政十五 直隶水利下》。
(36)《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38)《世宗显皇帝朱批谕旨》卷207上《朱批史贻直奏折》。
(39)《清世宗实录》卷89雍正七年十二月壬寅。
(40)《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8雍正八年十月初三日上谕。
(41)《清高宗实录》卷37乾隆二年二月己亥。
标签:我在大清当皇帝论文; 乾隆嫔妃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清朝陵寝论文; 雍正论文; 努尔哈赤论文; 高其倬论文; 乾隆论文; 风水论文; 钦天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