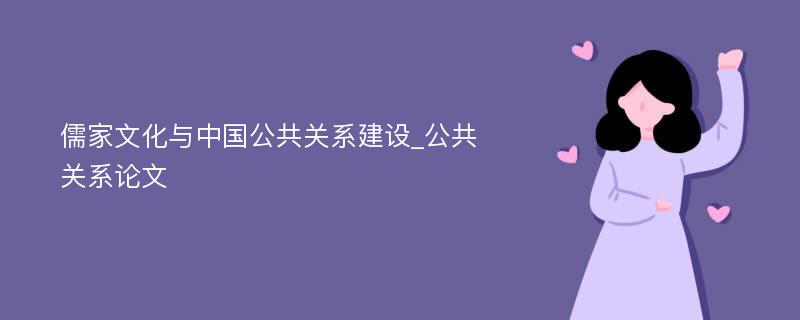
儒家文化与中国公共关系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公共关系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06[文献标识码] A
远东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研究公共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影响”模式在公关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公共关系在中国正向正规职业发展,我们认为,一个良好的哲学基础对中国公共关系职业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把台湾的具体情况作为探讨当代中国公共关系方面问题的样本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作为国际社会认为的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在其民主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正是当今所有中国公关业界人士所面临的问题。台湾的状况不仅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必须应对的问题,也暴露出一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所需适应的问题。第二,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台湾的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具有独特性,颇值得去探讨。
公共关系在台湾的发展沿革
与美国的情形不同,台湾的公共关系首先出现于政府和公共部门,而非私营企业。政府部门的公关实践最早可追溯到50年代。“行政院”于1950年设立了发言人办公室,并于1954年改名为“政府信息办公室”,负责统筹所有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1946年,政府要求所有邮政局设立公共服务部门。1979年,“行政院”所有部门都按政府规定不约而同地设立了指定发言人制度。
台湾的政治体制对公共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废除了长达39年的戒严法。自此,国民党政府当局逐渐从专制统治走向民主。这一政治体制的变化也导致了政府对媒介管制的相应变化。1987年6月以前,媒介仅仅是政府的政治工具和宣传机器。“戒严法”解除之后,相对“自由”的新闻界成为一个所有公共和私人组织都谋求去施加影响的领域。与此相联系,公共关系实践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1992年,公关公司数目已比1987年增加了10倍。
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第一,正如耶姆所述,在东亚的哲学和文化史上,作为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已超过了1,000年的时间。第二,儒家思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从哲学高度指引人们走向完满的一整套世俗宗教、教化系统或人类智慧的教义。第三,儒家思想也是一个视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社会基础的人性哲学。
尽管儒家教化在中国人的行为中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其在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同样应引起注意。当今传播和公共关系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便与儒家思想有关,特别是其双向非对等的世界观。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传统中强调权威、秩序、和谐、忠诚和人际关系的特质,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所存在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的成因,特别是在个人影响模式方面。儒家思想的特点在关系取向、互动方式的准则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1.关系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可概括为“关系取向”或“社会取向”。从本质上讲,东亚国家最显著的特点是对社会关系的重视。班德(BOND)和黄(HWANG)在分析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后得出结论,儒家教化的先决条件是人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他们指出,“中国人对个人社会行为的解释与西方认识个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把人看成是关系物,并在社会的互动情境中适应和被界定。”
因此,黄把这样的一个社会界定为“关系取向”:
“一个人是由他的特殊社会联系所组成的关系网络的中心。在此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人同样拥有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这些重叠和交织的个人关系网构成极端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同样,杨把中国人与社会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取向”。他把“社会取向”定义为:
“一种对社会整饬,非冒犯性策略,服从社会期望和关注外部舆论等行为方式的预先安排,以及期望在社会上达到获得回报,维持融洽,管理印象,保持脸面,社会认可和规避惩罚、不安、冲突、反对、受奚落和报复等一个或多个目标的努力。”
在这种“关系取向”和“社会取向”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中,传统的中国人从关系等级和关系亲密性两个方面来决定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依据与他人在等级性和亲密性上的程度来界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依此决定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就关系等级制度而言,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是按等级构成的,并从根本上遵守一个双向不对等的规则。在中国人的经验里,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概括了所有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儒家思想看来,社会上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可归为五伦中的一个或多个。
对于亲密性的程度,黄以表达性和工具性关联为基础,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达性关联。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表达性关联是家庭或其他亲密群体中成员间的关系。根据黄的理论,在这种联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需求准则:即人们有义务去争取满足每一成员的法定需求所必须的资源。
第二类是混合性关联,概括了个人的家庭成员之外的“关系”的特征。在混合性关联的关系模式中,人们往往与他人拥有一些共同点。例如,人们或许拥有共同的出生地,血统,姓氏;或拥有共同的经历,比如上同一所学校,在一起工作,或同属于一个组织。具体来讲,混合性纽带多发展于亲戚、邻居、同学、同事、师生、老乡之间。黄提到,人们在这一模式中常常运用“人情”和“面子”去扩展自己的人际网络并从资源分配者那里得到想要的资源。第三类是工具性关联。在这一模式中,一个人常常与他人建立临时性的和匿名性的关系,如顾客、销售人员、出租车司机等。在工具性关联中,中国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一般遵循平等原则。黄指出,人们在这一模式中常常把社会交换理论作为自己的处事准则:
“我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多少?为达到目的我要付出多少?当收支相抵后,我的最终收益与对方相比是怎样的?”
2.互动方式的准则。强调融洽和秩序,中庸和双向不对等准则从本质上来讲,儒家教化注重一个融洽的和秩序性的有机体。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持久的社会系统里,人们趋向于保持等级性的秩序和融洽的人际关系。比如,尚(SHUANG)在研究台湾戒严法解除前媒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实际上,媒介往往是为相互冲突的政治派别就某一议题达成妥协、寻得融洽提供一个工具性的论坛。在大多数情况下,媒介往往是尽力促成一致,并建立“一个明显的,有时是象征性的支持政治性权威的一致局面。”
黄在分析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在与周围不同的人打交道时倾向采取多元化的行为标准。他解释道,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打交道时,他或她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怎样?”“我们之间的关系牢靠吗?”对于这一问题,耶姆把儒家思想之下的人际关系的伦理概括为特殊性的、与西方文化下的普遍性的人际关系相对应。他认为,儒家思想对关系和环境所持的伦理是偶然随机性的,而不是一些绝对的标准。同样,苏(HSU)认为这是一个“中庸”的准则。
对于这一特殊性的准则,耶姆考查了四个儒家原则并认为良好的行为来源于此:即仁、义、礼、智。史(SHIH)的“双向不对等准则”为特殊性的关系准则提供了一个更有启发意义的解释。他认为当一个中国人认识到自己是处在一个上下级的关系中时,就会在日常的行为中运用双向不对等的准则。当处在这一关系框架中的时候,上级就会期望下级表现出“忠诚、服从、尊敬和服侍”的行为理念和态度。相反,下级也会期待上级表现出“仁、智、正直和领导典范”的行为理念。根据史(SHIH)的理论,在这一规范的系统中,个体能从中获得安全感。
更进一步来讲,在一个上下级的关系网络中,仁和智是首选的准则。耶姆认为,“仁”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根本上来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仁”体现了“互惠”的理念。在儒家教义中,“仁”意味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史认为,“仁”才是上级对待下级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同时,“智”是下级期待上级应遵循的准则。另一方面,“礼”即“忠诚、遵从、尊敬和服侍”也是上级期待下级应遵循的准则。作为一项社会秩序的客观标准,“礼”被认为是普遍的原则和人类行为最根本的规范。
问题和批判总的来讲,从正面看,儒家思想给人类提供了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人们可以很快地认识现实(与某些其他人的具体关系),并且使自己很容易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然而,从批判的观点来看,在这样一个各派别之间的关系已清楚地界定的社会里,中国人又发明了一种颇具中国文化特色,并且包含消极意义和不符合道德意义和指涉的词汇,即“搞关系”。
“搞关系”是指被压抑的阶层为了显示自身与权贵的联系并解决自身存在的实际的、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而运用的一种活动。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强调融洽和秩序。但是它们建构于一种双向不对等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班德和黄指出,那些产生不融洽的潜在因素应引起特别关注。因为,“五伦”关系中包含了许多的权力不均衡因素。他们进一步指出:
从一个大多数社会资源被少数权势控制的农业社会发展起来的传统中国,建构了一个以“礼”为中心的复杂体制。中国的礼文化要求一个人必须以不同的社会交换标准通过“关系”去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因而,在中国社会,对人际关系的操纵向来是一个人争取所需的社会资源的重要策略。
本质上,黄的“中国社会中的面子和人情模式”有助于去解释个人影响模式和搞关系所赖以发生的社会背景和运作手段。黄认为,为了获得被某一社会资源分配者所控制的资源(如金钱、商品、信息和地位),一个人可以动用多种策略去加大其对社会资源分配者的影响力。学者们指出,在中国最常运用的加强彼此间“关系”的策略就是通过拜访、送礼,或在一些家庭场合如婚礼、葬礼、生日宴会及节日等邀请赴宴的方式,有意加强彼此间的社会互动。在黄的模式中,“关系”、“人情”、“面子”常常是在混合性纽带的关系框架中运用的。当一个人和社会资源分配者不熟悉时,他或她就会“请求一位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中间人把自己介绍给社会资源分配者,进而请求分配者给予好处”,以此“拉关系”或“摘关系”。一旦这一运用“关系”的策略获得成功,人们就说开了“后门”。
全球公共关系理论
詹姆斯·格鲁尼格等六人从1985年开始进行了一项长达10年的国际商业沟通者协会(IABC)的卓越研究项目,他们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300多家企业进行了考察,并对数据资料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从而提出了一套一般性的全球公共关系理论。该理论提出了十条一般性的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卓越”公共关系的原则,换句话说,这些原则应成为有效公共关系的标准因素。
建构当代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
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台湾的公共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基于以上的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应该在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同时,吸收符合自身需要的西方理念。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的框架性建议。
1.引入整体性(HOLISM)理念,把视野由“延伸性的家庭”扩展到“社会”。首先,把人际关系取向从传统的“延伸性的家庭”转变为更具现代意义的“社会”观念,以此削弱双向不对等的关系结构,缩短人们之间的等级界限。具体来说,我们不应把“延伸性的家庭”观念仅仅视为“权位”或“拥有同一姓氏的人”。相反,应考虑到“社会”的观念。在现代社会,把“社会”的观念包含进“延伸性的家庭”有以下考虑。纵向来看,一个组织本质上应对社会负责和忠诚。横向上来看,一个组织应把传统上界定狭窄的“姓氏”观念推及到整个社会。正是基于此,这个建议还包含了全球公共关系理论中所涵盖的相关整体性观念。
2.重视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公众利益。在探讨了“延伸性的家庭”观念的拓展问题之后,引入社会责任和公众利益理念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社会责任已经成为1990年以后台湾企业组织的一个重要理念。亚姆班·罗指出,许多学者已从不同的社会环境出发界定社会责任。这一理念的要义在于“所有的决策、行为和结果都应最大限度地考虑到利益悠关者和社会的事务。”在所有的定义中,唐纳德森的“最低职责”和“最高职责”论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在实践中,公共关系部门应达到组织对社区、员工、顾客等这些利益悠关者所负有的“最低职责”的“底线”标准,并努力进一步实现组织的“最高职责”,即企业的“好公民行为”。
诺尔指出,组织的社会责任能够满足社会需要并促进社会福利。总之,为了让公共关系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倡导公共关系在促使企业成为良好公民方面应成为一支对社会起建设性作用的生力军。
重视公众利益也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本质上讲,当代社会中公关从业人员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既要满足其客户或组织的利益,又要符合总体上的公众利益。正如毕文斯所言,公共关系应拥有明确的职业规范和适当的机制,藉此,公众可就一些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议题展开公开、民主的讨论。
3.加强组织对外的透明度。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种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应清除“搞关系”影响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相反,应把人际关系在中国公共关系流动中的运用看作是一种常规和合乎规范的特征。鉴于“搞关系”往往隐含着一种反面的内涵和影响,在实践中强调“透明度”这一传播伦理的重要作用变得异常关键。恰如毕文斯所说,在传播过程中公开自己的动机(原因)能够确保道德标准得到贯彻。
4.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逐渐发展的“平等”的观念,也应被采纳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挑战。正如尚所说,平等的观念在民间文学中非常广泛,这显示出被压制阶层希望从现实的束缚中寻求自身解放的呼声。平等观念应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公平、权利、公正以及适当的企业与社会活动的收支平衡。亚姆班·罗指出,权利性原则强调对企业所影响的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对企业可能给个人所带来的伤害的预防。
[收稿日期] 2002-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