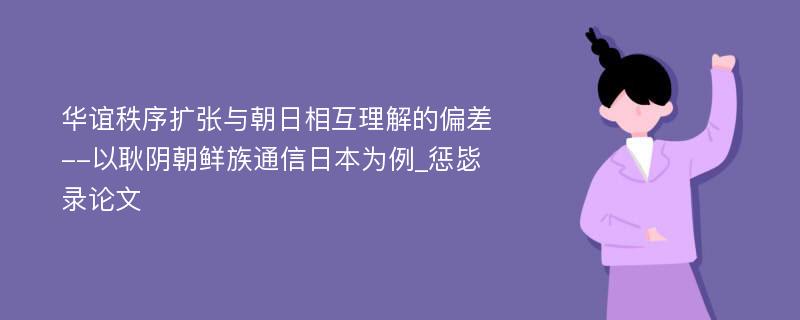
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日本论文,为例论文,偏差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政治关系,中外学者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为共识,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其具体表现。例如,关于东亚诸国向中国派遣朝天使和燕行使的情况研究已多,但对东亚诸国之间相互交往如鲜日通信的考察少见;①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华夷秩序(或言朝贡—册封制度)探讨已深,但缺乏对华夷秩序在周边国家的延伸的关注。具体到朝鲜与日本之间通信使往来,14至19世纪多达一百三十余次,②资料颇为丰富,然相关成果极不相称。③另一问题是,虽有学者注意到在朝日等国存在华夷秩序扩大化的迹象,但对这一迹象缺乏细节上的考察和问题上的分析。④至于把以上两种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则至今尚付阙如。发生在李朝宣祖庚寅年间(1590年,即明朝万历十八年)的鲜日通信活动背景复杂而典型,其间出现的诸多摩擦事件透露出华夷秩序在鲜、日两国的无形扩大及其影响,解读这些细节可以加深对传统东亚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一、庚寅通信始末 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日本使节橘康广到达汉城,通报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及要求朝鲜通使之意。⑤朝鲜不明实情,商议对策,很多人反对。例如,赵宪认为丰臣秀吉弑主自立,接待其使有违道义,主张诛杀来使表明外交立场;李命生认为鲜日邦交已久,接待叛逆使者有违交邻之义,而秀吉遣使刺探情报,居心叵测,主张拘留来使,通报明朝,然后派军讨伐。朝鲜王廷权衡再三,最终决定“但答其书契,而称以水路迷昧,不许送使”⑥。 万历十七年五月,秀吉又令宗义智和玄苏来求信使。这次形势有变,秀吉见朝鲜拒绝交往,决定兴兵犯境。而义智乃对马岛主,其岛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间,年产不过三月之供,主要依赖与朝鲜贸易,一旦中断贸易影响巨大。⑦故而义智冒死劝阻出兵,亲自出使斡旋。而朝鲜亦看重与对马关系,不忍自毁藩篱,同时担心惹恼秀吉,遭其蹂躏。于是,朝鲜这次廷议遣使问题出现分歧。以领议政李山海、礼曹判书柳成龙为首一些大臣开始主张遣使回聘;前参判李山甫依旧反对遣使;户曹判书尹斗寿则主张奏报明廷再说,由此“议久未决”。这时有人重提竹岛之役,认为可以要求日本刷还竹岛叛民,若其诚心照做,再议通信。⑧义智迅即派人回国报请,秀吉遣还叛民及被掳边民,并解释对日军剽掠竹岛并不知情。朝鲜王廷为此隆重庆贺,款待日使,柳成龙亦趁机上书,“启请速定,勿致生衅”。次日朝会,一些官员也建议借机观察日本动向。至此,朝鲜确定对日遣使。⑨ 万历十七年六月,朝鲜王廷任命黄允吉、金诚一为日本通信上、副使,许筬为书状官。次年三月,信使一行启程。四月,由釜山出海;五月,至对马岛;七月,达堺滨的引接寺;同月二十二日,入日本国都;十一月七日,拜见秀吉;万历十九年二月,回至朝鲜复命。⑩在这次交往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朝鲜使臣认为日本“违礼”的事件。归结起来如下: (一)宣慰使事件。宣慰使是负责欢迎和接待入境外国使节的官员,差遣宣慰使是外交礼节之一。对橘康广、宗义智之行,朝鲜均能依礼迎慰。但这次朝鲜使臣在对马岛登岸后,却未见日方来人。朝鲜信使认为日本交邻违礼,展开严正交涉,酿为事件。 当时,副使金诚一责问日方为何宣慰使违约未至,而译官以路途受阻应对。对此,正使黄允吉急于赶路,未打算追究。而金诚一强调事体重要,指出若姑息之,日方会照例因袭,更加怠慢。(11)在其坚持下,“平行长果以宣慰使来,待风一岐岛矣。”(12) 考查该事件记载,文献仅见金诚一与黄允吉往来书信。不过,还有史料亦可佐证两点:其一,事先朝鲜确曾与日方商约接待礼仪,金诚一责问之语不为虚妄。据朝鲜实录载,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三日黄允吉奏报:“臣见客使,问曰:‘我国之不通信于贵国久矣。一则畏风涛之险,一则虑海贼之患。今者我殿下重新王之信义,嘉客使之诚恳,特遣使臣,修百年永废之礼,此盛举也。吾辈到贵国,则国王必有接待之礼,其间节次,可得闻其详耶?……’玄苏答曰:‘弊邦接待之礼,余今难定,到弊邦当告云。’”(13)其二,朝鲜使节却曾在对马岛逗留多时。细查其行程:“(五月)初四日,到对马岛,传命岛主。……六月,发船泊一岐岛。”(14)一岐距对马仅40余里,到对马后信使们首先“登东峰,望一岐岛”。如此短促的距离和明确的登途意向,且无待风等其它必须之事,信使为何要逗留一月之久呢?使团六月出发到一岐岛就又驻留,并因是否主动约请宣慰使见面而发生内部争议。可见这一个月专为等待宣慰使到来。 (二)国分寺事件。在对马岛上,使臣受邀游览名胜。在国分寺,使臣在玄苏安排下入宴中堂。义智后至,竟然坐着轿子径直入场。金诚一认为:“咫尺之地,乃敢偃然乘轿,历阶升堂,睥晲使臣有若臣仆然。虽曰夷狄无礼,亦有君臣上下之分,义智何敢乃尔耶?”(15)。于是与书状官许筬等相继离席,以示抗议。见信使反映强烈,日方被迫道歉示好。先由船主派人传话,说是接待副官年轻失礼,非常后悔;继而告知岛主及都船主等闻知此事,切责副官;最后推说轿夫不听使唤,已经将其逮捕处刑。(16) 关于国分寺事件,《朝野佥载》云:“其在对马岛,平义智(17)请使臣宴山寺中。使臣已在座,义智乘轿入门,至阶方下。金诚一怒曰:‘对马岛乃我国藩臣,使臣奉命至,岂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即起出,许筬等继出。义智归咎于担轿者,杀之,奉其首来谢。自是倭人敬惮诚一,待之加礼,望见下马。”(18)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宗义智竟因一时失礼杀人谢罪,对于对马岛地方而言无疑是严重事件,但《宗氏家记》并无记载。宗氏既要仰仗朝鲜供给,又不敢违抗秀吉命令,不得不尽力周旋,很可能对此类事件有所忌讳,刻意隐瞒。 (三)“礼单”事件。七月至堺滨,“有西海道某州某倭等送礼单,其书曰:朝鲜国使臣来朝云云”。朝鲜信使认为:“倭人以来朝为辞,辱莫大也。辱身且不堪,况辱国乎?”为此拒绝接受礼物,一致抗议。面对强烈抗议,宣慰使和都船主先后派人致歉,解释文书是请人AI写作,而自己不通汉文,以致失误得罪。见其态度诚恳,朝鲜使臣勉强接受了礼物。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同月十一日肥前州官员馈食接待,公文亦写“朝鲜使节来朝”等句。这一次,通事陈世云未与正、副使沟通,私下里敦促日方作了修改。金诚一严厉斥责通事越权:“世云之罪可杖也。书辞如彼,则宜告使臣以听处分;而经草本,径自却之,是世云爲使臣也。”同时强调日方一再犯错,情结严重:“西海之倭,前既失辞,而使臣却之不严,故今又如此,其辱尤大矣。”为此,金诚一拒绝签名回礼,不受倭人酒食。(19) (四)传命事件。为了完成使命,信使一行急于见到秀吉,递交国书。然其七月份即到日本国都,十一月七日才“得以传命”。(20)这一环节耗时五个月之久,引起了信使的不满。金诚一云:“经夏涉秋,尚未致命,圣主宵旰之念,远臣闷迫之情,当何如耶?且古者交邻之义,必敬其使,而不敢忽焉。敬其使,乃所以敬其国也。使者入国,而怠于为礼,淹留旷日,不时接见,则是不有邻国也。此岂以礼为国之道乎?”(21) 于是,朝鲜使臣通过以下三件事情予以应对:第一,拒绝义智请乐。九月份,义智两次向朝鲜使臣“请乐”,希望朝鲜使团所带乐队赴宴助兴。朝鲜使臣强调未传王命不可举乐,并指责日方不重国交,而义智亦颇失礼。(22)第二,拒绝观光安排。十月二十八日,义智派副手通知,次日秀吉出游天宫,使臣可去观光。金诚一婉言谢绝:“异国光华,固愿见也。但王命未传,使臣义难出入也。”次日义智亲请,并恐吓“不从且有悔”。正、副使依然不应,只派书状官前去敷衍。第三,拒绝行贿秀吉左右。由于迟迟无法传命,有日人撺掇行贿秀吉亲信民部卿法印、山口殿玄亮等,金诚一当即反驳:“使臣衔命出疆,虽一于礼而不苟,尚虑失身而辱命,况可行货于左右乎?”其人辩解宾主馈赠属于常理,金诚一则认为“行礼有时”,王命未传无由馈赠。结果,“上使为之屈”,此议遂寝。(23) 关于礼单和传命事件,日本史料亦颇稀见。不过据载李朝英宗四十年甲申(1764)朝鲜士人赵观随信使至日,与日本太学士陶国兴交往,曾得一部秘录。尽管这部日本文献今难看到,但陶国兴与赵观书信及李家焕的题跋尚在,指出日本记载庚寅通信事与朝鲜文献“昭然如合契”(24),可以推测该文献所记述内容及所持观点与金诚一书信能相吻合。与此相应,庚寅通信后朝鲜上下盛赞金诚一“善使”,相关史料随处可摭,可见这些外交事件已广为人知。 (五)“书契”事件。丰臣秀吉回复国书出现问题,导致双方两点争议。 一是接受国书的地点与时间。十一月七日朝鲜使臣得见秀吉,然而并未当即得到日本答书。十一日,日方指令信使返程到堺滨等候答书。金诚一奋力抗辩,认为未受国书不能回返,关白人在都城而令使臣堺滨受书于理不合,令人难以相信。于是坚持留在日本国都,直至得到秀吉国书。(25) 二是国书言辞违礼问题。十九日使臣接到日本国书,但见其措辞悖慢。书称朝鲜国王为“阁下”,带来礼品为“方物”,遣使东行为“入朝”,显然视朝鲜为藩臣;而“一超直入大明国”等语,则张扬侵据整个东亚之野心。(26)金诚一写信与玄苏等辩论,一一剖析日本国书问题所在,表示不改国书决不回国。(27)玄苏辞屈,“许改‘阁下’、‘方物’、‘领纳’六字”,但“‘一超直入大明国’、‘先驱入朝’等语,诿以入朝大明,终不许改”(28)。 书契事件反映鲜、日外交摩擦达到白热化。该事件为两国朝野所重视,且经过亦在川口氏《征韩伟略》中引用《太阁记》、《征伐记》、《秀吉家谱》及五山藏书等日本史料翔实记述,情节亦无二致。(29)至于秀吉前后国书,在日、鲜史籍中多有录存,可以比照;关于国书问题研究,学界认为秀吉犯明意图明显,未见异议。(30) 二、华夷秩序在朝鲜和日本的扩大化 那么,庚寅通信与华夷秩序扩大化有何关系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透视。 (一)庚寅通信的特殊背景和性质 明初,太祖将朝鲜和日本一同列于不征之国,而朝鲜和日本亦向明廷定期朝贡并受其册封,此时二者皆处于以明代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圈内,两国相互遣使通信,属于藩国交往之常规。所谓“‘通信’者,传通讯问也”(31)。故而两国通信各不下60次,明廷并无异言。然而到16世纪中期,朝鲜与明廷关系愈加紧密,日本则退出了这个体制圈,两国往来已属“外交”。从藩国身份来讲,“臣子无外交”,朝鲜再无与日本独立交往的理由。因此,这一时期“朝廷以通信之称为嫌,且以不可奏闻天朝,故议改使号”(32)。朝鲜王廷以改使号等方式继续与日本私自往来,隐藏着其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之潜在目的。 考察朝鲜半岛史,可知该地是受华夷观念和秩序影响最深的地区。早自7世纪起,新罗就开始“以夷易华”之努力;至李朝成宗时期,朝鲜习惯自称“小中华”(33);宣祖时,甚至认为朝鲜“实中国之地,使我国治之”(34)。同时,朝鲜视女真、对马部族为“野人”。日本游离出明朝主导的“册封—朝贡”体制,“自甘为夷狄”,在朝鲜看来就是“化外之国”,不能与自己同等地位。回顾前文,朝鲜同意接待日使,是想到“化外之国,不可责以礼仪”;反对遣使通信,则因为“日本臣逐其君而我受之”,是“侮辱我礼仪之君臣”。其前后姿态无非表现朝鲜已然“礼仪之邦”,身亦“中华”国度,而对马、日本蛮夷也。实际上,朝鲜也的确建立了自己的华夷秩序圈。北之女真,南之对马,历史上确曾向朝鲜进奉方物,并接受朝鲜王廷封赏。琉球与朝鲜有官方往来,竟被其一概视为朝贡。至于日本,自然也在朝鲜华夷秩序圈的经略范围之内。 不过,朝鲜是把自身华夷秩序圈厘定在中国华夷秩序圈内的。总体而言,与中国交往是其外交重点,“事大”是其核心政策。而针对不同层面,朝鲜上对中国王朝行以“事大之礼”,下对女真、对马施以“字小”之仁,中对同为中国藩属的平行国家遵行交邻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朝鲜经营自身秩序圈的活动常会与“事大之礼”产生矛盾,也会受到中国王朝的强大压力。庚寅通信前夕朝鲜王廷的激烈争论和纠结心理,以及很长时期内因诱使朝鲜半岛北部女真等部族进贡而导致朝鲜与明朝之间经常摩擦等现象,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基于此,朝鲜经常把经营自身秩序圈的努力隐藏在内心,或默化为华夷秩序约束下文明的礼仪制度。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朝鲜视日本为蛮夷并欲纳为藩属的心理非常明显,但有时付诸外交却演化为交邻行为。庚寅通信就是这样,朝鲜不但国书强调“以敦邻好”(35),而且使臣也只计较交邻礼仪。 (二)朝鲜遣使的原因和目的 分析前文,当时朝鲜遣使理由有四:一是将日本纳入自己的华夷秩序圈内;二是刷还之事给足了朝鲜王廷面子;三是对马“作我东藩,义则君臣”,而面临战祸,不能不救;四是担忧拒绝遣使会导致丰臣秀吉出兵侵犯。庚寅之行,朝鲜使臣自称“传命”。“传命”何意?传达王命也。朝鲜视日本为藩属,意甚明了。刷还之事,本属朝鲜要挟,而在宗义智周旋下竟然得到日本积极配合。此时在朝鲜看来,似乎日本已经屈服,表明了藩属身份。因而朝鲜王廷倍觉体面,痛快遣使。考虑对马安危,是出自君臣之义,更能表现出朝鲜对自己华夷秩序圈的经营力度。至于担心秀吉出兵,纯粹是朝鲜国防需要。不过,朝鲜毕竟还是大明属国,并非不顾忌明朝态度。朝鲜君臣最初非常纠结。例如,李命生立足于事大之义严厉斥倭,主张拘留其使,上报明廷,众人以为并非善策,然亦担心明廷责难,同时把事大礼仪和本国需求诸多因素都考虑在内,乃至日夜讨论,难以决断。(36)最后,朝鲜还是瞒着明廷向日本派出了通信使,无疑,还是朝鲜自身的诸多利益特别是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华夷秩序圈的需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日本通使朝鲜之动机 日本之所以主动交通朝鲜,就当时形势而言,秀吉政权亟须朝鲜承认以获稳定,而长远看来则有更深意图。据已有研究,早在7至9世纪与唐朝频繁接触时代,日本注意吸收中国文化,受华夷观念影响,私以“中国”自称,而视虾夷、奄美等为夷狄,新罗、渤海等为藩国;同时开始从制度上构造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型华夷秩序圈的尝试。(37)从此以后,在很长时期内日本尽管并无足够能力确立宗主国地位,但其民族优越感和日本中心主义却逐渐膨胀。(38)特别在对朝鲜关系上,形成了朝鲜历来臣属日本的观念。川口氏《征韩伟略》开篇即引《日本书纪》云:“往古朝廷之盛,三韩朝贡。其服也,绥怀抚安;其叛也,征讨声罪。或置日本府其地以统驭,遇之以藩国之礼。”算是这种观念之阐发。到16世纪末期,东亚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明帝国已呈衰落之势,周边民族和国家趁机崛起。这时丰臣秀吉以其枭雄个性催生野心,多年筹划入侵中国大陆,同时致力于控制琉球、中国台湾乃至菲律宾等地,意在取代明帝国的宗主地位。(39)对于朝鲜,假道和占领是其经营规划中必须先行的一步,故而志在必得,毫无顾忌。在庚寅通信过程中,日本迎慰怠慢,奴视信使,胁迫观光,礼单、国书中更是张扬“来朝”、“入朝”、“方物”等字眼,无不透露着视朝鲜为藩属的顽固意识和将其纳入其控制范围的外交企图。 然而,华夷秩序在日本扩大化的态势与朝鲜迥异。由于处于东亚华夷秩序圈边缘,日本吸收华夷观念并不完整,夹杂了以神话传说为基础的神道思想,从而将维持王姓视为“中华”主要标准。在此观念主导下,它鼓吹天皇万世一系和日本中心主义,把自身摆到极高位置,甚而企望突破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来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秩序圈。尽管是在中国华夷观和华夷秩序圈影响下形成的,但日本“华夷秩序”与中、朝不同,实已变质。(40)具体到对外政策,由于很少受到华夷圈体制约束,日本鼓吹交邻原则。不过其所谓交邻政策,往往拿来针对东亚核心国家,企图与中国分庭抗礼。至于对待邻国,交邻则成为一种表面说辞。在庚寅通信活动中,丰臣秀吉将其发挥到极致。他一方面请求朝鲜答聘,另一方面则恣意违礼,非只侮慢朝鲜,甚至张扬侵犯和取代大明之野心。(41) 总之,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奠定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大局,这种观念和机制影响周边国家,导致朝鲜、日本等国形成各自的华夷观及秩序圈。日本学者川岛真认为,华夷秩序是东亚外交所共有的世界观,朝鲜、日本等国也以自身为华,周边为夷,并有着以自己为顶点的华夷秩序,这也许是源于中国的华夷秩序扩大化。(42)例如,将日本华夷观和秩序圈视为一类变种,此论不失为对该问题的一种共识。 三、认识偏差和摩擦事件 我们对朝鲜、日本等国华夷秩序圈的认识不应仅止于此,因为目前学界对其争议尚存。如日本型华夷秩序,不少学者认为在17世纪30年代得以确立,有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43)其实,争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这里存在着现实和观念两种不同层面,而学者各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朝鲜型华夷秩序同样如此,它对于马岛及某些女真部族,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现实意义上的华夷秩序,但对日本、琉球等国则从未建立起真正的朝贡—册封制度。特别在朝鲜与日本之间,尽管双方都视对方为蛮夷,且有将对方纳入自己华夷秩序圈的企图和努力,但在近代以前都未如愿以偿。具体到庚寅通信活动,在两国之间现实存在者仅是各自观念层面的优越感。(44)也正是双方都存在自我优越感,并试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的华夷秩序圈,才导致一系列摩擦事件的发生。 从宣慰使事件说起。朝鲜以礼仪之邦自视,非常重视使节迎慰仪式,“故东平馆接见之日,首及此事,则玄苏答曰,我国当差官迎送云云”(45)。可见朝鲜已经事先提醒,日使也痛快答应。但是当朝鲜信使踏上日本国土时,并无宣慰使踪影。金诚一对此严厉责难,日方才迟迟派人来接。在此处,朝鲜使臣以礼仪文明藐视日本,认为日本已经“违礼”;而日本原本就视朝鲜为藩臣,慢待是其心态初露。 不久,国分寺事件发生。宗义智乘轿登堂,在金诚一看来日方严重“违礼”,即使一般夷狄亦不致如此。日方遭遇抗议时虽委蛇应对,但无法排除其戏弄朝鲜使臣的动机。继而礼单事件迭起。日本地方官员两次书称信使“入朝”,可见以朝鲜为藩国的观念或意图并非秀吉一人所有,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已成共识。 观光、传命和书契事件的接连发生,可以说是两国对彼此政治关系认识偏差在交往碰撞中导致矛盾激化的表现。金诚一在应对行贿事件时曾明确表示:“堂堂大国之使,奉圣主明命,不能宣扬威德,使之稽颡于朝台之下,其屈辱亦已大矣。”(46)可见朝鲜使臣以传命姿态出使日本,极望使得日本俯首归化,经营其华夷秩序圈的意图非常明了。只是倭人冥顽远出意料,以至于金诚一等反应极其强烈。因而在这些事件中,朝鲜使臣拒绝观光秀吉出行,谴责日方拖延时日,最后以死抗议秀吉国书用词。或许有人会说,黄允吉和许筬与金诚一有所不同,似乎对日态度宽宏。然而看其“以为待夷狄之道,不可概以常规”、“夷狄不足与较”(47)等理由,及复命时认定秀吉发兵侵朝的做法,黄等则是因熟知日本蛮夷本性而不屑与争,甚至看透秀吉侵略意图而不抱外交幻想。 至于日本一方,正因其经营自己秩序圈的动机更强,野心亦大,使得其在通信过程中屡屡“违礼”,变本加厉。其欲令信使观光秀吉出行盛仪,从邀请到胁迫,乃至要赴约的书状官“三往乃得见之”(48)。其后故意拖延接见仪式,硬是消磨朝鲜使臣五个月之久。秀吉接见更是自张本心。朝鲜使臣回忆,当时日方“引我使就席,不设宴具……其礼极简,数巡而罢,无拜揖酬酢之节……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儿从内出,徘徊堂中。视之,乃秀吉也……小儿遗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应声走出,授其儿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无人”(49)。至交换国书环节,日方又以“朝鲜国王所赠书不应主公之意,以故不出答书,”(50)。而查朝鲜国书,并无对日本不恭的字眼。相反,日本国书则野心毕露,无所顾忌。 最后,对摩擦事件可以一言概之:日本“违礼”和朝鲜责难同样出于其自我优越感和经营企图影响下的相互认识差异。所不同者是基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和性质不同,朝鲜标榜礼仪之邦,力行文明感化,而日本追求实际效果,不惜野蛮手段。 庚寅通信揭示,古代东亚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大格局之下,存在着由其扩大所致,各以朝鲜、日本为核心的华夷观念和秩序圈。朝鲜与日本由于其各自的优越感和经营企图影响造成了对相互政治关系的认识偏差,导致了信使交往中的摩擦事件。应该指出的是,双方并未在处理摩擦事件中消弭偏差。相反,丰臣秀吉由此决定改行武力,倾其全国军队入侵朝鲜。而朝鲜一方面摇摆迟疑,使日本赢得机会,肆其猖獗;另一方面违制瞒报,造成明廷猜疑,救援迟缓,从而导致其壬辰战争初期几乎覆亡的巨大损失。 如果纵向考察,分析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长期演进的历程。华夷秩序扩大化可以视为传统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某种发展和变异,而其在朝鲜、日本两国的衍生情形则揭示了东亚近代国际关系格局演化的某些线索。近代日本侵略理论的形成与日本长期谋划建立以其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近代日韩关系的演变也受到两国传统交往方式的影响。朝鲜遵循中国华夷秩序理念,对外交往讲究礼制约束;而日本则变异出神道思想,对外强调武力征服。因此,日本吞并朝鲜并非偶然。 注释: ①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指出,中国学界尤其缺乏对日、韩等周边国家历史文献的关注,研究朝鲜赴中国的朝天和燕行使者,首先要与朝鲜赴日本的通信使者进行比较与参照。参见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7-288页。 ②据台湾学者罗丽馨统计,14至16世纪日本遣使朝鲜有60次以上,朝鲜遣使日本则有61次之多。参见罗丽馨《19世纪以前日本人的朝鲜观》,《台大历史学报》第38期,2006年12月,第159-228页;日本学者夫马进统计,1607-1811年朝鲜向日本派出的通信使有12次。参见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③关于通信使研究,国外研究较多,代表性著述有韩国李进熙《李朝的通信使——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朝鲜》(讲谈社1976年版)、辛基秀《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每日新闻1979年版)、李元植《朝鲜通信使研究》(思文阁1997年版)和上田正昭《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明石书店1995年版)、夫马进《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伍跃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等。不过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江户时期朝鲜12次行使活动,讨论核心也局限于“善邻友好”问题。参见王鑫磊《朝鲜时代赴日通信使文献价值的再发现》,《韩国研究论丛》第1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50页。国内则仅见陈文寿《丙子朝鲜通信使与近世日朝通交体制》(《韩国学论文集》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7页)、李永春《简论朝鲜通信使》(《当代韩国》2009年第1期)、徐毅《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罗丽馨《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台大历史学报》第41期)等8篇论文及2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时段亦局限于后期,内容则更有限。已有研究主要是探讨日韩政治友好、文化交流及对彼此习俗、社会的观察,而对两国政治关系的认知及互动的研究则有些不足。 ④川岛真著,田建国译:《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⑤《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十一,宣祖二十年九月丁亥条,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至1963年影印《朝鲜王朝实录》第25册,第570页。关于该次出使活动,对马岛文献《宗氏家记》和柳成龙《惩毖录》系之于1586年(川口长儒《征韩伟略》卷一,吴丰培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70页;柳成龙《惩毖录》卷一,吴丰培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册,第271页),时间与朝鲜针对这次通信请求的廷议活动(1588)相隔太远,且相关事件时序排列亦有矛盾,故不采信。使者橘康广,《宗氏家记》作“柚谷康广”,可能是姓氏汉写不同所致。申炅《再造藩邦志》、赵庆男《乱中杂录》等作“橘康光”、“橘光连”,则显然有误。据考证,橘光连曾以副官身份与橘康广同时出使,橘康光则在康广被杀以后出使朝鲜,并非一人,川口氏认为是康广族人,似较确当。 ⑥《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十一,宣祖二十年九月丁亥条,第25册,第570页。以上赵宪、李命生上疏事可参见赵宪:《重峰先生文集》卷六《请绝倭使疏》第二疏,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0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影印,第548页;官修:《朝鲜宣祖实录》卷二十二,宣祖二十一年一月丁亥条,第21册,442页。 ⑦森克己:《近世对朝走私贸易与对马藩》,《史渊》第45期。 ⑧柳成龙:《惩毖录》卷一,第273页。竹岛即今韩国独岛,位于庆尚道机张郡近海。宣祖二十年三月,日本十六艘兵船以朝鲜叛民为向导剽掠竹岛海面,杀鹿岛万户李大源,掳走不少沿海居民。 ⑨以上事情经过还可参见川口长儒:《征韩伟略》卷一引《宗氏家记》,第476页;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答许书状》,《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901册,第394页;官修:《朝鲜宣祖实录》卷二十三,宣祖二十二年八月乙卯条,第21册,460页;申炅:《再造藩邦志》卷一,朝鲜古书刊行会:《大东野乘》卷三十五,朝鲜古书刊行会1910年版,韩国古典数据库http//db.itke.or.kr/index.jsp,2013年10月11日;柳成龙:《惩毖录》卷一,第273页等。 ⑩《朝鲜宣祖实录》卷二十三,宣祖二十三年三月壬戌条,第21册,第478页;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附录》卷一,《年谱》,第1903册,第172页;川口长儒《征韩伟略》卷一,第479页。 (11)金诚一云:“今也必待宣慰而发程,则彼知大国信使之体,不可无宣慰而苟行也。继今使价之来,必先期迎迓,永为恒规矣。设若利于速行,不待而发,则非惟自处不重,彼将曰宣慰有无使臣不以为关。安知后日指此为故实,遂废而不遣乎?”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答黄上使》,第1901册,第391页。 (12)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附录》卷一,《年谱》,第1903册,第206页。 (13)《朝鲜宣祖实录》卷二十三,宣祖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子条,第21册,第466页。 (14)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附录》卷一,《年谱》,第1903册,第206页。 (15)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答许书状》,第1901册,第395页。 (16)参见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答许书状》,第1901册,第401-402页。 (17)平义智即宗义智。朝鲜最初以为义智属秀吉族系,受命取代对马岛宗氏,故称之平氏。其实义智乃明初对马岛主宗盛长七世孙,仍属宗氏。参见《征韩伟略》卷一,第471页。 (18)许筬:《岳麓先生文集》附录《摭遗》,《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57册,第412页。 (19)“礼单事件”所引文均出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倭人礼单志》,第1902册,第16-22页。 (20)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续集》卷四,《寄潗儿》,第1901册,第391页。 (21)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拟与上副官都船主》,第1901册,第405页。 (22)参见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副官请乐说》,第1902册,第1-3页。 (23)参见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客难说答上使》,第1902册,第4-6页。 (24)李家焕:《锦带诗文抄》卷下,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255册,第458页。 (25)参见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入都出都辨》,第1902册,第7-9页;《鹤峰先生文集附录》卷四,《日本陶国兴与花山士人赵相观书》,第1903册,第381页。 (26)原书云:“日本国关白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薰读,卷舒再三。抑本朝虽为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国纲,废世礼,而不听朝政。余慨然奋激,三四年之间,伐叛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谅予事迹,鄙陋小臣也。虽然,予当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风,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异,敌心自然摧灭,战则无不胜,攻则无不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怜悯独孤,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廷盛事,洛阳壮观,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年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愿无他,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领纳,余在别书,珍重保啬,不宣。天正十八年庚寅仲冬日秀吉奉复书。”参见佚名《续善邻国宝记》,近藤圭编《改定史籍集览》,第21册,近藤出版部1924年版,第35-36页。 (27)《鹤峰先生文集》录金诚一与玄苏、平行长、宗义智、平调信等人书信五封,计五千余言,多论国书问题。参见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第1901册,第446-476页。 (28)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附录》卷一,《年谱》,第1903册,第212页。 (29)《征韩伟略》卷一,第479-482页。 (30)罗丽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5期。 (31)雨森芳洲:《橘窗茶话》上,日本天明六年(1786年)木板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转引自徐毅《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32)洪启禧:《海行总载》第1册,卷首《前后使行备考》,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影印本,1986年,第1页。 (33)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49页。也有学者认为,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将高丽使臣馆舍题为“小中华之馆”始。参见黄修志《高丽使臣“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起源》,《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34)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35)朝鲜国书由柳成龙所草,在《朝鲜征伐记》中留存,书云:“朝鲜国王李昖奉书日本国王殿下:春侯和煦,动静佳胜。远传大王一统六十余州,虽欲速讲信修睦,以敦邻好,恐道路埋晦,使臣行李有淹滞之忧欤,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与贵价,遣黄允吉、金诚一、许筬之三使以致贺辞。自今以往,邻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录在别幅,庶几笑留。余顺序珍啬,不宣。”川口长儒:《征韩伟略》,第485-486页。 (36)《朝鲜宣祖实录》卷二十二,宣祖二十一年一月丁亥,第21册,422页。 (37)罗丽馨:《日本型华夷观——7至9世纪日本的外交和礼仪》,《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5期,2006年6月,第49-114页;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202页。 (38)罗丽馨:《19世纪以前日本人的朝鲜观》,第159-218页。 (39)川口长儒引《朝鲜征伐记》所记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的一段对话,谈及经略朝鲜和明朝的建议,认为秀吉当时已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谋划。参见川口长儒《征韩伟略》卷一,第470页。秀吉野心表现于多处,他在致琉球国书中称:“欲弘教化于异域者,素愿也。”参见川口长儒《征韩伟略》卷一引《外国往来书》,第484页。至于对琉球、台湾、菲律宾等地经营,可以参考罗丽馨的研究成果。 (40)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第55-60页;罗丽馨:《19世纪以前日本人的朝鲜观》,第159-218页。 (41)韩东育论及日本与中国式华夷秩序圈关系时说:“这意味着它将自立规则,也一定要产生出与那个圈子有别的价值观。如果把中国式华夷秩序赖以维系的纽带视为‘礼乐’,那么日本,尤其是武士当权的日本,其价值的最高体现便是‘武威’。”同样说明了日本型华夷秩序及其所谓“交邻”政策之实质。参见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第4期。 (42)川岛真著,田建国译:《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第23-24页。 (43)荒野泰典:《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形成》,《日本社会史》第1卷《列岛内外的交通与国家》,岩波书店1987年版,第217-218页;信夫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10页;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第55-60页;刘雅君:《论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以德川幕府外交为中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90-92页。 (44)朝鲜视日本为蛮夷众所周知。然而罗丽馨认为日本对朝鲜亦有类似优越感,“始于8世纪前后,此种意识持续至18世纪末”。参见罗丽馨《19世纪以前日本人的朝鲜观》,第159页。 (45)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答黄上使》,第1901册,第390页。 (46)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客难说答上使》,第1902册,第5页。 (47)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答许书状》、《答黄上使》,第1901册,第392、403页。黄、许断言秀吉必定侵朝可以参考《惩毖录》、《乱中杂录》及《朝鲜宣祖实录》等文献。 (48)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附录》卷一,《年谱》,第1903册,第210页。 (49)柳成龙:《惩毖》卷一,第278页。川口氏照录该节,可见日人认同,并无避讳。参见川口长儒《征韩伟略》卷一,第479页。 (50)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附录》卷四,《日本陶国兴与花山士人赵相观书》,第1903册,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