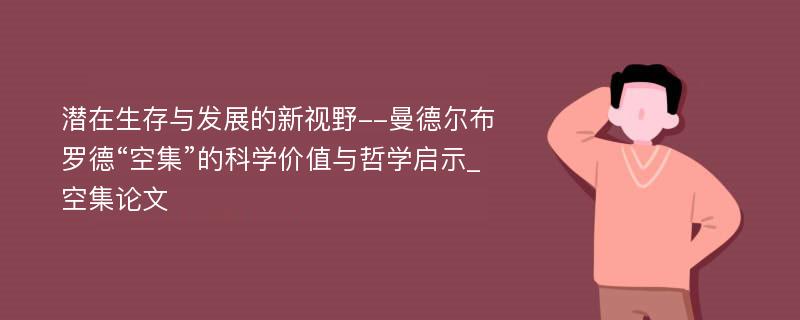
潜在存在与发展的新视野——曼德尔布罗特空集之科学价值与哲学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集论文,在与论文,布罗论文,启示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空隙——生长的活跃区
近年来,当代著名数学家、分形理论的开创者曼德尔布罗特通过对典型的生长模型DLA巨集团即受限扩散凝聚模型的进一步研究, 发现了分形生长更深层的新图景。〔1 〕他指出:生长实际上包括两大集团区域,一个区域是分形已经生成的部分,它不再因生长而进一步改变;另一个区域则是分形生长的空隙区,这是生长过程尚在继续的活动区。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区域像格式塔视觉变换那样交换一下背景与图象,立即就会发现:原来那巨大的空隙区,竟然也是一种分形!显然,对于生长,它比已经生成的部分更重要、更有趣。它是孕育分形生长的生命源泉,一个充满生机、可能性、对未来开放的空间区域。
当科学的视野从部分走向整体、从存在走向演化,大自然逐渐展示出与牛顿力学大异其趣的规律和世界图景,而要想清晰地观察和描述这一新图景,必须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转变。曼氏的突破正在于此:他将生长集团图形的纵向看作生长过程——一个演变着的、“活的”诞生与死亡集,而将其横切面看作瞬时生长切面——一个静止的或“死的”诞生与死亡集。由此可以在横切面上观察粒子生长的瞬时附着距离和尺度行为,并定量描述集团空隙随尺度变化之规律。对生长模型研究的这种新视野,向我们揭示出分形结构极为多样化的起源与生长过程。
本文将曼德尔布罗特的这一最新进展作如下概括:
1.生长集团是内在临界的,即生长结构自身决定了自己的边界条件与尺度,因此生长结构与生长过程具有不可逆的性质,并自然而然地生长成特定的分形结构。
2.为了分析和预测从早期阶段直至大尺度的生长过程,需要考察生长集团的其他定量特征,特别是空隙维性。
3.空隙分析与实体部分的分形图完全吻合,最大空隙行为与空隙效应共同展示出分形的生长规律,譬如DLA 集团漂移至日益紧密的多重分支形状。
4.我们可通过预先测量生长集团整体的空隙,来预计或假设集团生长的动力学行为。
5.以上规律具有普适性。
曼氏指出,为了更好地认识有关生长的复杂过程,给整体(包括实体及其空隙)定义维数并揭示空隙的物理意义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中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以上发现的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它向人们展示出:空隙与正在生长的物体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而对空隙规律的研究与认识则是把握生长的关键之所在。
爱因斯坦曾揭示了空间与物质的不可分性,但即使在广义相对论的视野中,物质仍然是基本的,空间则是派生的、静态的,质量分布决定了时空弯曲的程度;曼氏的发现则说明,在万物生长和演化的过程中,某种生长空间是更基本的:因为物质的生长显然要受到其生存空间的限制和制约,而正是空隙的维数特性决定了物质生长的趋势,预示了现实存在物未来发展的性质、形态和结构。
系统论的整体观,是西方科学从部分走向整体、从分析走向综合的重要标志,但系统论的整体概念仅着眼于系统结构的实体部分;曼氏的整体概念则将实体和空隙看作不可分的整个生长集团。这一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一直未曾被科学“发现”的空隙部分及其作用。“现象非到被观察之时,决非现象。”以往科学的观察坐标都建立在“有”,即物质实体之上,对空隙视而不见,分形生长的巨大空隙区仅仅被看作是物质运动和生长的背景而已,它对科学而言不过是“无”。笔者以为,曼氏对系统生长空隙区和空隙行为的研究成果,不仅证明:恰恰是空隙区,充满了大量的信息,蕴藏着无穷的生机,隐含着转化为“有”的全部可能性,对于生长,它是更基本、更重要的;而且进一步推动着整个科学观察的参照系从“有”到“无”(与有相对的无)、从“实”到“虚”(与实相对的虚)的重大转移。这一突破,大大开阔了科学的视野,使当代科学对整体和演化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空集和负维数——潜在存在的透视与描述
为了定量描述分形的本质特征,曼德尔布罗特曾推广了维数概念,提出了分数维数。他将客体维数与空间经典维数加以区分,以客体维数表示客体存在形式的维数,而以空间经典维数表示客体所存在空间的维数,进而将客体维数扩展为分数维,从而创立分形理论,引发了整个几何学的变革。现在,为了把握空隙的特点和规律,他通过推广交集规则,又进一步扩展了分维概念,结果发现了一个具有负维数的潜在存在的世界。
以往,空集通常作为交集规则的例外,认为无意义而被略去。(注:根据交集规则,若在欧氏空间E中取两个截面S和S,则S和S的交集S有共同维数:E-dim(S)=E-dim(S)+E-dim(S)。当E-dim(S)+E-dim(S)>E时,dim(S)<0,此时交集为空集。 )曼氏的创造性正是在人们认为无意义之处发现了意义,并且给出了定量证明。他指出,空集根据交集成为空的可能性大小,可表示出空的不同程度。譬如:两条线的交集和线与面的交集一般是0维,但若它们不相交, 交集的维数就是负数;而两条线的交集比线与面的交集更空,因为它成为空集的可能性更大。而负的分数维数即负分维,正好作为空集的空的程度的度量,并以此把握空隙的特征及变化规律,预测分形生长的可能性。他指出:负分维是分维的两个分立而对称的部分之一,负分维是潜在的,尽管隐藏着,但绝不可忽视和否认其存在,从而揭示了长期以来为西方科学所忽略的作为客观存在的另一半——潜在的存在,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于客观实在的认识。
笔者认为,世界本来就由隐和显或虚与实两部分组成,它们相互生成、互相契合、缺一不可,正所谓有无相生、虚实相含。正因为虚实相含,才可能有演化、有复杂性,否则世界上就只有简单的正方体、椭圆体等无空隙亦无生命的物质了;正因为有无相生,世界的演化才可能生生不已。分形结构的实体部分与空隙部分是同时诞生、同时生长、又同时消亡的。
由于西方科学的原子论传统是从“有”即物质实体或结构的质料出发,故以物观物,以有观有,见物质而不见“虚空”,见有而不见“无”,在这样的视野中显然不可能认识世界潜在的一面;以往一切物理量几乎都是对于现实存在物及其关系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通常被人们认为毫无意义的负数值,却曾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揭示出物理学未知领域中神秘的潜在世界。
20世纪以来,爱因斯坦首先否定了长期统治人们头脑的那种与物质毫无关系、不可观察的绝对空间。量子力学紧接着对此连连突破,首先是虚数“本质地”进入了量子力学,虚数不是代表实在数量的数字,它在经典力学中可有可无,但在量子力学中却必不可少,因为必须用复的波函数来描写德布罗意波,因此所有的波动方程皆由虚、实两部分组成,它向人们透露了:真实世界本是虚实相含的,而人们也终于发现,不能直接观察的波函数ψ,原来揭示了一种潜在的存在。另一个重大突破是狄拉克对负值能意义的破译,由于他坚持对相对论性电子运动方程的负能解作出物理解释,结果发现了第一个反粒子——正电子,使以往人们认为一无所有的真空显现了“大盈若冲”的“真相”:原来真空是一种负能态被填满的状态,当一个处于负能态的电子得到足够能量跃迁到正能态时,负能态的海洋中就留下一个空穴——它成为一个真实的电子——正电子,原来真空不空,“空空为实”,“真空”乃是一种充满无限之“有”的“空”,一种无休止地以“有无相生”的节奏脉动的“无”。现代场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真空实际上是处于基态的量子场,各种粒子都是真空的激发态,而以往所谓的“有”——粒子和“无”——真空,乃是同一量子场的不同状态,它们都由更深层的“无”——量子场所生成,量子场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还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真空态,而各真空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会导致各种虚粒子的产生、湮灭和转化。正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貌似静止的宏观世界深处,竟是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无”和“有”、“虚”和“实”的相互转化与刹那生灭。〔2〕
当科学揭示真空和空隙都是一种潜在的存在时,人们不禁想到亚里士多德几千年前的名言:“自然厌恶真空”。如果说,量子场论只涉及微观领域,那么,曼德尔布罗特具有负分数维数的空集则跨越一切尺度,从微观、宏观到宇观,而其观察坐标已不是“有”而是“无”,不是“实物”而是“空隙”,不是运动而是生长。参照系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以往无意义的空隙如今已成为富含信息的潜在之存在,一切新生似乎源源从“空”中涌出,由隐而显,由潜在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这正是活泼泼的“无中生有”的创生与发展过程。如果说信息即负熵,那它正是表示一种潜在的转化能力和潜在之可能性。曼氏指出,“潜在”这一模糊概念现在需要也能够被赋予精确和现实的意义了。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客观实在必须包括潜在的存在才是完整的。这才是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关于从还原论到透视论和整体论的最重要的涵义。那么,一切潜在的存在是否都具有负维空间呢?我们有必要对那些至今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无意义而略去的负值解,再次认真重新审视和检测吗?
三、一种新的空间观——生长与演化的空间
时空问题是西方科学的中心问题,也是科学革命的突破口。笔者认为,演化的科学及其自然观应以演化的时间与空间为基础,普里戈金在耗散结构理论中曾提出了演化的时间,即内部时间问题,认为内部时间是系统生成演化的内在尺度。〔3〕令人兴奋的是, 曼德尔布罗特的正负分数维空间,终于给出了可以用科学方法观察和度量的、与内部时间相应的生长与演化的空间。
曼氏指出,对于分形,欧氏测度(如长、宽、高、面积、体积等)尽皆失效,用严格的点、线、面不能观察无限的空间,小点、细支、薄壳也只能观察有限的空间窗口,分维却向我们提供了作为“生成力学”(generating mechanism)的可能窗口(此时整数维便成为特例)。但正分维尚不能穷尽关于生长数据的全部信息,因为它忽略了对象是一个虚实相含之整体的事实。负分维则能描述真正的正在生长的整体,通过对负分维的测度,我们将潜在的或隐藏的存在显示出来,或预演出来。负分维区分了各种不同的空集现象及其发生的原因,给出了更多的有关生成过程的信息,因而为生长模型与测量数据更好的相符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笔者认为,分数维的生长空间与内部时间具有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实际上,任何自然存在的物体,特别是生命体,都有其内部结构空隙和外部生存范围,因此都是分形的。以往我们观察一棵树苗生长时,注意的只是其实体部分,而若将树苗实体的发育与其空隙的变化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立即就会看到一种内部时间节律被翻译成一种空间节律的奇妙生长过程。显然,空间本身是生成演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具有负分维的空隙乃是生命之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普里戈金曾指出:现代科学的发展,“与几何概念的扩展紧密相联”,形态发生学的复杂现象,使“我们看到一个逐渐组织起来的生物空间,每个事件都在某个瞬时和某个区域进行,从而使过程的整体协调成为可能,这种生物空间是具有机能的空间,而不是一个几何空间”;“不可逆性,即空时中所含有的活动性,改变了空时的结构。空时的静态内涵被所谓空间的‘时间选择’这个更为动态的内涵所代替”,这是一种“富含信息的物质非对称空间形态”。〔4〕
艾根在超循环理论中也曾提出了“信息空间”的概念,他认为信息空间应由“群体变量以及其中的功能关系的集合所定义”,并指出:生命“所需的起始阶段的自组织,并不是物理学(例如几何的)空间中的自组织类型”,而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化合物中间的功能序”,“它是在一个有差别的空间中,也就是信息空间”中的空间组织。〔5〕
如今,几何学真的已扩展为对系统生长的动态描述,而不再限于对静物或物质运动的空间位移之度量了,而几何空间也不再只意味着没有生命的物理空间。曼德尔布罗特深刻揭示了被以往静态测量所掩盖的空间维性。分维与负分维的提出,开拓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它所描述的空间正是具有生命特征的生物空间与信息空间,它是不对称的、复杂的、具有生长功能的、内在临界的。这种具有生命性的分维空间或许正可成为对系统之内部时间的测度。
对随机多重分形的研究还证明,正负分维是统一的,互相嵌套、不可分割的。如果说正分维描述了随机分形测量的典型分布,或描述了分形的已经生成的部分,那么负分维所描述的则是分形的尚待生长的部分,它给出的是超样品,即可变样品中可预计的涨落。曼氏指出,随机性是允许广义维数成为负数的关键,正因为负分维空间具有不确定性,它才是富含信息的、允许有“时间选择”的、多样化的。
笔者认为,正负分维的完全吻合恰恰证明物质与空隙是同时产生的,有无相生、即有即无、非有非无,而它们又都由更大更深广的“无”所生成。无空隙、不可入的原子和完全独立的空虚空间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以往的正整数维空间未曾考虑系统的生成和演化,自然不可能考虑生长过程中互相转化的两部分:一部分为“正分维空间”,代表“有”,它是已生长的“显在”或“在场”部分的存在形式,相对稳定;另一部分则为“负分维空间”,代表“无”,是尚未生长的“潜在”或“将出场”而“未出场”部分的存在形式。曼氏的分形理论正是揭示了系统生长的这种空间维性。特别是曼德尔布罗特空集,揭示了相对实体为“无”的空隙才是生长的活跃区、信息源,“空隙”中不断生出新的“有”和“无”,解除着有关生长的不确定性,因而源源不断产生着信息。
现在我们可以说,空间也参与组建着世界。空间本身的存在不应再被简单理解为广袤物体的存在方式了,空间就是存在本身!世界并非现成存在于空间中,因为世界的整体性本身就包涵着空间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并非‘周围世界’摆设在一个事先给定的空间里,而是周围世界特有的世界性质在其意蕴中勾画着位置的当下整体性的因缘联络。”因此,“既非空间在主体之内,亦非世界在空间之内,……那空间倒是在世界‘之中’”。〔6〕
负分维的提出,使科学超越和突破了以往仅限于“以有观有”的眼界,并得以从有无相生、隐显相通的大视野中,把握现实世界整体的“大化流行”,从而向我们展现了更为生动的瞬息万变的演化图景。如今,科学的世界图景一如“复杂性对简单性国际研讨会”的会标,它已由“原子与虚空”转换为颇似太极的混沌——标志着科学从“无”出发,探索万物生成演化更深奥秘的一个新起点。
四、曼氏与老子的相互解读
曼氏的分形理论,不仅是西方数学和科学的重大突破,而且为东西方哲学之对话与交融提供了新的科学启示。
曼氏与老子虽然处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两者的思想却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二者的相互解读,一方面能使老子的思想获得现代意义,另一方面可以为生长演化的科学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与范导。
曼德尔布罗特关于“空集”和“负维数”的思维,曾启发笔者对老子宇宙论重新解读。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7〕并将宇宙创生之过程概括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42)。但老子所说并非指大爆炸后宇宙生成的早期过程,而恰恰是指向科学的言语间断处——大爆炸前宇宙潜在的演化过程。这里,“道”可谓最后的绝对的“无”,而一、二、三相对道而言为“有”,相对万物而言则为“无”,只是“无”的层次不同罢了,它们显示了宇宙“无形质”的隐过程,即潜在的不同演化阶段。直至“三生万物”后,“道法自然”之“体”才“发用”而生成由天地万物所界定的自然界。
我们若从老子《道德经》本体论的高度来解读曼氏现象界的空集,亦可使人茅塞顿开。曼氏探讨的是现实世界万物生长的直接原因,而老子宇宙论追寻的则是生成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尽管老子对经验世界万物生长规律的把握是从形而上之道一以贯之的推衍,是基于对大化流行的“执古御今”式的统摄,但当我们对曼氏生成论作进一步的形而上追问时,则不难看出两者思想的异曲同工之妙:无疑,经验世界万物生长的具体过程遵循曼氏所揭示的分形规律,但老子的思想是否可作为某种质朴性原理或范导呢?《道德经》指出:“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5)天地的空隙处,就好比一个大风箱, 它是充满生机的,一旦发动,便生生不息。说明天地之间的空隙乃是万物生生不已、用之不竭的源泉。而演化的普遍规律“反者道之动”(40),表明任何现实事物的生成都必有一个从隐到显、由虚而实的过程;而事物一旦生成,又不可避免地开始其趋向于“无”的运动。因此“有无相生”(2),有和无互相生成和转化,不可分割,即有即无, 非无非有。而通过曼氏所揭示的生长规律,我们可进一步体会到老子主张“动之徐生”而“不欲盈”(15)的深意,“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15)。正因空隙乃是系统生长的生命之源,保留充分生存和生长的空隙,才是保证万物新陈代谢、长生久世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如果说科学所需的本体论承诺,是现象与本体的同构,那么,老子的思想不正为关于生长演化的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本体论的承诺么?
《道德经》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21)因其之“大”,超越任何有形之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所以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14),我们不能感觉它。“道隐无名”(41),“无名天地之始”(1),“道”隐藏着,无以指称,亦非言语之可表达, 故不可限定,但它却是宇宙和万物生成的本根和始源。“大成若缺,其用不蔽,大盈若冲,其用不穷”。(45)似若虚空的道乃是大生成、大充满,其未显现的生机和创造力是用之不竭的。尽管老子与曼氏所言,一为形而上,一为形而下,但显然,两者都将“无”看作是蕴涵着无限之“有”的潜在之存在(“隐”存在),两者都将“无”、“空”看作生成万物的根源,两者都洞察到“无”和“空”的不同程度和层次。这里,重要的不在个别术语和概念的对应,而在两者对万物演化生成、大化流行的共同理解和世界图景的相似,在于某种人类伟大精神的跨时空的相遇相契。
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曼氏的整体观仍然是限于现象界的整体观,其整体是指现实存在物的实体与空隙合一的整体,因此,仍是“物”的或对象性的整体观;而老子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现出的系统思想之整体观,乃是心物不二的整体,其整体是作为本体的“天”和作为本体的人(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亦非生理或心理的人)合一的整体,即自然之体与心之体的统一,因此是非对象性的或本体性的整体观。
或许在更深层次,中国古代圣贤与西方当代科学伟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命状态自有其相契相通之底蕴。曼德尔布罗特曾说:“……我甚至怀疑……我是否存在,因为如此众多的学科之交集肯定是一个空集。”他称自己为“一切定型的学科之间的游牧民”。〔8 〕他不惮长期表现为一个外行,在数学中不时髦的角落持有非正统的看法,孜孜不懈地探索着不为人理解、不受人欢迎的理论;而在一个领域有所创见、留下一堆激动人心的问题后,却又转向另一学科。这种“空集精神”不正体现了道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7)、“无知而无所不知”的精神么?他的研究不为学科所限,不为名利所缚,故始终“能知”、“能为”而不为“所知”、“所为”所限定、所滞碍。他之为“空集”,不正是“为而不恃”(51)、虚怀若谷么?他那永富童心和原创力的探索精神不正冥合老子抱朴归真、涤除玄览(10)、“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1)的境界么?笔者以为,正是他“无执”的“空集精神”,成就了他“有执”的空集研究和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