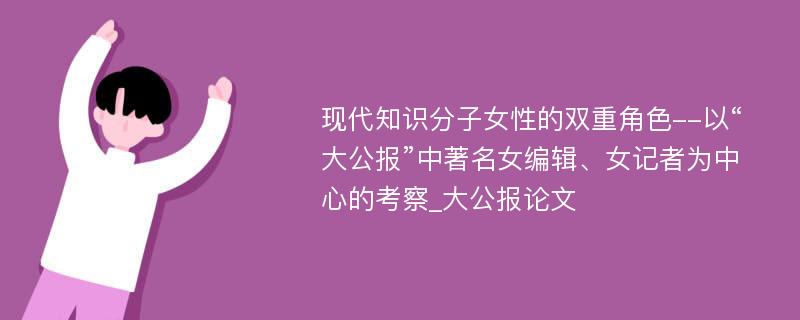
近代知识女性的双重角色:以《大公报》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近代论文,角色论文,编辑论文,记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5)01-0110-07
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很多女性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成为知识女性。进入社会后,她们选择了不同的职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了个人的价值。同时,她们也扮演了不同的家庭角色。本文拟以服务于《大公报》的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如吕碧城、蒋逸霄、陈学昭、彭子冈、杨刚(注: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出生在山西大原,曾创办中国华北地区第一所公立女子学堂。蒋逸霄(生卒年不详)出生在无锡陈墅,曾在无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南开大学等学校就读。陈学昭(1906~1991)出生在浙江海宁,曾在海宁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海爱国女校求学,后到法国留学。杨刚(1905~1957)出生在江西萍乡,曾在南昌葆灵女子学校、燕京大学就读,后到美国留学。彭子冈(1914~1988)出生于北京,后迁居苏州故里,曾就读于中国大学英语系。)等人为中心,探寻女性走出传统家庭,接受或者是发展新式教育,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以及生活道路,独身或者通过自由恋爱,建立小家庭的情形。透视近代知识女性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及其扮演的家庭角色。
一
本文所要讨论的这几位知识女性,或为《大公报》的专职记者、编辑,或为驻国外特约记者、兼职撰稿人。她们的童年经历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来自于传统家庭。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家庭于她们的实际作用与影响进行一番探讨。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不仅仅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且还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心。我们所要讨论的这几位《大公报》的女编辑、记者和兼职撰稿人先后出生于1883年到1914年的30多年间。其间,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尽管遇到极大的挑战,但仍然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由于她们都来自传统大家庭(注:吕碧城的父亲吕凤歧,进士出身,累官至山西学政。有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同母姐妹三人。蒋逸霄的父亲是读书人,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蒋本人是家中幼女。陈学昭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早逝。陈有四位兄长。杨刚的父亲曾任武昌守备,后又做过江西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杨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彭子冈的父亲出身苏州彭氏大族,为清代秀才。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东京,专攻博物学(即生物学),学成回到北京,在高等院校中任教授。彭有一姐一弟。),所以多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
彭子冈的父亲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威胁妻子说:如果再生女孩,他就要娶姨太太。显然,在父亲们的观念中,女孩子的出生并不是让人欢喜的事情。不仅作父亲的有轻视女孩的思想,而且同样身为女性的老祖母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杨刚的祖母就视女孩为“赔钱货”。
在传统家庭中,她们由于性别的原因而遭到轻视,受到了许多屈辱和极不公平的对待。在陈学昭很小的时候,大哥就想把她随意许配给自己同事的亲戚或兄弟;而三哥时常以莫须有的罪名痛打她,甚至无缘无故不让她吃饭。在唯一能帮助自己的母亲瘫痪后,陈学昭深深地感到身为女孩的无奈和悲凉。她尝言:“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注:陈学昭:《我的母亲》,邓九平主编:《寸草心》,同心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正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对传统家庭失去了天然的亲近感,相反倒有了一种本能的反抗意识。加上当时反抗传统家庭制度的舆论大行其道,家庭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好像“二十世纪生下来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有着改革大家庭制度的一个革命的观念”(注:仲芬:《告小家庭的主妇:工作与娱乐勿因袭大家庭之弊害》,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2月2日。)。有人甚至把反抗传统家庭对女性的压迫作为自己从事写作和开始记者生涯的原动力:“我觉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女人的痛苦是多种多样的,处境的艰难是无法形容的。我反抗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封建家庭给女人的压迫。就这样,我开始写东西,不断的写。”(注:陈学昭著:《我怎样开始写作》,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7页。)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的写作思想更加丰富,文笔日渐成熟,视野也越来越宽广,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而是逐步转向了社会,但是这种对传统家庭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对新女性抗争的极力赞同,则直接导源于在传统家庭生活中所孕育的对传统家庭乃至社会的叛逆心理。
我们也不应该彻底否认,在传统家庭中,家庭成员一方面给她们以性别压迫和歧视,另一方面也为她们提供了一些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她们都出生在传统文人或官宦之家,比较强调诗书传家,向往斯文,有的家庭本身就建有家塾。对她们而言,家庭成为“陶冶人最初的人文环境”(注:侯杰、范丽珠著:《中国民众意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页。)。另外,在当时很多年轻男性已经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们希望自己的配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些家长们逐步认识到:如果再继续秉承古训,女儿在长大婚配的时候就有可能跟不上时代潮流。出于“迎合主顾的爱好”和“早日打发出门”(注:天然:《女子是个人——读傀儡家庭后》,《大公报》1929年10月3日。)的考虑,也必须要使她们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者是染上一点“书卷气”。陈学昭的父亲临终前,曾再三叮嘱她的哥哥们:要给妹妹读书。陈学昭清楚地知道父亲的意图,因而要求:“将来嫁我时只要分点书画给我,别的什么也不用给我”(注:陈学昭:《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第7页、第84页。)。于是,这几位女编辑、记者从童年时代起在家庭中,接受了一些最基础的启蒙教育,阅读了一些有关传统思想文化的书籍,如《烈女传》、《女孝经》等。她们掌握了一定的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知识,并且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乃至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等问题开始了思考。在朦朦胧胧中,她们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甚至得到“曹大家是我生平最反对的一个女子,在幼年时,便觉得她所做的女诫七篇,把女子束缚得简直一些自由也没有”(注:蒋逸霄:《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56续,《大公报》1930年11月10日。)的认知。除了一些常见的书籍之外,她们还想方设法找一些被家长禁止接触的书籍来阅读,汲取更多的知识。如蒋逸霄所阅读的“《红楼梦》和《西厢记》是从大哥的书箱里偷出来的,其余的书都是自己在镇上的小书铺里买来。”(注:蒋逸霄:《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56续,《大公报》1930年11月10日。)虽然充满苦涩,但是启蒙教育特别是家塾教育,使得她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领悟,并促使她们成长,为她们以后从事文化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和文字功底。
二
毋庸讳言,这些知识女性最初接受启蒙教育时和同时代的其他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为了“能够认识几个字,记一笔日用帐,看得懂一封信,免得将来受人欺侮蒙蔽而已”(注:蒋逸霄:《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56续,《大公报》1930年11月10日。)。然而在这样的学习中,却孕育了她们对新思想的向往和追求。特别是当所得到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她们对新知的渴求时,她们便开始尝试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求取新知。
吕碧城12岁时父亲逝世,叔父霸占了她们的家产。“冀得较优之教育”(注:吕碧城:《予之宗教观》,刘纳著:《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的她,于是前往塘沽投奔作官的舅父。1904年为研究新学,她毅然决然地以脱离家庭的方式独自到天津求学,“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翌日逃登火车”(注:吕碧城:《予之宗教观》,刘纳著:《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由于吕碧城“国学根柢已相当深厚,当年京、津间已没有她可进的学校”(注: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页。)。于是,在《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等人的支持下,吕碧城萌生自办女学之心,并撰文就女子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非常独到的看法,先后刊登在《大公报》上。
在文章中,吕碧城提出:中国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女子不事生业,嗷然待哺于人,一生之苦乐,胥视一人之好恶。”所以,女子教育就是要“授以实业使得自养”,“必能自养而后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讲立身之道”(注:吕碧城著:《兴女学议》,《大公报》1906年2月20日。)。她的这些文字突出地把女子接受新式教育和谋求摆脱男性束缚,争取自身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时代先锋的味道。
为了求学,蒋逸霄也颇费周章。她知道“要向家庭请求供给是绝对的没有希望,……便向一个知己朋友借了一百块钱,偷偷地到上海去投考”(注:蒋逸霄:《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57续,《大公报》1930年11月11日。)。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女性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为了求学,不惜采取一些常人看来不太妥当的举动。
走出家门的她们,除非像吕碧城那样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才学,可以先在《大公报》找到一份工作,否则多是要经过求学的阶段,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独立于自己的家庭;遇到困难时,还不得不需要依靠家庭成员的帮助。因此,在求取新知、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这几位女编辑和记者似乎也并没有完全脱离原有的家庭。
蒋逸霄在进入无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后,每年需要的几十块钱零用,都是由她母亲私下筹措的,因为父亲不太主张女孩子读书。后来,她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其母依然为她私下筹划费用,并按时邮寄给她。1921年秋,当陈学昭进入爱国女学文科学习的时候,她的二哥除了给她付清学费、膳费外,还留下一些钱给她做零用。“二哥给我读了几年书,在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感激他”(注:陈学昭:《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第7页、第84页。)。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传统家庭的资助,她们几乎无法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新知识,更不用说以后在社会中谋求职业,施展各自的才华了。可贵的是她们并没有像社会中的某些女性那样,接受新式教育仅仅是“为了婚姻水准的提高,进学校去求智识,把妇女运动作为出锋头的工具”(注:励华:《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而是要依靠自身的才学,在社会中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她们深知“女子得了职业,然后经济方能独立,经济独立以后,自然可以增高妇人解放的势力”(注:汤鹤逸:《妇人问题》,《晨报》1926年3月30日。)。
三
加盟《大公报》,成为这几位知识女性共同的生活经历。吕碧城于1904年担任天津《大公报》助理编辑。蒋逸霄于1927年在天津《大公报》担任外勤记者,后成为副刊《家庭与妇女》的主编,1936年,担任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妇女访问记》专栏的工作。陈学昭于1927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担任《大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直到1931年。杨刚在1939年9月1日到香港《大公报》工作,主编《文艺》和《学生界》等副刊,后负责桂林《大公报·文艺》,1944年3月,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撰写美国通信。彭子冈于1938年1月到汉口《大公报》开始记者生涯,后到重庆《大公报》继续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仅1943年她就撰写了近百篇重庆航讯,曾被新闻界同行称为“重庆百笺”。1945年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记者。事实证明,在《大公报》的从业经历,使她们真正成为“能独立,能自谋为生,要锻炼自己的身体逃出了生理上的阻碍,要锻炼自己的思想打破了旧礼教的束缚”(注:懿行:《一篇演说——理想中的女性》,《大公报》1930年12月24日。)的职业知识女性。同时,她们也面临着是否要以及如何扮演家庭角色的问题。根据其不同情况,我们试作如下类型分析:
第一种类型:终身未婚。如吕碧城就极力打破传统女性必须“三从”的人生模式,选择了一条独特的生活道路。当她九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和同乡的汪氏订婚,但后来父亲去世,母亲因为堂叔霸占其家产被掠去并遭到幽闭,家道衰败。这一变故,给吕碧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对她的家庭观也有所影响。因为“家庭经济的窘迫,母亲的勤劳和一切痛苦的事项与儿童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人生真正的愉快和天伦之乐,不独没得享受,而反使她生一种痛恨家庭的观念。”(注:C.T.YIN:《我对于“独身”的见解》,《大公报》1928年3月22日。)特别是后来汪家因此而提出退婚要求,给她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吕碧城“方以才貌噪于时,遽蒙奇耻”(注:刘绍唐著:《民国人物小传·吕碧城传》,《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104页。)。此后,吕碧城的感情生活也甚为坎坷。她曾与诗人杨云史“诗筒往还,文字因缘,缔来已久”,甚至以“天地悠悠,我将安托”为寄,可惜的是,杨后来却和他人结合(注:云若:《隔一重洋各自愁》,《北洋画报》第243期。)。经历种种曲折之后,使得吕碧城对婚姻、家庭自有一番看法:“中国男子不识义字者比比皆是,其于父母所定尚不看重,何况自己所挑?且当挑时,不过彼此皆为色字,过时生厌,自尔不终;若是苟且而成,更是看瞧不起,而自家之害人罪过,又不论也。”(注:王栻编:《严复集·与甥女何纫兰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839页。)因此,当有人和她谈论婚姻之事时,她总是表明这样的态度:“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注:郑逸梅著:《郑逸梅选集》第三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4页。)这种想法,让她的老师、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深感忧虑,“此儿不嫁,恐不寿也。”(注:王栻编:《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493页。)其实,并不是她不愿选择婚姻,只是“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注:吕碧城:《予之宗教观》,刘纳著:《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机缘不合,使得她不得不延续着独身生活。后来,她曾游历欧洲诸国,最后,皈依佛门,终老于香港。尽管她个人的婚姻、家庭之路不同于常人,但在社会上确实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典范。
第二种类型:虽然自主地选择了婚姻对象,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并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但是却没有获得长久的幸福,最终以分离而结束家庭生活。分离后,她们都没有再组成家庭,而是保持独身的生活。如陈学昭、杨刚等人。
陈学昭留学法国时,过着半工半读的清贫生活,后来认识了自己的丈夫,由同情而结合。1935年2月,她带着两岁的儿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在国内,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陈学昭放弃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力,丈夫去哪里,她就跟去哪里。但是最后夫妻感情完全破裂,终以离婚告结。对此,她“并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注:李杨著:《陈学昭》,http://www.nbip.com.cn/books/jzwx/zgxdrwcj/20/013.htm)。婚姻的不幸,并没有影响到她的事业。在从重庆到延安的途中,她还在为《大公报》的姊妹机构国闻通讯社撰写陕北通讯。此后,她一直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封建这东西还是习惯地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行动和思想里”(注:陈学昭:《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第7页、第84页。)。
虽然说杨刚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似乎并没有陈学昭那样强,而且她和丈夫郑侃相识于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但是家庭生活也不长久。婚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杨刚渴望投身于革命中去,而郑侃则希望过平静的生活,两个人最后因为志向不同而分居。直到郑侃被日本侵略军炸死,两个人也没有在一起。如果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话,显然,杨刚选择了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但她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1939年,她开始负责《大公报》的《文艺》副刊,马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为祖国抗战宣传服务。1942年7月,她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到东南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从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发回通信10多篇,宣传中国必胜的理念。1944年,在美国期间,她又撰写了40多篇美国通信,在重庆和上海等地的《大公报》上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堪称佳作。
第三种类型:美好的爱情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最终获得了幸福而完满的结果,如彭子冈。中学时代的彭子冈由于才华出众,得到后来成为其丈夫的徐盈的关注,两人开始通信并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他们“鄙弃那无聊的一个劲儿缠绵的恋爱”(注:《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编:《新闻界人物》十,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112页。),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共同探讨人生,剖析社会。1936年秋,任职于《妇女生活》的彭子冈和时任《大公报》外勤记者的徐盈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便踏上了外出采访的道路。采访归来,他们才按照传统方式补办了婚礼。后来,彭子冈也做了《大公报》的新闻记者,从此两人并称《大公报》的“双子星座”。
在《大公报》,彭子冈的新闻成就丝毫不逊色于丈夫。她以文笔尖锐、泼辣著称。汉口《大公报》在《最近来汉的四位女作家缩写》一文中,称赞她善于写调查和访问,是一名很好的女记者。可是当徐盈要调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时,她毅然离开重庆,随丈夫到了北京,并任《大公报》驻北平记者。可以说,她在尽力兼顾家庭、事业。她曾单独闯到军调部美方人员那里,乘机去新解放的张家口采访,写出《张家口漫步》。1946年2月,她还前往山东兖州,揭露蒋介石挑起军事冲突和争端,加剧内战危机的内幕,写成《济南小组在兖州》。可见,即使为了家庭的完整,她要放弃一些事业上的追求,但是,依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这几位《大公报》女编辑、记者在家庭中不仅是妻子,而且还是母亲。在动荡的社会中如何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是她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结婚离婚,虽然可以取最简单最自由的方法;而对于儿童的养育,则不可不完全的责任。”(注:Y.D:《古本忒氏的婚姻问题观》,转引自梁惠锦著:《妇女与婚姻自由权(1920-1930)》,第6页。(未刊本))同时,也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因为那是她们不依靠别人、独立于社会的资本。这样,“每人都需要担负起她们自身在社会上的职业地位,和家庭中母性专差的两重担子”(注:虹弗著:《关于女性应有的常识》,《大公报》1933年10月29日。),加之她们所选择的新闻记者职业也比较特殊,既辛苦又需要四处奔波。为了维护家庭的安定,保证孩子们的顺利成长,她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尤其在战乱的时代。
在重庆为《大公报》工作时,彭子冈刚刚成为母亲。每次敌机轰炸的警报响起时,她都要抱着孩子,提着奶瓶、热水壶和尿布,到居所下面的防空山洞中去躲避。“在黑黑的洞内听够了‘嗵嗵嗵’的炸弹声,还不知回去后水电停了没有。”(注:彭子冈著:《熙修和我》,《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38页。)摘下著名女编辑、记者的光环,在家中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性,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既要关注柴米油盐,又要关注孩子的安危。
和陈学昭、杨刚比较起来,彭子冈还算是幸福的。因为陈学昭、杨刚无法一边工作,一边自己带孩子,所以只好把孩子寄养给别人或保育院。尤其是杨刚的女儿,除了幼年时代,几乎很少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在女儿出生之后不久,杨刚便与丈夫分开了,她带着女儿东奔西跑。杨刚的女儿郑光迪回忆说:“那时她带着我东转西转,我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或武汉,或香港,长则几个月,短则几个礼拜,真有如现在常用的一句话: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新到一处,她总是忙着。”(注:郑光迪:《怀念我的妈妈》,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51页、第552页。)后来,杨刚感到实在无法照顾好女儿,只好把女儿寄养在亲戚家。可以说,为了事业,她舍弃了亲情。杨刚曾非常痛心地写道:“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注:杨刚著:《〈桓秀外传〉·代序》,萧乾编:《杨刚文集》,第369页。)像是一种自责。但是,杨刚对女儿的爱确实是真挚的。当她看到女儿站在高处时,总不免“大吃一惊;然后细声劝我以后千万不能再这样”(注:郑光迪:《怀念我的妈妈》,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51页、第552页。)。
四
综上所述,我们从《大公报》这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的生活经历中可以看出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知识女性如何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开始新闻记者、编辑生涯,独身或者通过自由恋爱,建立小家庭,扮演起家庭角色的生命轨迹。其特点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她们都生活在多子女的传统大家庭中,而这种家庭所给予她们的,既有性别轻视和不公平的一面,引起她们本能的反抗,又为她们的成长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在保守而传统的家庭环境中,由于接受了一定的知识与文化,她们对新知识、新思想更容易产生探寻的要求,从而促使她们摆脱传统大家庭的束缚,接受新式教育。然而在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她们仍然无法完全脱离传统大家庭,尤其是来自家人的金钱资助。
第三,社会的急剧动荡,给她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她们通过职业的选择成为了生活的强者,为女性争得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帝国主义依然继续不断的对中国实施军事和经济侵略、境内军阀混战不已与连年灾荒、匪患,使人民常生活在逃兵、逃荒、逃匪之中,这对于农村凋敝和旧家族制度的崩溃,更发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注:梁惠锦著:《妇女与婚姻自由权(1920~1930)》,第3~4页。(未刊本))在动荡的岁月中,她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获得一份职业才能真正地在社会上立足,进而提高女性的社会政治地位。“一个妇女,在政治上争取地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争取职业上底地位也同样应该看重。……在职业上的地位提高同时也会促进了政治上的地位”(注:全衡:《访问陈学昭先生》,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第四,一般而言,婚姻自由和自主成为这一代知识女性独立的重要标志。有些知识女性由于“看到自由恋爱婚姻前途的暗淡与悲愁,在旧礼教下的牺牲,”(注:励华:《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因此抱定独身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建立小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在这样枯寂的社会里,足以安慰我们的,只有美满的家庭,”(注:蒋逸霄:《我们的旨趣》,《大公报》1927年2月11日。)因此,她们不懈地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家庭的幸福和婚姻的美满。然而在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中,她们更多地选择了事业,能够维持美满家庭生活者虽然存在,但失败者也不乏其人。当然,其原因并非是单方面的。社会的急剧动荡不安,使人们的家庭生活与感情世界都面临更多的危机和考验。为了克服这种种危机,勇敢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似乎只有强者才是最后的胜者。
可贵的是,由于这些知识女性普遍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因此在是否选择婚配,以及如何选择对象、缔结婚姻、安排家庭生活,乃至解决夫妻矛盾,结束婚姻关系时,她们都表达了自己的意志。而当自己选定的婚姻不幸福,以失败而告终后,她们一般都不会再结婚,而是选择独自生活的方式。可在单独抚养孩子的时候,又很难给孩子们一个比较稳定的、适合孩子们生长的环境,只好在一定的时期采取寄养的方式。
在《大公报》的百年发展过程中,工作其间的知识女性还有很多。她们对于事业与家庭的态度如何?在家庭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样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希望以后有机会对更多的知识女性的更多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