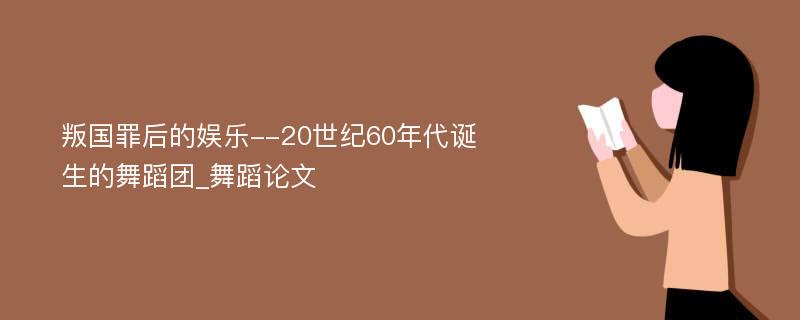
叛逆之后的娱乐——论60年代出生的舞蹈创作群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叛逆论文,群体论文,舞蹈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702 文章编号:1008-2018(2004)03-0049-06 文献标识码:A
错拍到切分
在一种孤立和经常单腿独立的状态下,舞蹈从来就是清高而又大同的发展,没有年代 ,混沌的帮派,个体作坊的独爽,学院权威的批发,游击队式炒更和大晚会的排场互不 干涉,学术思想的分流和编导实践的克隆都是一笑了之,从来没有特定新生代的标签, 建国前后的编导也在尝试新的言语结构方式,新老之间希望达成风格上的协调,造成这 一代舞蹈编导在时间上的概念是某种延时的错乱,由于舞蹈观念在80年代以后近90年代 初才有巨大的变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流舞蹈的创造者,也是延时的。
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舞蹈编导如张继刚、苏时进、孙龙奎、陈维亚等人的作品在80年 代初中后期已经有所成就,观念转变和技法风格的成熟也是在80年代末的,所谓形成了 今日舞蹈主流的风格特征,而同时期的王玫、高成明则是在80年代末才开始创作和崭露 ,同时期内也存在这相当大的延时。甚至60年代出生的舞蹈编导创作高峰与50年代末的 高峰,几乎在同一时间。
从“言语”作品,专注于舞蹈言语方式到“整合”作品,转型向大歌舞年代。所以60 年代出生的分类如果确定在80-90年代的主体创作上的话,泛化已是无法避免,并且产 生错拍的。而80年代初期的混乱与复兴,一部分是学院编导受西方现代舞激发观念的冲 击,肢体言语的“自我”爆发,而不是在传承图示和自娱的手段。另一部分是当时军队 舞蹈和地方舞蹈编导的表达复兴。在军营舞蹈编导长时间的占据创作主流之后,学院派 的咬文嚼字和对舞蹈技术、风格、本体概念的兴趣盎然,成为了另一个权威。
而60年代对于他们从来不是什么印记,在这个类群当中,看见西方到重识传统,由激 进批判的思想别处生存,到冷静漠然的商业现实口味,其中舞蹈动作与身体依附关系和 声出的意义,则是始终无法摆脱的情结。人们把最大的焦点放在了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 上。而且这一代的起点和创作理念是从摸爬滚打的实践当中得来,积累了编舞导演基本 素质,从一名舞者,技术上的,包括舞台的综合实践,灯光、舞美的实践,他们是从社 会经验回到学院理论的一代,是而不是纯粹从动作到动作的一代。所以在整合作品和表 达上,60年代出生的编舞有更多的自主调节的能力,同时对于审查制度和政治态度上也 有相当大的宽容度。
从80年代初,50年代末的舞蹈编导还完全处于本能的创作觉醒,被抑制的和雪藏的念 头在政治的身体中康复。但他们突然发现,正是这样激情四射说出的话,竟然还是过去 的句式,但是本来要高扬的语调已经变了,有点喑哑。舞蹈编导们开始体验到了人性在 运动中的变化,在死亡和谬境中的力量,新生和希望的破茧之痛。在80年代早期,蒋华 轩的《爱情之歌》苏时进的《再见吧,妈妈》《一条大河》华超的《希望》,把外在的 激情已经渐渐为肉体历练内敛为心灵的歌声。88年张明伟的一场《大地震》似乎成了80 年代一个尴尬的结尾。而其后,张继刚的前瞻和机智就在别人还在“伤痕”的时候,他 已经赶上了“寻根”的尾巴。他的《黄河儿女情》《献给俺爹娘》《黄河一方土》等作 品,则带着故土热度温暖,填充了不太丰盈的物质生活。
从陈维亚的《木兰归》《MONGDONG》《绿》《神曲》,范东凯的《长城》,痴迷于舞 蹈动作的变奏和交响,在后苏联交响大师格氏的芭蕾舞式中流淌着未完的宏大尾声。孙 龙奎的《残春》和《娜琳达》是另一次苏醒,似乎也最有代表苏醒迟来的心情,青春易 逝,残酷而又短暂,在青春的尾巴里,残破的精神和不完整的生命都变成了作品当中的 一声忘情的喊叫。朝鲜舞姿辗转低回,从最黑暗处缓缓走来,带着青春的微弱的气息, 也许是这一代的缩影吧。反省和拒绝反省,成为了这些从模仿走向风格,从技术到人性 的舞蹈编导们的两极分化。90年代的作品则集中在个性的偏执上。现代舞的技术观念介 入和传播其实只是某种尴尬的语法,编舞家们在对于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重新审视之后 ,才发现舞蹈言语书写的快乐,峰回路转才看见除了粉饰和附庸之外,自己经历的尴尬 和困境,或是出身背景,不在是掩饰和淡化,反而成为了张扬和夸大,凸现的标志。
60年代类群的创作群体之中,也是经历了两个孪生的轮回过程,由开始以传统的言语 方式叙述新主题,到用新的技术手段言说传统故事,其实在原地打转,但分化情绪和姿 态却是越走越远。文革的后期影响,80年代的思想解放,90年代的物欲冲击,理想追忆 的岩石碎末,信仰的从有到无,在身体柔媚或执拗地动作里,不再重要,变成了一连串 苏醒的过程。
实验性的群体则把延时的舞蹈发展加进了切分的新鲜。
《年轻的天空》《神话中国》《鸟之歌》《三个浪漫的中国人》,曹诚渊已经把城市 生活和现代人的形态心境,跳进了一片秧歌和乡情的舞蹈舞台上。他的作品和一系列活 动给60年代城市实验性的创作群体起了一个天马行空的“范儿”。上海都市的景色中, 胡嘉禄却在“喧闹的城市里,唱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同样是一位城市实验的先行者 。胡嘉禄算是舞蹈界中的一个例外,他的《绳波》《对弈》《血沉》《彼岸》《独白》 ,准舞蹈和边缘化,强调概念和意象,简约而沉重。
大众的脸谱被一张张固定了特殊表情的脸所代替,表达自己成了乐事,解构传统成了 时髦。但真正追溯中国舞蹈的内在心源,散发着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把中国舞蹈精神 发挥到极至的则落在了台湾的50年代初的林怀民身上。从70年代末的《薪传》到90年代 的《流浪者之歌》和《竹梦》,把大中国人文精神,水墨意境和诗文经书,不是临摹而 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浸到骨髓之中的归属感,恍若在过去和现在的时间通道之中, 浓浓古意搀杂一点后现代的荒唐浪漫。也是这位关注民生,关注自己的呼与吸的林怀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作品正是在试图超越时代,在整个东方精神上给予了新生代 坚实的慰籍,对于这一代迷失的灵魂指出一条心灵之路,古典的重新解读和译释,才出 现了能够嘻笑怒骂的云门二团。
90年代以后,作品的意识慢慢转为新生代崛起的象征,而主流的编舞家们则整体视觉 上做文章。从“灵化”的热土转向了物化的灵魂,似乎人们享乐了视听视幻,而忘记了 动作的意义。从此,身体意识的唤醒和沦落又在这些似乎已经沉淀了的或是沉默了的人 群当中不断地分裂。
木头人游戏
令我们视线兴奋起来的,应该是现在进行时的倒叙。王玫、万素、文慧、梅卓燕、罗 曼菲、江青等这些现代舞的女性书写者,以细腻而又大胆的触角,做着一些让人不安或 是掏出镜子的动作。王玫的探索把学院的精细和各种游戏的可能发挥到了游刃有余的境 界。这位曾在中国民间舞里浸淫的编舞者,在80年代接触到现代舞时,已经有了传统技 法流畅的《春天》,在新民间舞当中希冀有所突破的作品。此后在欧美现代舞冲击之后 ,有了《潮汐》,有了《我心中的钗头凤》,不想在90年代初,王玫的作品风格突变, 呼吸的破碎节奏,童年游戏的变奏,唤醒情爱的生活动作,神经质的重复,《椅子上的 传说》《红扇》《两个身体》中双人对话的纯粹和回响,现出了她细密清澈的动作逻辑 ,《99蒙太奇》《随心所舞》则是她貌似冰冷动作编织下的动情低语。在《爱情故事》 和《国色天香》里,2000年始王玫已经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拥戴者,自己衍生出的新生代 ,她带领着他们舞出了《我们看见了河岸》《雷雨》,同样风格化动作,黑暗里的短促 有力呼吸,纯粹直接的动作关系,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另外一个王玫,不止是纠缠于动作 世界的游戏,出现了责任,关于中国现代舞的位置和形态,出现了对更广泛的社会现实 反思。正如她所言“人怎样的生活,就跳怎样的舞”。在《黄河》的交响当中,在《雷 雨》的悲剧氛围当中,王玫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我们思考的还不够!《我们看见了河 岸》王玫在“黄河协奏曲”中摆放着当代人的群像,东奔西走,失去方向的赶路人,机 械化的白领,新的不平等和困境,现在没有炮火,依然是一场革命,对自己心灵的革命 ,才可以看见民族的彼岸。而在《雷雨》当中重新演绎了每个人物,在那个时代,每一 个人都是悲剧性的人物,错综复杂的动作关系,以图纯粹身体的言说和叙事。在很多作 品当中,游戏不仅仅成了手段,也成了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心理联系。
学院之外的声音,则在出身学院的编舞者文慧身上看到。舞蹈剧场和多媒体,环境编 舞的尝试当中,在舞蹈圈内若隐若现,但与其他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的合作,使她在整 个艺术领域赢得了更多的营养和关注。早期在先锋话剧当中的表演和编舞,后来在语言 的捕捉上也出现了《一百个动词》,后来的“报告”系列,《生育报告》、《身体报告 》中国舞蹈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多媒体舞蹈剧场探索作品之一。虽然多媒体的参与和声音 言语的介入,陌生身份的转换和文字力量的验证,窥视的压迫和自我的解剖,手段的繁 多,日常的视幻遮掩,依然看到身体本能的能量,文慧作为女人的体知历程则在报告中 间刻骨铭心的流露。《与民工一起跳舞》在体验平民生活。文慧在想把舞蹈还原为人最 基本的娱乐的时候,却不经意的与民工们的自尊产生了化学反应。舞蹈所能关心的是现 实,还是一场利用现实的秀?
游戏,爱情、女人,是她们的通用语,对于万素则是关键词。纯粹动作的实验和游戏 逐渐变成了女人心路的舞蹈写照。对镜梳妆般的庸常心绪,青春与容颜,爱的得失,去 不断的诉说。万素的《祝福》《同窗》开始,把面目可憎的伴舞,编成了煽情和有点媚 俗现代芭蕾织体,在依附和破解流行音乐的同时,角色变换不再重要,而是与观众对话 的方式更加像一个普通人,像一个矜持的音色优美的卡拉OK者。一个动作节奏感及其敏 感和细腻的编者,再次从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芭蕾、现代舞的自由而多产的创作当中 ,从校园到社会之间的青涩怀念中飘荡,把民间的俗情在动作视觉上,在道具的改善上 ,找出新式的格调和情趣。《扇妞》《新衣服,旧衣服》,从民间舞蹈的样式和情感, 扩展到了《磨合》《咦呀哦嗨呦》对婚姻,对男女之间的拉扯,女人世界的自决,这些 当代民间俗情的描述,但表面的游戏却化解了这一切的力度。
当技法,技法,技法解决不了城市实验性群体的发声,他们开始拿自己和社会开刀了 。金星、沈伟、李捍忠、邢亮、桑吉加这些大多数的男性书写者,都曾经是技术强悍的 舞者,而其编舞的风格则是一个技术流变的例证,谁都没有放弃技术,在唯美的动作上 雕刻还是在技术的足尖上思考,他们在创作中寻求答案。80年代的技术炫耀,解放的姿 态到90年代稀释了的愤怒,在自己个体和舞者身份的生存境遇中挣扎。谁都学会了波普 和离谱,学会了一动不动和疯狂即兴,学会了极少和极多,学会了紧张和放松的新技巧 ,但始终没有忘记提问题,然后自己也躁动着想象,想象着从抗拒和迷惑于精神和物质 的困境,到沉溺和享受于这种不清醒,从对社会现实的言说泄愤到随遇而安的婉转表达 ,如何来完整舞蹈的生命和真实。
如今已经在海外的编舞沈伟,物欲噪音在他身体划过的血丝,是《不眠夜》里如坐针 毡和枕头般的生命之轻。绘画和湖南花鼓戏,都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敏感,神经纤细的 编舞,成为早期广东现代舞团舞者与编舞。物欲在窗外的身影不仅令他失眠,也令他止 步。《小房间》的封闭自语和手纸的裹缠,似乎是每一个犹豫而又胆怯的自闭和封锁, 也有一触即发的困兽犹斗。表现庸常生活,无能为力的跟随这种生命正常沉闷的节奏。
邢亮几乎是中国舞者“完美”的象征,头一次在90年代的舞台上,只要出现他的名字 和身影,就会引起无数尖叫,编舞与跳舞对于他来说,从来是无法分割的一件事情。动 作的精确和细节纤毫必现,后来他的舞蹈工作室“动作纤维”倒也很合贴。也许尖叫磨 的耳朵起了茧,邢亮慢慢抑制了技术的张扬和迸发到了不露痕迹,更多在状态的打磨, 以静制动,留白然后穷竭。《光》在邢亮的手里和心中是可触及,可以灼伤,可以穿透 的。堪称完美的动作诉说和舞蹈棱角破碎的编排,邢亮几乎影响了90年代的现代舞者舞 者风格形态和审美向往。速度,力量,只有自由的身体才能自由的表达,高难度的技术 和内在节奏心理控制,清淡的神情,无论是在痛快的动作风暴里,还是一个慢慢张开的 手掌,都是一句灵光一闪的智语。“动作纤维”时期的多媒体作品《发生进行式》,是 把动作发泄为无名的愤怒和指责,不停地在转椅上旋转,影像中在宗庙的舞蹈打斗,舞 蹈中细细的血色丝线拴住邢亮的手腕,但红线剪断之时,切脉的之后隐痛和电子的麻醉 ,他望着他自己,那个偶像精确的倒下了,变成了《情男色女》,进行了《一百八十度 …悲与欢的转换》。
在技术褪去的同时,从民间舞的表情氛围,跳离到现代舞的原创之路,李捍忠、马波9 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不断的积累,写下了社会角度的舞蹈日记。原来对于动作创新的兴 趣转移到对于动作质感和意义的发觉,这也是这一代编舞与主流的不同和提前的觉醒。 略去文学性表达的繁缛和细节,强调直观视觉冲击的《不定空间》和《生命回忆录》。 而《雷动》电子音乐中的动作、心情的拼贴重新反驳了与传统的音乐贴合和协调:舞蹈 与音乐关系的疏离,解放了形式的自由和意义的偶然。《野性的呼唤》动作的稠密紧张 ,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充满了抑制下的张力,像是这个时代条件反射。《大放松》 正是从动作的痉挛到精神的放松,释放了放松之后的恐慌和无稽,放松之后的平淡和木 纳。放松是对于欲望社会的暧昧默认。我们对于人性缺乏理由的、过度的拷问,而当放 松和漠视,搞笑和“后”现来临之时,所谓的人性深度已经逐渐让位与日常生活的潜流 ,让位于爱迟到的戈多。
如果有一个人来结尾这场难以入眠的时代夜晚,应该是金星。这些失眠的不安,竟然 绚烂的成了那喀索斯的镜像。金星的《红与黑》象一个干脆的耳光,美妙的滑过空气, 什么也没有伤害,但是成为了当代中国舞蹈的一个典范的小品。在这一个没有超过5分 钟的作品之后,他可以大胆进行实验。金星出身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曾经中国舞蹈最 高奖“桃李杯”古典舞金奖演员,一个对什么都没有什么顾忌的性情中人,军队的严格 规制是否成就了他另外一性格。
《半梦》《向日葵》《贵妃醉久》一路走来,到2003的《从东到西》多媒体的介入, 现场音乐,多国艺术家合作,一直走在先锋前沿,而他本人却是依照艺术的本能在自我 更新,而性别转化的主题,舆论的口水都在剧场的那一刻不自觉地咽了回去。对于她来 说,作品和人都不是“想要怎样”而是“本来应该这样”,还原自己,还原当下最直接 的言语,是动情的,朴素的还是一句粗话。《半梦》里除去古典情怀的梁祝,晓风残梦 ,《小岛》的干净轨迹和《红与黑》的扇子利器显示了游历欧美的娴熟技法和中国古典 技巧的谙熟于心。金星在《贵妃醉“久”》里是一位浓彩戏装的贵妃,一边费力的给自 行车打气,一边唉声叹气,传统在她看来,已经在机械的时代里变得不合时宜,变得力 不从心。整个舞台设计成医院让人看到自己的病态。
以独攻独
曾经在80年代末提出身体技能的生命情调化,总结了一批肆意身体情感的编舞,一批 从古典中浸染走出又延伸着古典审美趣味的编者。陈惠芬、华超、杨丽萍、沈培艺、张 羽军、张建民、高度、刘立功、黄蕾、盛培琪等。在承袭了高技巧的比赛模式之后,他 们也沉浸于舞蹈用词的独特和外化内心,个体诗情的抒发,灵性的生趣,低调和自我意 识的坚持,成为古典主义的另一种时代变形。古典的审美情趣和舞蹈自身规律的发展, 让这些编舞者脱离更多的外力,在舞蹈自身书写当中,作品本身自圆其说,独善其身, 但技术语言的焦点却也消解了散淡的随笔,诗意和忘却,在这个时代,成了幼稚的消费 。
杨丽萍更大意义上是一个独特的舞者,一个艺术家,别人模仿她是效颦,她也无法效 仿别人,她只能自己跳自己的舞蹈,自己创作自己的舞蹈,自己的动力定型和惯式。这 种完全自我,依赖和相信自我身体的念头,来自于内心的力量,但是《雀之灵》《两棵 树》到21世纪初的《寂静的知觉》,却现了个体编创的另一个问题,所谓“独特”的缓 慢变化,但这种独特已经成为了某种文化形态的象征,而超脱出单纯动作的范畴。很有 暗示的几句话,杨丽萍曾经在第二届舞蹈比赛之后,说道,“我赢了,是因为我们没有 对手,创作的路子不同,他们无法与我相比”。
技巧的滥觞和心灵的独语,不成比例而又相映成趣的进化着。追求个性言语的灵性之 “独”,低调成了闭门造车的话,“15年才有作品的话,才有进步的话”,这种个体的 诗意势必被历史不断更新的独特和诗意的最新版本所淹没。当然,如果我们不用流行的 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舞蹈话,却是具有极强的形态表征,同时对于这种独特的追求和个体 意识的抒发,的确有心远地自偏地幻视。陈惠芬的《小小水兵》《天边的红云》,沈培 艺《俪人行》,盛培琪的《江河水》、黄蕾的《飞往天堂的蝴蝶》,诗意的悲欢和独在 的意境,这些美丽的独体,让古典审美范畴中多了些内省的味道。在这些独在的追求当 中,童趣、幻梦、古意、悲悯,每一个独特的亮点都象孤独的默语,有自己的节奏,消 隐了生不逢时,断裂,与时代的反差倒是成为了个体独舞安然存在的理由。
中国舞蹈没有真正的形式主义者,至少这一代没有,如果有,也是自我狐疑的,急于 表达的。说到底,这是一场技术之独与精神之独的消耗战。
学院精神和探索同样有着某种独孤求败的气质,在动作上进行院墙内的“拆”和“重 建”,象牙塔内的探究其实可以衍生出对于技术言语的熟练把玩和更多可变之规范,但 这种概念化和太多的是非探讨,争论当中,创作力则成了十年磨剑和一剑用十年的幻觉 。张羽军姚勇的《黄河》,由一部血脉贲张的舞码,燃烧到一轮又一轮舞者必跳的作品 ,而规矩教学化,脱离了原有的感动和意义,依赖于不同舞者的阐释。虽然甚至很多年 以后,才有另外的版本重写他,却依然无法逃出窠臼,虽然经典之作一再被学院的独立 所创作出来,这种独孤的交响激情和中国古典舞身韵技术的集中凸现,黄河也是这一代 的心结,一种完全的灵魂放置与热土地情怀。强烈的本土意识的勃发,从刚烈勇猛的动 作呼喝,到沉溺于太极和易经的调息稳脉,张羽军的变化在中国舞蹈全面“现代”的同 时,想在熟识传统和解构传统当中,找中国古典舞的坐标。动作解构实验是影响了古典 舞创作,使之从姿态模画中摆脱出来,动作的分解重组,不断持续的动作源轻松地为古 典精神的发散制造了通道。学院的新交响就在《黄河》《源》张建民《垓下雄魂》等等 实验中,逐渐地褪去苏联舞剧舞蹈模式。
灵化的热土到物化的水泥
50年代末的舞蹈编导们,对于60年代末的新生代来说,无疑是一批大龄青年,在中国8 0年代的舞蹈发展当中,舞蹈的新生代还在朦胧的兴奋当中,他们已经狂热的待在排练 教室里急于舞蹈出各种的冲动。思想解放,改革机制,舞蹈有太多从未触及的主题,无 论是挖古董,还是新民间,无论是儿女情长,还是生死悲怒,还是形体的坦露尺度,都 是在刺激着大龄青年们的创作欲望。
张继刚、陈维亚、范东凯、孙龙奎、丁伟、张守和、赵明、杨威这些中国主流的编舞 们,经历了80年代时期精神和表达形式的挣扎和困惑中,也享受了一部部心灵之作的交 流快感,结构、本体、交响、人物、戏剧、本土、雅俗,现在谁还会去讨论这些曾经让 他们激动却又无比无聊的话题了呢?从精神的脱缰到物欲的困境,没有人在90年代后期 还去关心现实的生存和思想的快感,而是在于一部部超大型舞剧制作上比拼,曾经的理 想主义和对生命的尊严傲气,在大型的整合舞蹈当中,悄悄退场。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生猛的创作洪流,张继刚引领了一次煽情运动。在此之前的作 品,要么学院气十足,要么偏重教学的创作剧目,讲求技法,讲求气韵,人物塑造,空 间处理,场面调度,张继刚也是经历了学院教育,但却肆无忌惮地发泄情感,具有原始 野性,浓重的黄土地气息,集体无意识的开发,对原始唯美的一味追求,不厌其烦的赚 取观众的眼泪,对于故土乡民的生存关注,从《一个扭秧歌的人》民间艺人的内心跃动 和静寂,生存的心酸相忘于散发而歌的狂放之中,草根的精神暗合,获得了更多的观众 合认同。《献给俺爹娘》《黄河儿女情》的主题晚会,则以高浓度的渲情和思念来向观 众捧出乡愁和为大家不屑的“俗情”。百试不爽的金三角队列,穷竭力量和神经的递进 模式,个体与群体的强烈空间对比,成为90年代初期所有中国民间舞古典舞编导的崇拜 模式,忘情的呼喝,超出规范的动作,生命尊严的本能捍卫,群体的迷狂,同样成为其 他编者的情感表现追求。民间创作力量同时也通过张继刚直白情感表述,让人无处可藏 的真诚,获得了复兴的机会。几乎成为编导界的神话,张继刚还在别人开始追捧得时候 ,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讨论中,拓展了他的艺术“野心”,正如陈维亚等 主流人物,多方面的涉猎,音乐剧、歌剧、杂技、残疾人舞蹈、综合晚会,正在成为整 个表演艺术、视觉形体的参与和导向者。
丁伟是民间舞先锋者,紫色工作室的成立,一方面描摹了欧美现代舞的结构和动作形 态,另一方面逐渐走泛亚洲,东方情调,中国民间风情的整合和变形。《小河淌水》的 闲情,《清风》的日本调式和身韵开合。张守和则是学院现代舞的开拓者之一,《秋水 伊人》,《胜似激情》,《红旗颂》老派的现代舞编舞,在美国现代舞体系玛莎·格莱 姆的收缩放松当中,阳刚的气质,和革命情怀联系在一起。
陈维亚早期的《木兰归》《绿》技法和动作的练习,而真正影响中国古典舞坛90年代 末的独舞作品《秦俑魂》到四人舞《秦王点兵》,圆润流畅的古典舞运动倾向被棱角顿 挫的动作切割得耳目一新,大家突然注意到了动作质感的变化,曲线圆润,僵硬直线, 动势和质感的改变,作品本身就引来了无数的效仿。但这期间学院对于动作解构却没有 得到更多人的注意,动作连接的无形而又不着痕迹,古典动作的切分和粘稠也是实验之 中的。孙龙奎的人性力量和心灵结构则是在一片喧嚣当中,最为始终如一的纯粹和宗教 般的虔诚。他的《生命》动作结构、《图腾祭》的原始力量,都在舞蹈的灵化上继续着 单纯的信仰。
虽然这些作品之后,50年代末的编导都转向了舞剧的创作,这也代表创作的新标准, 以陈维亚《秦俑魂》自己的蜕变,也终结了90年代末“舞蹈作品”的繁荣和亢奋,终结 了大家对动作风格格外邪门专心的风潮,暂停了大家无限的对自己的东施效颦。重回了 舞剧作品的结构时期,整体的失去了对动作本身,对动作意义的关心,也失去了对当下 发生的知觉。如果说他们更倾向体验舞剧带来的编舞成就,却也无法不提其中的功利味 道和舞台艺术的整体覆盖。张继刚的《野斑马》,陈维亚的《大梦敦煌》丁伟的《玛勒 访天边》杨威的《红梅赞》赵明的《闪闪红星》,一些令人坐立不安的大型制作,铺天 盖地的占领了人们的视线,民族风情的展示,革命题材的重编,历史神话的演绎,只有 杨威重提了信念的话题,语气很快被冲淡,大家一起秀色可餐的愉悦了新时代的观众群 体。这种不安暗示了人们眼睛的渴望与心灵干涩的矛盾,商业化的炒作和包装,市场和 大众趣味的绝对势力,让伴舞以更精美的方式出现,这是对一个舞蹈世纪的礼物,还是 一个对20世纪初吴晓邦先生“为人生而舞”的一个反讽。
毕竟主流的内涵,由政治上的粘贴和认可,风格的影响程度已经暗转到了票房的标准 ,媒体宣传的认可度,以及操控大型演出的数量和质量。
杨威、赵明和陈惠芬王勇的作品,再次表明军队主流创作的事态。大型晚会的彰显, 大型舞剧的虚胖,几乎遮挡了所有60年代创作的声音光彩和曾有的诗意张力。张继刚的 《野斑马》和《献给俺爹娘》的对比,有人说张继刚作品的忘本和失去了深刻的感动, 从自诩农民舞蹈家到舞蹈的世纪新星,人性的深度早已沦丧为拉斯维加斯的秀场,但如 果我们脱离狭隘的本土意识和老套的表情模式,从情感的力度到讲究视觉的完善和华美 ,张继刚的自我更新速度的确实令他人所不及。
人性如今已经成为了幌子,谁还会为之感动呢?只是大家在急躁的忙于秀场的时候,舞 蹈已经被遗忘,成为了工具,而从身体的意义上飞离了。当一些物欲来得措手不及的时 候,旧瓶装新醋,赤裸的“拿来主义”成了他们的创作流水线。看不到当代人动作行为 的改变,便看不到舞蹈的方向和意义。理想的陨灭是否要靠无厘头和玩笑的散漫天真所 安慰,所代替,精神至上和渲情的尺度是否也要用泛化的关心和多元化的旨趣所置换, 我们还是缄默地好。泛化的一代,在90年代的中后期树立了一些宽容和随和的形象,而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逐渐为自己内力的化解所担忧,或是无谓着。动作实验性群体大 多数,也是首批大规模的以舞游历世界的进行流动群体,在力夺了国际比赛的金奖之后 ,依然能够执着于自在。提升了本土的动作精神追求,提升了沉睡的身体意识。虽然民 主化的身体观念,人人皆可舞的理想一支脚踏在了70年代人的边缘上,但人性已经象一 件紧身衣,令人有点尴尬的开放着。动作实验性群体都在现代和当代的名词中寻找青春 和再生能力,更换版本,生于60年代,生于70年代,生于80年代,都在寻找归属,标榜 ,区别,类群的不同趣味,间隔得越来越快。区别的必要,不是划清界限,而是善意的 提醒。不依赖于大型舞团,国家舞团的机制和演员,小型作坊的制作也将是这一代的多 数趋向。
独自的人格力量是他们的创作的灵魂,虽然有人失去了,有人坚持着用作品来说话, 但毕竟与下一代纯粹技术化、电子化,多媒体化的群体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在明确着自 己的生活态度,而不是艺术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