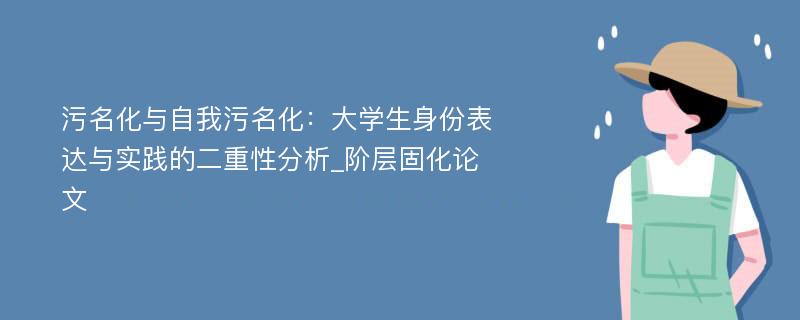
污名与自我污名:大学生身份表达与实践的二重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污名论文,身份论文,自我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屌丝”、“屌丝逆袭”、“高富帅”、“白富美”、“土豪”等是中国70后、80后青年自我解嘲、自我宽慰、自我戏谑的网络话语,虽然不雅,但作为一个隐喻,对于理解青年一代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理解中国特有的社会潮流和文化现象有特殊的社会学意义。这种污名文化所反映的集体认知,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折射,它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社会矛盾,因此对于污名及自我污名现象的文化理解与意义阐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现实;不理解话语,就不能理解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经历和我们自己”。① 理解与阐释的目的并不是为污名翻身,也不是为庸俗代言,而是理解和阐释污名话语和文化背后的社会逻辑,理解和阐释此种话语下个体、社会结构、他者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建构,发掘个人的文化理解和实践逻辑,有助于揭示当下中国各种“污名”背后权力关系与价值逻辑发生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实现不同阶层间真正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合,促进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 一、污名及自我污名的流行:新犬儒主义的文化表达 污名及自我污名文化的滥觞,以“屌丝”话语的产生为代表,2012年11月3日,“屌丝”一词登上《人民日报》十八大特刊,引发了网络和社会热议。在此之前,人们更习惯于用“草根”来作为底层人们的隐喻,然而,“屌丝”的产生将“草根”这种中性的表达污名化,并相应而生了“高富帅”、“白富美”、“土豪”等一系列污名词汇。董海军认为,网络话语建构下,“屌丝”主要用来描述在人力及经济等资源上相比参照群体不足的男性青年。其中,人力资源主要包括外形相貌、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等特质,经济资源主要是指财富的拥有状况。屌丝往往以在内质与外质资源上存在明显优势的“高富帅”群体为参照,并且他们往往自称弱者。比如屌丝往往使用“穷、臭、矮、矬”来描绘自己,在他们看来,爱情上只是“女神的备胎”;生活中是“奴才命”;未来发展上“永无翻身之日”。②总而言之,屌丝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李斌也认为这是“底层文化的言语表达”。③ 然而,这些词汇广泛流行后,其原意、适用群体、使用情境发生很大变化。比如,“屌丝”慢慢演变为一种社会性的自嘲,人们乐于品味小人物自己的故事,更爱看对“高富帅”的嘲讽。很多表面不符合屌丝定义的人,和屌丝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甚至“高富帅”们都在争相认领这一名号,比如作家韩寒,人气乐团五月天,球星李毅等。韩寒说,我是纯正的上海郊区农村“屌丝”;人气乐团五月天说,走下舞台我们就是“屌丝”;中国球星李毅说:“现如今的流行风尚改了,自嘲成为更高尚的生活方式,好像有返璞归真的意思,大家都不用活得那么虚伪。” 对于污名文化的理解,现有研究的定位主要包括反抗传统的青年网络亚文化,阿Q文化,解构文化,新犬儒主义,等等。 李超民认为,屌丝等话语的流行,是新型的网络亚文化,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网络语言文化,其边缘性、批判性、反抗性、开放性和娱乐性等都彰显了后现代社会文化特性……是青年反抗传统文化、彰显自身个性特点的工具。④他也指出,这种解构文化既有自暴自弃的颓废,也有蔑视主流的骨气。⑤王玉香也认为这是一种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与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⑥2012年,《新周刊》专门结集出版《屌丝传》来讨论这种社会学现象,并认为屌丝是一种新型的阿Q精神胜利法,“屌丝宁可貌似自我矮化的方式来接受现实,他们并非沉沦,而是以新的方式来取得跟社会、跟自己的和解”。程和祥认为“屌丝逆袭”只是阿Q似的自嘲、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⑦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新时期的犬儒主义。《现代性后果》里提到“犬儒主义指的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一直情绪上焦虑的模式”,⑧《新周刊》也称,“从历史线索来看,这是一种精神世界随遇而安的支流:你追名逐利,我自狂狷;你要做人上人,我安贫乐道;你有你的实力,我有我的精神胜利法;你追求崇高,我躲避崇高;你要你的成功,我要我的快乐……自称为屌丝的人,不是社会的负担,也不要博取任何通气,他们真实生活,也搜索各种正能量”。⑨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屌丝文化真的是“弱者”的武器么?很多强者也参与了它的建构和流行,“高富帅”们也常以“屌丝”自称。另外,污名文化真的是反叛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么?“逆袭”就是为了进入主流文化,可见,污名及自我污名文化比表面所表达的更加复杂。 二、自我污名文化的代表性群体:大学生成为新的底层来源 从各类污名词汇的产生来源和使用者来看,他们多是80后或者90后的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或是在校大学生。李斌认为,大学生是屌丝等污名文化的代表性群体,他们有认同其身体属性、心理属性、工作属性和群体属性消极面的倾向,愿意将自己归类于社会底层。不过到目前为止,大学生群体对“屌丝”及类似词汇所内含的各种属性还没有达成整体性认同,其认同区间值在30%~60%之间。 李斌认为,大学生也是现阶段中国新的底层来源。超过50%的大学生高度认同污名词汇使用者的底层社会特征,并认为社会底层可以通过自嘲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保护和认同,进而宣泄不满情绪,实现某种群体性的“狂欢”。这暗示着中国社会的底层已经将昔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纳入到其中,致使中国底层社会又有了新的来源。⑩ 笔者认同这个观点。刘云杉曾论及“寒门难出贵子”,“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尤其是城镇与农村的中国家庭,通过高等教育完成城市化的历程是制度为其留出的有限且安全的通道。扩招刺激了更多人的热望,大量新型学生及其非传统境遇的出现,是一个高等教育乃至全社会均需面对与承受的实践难题”。(11)与此相伴的是,“教育的筛选功能遭遇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文凭作为能力识别标志、身份识别符号以及市场交易符号,在不断膨胀中迅速贬值……穷孩子早已玩不起这场竞赛。然而,以前静态的社会金字塔结构已经变成一场动态的马拉松比赛,过去尚可待在底层,现在却要使出全身解数,投入奔跑。假如停下来,即意味着再也找不到位置,哪怕是最底层的位置”。(12) 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文化再生产指的是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一起使得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代代相传。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文化资本是某种形式的权力资本,文化资源,比如教育文凭,已经作为一种资本发挥作用,因而已经变成现代社会中新的、独特的分化根源,文化资本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然而,自称“屌丝”的大学生的家庭更多地集中于中下阶层,尤其是中国的劳工或农民家庭,其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稀缺,在中国城市化的大洗牌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其向上流动的过程越来越艰难,但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他们已难以认同乡土文化,用自嘲和反讽的“屌丝”文化最能表达他们的反抗情绪而又掩饰着他们的身份尴尬。 社会学家威利斯在《学做工》中也指出了这种现象,他认为,劳工子弟在部分地洞察主流文化时,也以反抗主流文化的形式选择自己的道路。劳工阶层子女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具有文化上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很难摆脱父辈的命运,继续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威利斯描述的英国劳工阶层子女的命运与当下“屌丝”大学生群体的状态非常相像。 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新来源,大学生成为自我污名文化的代表性群体并不奇怪,他们才是污名文化的真正消费者和传播者,但还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何接受了精英教育的大学生不选择一个更为雅致的词汇来自嘲,而要用如此低俗的字眼来自辱呢?大学生自我污名,是否代表他们就认同此污名?这需要深究污名文化的产生与流行原因。 三、自我污名文化何以产生:现代性与去经典化的社会认同 污名话语为何产生和流行?比较普遍的解释有社会阶层固化和贫富差异引发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庶民的社会认同,网络技术推波助澜以及大众流行文化具有独特价值。 李斌、程和祥、董海军均认为屌丝等污名词汇的产生是社会阶层固化和贫富差异引发的冲突。我国的社会结构逐渐定型,代际流动非公平与代内机会非公平日益显著,阶层之间的边界和藩篱日益清晰,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屌丝也就变成了弱者在困境中的呐喊。 张昱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在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情况下,人们往往通过将他者污名化来进行自我保护、身份区隔和群体标志,形成一种负向的自我防卫机制,致使泛污名化现象普遍出现。(13) 就前两者观点而言,污名文化是现代性的后果。社会学家吉登斯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现代性即城市化对城市本身兼具创造与破坏作用。一方面,城市化集中了人力、物资、服务与机遇,同时也分裂、削弱了地方传统和现存网络的完整性。与集中化和经济增长并存的是边缘化所造成的危险后果,使得发展中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大量城市居民处于边缘状态。这种状态威胁了人的本体性安全,让人产生本体性焦虑。(14)在这时,人们往往采取犬儒的应对方式,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抑制情绪上的焦虑。(15)这一点与前面所提到的新犬儒主义是相通的。 蔡润芳认为,这代表着庶民的社会认同,是社会对庶民编码、言论自由的尊重和自我心理上的某种共鸣。“屌丝”从线上走到线下,从名副其实的真屌丝到都市白领、高校学生的争相追认,体现的是一种主动或被动的用标签来给社会群体归类的过程,是社会人群互动后自我认同的产物。(16) 陆杨认为网络的去经典化特征对此推波助澜,以及大众流行文化独有价值,因为使污名话语广泛流行。他指出,网络社会里的消费行为与生俱来具有去经典化的特性。网络传播技术发展和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为全民“恶搞”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网民是自主的、独立的,可以占有网络传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自主地决定传播和接受信息的时间、地点、方法和内容;另一方面,网民的匿名性,使其摆脱了社会关系和社会习俗的控制和压制,表现出群体心理的感染性和夸张性以及群体行动的冲动、盲目,而做出一些违背社会伦理和挑战社会权威的事情。网络传播主体的匿名性,赋予了网民“恶搞”经典的勇气。 在传统大众媒介社会中,身处底层的人难以逾越阶层,轻易地观察到上层社会人民的生活状态,也难以对整个社会分化有着清晰的、深刻的认识。互联网社交媒体打破了这一形态,社交网络的开放性使整个社会的透明度急剧提升,社会分化清晰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时空的打破也激发出社会人心中的“公平”感,身份比较的范围也无限扩大。在大众传媒时代,外边的世界遥不可及,个人幸福感是在和同城、同村或同区的比较中建立起来的,而在社交媒体时代,整个世界紧密不可分,个人的幸福感再也不可能仅仅建立在狭小一隅,而是更彻底的以世界为单位的等级比较。“高富帅”与“屌丝”的二元对立格局就是在这互联网时代文化身份格局被打破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出来的产物。(17) 综上所述,污名及自我污名文化的产生机制主要包括现代性后果在中国的体现,网络文化的兴起和污名具有社会认同(分类、排斥)的心理、社会作用。不过,对污名及自我污名的现有研究对于以下方面的认识不足:一是未能揭示高学历群体采用低俗文化以自嘲的深层心理过程和逻辑;二是未能揭示不同社会结构之间产生了不同话语的深层逻辑;三是未能揭示个体对于污名词汇宣称的话语与行动之间的矛盾性或二重性。 四、自我污名与泛污名化:底层叙事与权力更迭 欧文·戈夫曼把污名定性为“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其本质是“由于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而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污名就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标签的人有一些为他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上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其产生不公正待遇”。(18)戈夫曼的定义可以用“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一词来形容:污名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侮辱同时意味着或直接带来后者利益的损害,久而久之,这种污名会自我内化,使被污名者产生类似自我认同,并固化利益的损害。 戈夫曼同时提出了自我污名的概念。自我污名是当公众污名产生之后随之伴随出现的自我低评价和自我低效能。即某一群体或个体在遭受公众污名贬损之后,在主观上产生的自卑感、自羞感和自责感。然而,从上文的综述可以看出,“屌丝”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自我污名有了新的特点: 首先,“屌丝”、“土豪”等污名不是自我对他人命名的内化,从其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是一种自我命名,被命名者也未必会认同这种污名,“身份表达”仅仅是话语假象。 其次,自我污名的人并不会产生羞愧、耻辱和犯罪感,有时还以此为乐,以敢于自我“侮辱”的“坦白”和“真实”为荣,这是戈夫曼当时的研究未能涵盖的。 再者,自我污名群体扩大化或者说泛化了,也就是说泛污名化。张昱指出,“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污名化现象亦不断增加与扩展,出现了个体自我或群体自我、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或自我赋予,或相互赋予负面的、嘲弄性的、侮辱性的标签和特性的现象,并由此导致了污名现象不断增多、污名对象不断泛化、污名内容逐渐多样、污名关系愈加交错复杂的污名化等新趋势。同时,社会大众在对这种泛污名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和强烈的同时,却存在受污者自身的心理感知相对弱化的趋向,进而影响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群体认同”,(19)也就是说,一是污名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改变,不完全是强者对弱者,从他人命名发展到自我污名;二是人们对极端自我污名的宽容度增加,被污名者感知度下降。 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该群体之上的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和另一方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他将污名化作为社会建构的中心,并把它描述成“一种特征与一种僵化教条观点的特殊关系”,它植根于一种语言关系,并且污名体现了事实的社会身份与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异质性。从屌丝一词的发展管窥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当下中国的污名现象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反映出泛污名化现象的增多及其背后权力关系的转变。 首先,污名从他人污名转变为自我污名,而且与戈夫曼的定义不同。屌丝是李毅吧粉丝的自我称谓,从产生之初便是一种自我命名,但与戈夫曼对于“自我污名”的定义不同,他们自我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在主观上产生自卑感、自羞感和自责感,反而是讽刺不劳而获的“高帅富”。屌丝们对以屌丝自称或是被他人称作屌丝看得很淡,他们知道自己出生卑微与平凡、生活平淡无奇、平淡无光的现状,知道自己身份低微、生活平庸的现状,但不抱怨,丝毫没有以此控诉社会的意思。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污名者与被污名者话语权力关系的转变——单向度污名化变为双向度污名化或反向度污名化,并具有底层叙事道德倾向。陶鹏也指出,在传统的污名现象中,社会优势群体通常是污名化现象的制造者,社会弱势群体则是污名化的被动接受者,社会优势群体借此来表达对某些特定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然而虚拟社会完全颠覆了传统污名现象中的二元权力结构,原本被固化的污名关系得以重新建构。大众阶层作为现实社会中遭遇污名体验的弱势群体,现在成了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制造者,现实中的权威阶层、精英阶层反而经常成为虚拟社会污名现象的被标签化群体,在虚拟公共领域里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大众阶层采用戏谑化的方式制造污名,使用“公务猿”(公务员)、“砖家”(专家)、“叫兽”(教授)、“妓者”(记者)、“呕像”(偶像)等网络词汇指称某些现实社会中的特定优势群体,一些特殊群体也被赋予了“富二代”、“官二代”等带有人格贬损意涵的标签。许多虚拟社会污名现象产生之初,就已经预设了支持底层大众诉求和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倾向性前提,并且存在非常明显的底层叙事道德倾向。(20) 五、结论:自我污名文化表达与实践的二重性分析 黄宗智在《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了“表达”与“实践”的著名概念。他认为,“表达”(representation)是对事实的描述,可能符合真相也可能与之相背离……在现实中,表达与实践往往是相悖的。(21)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自嘲为“屌丝”,但内心并不认为自己是屌丝。对“屌丝”身份的表达并不意味着“屌丝身份”的实践。相反,还可能出现“去屌丝化”符号的实践,在消费、仪表、服饰、生活习惯及思想观念方面向“高富帅”、“白富美”靠近。 笔者访谈了一名北京高校的大学生林夕,他自称“屌丝”只是无奈——自己确实没有背景、出身草根,是农民的儿子;但他考大学,读博士等一系列选择都是为了“逆袭”,为了“去屌丝化”,成为“高富帅”群体的一员。最为明显的是他的穿衣打扮和消费方式,“平常省吃俭用买衣服、买鞋都会时尚一点,贵一点,不用多,要有一两件表示身份的衣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虽然他看不惯很多北京人歧视外地人的行为,但仍然想有个“北京户口”,成为真正的北京人。不过他也认为,他虽然有“屌丝”身份——农民的儿子,而且人离乡贱,但走到哪里心不会变——像“屌丝”二字赤裸裸的低俗表达一样实在、真诚。尽管林夕以红楼梦中晴雯的“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自比,但他却不甘心与晴雯拥有一样的悲惨命运,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而且他认为“付出和回报虽不相当,但肯定是呈正相关的,在这个信仰丧失、道德沦丧、举世浮躁的年代,我们不缺少思接千里、眼界开阔、无所不知的思考者和聒噪者,缺乏的是一根筋的许三多式的执著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坚持到底,不忘初衷,咬定牙关不放松”,可见“屌丝”的自嘲却仍带着草根特有的“春风吹又生”的坚韧和“屌丝逆袭”特有的对未来的信心与乐观。一方面是自嘲、自贬,一方面又憧憬、向往,林夕对“屌丝”的身份表达与“去屌丝化”的实践有重合,也有背离,具有二重性、复杂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污名及自我污名文化在大学生中间的流行带有复杂性特征,主要体现在: 首先,污名词汇背后有多重的“发声者”,作为一种污名,其背后有多重动机和多重权力关系,在这种话语体系里,不仅“屌丝”是污名,其对立面“高富帅”、“白富美”也是一种污名,因为就屌丝产生的互动机制而言,并非为赞美对方而产生。 其次,自我污名并不代表污名认同,这与戈夫曼的研究有所不同,“屌丝”、“高富帅”等词汇的身份表达与话语实践之间存在分裂与统一,这种“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并非是人性虚伪的体现,而是人类在现代化浪潮中被异化又反抗被异化的矛盾性写照和冲突性表达,本质上是在文化冲突中消除身份认同焦虑的文化适应过程。 最后,自我污名是个体与社会结构、他者互动的产物。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之所以能认识万物,是因为人一向融于世间万物之中,一向生活于、实践于世界万物之中”。(22)大学生污名自我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社会关系,改变了社会结构,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 注释: ①詹全旺:《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建构主义认识论》,《外语学刊》,2006年第2期。 ②董海军、史昱锋:《青年代际流动与代内机会非公平》,《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 ③⑩李斌、汤秋芬:《走近“屌丝”——大学生底层化表达》,《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 ④李超民、李礼:《“屌丝”现象的后现代话语检视》,《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 ⑤李超民:《大学生“屌丝”现象的兴起与应对策略》,《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9期。 ⑥王玉香:《新媒体时代透视青少年“屌丝”文化现象》,《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9期。 ⑦程和祥:《新阿Q精神:屌丝逆袭》,《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6期。 ⑧(15)(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120页。 ⑨新周刊杂志社编:《屌丝传》,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1)刘云杉:《培育双重资本,应对奥德赛期》,《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9期。 (12)刘云杉:《寒门难出贵子: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双重困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7日B01版。 (13)(19)张昱、杨彩云:《泛污名化: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表征》,《河北学刊》,2013年第3期。 (14)(英)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页。 (16)蔡润芳:《屌丝的逆袭史——网络亚文化传播管窥》,《今传媒》,2013年第9期。 (17)陆扬、张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316页。 (18)(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0页。 (20)陶鹏:《公众污名、自我污名和媒介污名》,《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1)黄宗智:《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页。 (22)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