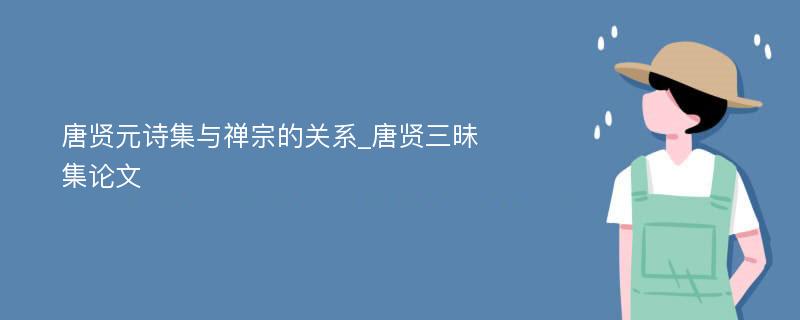
《唐贤三昧集》与诗、禅的分合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合论文,关系论文,唐贤三昧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唐贤三昧集》的成书情况
《唐贤三昧集》是清人王士甪(字阮亭,号渔洋,1634 —1711 )编辑的一部颇具特色的唐诗选集。其自序云:
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妙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合《文粹》、《英灵》、《间气》诸选诗,通为唐诗十选云。不录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张曲江开盛唐之始,韦苏州殿盛唐之终,皆不录者,已入予《五言选》诗,故不重出也。康熙二十七年七夕后学士禛阮亭书。
从这篇自序可知,本书是王渔洋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春杪”至“七夕”间编辑的,仅用了一、二个月时间,话说得似乎十分轻巧。而事实上,此书决非率尔操觚之作,在这之前的酝酿,以及此后的校订,前后延续的时间竟达十年之久。据徐乾学《〈十种唐诗选〉书后》,早在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孟秋,在王黄湄(又旦)、汪季甪(懋麟)、陈说岩(廷敬)、徐乾学及王渔洋五人的文酒会上,众人即向渔洋有“仿锺嵘《诗品》、抒山《诗式》之意,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之请,渔洋“笑而颔之”。这是此事之缘起。而渔洋门人盛符升《〈十种唐诗选〉序》,又有“壬申春,我师渔洋先生以《唐贤三昧集》垂示,因受而雠校之。集成,读者靡不叹其神简”云云,则直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昧集》始校定。从康熙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这数年间的搁置,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等待校雠,编者必苦心斟酌,有所增删改订。徐乾学于康熙三十一年就全书之成回顾云:“今新城先生选定《唐贤三昧集》,又选刻十种唐诗,余畴昔昌言,可以晓然共喻。回思城南之会,荏苒遂已十年。”(《〈十种唐诗选〉书后》)十年光阴,磨砺一书。如此郑重审慎,是因为这一部诗选在渔洋心目中占据着极大的比重。他晚年总述一生的诗风变化,便特为提到本编:
吾老矣。还念平生,论诗凡屡变;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随影,忽不知其转移也。少年初筮仕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选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此老矣。(引自俞兆晟《渔洋诗话序》)
指出《三昧集》的选编,是被当作一生出唐入宋之后的一个总结对待的,可见其重视的程度(注:徐乾学《〈十种唐诗选〉书后》尝记与汪懋麟争论渔洋诗学宗唐抑或宗宋的指向,汪氏认为以宗宋为主,徐氏则力辩以宗唐为主,终不如渔洋本人的上述之言圆通。)。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亦有本编“乃其生平宗旨所在,去取较为精密”的评价(《〈十种唐诗选〉提要》)。本人的重视与历史的优评,也应该是上述精心磨砺之编选过程的一个旁证。
又渔洋在另一部笔记《居易录》中曾提到,他少时尝与兄士禄编有《唐诗七言律神韵集》,后为人改窜,已非其旧。故渔洋五十五岁以后,用数年时间着手重编而成《三昧集》,也并非仅如上述徐乾学所言,纯为受人托请之举。如果扩大一步看,此举也可说是在实现其贯穿一生的一个志趣,而至晚年终成定论。
在编选改订《三昧集》的过程中,渔洋同时还集中删订了唐人所选之唐诗总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国秀集》、《箧中集》、《搜玉集》、《御览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及宋人姚铉之《唐文粹》,共十种,其“去取一以神韵为宗,犹其本法”(《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四《〈十种唐诗选〉提要》)。由于体例和宗旨相同,《唐贤三昧集》最初即与这十种唐诗选本合刊。
晚年的王渔洋,通过这一批唐诗选本的整理,较为突出地宣示了自己的论诗旨趣(注:渔洋逝世前三年还删订了宋人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齐鲁书社1995年校注本),亦是此种旨趣的沿续。)。其中尤以《三昧集》的编辑,由于完全出乎己手,比之前人已有选本的二度删改,自然更能体现本人的诗观,所以更加受到重视,后人颇有抽出别行者。除四库全书本外,乾隆五十二年(1787)听雨斋刊行过吴煊、胡棠的笺注本;光绪九年(1883)翰墨园又予以重刊,并朱墨增印入黄培芳嘉庆十年(1805)之批点文字。此外,本书之后,又有史承豫辑《唐贤小三昧集》,周咏堂复辑有《唐贤小三昧集续集》,本渔洋之旨,接着盛唐选录中唐以下诗人。两种均未刊,虽然本身的影响不大,但却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王渔洋《三昧集》的影响。
渔洋自序谓本书收盛唐王右丞以下42人,今听雨斋本、翰墨园重刊本则为43人,四库全书本又增为44人(较听雨斋本等多出最末之万齐融),微有出入,未知出于渔洋本人改订,抑或门生后人编辑之所为。本文据四库全书本,此本收诗凡404题、415首。
二、《三昧集》与渔洋诗论的“禅味”
如上所述,《三昧集》既是渔洋晚年作为本人诗学的一个总结而加以精心编辑的,那么它的主要旨趣是什么呢?从题名来看,是禅趣。初刊本载有渔洋门人盛符升、王立极两篇后序,其中王氏之后序解释集名,即云:
昔人谓释言三昧,犹夫道言贞一,儒言致一。盖一即有二,因至于三,言三即昧在其间。大要得其神而遗其形,留其韵而忘其迹,非声色臭味之可寻,语言文字之可求也。
按唐释道宣《广弘明集》,载晋释慧远《念佛三昧集序》及王齐之《念佛三昧诗》四首。王氏后序所释“三昧”之义即通于此;而本书题名的来由,亦可上溯于此。再从上述自序引用严沧浪与司空图之语来看,对此也表示得很明白,尤其是沧浪之语,已是直接以禅语说诗。而在另外的场合,渔洋也往往运用禅语,来说明《三昧集》的宗旨。如其《居易录》记载:“《林间录》载洞山语云: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予尝举似学诗者。门人彭太史直上(始抟)来,问予选《唐贤三昧集》之旨,因引洞山前语语之。”“语中无语”者,即严沧浪、司空表圣前二语的禅译。又如刘太勤《师友诗传续录》载:“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之矣。”这一些自白,都可以见出本书编者主观上欲以诗通于禅的自觉程度。
如所周知,渔洋诗学标举“神韵”。这是一个中国传统诗学语汇中与禅学最为亲近的名辞。在这一点上,他与有清一代的“格调”、“性灵”、“肌理”等说都大为不同。在他晚年所作的几种笔记中,谈诗往往必连带及禅,禅锋甚健,以致远过于他的以禅喻诗的前辈严羽。例如,他认为诗与禅是一回事:“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香祖笔记》)学诗、作诗的方法也等同于参禅的方法:“石门聪禅师谓达观昙颍禅师曰:此事如人学书,点画可效者工,否者拙。何以故?未忘法耳。如有法执,故自为断续。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此道人语,亦吾辈作诗文真诀”(《居易录》);“佛印元禅师谓众曰:昔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其语,见即骂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时稗贩我去!’学者渔猎语言文字,正如吹网欲满,非愚即狂。吾辈作诗文,最忌稗贩,所谓‘汝口不用,反记吾语’者也。”(《居易录》)而诗也直接成为解禅的教科书了:“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香祖笔记》);“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廉,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昚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蚕尾续文》);“象耳袁觉禅师尝云:‘东坡云: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芦雁,坐我萧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傍人云是丹青。此禅髓也。’予谓不惟坡、谷,唐人如王摩诘、孟浩然、刘昚虚、常建、王昌龄诸人之诗,皆可语禅。”(《居易录》)诸如此类热衷的话头,渔洋集中俯拾皆是。显而易见,渔洋晚年是以禅宗的理趣乃至语言作为主要的材料之一(另一种材料是所谓“南宗画”的理论)来构筑自己的诗学的。他着意将《唐贤三昧集》编成一部解禅的“教科书”,也正是此意。
王渔洋作为诗人兼诗学家,有“一代正宗”的美誉。从同时代的徐乾学到清季的李慈铭,对渔洋其人其诗的“国朝正宗”、“诗人之诗”的地位,评价基本维持如一。这样一位诗人及诗学家,一方面对于诗禅相通之理作出了颇为系统的论述,一方面又通过编选盛唐诗人之诗予以昭示,这不仅充分表明了渔洋对于他本人的诗禅合一之诗学的信心,同时也颇具权威地加强了“诗禅相通”作为中国诗学的一个普遍原理的可信度。尤其是这一部《唐贤三昧集》,由于出自他的精心结缀,又由于诗论与诗创作的非同一性原理,使之颇为难得地具备了可以从终端(作品)检验“诗禅相通”之说的特殊的、典型的意义。
三、《三昧集》入选诗人分析:“诗佛”王维独占鳌头
《唐贤三昧集》以“盛唐”作为选辑的时间范围。从严羽《沧浪诗话》、高棅《唐诗品汇》以来的划分,“盛唐”期大约指明皇开元至代宗大历初的这一时段(注: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岁至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岁,凡95年。盛唐自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岁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岁,凡53年。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70年。晚唐自文宗开成元年丙辰岁至哀帝天祐三年丙寅岁,凡71年。溯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帝末年丙寅,总计289年,分为四唐。”(载《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划分。而渔洋自序对此的划定,以诗人为具体标志,其起迄为“张曲江开盛唐之始,韦苏州殿盛唐之终”。由于唐人行年颇有无从确考者,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考定的可援以为据的唐代诗人系年表。姑且据《全唐诗》的排列,比勘本书所收的人物。《三昧集》所收的丁仙芝在《全唐诗》中排列最早,然踞渔洋指为标志的张九龄晚出209位; 《三昧集》所收的沈千运在《全唐诗》中排列最晚,较渔洋指出的标志性人物韦应物晚出132人。这样, 由于渔洋不收张九龄,《全唐诗》对应于《唐贤三昧集》的范围,即从丁仙芝到沈千运的诗人数是227位。《三昧集》中入选的44位诗人, 约占这个同期诗人大致之数的五分之一强。
在这一个范围中,最为显眼的是刘长卿、李白、韦应物、杜甫四家的落选。渔洋自序特为说明不选李、杜、张(九龄)、韦的理由:“不录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张、韦“皆不录者,已入予五言选诗,故不重出也。”这两个理由,前一个显得较为勉强,所以渔洋的弟子当年对此也颇致疑窦(注: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载刘问:“《唐贤三昧集》所以不登李杜,原序中亦有说,究未了然。”(载《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然其师之回答老调重谈,仍无进一步之说明。),盖渔洋对于旧题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实并未见赏,他曾购得王荆公的这一部《唐百家诗选》,“意欲有所论正”(尤侗《十种唐诗选序》)。而从他的《蚕尾续文》、《香祖笔记》、《渔洋诗话》、《分甘余话》诸种笔记看,他所作的“论正”,便是反复讥诋《百家》选旨,绝无恕辞。所以不选李、杜,这里不过是随手拈来的搪塞之辞而已,不必当真,而真正的原因仍未说出。后一个理由则大抵信实,他的《五言诗选》,于唐人选了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等五家,张、韦两家诗风与王维近(注:张九龄、王维、韦应物之间诗风的关系,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九有云:“张子寿首创清谈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清谈,而益以风神者也。”),既入彼,则不必再入此。历来以为上述两点是渔洋为自己偏嗜王维、孟浩然一路冲淡悠远风格所设的遁辞,似不尽然。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论。至于不选刘长卿,可能是嫌其“思锐才窄”,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这一评价,删订此集的渔洋想来是熟悉并首肯的。
渔洋删存而入《三昧集》的44位作家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按照各家入选作品数目的多寡,约可分为四个层次。王维诗112首, 孟浩然诗48首,分列第一、二。然而,第一、二位之间,竟有超过倍数的悬殊,并不能够归为一个层次(注:渔洋对王、孟之间的差别明确有云:“譬之释氏,王是佛语,孟是菩萨语。孟诗有寒俭之态,不及王诗天然而工。惟五古不可优劣。”(刘太勤《师友诗传续录》)。);而孟浩然与第三位的岑参(38首)、第四位的李颀(36首)、第五位的王昌龄(33首)则十分接近,可划为一个层次;第六位的高适(18首),以及裴迪、常建、储光羲、祖咏、崔颢、刘甪虚、崔国辅、陶翰、贾至等10首上下者,属于一个层次;其馀只有数首乃至1、2首的各家,归入一个层次。四档之中,王维一人独占鳌头,他入选的作品数,竟然占到全书415首总数的四分之一强;而另一方面,末档中只录1、2 首的作家就有20位之多。这样一种极端的比例“失调”,在历来的总集性质的选本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从而形成为《三昧集》的又一个特点。
《三昧集》的入选诗人编列,也如同入选作品的数量一样,以王维为绝对的中心。卷上收录的9位诗人,王维列首位,其他8位都与王维有着直接的关系:顺次而下,王缙系其胞弟,裴迪系其密友,崔兴宗系其内弟,为人所共知(注: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卷十六即以此四人为一卷,按王、王、裴、崔的次序排列。渔洋或本于此。);再次而下的储光羲、丘为、祖咏、卢象、殷遥,史载与王维亦均有交往。卷中亦收入9位,孟浩然列首位, 他与王维的诗友关系更是千载之佳话,王昌龄、李颀、綦母潜与王维也有交往,刘甪虚、张子容则与孟浩然有交往。而卷下所载的26位诗人,除薛据、贾至两位外,其他都还未见有史料表明他们与王维有过直接间接的个人关系。这样一种与王维由“亲”而“疏”的分卷编排方式,难道不是编者有心为之的吗?退一步而言,即使是无心所致的自然之结果,也同样可以说明编者心目之中的“王维中心”意识。王维“笃志奉佛”(《新唐书·本传》),在有唐一代诗人中独拥“诗佛”之尊号。确立他在本书的中心位置,与本书标榜的诗禅互通的宗旨是统一的。
欲在盛唐这一时间段中确立王维的中心位置,时至清代的王渔洋,必须妥善处置李、杜两位大家,他已不能如唐人选唐诗那样的无视李、杜,所以才不得不在自序中作那一番辞不达意的交代。但是他还是断然地不选李杜,应该说,这是保证突出王维中心位置的唯一手段,舍此别无它途。这才是《三昧集》不选李杜的真正原因。
《三昧集》不选李杜,但却又较为丰裕地选了岑参、李颀、王昌龄与高适等四家,紧随于王、孟其后。其中王昌龄诗“绪密而思清”(《新唐书·本传》),李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河岳英灵集》评语),李颀为人且“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唐才子传》),与王维甚近,两人且与王维都有交往,可以不论。而诗风不同的高适、岑参在书中占据较醒目的位置,是否可以看作是不选李杜的一种变通乃至弥补呢?尤其高适,与李杜交往甚密,三人曾“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三人间唱和致意之作甚多,集中现存者斑斑可见。高适与杜甫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两人的晚年。岑参诗风“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激。”(《沧浪诗话·诗评》)(注:渔洋则认为高、岑诗风不同,他曾回答弟子之问云:“唐人齐名如沈宋、王孟、钱刘、元白、皮陆,皆约略相似,惟李、杜、高、岑迥别。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锺伯敬谓高、岑诗如出一手,大谬矣。”(《师友诗传续录》)其评较前人为精,但并不影响本文立论。)高、岑之诗在《三昧集》中的赫然存在,再加上高适十分赞赏的沈千运(注:高适《赠别沈四逸士》:“沈侯未可测,其况信浮沉。十载常独坐,几人知此心。乘舟蹈沧海,买剑投黄金。世务不足烦,有田西山岑。我来遇知己,遂得开清襟。何意阃阈间,沛然江海深。疾风扫秋树,濮上多鸣砧。耿耿尊酒前,联言飞愁音。平生重离别,感激对孤琴。”)、诗体“祖述沈千运”(《中兴间气集》评语)而与杜甫亦多酬唱的孟云卿,以及“性梗僻,深憎薄俗,有忧道悯世之心”(《唐才子传》)而深见赏于杜甫、又交厚于孟云卿的元结(注:元结在道州时曾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杜甫后作《同元使君舂陵行》,小序深赞云:“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诗亦赞云:“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元结与孟云卿的交谊,从其《送孟校书往南海》诗序可见出,序云:“平昌孟云卿与元次山同州里,以词学相友,几二十年。次山今罢守舂陵,云卿始典校芸阁。於戏!材业次山不如云卿,词赋次山不如云聊,通和次山不如云卿,在次山又诩然求进者也。谁言时命,吾欲听之。次山今且未老,云卿少次山六七岁;云卿声名满天下,知己在朝廷,及次山之年,云卿何事不可至?勿随长风,乘兴蹈海;勿爱罗浮,往而不归。南海幕府有乐安任鸿,与次山最旧,请任公为次山一白府主,趣资装云卿使北归,慎勿令徘徊海上。”殷殷叮咛,一往情深。),诸人似可合成一个“亚杜甫”,而足与王孟存异。
这样,《三昧集》的入选诗人,便被精心结撰成一个既以王维为中心,而又不废李杜的体系。这样一个诗人体系,对于本书“诗禅相通”的旨趣,乃至扩而及于作为一般原理的“诗禅相通”之说,实际上表示的是一种既首肯而又有所保留的立场。
四、《三昧集》入选作品题材的现实性及其通向禅悦的可能性
分析入选集中的“四百余首作品的表现题材,约可归纳为赠别怀人、田园闲居、山水旅次、边塞军猎、咏物怀古、寺院禅师等六类,尚有一些作品难以遽然归入某一类。
在这些题材类别中,寺院禅师类直指禅之世界,应该与本书宗旨最为相惬。例如:孟浩然《寻香山湛上人》描写山寺环境与僧人生活:“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野老朝入田,山僧暮归寺”;《题大禹寺义公房》描写僧房环境并推想主人之功:“义公习禅处,结构依空林”,“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常建《题破山寺后院》描绘出古寺禅房的幽寂:“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李颀《题璇公山池》想象山池亦具禅功:“片石孤峰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指挥如意天花落,坐卧闲房春草深。”岑参《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记述了“山阴老僧解楞伽,颍阳归客远相过”的逸事。而崔国辅《宿法华寺》、陶翰《宿天竺寺》、崔曙《宿大通和尚塔赠如上人兼呈常孙二山人》等诗写各自过宿寺院的体验,以崔国辅一诗写得最好:“松雨时复滴,寺门清且凉。此心竟谁证?回憩支公床。壁画感灵迹,龛经传异香。独游寄象外,忽忽归南昌。”王维诗中更有直写禅法的句子:“一施传心法,唯将戒定还”(《同崔兴宗送衡岳瑗公南归》)、“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如此等等。
但这一类直奔禅旨的作品入选数量反而出奇的少,总共才只有32首而已,较之最不惬禅理的边塞军猎类的39首还少7首, 是数量最少的一类。编者取舍时,甚至有意不选禅题材的作品。《王右丞集》中,以寺院僧人为题的作品约有近30首,而《三昧集》仅选了7首。不仅如此, 在禅题材的作品中,越是直接地表达禅理,似乎越不易得到渔洋的青睐。如王维有为“胡居士”所作的诗四首,《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等三首直接谈论佛理,未能入选;而一般怀人的一首《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却赫然在选。这里似又显示出诗、禅相通原理的一道限制。可见,渔洋并不认为禅旨的表现必然对应于禅的题材。
事实上,《三昧集》的禅旨,同时亦由现实题材的作品表现出来。而且由于这些作品在数量上的优势,甚至构成了反映《三昧集》禅趣宗旨的主要成分。赠别类、田园类、山水类中,带有禅意的作品更为集中一些。像被渔洋许为最得禅意的王维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等句,便分别是《山居秋暝》、《终南别业》、《秋夜独坐》之类现实题材作品中的句子。
现实题材的作品也能表现禅意禅趣,这与由道信、弘忍创立的中国佛教——禅宗专注于介入现世生活的性质有关。与西方宗教、印度佛教严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不同,禅宗主张当下即佛,只要把持住本心,在任何生活环境中都可以成佛。所谓“佛性在烦恼之中,佛身即众生之体,大法平等,无所不同”(李华《润州天乡寺大德云禅师碑》);“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楞伽师资记·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这就抹去了难以企及的彼岸世界的神圣性,泯灭了两个世界间的界限,将教义的重心完全落在了此岸世界。这是中国宗教思想与信仰的基本特点之一。这样,禅宗关注的范畴便与诗创作的题材大致达到了同一,即同一于现世生活及心的自由。到盛唐时,禅宗更已经发展到慧能、神会分出南、北宗,并以南宗压倒北宗的阶段,由众生本心通向佛界的途径变得更加便捷了。人在随时随地、一举一动中皆可悟禅。像上述王维所临的“山居”、“独坐”之处境,“秋夜”之时刻,由禅悟便极易进入宗教的境界。而西洋虽也有“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真僧侣亦必有诗人心”之类诗与宗教相通之说(诺瓦利斯《碎金集》,转引自钱锺书《谈艺录》),但西方的宗教诗数量并不多,这可能与西方宗教重视上帝所在的彼岸世界,从而大大限制了诗创作的题材范畴有关(据HelenGardner《宗教诗歌》中译本相关论述)。
《三昧集》通过不选李杜、以及入选作品的比例安排等极具用心之举(注:实际上杜甫与禅的关系亦很深,参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三章。但杜甫主要以儒家思想立身,《三昧集》不选他的禅的成分,显示出渔洋从本质上把握诗人的眼识。),将“王维是盛唐最得现实生活之禅意的诗人”这一结论建立起来,是颇为精当而且合于史实的。对于所选王维之诗,渔洋同样颇费思量。入选的王诗题材主要是“赠别”与“田园”两类,这也是《三昧集》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两类。一般而言,这两种场合最易兴发人生如幻与世事兴衰轮替之念,参透佛家无常之义谛。如王维与裴迪唱和的《辋川集》组诗,是成功表达田园生活中的禅悦的名诗。作者饶有兴致地拉了“道友”(小序语)裴迪一起,精微地刻画了自己生活其间的辋川别业的全景,并网罩般地随处融入了由园居生活启迪而获的禅悟。原唱20首,渔洋从中选入15首,几近于全选;裴迪的20首和诗,也选了11首之多。这是各家选本中入选数量最多的(注:连陈贻焮《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亦只选了12首。),大致保持了这一组诗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不仅如历来认识到的只是地理方面的(20个景点),而且更是诗的与禅的(注:关于王维《辋川集》组诗的诗与禅的整体性,近来陈允吉先生论述颇为精详。可参其《〈孟城坳〉佛理发微》、《〈华子冈〉诗与佛家“飞鸟喻”》等文。),又是由王、裴两人合成的(注:例如对于王裴唱和,渔洋便不同意历来扬王抑裴之论,其《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云:“盛唐王裴辋川唱和,工力悉敌。刘须溪有意抑裴,谬论也。”所以《三味集》入选的裴迪和诗数量与王诗相近。)。若拆零而论,或扬王抑裴,其诗味与禅味必大有所损。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只选了王诗四首(裴诗一首未选),以致组诗变异成了单首之诗,禅悟也随之淡化为“达人之想”(《唐诗别裁集》评语)。而渔洋之选不惜篇幅,力图保持原作的整体性,说明他确实敏感于王维为代表的盛唐诗的那一份禅味。
从现实题材传达出禅的意蕴,加上禅题材那一部分,使《三昧集》建立起优游不迫的基调。但另一方面,有相当数量的题材及作品的意蕴,则又并不是指向禅悦的。如边塞军猎类作品普遍具有的那种苍劲爽朗的性质,最为明显地不易通于禅。同样以王维为例,他的边塞题材的名作《陇头吟》、《老将行》、《使至塞上》、《出塞作》,以及带有边塞气息的《夷门歌》、《少年行》(两首)、《观猎》,都赫然在选。他的属于赠别类的《送平澹然判官》、《送刘司直赴安西》、《送元二使安西》、《送韦评事》等作,被送者的边塞之归使他开怀唱出的爽直之声,成为本书赠别诗中的别调。其中“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以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等句,更是成为涵盖盛唐人送别怀人之情的经典之句;咏物类中的《相思》:“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也成为青春男女表达爱情的最为美好的语言……这些诗篇表达的都是尘世之情趣,是“禅”的趣味所无法牢笼的。
类似王维的情形,王昌龄、李颀、常建、王之涣、陶翰等家也多有存在;而对于高适、岑参这两位本来即以边塞题材擅胜的诗人,以及元结、孟云卿等人,渔洋之选能够一如其原貌,以致如元结《贼退示官吏》一诗,亦得以入选。正如黄培芳就此诗所批:“真朴恻怛,如读变《风》、《小雅》。可知此选浑成者即收,其实不名一格。世以幽淡之作即目为渔洋三昧,何曾窥见!”事实上,渔洋本人对此曾经一再以“闲远中沉著痛快”(《居易录》),“沉著痛快,非唯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谢、王、孟而下莫不有之”(《蚕尾文》)解释之,有意识地试图打通“王孟”与“李杜”之间的间隔,或曰扩王孟而使之与李杜齐肩。这也是他出入唐宋以后才能有的较为开阔的认识。上述《三昧集》在优游不迫的基调中嵌入沉著痛快的别调,正是这一认识的一次认真的实践。渔洋选定的王维,本是盛唐时代的艺术全才,作为盛唐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风也确是多方面的(注:王维诗风的全面性,林庚先生有精辟详尽的论述,可参其《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文学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著作。)。他的诗歌风格的丰富性,也正是盛唐诗歌风格丰富性的反映。《三昧集》之选,大致包括了他的所有最好的诗作,渔洋的识力确实不俗。但是正如钱钟书论定的,李杜与王孟诗题诗风的大小区别,在中国诗史上又是一个难以抹去的客观的存在(注:参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载《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又钱氏曾驳渔洋此说:“沧浪独以神韵许李杜,渔洋号为师法沧浪,乃仅知有王韦。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盖尽失沧浪之意矣。故《居易录》自记闻王原祁论南宗画,不解闲远中何以有沉著痛快;至《蚕尾文》为王芝廛作诗序,始敷衍其说,以为沉著痛快,非特李、杜、昌黎有之,陶、谢、王、孟莫不有。然而知淡远中有沉著痛快,尚不知沉著痛快中之有远神淡味,其识力仍去沧浪一尘也。”(《谈艺录》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如此,则“禅”的题材虽在盛唐诗人手上得到了充分的开掘与表现(中唐直至北宋仍相延不绝),却仍然不是“诗”的全部题材。这是诗、禅相通的又一道阻隔。
五、“三昧”之旨的结穴处在诗的言意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三昧集》在入选诗人、诗作题材及趣味等方面,渔洋都是既以禅为旨,实际上又都无法无所保留。那么,他在《三昧集》自序中最直言不讳地用禅于诗的一个方面,即“诗法”的方面,情形又如何呢?
前引渔洋自述《三昧集》宗旨,所言均直接落在诗歌语言表达意蕴的方式上,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味在酸咸之外”、“语中无语”种种说法,都是渔洋认定的诗歌言、意表达关系的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换言之,即要求赠别怀人、田园闲居、山水旅次、咏物怀古、边塞军猎、寺院僧人等一切题材中,不仅均应有寄托之深意在,而且必须实写题材,虚写寓意,造成一种言简意远、意在言外的传达效果。这是造成“优游不迫”风格的基本的手法。如王维的《送别》诗:“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前四句一问一答,直来直去;末二句又像是第一人称的答语,又象是第三人称的叙述,在字面上维持住了全诗的直朴的问答形式,但末句却如神来之笔,用“无尽”的“白云”将此君归卧的南山之陲缭绕起来,顿时令人遐想翩翩。再如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远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坐闻钟。”也是实写旅次,末句用悠远无定的钟声,将诗人的尘外之想传达开来。两首诗的成功原因当然不尽于此,例如诗中所用的各个物象都十分地好;但将形迹无定的白云、钟声放在诗尾,确实决定性地延续了诗的余味。纵观入选本集的各家、各类作品,体现此种趣味的典范之作数量甚多,故本集的与禅相通之处,可谓主要即通在禅宗的“不立文字”这一点上。而渔洋“神韵说”的旨趣所在,本也主要在这一点上。
不立文字,言外见意,此义若就诗学原理的层次言,实际上隶属于诗的形象性原则,是对于诗的形象性要求的坚持,即诗只须提供物象,讲述事由,其蕴含之意义则不必形诸文字,直接道出。由于这一要求的重点被放在言外见意之“意”的无迹象可求上,因而对于入诗的物象、事象的选择、锤炼,要求反而更高,只有极其精微的物、事之象,才能将所含之意传达得悠远。这一积极的创作现象在盛唐诗中已经成熟,其中尤以王维为代表。中晚唐的诗论家们如皎然、司空图等已经注意于此,南宋末严羽又作出了总结;至清初,王渔洋通过《三昧集》,将这一总结作得更加具体精致。如渔洋的宗王维(非“王孟”),若仅就这一旨趣而言,便较沧浪的宗李杜显得更相契合。
主要借助于禅理禅语建立起来的这一诗创作的原则,是“诗禅相通”之说的实质所在。但这一表现原则运用于实际创作,如同诗人领域与题材领域一样,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限制的。在禅一方面,是不宜搬用禅语来直写禅悦、直说禅理,如王维的《谒璇上人》、《饭覆釜山僧》等诗,通首说禅,表达的无非就是其“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的愿望,以及“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的满足,意趣反而显得十分单调,也毫无馀韵可言。《三昧集》不选这两首禅意尽在言内的诗,表明了渔洋把握诗禅相通原则的尺度之精严。清人对此是有共识的,如稍后的沈德潜也同样持“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息影斋诗抄〉序》)的认识;纪昀批《瀛奎律髓·释梵类》,亦以“诗欲有禅味,不欲着禅语”(卢纶《题云际寺上方》诗批语)为原则而用之再三。但沈德潜对于诗禅关系的理解,似仅得其表,而不及渔洋精审,他的《唐诗别裁集》便选了王维这两首诗,虽是有意与《三昧集》立异,却失之于裁断。而纪昀于此道,则一如渔洋之探本,如他于《瀛奎律髓·释梵类》所选的王维二诗,深赏《登辨觉寺》而不取《春日上方即事》,即正与《三昧集》之取舍相同。
在诗一方面,不立文字,言外见意的要求,似乎更适合篇幅相对短小的五言,而不适宜于以沉著痛快见长的七言,渔洋师生间曾围绕《唐贤三昧集》讨论过这个问题:
问:《〈唐贤三味集〉序》“羚羊挂角”云云,即音流弦外之旨否?间有议论痛快,或以序事体为诗者,与此相妨否?答: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之矣。至于议论叙事,自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
许昂霄(嵩庐)也曾就这一段问答批云:“似专论五言”(《带经堂诗话》卷二九)。五七言诗的分际,是渔洋诗学的精湛之处,所谓“作古诗须先辨体,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不可虎头蛇尾”(《池北偶谈》);“五言著议论不得,用才气驰骋不得。七言则须波澜壮阔、顿挫激昂、大开大阖耳”(《师友诗传续录》);“五言以蕴藉为主,若七言则发扬蹈厉,无所不可”(同上);“五言难于七言,五言最难于浑成故也,要皆有一倡三叹之意乃佳”(同上)云云。他甚至在五言内部再分:“感兴宜阮、陈,山水闲适宜王、韦,乱离行役、铺张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池北偶谈》)这些议论,实际上道出了不著一字、意在言外的表现原则,其适用范围只是在五言诗一体内,甚至只是在五言诗的“山水闲适”一题内。《三昧集》中七言诗(包括一部分杂言诗)入选110首, 这还是渔洋有意为之的结果,但仍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而已,两体是失衡的。可见诗歌语言表达意蕴的手段,援禅入诗的意义是有限度的。故渔洋诗学的精粹在此,局限也在此。后世每讥其“一代正宗才力薄”(袁枚论诗诗),触到的正是这一局限之处。渔洋本人对此也未尝没有认识,他中年出唐入宋,欲以宋济唐;晚年编《三昧集》,又对此作了种种补救,如上述以王维而非王孟为宗,以高岑济王孟,以沉著痛快济优游不迫,以七言济五言等,但都无补于总体性质的改观。至此,“寄植”于渔洋诗学的“诗禅相通”之说,在这一个方面的滞碍难通自然也就不言而自明了。
结束语:诗禅关系的一般限度
上述分析表明,《唐贤三昧集》这一部历来被目为最具禅味的唐诗总集,其与禅的相契程度仍然是有限度的。这些限度对于诗禅关系亦即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具有一般性的意义。诗的世界与禅的世界,只是部分交叉相合的关系。渔洋在他的诗论中着重阐发了诗禅相通的一面,而他精心编纂的《唐贤三昧集》,则对诗禅相通的局限性亦有所表示,能够同时读出这两种相反然而相成的意见。
考察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就中国古典文学而言,最普遍也最典型的现象,便是诗与禅、诗人与释子之间的关系。如元末欧阳玄曾概述唐、宋以来禅与诗两方面的大师之心印史:“由唐至宋,大觉琏公、明教嵩公、觉范洪公,以雄词妙论大弘其道于江海之间,一时老师宿儒若我先文忠公及韩琦、苏轼,莫不敛衽叹服。皇元开国,若天隐至公、晦机熙公,倡兴斯文于东南,一洗咸淳之陋,赵孟頫、袁桷诸先辈,委心面纳交焉。晦机之徒笑隐诉公尤为雄杰,其文太史虞集尝序之矣。诉公既寂,丛林莫不为斯文之嘅。翰林修撰张翥橐示豫章见心复公所为文,以敏悟之资,超卓之才,禅学之暇,发为文辞,抑扬顿挫,开合变化,蔼乎若春云之起于空也,皎乎若秋月之印于江也。溯而上之,卓然并驱于嵩、琏诸师,无愧也。”(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元以后如见心复公这样能诗的高僧仍不竭于史,明代据钱谦益《列朝诗集》所载便有70余位。而僧诗集亦屡见于著录,以总集为例,即有数人合集的《唐四僧诗》、宋《九僧诗》、明《三僧诗》等,断代的《唐僧宏秀集》、《宋高僧诗》,乃至统贯历代的《古今禅藻集》等。
高僧能诗,但僧诗的成就却始终不能与诗人之诗同日而语。唐代最好的诗僧皎然、齐己,被陆游《老学庵笔记》誉为南宋诗僧之冠的如璧(饶节),被吴梅村、王渔洋先后推为释子中第一的晚明云南高僧读彻,都只能是各自所属时代的二、三流诗人而已。清季的八指头陀在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被尊为天罡星(鲁智深)中的一员,似乎置身于一流;但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则黜其等而入地煞星(朱富)之列,其地位还是在一、二流之间摇摆。清初黄宗羲云:“诗为至清之物。僧中之诗,人境俱夺,能得其至清者,故可与言诗,多在僧也。”(《文集·平阳铁夫诗题辞》)这是从“僧”的角度言“诗”;如从诗的角度言僧,情况便没有这么乐观,如清末李慈铭云:
浮屠氏之于诗,其难工乎!盖彼之为教者,一以灵净虚无为宗,举人世忧乐爱恶之境扫而定之,以归于至寂。而诗之为道,非得于忧乐爱恶之深,则所作不工。两者既格不相入,无怪彼中人之称诗者,率荒忽鄙俚,入于宗门语录而不知返也。(《释彻凡募梅精舍诗序》,《越缦堂日记》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此论严峻地从根本上斩断了诗、释之间的关系,大抵代表了儒家诗论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全面而论,诗、释关系的上述两个方面是同时成立的。黄宗羲所谓诗的“至清”的性质,实际上不仅表现于“人境”,更表现在“语境”上,即诗是最讲究语言精致的一种文学形式。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标榜文字“无迹可求”的选旨,深得诗之本旨。他用“禅趣”来表达这一诗旨,又尽选“诗人之诗”来表达这一禅趣,获得的效果也是“连环”的,即:既以禅之趣坚守了正宗的诗的立场;而带着禅风的诗,却仅及五、七言两体中的一体,仅及沉著痛快、优游不迫两种风格中的一种风格。以致在“诗”这一领域,王维的“佛”之地位,终究不敌杜甫的“圣”之地位。这实是中国古代儒释相通而以儒为主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在文学中的反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