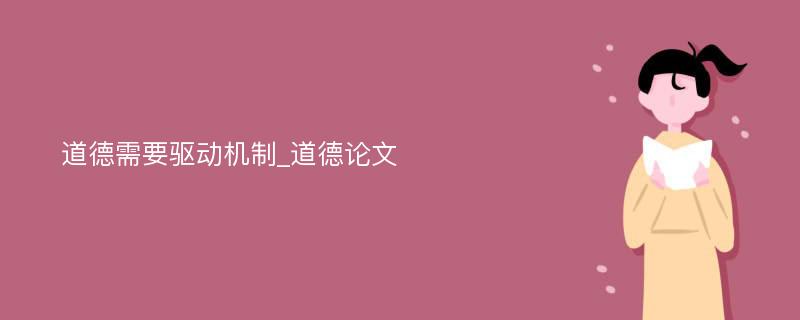
道德需要驱动力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驱动力论文,道德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0)02-0007-07
中国虽然是道德的文明古国,但现实中不时袭来的道德危机的冲浪,敲响了让人惊醒和思考的警钟。道德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人和自然的感性朋友。但是,道德能否在生活中得到表现,关键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自觉地认识,成为调控人们行为的一种恒常的自觉意识。换言之,就是能够自觉地把道德认知转变为实际行为的整合能力,这是一种实践的道德能力。现实生活里道德的缺失,就是个体整合能力低下的具体表现;在我认为道德就是个人目中有物、心中有他的意义上,道德的缺失就是个人目中无物、心中无他的事实。所以,道德的实践,就是要锻造人整合物际、人际关系的能力,或者说就是如何使物、他走进人的心目的实践。可是,在重视道德实践这个问题上,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我们的投入与收获不成比例,根本没有效益可言,这是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地球村的态势给我们留下的自我丰富的空间已经无几。
在一定程度上,任何时代、任何人的研究,都是当下的研究,都是个人的研究,这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是,这也不等于暗示一切研究就没有客观的标准。研究必须存在客观性,这种客观性的可信度往往与研究主体的良心相一致,而研究主体的良心的价值意义,只能在紧紧贴近客观事实的基点上才能显示其应有的价值。历史的客观事实就是历史之“是”,本着“是”而研究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如是说”的方法,这是研究历史必须采取的唯一方法。自然,“如是说”与“照着说”并不一样,“照着说”是没有任何研究主体意识的被动消极的简单复述,没有任何创造的价值。而“如是说”虽然紧紧依据客观的历史事实,但它尽可能地勾勒出事件之间的客观联系,以及存在的必然关系,并提醒人们去思考这些必然关系与社会的关联。毫无疑问,“如是说”是历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也是研究者的责任所在,它需要踏实的作风来支撑。
在现实生活里,人们与其重视“如是说”的方法相比,而更推重“如何说”的追求。“如何说”的具体施行,全在研究者自己的设计,理想性淹没了客观性,故对现实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对现实的人而言,难免得到口惠而实不至的品尝。因此,在根本的意义上,它对人们不可能形成积极的指导性意义。而且,当一个社会的大趋势都侧重于“如何说”的追求时,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来自虚无的恐慌,因为它没有能否产生实际的效用、以及如何才能产生实际效用等现实问题的运思,没有责任意识。这些被忽视乃至无视的问题,就是“如何做”的问题。人们之所以没有余暇来顾及,在本质上又为具体操作性的“做”的方面,往往被人认为没有学问的现实所限制。因为,它往往是一目了然而无需深究的,而体现价值的东西仅仅是纯粹理论性的高谈阔论,为人所不懂的程度越大,说明你的学问就越高。这是与现实严重脱离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怪异现象,是知识分子知性高度异化的表现之一。
现实社会虽然需要“如何说”,但更需要“如何做”,因为光会说而不会做的现象,最终对社会和在社会上生活的人都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从人的成长过程来看,1岁前几乎没有说话的能力,3岁前几乎没有识字的能力。所以,在这期间的日常生活知识的教育都是通过具体的示范来完成的,孩子在照着做的过程里,把父母大人的示范变成了自己行为的一部分。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有一个习惯成自然的过程,许多东西并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只要实际去做就行了。问题是一些貌似简单的事情,对一些在高深问题上侃侃而谈的人,就成了难题,困难的不是内在理论的高深,而是因简单而无意坚持实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譬如,不随地吐痰和扔东西,作为一般生活的起码操守,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而且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处。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并非人人都能自觉做到,有许多人就是不自觉地吐痰和扔东西,而且跟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也没有什么关系,这都是习惯使然。因此,中国的公共卫生的维持就非常困难,导致一些大城市白天都有环卫工人在打扫马路,从环境保护和健康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违背理性规律的,但不如此行为的话,社会的正常面貌又很难保证,真是两难的选择。所以,只能选择违背一般理性的做法。
我们平时提倡文明行为,讲道德实践,实际上许多内容都是日常的行为规范,并没有大道理,关键在做。所以,我们应该从“如何说”转向“如何做”,这转变越快越好,理论研究也应该转向“如何做”的方面,把考虑操作的具体方法列入自己的主要视野,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争取自己份额工程的起码前提和条件。人文素质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只有在具体行动的氛围里才能让人切实体会到,而不是关在办公室里的对人的演说。我们的社会应该提倡做的哲学,哲学只能在做中成文章;道德的力量只能来源于做的实践。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儒教一统的社会,但儒教的本质特点在于它对世界的适应性,而不是对世界的调整性。德国汉学家马克斯·韦伯说:“儒教要求始终清醒地自我控制,维护各方面都完美无瑕的善于处事的人的尊严,清教伦理要求自我控制,则是为了把调整的标准有计划地统一于上帝的意志。儒教伦理把人有意识地置于他们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或通过社会的上、下级联系而造成的个人关系中……除了通过人与人之间、君侯与仆臣之间、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父子、父兄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的个人关联造成的人间的忠孝义务以外,它不知道还有别的社会义务……虽然不仅是从那种社会伦理立场,而且也从政治统治结构的固有规律性中,但主要还是从前者导致了中国对宗族制约的维系和政治、经济的组织形式完全系于个人关系的性质。这些组织形式明显缺乏理性的客观化和绝对的人际目的联合性,一开始就没有独立的团体,尤其在城市中,最后也没有完全客观地与目的结合起来的经济客观化的形式和企业形式……一切共同体行动在中国一直是被纯粹个人的关系,特别是亲戚关系包围着,并以它们为前提,此外,也与职业方面的结拜兄弟关系有关。反之,清教则将所有这一切都客观化了,消化为理性的‘企业’和纯粹客观的经营关系,并用理性的法律和契约代替了中国那种原则上万能的传统、地方习惯以及具体的官场上的任人唯亲。”[1](P293-294)儒教重视自我控制,其依据的标准在人自身以及人际关系,而血缘关系又在人际关系里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成为中国维系政治、经济关系的唯一纽带,即使在企业关系里,儒教也强调任人唯亲操作链的重要性,具有主观随意性的特点;不同于此,清教伦理虽然也要求自我控制,但它是与上帝的意志一致为依据或目标的,关系的网结就被消解为理性的客观关系,诸如在经济活动里,法律和契约成为顺利运作的因子,而非血缘人际关系,具有客观稳定性的特点。换言之,儒教自我控制的依据在内在的人自身,而清教伦理在外在的上帝;前者具有主观性,存在任意而为的危险性;后者具有客观性,存在着理性行为的支撑。这是明显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人外在规范等的实践,始终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
自我控制实际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由于没有客观的标准,最终走向虚无。马克斯·韦伯又说:“儒家慎独的出发点是保持外表仪态举止的尊严,是顾‘面子’,其实质是美学的,基本上是消极的,‘举止’本身并无特定内容,却被推崇,被追求。清教徒也讲清醒的自我控制,却有积极的目的:有一定质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比较内在的东西:系统地抑制自己那种邪恶、堕落的内在的天性。彻底的虔信派信徒用簿记制定了抑制了内容清单,就连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追随者每天也要按照这份清单对照检查自己。超凡的全知的上帝注意中心的内在的态度,相反,儒家所适应的尘世则只注意优雅的姿态。儒家君子只顾虑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1](P296)慎独的修身由于没有实质的内容,是一种“面子”工程,而且是表面的,根本没有投入真情实感,这种行为本身就表示着对他人的不尊重和不信任,加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都为人际关系所支配,所以,这种不尊重和不信任的客观效应,自然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清教伦理却相反,它的自我控制不仅有积极的目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内容,即系统抑制自己那种邪恶、堕落的内在的天性,并且每天具体对照检查自己的行为,在理论到实践的环节上,明显有着严密的连接倾向,这在儒教那里是没有的。换言之,儒教的修身是为他人的,因为“面子”是给他人看的;清教的自我控制完全是为个人的,不使自己的天性走入歧途。
关于这点,日本实业思想家涩泽荣一的总结非常精当。他说:“修养必须达到什么程度,这是没有界限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切勿陷入空理空论。修养不是理论,应在实际中去做,所以必须同实际保持密切的联系……理论与实际、学问与事业如果不同时发展,国家就不能真正兴盛。不管一方如何发达,两另一方如果不与之相结合,这个国家就不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不能只满足于事实,也不能唯理论是从,必须是两者能结合,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即是文明富强,作为人则成为完全的人格者。上述情形的例证很多,就汉学来说,孔孟的儒教在中国最受尊重,称之为经学或者实学,这和诗人墨客用以游戏人间的文学,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对儒学研究最深,而且使之发展的是中国宋末的朱子。当然,朱子非常博学,而且热心讲学。不过他所处的时代,即宋朝末期,政治颓废,兵力微弱,丝毫没有实学的效力。也就是说,学问尽管非常发达,但政务极为混乱。换言之,即学问与实际完全隔绝了。总之,儒家的经学到了宋代尽管有了大大的振兴,但并没有把它运用到实际中。”[2](P128-129)显然,儒学发展到宋代,走上了理论与实践完全脱离的轨道,事实上成为一种空洞的学问,在客观层面上的直接效应就是“政治颓废,兵力微弱”,理论只有与实践具体结合,才能使国家“文明富强”。
就实践的情况而言,忽视乃至无视实际、实用,一直是儒学的特色,也是中国学术的主要倾向,自然,它也是中国发展状况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样一来,重视道德的儒学,由于忽视其实践转换的内在机制,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空洞说教的代名词。注重“面子”的修养实践,不可能给个人带来真正道德能力的积累。在整个中华民族振兴的历程中,诉诸道德来拯救民族又是最基本的选择之一,尽管有近代洋务实业的冲击,但最终并没有能够改变道德救国的主要价值取向。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近代思想家的轨迹就足够说明问题。譬如,严复认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3](P380-381)。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主要就在于这三者关系的协调和优化,他观察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正在这一关节点。他又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P382-383)。“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的确是问题的关键,严复的看法无疑入木三分。为此,严复选择了学习“西学”作为切入口。他说:“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夫如是,士之能于此深求而不倦厌者,必其无待而兴,即事而乐者也。否则刻棘之业虽苦,市骏之赏终虚,同辈知之则相忌,门外不知则相忘,几何不废然反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3](P385-386)在这里,他等同西学与实学,学问不能离开“事功”,而西学就是重视“事功”的功利主义学说。应该说,重视实、事的方面,不仅对当时的中国最为迫切,而且在学理上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严复最终认为,中国民众缺乏“自治”的能力,最多只能实行“开民智”等方面的改良,而诸如西方的民主制则在中国不存在施行的土壤,在这个结论下,诸如作为施行实学条件的选举法等的革命也只能趋于夭折,而他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也几乎完全消解。
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提出“新民”的救国模式。他认为“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4](P206),“新民之道”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法宝,即“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4](P210)。关于“新民”的具体内容,他也有明确的表达:“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4](P211)新本有、增新有,这就是他所说的“新民”之意。“新民”的具体内容则是道德、风俗等精神方面的工程,而不是其他。下面的表达更明确:“古哲不云乎:‘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今日稍有知识稍有血性之士,对于政府而有一重大敌,对于列强而复有一重大敌,其所以兢兢业业蓄养势力者宜何如?实力安在?吾以为学识之开通、运动之预备,皆其余事,而惟道德为之师。无道德观念以相处,则两人且不能为群,而更何事之可图也。”[4](P264)只有道德最为重要,没有道德,群居生活无法维系,群体不能协调一致,就无法抵御外敌,即“群学公例,必内固者乃能外竞,一社会之与他社会竞也,一国民之与他国民竞也,苟其本社会本国之机体未立、之营卫未完,则一与敌遇而必败,或未与敌遇而先自败”[4](P260),而道德就是实现“内固”的唯一选择。“内固”虽然为形成民族力量之必须,但不等于力量本身,他在这里以道德为力量,而把开通学识等科学实践作为“其余事”。显然,这样的“新民”设想,只能是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在现实面前最终也只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也是它能带来的唯一结果。
显然,严复、梁启超在中国面临亡国的灾难面前,都思考了如何做的问题,具体的答案就是通过“新民”来拯救国家。但在如何“新民”的问题上,又真正演绎了“中体西用”的实践,死死为自己接受的儒家道德所牵引,把道德作为“新民”的根本。以道德为本的新民,自然不能对抗西方科技的威慑力。儒家道德的侧重在内在的修养,忽视外在客观理性的认识,严重脱离客观的实际;而且修养也是“面子”工程的需要,而不是个人内在的意欲,不仅缺乏内在的动力,而且没有现实功效的积累。因此,道德救国不仅无法与西方科技的威慑力相抗衡,而且也根本没有进入与功利、功效相一致的道德实践的大门。这也是道德乏力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儒家道德以及中国推重儒家道德的事实的客观结果,就是上面分析的道德乏力的现实。但是,同样在儒家文化氛围里走出来的日本,现实社会的道德高水准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其内中的缘由。在日本思想史上,朱子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是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只是对中国儒学思想的简单运用,没有形成自身的特色,对日本社会发展形成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在朱子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学派、古文辞学派,因为,后者不仅洞察到了人与自然的区别,而且明锐地区分了人事与法律,这是朱子学也就是儒学本身所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儒学那里,不仅自然与社会合一,而且人情与法律混同[5]。所以,在最初基础的设置上,它就缺乏明确的多种关系的客观规定,根本无法形成合规律的张力,自然也就缺乏克服自身矛盾的内在机制,因为,它忽视乃至无视了认知对象的严格区分,其直接后果是知识的模糊性,由于知识没有直接的针对性,所以,知识实际上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仿佛语言一样成为抽象的符号,对人没有任何直接的指导意义。换言之,儒学本身不存在活力源,所以,越是往后走,路径就越发狭窄。日本古学派、古文辞学派所注意到的问题,其意义不仅在克服儒学本身的局限性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思想体系,反对空谈,注重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而且它们的思想直接与日本社会紧密结合,对凝练日本的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际上,日本民族紧贴实际的习惯,其原点绝非古学派、古文辞学派,在朱子学盛行的时候,事功就是它们注意的一个重点。在这里具体分析这一段历史显然缺乏合适的理由,因此,只想通过日本思想家涩泽荣一的论述来自然解明这一点。他说:“然而在日本却利用了被弄成空理空文死学的宋朝的儒教,而发挥了实学的效验。最善于利用的是德川家康。元龟、天正之际,日本号称二十八天下,国事乱如麻,诸侯都只热心军备。可是家康却十分明智,了解到只靠武备是不能作为治国平天下之策的。他以大力灌注于文事方面,采用了在中国作为死学空文的朱子儒学。首先聘请了藤原惺窝①,继之又任用了林罗山②,完全把学问运用到实际中,也就是说,使理论同实际相配合、相接近。”[2](P129)“宋朝的儒教”也就是朱子学,当时已经是“空理空文”,完全脱离实际,成为“死学”,这是日本人对儒学的客观评价。
但是,德川家康却以它为武器,统治日本达300年之久,依靠的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把学问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具体的做法就是:“朱子派的儒教主义,被在维新之前掌握着文教大权的林家一派的学说赋予了浓厚的色彩。他们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林家学派的宗师朱子,只是一个大学者,是口说实践躬行仁义道德,而并不躬亲履行的人物。因此,林家的学风也产生了说和行的区别,即儒者是讲述圣人学说的,而俗人则是应实地履行者,其结果是,孔孟所说的民,即被统治阶级者,只是奉命而行,驯致成了只要不懈怠一村一区课役的惯例就足够了的卑屈劣根性,仁义道德是统治者的事,百姓只要耕种政府所给予的田地,商人只要能拨动算盘珠,就是尽到了责任,这种结果成了习惯,自然就缺乏爱国家、重道德的观念”[2](P173-17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治国的原则,就成了幕府的方针。所以,当武士的必须修习所谓仁义孝悌忠信之道。他们是仁义道德治理人的人,则同生产谋利不发生关系。也就是根据‘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而使之见诸于实际。治人者一方是消费者,不从事生产,而从事生产致富的则与治人、教人者的身份相反。由此出发,一般认为,武士必须保持有不饮盗泉之水的高风,治人者被人所养。所以,食他人之食者为他人而死,乐他人之乐也忧他人之忧,这就是他们的本分。由于生产谋利被认为是与仁义道德无关系的人所承担的,所以,结果恰恰就成了与过去‘所有的商业皆罪恶’那种相同的状态。这几乎成了300年间的风气。这在开始时用简单的方法,还可以扭转,但以后逐渐落后,活力衰退,形式繁多,最终武士的精神颓废了,商人卑屈,社会上虚伪横行。”[2](P177-178)朱子是“口说实践躬行仁义道德,而并不躬亲履行的人物”,换言之,在儒学这里,显示的是只说不具体做的价值方向,理论与实际是相脱离的,因此,其理论也只能是虚无的存在。而德川家康的巧妙运用,就在于把理论与实际置于“两端”:明确武士和农工商者两端。前者专讲仁义道德,修习仁义孝悌忠信之道,他们是统治人的人即统治者;后者则被排除在仁义道德的门径之外,只要耕种好政府所给予的田地,只要能拨动算盘珠就行了,而且他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受道义约束的必要。尽管这谋利和谋道的“两端”是截然分开的,但它之所以在日本当时能有效运作,就在于这种“本分”意识的牢固确立,各自坚守“本分”的领地而勤苦耕耘,其客观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实际富裕和厚实。显然,对谋利者来说,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就算尽责了的行为认识,如果放到一个市民的角度来审视的话,不进一步追问对国家的更重大的责任,也根本激发不起爱国的热情,缺陷是显然的;另一方面,谋道的人实际是由谋利的人所支持而生活的,但却没有谋利者的社会地位。所以,社会上只能是“虚伪横行”,缺乏活力,最后走向衰落。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后来古学派、古文辞学派的课题,我不想在这里论述。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仅仅把眼光放在利用朱子学来立国而最后社会走向衰亡的一个时点上,应该注意日本对儒学的借鉴本身,与中国本土儒学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别的,正是日本民族对耕地、打算盘等等具体实业的重视,从儒学原有的注重内在的修养即伦理的实学,转向了外在的实业,也就是丸山真男所说的“物理”的实学③,日本人对物理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区别上,而且表现在武士与农工商的明确区别上,这内外两个方面的区别,表现了日本人对儒学认识的飞跃。关于这一点,笔者想通过福泽谕吉的总结来搁笔:“说起来,我的教育主张是着重于自然原则,而以数、理两方面为其根本,人间万事凡是具体的经营都拟从这数、理二字推断之……自古以来东方和西方彼此相对,而察其进步之先后快慢,两者的确有很大的差别。不论东方或是西方,都有道德方面的教育,也有经济方面的议论,文化武备各有短长。但从国事总体来看,说到富国强兵、绝大多数人享有最大幸福的情况,则东方国家必居于西方国家之下。国势如何果真取决于国民教育,则东西两方的教育法必然有所差别。因此拿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方的文明主义相比,那么东方所缺少的有两点:即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往近处说,只要有今天所谓的立国;往远处想,只要有人类,那么可以说人间万事绝不能离开数理,也不能撇开独立。然而,这种极其重要的道理在我们日本国内却遭到轻视。这样下去,当前不会使我国做到真正开放而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我深信这完全是汉学教育之过。”[6](P179-180)“有形的数理学”就是实学。显然,注意实学绝不是福泽谕吉的功劳,因为,这在福泽谕吉所否定的儒教主义(主要是日本的朱子学)里就已经有了基础,这也是与中国儒学的主要区别之一。在日本思想史的意义上,正是有了朱子学在耕地、打算盘等实业的重视,才顺利过渡到古学派、古文辞学派的对“事”的重视,直到后来福泽谕吉对学问和生活如何结合即结合方法的重视④。因此,以生活为唯一的平台来追求和实现学问的价值。在一般的意义上,人是生活的主体,生活实用也就是个人实用,这里的基点在人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其他因素诸如中国的“面子”。在现实生活里实用和“独立心”养成的实践,本身就是依托有形的生活来锻铸道德长城的行动,它是日本民族的一贯追求,值得我们深思。
儒教与生活脱离而成为空洞的说教,“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儒家对于那些以科学来了解自然,及寻求工艺的科学根据及发扬工艺的技术都持反对的立场”[7](P12);儒家重视内在修养的道德,以外在“面子”为依归,不仅个人修养缺乏内在动力,而且使修养实践呈现被动而无奈的倾向。因此,儒家道德没有内在的积淀机制,自然也不可能形成驱动道德实践的动力因子,个人道德实践的一切努力,都在“面子”工程里流失殆尽。道德不是“如何说”的作品,而是“如何做”即实践的结晶。要做好这个实践工程,我们一方面应该借鉴日本儒教本土化实践中的经验,另一方面则应该迅速从目前单一化的儒家价值观里挣脱出来,采用多元的价值选择,尽快吸收道家、墨家等重视自然的思想,以及由之而来的对物的科学审视的方法和重视技术以及工艺精良的特性,切忌泛道德主义的行为。把“如何做”作为道德实践的根干问题来定位,确立道德就是目中有物,心中有他。目中有物,心中有他,靠的不是口头语言的表达,而是身体语言的示范,而身体语言是人类最自然素朴和原始的交流方式,这才是道德最基本的驱动力,而做好这一工作就是解决道德驱动力机制的最大课题。
总之,儒家虽然重视道德,以道德为一切,但是,它的切入口在单一的社会的绝对稳定,因此,考虑的是如何控制、整肃个人,个人与社会处在对立的两极,而不是统一体。所以,如何把外在的道德变成个人内在自觉的问题,自然也就毫无意义,所以,儒学也就不可能去关注它,其结果是,关注日常道德的儒学,而缺乏道德如何日常性的运思和设计。这是儒学的关节点,是导致空虚的枢机。在历史的视野里,道德不适当的定位,为道德永远无法满足人的期望设置了一个无形而难解的泥潭;在动态的层面,通过道德实践来解决现实道德的不景气,又成为中国人代代选择的接力棒。而这一切又都为中国的道德缺乏内在的积淀机制,最终走上劳而无功的航程所定位。这些就是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运思我们国力实践时的必然课题。而当今日本伦理研究所富士山训练基地的建立,并在全国推行的每日的“朝礼实践”以及每日的企业“朝礼训话”,直接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驱动源,值得我们深思和参照。
注释:
①藤原惺窝(1561-1619),日本安土、桃山至江户前期的儒学家,日本近古朱子学之祖。
②林罗山(1583-1657)日本江户初期的儒学家,致力于朱子学的普及。
③参照“对于福泽来说,日本近代化的课题,首先是作为文明的‘精神’的确立问题来把握的。当时出现了急切追求采用‘文明的外形’——物质文明、‘把精神文明放置不顾’的文明开化风潮。而对这种风潮作出警告,正是《文明论之概略》的根本动机。他把物理学视为学问的原型,并不是轻视‘伦理’与‘精神’,恰恰相反,他是把物理学作为新的伦理与精神确立的前提。引起他关心的,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本身或其带来的成果,不如说是更根本的,即创造出近代自然科学的人的精神存在方式。正是这种人的精神,形成了近代的伦理、政治、经济、艺术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伦理’实学与‘物理’实学的对立,根本上可以归为产生东洋道学的精神与产生近代数学物理学的精神的对立。”([日]丸山真男,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现代化:福泽的“实学”的转回——福泽谕吉哲学研究序论》页30~31,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0月)
④参照“如果福泽的主张真的仅仅止于‘学问的实用性’、‘学问与日常生活的结合’,那么其思想决不是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光是这一点,福泽只能算是一个继承者,而决不是革命者。忌讳空虚的观念思辨,要求学问仕奉于实际生活,这不如说是日本人生活观念中的传统态度……而且,当宋学传入我国在德川初期达到全盛不久,熊泽蕃山、山鹿素行等便已指出其具有观念的、思辨的性格。比如山鹿素行认为,不符合正确的学问条理之学,‘即使修身正言行,背诵千言万句,亦不外是杂学,显然不能属圣学之条理’(《配所残笔》)。排除‘暗于日用’的‘文字学者’,认为‘文字和学问都不能列入圣学之中’,真正的学问应是‘有益于今日之实用’(同上)的,这叫实学……或者人们还会主张说,古学和水户学所提倡的日常实践是专以武士阶级为对象的,而与之相对,福泽的日常实践说,是以庶民为对象的‘劝学’。但是,在把庶民生活与学问相结合之点上,也不能把先驱者的地位归给福泽。众所周知,我们的心学前辈已拥有此地位。比如石田梅岩的《都鄙问答》。在那里,梅岩极力抗议‘商人不要学问’的说法……指出……所谓真正的学问,不外是日常的人伦,即‘不疏于家业,理财上知道测其量而支出,守法治家’……福泽实学中的真正革命转回,实际上并不在于学问与生活的结合和学问的实用性之主张中。其问题的核心在于学问与生活如何结合的结合方法上。这种结合方法上的根本转回,起因于其学问的本质结构的变化。究明其变化的意义,是解释福泽实学‘精神’的关键。”([日]丸山真男,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现代化:福泽的“实学”的转回——福泽谕吉哲学研究序论》页27~29,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