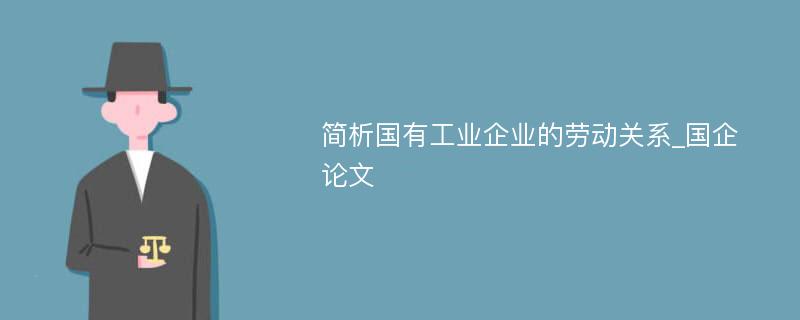
国有工业企业简单控制型的劳动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企业论文,劳动关系论文,简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有企业改制及劳动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1995年前后,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和“抓大放小”的方式进行改制。目前,这一改制基本完成,国有企业从一个计划体制下的“单位组织”成为了市场体制下的生产组织。统计表明,国有企业职工数明显下降,但效率有所提升。
从下表看出,国有单位职工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迅速下降,2006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总数的55.28%,比1993年的比例减少了18%。同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在提升。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是在怎样的劳动或权威关系中实现的呢?这是本文关心的重点。
表1 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变化*
年份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万)职工总数(万)国有单位职工人数所占比例(%)
1993 10920
14849 73.54
1995 10955
14908 73.48
2000 787811259 69.97
2005 623210850 57.43
2006 617011161 55.28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38页计算。
社会学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延续了以华尔德(1996/1984)开启的单位组织中上下级间的忠诚—庇护关系视角的研究传承(注:[美]华尔德,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英文原著于1984年发表),牛津大学出版社。),后续有Oi等人的研究(注:Oi,.Jean C.1986."Peasant Households between Plan and Market:Cadre Control over Agricultural Inputs." Modern China 12:251-23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中庇护关系在改革后有所变化和发展。在国有企业中出现的利益分化主要表现为单位集团化,而不是社会阶层化(李培林等,1992;张静,2001)(注:李培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尽管单位之间的收入差别拉大了,单位内部却保持收入均等化和同质性(王汉生等,1992)(注:王汉生等:“从等级性分化到集团性分化:单位制在现阶段城市分化中的作用”,《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1期。)。工人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很强的依附性关系(李汉林、李路路,1999)(注:李汉林、李路路:“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上述研究主要针对1995年国有企业改制前的分析。也有研究认为改制过程中依然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的松散性和人情味,其传统管理模式的存在(注:李铒金:“车间政治与下岗名单的确定——以东北的两家国有工厂为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
表2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及年增长率*
年份工业总产值(亿元)年增长率(与上一年度比)
200040554.4
-
200142408.5
4.4
200245179.0
6.1
200353407.9 15.4
200465971.1 19.0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27页计算。在提升。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是在怎样的劳动关系或权威关系中实现的呢?这是本文关心的重点。
第二种路径以阶级构成(class formation)为分析框架。李静君(1999)认为“共产党的新传统主义”已成历史,出现了一个新的“失序专制主义”(disorganized despotism)。这个概念是指国家的权威由厂长和管理层总揽,而出现专制管理——党组织及工会在企业内几乎全听命于管理权力;而合同制、企业自主、科学管理的引入,令以往的互惠关系消失;国家的相关条例,比如社会保障也没有起到效果,因此,工人实际处于旧体制已消失,新体制未建立起来的裂缝中。(注:李静君,1999,Ching Kwan Lee,"From organized depo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The China Quarterly,No.157(1999),pp44-71.)进入二十一世纪,有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即随着“世界工厂”的出现,中国正在重新形成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注: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第三种路径是劳动过程研究。认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工厂政体”的博物馆。从最原始的“工厂专制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特有的“霸权体制”都在同一时间点上并列杂陈,展示出各自的特性。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各种先赋性关系被直接纳入劳动过程,转变为支配与反抗的资源,这种特殊类型的霸权被称为“关系霸权”。(注: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页。)这一研究视角是以劳动过程为出发点揭示在劳动的各种分工和操作中剩余价值是如何被掩盖的。
第四种路径是“实践社会学”研究。强调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形态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遗风,又带有市场经济的冲击,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路径力求将研究带回到中国特定的发展道路中。(注:佟新:“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本文以“实践社会学”的研究立场为主,以个案研究资料为基础,分析当代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关系的状况。2002年8月以来,我们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劳动关系进行了持续的深入调研,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注:2002年至2005年,由朱晓阳、佟新、冯同庆、Anita Chan(陈佩华)、陈美霞、戴建中等组成“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企业治理与职工民主参与”课题组带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展开以案例为主的调研。后来以课题组成员为主,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一直持续相关研究。)。本文以四家国有工业企业调查为基础,分析国有工业企业中劳动关系主体的构成状况、权威关系模式以及特定权威关系模式建立的社会基础,及其与国家、跨国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二、国有工业企业改制:生产组织的重构
下面以四家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结果,了解国有工业企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组织向市场化现代公司制的转型。
(一)样本简介
1.BR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BR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下简称BR公司)地处北京,是中国最大的胶印机制造厂,隶属于BR集团公司。
该企业始建于1952年,1958年大跃进时整合了几家小企业,成为正式的机械企业,隶属于市机械工业局。改革开放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先是以“总厂”形式进行改制。1985年,总厂开始实行承包制。这种承包制的具体做法是:由总厂下达生产数量和利润指标,与各下属公司或分厂签订承包合同;厂里再将承包任务分解到各个车间,只要产品入库即完成计划。1993年是该企业上市的一年,它成为首批在境外上市的九家H股企业之一,成为真正市场意义上的现代公司。在这一年,公司实行了以利润为主的综合承包,总厂只下达利润指标,将销售权下放到了各分厂,必须产品售出、价款收回方计利润,分配权由总厂控制。1994年,该公司在上海A股市场上市,形成集团控制,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产品有不同类型和规格的胶印机80多种,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为60%以上。2000年,该厂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完成了以土地置换为主的设备更新,一些不愿意到郊区工作的员工自动内退,招收了一批来自北京郊区、年轻的中专毕业生为工人。
2002年8月课题组对该企业进行调查,进行了35人次的访谈。访谈对象中有19人是管理人员(包括政工干部),5人是一般科员,7人是工人,1人是技术人员,此外还有3人是退休职工(其中2人是工人)。访谈时间为40分钟到2小时,录音整理资料达100多万字,还对200名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注:2002年8月参加调查的人有朱晓阳、佟新、冯同庆、Anita(2han(陈佩华)、陈美霞、戴建中、龙彦、朱庆华等。)。
2.DL造船重工有限公司
DL造船重工有限公司(下简称DL公司)地处大连。该企业创建于1898年,先后经历过日本、俄国的殖民统治。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苏联援建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的现代化重工业基地,国家部属企业,且具有军工性质,部分产品专门为军队所用。
改革开放后,DL公司的改制是与上级主管部委“脱钩”的过程,其产品不断市场化,目前只有很少的军工定单。2006年,DL公司与“DL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整合成立了“DL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前身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六机部)控股的特大型综合性造船企业。“DL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组织结构是:董事会和监事会下设经理层,经理层下设有20个职能部,在20个职能部下面设有16个分部(如传统制造车间改为分段制造二部等),同时经理层还管理着20个以服务为主的分公司,如DL公司钢结构制造中心等。集团公司有员工11000人左右,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500余人,工程技术人员1400余人。DL公司是集团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调查组在2003年暑期、2004年暑期和2005年暑期三次进企业调查,2004年8月,调查时DL公司的职工有7000人,在岗工人有6000多人,其中生产工人、辅助工人以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共计访谈各类员工47人,整理资料达100多万字。(注:2004年8月19日进行的访谈,访谈参与者有佟新、梁萌、王迪、卫姗、王春来,资料整理:王春来。其他时间的访谈人员还有谭宝桂等。)
3.YC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YC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YC公司)隶属于YK集团公司,地处山东省某市,是一家拥有近10万人的大型国有股份有限企业。YK集团的前身是YC矿务局,成立于1976年。集团公司1996年整体改制组建为国有独资公司。
1998年,YC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纽约、上海三地上市,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的百强企业。其煤炭资源有8亿多吨,估计能开采二十多年,为了可持续发展,集团制定了走出去战略:一是在国内收购开发煤矿,二是到海外去,如收购澳大利亚等国的煤矿,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集团。其管理体系完全是依公司法的要求建设的。
2007年春天,我们进企业调查,到了YC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三个矿,开了三个座谈会,深入访谈9人。(注:2007年4月17-21日对YC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三个煤矿进行调查,参与调查的人员有冯同庆、佟新、胡瑜、王春来、吴凌和陈亮。)
4.JD油田分公司
JD油田分公司地处河北省某市,是一个四级公司(下文简称JD公司),其集团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其二级公司是华北石油管理局,其直属公司为“井下作业公司”。1975年,华北油田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1999年10月,按照国务院对石油石化企业进行重组改制的总体要求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原华北石油管理局重组为上市和未上市两部分。我们调查的JD分公司是上市公司的一部分,其“井下作业公司”有员工5000多人,因市场需求,该公司的副总经理任JD分公司的经理,到离公司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唐海,与另一家石油公司签订合同进行作业,JD分公司有600多人,因为远离公司,实行着特殊的工时制度,即有四分之一的员工轮换着每月回家一次,一次休息8天,其余的工人在石油工地上连续工作。职工全部是男性。
2008年春天,我们到JD分公司的工地进行调查,对包括经理、书记、工会主席、小组长、工人和劳务工等9人进行了深入访谈。(注:2008年3月4-6日到HD分公司调查,参与调查的人员有佟新、杨易、王叶,访谈经理、书记、工会主席、小组长、工人和劳务工等7人。)
(二)国有工业企业改制后的体制
从四家国有工业企业改制看,国有工业企业基本完成了其市场化的改制,其企业形态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法意义上的生产组织。我们也看到国有工业企业的一些体制性特点。
首先,国有企业改制中强调的“抓大放小”,使现有国有工业企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特别是在国家命脉的行业中,如石油、煤炭、机械等行业中具有垄断地位。
第二,国有工业企业在市场化下的公司建设是完善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来说,一方面,资本市场已成为大型国有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身份使国有企业处在现代公司法和股东们监督之下。这强化了国有工业企业在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传统国有企业以意识形态为目标的体制建设转向了以绩效为目标的企业建设。
第三,国有工业企业较好地保留了工会。《公司法》的要求和计划经济时的传统共同形成了工会的状况,调查的四家公司都有专职工会干部,且结构完备,有从公司级别到班组级别的工会组,并有至少一年一度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国有工业企业的转制意味着完成了公司化和市场化改革,这种转制是“转化式适应”。所谓“转化式适应”是由日本学者大野健一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不是从内部生长的,而是从外部注入的,是国内体制和国外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注:大野健一:“日本发展之旅的经验”,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4期(2006年),第182页。)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不是在纯市场条件下产生的,而是在政府主导下,由那些在计划经济时有较好基础的企业来完成的改制。因此,国有企业改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国有企业的传统;同时也适当地引进了市场规则。
三、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关系主体的等级化
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关系的主体由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构成,但这四类人员归属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在国家、资本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作用下劳动关系主体呈现出等级化特点。
(一)经营管理者的官本位和市场化激励
2000年10月27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宣布国有企业经营者脱离“干部序列”,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组织确定企业经营者的待遇,实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者管理办法。由此,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脱钩”,但调查发现,企业经营者与上级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有企业的经营和高级管理者的选拔绝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它是在封闭的条件下,以“内部人”方法选拔的,并要经上级党组织的审批和考查。可以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本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官僚体制对经营者的控制以及经营者对官僚体系的依附皆存在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放权让利”给经营者合法的、可索要剩余的管理权,即市场化的巨额利益回报。政府倡导的“放权让利”绝不是对工人的放权和让利,而是对经营者的“放权让利”。正是在2000年各省市的国资办、经委、劳动局、财政局等都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实行办法(试行)》的相关文件,给予经营者物质利益。所谓年薪制多是对年利润额超过百万以上的国有企业而言的,是按企业经营年度(一年)确定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报酬,并视经营业绩的好坏计发其年度工资的制度。年薪一般由基薪和风险收入两部分组成,基薪是年度经营的基本报酬,风险收入是年度经营效益的具体体现和年度经营业绩的积累,包括生产安全等。调查的四家国有企业对高层管理者都有“年薪制”或“高额年终奖”,它肯定了经营者对企业剩余的索取权,成为主管部门对经营者的新型庇护。
YC矿业集团和JD油田分公司都明确实行年薪制,且薪酬水平很高,与其他员工的报酬形成巨大的反差。JD公司的经理谈到:
“我们石油企业对安全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固有的指标,不能超,超了以后呢,那个损失更大,企业的领导人要被处罚,每年都要兑现的。2007年我们的年终兑现应该是超过20万,结果就在差几个小时送走2007年的时候出了个事故,我被扣了4万块钱。”(注:2008年3月5日访谈,访谈人:佟新、杨易、王叶,资料整理:王叶。)
这可见年薪制的一斑。
传统官本位的权力授予方式的延续决定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行动取向是“对上负责”,并以上级主管部门为靠山,这种政府给予的政治庇护,保留了传统国有企业精英的政治权力;同时,高额年薪制的物质激励又使企业经营者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精英;国有企业经营者具有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双重身份,他们的特权在于:他们替国家行使对现代国有公司的控制权,成为在国有企业制度中占居高等级地位的人,在企业中具有绝对的支配性。
(二)跨国资本促成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个体性谈判
在跨国资本的作用下,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由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它决定了国有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的谈判能力和结构位置。
访谈发现,四家企业都遇到了技术人员短缺问题,并形成了一套高级技术人员个体性谈判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是跨国资本对中国高级技术人员的觊觎,他们多以高于国有企业5~10倍的工资“挖走”优秀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大量的科技、管理人员从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民营企业中“跳槽”,其中一半以上进入在华跨国公司(注:罗进:《跨国公司在华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BB公司作为机械行业的重头企业,技术人才十分重要,他们很早就遇到了高级技术人员流失问题,并在1996年首先实施了在全国引起关注的“与科技人员谈判工资”的做法,以灵活的工资留住人才。2003年作为该公司第四分厂的书记说:
“市场已经形成,人才不可能为单位所专有,再坚固的围城也会被打开缺口。九十年代中期,我们曾要求技术人员签长达10年的合同,收高额违约金,扣留人事档案,还对引进大学生实行‘三不要’政策:名牌大学的不要,发达地区和城市生源不要,成绩太好的不要,即便这样,也挡不住人走的脚步。我们那时都怕开国际印刷机械博览会,因为看到国际大公司驻华机构的技术人员或是副总一类的都是从我们厂子出去的。那时我们支付科技人员的工资比市场价格低了近一半,有3~5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1996年的市场价是1.8万元(年),三资企业更是高达数十万元,而我们只有七、八千元。原有的结构工资是典型的大锅饭,同年进厂的大学生,三年后有的已挑大梁担当主设计,有的还不能独立工作,而他们的收入几乎完全一样,区别仅在于奖金相差20~30元。倘若固守这一模式,怕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发展。我们试着实施了谈判工资。首先,参照人才市场价格确定职工工资水平,把有限的工资总额盘活用好,留住直接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人才。其次,谈判工资解决了传统工资分配中按级别论价、‘工资管看,奖金管干’的弊端,收入多少直接与贡献大小、工作难度系数及风险责任挂钩,进而达到激励人才创新的目的。第三,平均主义被打破,完全凭个人的能力和实绩说话,工资能升难降的刚性被打破,提高了工资的使用效率。1997年第一轮谈判的结果是,61名技术人员重新确定了工资数额,月薪最高2100元,最低的700元,月增资500元以上11人,占技术人员的20%,100元~500元的32人,月增资100元以下、未达到职工当年平均工资额的14人,占全科人数的20%,未升级的1人,降级的3人。工资月差由原来的20~30元上升为400~500元,最高相差900元。1998年第二轮谈判后,54人升级,最高月增资400元。我们技术人员的收入逐渐与同行业的市场工资水平接近,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还是无法与跨国资本竞争,成长起来的技术人员还可能走,特别是外语好的。”
DL公司也遇到了相同问题,公司劳动和人事处处长说:
“知识分子要跳槽,那也要分析原因,有的是待遇问题,有的是怀才不遇,还有周围的环境、领导不器重啊、人际关系。大部分都是因为待遇问题跳槽,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工改(工资改革),还搞了人才库。尤其是对优秀的人,相对还是多拿一点,但是也不完全是高位。工资增长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人家(外资)仍然还有优势,人才该走的还要走。”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初起,DL公司每年只招收100多人的大学毕业生,再没有招过一线工人。
在市场作用下,国有企业技术人员获得了较高的谈判能力,但其工资水平低于管理人员。YC公司的技术人员说:
“主管矿长是年薪制,拿得多。我们不是年薪,拿得比管理人员少。有觉得不平衡的人,不行就走吧。但是大多数人都忍了,懒得动了。”
调查表明,那些年轻、专业有市场需求、外文水平较好的技术人员“跳槽”到外企的可能性较大;而40岁以上的技术人员多稳定地留在国有企业,国企稳定的工作是有吸引力的。国有企业技术人员身处开放的高级劳动力市场,但多以个体化方式参与竞争,其竞争能力是有限的,个体化、碎片化和高流动性成为这一群体的基本特性。
(三)技术工人的老龄化和内部接替制度
从表一可以看出,整个国有企业的用人规模是不断缩小的,调查的四家企业的情形亦如此。这四家公司在2000年后几乎都没有招收过正式工人,只是个别的接受过本单位退休人员的子女就业,并且要求这些子女们一定具备本行业认可的专业学历。其结果是,国有企业长期合同的技术工人严重老龄化。
在DL公司,多数技术工人是1968年入厂的,那一年工厂招收了1000多名“根红苗正”的人进厂。在改制过程中,先是停止招收工人,二是以各种方式动员工人退出。1995年前,该企业有各类工人5000人左右,到2004年调查时仅有2500人。该公司的劳动和人事部部长说:
“1995年,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这个改革比较大,除了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以外,每个员工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在管理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二是公司制以来,根据国营企业包袱重的情况进行了减员,主要是提前内退、息岗、转岗再就业和很少量的末位淘汰。……因为我们厂给的条件好,职工不怕走,二线工人(辅助工人)原来每月能挣一千三、四百元,现在退休了也能挣一千块钱,在家呆着也挺好的。工人自己写申请就可以退,有人愿意走。有人在外面有个小企业,拿着退休金再做别的事。退休走的女同志最小的48岁,她母亲生病,申请就退休走了,她每月还能开900来块钱。2002年我们减员1300多人。此后,进行了工资改革,大幅提高了在岗工人的工资水平,原来人均一年一万七八千块钱,调整后,人均一年两万四千块钱。”实现了减员增效。
JD公司也有相同的情况,某工地的队长说:
“我们油田是1976年成立的,都是老石油工人,当时就是这块儿发现大油田了,你们厂出多少人,我们厂出多少人,大家一起会战,所以那会儿的石油工人是没有多少东西的,就是那么一两个箱子,一个行李拎上就走了,没有这个什么家不家的这个概念。现在的工人对国家的概念要淡了,现在是谈我个人的价值是怎样的。但是还是看环境,我们石油行业还是有传统的。在2002年以前,只要是自己的子弟,上我们的技工学校就能回油田工作。我们是喜欢要他们,因为作为子弟,不用特别的动员,因为那些老职工们还会把对于党和企业的感激传递给年轻一代的。你想他们这些孩子都是在油田当中一天天的看着长大的,那么对油田的这种氛围,对员工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们都早就耳闻目染。”
四家国有工业企业正式招工的技术工人都签订有长期合同(一般是五年和十年以上),这些技术工人以中专以上毕业生为主,是工会会员,且在一线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如队长或小队长。这些工人在工资收入、劳动保护、劳动保障等方面有较好的待遇。这部分与传统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技术工人队伍是当今国有企业重要的生产力量,但青黄不接,老龄化严重,其稳定和优势地位难以得到进一步的延续。(注:接替制度的形成非常复杂,在DJ公司就出现过因企业停止对职工子弟的招工引发了老工人的抗议。本人将继续深入研究,在思考成熟时发表相关研究。)
(四)国有工业企业大量使用廉价的非正规劳动力
调查发现国有工业企业大量使用廉价的非正规劳动力。这些非正规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其规模占到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非正规劳动力的收入和劳动保障条件比正规劳动力低得多。研究发现至少存在两种使用非正规劳动力的文献,一是外协制(转包制);二是劳务工。
1.外协制工人
外协制(转包制)是独立于国有企业的一个用工体系,又称为外包队或包工队,具有明显的包工性质,外协队队长相当于包工头,他组织农村户籍的青壮年劳动力组织和完成由外协队承接的生产任务。外协队与工人签订短期合同,一般多为一年,具有临时性。
DL公司使用大量的外协工,调查时的场面令我记忆犹新:在同一蓝天下,国有固定工和外协制工人在完全不同的劳动环境下工作,吃饭、洗澡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但外协队的工人们承担了企业近半数的生产任务,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工作,其收入仅是固定工的一半。2004年调查时,DL公司有长期合同工2500人,有外协队30~40支,每支队伍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二、三百人,其总数达1900多人,占到用工总数43.2%。外协工人已经成为LD公司举足轻重的生产力量。为了便于管理,DL公司的劳动人事部专门设置了一个外来用工管理科,派专人进行管理,该科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协队进行质量审核,其说法是:“每年都要对外协队进行审核,几乎每年都有被淘汰的,整改那些不合格的队伍,主要是有关安全和工资方面。”DL公司还实行“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在车间一级直接使用外协工人。
“JT船务公司”是一家外协队,其队长刘先生是1967年出生的年轻人,他原籍江苏南通,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船舶公司工作,因工资收入不理想,九十年代初下海,三年后因为与各类造船厂的领导们比较熟识,能够拿到订单,就开始自己组织外协队到造船厂工作,至今他自己组建的公司和队伍已经在造船厂干了10多年了。“JT船务公司”最初有50多人,我们访谈时(2004年)有100多人。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多数没有技术,是来到造船厂后临时培训的,也有少数年轻工人是技校毕业生,以电工等为主。在这一包工队中年龄最大的不超过45岁。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500元左右,整体水平比国有固定工低。刘先生说:
“这个厂(DL公司)现在的状况啊,可以这么说吧,以外协队为主,以国营工人为辅,9个包工队,就能(干)下9条船。……外协是一个趋势、必然趋势,将来很多国营企业单位就不复存在了。”(注:访谈人:佟新、王春来,整理:王春来。)
2.劳务工
劳务工也称为劳务派遣工,是由地方劳动部门作为中介为用人单位代招的农村劳动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力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二是劳动力直接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这些合同都是短期劳动合同,一般为一年。
JD公司使用了约三分之一的劳务派遣工,其中有从甘肃某县劳动服务公司招收的农民工,它是公司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工人的工资也是通过这一劳务公司发给员工的。而河北省某县劳务工,地方劳动服务公司仅是代招,劳务工直接与企业签订合同。这些劳务工的工资收入约为正规固定工的三分之二(少的三分之一主要就是劳动保障的成本);这些劳务工在JD公司享受工伤保险和基本的劳保用品,没有其他劳动保障,不能享受与正式固定工相同的休假。但是,由于JD公司期望有一个长期的用工制度,因此,他们与劳务工虽然签订的是一年合同,但是承诺如果劳务工能够在企业工作满8年,可以转成正式工。
干同样的工作,却有较低的待遇和报酬,这样的用工制度是不平等的极致,但却在国有工业企业普遍存在,且成为企业降低用工成本的最佳办法。
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关系主体呈现出等级化态势,经营管理者与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得到其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庇护,并具有绝对支配权;技术人员有明确的市场优势,却是个体化和碎片化的;技术工人虽享有传统国有企业的保护,但却呈现老龄化趋势,后继乏人;而大量低价非正规劳动力的使用使等级化的用工模式达到极端,这种等级化的劳动关系主体结构是构成其特定劳动关系形态的重要基础。
四、简单控制型劳动关系
无论是何种所有制的企业,都会面临着权威和控制问题,经营管理者即使是视工人为纯粹的商品,也要承认工人的基本权利,并要有相应的奖惩制度来控制员工,以实现效率;此外,工人们无论面对怎样的控制,他们都是积极的行动者,有其自己的能动性和行动逻辑,有着选择斗争、谈判、妥协和同意的可能性。
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借助于等级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了对工人的简单控制。所谓的简单控制是借用了爱德华兹(Edwards,1979)的研究,他在分析现代工业生产组织中的控制模式时指出,现代生产组织的控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简单控制(simple control),包括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计划的制订、任务的分配和具体生产的实施。二是技术控制(technical control),通过评估完成的工作来实现的。它依赖组织本身监控技术及其相关环境和条件的发展。这种控制是伴随着流水线的标准化生产而产生的,它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者个人对规则的服从。三是科层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指通过奖励和惩罚工人而实现的一种控制机制,这种控制机制嵌入到整个企业的科层制的社会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必须以技术控制的实现为前提和基础(注:Edwards,Richard.1979.Contest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Heinemann.)。对爱德华兹的批评多强调,这三种控制形式并非是时间序列,而可能是共存的。本文认为,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形成了一整套以上下级之间忠诚与庇护的关系的话,今天这种控制关系早被简单化,即使存在着技术控制和科层控制它也不是主流,主流就是单方向的经营管理者依靠其坚实的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虽有激励与惩罚制度,那些制度也因外部市场强烈的不稳定性而几乎可以等同于工资的一种补充。这是国有企业在管理手段上的一种倒退,传统国有企业中一些优秀的传统正随着老一代工人退出劳动领域而消失。
(一)经营者以绩效和安全为目标的强支配
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行为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控制者转变为以绩效和安全为目标的控制者。从1987年开始,国有企业就以“厂长责任制”的方式给予经营者独立的管理权。国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让权放利”的最终结果是经营者将自身利益纳入到绩效的追求中。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有多种,如技术创新、开拓市场以及减低人力成本,但在当国家是企业经营者的授权者时,其短期效益决定了经营者采用最简单的控制人力成本的方式提升绩效。这直接导致了劳动关系中管理者对劳动力的简单控制式支配,其目标就是在安全生产的条件下完成任务。在YC公司,直接的管理方式就是“半军事化”管理,某矿队长说:
“在行动上,因为要求工人一丝不苟,按规矩办事,所以对工人行为进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这不仅体现在工作的时候,在矿区其他地方,包括走路吃饭都是如此。在路上要排队走。现在可以说,各个岗位工作都有各个岗位工作的制度。包括开始下井,到工作面,到你怎么干的,这些制度都有,都是定好的。然后这些制度呢,有些工作场所呢,它这个岗位制度都挂在它工作的地点上。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你在这里干,应该干的程序,都有。奖的制度很多,罚的制度也很多。比如,今年采取的一个全月安全比呀,只要你这个月你本单位,没有工伤,没有大的严重‘三违’现象,没有红牌、黄牌,一个季度下来三个月一个人奖一千五。是奖班组全部人员,一个人奖一千五。安检员、区队管理、机关科室的管理人员,都有权罚。”
军事化管理和奖罚制度的指向并非是如何通过技术有效地提升劳动生产率,而更多地是为了安全生产,其方法显得简单和粗暴。在这样简单的控制下,工人成为被制定好的生产程序中顺从的工具。
(二)工会维权功能名存实亡
以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的形成是要有工人群体利益作为后盾的。调查发现,虽然企业都有着完美的工会组织,但是其职能的发挥却是在与简单控制型的劳动关系相互呼应,很少能够做到为工人维权。一方面,工会组织的范围是特指长期固定工的;另一方面,在管理者眼中,工会并没有成为可以与其相谈判的力量,而是一个可以配合其组织安全生产的工具。
DL公司的工会很建全,但其工作主要是:纠纷调解、女工的孕期保护、身体检查、计划生育以及死亡职工的丧事筹备等;工会还利用工作之余组织文体活动,例如广播体操、足球赛、羽毛球赛、踢毽子比赛、爬楼梯比赛等;此外,工人的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也是工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工会配合教育处办夜大,组织电脑培训、文化补习、党课学习,出黑板报,开办图书室,进行安全教育、安全生产监督等。对工会的性质和功能,2003年刚刚退休的厂工会主席说(注:被访者曾在1991-2003年间担任三届工会主席。访谈人:佟新、王春来,资料整理:王春来。):
“工会首先要维护企业的利益,才能真正维护工人的利益,不能只是片面地强调单方面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就是生产和经营,要把工会工作融入到生产中去,只有这样行政部门和党委才能都满意……十多年来,我们工会工作都是用在生产上,如上岗培训、劳动竞赛、提高工人自身素质……。车间工会工作主要围绕生产展开,工会作用中很重要的是自己配合行政,把生产经营搞上去,要把握好角色,找好自己的位置,做好配合工作。工会没有实权,工作就是靠感情、靠面子。工会有很多事都要依靠行政去办,比如批假、给钱、分房等。女工孕期可以回家休假,能保留岗位,但只能给三、五百块钱,工会可以出面给她协调安排,要靠你的面子去跟下边车间说,主席太年轻了人家不给你面子,你就办不了……所以工会主席的工作靠人熟、靠人缘、靠面子而不是靠权力,所以还是年纪大点好办事。”
工会的初衷应该是代表所有工人的利益,但是对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务工来说,工会显得无能为力。DL公司的工会主席说:
“工头带来的人,干的也都是造船厂的活,只是采取的是承包方式,我们负责质量监督和考核,船东也监督。包工头都有技术证书,这些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就相当于外来公司派到我们厂干活的人,从关系上来讲,应该是不归我们管,但是老板是不可能维护工人的利益的,如果我们不管,这些人是最惨的。有的工人来找我就是因为工头不给工钱。他们是在我们厂的大院内干活儿,虽然不是我们厂的人但我认为也应该管一点,但不能像国企职工那样往上套,要一点一点地渗入。我们现在还没有要求他们建工会。”
包工头(JT船务的包工队长刘先生)对工会的理解是:
“正八经儿建立好的工会对我们确实也有好处,因为中国的工会和外国的工会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工会最好不能特别向着工人,但他们会在工人稳定性上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工人本身没有要求建工会,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
在市场压力下,工会认同企业的绩效目标,在这一简单化的目标下,工会很难做到为工人维权。
(三)低价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不公正性和残酷性
以农民工为主的、低价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曾远离国有企业,他们仅仅是民营企业或外来加工业主要的用工形式。而对国有企业大量使用农民工的发现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一个低价的、以农民工为主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公平性,它强加给所有劳动者一个重要的特性——工作的不稳定性。
此外,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用工体制和农民在农业上的低收入形成了对农民工剥夺的合法性基础,有利地支撑了国有工业企业简单控制型的劳动关系。当国有工业企业技术人员呈现出个体化谈判谋求其市场利益时,固定工和劳务工的分化强化了市场分割,农民工成为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供给的最大的蓄水池,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促成了残酷的竞争。爱德华兹在分析权威关系时重视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把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部分地视为企业内的劳动交换体系,以解决晋升、替换工作、设置工资等问题。布若威则进一步讨论了内部劳动市场有助于促成掩饰及确保榨取剩余价值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方法。(注:[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1页。)国有企业只需要透过低价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员工激励、晋升、替换工作等问题,
外协队或劳务工之间还存在激烈竞争,这不仅弱化了外协工人斗争的可能性,同时,它还有效地压低劳动力价格。DL公司包工头刘先生说:
“存在竞争问题,要是我给工人工资低的话,他会跳槽,有时只因为日工资相差一元钱,他就会到其他队去,特别是四川籍的人很计较。……我打个比方来说,按照他的技术水平只拿到30(元)到40(指日工资),40就顶天了,拿30不为过,但是人家(其他的包工队)给提上来,一个月给你60,这种情况也有。于是这个人就说,哎,人家给我60,你给我加20。这能加么?肯定不能加,因为他的技术水平我知道,就值40块,你跟我提出来了我也不能加,不能用你,所以他只能到别的外协队去。上别的队后可能头一、两个月给他60块,因为既然叫你来了,得把我这摊儿给支起来。等这个队人员满了,全队人够了,他(指另一个外协队长)就开始压工资或砍人了,不干你就给我走人,我不要你了。”
上述谈话暗含了工人与包工头们之间的斗争,其结果却是令人无奈的,而对抗争结果的预期会进一步增强包工头的心理优势,促成包工头之间的结盟,从而瓦解了工人斗争的可能。DL公司的外协队中,我们发现出现了工人基于地缘关系的“抱团儿”现象,有“四川人爱抱团儿”、“安徽人抱团儿”等说法,这些“抱团儿”的工人有时会一起要求涨工资。但这种地缘关系建立的非正式组织,几乎没有组织化程度可言。与此同时,外协队的队长之间由于害怕出现因工资差异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也展开了合作。有9个外协队签订了一个共同协议,内容是不能随意接受其他队的工人。这虽然没有完全克服工人的流动,但包工头间的结盟也得到了DL公司的支持,它使外协工人的抗争弱化,并加剧了外协工在DL公司的扩大化趋势。
JD公司的情形也有相似之处,他们是通过与劳务工签订短期合同来大量使用农民工的。前文谈到,这家公司由于远离其居住地,正式的固定工每个月是连续工作22天,再回家休息8天。而这8天的工作替换全部由劳务工解决。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为国有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工资收入低又好操控的劳动大军。杜师傅是来自河北省的一名合同工,32岁,已在JD公司干了一年多。他说:
“我们那边的劳务公司招了五百多人吧,光到华北井下就一百多人,到这里也是一百多人,我们的合同上写了,只要能够干满8年,就可以转成这个正式工。我们没有加入工会,这个正式职工肯定都有工会吧。我们喜欢在国有大公司,工资是有保障的。好的一年挣两万块钱吧,不好的一年也挣一万四五,要是不回家的话,一年也是一万七八。在老家,一般像我这个年纪的几乎都出去了,他不可能在家,在家干嘛啊?农业几乎是没什么收入。一般是种了一年的地,有种子钱,有化肥钱,现在机械化这种东西比较多,好一点的机械化的费用也不能留多少钱。我们家的地也不是特别多,因为原来是有六亩地,国家要求退耕还林,我们退了一亩二,还剩不到五亩地,由老婆在家做。我们好像没有老乡关系,只要能说到一块儿去,合得来的就行。另外,国有大公司的好处吧,是万一出了事是有人管的。我们都上了工伤保险。我原来曾在我们家那边的一个工厂做,是做铁加工的,那要出了事,人家能赔你一、两万就不错了,而国有大公司先是很少出事,再是给付的也多。”
正是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具有的弹性和低价,为国有工业企业简单控制的劳动关系奠定了基础,并破坏着固定工可能潜在的各种反抗,为寻找稳定的工作,固定工们都很驯服。正是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将固定工与劳务工们各个击碎,成为生产的工具。
五、小结和理论讨论
目前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的转制基本完成,形成了现代公司法要求下的国有公司。在公司化的国有企业中,劳动关系主体呈现出等级化形态,每部分劳动关系主体隶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并有不同的行动逻辑。经营管理者不仅被纳入到政府官本位的官僚体制内,他们还在政府的鼓励下不断实践着以绩效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目标。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固定工和劳务工处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中,并经由这些市场在分配、社会保障水平、奖惩制度及进修培训等方面出现等级化的特征。
劳动关系主体的等级化为国有工业企业简单控制型的劳动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一劳动关系形态的产生绝不是简单地在企业内部完成的,它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有着重要的依存关系,它深刻地依赖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体制,以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实现了对劳动力最低成本的简单控制。同时,这种简单控制型的劳动关系被多种国家力量所默认,它有效地瓦解了工会的作用,并使固定工以及劳务工们在市场中碎片化。
第一,简单控制型劳动关系与李静君曾经提出的“失序专制主义”不同,一方面本文不想使用太过西化的“专制主义”或“霸权主义”等提法;另一方面,我们在国有企业看到劳动控制是如此的简单和粗暴,在管理者的支配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管理者是有意识地、公开地利用了低价的非正规劳动力,将其视为实现企业绩效的法宝。这个残酷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实现了管理者的简单控制。第二,国有企业中上下级之间的忠诚与庇护关系是否存在呢?如果说它存在的话,它只存在于国家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上,国家不仅授权经营者,还给予了他们重要的物质庇护。而国家对劳动者的庇护已经交由市场了,还有一些老员工受到国家相关劳动保障政策的庇护,但随着这些工人的老化,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就更多地被市场化了。第三,在上述意义上,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显示出国有企业的发展前途堪忧,因为简单控制型的劳动关系以短期绩效为取向,破坏了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以信任为主的社会资本的积累。那么,以非正规劳动为基础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很难建立起以集体谈判为基础的和谐劳动关系,并潜在着诸多安全隐患和合法性危机,重新建立一支具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能够团结的劳动者队伍是国有企业最具现实意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