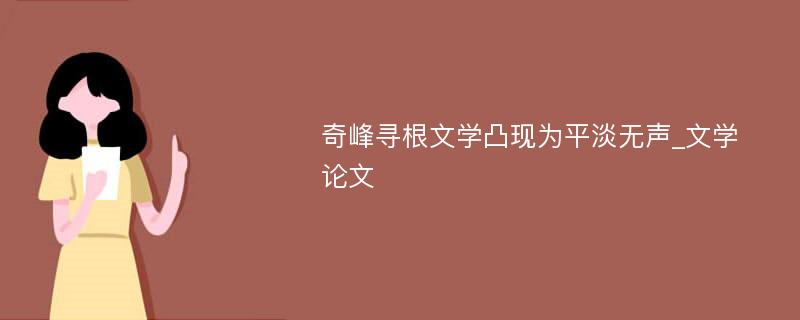
由奇峰突起到平落沉寂的寻根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峰论文,突起论文,沉寂论文,文学论文,到平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以开掘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为特征,以重塑民族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为宗旨的寻根文学,产生于世界涌动着的“同祖先对话”的文化潮流的大背景之下,而无力抵御传统文化道德中的消极成分的影响则是其由奇峰突起走向迅速平落的根本原因。
主题词 寻根文学 突起 平落 审视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许多人还沉湎于反复抚摸因十年动乱给人们留下的难以弥合的伤痕,或者还在对造成这场空前浩劫的成因进行反思探索的时候,中国文坛上突然涌起了一股以向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开掘为特征,以建树民族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体系为宗旨的创作潮流,这就是“文化寻根”小说。
寻根小说由八十年代中期的奇峰突起到八十年代末的突然平落,前后历程不过四、五年时间,但它却给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对中国古典美学境界的有意识的追求和重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回顾和审视这一文学思潮,我们不难发现:国际性的“同祖先对话”的潮流是其产生的文化大背景,将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是其鲜亮的理论旗帜,重塑民族性格、精神、品德是其创作上的目标追求,而无力抵御传统文化道德中的消极成分的影响则是造成其迅速归于沉寂的根本原因。
一、时代背景:世界涌动着一股“同祖先对话”的潮流
早在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并号召广大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到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中去,确立为人民大众特别是为工农服务的思想,以自己的创作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大批作家就自觉地分赴到曾经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赖以发育成长的重要摇篮——黄河流域的那一片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神奇的黄土地,深入到了他原先并不熟悉的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之中,去认真体味研究中国农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努力发掘钻研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民族风格,很快掀起了一股以表现北方农民的生活、命运为中心的“寻根究源”式的创作热潮,并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与工农民众生活土壤的成功的作品。《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些作品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民众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热情讴歌了他们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风姿与意志,也创造出许多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既有民族传统色彩又富有新的时代气息的艺术形式,从而真正实现了“五四”以来长期处于狭小读者范围的新文学与广大中国农民的历史性的“对话”:农民从新文学中得到现代科学、民主与文明的启蒙和影响,并加速了自身的觉悟;农民的觉悟则促进了解放区群众性文艺创作热潮的兴起和民族传统文艺的复兴;传统艺术形式的发掘与追求又有力地推动着作家、艺术家们更加自觉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无庸讳言,解放区文学的“寻根”运动既促进了新文学与千百年来生养栖息在黄土高原的北方爱情的“对话”,但也由于这一运动过份地强调了作家要到农民中去接受教育与改造,使其在接受了农民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阶级意识以及他们身上所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情操和审美意超的同时,又因对农民意识中的狭隘、保守、消极的成份缺乏自觉的抵制而不自觉地接受了某些传统文化道德中的封建性因素和农民的小生产意识的消极影响。这一消极影响不仅束缚了解放区文学“寻根”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将是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涌现的“文化寻根”小说热潮迅速平落的重要原因。
滥觞于日据时期,兴盛于五、六十年代,延续至今天的台湾“寻根文学”,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是台湾文学中举足轻重的、带有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一百年前的甲午之战,清廷拱手将辽东、台澎割让给了日本。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但不久又因国民党败据海岛而继续与大陆隔绝分离。即使如此,人们仍然看到,在民族紧要关头,两岸人民始终以同胞骨肉的情谊,并肩迎接历史的挑战。因此,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台湾的文学家们仍然顽强地思念和认同于祖国大陆。如赖和的《讼善人的故事》,杨逵的《模范林》,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钟理和的《原乡人》,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浊流三部曲》都自始至终将台湾的命运和祖国大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或认同、或回归、或关怀思念祖国大陆的倾向。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寻根文学”,可以说是继承了三、四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这一光荣传统,虽然它少了反抗外来侵略的那份悲壮,但仍然表现出凄凉哀伤而又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例如钟延豪的《过客》,写老兵罗多年从部队退役后已做了中学教师,却“终日里只捧着发黄的、大陆上的妻的照片喃喃地念着。”曾心仪的《等》,写一个退伍老兵,为了生活,用伤残的手给人擦皮鞋,可心中深藏着等待有朝一日返回老家湖南的故土之恋。聂华苓在《台湾轶事·写在前面》中说:“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於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写在前面”中说:“书中牟天磊的经验,也是我的,也是其他许许多多年轻人的。他的‘无根’的感受,更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共同感受的。”白先勇在《蓦然回首》一文中也说:“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诗人们则祷告着“请让我留在梦中不要哭醒才好”(纪弦《梦终南》),询问着“哪一朵白云下是我的故宇”(符节合《白云》),呼唤着“让我回到你们的怀抱里久久的安息吧”(钟鼎文《留言》),悲泣着“故国的泥土/ 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洛夫《边界望乡——赠余光中》),惊喜于“而孙子却说/那地方好近/把岸拉过来/ 不就是老家吗”(罗门《遥指大陆》)。由此可见,台湾及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学”,实际上反映的是离乡去国的游子们的那种依恋民族故土、思念亲人同胞的痛苦情怀。
由于无根,便有了乡愁,于无边的乡愁中便渴慕着寻根、渴慕着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这就是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寻根文学”的发展走向,即由悲怆哀歌的“无根的一代”向回归觉醒的“归属的一代”的转变,例如余光中在诗中将自己比喻成“在国际的鸡尾酒中,我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到台湾后怀念大陆。在海外怀念的是整个中国”。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留学美国,度过漫长的漂泊寂寞的生活,学成回台省亲,亲眼看到台湾人的无聊与空虚,但在金门岛眺望祖国大陆时,迷惑中却深切地感受到,根就在隔海的那一边。《傅家的儿女们》则借人物之口明确表示:“现在台湾是中国的,将来台湾回归也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旅居瑞士的赵淑侠的长篇小说《塞纳河畔》,也以众多的人物形象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了旅欧华人同时以大陆和台湾为根的动人故事。这些作品都以新的视野展示出了台湾及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学”的新风采,少却了许多的悲怆与绝望,增添了无穷的觉醒与光明。
虽然台湾的“寻根文学”与产生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寻根文学”,在其产生的社会形态、人文环境方面,以及作品具体内涵和作家的生活经历等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但作品中透露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企求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促进民族自强自立,以及以执著地认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渗透着某种文化批判精神与文化再造的追求上,却有着相当惊人的一致。
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自1976年问世后,不仅震憾了美国黑人的灵魂,唤醒了他们的寻根意识,而且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小说具体而形象地描写了一个黑人家族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小说深刻地揭露了种族歧视政策的罪恶:仅仅因为黑种人天生的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就受到无穷尽的压迫凌辱,被捕捉,被拐卖……他们被剥夺掉包括姓氏在内的一切,成为没有归宿的“黑鬼”游魂。但是,他们却偷偷地、固执地保持着本土习俗,用石子记年,用土语说话和指称事物,一代接一代地传述着自己的经历和家史,念念不忘自己的“根”——非洲人。小说真实地叙述了这个家族前后6 代人如何丧失家园、丧失自由,沦为奴隶和在重新获得自由之后自强不息的奋斗过程。小说还对非洲古朴的奇风异俗,黑奴被贩卖的苦难历程,美国农奴主的斗鸡竞富等情景进行了细腻传神的描绘。这些都为后来各国的“寻根文学”提供了写作上的成功范本。
与当年哈利远赴西非“寻根”相呼应,九十年代一大批大洋洲作家也争相撰写反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代历史生活的作品,掀起了一股更强劲的“寻根”热潮。例如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斯·科特纳的长篇小说《土豆工厂》,通过一家几代人都靠在土豆工厂削土豆皮谋生的命运历程,回顾了当年的澳大利亚曾作为英国流放罪犯的海外农场及土豆加工厂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新西兰虽然没有象澳大利亚那种被英国作为罪犯流放地的“历史的尴尬”,而那些由英国移居来的当年的手工业工人的后代们,却在寻求祖先根源的过程中,发现了他们已拉远了与英吉利民族的距离而更接近于亚洲的“地理的尴尬”。因此,当文森特·奥萨利文的追溯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那段历史的小说《大河奔流》问世后,马上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一方面对作品中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古朴的风俗文化产生出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情,另一方面又对于英裔新西兰人那一段令刻骨铭心的偏离本民族发展“跑道”的历史而感到难堪和迷惘。正如新西兰著名书评家克·利所感叹的:“同祖先对话的结果,是让心境得到了宁静呢,还是更加困扰?”
同祖先的“对话”,不但表现为文学的“寻根”,还体现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例如近年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兴起的儒学热。学者们不仅高举起“儒学文化圈”的旗帜,而且公开宣称,儒家思想已不再是中国的独家财富,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变成了他们各自的国家学说。有的国家甚至将其奉为治国安邦的法典。许多日、韩企业家,运用儒家学说管理企业,在企业内部营造出“家”的氛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东南亚各国华裔则普遍认同于“炎黄文化”,景仰忠孝仁义,崇拜孔圣关公。
这一切都说明了,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寻根”热,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可以说,纵向上它承继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探寻源泉的传统,横向上则是对延绵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寻根文学”的呼应;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学文化)的赞美,以及世界范围内涌动的“同祖先对话”的潮流,加速了它的发育成长;但浩劫过后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要求追回被“十年文革”所割断了的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才是其赖以生存的真正的广袤土壤。
二、理论旗帜:文学之根应深值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寻根文学不仅在主题和题材的开拓方面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表明了它的卓然独立、与众不同,而且也是新时期唯一的能在文学视角和文学思维方式的探索方面由作家们自己树起鲜亮的理论旗帜的文学创作潮流。
早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浪高过一浪地涌上新时期文学圣坛的时候,不少作家已悄悄将目光转向对千百年来积淀的历史和传统的反顾之中。他们以各自特定的人文地理区域的风土人情描写来营造崭新的作品风格,以浓郁的哲学思辩意识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观照来区别于传统的“乡土小说”,很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创作群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许多作家已经显示出确定的地域文化特征,例如贾平凹对商洛文化的审视,王安忆对黄淮文化的眷恋,韩少功对湘楚文化的开拓,莫言对齐鲁文化的钟情,李杭育执着葛川江文化寻根,乌热尔图留连于大兴安岭的原始风光,郑万隆漫话着北大荒的异乡异闻,郑义固守着晋文化的营盘,阿城盘桓在云南丛林……。最初,尽管他们极力避开都市和现代生活,执意描写原始荒野的奇风异俗的创作成绩亦曾受到评论界的注意,但作为一种共同的追求和总体的趋向却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于是,作家们禁不住自己站了出来,阐明其创作主张,亮出其理论旗帜——“寻根”。
1985年4月,寻根文学的首倡者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 紧接着,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贾平凹的《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李杭育的《文化的尴尬》和《理一理我们的“根”》,以及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文章相继发表。其间,《文艺报》在发表了阿城、李陀、郑义等人的文章及编辑部整理的《他们在寻“根”》的理论动态后,于8月10日起, 组织发起了“关于文学寻‘根’问题的讨论”,适时地将“文化寻根”的理论探讨迅速推向了高潮。
综观这场由作家们发起,同时又以作家为主体的理论论争,尽管在探索的深度和广度上并不一致,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意见相左,但在对“根”的内涵的理解、“寻根”的目的和方式等方面,作家们则有着十分一致的认识。
在对“寻根”内涵理解上,作家们普遍认为,所谓文学的“根”,就是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而且,这种寻根“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韩少功还说:“毛泽东同志说过源与流的关系。我们说创造源于生活,一方面指源于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另一层意义,应该是指源于劳动人民中间丰富的文化成果,即大量的还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吧。”这些论述,既是韩少功对文学源泉的理解,也是他对文学的“根”的界定。因此,他特别强调对于民族甚或民间的传统文化的开掘,并指出:“如果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就更加前景暗淡了。”贾平凹很赞赏这一观点,因而在《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中肯定地说:“中国的文学是有着中国文化的根的。”李杭育在《文化的制约》中也明确地认定,所谓“寻根”,就是重新认识我们的民族,“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尽管他们的表述语焉不详,但都认同于韩少功的理解与界定:“根”即民族传统文化。基于这同一认识,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便无一不是取材于穷乡僻壤、大山峡谷、荒原老林、古堡江滩,无一例外地表现一种原始、闭塞、古朴的地域文化与蛮荒生活。
关于“寻根”的目的,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是这样表述的:“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情,来自铸和镀亮这种自我。”在《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一文中,他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东方文化自然有很落后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阿城则认为:“中国文化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先进水平对不起话的。”所以他断定:“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综上所述,“寻根”的目的,初级层次是促使文学的进步,以期望能与世界先进水平对话;高级层次是寻找东方文化的优势,镀亮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的自我;最终目的则是重建东方精神文明,为中华民族的发达腾飞作贡献。
关于“寻根”的方式或者怎样寻根,作家们认为,一是要努力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即民族的文化积淀,二是努力把握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郑万隆在《我的根中》中说:“如若把小说在内涵构成上一般分为三层的话,一层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的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曰文化结构。所以,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他们都主张从深层次上去重新认识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至于如何突破认识上的拘囿,郑万隆主张:“文学的丰富个性、主观性和具体性的美学魔力,来自于把握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独特理解。”他们特别强调的是营激活起自身的全部感官去拥抱生命、感知生活,藉此去“跨越文化断裂带”(郑义语)。于是,在寻根小说中,充溢着“理想世界和经验世界的投影”(郑万隆语),人们生活在初始的文化洪荒状态,生命在混沌无序的自然状态中运动、撞击、升腾和坠毁。
三、创作追求:重塑东方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
康濯在《治伤思过和“寻根”》中指出:寻根文学是“以宏观上对我国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的追求为特征,微观上则体现了对我国人民生活中民族性格、精神、品德,以及文化和哲学心理、历史传统和民风习俗的重视。”这既是对寻根文学内涵的界定,也是对寻根文学特征的概括,同时还揭示出寻根文学创作上的一种理想追求。当然,这种理想追求的最直接的表述,还是韩少功所说的,重塑东方民族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体系。
寻根文学在重塑东方民族新人格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为潜力发掘生活在初始文化状态和蛮荒历史陈迹中的先民们的那种原始情操和原始人性,展示出我们古老民族所固有的那种于愚昧中透出淳朴风情、于麻木中显露坚毅韧力、于残忍中示展顽强精神的人格力量。
例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丙崽的身世命运,既集中了我们民族的自以为是的、不事上进的劣根性,又观照出整个民族陈腐没落而又生生不息的生存意义,既象征着一种退化了的历史文化生态,也揭露了我们民族本性中的赖以生存却又难以奋进的一个“谜”,这就是:愚昧与纯朴、麻木与坚忍、残酷与顽强并存的不死的民族人格精神。
寻根文学在重塑东方民族新心态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努力探究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嬗变的轨迹,重新审视原始生命状态下的古老民族如何在压抑中奔突、重负中挣扎、逆境中苦斗的艰难前行的心路历程。
如果韩少功的《爸爸爸》是旨在揭示历史文化积淀中的劣质性的话,那么阿城的《棋王》则是侧重于寻求民族民间文化中的优质性。阿城在谈及《孩子王》的创作体会时曾说:“文化所涵,博大精微。……我们许多不自觉的行为,无意识的表露,愚蠢的背后,固执的念头,无一不是我们的心态。”《棋王》正是通过对下层平民本于衣食而超乎衣食的生活态度的探讨,来展示老庄思想影响下的知足常乐、无为而无不为的民族文化心理;并通过“我”对王一生的认识了解,来揭示出一个平常百姓了悟人生的心态历程。王一生不因逆境而悲,以知足为乐,“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不以名利为贵为荣,不以朴俗为贱为辱,安贫乐道,归朴守真;不以“智者”为智、“愚者”为愚,拒绝给地区副书记送礼,而甘拜拣破烂的老头为师,这些都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我”虽曾有过衣食无着的经历,却羞于谈吃,觉得如此这般会腐蚀了自己;虽然觉得山沟里会“活不出个大意思来”,却总是“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只有在亲历目睹了王一生拒绝突然降临的参赛夺魁、调文化馆的机会和车轮大占获胜后的那份平静坦然,才明白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于是在王一生的鼾声中,“我”终于悟出:“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象人。”这恐怕正是作者所要寻觅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种“根”和旨在向国民推崇的超乎俗见的优秀的东方民族新心态。
寻根文学在重塑东方民族新精神方面的努力,基本着眼点在于关系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的发现与寻求,它既包括对生命的起源与存在的秘密的寻找,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的感应、生命与宇宙的交流的寻找,还包括对民族精神中的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肯定和对平稳恒定、中庸之道的批判。
莫言在《红高梁家族》中借助先辈中国人波澜壮阔的生活场景,写厮杀、写恋情、写乡土人情,满怀崇敬的激情讴歌民间村野的自由抗争精神。作品所展现的种种村景民风,以及粗犷的爱情、殊死的战斗、暴虐的场面,都带有浓烈的主观激情和浪漫色彩。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罗汉大爷还是我爷爷或者我奶奶。无一称得上英雄人物,身上亦不乏并不光彩甚至阴暗的东西,但是他们都具有一股荡气回肠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写一名鄂温克族少年,冬日首次狩猎打伤了一头七岔犄角的公鹿,第二天追踪时却被它顽强与狼搏斗的英姿所震撼。开春后与继父出猎重遇这头公鹿,并故意将它惊跑。第三次遇到这头公鹿正是它被狼群包围的时候,他开枪救了它却反被它踢伤。小说通过鹿的意象,揭示了一个被遗忘的民族的历史命运,也发现了鄂温克人朴素的生存信仰;通过东北密林自然景观和狩猎场面的描写,创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神奇世界,并折射出鄂温克少年纯真美好的精神世界。扎西达娃在《西藏,系在皮带扣上的魂》和《西藏,隐秘的岁月》等作品中,发现了藏民族在现代的物质潮流中,与传统与历史割不断的精神维系。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描写了回回与麦绒(《鸡窝洼的人家》)、才才和王和尚(《小月前本》)们在变革大潮中,安于现状,死守着“向土坷垃要吃喝”的陈规,在平稳恒定中与时代拉下很远的距离。王安忆的《小鲍庄》描写了一个充满传统美德“仁义”的小鲍庄人,骨子里竟是那么因循守拙,那样愚昧绝情,拾来与寡妇二婶因相爱相怜而结合却不被小鲍庄人所容忍;鲍秉德妻子的发疯和自杀的原因是连生了五个死胎并受不了人们的闲言碎语;鲍秉德固执地认定妻子疯了本属天意用不着送医院治疗……。小说试图通过展示“仁义”这种传统道德在贫困、闭塞的乡民们身上具体而复杂的渗透和影响,勾画出一种凝滞的生活和思维模式,以此来辨析数千年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对于现代生活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而达到去劣扬优的目的。
寻根文学在重塑东方民族的新思维和审美体系方面的努力,常常是通过刻划人们的行为习惯来探索传统文化制约下的人的思维定势与行为模式,表现普通人在历史文化熏染下的审美标准和生活态度;其笔触由现实的表象探向历史的积淀的目的,一是寻找东方文化的优势,一是疗治现实承袭的疮痕。
韩少功在《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中曾经指出:“东方文化自然有很落后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寻找优势的目的是,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的体系,以此来影响社会的意识与潜意识,为中华民族的发达腾飞作出贡献。他的《爸爸爸》恐怕正是由这种“寻根”意识结晶出来的一个重要成果。郑义笔下的老井村原本是个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的“世外桃源”,由于人们开荒垦地,砍伐树木,致使自然生态失去平衡,河干井枯,吃水困难,受到了自然规律最严历的惩罚。虽然生的艰难培育了老井人顽强不息的精神,生的延续又激励着老井人互助求同的仁义理想;但老井人精神上的匮乏,又直接折射出民族文化中的暗谈的一面。李杭育在“葛川江系列”小说中,用葛川江即大自然的眼光来审视人类活动的历史。葛川江的波涛既陶冶了两岸人民慓悍不羁的性格,也造就了他们的顽固愚钝的思维。《珊瑚沙的弄潮儿》中的弄潮老头,固执于自己的迷信,固执于自己的自负,宁死不肯跟二潮头上岸,结果在潮水中丧生。《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渔佬,在已经前进的时代面前,仍然顽固地坚持从上一辈渔民那里继承来的生活方式,结果被时代抛弃,连相好的女人也离开了他。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以黑龙江边一个汉族淘金者和鄂伦春猎人杂居的山村为背景,刻划了一个放逐于现代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心理意识,充满神秘色彩、奇人异事的世界。
与寻根小说创作理想的追求相一致的,其艺术风格也呈现出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将笔触伸向区域文化。寻根小说的作者,大都立足于各自的地理区域,努力发掘民族文化心理、历史文化背景、传统文化素质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潜心创作出不同文化领域的作品。如韩少功湘楚文化的恢弘,李杭育吴越文化的气韵,贾平凹秦汉文化的古朴,郑万隆远东文化的神奇,钟阿城道家文化的玄远等等。二是将目光转向神话传说。寻根小说的历史指向决定了它不同于以往写实小说的审美选择,努力利用神话、传说、梦幻、奇风异俗以及来自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来构建小说的气氛、情绪和意象,是其突出的艺术特征,小说的深层意蕴也往往就在其象征意味与神秘感之中。
四、平落原因:无力抵御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的影响
寻根文学的历史功绩在于:其一,深入开掘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拓展了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内蕴,丰富了小说创作的审美内涵,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具有了世界意义,并在相当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潮。其次,寻根文学的出现,使得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由政治的批判、经济的思考推及文化的审视,由现实的生存处境推及历史文化的积淀,由民族的生态推及民族的心态,由改革的艰难推用民族命运的艰难——这种文学视野的变革带来了文学思维方式的更新,从而使作家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综合立场来鸟瞰现实。
寻根文学从八十年代中期的奇峰突起到八十年代后期突然归于平落沉寂,前后不过三、五年时间。平落的原因,除了商品大潮冲击下的作家队伍的分化之外,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对于传统文化道德中的消极因素抵制不力,因而影响到作品的品位和探索的深入。就创作实际而言,有的作品在对待传统文化消极方面的影响的态度上,欣赏有余而批判不足,有些作者津津乐道于某些与民族文化道德和民族欣赏习惯不符的恶习陋俗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沉溺于从歪曲畸形民族风情、背道离经的宗教传说中“寻根”;有的作品在表现民族文化劣质心理时,对那些远离时代、远离社会的邪恶、仇恨、隔膜、荒唐的现象一味地客观展览,思想内容庸俗,文化格调低下,甚至带有民族鄙视性,因而引起少数民族同胞的不满和反对。就理论探讨而言,由于人们对文化的内涵理解不一,对于文化这一涵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总和的大概念认识不足,所谓文学“寻根”成了以枝叶而寻根本,这就很容易造成文化大概念与文学小概念之间位置的本末倒置;其次,“文化断裂论”的提出,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也否定了新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渊源关系,不仅客观上不符实际、理论上失之偏颇,而且给人们以虚无主义之误导,为稍后出现的某些否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绩的论调提供了口实。
文化寻根的热潮虽然早已沉寂平落,但它在推动新时期小说探索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它在拓展小说创作文化内蕴上的努力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的共识。
注:收稿日期:1995-11-01
标签:文学论文; 寻根文学论文; 韩少功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寻根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台湾生活论文; 爸爸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