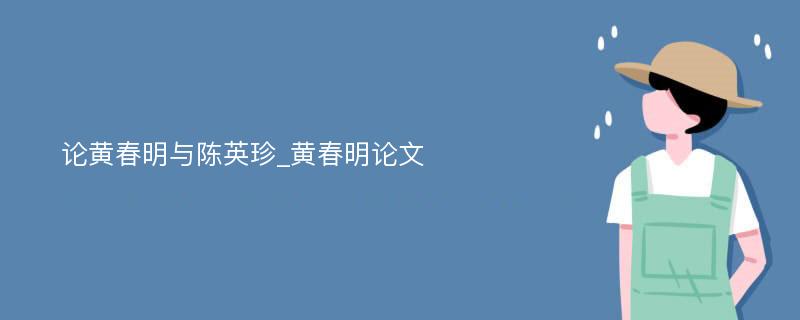
试论黄春明与陈映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黄春明论文,陈映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黄春明文学创作的动能,来自他自己的生活记忆。相对于疾步资本主义化的台湾西部平原,黄春明位处东北海岸的故乡,一直保持着更贴近土地的踏实与素朴。这样的人民日常生活,成为黄春明记忆中的最鲜活跃动的场景。这些扣紧特定历史脉络、生活场域与生命经验的“记忆”,可以说是激发黄春明文学创作的原动力。黄春明的作品分期,有两阶段论,也有三阶段论。当然所有的分期都只是为了讨论上的方便。在此,本文以两阶段来区分,早期是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其中大部分是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少作;后期是一九六七年以后,风格明显包括两种,一是书写宜兰乡土人物,见证时代变迁中小人物的种种反应,二是移居台北,任职广告公司后所见的都市人事物,特别是几篇跶伐美、日两国有形无形的经济、文化侵略的作品。
黄春明最早出现于台湾文坛的时间是一九五○年代后半期,他的处女作《清道夫的孩子》,于一九五六年以春铃的笔名发表于“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团务通讯《幼狮通讯》,当时还是屏东师范的学生,这个时间约略是六○年代现代主义萌芽之前。六○年代前半期,在一片“现代”声中,他创作出一系列被《联合报》副刊主编林海音赏识的短篇小说,可是这些少作,被后期的他自己消遣说其实非常心虚,只知道拼命跟着人家“现代”,就仿佛他其中一个短篇的名字:《跟着脚走》。这意思是:跟着脚步,脚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头在这里似乎是没什么作用的——十足黄春明式的自我嘲讽。时间进入一九六七年发表《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之后,他找到一个比较不心虚的出路,就是书写他最熟悉的故乡人事,这批小说到了一九七○年代,“回归乡土”之大纛高举时,甚且还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尽管他本人并不十分认同这种“称誉”。对他而言,“乡土”并非刻意标榜或建构出来的文学虚像,反倒是真真实实的生活实存,这些他十分熟悉的人、事、时、地、物,这些确曾发生过的生活场景,在他提起笔、摊开纸张之际,自然而然地进入他的思绪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文学的素材与图像。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屋顶上的蕃茄树》一文中,黄春明清楚地述及他的文学泉源,那些乡俗小民似乎想借黄春明的纸笔发声一般:
他们像人浮于事,在脑海里涌挤着浮现过来应征工作似的,……费了很大的劲儿想把脑子里的老乡拂去。但是他们死赖活赖不走,还有我自己温情的根性所缠,只好让他们在那里吵嚷,而无奈于对。(注: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收于《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一九八九年七月),页三三。)
黄春明其实很清楚自己文学关怀的面向与缘由,真诚的“感动”是他书写的能量,他坚持写能够感动自己的题材,因为文学创作者唯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黄春明笔下的乡俗小民之所以能够感动他,在于他们内蕴的深沉生命力,而他不仅想用文学来描绘这股强韧的生命力,还要去探究这股生命力之所以燃生的原因:
我在想,所谓小人物的他们,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这么有生命力呢?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如果能写成功这种作品,永远永远,不管何时何地,都会感动人的心灵的。(注: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收于《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一九八九年七月),页四一。)
通过这一类乡土作品,黄春明与笔下的小人物都活生生地存在读者心中。随后他笔锋一转,开始以冷辣的观察、喜剧的夸张手法,点出七○年代台湾依附于美、日经济强权下,种种光怪陆离的跳梁人物。基本上已经把生而为人的种种软弱与限制都考虑进去了,所以它只反映少数细节,细节堆叠出怎样的社会实像,这还要看读者配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批显然更被理性头脑引导的作品,在主题上几乎与他《文季》时代的旧友陈映真不谋而合。第三世界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的困境,不亚于殖民时代的强力剥削,美/台、日/台间长年纠葛不清的政经依附关系,都是他们作品中挥之不去的绝对低音,反覆回旋。本文试图比较几篇黄春明与陈映真主题相近的作品,探讨其中所显示的意义。
陈映真的作品分期同样可分为三期,也可大略分为两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七年七月,也就是《面摊》至《六月里的玫瑰花》是第一阶段;一九六八年五月民主台湾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一九七五年七月蒋介石死后,减刑出狱,再经数年的沉潜、思考,一九七八年三月《贺大哥》、《夜行货车》开始一系列的“新帝国主义”作品,以迄《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系列以白色恐怖为题的作品,皆可归于第二阶段。黄春明与陈映真属于相同的文学社群,若就各自的两阶段来看,相当值得观察。
二、黄春明、陈映真小说对照年表
由附表(见第100—102页)可见,陈映真的处女作尚且晚于黄春明出现,但他的作品却一开始便集中于《笔汇》、《现代文学》、《文季》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而那早期陈映真式的苍白无告、人道关怀风格,持续的时间长达八、九年。黄春明初次跃登全国重要副刊联合报的作品是《城仔落车》,标题中已隐然显现他对城乡问题的思考,以及他小说中人物该使用何种语言的问题。也是因为这篇文章遇到了林海音,林海音的温暖鼓励和对作品的绝对尊重(一字不改,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标题),才有了后来的联副九作,时间一直持续到林氏离开联副,黄春明在这段时间内以行动表现出对编辑的忠诚度,也经由此过程逐渐成就了自己(注:黄春明出版《小寡妇》(台北:远景,一九七五年二月)时,即请林海音写序,在序文《这个“自暴自弃”的黄春明》中引述黄春明的话说:“如果您在十几年前退了我初次的投稿,我就不会继续写小说,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了。”)。
和陈映真相同的,这些作品正好也是他的现代主义实验期。但陈的为文基调已经成型,并且他一开始就是用理性思考写作的人,他写他应该写的东西、反应他认为该反映的现象与问题,黄却仍像初生之犊,在青涩中仍看得出强大的丰沛生命和极大的可变性,可以说,这只是他的试笔之作而已。
三、关怀主题的双重旋律
陈映真曾经把一九六六年当作他向新风格过渡的一个转捩点,他说:
一九六六年以后,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当陈映真开始嘲弄,开始用理智去凝视的时候,他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和他所处的世界对决。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注:许南村《试论陈映真》,收于陈映真《将军族》(台北:远景,一九七五年十月),页二六。)
陈的转变来自对现代主义的不满,他认为现代主义必须再开发,而开发之道一是回归现实、反映现实;二是知性与思考的建立,他本人很清楚地朝这方向努力。表现在作品中的就是题材多样化的切入社会各阶层,也呼应时代的脉动,例如《六月里的玫瑰花》写越战的黑人士官和台湾吧女的恋爱,《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写父子关系,也带进大陆人流寓台湾的失落和哀愁,《第一件差事》着眼点同样是来台大陆人,显见此一题材为他所独钟,一再使用各种角度,试图把一个一个个人的感情,凝塑成一种台湾时空下的生活实像(注:参见宋冬阳《缝合这一道伤口——论陈映真小说中的分离与结合》,原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美丽岛》杂志四十七、四十八期。本名陈芳明的宋冬阳在详细讨论陈映真的小说人物之身分与结局之后,指出:“以陈映真的早期小说为例,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似乎没有互相认同的地方,他们各自背负自己的历史命运,也各自生活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两个陌生的世界交会时,自然就产生了种种的冲突与悲剧。”见《陈映真作品集14》,《爱情的故事〔论陈映真卷〕》(台北:人间,一九八八年五月),页一三九。)。为表示对首善之城台北知识界的不满,特别是某些理论学说如野草般的遍地生长,知识分子却无能检验,一味盲从西方,他创作了《唐倩的喜剧》、《最后的夏日》,着实地讽刺了知识分子的虚矫姿态和无根的追逐。
一九六六年正巧也是黄春明辞去中广宜兰电台的工作、结婚、移居台北的时间,就是在这一年,他经由七等生的引荐结识了尉天骢等人,并且参与了《文季》的编辑工作。这个阶段的黄春明还在犹疑不定,台北人人都在说现代,不跟大家一样好像令人恐慌,但真正写来也有点心虚,就这样彷徨犹疑中,他留下《男人与小刀》、《跟著脚走》、《没有头的胡蜂》、《他妈—的,悲哀!》和剧本《神、人、鬼》等等他后来未收入皇冠版集子的作品。这时,他的说书人(stoy teller )特质早就受到文坛惊喜地注意,许多人肯定他的语言魅力,甚至建议他直接以录音带出版。他最擅长述说的当然还是他家乡罗东的人、事物,但这两项“擅长”的结合,还需要一段酝酿期,才会出现一九六七年以后。不过,加入《文季》,以及开始在联通广告公司上班,这样的新环境必然带来新刺激,对于美、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侵略渗透,陈映真有他的理论来源,而黄春明却有着他自己的生活体认。刘春城在《爱土地的人》一书中如此描述:
黄春明的日文不错,他不会不知道这些道理,那时台北广告公司几乎都沿用日本制度,从日本学习广告技术,上上下下满口日语和日式美语,也运用日本那一套管理观念,——员工必须绝对终于公司和工作,只是避而不谈对员工的照顾,乡下人请长工还讲一点道义,台北的工商界是决心不顾了,而我们就凭这些廉价易得和勤奋不懈的劳力创造了经济奇迹,……黄春明这个广告奇才,在那时已看出工商界的毛病,无非都是美日资本社会对付开发地区的伎俩,假本地资本者的手做代理人,来剥削一般劳苦大众罢了,跟日据时代并无差别。(注:刘春城《爱土地的人》(自印,一九八五年十月),页二五一。)
同样的,这类生活体验也必须经过沉淀,才能化为文字。他可以说是一边把那些潜藏在他心中的捶鼓呐喊、不时想要挣脱出来的故乡人物一一点化成真,一边敏锐地注意身边正发生的“台北都市进行式”,所以才有一九七一年以后的八篇城市小说出现。这些作品极其尖锐地点出台湾处于为美日两国政经边缘地带的位置和扭曲,若非如此尖锐辛辣,恐怕也难以如实反映一九七○年代一连串重大事件给台湾民众心理上带来的冲击。
黄春明笔下乡俗小民的“生命力”,展现得既卑微又尊严,既原始又真诚,总是在逆境中卖力生活,人们虽无权自主选择生命起源的时空,却有权决定如何让生命落实茁壮;黄春明笔下的人物,如《看海的日子》里的白梅,《青番公的故事》里的青番,《儿子的大玩偶》里的坤树……,都是在大环境中无法自主的卑微小人物,然而他们也都努力想在逆境中找寻可以着落茁长的土壤。
相反的,黄春明笔下的知识分子,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可以拥有较多的生活资源,但比起乡俗小民来,却似乎更加难以挣脱生命既有的框架,光鲜的外表底下,生命却无有尊严,甚至为了生活,必须甘做被摆弄的棋子。在《莎哟娜啦·再见》一文中,以日本的买春商团为主体,衍述作者对于商业逻辑非人性机制之批判,而随着黄春明本人离开素朴的罗东小镇,来到台北都会谋职,生活场域的变迁,使他更加贴近地看到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台湾急速流行与播衍的情况,也更加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迁所导致的台湾社会变迁与文化异变。被迫带领“千人斩俱乐部”的一干日本人到礁溪去嫖自己同胞姊妹的黄君,即是典型的例子,由于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跨国网络之中,充当商业资本之流通与再生产的一颗螺丝钉,黄君的身体自主权更加薄弱,他虽有满腔的不愿与不满,却无法抗拒这项充任“皮条客”的任务,至多只能借着言语嘲讽与调侃来自我安慰,用阿Q精神来壮大自己。比起《看海的日子》里的白梅, 叙述者黄君空有较好的谋生技能与社会位置,却也只能匍匐在日本“千人斩俱乐部”的“利剑”之下,成为“去势的男人”。台湾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其被殖民的状况比之日本政府领台之际并无太大差异。《莎哟娜啦·再见》中的角色与情节皆夸张地加以表现,但把台湾当年的历史情境与文化脉络则陈述得颇为贴切。
六○、七○年代以来,美国文化透过强势的国家机器以及商品行销机制进驻台湾,黄春明对此有很深沉的思索与批判,他透过俗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勾勒出一幅新的台湾民间社会图象。在这个社会图象中,生活形态的改变仅是表象而已,细究之下,黄春明更急于陈述的,是台湾既有文化价值体系的崩解,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与疏离。收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我爱玛莉》一书中的若干篇章,便是在这样的价值关怀与深沉观照中诞生的。其中,《苹果的滋味》里的建筑工人阿发,在洋人所“赠予”的苹果的滋味中,浑然忘却自己已然失去一条腿,失去可以自主的谋生资本。然而,苹果之所以美味,却并非缘自苹果本身的肉质,而是延伸自“洋人所送的苹果”之象征性意义;对阿发与家人来说,他们嚼在口中的汁液,其甘甜与其说是来自苹果本身,不如说是来自于对与西方文化沾上边的喜悦。在西方文化巨大的侵蚀力底下,一如阿发这样的庶民,长久以来为别人盖高楼,却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优质生活空间,也只能以尝得“苹果的滋味”来自我安慰。
世界体系中的主流文化挟其丰厚的商业资本,并且凭借媒介无远弗届的延展力与穿透力,对弱势国家造成经济的剥削与文化的渗透,而弱势国家的主体文化则相对地产生“渗漏”的现象,无法在保有主体意志与文化脉络的前提下向前发展。《苹果的滋味》中的阿发以嚼食洋人馈赠的苹果为乐,呈显的是令人鼻酸的卑微。然而,《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却是“黄皮肤白面具”的“洋奴型”人物,以西方生活方式为最高的价值取向,甚至甘于扬弃自己的名字,呈显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无奈的卑微,而是可厌的卑屈了。黄春明对这样的现象与其说是忧心,不如说是悲愤,他以一贯的幽默嘲讽的笔调,勾勒出所谓“洋奴”的样貌,但他真正要批判的,却并非台湾洋奴,而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巨大跨国资本体系对其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支配。
黄春明在七○年代即敏锐地观察到西方强势文化渗透、台湾主体文化渗漏所衍生的文化认同危机。他透过文字所预言的结果,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都已不幸言中。做为一个作家,黄春明有其一贯的社会关怀与人性观照,也有无可剥离的土地认同与历史记忆,以及向未来探照的纤敏触角。黄春明透过他一系列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在测量社会脉动,挖掘社会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是在探寻自己做为一个作家(知识分子),所能够站稳的着力点。
黄春明小说的主题意识,几乎完全缘自他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反思,其主角无论是乡俗小民、都会里的边缘族群、跨国资本体系中的一颗小螺丝钉,或者是以西化为傲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无法自主的无奈。黄春明对于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涵的“变迁”有着相当多的感触与思考,由于他经常是以俗民的日常生活为文学的基本视点,因此,他所见到的“变迁”便充满了无奈、矛盾与冲突,而非仅止于生活方式的皮相改变而已。
陈映真从早年左倾社会主义思想,入狱后构思“冷战体制论”,出狱后借助“依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体制。做为思想家的陈映真批判了自七○年代以来的大众消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知识分子的种种弊病,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不管赞同或反对陈映真观点的文化界,对于滔滔不绝的陈映真,都充分感受到他的雄辩。这样的雄辩家,写下了系列的经济小说《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货车》、《云》、《万商帝君》,对于跨国企业的“新殖民主义”表达了强烈的控诉。他对台湾问题的思考也开始较像是社会学家而非小说家,小说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表现工具。这可以从他出狱后,也开始从事评论工作看出来。他首先拿来开刀的作家就是他自己,这种自我批判,黄春明一九七八年乡土文学论战的尾声时也发表过《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注:《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原是黄春明一九七八年元月十六日应政大西语系邀请的演讲词,刊于二月号《夏潮》第四卷第二期,收于尉天骢编《乡土文学讨论集》(自印,一九七八年四月),页六二九——六四七。)。评论家许南村出现,带来结构庞大的后冷战体系、新帝国主义等理论。陈的英文程度本来就很好,直接吸收西方理论不成问题,加上他自己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间的亲身体验(美商瑞辉药厂),表现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过度资本主义化、人类被异化、驯化的忧心的一部分,加上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既位于东、西世界霸权争夺战中太平洋战略位置的中点,又有五十年被日本殖民统治之经验,自然大有再度被不知不觉地殖民化之危险。一般平民百姓见不及此,他这种出身小市镇,特别能体察民瘼的知识分子不能不知,更不能知而不言。黄春明本来没有这么大的包袱,然而他一定也体察到那些社会现象,因为他也任职于外资为主的广告界,既身为《文季》的大将,对于社会怪现象,不能不一吐为快。然而这类反映“买办经济”、“跨国公司”的小说,如《小寡妇》、《我爱玛莉》,由于太过急切表达理念,反而没有先前的作品自在,而充满了凿枘之迹(注:比如说评论家彭瑞金即有《我不爱玛莉》之评,吕正惠在《黄春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文星》100期, 一九八六年十月)亦如是说:“经济的矛盾必须从情节中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来,而不是让情节成为某种政治经济哲学的傀儡,不是‘创造’一个框架以后把自己的观点套进去。在这方面,《苹果的滋味》和《莎哟娜啦·再见》无疑要胜过《小寡妇》和《我爱玛莉》,也要胜过陈映真的‘华盛顿大厦’系列。”见《文星》100期,页一三七。)。
四、结论
黄春明本身是没有太坚强理论架构的人,但是由于文学活动和文坛结社的关系可以推测,他以他的敏感和直觉所感受的社会现实,经过与“亲密的战友”陈映真的相濡以沫之后,会更形确定,试着将其文学创作纳入一种巨大的解释框架中。
黄春明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得到第二届“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注:评审委员如下:王拓、余光中、李瑞腾、季季、洪铭水、陈晓林、黄碧端;得奖理由如下:“黄春明的小说从乡土经验出发,深入生活现场,关怀卑微人物,对人性尊严及伦理亲情都有深刻描写。其作品反映台湾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变迁轨迹,语言活泼,人物生动,故事引人入胜,风格独特,深具创意。”见《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会讯》第十期,页三。),他第一个想起来的人是他初中时代的国文老师,王贤春。这位年方二十五、六的年轻老师,据说是属于中国共产党青年南方工作队的匪谍,死于白色恐怖时代的枪下。她的温柔鼓励,对黄春明一生走上文学之路有莫大的影响(注:黄春明的王老师在他生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多么类似于少年陈映真崇拜与学习的陆姓外省小姐姐,她也在白色恐怖下牺牲了。参见许南村《知识人的偏执》(台北:远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自序《鞭子与提灯》,页二四。)。黄春明从来不曾表明他有社会主义思想,但从他这篇得奖感言中可以窥见,他对他敬爱的王老师的政治信仰,是同情的。他说:
她那么年轻就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纵使她的信仰跟此地的环境不符,可是她爱国家、爱民族、爱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的那种情操,不是我们一再在学习和修炼的功课吗?(注:黄春明《王老师,我得奖了》,《联副》,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文中还提及“王老师介绍我看巴金,还有一些大陆作家的作品。另外她还送我两本她的旧书;一本契诃夫短篇小说集,一本沈从文的小说集,并且常找时间问我读小说的心得。”这种影响,绝对是根源性的影响。)
这种对社会主义模糊的好感,加上对美、日资本主义明显的厌恶,使得他小说从事批判的时候,虽然可能格局不大,但目标明确,决不致误失准头。
陈映真就不同了,他在六○年代便醉心于马克思学说和毛泽东思想,并且深深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残破的中国,对共产党寄予很大的希望。一九六八年,他因“民主台湾同盟案”入狱七年,在狱中“直接会见了少小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年代”,“也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不间断的思考,形成他巨大的理论架构,他描写跨国企业也好,白色恐怖也罢,都可说是这一套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某处程度上黄春明批日批美挞伐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其基调是相当贴近陈映真的。他虽没有因政治的狂热而入狱,却也对社会主义信仰所具有的高度纯洁与理想色彩而感动;他们同样曾经服务于美、日资本为主的跨国公司,看尽外人与台人的各种丑态,非形诸辛辣尖刻的文字不足以排除心中的愤怒。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对抽象的理论之吸收并提升理论之高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之文化、政治、经济评论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占有相当的份量,也有足够的力道足以拥有甚多的信徒;黄春明则是小乡镇商家之子,多了一些世俗性、庶民性,少了一些无奈、苍白、自怜、沮丧和彷徨,他以丰富的生活体验将各色人等演绎得自然合理,人物面目身影跃然纸上。
黄春明凭着感觉,创造了丰富的文学风貌;然而当他跟着“头脑”的指导而走时,有时不由得心虚、恐慌;跟着巨大的理论试图写大作品,他的小说风格越是模糊;他越靠理论来支撑时,他的小说越变得只是演绎理论的工具。黄春明其实是不需要理论的,社会本身是他最大的一本书,生活其间,细心观察人世间的形形色色,文学家的黄春明越能得其所哉。
黄春明、陈映真小说对照年表
黄春明作品发表年代发表刊物
清道夫的孩子 1956.12.20救国团团务通讯
(幼狮通讯)63期
小巴哈
1957 新生报南部版
1962.3.24 中央日报副刊
城仔落车 1962.3.20 联合报副刊
北门街
1962.3.30 联合报副刊
玩火 1962.5.21 联合报副刊
胖姑姑
1963.2.26 联合报副刊
两万年的历史 1963.3.15 联合报副刊
把瓶子升上去 1963.3.27 联合报副刊
请勿与司机谈话
1963.4.13 联合报副刊
借个火
1963.4.29 联合报副刊
丽的结婚的消息
1963.59
联合报副刊
没有头的胡蜂 1963—1965
神、人、鬼
1963—1965
男人与小刀
1966.4台湾文艺11
照镜子
1966.10
台湾文艺13
他妈—的,悲哀! 1967.4台湾文艺15
青番公的故事 1967.4.10 文学季刊3
溺死一只老猫 1967.7.10 文学季刊4
看海的日子
1967.7.10 文学季刊4
癣
1968.1.1 草原2
阿屘与警察
1968 仙人掌
鱼
1968 中国时报副刊
儿子的大玩偶 1968.2.15 文学季刊6
锣
1969.7.10 文学季刊9
大玩偶》 1969.10
仙人掌出版社
甘庚伯的黄氏 1971.1.15 文学双月刊1
两个油漆匠
1971.1.15 文学双月刊1
苹果的滋味
1972.12.28中国时报副刊
莎哟娜啦·再见
1973.8.15 文学季刊1
鲜红虾——
"下消乐仔"
1974.1.1 中外文学20
小琪的那 1974 中外文学
一项帽子
《锣》
1974.3. 远景出版社
《莎哟娜
啦·再见》
1974.3远景出版社
小寡妇
1974完稿
《小寡妇》
1975.2.1 远景出版社
我爱玛莉 1977.9中国时报副刊
《我爱玛莉》 1979.3远景出版社
《儿子的大玩偶》 1981.12
大林出版社
大饼 1983.7文季2
《青番公的故事》 1985.8皇冠出版社
《锣》
1985.8皇冠出版社
啦·再见》
1985.8皇冠出版社
黄春明电 1989.12
皇冠出版社
陈映真作品 发表年代发表刊物
面摊1959.9.15 笔汇1:5
我的弟弟康雄1960.1 笔汇1:9
家 1960.3 笔汇1:11
乡村的教师 1960.8 笔汇2:1
故乡1960.9 笔汇2:2
死者1960.10笔汇2:3
祖父与伞1960.12笔汇2:5
猫它们的祖母1961.1 笔汇2:6
那么衰老的眼泪 1961.5 笔汇2:7
加略人犹1961.7 笔汇2:9
大的故事
苹果树 1961.11笔汇2:11—12
文书1963.9 现代文学18
将军族 1964.1 现代文学19
凄惨的无言的嘴 1964.6 现代文学21
一绿色侯鸟 1964.10现代文学22
猎人之死1965.2 现代文学23
兀自照耀
着的太阳1965.7 现代文学25
哦!苏珊娜 1966.9 幼狮文艺153
最后的夏日 1966.10文学季刊1
唐倩的喜剧 1967.1 文学季刊2
第一件差事 1967.4 文学季刊3
六月里的玫瑰花 1967.7 文学季刊4
注:1968.5民
主台湾同盟案被
捕,判刑十年
永恒的大地 1970.2 文学季刊10
累累1972.10香港某刊物
刘绍铭编
《陈映真选集》 1972
香港小草出版社
某一个日午 1973.8.15 文学季刊1
注:1975.7
蒋介石死后,
《第一件差事》
《将军族》 1975.10远景出版社
贺大哥 1978.3 雄狮美术85
夜行货车1978.3 台湾文学58
《夜行货车》1979.11远景出版社
云 1980.8 台湾文艺68
《华盛顿大楼》 1982.7 远景出版社
万商帝君1982.12现代文学复刊19
铃铛花 1983.4 文季1
1983.8
1983.10.2获
山路得《中国时报
文季3
》小说推荐奖
选、插绘《陈1985.12《人间》创刊
映真小说选》
收藏版
《赵南栋及陈
映真短文选》1987.6 人间出版社
陈映真作品集1988.4 人间出版社
十五卷,其中
小说部分为:
《我的弟弟康雄
》、《唐倩的喜
剧》、《上班族的
一日》、《万商帝
君》、《铃铛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