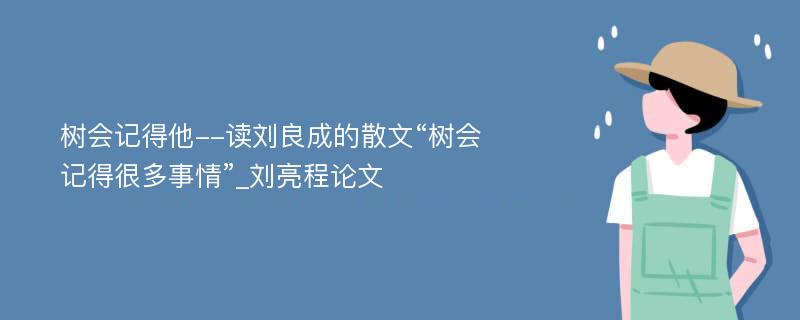
树会记住他——读刘亮程散文《树会记住许多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刘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亮程是近两年崛起的一位农民散文家,被林贤治称为“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其散文《树会记住许多事》(被《散文选刊》推荐为2000年中国散文排行榜作品)是一篇不怎么好读的作品,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梳理一下文章的大意和思路。
先看题目。有两个问题:树怎么会记住许多事?记住的是什么事?文章第一部分由五个自然段组成,作者引类设譬,以“路”的不定和“风”的随意表明它们的记忆靠不住;只有树,“从不胡乱走动”,始终在老地方站着,所以烙进树纹里的人的生存欢乐和悲哀,才会珍藏在树的记忆里。这是第二部分也即第六段所要告诉我们的。这可以说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这两部分我们不妨当作成人的童话来读。多么孩子气的设问啊!“譬如路,会丢掉(埋掉)人的脚印,会分叉,把人引向歧途”,幼稚的常识却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风从不记得那年秋天顺风走远的那个人。也不会在意它刮到天上飘远的一块红头巾,最后落到哪里”,风的懵懂无知体现在人格化的述说中,既趣味盎然又诗情洋溢。大巧若拙,于孩子气的好奇探询中,尽得一个诗人、哲学家的风流。这就是刘亮程散文的典型风格。
第二个问题,树记住的是哪些事呢?这便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所要陈述的内容。作者先是描绘了一幅静止的风俗画:全家人以父亲为中心正坐在树下吃饭喝水。这是纯白描手法写成的,朴素得无声无息。接着是写对亡父的思念之情。虽然父亲的去世,使一家人“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消失了,但作者的感情非常克制,全然没有通常那类思亲文章所具有的煽情意味。只有那句来自心灵的忏悔“我会找到早要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才情不自禁地披沥了作者的温热情怀——“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对亡父的思念提升了作者的人格操守。
树记住的第二件事显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者8岁那年,母亲在树枝上挂了一个筐;11岁那年,父亲在树杈上夹了一捆麦子;之后,就再没有取下来过。从时间上推算,约在七十年代初。一句“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隐约透露了那个时代的荒谬性。紧接着写的是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颇具反讽意味的一笔。树会记得农村的苦难。作者为什么不对那么荒诞的时代发点牢骚呢?为什么对苦难的生存状况安之若泰,丝毫没有怨天尤人的意思呢?难道“从来如此便对么”?难道存在的真的都是合理的吗?其实,这只是刘亮程人生哲学外显的一面,即肯定、认命、隐忍,其隐性的一面则是怀疑、否定和反抗,两种对立的哲学观奇妙地统一在他从容散漫的述说中。
散文的最后部分演示了树自身的命运,也即衰老的过程:先是叶子走了,树干站不住了,倒了,再挖出树根,与树干对一阵子话后,躯干被时间蚀空了,没话可说了,最终连记忆都失去了。树的命运隐喻着人的宿命,世界从来就是这样,世间万物从始至终都无法摆脱这样的悲剧意味。最后,作者只能无奈地叹息:“至少,能有一棵老榆树活在身边,与我共享全部昔年。”
刘亮程走近一棵草,一棵树,一条牛,一只虫子,在最平凡琐屑的生活细节中,体察人和自然的命运,展呈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哲学家独特的生命体验。
刘亮程志不了一棵平凡的榆树;同样,树也会记住他的。
【附】
树会记住许多事
刘亮程
如果我们忘了在这地方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锯开一棵树(院墙角上或房后面那几棵都行),数数上面的圈就大致清楚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其它东西也记事,却不可靠。譬如路,会丢掉(埋掉)人的脚印,会分叉,把人引向歧途。人本身又会遗忘许多人和事,当人真的遗忘了那些人和事,人能去问谁呢。
问风。
风从不记得那年秋天顺风走远的那个人。也不会在意它刮到天上飘远的一块红头巾,最后落到哪里。风在哪停住哪就会落下一堆东西。我们丢掉找不见的东西,大都让风挪移了位置。有些多少年后被另一场相反的风刮回来,面目全非躺在墙根,像做了一场梦,有些在昏天暗地的大风中飘过村子,越走越远,再也回不到村里。
树从不胡乱走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那棵榆树,还在老地方站着。我们走了又回来,担心墙会倒塌,房顶被风掀翻卷走,人和牲畜四散迷失,我们把家安在大树底下,房前屋后栽许多树让它快快长大。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人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住。像一辆奔跑的马车,摔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附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土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
风刮到头是一场风的空。
树在天地间丢了东西。
哥,你到地下去找,我向天上找。
树的根和干朝相反方向走了,它们分手的地方坐着我们一家人。父亲背靠树干,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地上或木头上。刚吃过饭,还要喝一碗水,水喝完还要再坐一阵。院门半开着,能看见路上过来过去的几个人、几头牛。也不知树根在地下找到什么。我们天天往树上看,似乎看见那些忙碌的枝枝叶叶没找见什么。
找到了它或许会喊,把走远的树根喊回来。
爹,你到土里去找,我们在地上找。
我们家要是一棵树,先父下葬时我就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们也会像一棵树干一样,伸出所有的枝枝叶叶去找,伸到空中一把一把抓那些多得没人要的阳光和雨,捉那些闲得打盹的云,还有鸟叫和虫鸣,抓回来再一把一把扔掉。(不是我要找的,不是的。)
我们找到天空就喊你,父亲。找到一滴水一束阳光就叫你,父亲。我们要找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它消失了,又正在被遗忘。
那根躺在墙根的干木头是否已将它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我走了,我会记起一生中更加细微的生活情景。我会找到早要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如果我忘了些什么,匆忙中疏忽了曾经落在头顶的一滴雨、掠过耳畔的一缕风,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就会提醒我。有一棵大榆树靠在背上(就像父亲那时靠着它一样),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我8岁那年,母亲随手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筐,已经随树长得够不着。我11岁那年秋天,父亲从地里捡回一捆麦子,放在地上怕鸡叼吃,就顺手夹在树杈上,这个树杈也已将那捆麦子举过房顶,举到了半空中。这期间我们似乎远离了生活,再没顾上拿下那个筐,取下那捆麦子。它一年一年缓缓升向天空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没看见。
现在那捆原本金黄的麦子已经发灰,麦穗早被鸡喙空。那个筐里或许盛着半筐干红辣皮,一直举过房顶,举到半空喂鸟吃。
“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
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后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
大哥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我们全仰起头,这才看见夹在树杈上的一捆麦子和挂在树干上的那个筐。
如果树也忘了那些事。它早早地变成一根干木头。
“回来吧,别找了,啥都没有。”
树根在地下喊那些树和叶子。它们听见了,就往回走。先是叶子,一年一年地往回赶。叶子全走光了,枝干便枯站在那里,像一截没有走的路。枝干也站不了多久。人不会让一棵死树长时间站在那里。它早站累了,把它放倒。(可它已经躺不平,身躯弯扭得只适合立在空气中。)我们怕它滚动,一头垫半截土块,中间也用土块堰住。等过段时间,消闲了再把树根挖出来,和躯干放在一起,如果它们有话要说,日子长着呢,一根木头随便往哪一扔就是几十年光景。这期间我们会看见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等到全身开满口子,木头就基本没话可说了,我们过去踢一脚,敲两下,声音空空的。根也好,干也罢,里面都没啥东西了。即便无话可说,也得面对面呆着。一个榆木疙瘩,一截歪扭树干,除非修整院子时会动一动。也许会绕过去。谁去管它呢。在它身下是厚厚的这个秋天,很多个秋天的叶子。在它旁边是我们一家人、牲畜。或许已经是另一户人。
那时候我的记忆是多么孤独。我将一个人沿着荒远的回忆之路,一直走去。我知道它们全在那里,一个布条一个头发丝都不会少;树、鸟、鸡、麻袋、米、筐和绳子、锨、农具、开门声和狗叫,连傍晚洒在落叶和锨刃上的细碎阳光,都一点没有流逝。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永远地不在世间。
我走的时候是多么希望那些曾经的旧东西相伴身边。至少,能有一棵老榆树活在身边,与我共享全部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