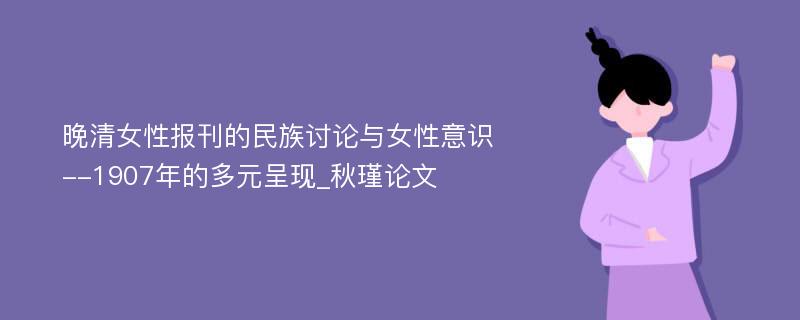
晚清女报中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1907年的多元呈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论述论文,意识论文,女性论文,女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4-0118-15 1907年是中国女报界迅速扩展的一年,《中国近代报刊名录》所附《中国近代中文报刊创刊年表兼索引》在该年项下便至少列出了十种杂志①。其中,在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三份女报为:1月在上海出刊的《中国女报》,2月、6月在东京先后面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与《天义报》②。这三份新出女报的共同特点是,“编辑兼发行人”均为女性,且都有留学或居留日本的经历。而即便在当年,7月印行的《(续办)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六期不仅同时为三家女报做了广告,并且也在“记事”栏发文介绍,称赞秋瑾主持的《中国女报》与燕斌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二女士皆东京留学生,品学兼优。而此二大杂志亦各有所长。”更推许“《天义报》系东京新出,尤为完善”③。可见三报一出现便已引起关注。何况,秋瑾与燕斌亦有交往,1905年底秋瑾离开日本之际,燕斌曾作《送竞雄女士归国》诗相赠;对燕斌所编杂志,秋瑾也曾有评说④;而秋瑾身后所出版的第一本诗词集,乃由何震编印⑤。凡此,都为将三份刊物放在一起讨论提供了理由。当然,最重要的是三家女报的同中有异以及对话场域的形成,在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上亦有呈现,只有经由彼此的观照,才可以分梳清楚。 需要先行说明的是,出于论题的考虑,本文应采用女作者的文字,方足以考知其对自我身体、权力与身份的自觉与期待。而晚清女报中笔名的混杂,则使作者性别的判定难度綦大。为尽可能保证论述的可靠,笔者将以三份女报主编发表在“社说”(或“论著”“论说”)与“演坛”(或“演说”)的论说文为主,参以三人在其他栏目以及其他女作者在上述两栏目中的撰述。如此,也有利于呈现三家女报各自的主导趋向。 一、《中国女报》中的“汉侠女儿” 《中国女报》是由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创办。发刊之前,秋瑾曾于1906年7月31日至8月9日在上海的《中外日报》连续登载广告,拟筹集股金万元,可惜应者寥寥。在“经费很为难”⑥的情况下,《中国女报》仍勉力出版了两期。第三期文稿1907年6月中旬前也已编就⑦,但因秋瑾随后的筹划起义与迅速就义,而未能付印。 检索两期杂志,秋瑾以本名或“鉴湖女侠”之号刊载的论说文字并不多,第一期里只有“社说”栏的《发刊辞》与“演坛”栏的《敬告姊妹们》,第二期更仅见卷首的《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一篇广告,余外便是译稿《看护学教程》与诗歌作品了。而第二期分列“论说”与“演坛”的《女子教育》与《恭喜恭喜》,虽然署名不同,却均出自后来担任《(续办)女子世界》主编的陈志群(本名以益)之手⑧。于是,另外一位作者“黄公”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此人在《中国女报》的重要性显然不亚于秋瑾,两期理应由报社中人执笔的“社说”文字,竟然都由“黄公”具名。而第二期中“钝夫”即陈以益的文章特意放置在“论说”而非“社说”栏,也显示出“黄公”乃是自家人。因而,尽管目前没有更确凿的线索,笔者仍希望能对其人稍作推测。 秋瑾遗稿中有一部《精卫石》弹词,今存完整的前五回及第六回前半篇残稿。学界一般认为,第一册1—3回写于1905年秋瑾留学东京时,第二册4—5回为归国后1906年续写,第六回残稿则大致草于1907年⑨。按照其弟秋宗章的说法,“姊所撰《精卫石》弹词手稿四本,初意在《中国女报》逐期刊布”⑩。尽管因为第三期的夭折,我们不知此说是否可靠,但起码可以引起关联的是,弹词主角黄鞠瑞的故事,确为秋瑾自身心事、行迹的影写。而依据第六回所述,黄女赴日留学后,改名“黄汉雄”,而非秋瑾原拟回目中设定的“黄竞雄”——后者显然与秋瑾已经流传于世的“竞雄”名号相同。此回弹词也在大肆铺写“真革命党”光复会在各地的分支系统⑦,亦与秋瑾其时正在组织的武装起义情实吻合。因此,经由“黄汉雄”的性别变异,笔者也怀疑“黄公”实为秋瑾的化名。如此也可以解释,秋瑾以本名或人所熟知的“鉴湖女侠”名号在《中国女报》发表的诗文,为何全然不见种族革命色彩,只因这类言说已由“黄公”包揽。更何况,从秋瑾致陈志群信中可知,《中国女报》编务完全由秋瑾一人承担,所谓“前瑾至沪,略为料理报事,嘱樊君付印,近可出版。瑾因绍中校事(按:指大通学校),友人倩代襄理,故在绍日多。樊君于报中文字茫无头绪,不能代理,故不能不二处兼顾”(12),因此,报馆中也确无其他人可分担秋瑾的主笔职责。 明白了《中国女报》作者笔名中的奥妙,便可将报中的启蒙文字分为两个层次,即面向女性大众的发言与针对女性知识者的立论。前者以秋瑾代表,后者由“黄公”主持。 在最低的层次上,秋瑾见于《中国女报》的言说只揭出“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虽然也用了不少形容词语描画“黑暗”与“危险”,如“黑暗界凄惨之状态,盖有万千不可思议之危险”,但此“中国之黑暗”与“前途之危险”究竟何所指,却并未落实。因此,“爱国”多半成为秋瑾的自我表白,并不作为对女性的普遍期待。这一低姿态的启蒙预设更进而引导以秋瑾之名发表的论说,其重心均放在“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13)的阐发上,从而凸显了对女性自身解放的高度关注。 由此看来,《发刊辞》与《敬告姊妹们》二文更像是彼此关联的上、下篇,前者提出对中国女界黑暗与危险的设问,后者作出回答,展现了中国女性生存的现实情境: ……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札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其中对于缠足、装扮的否定,早有先进者发明在前,算不上秋瑾的特识。秋瑾言说的长处因而只在用类似戏曲唱词的表述,突出呈现了女性身体被男性拘缚的状况:“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铷[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显然,在秋瑾看来,身体的拘禁实为女性失去自由最重要的表征与根源。以此,那些“安富尊荣”“自己以为我的命好”的“太太奶奶们”,落在秋瑾眼中,照样是“没有一毫自主的权柄”的可怜女同胞(14)。故而,恢复女性身体与行动的自由,便成为秋瑾整个论述的基点。而其设定的抗争对象,也首先指向家庭中的男性。 正是在西方文明、自由理念的观照下,上述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桎梏,被秋瑾恰当地概括为女性成为男性的“囚徒”与“奴隶”:“总是男的占了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而且,女性“为着要倚靠别人,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这个幽闭闺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既然“这奴隶的名儿,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人肯受的,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呢”?秋瑾指出,其原因纯粹在于女性无法自谋生计,只好依赖丈夫。于是,为女子设想“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秋瑾也指明向上一途:“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而女性拥有自立的能力固然有益家庭,所谓“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可使家业兴隆”;不过,秋瑾更看重的实在第二义项,即“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女性所获得的这种“自由自在的幸福”,也不只是在家庭中得到男子的尊重,以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之乐,还包括了走出家门后,在社会上与男子平等、自由的交往,这就是秋瑾所描述的“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并且,不止此也,经济自立的更上一级,才是秋瑾理想中女性可达致的最高境界:“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虽然关于“名誉”与“功业”所指仍然语焉不详,但由秋瑾所描绘的无论哪个层级的女性解放前景,都昭示出一个“美丽文明的世界”(15),却已毫无疑问。 这种对于女性自由的热切呼唤,在第二期“唱歌”栏刊载的鉴湖女侠秋瑾所作《勉女权》中获得了集中呈现: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16)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7)全篇实际是以歌曲的形式,对前述二文核心观点所作的总结与提升。如《敬告姊妹们》的反问:“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18)在此也得到了正面的肯定。最明显的是,“自由”与“奴隶”的赫然对立贯穿前后,根除奴性方能获得自由与独立,在歌词中已有了最精炼的表述。引人注目的尤在意义的提升与发挥。《发刊辞》与《敬告姊妹们》文中并未出现的“女权”或“男女平权”词语不但进入标题,也成为整首歌词的焦点。“自由”的真义就是“女权”或曰“男女平权”的实现,而这种权利本应是与生俱来(“天赋就”),那么,女性的牛马、奴隶境遇即意味着应有权力的丧失,收复女权的正当性由此产生。 只是,这样的释读仅停留在对女性自身权益的关注,仍属前述低层次的要求。而秋瑾对女同胞原本还有更高的期待,所言“伟大的功业”,在《勉女权》中已被具体化为“恢复江山”。与之相关的“中国之黑暗”与“前途之危险”,自然亦指向国家的沦亡。女性因此不只是作为家庭中的母亲、妻子、女儿存在,同时也具有了国民的身份标识,而与国家发生关联。救国于是被秋瑾视为女子理应承担的责任,实践这一理想的女性,方能获得“国民女杰”的荣誉。其间,“女权”和“国民女杰”的关系,固然可以从女性应拥有参政权一面设想,但“责任”与“权利”在现实中往往并不等同,以救国为己任的中国女杰,获得选举权与参政权的道路仍然漫长。而假如我们另辟蹊径,不拘于秋瑾的言说,而引进“黄公”的论述,“女权”在《中国女报》中的特殊意指即可获解,秋瑾提倡“女权”的深心亦可得到发覆。 据此,《中国女报》第一期“社说”栏刊载的“黄公”《大魂篇》便显得意义非凡。此文大张旗鼓地宣扬种族革命,诸如“中原铁血,大地腥膻,禹氏九州,已无复一寸干净土,为吾黄帝子孙立足地”这类其时反清志士常用的表达,在此文中也一泻无余。而“种族之思想”更被作者认定为区分人类与禽兽的界标,得到高度肯定。因此,“大好河山”被蹂躏,在黄文中首先指向满族对汉族的奴役。其次,窃取了汉族国家的满人,又任由异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则为“神州陆沉”的第二义。所谓“甲国范围线,乙国势力圈;鲸吞者封豕长蛇,蚕食者朝削暮翦”(19),便是此一情境的激愤写照。种族革命因此需要在民族与国家两个层面展开,反抗清朝统治与抵抗列强入侵于是联为一手。《勉女权》中尚嫌笼统的“恢复江山”,至此也有了明晰的答案。 而在这一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民族国家论述框架中,“女权”也被委以重任。其说大而言之有谓: 国民者,国家之要素也。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故今日志士,竞言招国魂,然曷一研究国魂之由来乎?以今日已死之民心,有可以拨死灰于复燃者,是曰国魂。有可以生国魂、为国魂之由来者,是曰大魂。大魂为何?厥惟女权!“女权”被作者尊称为“大魂”,端在其能够诞育、铸造“国魂”,使得国民有生气,国家得复兴。而追溯女权之所以具此伟力,作者给出的回答其实不脱其时先进者已经阐发的精义:“女界者,国民之先导也。国民资格之养成者,家庭教育之结果也。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20)比较1903年林宗素之言:“女子者,诞育国民之母。……故今亡国不必怨异种,而惟责我四万万黄帝之子孙;黄帝子孙不足恃,吾责夫不能诞育国民之女子。”(21)也就是说,由性别构造所带来的生育能力以及作为家庭教育最早的实施者,都使女性具备了养育国民身体与精神的母体本原的特质。汉族的疲弱与国家的沦亡既源于女界的沉沦黑狱,则汉族的崛起与国家的强盛,势必也要归本于女界。是即黄文道破的:“欲收他日之良果,必种今日之好因。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22) 然而,负有“生国魂、为国魂”重大使命的女界,现实的情况远不能令人满意,其本身即为病体,需要全面医治。而“黄公”开出的药方,包括了德育、体育、智育三方面。德育以破除“三从四德,数千年来之古训”为急务,体育以戒除缠脚、“人人尽复其天足”为前提,智育以根除“女子无才便是德”为起点。凡此,“曰三从四德也,培养奴隶之教育也;曰缠足也,摧残奴隶之酷刑也;曰女子无才便是德也,防范奴隶之苛律也”,其要义均在以女子为奴隶。而要革除奴性,将女性从“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中解救出来,首先就要改变女性无权的处境。结论是: 故振兴女界,万绪千端,挈领提纲,自争女权始。如能“争已失之女权于四千年”,即能“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万世”(23)。女权因而成为再造国魂的“大魂”。 而女权如何收复,在晚清也是检验女性意识是否完足的一方试金石。其时已有诸多热心“女界革命”的男子发表了各种论说,但女界先进者仍坚定地发出了维护女性自主权的声音。如林宗素即不以金一《女界钟》“为我女子辩护”“代谋兴复权利”为可凭恃,因为,“权也者乃夺得也,非让与也”。即使“彼辈男子慨然尽举畴昔所占据之权利,一一让与而还付之于我女人”,也不能“保护享受于永久”(24)。“黄公”正是延续了这一思路,力言:“(女权)争之若何,亦自为之而已矣。幸福固非他人所能赐予者。”(25)并且,不仅于此,黄文对女性其实还另有崇高的期待。 在这一更高的层级上,“黄公”要求于晚清女性知识者的“名誉”与“功业”已远远超越家庭一隅,而立身于民族国家的高度。故谓,“贤内助之资格,于彼男子诚利矣,与吾女界何?与吾祖国何?”其所寄望于同胞姊妹的上乘境界,实为“宏其愿,达其识,肩任立功,以与天下男子争着鞭”。因此,女性的任务不只是夺回女权,而且,“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亦被规定为“我女子之天职”。《大魂篇》也在激昂的种族革命与女权革命合一的话语中结束: 尽我天职,以效祖国,凡我女子志愿所及,即我女子权力所及,当仁不让,夫何吝于先着鞭?噫嘻!兴矣。近以挽狂澜于既倒,远以造国魂于将来。伟哉女权!伟哉大魂!魂兮归来,吾将见之,吾愿买丝以绣之,酬金以铸之。(26)而能够担负此重任的女性,自然是“国民女杰”;若兼顾从异族手中夺回主权的使命而言,其命名则以秋瑾在《精卫石》上的署名“汉侠女儿”最为贴切。 因应晚清女界的现实状况,《中国女报》将读者群区分为大众与精英两类,分别以秋瑾与“黄公”两种论述层次进行启蒙。从最低的启发女性挣脱奴隶地位,经由国民意识的加入,最终提升到赋予女子从清朝与列强手中拯救中国的至高责任,女子的性别身份也相应地从贤母良妻、国民女杰直指汉侠女儿。而无论隐显,作为全部论述的核心理念,实为“女权”。 二、《中国新女界杂志》中的“女国民” 与秋瑾的归国办报不同,燕斌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之际,正在东京早稻田同仁医院留学。除为此刊主编、主笔外,时年三十九岁的燕斌还同时担任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对外书记。加以1905年冬留学之前,燕斌自称已“奔走遍十二行省,名媛贵妇,订交论学,相追随而莫逆者,颇不乏人”(27)。以其在国内、尤其是留日女界中的资历与声望,《中国新女界杂志》既吸引了诸多留学生、特别是女生参与其中,出刊后,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第三期的发行量便“已及五千余册”(28)。然而,由于内地代销报费多有拖延,致使该刊“经济异常困难”(29)。先是自第四期起开始延期出版④,至第六期印行后,杂志终于被迫停刊。 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主要使用“炼石”的笔名,室名亦署“补天斋”,显然以女娲补天的功业自期,志向可谓宏大。其办刊发论,也立意高远,且多长篇大论。因此,出自其笔下的文章,重要者如《女权平议》《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女界与国家之关系》《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婚俗五大弊说》,均未完篇。很可能为其另一笔名“娲魂”所写的小说《补天石》,甚至连卷一“楔子”亦未刊全。这也令人疑心燕斌眼界虽高,却力有未逮;同时亦为完整考察其女性观带来一定困难。 燕斌自记其十余岁时与女友一起读书:“每披阅史鉴,同概[慨]人事之不平。读大家《女诫》,尤窃相议之,以为女子亦人类,何卑弱乃尔,无或谬乎?”而当年不能明白宣说的质疑,始终“盘结于脑际”,便成为其“他年提倡学说,扶植女权,为女同胞谋幸福之心”(30)的萌蘖。因而,《发刊词》之外,《中国新女界杂志》刊出的第一篇论说,标题即为《女权平议》。只是,与《中国女报》倡言的“女权”带有鲜明的民族革命印记不同,燕斌的阐说别有会心。 按照燕斌最初的设想,《女权平议》本是一篇宏论: 今欲推翻已往之腐败社会,扶植女权,催其发达,当首令吾女同胞,知女权之原则,与女权之设施,及女权之将来;次宜就中国历史上之性质,所以妨害于女权之故,精研而深究之;证以欧美之事实,斟酌损益,以定吾中国提倡女权之方针,分其次第,期以实行,而后中国女权之发达,可企而待矣。只是,此篇论说只刊出一次,即不见下文。所述也仅及第一个小话题,即“女权之原则”。经过一番人类史的考证,燕斌指出:“夫世界人类,既只有男女,男女之数,又常平均,可知造物生人之本意,其视男女,皆人类而已,无所偏于男,无所重于女。”由此证明,男女两性天生平等,女子与男子本有对等的人权,是即女权。而“夫妇之名,嫁娶之制,男刚女柔,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习俗观念,均属后起的“不公平、不道德”的“人为之习惯”,应予破除。收复女权对于女子而言,因此具有天然合法性。此节结尾便极言: 语曰:不自由毋宁死!吾窃一易说曰:女权不复毋宁死!此女权之原则也。(32) 尽管《女权平议》只是残篇,不过,如结合《中国新女界杂志》的诸多论说,钩稽铺排,还是可以大致了解燕斌的思路。如从历史上考究妨碍女权之缘故,有忏碧所作《妇人问题之古来观念及最近学说》的系统论述,也有散见各篇的对于“男尊女卑”一类旧学说的批驳。而介绍欧美女界情况,则以燕斌本人最为用力,先后刊有《美国女界之势力》《请看俄罗斯二百年前之妇人界》《欧美之女子教育》《纪美国妇人战时之伟业》(33)诸文。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类文字无论反观历史,还是远究域外,都是针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发言,具体说来,即是“以定吾中国提倡女权之方针,分其次第,期以实行”。 由“女权之将来”以及“分其次第”之言,可以意会,在燕斌看来,“女权”的内涵既在不断进化发展,其实现也需要经历若干阶段。或者可以说,在不同的阶段里,女权应有不同的实践形态。故此,为因应晚清中国的现实情境,燕斌所要“扶植”的“女权”也染上了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 按照燕斌的女界进化观,中国女界应“由家族的妇人地位,进而为国家主义的妇人,更进而为世界主义的妇人”。“世界主义”属于未来的理想,燕斌对此不及讨论。而晚清女性尚处于“家族的妇人地位”,当务之急是将其提升为“国家主义的妇人”(34)。后者即为《中国新女界杂志》大声呼唤的“女国民”。还在《发刊词》中,燕斌已以“欧美诸强国”为表率,赞扬“其女国民,惟日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亦不之惜。斯其国始得为有民,宜其国势发达,日益强盛,而莫之能侮”。中国的状况恰与之相反,“虽有多数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多数女国民之精神,则有民等于无民”。故燕斌认为,中国“以硕大民族,势力衰微”(35),根本原因在此。既然国力的强盛与女国民的质量与数量成正比,祈望中国迅速强大的燕斌,于是也将培植女国民确定为其所办刊物的主旨,自白: 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是这四个大字。本社《新女界杂志》从第一期以后,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翻覆解说这四个大字。(36)女国民由此成为《中国新女界杂志》对晚清女性群体的普遍期待。 在燕斌的用语中,“女国民”既等同于“国家主义的妇人”,便意味着对现行政权所代表的国家有认同感。这也使其区别于秋瑾激烈的种族观念,在政治立场上更接近于温和的改良派。《发刊词》中称“近年以来,朝野上下,始从事于女子教育问题”,是“为吾女学界开一新纪元也”(37),已露端倪。更明显的是对“女子国民捐”的全力肯定。燕斌为此专门写了一个长篇演说文,不但赞美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的预备立宪上谕“放出祥光瑞气”,而且针对批评“国民捐”的议论,也坚定地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予以反驳。因为“有人说,他捐的钱,都交在户部银行,明明是为虎作(伥)呢,不过去供给政府的霍挥[挥霍]罢了。提起赔款来,一定还是去剥削百姓罢”,燕斌的辩护就很有些强词夺理:既指责“女子国民捐”发起一年来,得款甚少,“还不够零头的零头呢”,“这能怨他不得已,又去剥削百姓么”?又说,“就任他挥霍了,究竟还是用在政治上面,终须有个报销,有个着落,也比那太太们奶奶们,整日里施僧修庙,焚香赶会,拜佛念经,拿着有用钱财,去供给老和尚挥霍,强的多罢”(38)。此类言说已经明白显示出燕斌的国家至上立场。其逻辑起点为,国家的权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凌越于个人权益,而唯此为大。 当然,这也不表示燕斌全盘认可现政权的作为,相反,对于历代相传、亦为清朝所承袭的专制政体,其《本报关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一文即曾痛加批判。只是,由于该文采用了寓言体,作者只形容它是“两个字里头的最大怪物”,“发出凶光万丈,臭气千条,恶不可当;所有一切的字,若是会奉承他,还可偷生苟活;若是稍微冲犯着,可就没有命了”;述其历史,在中国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发作,西洋各国则是19世纪以后,先在欧洲站不住脚,四十年前,在日本也被打出来,俄国早晚也不能住了,“唯独中国,本是他极好的一个养老院”,却又有五百零九个字合成的上谕“颁行各省,声明教大家预备资格,约定年限,定要把他两个字合成的大怪物,在中国几千年放出的毒气,斩草除根似的,拆开了消尽了,不准他们两个字再到一堆,结合起来害人”(39)。这样缠绕的表达,“专制”二字始终未道破,确会造成额外的困扰。难怪秋瑾对《中国新女界杂志》大为不满,严词斥责: 某某之杂志,直可谓之无意识之出版,在东尚不敢放言耶?文明之界中乃出此奴隶卑劣之报,不足以进化中国女界,实足以闭塞中国女界耳,可胜叹息哉!而其第三期《中国女报》拟定的一则“演坛”题目,即为“专制毒焰之澎涨”(40),亦不无针锋相对、纠偏补弊之义。 以国家主义为救国方策,燕斌关于女性权益的所有思考,从人身的自由开始,包括其在《女权平议》中所称羡的欧美女子享有的“姻婚[婚姻]之自由,学问之自由,生业之自由”(41),因此无不置于这一理论中。 对于女性人身自由的讨论,在晚清主要集注于身体与行动两项最基本权利的拥有。前者以抨击缠足为极致,后者多半关涉“男外女内”的规限。燕斌也是如此。依据人道主义女权观,燕斌既痛心于“吾中国社会,对于女子,更有最不仁之行,为世界所未有者,则缠足是矣”,又揭示其危害不仅及于女子一身: 迟之既久。举步维艰。周身气血,不能流通,斯疾病生矣。此时为病女。将来即为病妇。病体之遗传,势必更生病子孙。使仅为一人一家之事实,则所关尚细;无如千百年来,统二万万之妇女,已皆沦于此境界,迄未改革焉,则其人种之健全,必不可得。彼“东方病夫”之徽号,诚哉其有自来矣!(42)小说《补天石》则从禁锢女性于家中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只因数千年来,有一个最奇的习俗,凡是女子,都须收藏在家里,连风儿都不叫吹着。虽有手却不让他做事,虽有脚却不让他走路,只算是男子的玩物罢了。因此那汉族的女子,都衰弱起来。女子既然衰弱了,那女子所生的男子,自然就一代不如一代,也衰弱起来了。列位请想,一国的民族,既然成了这种现象,难怪外人呼他为病夫、为老大罢。(43)总之,在燕斌的追究下,无论缠足还是幽闭女性,都造成了汉族人种的衰弱(因缠足为汉族风习),乃导致中国国势衰微的深层原因。结论于是也很现成:如要振兴国力,必自恢复女性的人身自由权开始。 言及婚姻自由,燕斌专有《中国婚俗五大弊说》详加阐论。而无论其弊端为“媒妁”、为“早聘早婚”,还是“迷信术数”等,无不危及国家前途。如媒妁撮合男女,于“财利之外,他非所顾”。如此漠视性情才德的婚姻,往往造成“夫妇之情意不洽”,并由此带来一连串恶果——“情意不洽,则气脉不融;气脉不融,则种裔不良;种裔不良,则国脉之盛衰系之矣”。而早聘早婚同样被斥为“中国人种日劣之大原”。凡此对于中国婚姻旧俗“贻害无穷”的清算,概言之即为: 吾恐其患之中于个人者尚小,而无如养成依赖之性根,损失家庭之幸福,消耗社会之资材,演成种裔之悲剧,而国民之生殖力、发展力,亦以俱形其薄弱也,其害可胜言哉!因此,燕斌反对“唯凭父母之意见”、以“父母为绝对的主体”之“父母专婚”,而肯定青年男女“请命于父母”“以请命者为主体”的“父母主婚”(44),也应放在这一笼罩婚姻、家庭的国家主义背景下考量。女性的婚姻权因此也与国家发生密切关联。 至于生业的自由,由于中国女子被禁闭家中,此项权利自是完全缺失。尤其是在与女界“最有势力的,以美国为第一”的对比中,美国女界“于事业的各方面,不但与男子平等,并且还有强似他的地步”,中国女子却“没有独立的事业,凡事皆仰给于男子”(45),两个国家的盛衰强弱,在此也立分高下。 而《中国新女界杂志》、也是主编燕斌最关心点,尤在“学问之自由”,即女性教育权问题。“鼓吹教育”尽管被列于该刊“五大主义”的第三条(46),对于报社同人来说,却实为其倾心致力之首务。《本社征文广告》已明言:“本社创办杂志,原以开通风气,提倡教育,为最要之主旨。”(47)而教育作为“女权”的第一义项,在燕斌的如下表述中也得到凸显: 所以本报提倡女权,是要指望大家先从真实学问下手,然后从事于各种事业。(48)当然,此一对于女性教育的强调,亦与国家主义的整体语境相关。援用燕斌的说法即是:“故论女子之时代,其与国家之密接关系者,就普通论之,当以教育为急。”(49)准此,女性教育权及其实施,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以培养女国民为目标。 依照燕斌的构想,女国民教育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次。燕斌最先在《发刊词》中引其端绪,紧接着,《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二期即刊出了以“中国女子教育之方针”为题的征文广告: 女子教育之于中国,其关系固不待言。然奴隶的教育,与国民的教育异;物质的教育,与精神的教育异。种如何因,即收如何果,则施措之方针,宜早定也。本社恐仅就个人意见,不足以端海内之趋向,愿我同胞,各抒伟论,以解决此问题。谨择尤登布,庶从事斯道者,有所折衷焉。(50)可惜,这一面向东京与国内的征稿,经过再次刊求,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投稿虽然不少,燕斌却认为多半“与本报的主义不能相合,以致不便登载”(51)。而其间的缘故,主要在于对“精神的教育”论述不合格。 推究《中国新女界杂志》所谓“物质的教育”,大体相当于智育,指各种专门知识与职业技能的培训。燕斌以日本为此类教育的典型:“教育虽普及,究其实际,因被男界限制之故,所得者仅物质上的文明。”而由此“所造就者,良妻淑女,其上选也”。因此,日本的女子教育尽管比中国先进,燕斌也主张中国女学“不妨近取诸东洋,以医痼疾”;但她仍然认定,“物质的教育”尚属粗浅层次,其所培养的“良妻淑女”更适合“家族的妇人”时代,而非目前急需的“国家主义的妇人”(52)。 燕斌所理想的完全的女国民教育,则应在“物质”之外,更施以“精神的教育”。根据《发刊词》所述,“但深望当事者,勿徒尚物质的教育,必发挥其新道德,而活泼其新思想”(53),可知“精神的教育”实指向“新道德”与“新思想”。这也是《中国新女界杂志》之所以将“提倡道德,鼓吹教育”并列,作为第三条主义的深意(54)。而此一更上层楼的教育,所取法者乃是欧美,燕斌即坦言,“精神上的教育,则断宜以欧美为师”(55)。 这一源于欧美的“精神的教育”既以“新道德”为主体,《中国新女界杂志》因此大加提倡,推许其“乃是世界通行的女子新道德”。而对此“新道德”的阐释,单看燕斌于《本报五大主义演说》所述,不无夹缠不清处,远不及巾侠的《女德论》取镜欧美女权精神,提出的“慈爱”、“高尚”、“侠烈”、“勇毅”(56)之四德明晰且系统。不过,参照《发刊词》中燕斌赞羡“欧美诸强国”“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也不难理会,爱国思想理所当然应为“女子新道德”的基本要素。因此,说到“新道德的好处”,燕斌也必以此居先:“第一件是女子的新道德,若果然发达了,便可与男子,同具有国民的资格,尽一分国民的义务,国家便可实在得着女国民的益处了。”而“这担任国民义务,必先富于爱国思想,把国看的,比自己生命还重,无一刻能忘了”。经过这样充满爱国思想的“精神的教育”洗礼,燕斌所期盼的“斯教育一女子,即国家真得一女国民”(57)方可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个层次的女子教育,燕斌都以为应与男子教育毫无差别。“凡男子所能学的,无论是什么海陆军,政治、法律,工业、农业、商业,哲学、理学、文学、医学等等,都要分配开了,去研究个毫无余蕴。”(58)而只有获得同等教育,女性才能够在择业上与男性享有同等待遇,进而在一切的权利上与男性平等。这也是燕斌特为看重女学的缘故。 虽然在燕斌的论述中,“欧美女界”作为超越日本的典范,其女权之发达已足令中国女界艳羡,但其实“欧美”之中,仍有轩轾,燕斌最赞赏者还在美国。断言“近世女权之最发达者,当以北美合众诸州为最;女权之最不发达者,则以吾中国为最”(59),已尽显此意。美国与欧洲的差距,归根结底在参政权。译述《美国女界之势力》时,燕斌于是特别致意于美国女性在“官吏界”与“议员界”的任职,一则说:“世界上各国的官吏,无论大小,皆是男子的专业,从来没有女子作官的。”一则说:“必有选举权的人,方能举别人作议员;必有被选举权的人,方能被别人举他作议员。这是一定的道理了。但是各国宪法上,从未认许女子,有这个权利。”而唯独美国女界首开风气,享有此权(60)。由此可见,燕斌倡导女国民“精神的教育”,所要达致的最高目标,实在女性获得参政权。而必至此境界,才可谓为完全的女权。 从强烈的国家主义理念出发,由燕斌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塑造具有“新道德”的女国民为中心,燕斌充分展开了对于逐步实现女权的设想。而其问题意识既得益于留学日本、汲引最新学说的便利,又充分体现出杂志同人所代表的留日女学界炽热的救国情怀。恰如燕斌在《中国女报》上发表的一首诗作所吟诵:“女学苟不振,国民安可兴?女界不维新,教育胡能成?关键于爱国,吾侪务血诚。”(61)其所吐露的心声正可作为创办杂志的缘起解读。只是,由此引发的国家至上,在实践中也会导致集权统治,对其间可能存在的弊害,燕斌等人显然缺乏意识。 三、《天义报》中的女虚无党 何震作为《天义报》的编者,过去一直不被认可,近年学界则多持肯定态度。笔者认为,两说都存在偏差。实则在办刊方面,何震初期投入较多,嗣后热情退减,故杂志主要仍由何震的丈夫刘师培支撑(62)。创刊之际,曾在多处登载的《〈天义报〉广告》,已明确将该刊定位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63)。虽然很快又兼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会刊,但刊期到19卷的杂志,多半将有关女性的论述置于“社说”(或“论说”)栏首位,仍体现出对“女子解放”话题的突出关注。而何震本人的写作也如同火山爆发,数量之多在其一生中空前绝后。 有趣的是,《天义报》第一期卷首,刊发了何震绘图的《女娲像》,恰与燕斌的“炼石”别号相对应。不过,与燕斌的志在“补天”迥异,何震突出的是女娲“断鳌足,杀黑龙,先禹有功抑下鸿(按:通“洪”),辟除民害逐共工”的伟业。凭借这份救世济民的功劳,何震认为女娲应“与轩、羲并隆”(64),即与黄帝与伏羲一起受到后人的尊崇。此图像与赞语有意将女性对于人类的贡献追溯至历史源头处,实为何震所持男女平等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追溯何震的思想轨迹,1907年2月同刘师培一道赴日后,夫妇二人与日本社会党中的激进派多有接触,因而迅速接受了无政府主义(65)。何震当年曾坦言:“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66)而建基于无政府主义之上,也使得何震的男女平等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 无政府主义最核心的理念是消灭阶级、废除国家,反对一切统治关系的存在。秉持此意,何震等《天义报》发起人也认定,“世界固有之社会,均属于阶级制度”,“均含有不平之性质”,故“非破坏固有之社会,决不能扫除阶级,使之尽合于公”(67)。革命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由此发生。而《天义报》区别于其他无政府主义报刊的独特处,乃是在所有领域的革命中,将“女界革命”(亦称“男女革命”)放在第一位。创刊号登载的《简章》已宣告: 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名曰天义报。(68)“天义”在何震等人的语境中,相当于“真公”“至公”,意指天下正义、公道之所在,实以平等为旨归。因此,“女界革命”所要达致的男女平等,本是无政府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何震所言:“盖无政府之目的,在于人类平等,及人无特权。若男女平等,亦系人类平等之一端;女子争平等,亦系抵抗特权之一端,并非二主义相背也。”⑧这是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逻辑推演出来的道理。只是,何震以“女界革命”居先,还另有深意。 就人类最基本的关系构成而言,实属男女两性。而自原始社会(何震谓之“图腾社会”)解体,父权制建立,女性即受制于男性。这就是何震等人所谓“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由此,男女权利的不平等,也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决定了社会的阶级属性,并深入到人们意识的最深处,以致其他阶级关系的改变,亦不能影响男权即男性特权的尊崇地位。用何震的说法,即是女子“贵为王后,其身不可谓不尊,而受制于男自若也”。既然人类平等乃是“天义”,占人类半数的女性无权状况自不可容忍:“使女子而非人类也则已,使女子而为人类,又安能日受压抑而不思抵制乎?”于是,在《天义报》发起人那里,结论也很现成:“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而必须优先进行的“女界革命”与其他诸种革命的关联便呈现为:“夫以男女阶级之严,行之数千载,今也一旦而破之,则凡破坏社会之方法,均可顺次而施行,天下岂有不破之阶级哉!”(70)在此,“女界革命”显然被认定为具有动摇现行社会结构全局的突破效力。当然,这只是理论推导的结果,占先并不意味着可以单独获得成功,何震即一再强调:“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71)因此,更值得重视的是何震凸显“女界革命”重要性的思路。 尽管随着“社会主义讲习会”内容比重的不断加大,当年10月底《天义》第8—10卷合册出版时,更正后的《简章》已将最初列于首位的“提倡女界革命”,替换为“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72),并移至五条纲领的最后一项,但其精神仍前后贯通。甚至可以说,经由后者的概括,何震倡言的“女界革命”底蕴也得到了精粹揭示。 阅读何震在《天义报》的所有论述,不难发现,“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乃是其统贯的立场与信条。“女界革命”正以此为目标,极言之则谓: 要而论之,男女同为人类,凡所谓男性女性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亦必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此诚所谓男女平等也。(73)显而易见,何震所谓废灭“男性女性之名词”,并非指消除男女两性的自然特征,而是要求泯灭男女在社会性别上的差异。因为社会性别歧视乃是由习惯与教育等社会文化与制度塑造形成,而在何震的语汇中,这些人为的规范、制度统称为“人治”。 在批判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时,何震也采取了和前述两份女报完全不同的论述方式,放弃了更贴近其时女性日常生活的话题,乃至不涉及两报热衷抨击的缠足、包办婚姻等陋习,而是直抉根本,专一从清理制度入手。《女子宣布书》最典型。何震揭发男女不平等的“古制”,归结为四事:“一曰嫁娶上之不平等”,“二曰名分上之不平等”,“三曰职务上之不平等”,“四曰礼制上之不平等”(74)。其中第一条检讨的是婚制,痛斥男子多妻,明显与燕斌关注“婚俗”中的“媒妁之弊”“早聘早婚之弊”等异趣(75)。 针对“男女之间,其制度失平”(76)的现状,何震在批判的同时,也要求遵从男女平等的原则,逐一加以矫正。如以“实行一夫一妻之制”,革除婚制中的不平等;以“无论社会间若何之事,均以女子参预其间”,破除职业上的不平等。而其首先身体力行的,则是对姓氏制度的革命。何震尖锐地指出,姓氏所涉关系重大,女子“姓则从夫”这种名分上的不平等,实乃“以女子为男子附属物”的表征。由此,针锋相对的解决之道即为: 既嫁之后,不从夫姓;如从父姓而遗母姓,仍属不公。故生当今时者,当并从父母得姓(即双姓并列是)。俟满洲革命以降,则男女均去其姓,以合至公之理。(77)虽然因应现实,“双姓”与“废姓”在推行时尚需分别先后,但在首倡者何震本人,自《天义报》创刊伊始,便已将二者同时付诸实行:第一号目录中所列作者署名均为“嚣震”,正文则一律为“震述”。其关注男女平等的实现以及实行之决心,于此清晰可见。 而采用“双姓”与“废姓”,也是何震主张“男女绝对之平等”的绝佳例证。实际上,只有从追求绝对平等的角度,何震诸多奇特惊人之论才可以得到准确解读。 《女子复仇论》可谓何震最有名的文章。其开篇提出的“男子为女子之大敌”的观点,在作为何震“女界革命”论纲领的《女子宣布书》中先已倡言。而其前提是“女子受制于男,已历数千载之久”,故“女子一日不与男子平等,则此恨终不磨”(78)。可见,看似荒谬的男子为女子大敌、女子要向男子复仇的立说,本是起因于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从而集中体现了女性先进反抗男性特权压迫的高度自觉。并且,何震用激烈语气表述的“复仇”,只不过是“复权”的别一说法,但更突出了其间“实行”的意涵。也就是说,何震是将反抗男权压迫以实行男女平等的自觉行动称为“复仇”。为此,何震甚至一再倡导使用暴力,如《女子复权会简章》规定的两条“对于女界之办法”,一为“以暴力强制男子”,一为“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79),其所惩治的对象也包括了女性自身。显然,何震认为,暴力是在“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的“女界革命”过程中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另一“如有以未昏之女,嫁再昏之男者,女界共起而诛之”的规定,更是在当时已引起争议。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便表示“不解”,因“爱情为男女交际之要件”,其他均无关紧要,故怀疑何震“仍为古来‘贞女不见二夫’之陋道德所染”。实则,何震之说系由“以初昏之男,配初昏之女”推衍而来,仍是出于谋求男女绝对平等的考虑,并将之推行到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层面。秉持同样的理由,在反对“男子多妻”的同时,何震也大力谴责以“抵制男子”为名的“女子多夫”。对何震而言,“平等”比“自由”更重要,她正是以此概括与幸德的分歧:幸德之意“在于实行人类完全之自由”,己意“则在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80)。这种对“平等”的绝对尊重,以致置于“自由”之上,也是何震区别于其他晚清女权论者的特出之处。 由上可知,何震那些貌似偏激的言论,其实往往同时兼顾男女两性立言,绝无例外。故其对于“复仇”的界限也有明确的提示:“盖女子之所争,仅以至公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而何震对于平等的绝对化诉求,正是源自其当时崇信的无政府主义: 盖政府既设,即有统治机关。而统治机关,必操于男子之手,是与专制何异?即使男女同握政权,然不能人人均握政权也,必有主治、被治之分。以女子受制于男,固属非公;以女子而受制于女,亦属失平。故吾人之目的,必废政府而后已。政府既废,则男与男平权,女与女均势,而男女之间,亦互相平等,岂非世界真公之理乎?(81)换言之,只有进入无政府社会,何震所致力的“男女绝对之平等”才可以真正实现。因此,“颠覆一切现近之人治”(对于女性来说,则是“覆人治以弭男权”)(82),也被《天义报》同人视为实现人类平等、包括男女平等的必由之路。 小而言之是男女平等,大而言之为人类平等,要达到这一目标,《天义报》在讨论与“女界革命”并行的“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时,也始终坚守了无政府主义立场。 主张“驱除鞑虏”的革命派,尚可算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半个同路人。况且,何震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从民族革命到无政府革命的转变。不过,《天义报》时期的何震与刘师培已明确在二者之间作出界划,二人联名发表的《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对此进行了集中清理。何、刘认为,革命派实行的种族革命仍存独尊汉族的民族不平等观,与无政府革命以“满人之当排,非以其异族而排之也,特以其盗窃中国,握中国之特权”的出发点不同。并且,革命派于“革命之后,希冀代满人握政权”,亦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因此终不如无政府革命纯洁、彻底:“满洲政府既覆,则无政府之目的可达”;而“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则革命出于真诚”。因此,无政府革命实为包含了种族革命“排满之目的”,且更高一筹、“一劳永佚”的革命(83)。 相对而言,努力推行新政的改良派与立宪派则被视为无政府革命的敌人。刘师培专门写过《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一文,阐发此意。由何震参与的论说也指认,新政崇信与效法欧美、日本的“伪文明”,不仅将中国传统的“放任之政府”变为“干涉之政府”,“自由之人民易为受制之人民”,加大了无政府革命的难度;而且,对人民的剥削、压制更甚。因此,对所有可能加固清政府的新政举措,何震等人也一律猛烈声讨:“以法治国”被认作“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建立议院”则“为政府所利用,以病其民”;“振兴实业”“不过为竣[朘]削贫民计”;“广设陆军”又“不过为镇压民党及戕贼弱种计耳”(84)。至于燕斌极力赞美的“女子国民捐”,其倡导者吴芝瑛干脆被骂为“女子而为盗行”,乃是“吸国民之产,以为腐败政府效忠”(85)。 在此理路中,作为新政之一的新式教育当然也会遭到痛责。女学也不例外。《女子教育问题》开门见山即指出:“近日女子教育,均奴隶之教育也。不惟亚东为然,即欧美亦然。”在燕斌那里更为先进、属于“精神的教育”典范的欧美,依何震等《天义报》同人之见,因其施行“宗教教育”,照样不脱“形式之解放”的窠臼,距离“排除一切奴隶教育”的“思想上之解放”尚远。日本与中国的女子学校,又“非迫女子为家庭奴隶,即迫女子为国家奴隶,其立意虽殊异,而其为奴隶教育则同”。就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奴隶”的提法。出于无政府革命的理念,何震等反对以军国主义、尚武精神“提倡于女界”,故指控“仅勉女子以爱国,则是导女子于国家奴隶耳”;而“关于国家主义者,宜在屏遗之列”(86),自然成为革新女子教育必不可少的一节。在此也昭示出《天义报》同《中国女报》、尤其是《中国新女界杂志》之间深巨的鸿沟。 更进一步,出于对任何权力的警惕,即认为权力都会带来不平等,所谓“盖人治一日不废,权力所在之地,即压制所生之地也”(87),何震对“女权”的使用也相当谨慎。在参政权态度上,尤可见出其思考的深入与透彻。无政府主义既认为“政府者,万恶之源也”(88),政府当然也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如要“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自须先废政府。在此意义上,何震提出了“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的理想,并指出:“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对先进者视为女权最高级别的女子参政权,何震不仅不予提倡,反断然否定,以为其违背了“国会政策为世界万恶之源”的无政府原则,也势必在女子之间造成新的不平等,故要求“有志之妇女”将争获参政权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据此,何震也将“解放女子”的“根本改革”之道归结为“尽覆人治”,而不以女子“对男子争权”(89)为然。 由上可知,对于排满的“种族革命”、推翻君主制的“政治革命”,《天义报》指出的光明大道,最终都通向无政府革命。所言“经济革命”同样如此,何震即概括其内涵为“颠覆财产私有制度,代以共产,而并废一切之钱币是也”(90)。其实,无论何种革命,何震等人明示的实行方法均不外“反抗在上之人”一策。而以弱势者反抗强权,除去不能持久的“全体罢业”(91)之类消极抵抗,便只剩下暴力抗争一途。而这也被何震视为最有效的革命手段,故力言:“特无政府主义,不仅恃空言也,尤重实行。”受其时俄国民意党不断得手的暗杀恐怖行动的鼓舞,何震也肯定:“世界无政府党,以俄国为最盛。”“盖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92)投掷炸弹的女虚无党,于是成为何震对中国女子的最高期望。 基于无政府主义理想,《天义报》所倡导的“女界革命”以“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为精义,带有强烈的理论色彩。由此,既造成了何震等人思考的彻底性,不纠缠于枝节,而始终寻求根本解决之道;同时也因悬的过高,不顾及现实国情,躐等而行,渴望毕其功于一役,以致阻断了实际进行革命的路径。尽管其说不乏偏执,但从中透显的思想的深刻,仍使《天义报》在当时的女报界独占鳌头,并光照后世。 总括而言,1907年确可谓中国女报的黄金时代,其异彩纷呈令人惊叹。而无论是秋瑾主办的《中国女报》之提倡民族主义、燕斌主持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之宣导国家主义,还是何震编辑的《天义报》之标举无政府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切近了女性与国族的关系问题。而由此形成的多元论述,无疑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图景,也是一笔至今引人不断回味的精神遗产。 收稿日期:2014-04-10 注释: ①即《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日本·东京)、《女学报》(北京)、《天义报》(日本·东京)、《天足会报》(上海)、《中国女报》(上海)、《中国妇人会小杂志》(北京)、《中国新女界杂志》(日本·东京)、《妇女会报》(北京)、《星期女报》(北京)、《神州女报》(上海)。见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407页。 ②自第3卷起,刊名改题《天义》。 ③如瑾(陈志群):《女界二大杂志出现》,《(续办)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第113页,1907年7月。另,《天义报》广告刊此期杂志卷首,卷末则有《中国新女界杂志》与《中国女报》广告。 ④见《中国女报》第1期,第47页,1907年1月;秋瑾:《致陈志群》其三(1907年4月3日),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2页。 ⑤何震于《天义》第7卷(1907年9月)发表《〈秋瑾诗词〉后序》,言及:“秋瑾罹祸之岁,七月初旬,得其诗词若干首,各为一卷,乞太炎先生及吾师曼殊为序,并由吾友王芷馥女士助资排比,阅二旬而成。”(第45页)其所得秋瑾遗稿来自陶成章与龚宝铨(见龚氏《〈秋女士遗稿〉跋》,《秋女士遗稿》,东京,1910年)。《秋瑾诗词》出版后,凡订《天义》全年者,“均附送一册”(《〈秋女士诗词〉出板豫告》,《天义》第5卷,卷末,1907年8月)又,该刊并刊发过《秋瑾传》《绍兴某君来函论秋瑾事》及《秋瑾死后之冤》诸文。 ⑥参见秋瑾:《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敬告姊妹们》,《秋瑾全集笺注》,第376—377、386页。 ⑦秋瑾《致陈志群》其九(1907年6月17日)中提及:“《女报》编辑已就,前因无暇,约于此月必行付印。”(《秋瑾全集笺注》,第458页) ⑧《女子教育》署名“钝夫”(目录)或“纯夫”(正文),此文后在《(续办)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刊出修订稿,自署“志群”,与《恭喜恭喜》一文作者名相同。实则,“志群”即陈志群,本名陈以益。 ⑨参见郭延礼:《秋瑾年谱简编》,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⑩秋宗章:《六六私乘》,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133页。 (11)汉侠女儿:《精卫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秋瑾史迹》,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162—168、28页。 (12)秋瑾:《致陈志群》其一,《秋瑾全集笺注》,第450页。 (13)秋瑾:《发刊辞》《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第1—2、13页,1907年1月。 (14)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第13—14页。又,“奴仆”后原多出一“奴”字。 (15)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第14—15页。 (16)“若安”为法国救国女杰圣女贞德(Jeanne d'Arc,1412—1431)的译名。 (17)鉴湖女侠秋瑾:《勉女权》,《中国女报》第2期,第48页,1907年3月。 (18)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第15页。 (19)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5—6页,1907年1月。 (20)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7页。 (21)林宗素:《叙》,第1—2页,金一:《女界钟》,1903年。 (22)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8页。 (23)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8—10页。 (24)林宗素:《叙》,第2—3页,金一:《女界钟》。 (25)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10页。 (26)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10、9、11页。 (27)参见《论女界医学之关系》之炼石志、《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成立通告书》、炼石:《罗瑛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2、5期,第19、75、51页,1907年2月、3月、6月(实际大约11月出版)。 (28)中国新女界杂志社:《本社特别广告》,《中国新女界杂志》4期,卷首,1907年5月,实际大约7月出版。 (29)参见《本社特别广告》《本社借股诸君公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第6期,卷首,1907年6月、7月,实际大约11月、12月出版。 (30)第4期《本社特别广告》称:“惟前因特别事故,以致未能如期出版。” (31)炼石:《罗瑛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第54页。 (32)炼石:《女权平议》,《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2—4、6页。 (33)其中《美国女界之势力》与《纪美国妇人战时之伟业》署“炼石”,刊《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2、4期;《请看俄罗斯二百年前之妇人界》与《欧美之女子教育》署“娲魂”,刊第1、2—6期。 (34)炼石:《留日见闻琐谈》,《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34页。 (35)炼石:《发刊词》,第1—2页,《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 (36)炼石:《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42页。 (37)炼石:《发刊词》,第2页,《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 (38)炼石:《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3期,第44、24—25页,1907年2月、4月。 (39)炼石:《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43—44页。 (40)秋瑾:《致陈志群》其三、其四(1907年4月3日、4月23日),《秋瑾全集笺注》,第452、454页。 (41)炼石:《女权平议》,《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6页。 (42)炼石:《女界与国家之关系》,《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3页。 (43)娲魂:《补天石》,《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49页。 (44)炼石:《中国婚俗五大弊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第3、5、8、2、6页。 (45)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79、81、80页。 (46)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3页。 (47)《本社征文广告》,《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卷首。 (48)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81页。 (49)炼石:《女界与国家之关系》,《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3页。 (50)《本社悬赏征文广告》,《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卷首。 (51)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4期,第20页。杂志第三期再次刊登《本社征文广告》,吁求“男女同胞”踊跃发表意见,“想热心君子,必不忍坐视而缄默耳”。 (52)炼石:《留日见闻琐谈》,《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32、134页。 (53)炼石:《发刊词》,第2页,《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 (54)参见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4期,第13、19—28页。 (55)炼石:《留日见闻琐谈》,《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34页。 (56)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4期,第21页;巾侠:《女德论》,第1期,第13—15页。 (57)炼石:《发刊词》,第1、2页,《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本报五大主义演说》,第4期,第24—25页。 (58)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80页。 (59)炼石:《女权平议》,《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1—2页。 (60)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97—98页。 (61)燕斌:《浩气吟》其四,《中国女报》第1期,第47页,1907年1月。 (62)参见笔者:《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辑,第311—350页。 (63)此广告至少在《(续办)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复报》第10期以及《神州女报》第1号刊载过。 (64)何殷震:《女娲像并赞》,《天义报》第1号,卷首,1907年6月10日。 (65)参见万仕国:《何震年表》,第3页,自印本,2010年。 (66)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第30页,1907年9月1日。 (67)何殷震等:《〈天义报〉广告》,第1页,《(续办)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1907年7月。 (68)何殷震等:《简章》,《天义报》第1号,卷首。 (69)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第30页。 (70)震述:《女子复仇论》,《天义报》第2号,第4、1页,1907年6月25日;何殷震等《〈天义报〉广告》,第1—2页。 (71)何殷震等:《〈天义报〉广告》,第2页。另参见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6页。 (72)何殷震等:《简章》,《天义》第8—10卷合册,卷首,1907年10月30日。 (73)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6页。 (74)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1—2页。 (75)炼石:《中国婚俗五大弊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第3—10页,1907年4月。 (76)何殷震等:《〈天义报〉广告》,第1页。 (77)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3、4、2、3—4页。 (78)震述:《女子复仇论》,《天义报》第2号,第1页;《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3页。 (79)《女子复权会简章》,《天义报》第1号,卷末。 (80)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4、6页;《幸德秋水来函》及其后之“震附志”,《天义报》第3卷,第45、46页,1907年7月10日。 (81)震述:《女子复仇论》,《天义报》第2号,第3、2—3页。 (82)何殷震等:《简章》、震述:《女子解放问题》(又题《妇人解放问题》),《天义》第8—10卷合册,卷首、第5页。 (83)震、申叔合撰:《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第17—19页;第7卷,第22页,1907年9月15日。 (84)震、申叔合撰:《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7卷,第20—21、16—18页。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刊《天义》第8—10卷合册。 (85)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第5卷,第33页,1907年8月10日。“志达”很可能是何震的另一笔名,《天义》第13、14卷合册所载《女子教育问题》与《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二文,目录页与正文中作者署名之“志达”与“震述”相互易位,此后亦未有更正说明,可见二者本可置换。而阅读“志达”的文字,其思路与表述也与何震、刘师培最接近。 (86)志达:《女子教育问题》,《天义》第13、14卷合册,第1—2、6页,1907年12月30日。 (87)震述:《女子解放问题》,《天义》第8—10卷合册,第3页。 (88)志达:《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第3卷,第34页。 (89)震述:《女子解放问题》,《天义》第7卷,第5页;第8—10卷合册,第1、6页。 (90)震述:《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天义》第13、14卷合册,第20页。 (91)震、申叔合撰:《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第15页。 (92)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