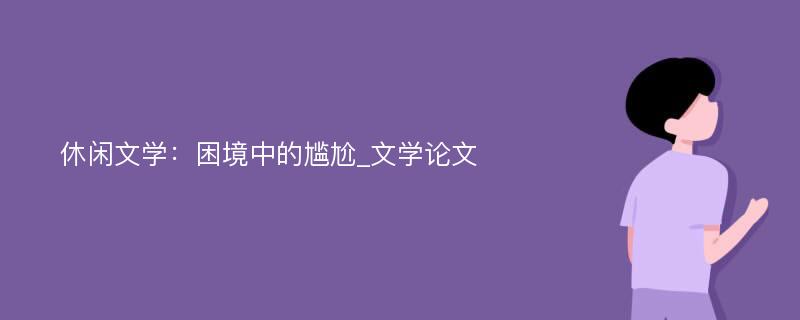
休闲文学: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右为难论文,处境论文,尴尬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饴先生的第一篇文章(即《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见《文艺报》2000,4,25)确有石破天惊之功,因为他毕竟指涉了当今社会所的确存在而别人未曾言说的话题,并第一次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归纳与总结。因为发其端,所以在其对休闲文学的定义界说与理论阐述中必然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缺陷与幼稚,但恰恰就在这些幼稚之中蕴藏着他对休闲文学清晰的定义与言说方式:“我的所谓的休闲文学就是指以写休闲并以供读者休闲为旨趣的一类文学作品。”(见4月25日文)并进而从题材特点、审美特征和价值上加以补充说明,“题材上的特点最明显,即具有休闲性,也即必须写休闲”,从审美特征而言“即具有审美性的特点”,从价值而言,“休闲文学亦不同于一般的审美,它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让读者从社会政治中跳出来,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体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真我’‘本我’上来。”当然,这些言说尚有可议论的地方,暂且不论。但在这里魏饴先生毕竟给我们明确的描绘了休闲文学的基本形态,在理论的不成熟性中却还隐有其自身的明晰性;休闲文学完全与政治功利无关,或者说休闲文学无论在题材、审美特征和价值实现上都摆脱了阶级与政党工具的角色地位。这一思想其实也贯穿于魏饴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中(即《再谈休闲文学——兼与张炯先生商榷》见《文艺报》2000、8、15)这篇文章是魏饴先生在看到5月23日《文艺报》所刊发的张炯、陆贵山(包晓光)、童庆炳、陶东风等先生的文章而写的。受这些文章的影响,魏饴先生自然是对他们的建议有所吸收以补充修改在第一篇文章中的疏漏与不足,但也正是在此,魏饴先生却将休闲文学置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在这篇文章中魏饴先生对休闲文学的论述是在区分休闲文学与文学休闲中展开的。他指出张炯之所以认为其他文学也能满足人们休闲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张炯混淆了休闲文学与文学休闲的关系,“我认为休闲文学的休闲境界是一种轻松自在的、注重品位人生乐趣的、没有政治功利性的休闲;而文学休闲的休闲则是一种在审美自由的境界下接受道德教育、带有政治功利的休闲。这就是说休闲文学的休闲不仅仅是审美的自由与休闲,还在于是实实在在的自由与休闲。”(见8月15日文)并借用“安适的休闲”与“忧患的休闲”的划分将休闲文学界定为“以读者的安适休闲为旨归”。这些论述主要是沿用了第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在这里魏饴先生却十分巧妙地运用了逻辑学中偷换概念的方法将“休闲文学”与“文学休闲”置换成“休闲文学的休闲”与“文学休闲的休闲”来反驳张炯关于后两者相同的观点。实际来看,魏饴先生的论述与其说是两种休闲的区别,倒不如说是两种文学题材的区别,因为就休闲来说,无论是“休闲文学的休闲”还是“文学休闲的休闲”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就主题内容来说休闲文学除却休闲之外别无其它,而文学休闲则还有休闲之外的道德教育和政治功利性。其二魏饴先生将休闲划分为“安适的休闲”与“忧患的休闲”来指称休闲文学与其他带有政治功利性的文学尚有可商量的余地。且不说小至个人中到整个国家、民族大到全人类处于忧患时是否能休闲得起来,单是这“忧患”与“政治功利”就难以并举,政治功利所言说的是文学的一种存在状态,而忧患呢?休闲文学固然可以“安适的休闲”为旨归,但带有政治功利性的文学能以“忧患的休闲”为旨归吗?我看未必。假如能够,则这一论点又为魏饴先生以后的论述埋下了自相矛盾的种子。
在魏饴先生看来如何言说道德教育、政治功利性与文学的关系是决定文学作品能否成为休闲文学的关键。休闲文学是远离道德教育与政治功利性的,这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但是“休闲文学不要求有什么政治功利性,不去追求主体的重要意义,不等于就是那些摆满地摊的形形色色的单纯供人消遣的低趣趣味的东西”,(8、15文)魏饴先生注意到休闲文学的高品位,这是比第一篇文章成熟的地方,显然是受了其商榷文章的影响,“这一点,在笔者的前一篇文章中未能涉及,但这又的确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同上)魏饴先生在界定休闲文学的高品位时说:“休闲文学的高品位,意在要求休闲文学要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不过它的思想价值不是指一般意义的政治功利,而多是指超出了阶级利益和政党利益的,诸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人文关怀、环保意识、山水之美等,体现的是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同上)魏饴先生在这段看似完美(因为它解决了休闲文学受到指责的一个大问题)的论述中又给我们留下了疑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在当今社会超阶级利益的人文关怀、环保意识、山水之美又何以存在?尽管这些是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但又何尝与每个国家、每个阶级的利益不无干系。其二,就人文关怀来说,文学在关照人的生存发展现状时又能哪些是以休闲姿态出现的?无论西方人文传统中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当代对人的反思与追问,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人的拷问以至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又有哪些透露出了休闲意识?环保问题更是如此,人类在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中更多的是忧患、恐惧与无奈,因为人类在近几百年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在对大自然的暴虐中种下的是受大自然报复的种子,面对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休闲又存在何方?相对于阶级利益和政党利益,这些关系到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题似乎更沉重,而依此为界定休闲文学高品位的标准,读者恐怕连休闲的影子也找不到。休闲性与高品位相互撞车,从而表露了对以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来界定休闲文学高品位的怀疑。这是魏饴先生的失误,而在文章最后魏饴先生则坦然地承认了这种失误,从而在休闲文学的休闲性与高品位的二难选择中陷入了尴尬境地,“休闲文学的高品位与号角文学的高品位也不是对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事业,从大文化的角度,其休闲文学高品位追求的内容应该包含在我党所倡导的主旋律文学或号角文学之中,只不过是各有侧重,各具特色而已”。尽管强调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魏饴先生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清晰描述过的休闲文学的形态终于在第二篇文章中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以至终于将再三强调脱离政治功利性的休闲文学在高品位处重又嫁给了号角文学。
对此,我们应该作出以下的思考或怀疑:
首先,在界定给读者以安适的休闲为旨趣的休闲文学时,只是以排除了道德说教和政治功利性为标准是否可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定了道德说教与政治功利性只是解除了硬套在文学上的工具性枷锁,将人拉回到了文学的视野之中,用文学的思维方式去关照人的生存、发展以及生命情感等复杂的世界,实现文学与人的对话从而完成人的诗意性的栖居。而这些与休闲文学却还差之千里。
其次,休闲文学的高品位是休闲文学得以正确引导人们消闲闲暇时光的重要根据,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休闲文学的高品位。笔者以为以思想内容或思想内容的价值为标准来界定休闲文学的品位高低似有不妥。如果相反,则魏饴先生所列举的诸多以写休闲为内容的报刊如《花木盆景》《八小时以外》《美食》《健与美》等其思想内容与思想意义又在哪里?因此笔者以为核评休闲文学是否高品位应以其是否能积极健康地正确引导读者度过闲暇时光为准,并且闲暇时光之后不至于给读者造成生活上的倦怠、精神上的萎靡,而应还他一个轻松愉快乐观向上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