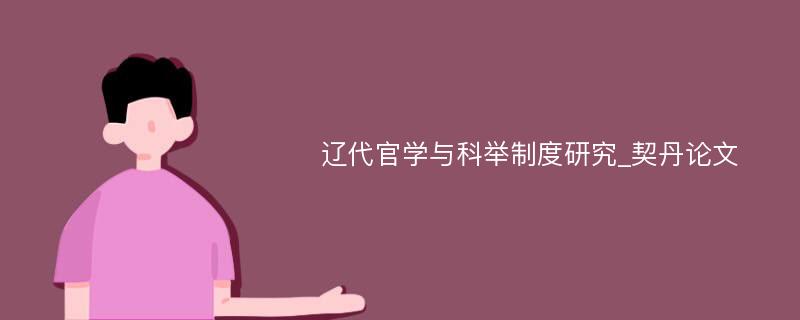
辽代的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科举论文,制度论文,官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是契丹民族于唐末五代之际,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国家。辽在建国以后,推行了一套开创振兴文教的举措,大大地推进了包括契丹民族在内的辽代文明。在封建时代,教育是科举的基础,科举则是教育的终极目的,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辽文明的兴盛与它所推行的教育、科举政策密不可分。
一
辽代学校的兴建,始于辽太祖时,其后各代君主都相继扩建或增设,学校的设置由京城向各地发展,最终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规模。
辽的中央教育机构包括国子监和五京学。辽太祖建国初就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作为京城教育的管理机构;上京还设有太学,负责对生员传道授业(《辽史》卷47、48)。辽太宗讨平幽州,又于燕都建南京太学(同上,卷48)。辽道宗即位伊始,于清宁元年(1055年)下诏设学养士,中京、东京、西京国学即在这一时期内相继兴建。清宁六年道宗又诏建中京国子监,其建制全仿上京的规模,并亲临祭祀孔子庙(同上,卷48)。这样,辽的中央官学机构就配备齐全了。辽代国子监官为升朝官,五京学学官为京官,国子监官属有祭酒、司业、监丞、主簿,京学属官有博士、助教各一员。在辽统治相对安定的时期,五京学的规模得到较好的发展。圣宗时南京太学生员不断增多,到统和十三年(995 年)出现了供养不足的矛盾,圣宗特赐水硙庄一区,以便赡养(同上,卷13)。
地方官学在辽初并未普遍设置,往往根据地方需要而权宜建立。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归州奏报朝廷说:“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朝廷允准了归州的请求,设置归州州学(《辽史》卷15)。大规模建设地方学校是在辽道宗时。前面已述及辽道宗于清宁元年下诏设学养士,扩大学校规模,并颁赐《五经》传疏给地方官学。至此,辽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委派博士、助教作为专任职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这套教育机构完全是按照中原地区学校的模式而建立的。有关文献记载, 大公鼎在咸雍(1065—1074年)时为良乡县令,建孔子庙学;耶律孟简于大康(1075 —1084年)时为高州观察使,修建学校,招纳生徒(同上,卷104)。 辽西京的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辽史拾遗》卷16引《宣府镇志》),辽的学校规模蔚然可观。
在学校师资配置上,辽朝廷主要任命一些汉学儒生充当学校教官,在士人匮乏的时候,甚至还任用一批投诚的敌国士人充当教官。如武白,原为宋朝国子博士,被俘入辽,被委任为上京国子博士(《辽史》卷82)。辽圣宗统和七年,宋朝进士17人携家眷北来归顺,辽朝廷命有司考校,中第者补为国学教官(同上,卷12)。不难想象,这些学官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于儒学的态度会与中原地区有什么区别。
除了中央、地方的各类学校以外,辽朝廷还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诸王文学馆,并安排老师授课,类似于历代皇朝的师、傅之职。东丹王耶律倍曾接受张谏的训导,“让国皇帝在储君,虽非拜师。一若师焉”(《全辽文》卷4赵衡《张正嵩墓志》)。辽圣宗太平八年(1028年), 长沙郡王耶律宗允等奏请遴选诸王伴读。重熙(1032—1054年)中又挑选进士姚景行为燕赵国王教授(《辽史》卷47)。这些教官保证了皇室成员接受良好的教育。辽代皇室子弟的文化水准往往高出时人,这与他们接受专门的贵族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像辽圣宗、兴宗、道宗、耶律倍、耶律隆先、萧孝穆、萧阳阿、萧柳、萧观音、萧瑟瑟,他们或为皇亲国戚,或为帝王后妃,都对汉文化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其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契丹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辽代也是出类拔萃的。
崇儒尊孔是辽代学校教育的主导思想。这一思想与辽代君主深受儒家知识分子的影响密切关联。辽立国之后,一批汉族知识分子作为君主的高级顾问侍从于皇帝左右,受到重用,有名的像韩知古、康枚、王郁、韩延徽、张砺等人,在立国方略上都对辽君主产生了极大影响。受汉族士人的影响,儒学体系也就理所当然地移植于辽的教育中。辽太祖立国之初,修建孔庙、佛寺、道观,似乎对三教还存有不偏不倚的倾向。辽太祖询问左右侍臣说:“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大臣们都认为应敬奉佛祖,辽太祖却并不同意,回答说:“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回答道:“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礼宜先。”太祖大悦,诏令修建孔子庙,命耶律倍春秋二季行释奠礼(《辽史》卷72)。对这则记载,我们尽管可以怀疑是史官的溢美之词,但是从辽太祖回答的话语中,大致可以揣测到辽太祖的心态,弃佛尊孔既是契丹民族吸收先进文明,促进本民族进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笼络北方汉族士人所作出的姿态,毕竟儒学在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影响,其影响绝非外来的佛教所能比拟。后来的辽代君主越来越表现出对传统儒学的偏倚,祭祀孔庙,亲临讲筵,翻译刊修儒学典籍,这与金、元两代君主尊崇佛、道的做法有明显的区别。
在教学科目上,辽代也以儒学经典作为主要研习内容。辽道宗即位之初曾颁发《五经》传疏于学校,作为学校教材(《辽史》卷21),后又令有司刊行《史记》、《汉书》等史籍让学生学习,并诏谕学生要“穷经明道”(同上,卷23、25)。而贵为皇帝的辽道宗本人,也亲自聆听儒学侍臣讲经论道,表示出对儒学的尊崇。大安二年(1086年),辽道宗召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讲授五经大义;四年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命燕国王耶律延禧书写《尚书·五子之歌》,以加强对皇子的儒学教育(同上,卷25)。
二
辽代开进士科取士的创始时间,据文献记载,大概是在太宗时代。太祖朝未曾开科举。《契丹国志》称:“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傯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辽史》记载室昉于会同(938—946年)初登进士第(《辽史》卷79),太宗朝的科举仅有此一例。后来,景宗保宁八年(976 年)曾下诏恢复南京礼部贡院(同上,卷8),既开贡院,就必然有科举之事。 清人厉鹗也找到了保宁九年易州进士魏璟登科的记载(《辽史拾遗》卷16引《易水志》)。不过。这时的科举并非常制,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科举是“偶然为之,是为在出使、报聘、接送外国使者等对外交往活动中,为避免鄙陋无文,让人耻笑,而临时作出决策,吸收一批文化人才”(注:程方平《辽金元教育史》第四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辽代科举作为定制始于圣宗耶律隆绪。圣宗统和六年诏开贡举,是年放进士一人及第(《辽史》卷12)。此后科举延续不断,到圣宗太平十年下诏将于明年施行贡举法。次年圣宗驾崩,继位的兴宗具体实施了新的贡举法。辽圣宗所颁贡举法的内容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具体条文已无从得知。然而根据后来的考试情况推测,可能包括了科举考试年限、程文和及第人数等诸方面的规定。《辽史·兴宗赞》称兴宗“亲第进士,大修条制”,“求治之志切矣”,这一赞语当与他在科举方面实施其父教令的行为有关。辽道宗也对科举持积极态度,他贯彻了兴宗以来的科举条例,并有所发展。咸雍十年,辽道宗亲自出题御试进士,并且增设贤良科目,这些做法在辽代都属首创(同上,卷23)。此后,辽的各代皇帝都坚持科举取士,即使到天祚皇帝末年,辽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宣宗耶律淳还于建福二年(1122年)开科举,放进士19人及第;皇后德妃执政,又开科举,放108人及第。
辽代科举经历了一个从随宜到有定制、由小范围到大规模的演变过程。辽初科举无定制,圣宗时考试时间订为每年举行一次。自圣宗统和六年至十八年,连续进行了12次科举考试,其间仅统和十年停考一次。这一时期开科频繁,而及第人数极少,每科多则3人,少则1人,全部总计及第者仅23人而已。自统和二十年至兴宗太平十一年间,大致实行的是每两年考试一次(注:这段时间也有例外的年分,如统和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开泰元年、二年、三年就不间断地连续举行科举考试。),共举行了18次考试,及第人数增多,每科可录取50馀人,及第总人数达到548人。在这一时期内,有的考试是皇帝临时增开的恩科。 如太平五年圣宗饮宴于内果园,宣召进士72人,试以诗赋,分出等第,任命前14人为太子校书郎,后58人为崇文馆校书郎。二十九年,平定沈州宗室叛乱,对于协助节度使张杰坚守沈州的士人张人纪、赵睦等22人,召赴入朝,以诗赋考试,全部赐进士及第(《辽史》卷17)。自辽兴宗重熙元年开始,直至辽灭国,基本上实行四年一次的科考制度,其间共举行考试25次(包括耶律淳、德妃监国时的考试)(注:《辽史》记载于太平十一年及重熙元年两次考试,放进士刘贞等57人及第,实际上为重复记载,两年内仅举行过一次考试。),录取人数更是大为增加,最多的一次有138人,总及第人数达1786人(注:《辽史》、 《续通考》记载有重熙十九年、咸雍十年两次科举,却无及第人数的记录,只好暂缺。)。
辽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在圣宗时仅设了词赋、法律两科,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契丹国志》卷23),词赋科与唐宋的诗赋科相仿,法律科当是为选拔精通法律条文的人才而开的科目,与宋代明法科相似。辽道宗咸雍六年,又增设贤良科,诏应该科试者,首先进上所业十万言(注:厉鹗《辽史拾遗》卷一六《补选举志》引李世弼《金登科记》:“天会四年,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诗》、《书》、《易》、《礼》、《春秋》为次。盖犹辽旧也。”按照这一说法,辽代的科目就应不止是词赋、法律、贤良科,还有经义等科目,但是《登科记》所言只是金代科举的情况,辽代科举与此不一定全相吻合。姑附于此,俟考。)(《辽史》卷23)。辽代科举也分甲、乙科录取,按考试成绩区分出等第,如杜防中开泰五年进士甲科(《辽史》卷86),杨皙中太平十一年进士乙科(同上,卷89),赵徽中重熙五年进士甲科,姚景行、王观中当年乙科(同上,卷96、97)对于及第的进士,直接除授不同职官,第一名授予奉直大夫、翰林应奉文字,其馀人则授从事郎(《契丹国志》卷23)。
辽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按照《契丹国志》的记载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辽史》卷23),却没有提及廷试的情况。辽圣宗有两次御前引试的纪录:统和二十七年,御前引试刘二宜3人;二十九年,又御试高承颜2人(同上,卷15)。但是这时的御试还未形成定制,往往是临时的举措。辽兴宗重熙五年御元和殿试进士,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作为考试题目,开了辽代御试进士的先例(同上,卷18)。自此辽君主御试进士也就成了定制。
辽朝廷竭力鼓励士人参与科举考试。有的读书人不愿意赴考,州县还要“根刷遣之”(《契丹国志》卷23)。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对于归顺契丹的敌国士人,辽皇帝也采取了不拘一格、取才异代的宽容态度。前述统和七年,宋朝进士17人归附辽朝后的安置事例即为明证。统和十二年,辽圣宗又下诏各部:“所俘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接着又下诏郡邑贡明经、茂材异等的人选(同上,卷13)。可见辽代统治者对士人应举的态度是积极鼓励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国家对应试者的资格有种种限制。首先辽朝廷拒不允许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契丹人耶律蒲鲁曾于重熙中参加进士科举并且及第,主考官以没有允许契丹人参加科考的条文为由,禀报兴宗,以蒲鲁的父亲擅自让儿子参加考试,实属违法,处以鞭刑二百(《辽史》卷89)。这种限制乃是对契丹民族文明的进步起着阻碍作用的一种愚蠢至极的行为。我们从有关文献中查找到的契丹籍进士仅有耶律大石一人,为天庆五年(1115年)进士(同上,卷30),而他本人原是皇室成员,后来曾经建立西辽国,他能参加科举考试恐怕应当算是一个特例了。辽兴宗于重熙十九年(1050年)下诏限制医卜、屠贩、奴隶及悖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天祚帝乾统五年(1105年)又明令禁止商贾之家不得应进士举(《续文献通考》卷34)。这些条例包括了对应举者职业和所谓道德品质的限制,表现出辽统治者对医、贾等行业的轻视,同时也是对儒学士人科举专利的一种保护性措施。
有辽一代,科举成为读书人入仕的主要途径,由科举而成为辽代重要官吏的人为数不少,例如:张俭,统和十四年为进士第一,官至南院枢密使、左丞相,封韩王;杨绩,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官至南府宰相、南院枢密使;赵徽,重熙五年中进士甲科,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门下侍郎、平章事;李俨,咸雍进士,官至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封漆水郡王,赐姓耶律;张孝杰,重熙二十四年进士第一,官至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北府宰相,赐名张仁杰,以比唐代名臣狄仁杰。刘二宜、刘三嘏、刘四端、刘六符兄弟都曾进士及第,三嘏、四端还娶辽公主为妻,刘氏家族成为了辽的重臣世家。
三
关于辽代教育、科举方面的研究,历来都未得到足够重视,有的研究著述或矢口不谈,有的则或贬之过甚。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不少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关注,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这是一种可喜的学术现象,但是总体来说研究还有待深入。我们也想就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一点自己肤浅的看法,试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辽代的教育科举制度持否定者有之。金代作家元好问就认为“辽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厉鹗《辽史拾遗》卷16引),后来有一些研究者也以此持论,以为辽代教育、科举一无是处。我们认为这种见解有失偏颇。契丹民族一旦从鞍马游猎的原始生活中走出来,能够迅速地吸收汉民族先进文化,改变过去那种依靠结绳记事的愚昧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仿效行为而加以指责。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封建时代科举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因而封建时代的教育(尤其是官方教育)就必然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乃是封建时代教育的通病,在此我们就不能够苛责辽代所存在的缺陷了。至于说辽代科举“视五季又下衰”,也有欠公允。辽代的科举应该说是颇有成效的。首先,它改变了辽的统治构架,使其从最初的部族世选与地方豪族执掌朝政的模式,过渡到兼用科举入仕的制度,这显然是契丹社会文明的开放进步,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契丹统治者允许境内的汉人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以科举入仕,参与朝政,大批汉族士人得以进入官吏阶层,形成所谓的“儒吏”集团,这对于改变辽官吏的人员组成和文化素养,推行以儒家原则治国的方略(至少在北方汉人区域是如此),具有重大影响。其次,契丹统治者所推行的文教政策,对于消弭契丹、汉民族间的隔阂,维护北方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延续辽国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建国时代的阿保机开始,以至后来的圣宗、道宗,他们都是深受北方汉族士人影响的帝王,在其治国方略中体现出的儒学思想,是汉族士人薰陶的结果;同时辽朝廷推行的科举制度又能保证汉族士人入仕,继续扩大其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纵观辽立国的历史,其政权能够延续百年之久,一套得当的文教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又,辽代通过教育、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既充实了自身的政权,在辽亡以后,这批人转而为嗣后的金代所用,其影响甚至还可以延续到金以后的元代。从积聚人才的角度来看,辽代教育、科举也是功不可没的。金代初年的卓有成就的文学家,除了一部分是由南而北的宋人以外,其余都是自辽入金的人才。金开国之初实行“借才异代”的政策,如果没有辽为其提供人才,也将只是一纸空文。元初著名政治家、作家耶律楚材,就是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的耶律氏家族的传人。再次,辽代教育、科举所孕育的辽代文明,产生出了一批辉煌的硕果,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古文明的一部分。辽的契丹大、小字,被女真人吸收,成为女真文字创制的蓝本,一直通行至金代中叶。辽代的建筑、音乐、雕刻、绘画、服饰等艺术,流传至今还是极其珍贵的历史瑰宝。
然而,倘若将辽的教育、科举与金代、元代、清代作一比较,我们又可以发现,辽代的成就确实远逊于后者,尽管金、元、清三代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金、元两代立国的时间也与辽大致相同,但辽代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进一步研究辽代教育、科举的状况,还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辽代的最高统治者,如皇帝、后妃、亲王等,对于吸收汉文化大多具有浓厚的兴趣,往往还有较高的造诣,但是契丹统治者对于契丹族人,却从未像女真人、蒙古人那样设立女真、蒙古学,或是开设女真、蒙古进士科,真正来全面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兴办教育、开设科举只是为契丹人所统治的北方汉民族而设。其次,辽代的契丹统治者对汉族士人既没有像清代那样实施残酷的文字狱,但也没有组织人力去编纂《四库全书》那样浩大的文化工程,契丹统治者对实行文治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因此导致了辽代文化发展的滞后。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契丹统治者所采取的“北南分治”政策所致。辽在立国之初,就从政治、官吏制度上划分了北、南的界限,《辽史·百官志》称:“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北、南分治,这对两个文化传统、生活习俗迥然有异的民族在同一政权下相处,恐怕是不得已的权宜措施。北方的汉民族需要分治,是要避免落后民族的野蛮干扰,是一种消极的避难措施。辽太宗攻克汴京后,其智囊人物张砺就曾经向太宗建言:“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同上,卷76)辽太宗没有采纳张砺的谏议,辽最终还是失去了中原。作为战胜者的契丹民族,在拥有北中国的土地之后,辽统治者一方面对汉族文化需要大量吸收,对汉族士人需要大力接纳,以利于自身统治;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契丹民族原来具有的鞍马游猎、崇尚武功的习俗却绝不能丢弃,不允许契丹的民族特性中融入汉民族文化的因素,对契丹族人的汉化过程始终怀着畏葸抵御的态度,“以国制治契丹”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北南分治”正是基于此目的而产生的。北南分治的负面影响是加深了蕃、汉之间的对立。蕃、汉之别在辽代是极其严格的,即使是那些学习中原文化很突出的辽代君主,在他们的心目中也仍然存在着森严的壁垒。辽太宗第一次南征幽州失败,撤回上京时,太后告诫他说:“使汉人为胡主,可乎?”太宗说:“不可。”太后又说:“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资治通鉴》卷284 )辽太后明确地批判了辽太宗觊觎中原的做法。后来辽太宗攻入汴京,作了短暂的中原皇帝,在中原汉族百姓的反抗下被迫撤离,对大臣说:“吾在上国,以射猎为乐,至此令人悒悒。今得归,死无恨矣。”(同上,卷286 )这大概也是辽太宗畏惧汉民族文化习俗的真实心声吧。前面我们提及的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也正是害怕文教扰乱了武功,反映出辽代统治者抱残守缺的态度。
另外,我们还要附带提及辽代严厉的书禁制度,这也是制约其文化发展的因素。宋人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说:“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卷15)沈括曾经在熙宁年间出使辽进行边界谈判,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当北宋的学术迅速发展的时候,辽的书禁制度却严重地阻隔了与北宋的文化交流。不过这种官方的书禁制度并未完全隔绝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非官方渠道,仍有一些北宋作家的文集在辽境内传播。苏辙在宋哲宗元祐时出使辽,途经燕京,接待使与其谈及苏洵、苏轼文集流传的情况,对未能见到苏辙文集表示遗憾,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诗中对此颇有感慨:“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出使回朝后又上奏章请求朝廷禁绝诏令文字流入北方(《栾城集》卷42)。民间的文化交流毕竟比不上官方的规模,而且违禁的偷刻翻印大多以牟利为目的,书贾的兴趣只是集中在那些受时人欢迎的文集上,因此北宋学术著述大部分不能传入辽,辽的大部分典籍也始终未能传入中原,现存辽代书籍数量极少,大概是书禁制度带来的恶果。
对于先进的文明不能兼包并容,反而闭关自守加以封锁,辽的这种文化政策就历史地决定了辽代文明发展进程的缓慢,辽代的文化成就注定不及金、元等朝代。
综上所述,我们对辽的教育、科举制度可以概括得出以下结论:辽代的教育、科举制度上承唐、五代,仿效宋代,下启金、元时代,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域建国以来的创始。契丹统治者所推行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一方面是对北方汉民族文明的延续,另一方面却又禁止契丹民族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制约了契丹文明的进程。
标签:契丹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契丹国志论文; 宋朝论文; 国学论文; 辽史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