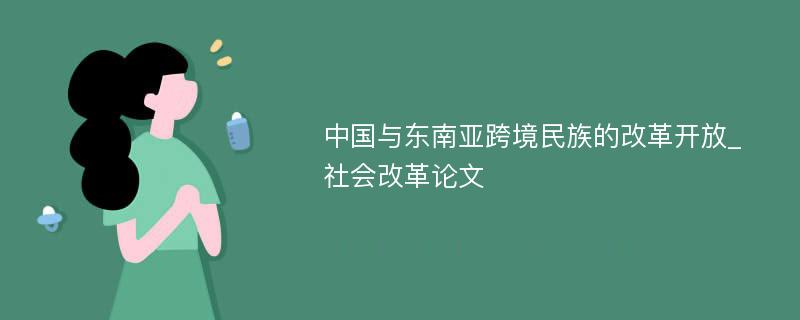
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的改革开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 (2000) 04-0013-08
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中国西南如何发展。而探讨在我国境内的这些民族如何更好地利用与周边各国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以促进我国跨界民族和西南各民族的发展,则是中国学者、特别是民族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
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和广西,有长达5000公里左右的陆地边界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边境内外分布着10余个跨界民族;泰国虽未和我国直接接壤,但地域紧邻,且两国的民族源流、历史文化、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多有共同或相似之处,与我国跨界民族的发展更有不可忽视的特殊关系,自然也应是我们研究的范围。本文讨论的,是在这片富饶、丰裕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我国境内的跨界民族: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族、傣族和布依族;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藏缅语族的彝、怒、哈尼、景颇、傈僳、拉祜、独龙等族和语言系属尚未属后确定的京族;还有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此外,散居于东南亚各国、人数多达2000万以上的华人,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跨界民族”,但和我们所要探讨的跨界民族的改革开放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所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复杂原因,我国西南的跨界民族在社会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语言文字使用、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崇拜等各方面,既有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迄至20世纪50年代初,其居地与缅甸、越南、老挝3国接壤的傣族(缅称掸族,越、老、泰均称泰族),由于封建领主制和农村基层所保存的古老的村社制度的封闭性,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当缓慢,生产耕作粗放,技术条件落后;长期的封建领主的统治和封建领主土地制的制约以及农村公社的存在,使他们的社会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畜牧业、家庭副业等方面都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1]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上述制度才逐步废除,社会经济才有了较快的发展。跨中、越、老、泰、缅5国边界而居的苗族,基本的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山地农业,且长期处于不断迁徙游耕的状态。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其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家庭手工业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铁制工具,尚未出现职业商人。同苗族一样跨居5国边界的瑶族,亦以游耕经济生活著称于世。长期频繁的迁徙和流动于国内外,使其经济发展水平极低,个别地区甚至还保留着氏族制的残余。其他一些民族,如中越边界线上人口最多、分布面最广的跨界民族壮族(越称岱族和侬族),跨居于中越两国边界的布依族,聚居于中、缅、泰3国边界的傈僳族,中、缅、老、越等5国都有分布的拉祜族、哈尼族(越称哈尼族,缅称高族,泰称“卡果”、“果”、“依果”,老称“卡果”、“依果”)和克木人(泰、缅亦称克木人,越、老称克木族),跨中、缅两国而居的景颇族(缅称克钦族)和德昂族(缅称崩龙族),散居于中、老、越3国的彝族(越、老均称倮罗族),中、越两国的京族(越称越族),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前述跨界民族的一些基本的经济、社会特征,处于相当低下的社会历史起点。[2]而尤具典型意义的是,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西盟、沧源、孟连等地的我国佤族(缅也称佤族,泰称拉佤族),自19世纪以来,社会虽然发生了某些显著的变化,但在阿佤山中心地区的西盟及沧源的部分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社会经济处于相当封闭落后的状态,其社会组织是原始的农村公社和部落,其信仰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不但大量宰杀畜禽祭鬼,甚至还有猎人头祭鬼的习俗[3]。
这些现象,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
前些年,杜玉亭同志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脱胎差异和云南后进民族的历史跳跃性等问题时,曾将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少数民族所处的丰富多彩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分成若干种类型,有过精当、中肯的分析。这种分析是符合我国西南跨界民族的实际的。他举例说:“如,人口在百万以上的苗、瑶、哈尼和人口数十万的傈僳、拉祜等族,其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虽然不典型,但其社会总体发育水平不仅未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还存在着农奴制、奴隶制以至原始社会的遗迹”[4]并认为,“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以致在这种极不平衡中可以发现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即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中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原始公社——奴隶制——农奴制——汉族式地主制。”[5]就是在这种十分低下的历史起点上,经过50余年艰苦、曲折的奋斗,我国西南的跨界民族目前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上,各民族已经彻底摆脱了旧社会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羁绊,实现了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保障的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大多数跨界民族生产方式较前有所改变,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有了可喜的开端;民族文化逐步繁荣,社会事业有所发展。在我国境内的跨界民族,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的影响。[6]而相邻各国的同一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大体与我国相同,但各国政治制度不同,民族政策各异,经济措施也有较大的差别;加上各国时有政治变动的发生,一些国家甚至局部战争不断,某些边境争端而导致的武装冲突和围巢贩毒集团的武装斗争等因素,也妨碍了这些民族的发展。目前,各国跨界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并不高,同时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复杂格局。
二
研究我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民族及改革开放的问题,首先应当将其置于当代世界、尤其是亚洲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社会的宏观背景中去考虑。这一背景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是当今世界形势剧变,旧的格局已经终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正在加速。近年来,世界不少地区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加深,而亚洲地区虽然也显现或潜伏着民族冲突、教派纠纷、种姓对立、贫富矛盾等等问题,但总的说来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如东南亚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0多年前不到1/6,至90年代已上到1/4。[7]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6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约达32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达3400亿美元,外国旅游者超过2000万。[8]近年来,这两方面的发展仍保持了增长势头。整个亚太地区政治局势比较稳定,区域内经济关系逐步扩大。[9]世界经济的重心正逐步向东转移,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热点。这就为我国西南的跨界民族及整个西南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扩大,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本文认为,研究我国西南跨界民族的改革开放问题,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主要是:
首先,要巩固和维护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其特殊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对我西南及全国国防的巩固和边境的安宁,有特别的重要意义。50余年来,国外某些敌对势力一直利用西南边境对我国进行破坏和渗透,特别是近些年来境内外贩毒集团采用各种形式大肆向我境内输入毒品,造成边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经济破产,家庭解体,感染艾滋病,甚至冒险犯罪,不但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民族、社会造成许多新的不稳定的因素,并严重地损害了民族人口的素质。[10]另一方面,由于西南各跨界民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境外敌对势力的挑唆、破坏,加上西南边疆自然地理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各民族语言不同,性格各异,一些民族内部存在着繁多、复杂的支系,少数地区还出现过土地、水源、林产等纠纷,等等,这些,都给边疆民族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要保持边疆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在加强边防,反对敌对势力(包括贩毒集团)的破坏的同时,当前要继续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使民族平等、互助、团结的观念真正深入到各民族群众心里。尤其要强调对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帮助各民族群众认识民族内部各支系之间,各民族之间生产、生活、文化、语言、风习的某些差异的历史、社会原因,引导各民族群众认识对方的特点和长处,促使其相互学习,彼此尊重,造成民族团结互助的良好社会风气,为边疆的安定团结作出贡献。
其次,要充分尊重、利用和不断拓展、疏通西南跨界民族和国外同族系民族的民族感情、亲缘关系,大力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共同的民族源流、密切的姻亲关系、相同和相似的宗教信仰及风土习俗等诸多原因,我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民族大都具有朴实、热情的民族性格,恪守信义的优良传统,这就为我国西南跨界民族加快发展民族生产力,促进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积极参与国际间的贸易往来、经济合作、劳务输出等,提供了地利人和的优势。当前东南亚内陆5国,除泰国外,对外开放均处于起步阶段,但各国对外开放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可以视为“天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条件。但要做的具体工作仍然十分繁重、艰巨。主要矛盾是:(1)一部分跨界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当恶劣,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如广西壮、苗、瑶等民族所处的大石山区,尚有大片荒山秃岭,人、畜饮水都成问题,农业生产的条件相当恶劣[11]。(2)边境民族地区缺乏建设资金、技术和人才,亟需通过多渠道、多途径引进。(3)一些落后的传统习俗至今仍严重地制约着跨界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而在当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又从多方面影响、阻碍了民族的发展。这些,需要我们密切注意如下问题:(1)加强跨界民族地区农、林、牧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和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如:借鉴云南剑川、广西田林等县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的先进经验[12],强化民族生态意识,尽快逐渐增加生态保护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推广云南文山州领导互签责任状,10年绿化文山大地的先进经验[13],使边疆民族地区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为跨界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与东南亚区各国的友好往来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2)根据跨界民族自然地理、民族传统特点,选择、实施确有实效的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这方面,云南元江、景东等县和广西都安、巴马、大化等县的哈尼、傣、彝、瑶族群众已经闯出了可资借鉴的路子[14],各跨界民族之间应当提倡相互学习,大胆试验。(3)要注意发挥边疆民族地区现有的农场、工矿企业的作用,发挥其向周边民族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学习已有的成功经验[15],继续调查、挖掘现有的生产潜力,既要提倡扶贫济困、民族团结的精神,也要遵循工农互助、互利、互惠的原则。同时,要注意学习、借鉴泰、韩等国保护民族工业的作法,使跨界民族地区新兴的工、矿企业加快发展[16]。(4)利用跨界民族在东
南亚各国广泛的姻亲关系和文化联系,发挥东南亚各国华人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和对中华文化认同、民族感情深厚的优势[17],不断拓宽经济、文化信息渠道,引进资金、物资、技术、人才,并有选择、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以“利国、富民、睦邻、安邦”。
第三,要花大力气狠抓跨界民族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培养、吸引、稳定和建设各民族人才队伍上拓宽渠道,多出新招。西南各跨界民族文化教育落后、劳动者素质低下的状况令人忧虑。这些年来,滇、桂两省区的民族教育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已对之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18]有识之士认为,要“改变对民族教育一刀切做法,对特殊民族采取特殊政策。从多元文化视野对待‘双语教学’……扶持民族语文教学。从大文化角度,……建构宗教与教育的调适机制。”[19]同时,在跨界民族地区,目前应重点狠抓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借鉴云南双江、金平、景谷、勐海等县一些地区、学校的成功经验,[20]使跨界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与成人科技文化知识普及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根据民族和地区的特点逐步普及、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迅速、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长期以来就是困扰我国西南跨界民族治穷治愚,发展生产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医科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云南分所等几个科研单位派人长期深入基诺族村寨,手把手地向基诺族同胞传授实用植物栽培技术的成功经验,是值得跨界民族地区借鉴的;[21]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石通扬、王天津同志关于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立足当地资源优势,确定春烤烟、甘蔗、木薯的基地建设和葡萄酒厂调味酒生产线技术改造的科技扶贫的建设,也可供跨界民族地区参考。[22]发展跨界民族文教、科技事业,需要:①增加经费投入,以多渠道集资的办法使科技教育资金较快地落实到位。②针对西南各跨界民族地区一方面科技人才奇缺,另一方面某些科技人才又相对集中的特点,制定特殊的政策,以较为优厚的待遇和入情入理的宣传,吸引和鼓励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生活条件较差,而目前又最需要科学技术的地区,传授以“短、平、快”的实用技术为主的农、林、牧、渔业等各类科技成果,使之较快地产生示范效应,迅速转化为生产力。③对不同年龄层次的科技人员和各民族群众,要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促进双方的文化适应过程,即:相互之间对民族语言的学习、运用,对民族风俗的了解、尊重,对地理环境的适应、熟悉,对专业技术的传授、掌握,等等。
第四,需要充分利用西南跨界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民族优势,加快西南边境贸易口岸的建设,推动边贸事业的发展。早在秦汉之际,西南边疆从川滇就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和南亚、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迄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古西南丝路是滇、黔、川三省物资出境的主要通道之一,其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十分显著;而西南跨界民族所处的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则是重振西南丝绸之路,扩大向东南亚和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我国西南跨界民族许多群众懂得邻国同一民族或异民族的语言,熟悉邻国各民族的社会文化、风习,是发展古已有之的边境贸易的民族优势。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发展边境贸易,开展双边、多边和转口贸易,发展边贸的前景十分广阔。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南边贸口岸的建设已有一些基础,国家已在滇、桂边境设置一类口岸8个、二类口岸19个,还有数十个边境互市点和上百条水、陆对外通道[23]。边贸发展的形势十分喜人。跨界民族地区要进一步利用本地特殊的地理、民族环境,更多地选择和建设合理的边贸口岸,“建立对南亚和印支大陆的‘边境贸易开发区’。建设内地通向边境口岸的快速交通干道,重开南方丝绸之路,扩大对东盟6国和印度、孟拉加等国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24]。要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地区靠贸易起家的经验,总结跨界民族地区发展边贸已有的成功经验[25],继续抓紧边贸口岸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内引外联。西南各跨界民族的群众,还应当学习素以经商著称的回、维吾尔等民族同胞勇闯天下的气魄和才干,不但在东南亚各国发展,而且迈开步子走向世界。边贸和国际贸易活动,对培育和增强西南各跨界民族群众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质量意识、公关意识等,有着重要作用;对开阔他们的视野,促使其接受进步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五,要充分开发和利用西南跨界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以民族旅游业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我国西南跨界民族地区,风景名胜、人文古迹多姿多彩,大力发展以民间艺术节、民族土、特产品购物和民族风情旅游等为特点的民族旅游事业,具有巨大的潜力。这些年,西南民族地区对此已做了大量工作,举办了广西北海首届国际珍珠节、南宁第四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昆明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等重要的民族民间文体、商贸活动,已经修建云南民族村、广西北海银滩南珠娱乐旅游中心(由海外商人组成的海泰集团投资)等旅游、娱乐设施,成功地举办了昆明国际园艺博览会;中、缅、老3国的边境旅游已经开展,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就批复同意广西与越南开展凭祥至谅山一日游、东兴至芒街一日游、防城至鸿基三日游、南宁至可内四日游等边境旅游业务;同意广西组织海外游客经我国往返越南的跨国旅游业务[27]。在目前各项建设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要借旅游业发展的好势头,学习上海、海南、浙江、山东等省、市的先进经验,对跨界民族旅游事业的发展实行倾斜政策,增加投入[28];要利用边疆民族地区风景绮丽优美、民俗多彩多姿的天然优势,在已经开辟“西南少数民族风情游”的专项旅游路线的基础之上,以桂林、昆明、大理、丽江、德宏、西双版纳等旅游开发区为重点[29],继续拓宽民族、民俗旅游的路子,加强滇、西桂两省区和西南各省区的旅游业联合,学习、借鉴新加坡、泰国等国发展旅游业的先进经验[30],以更快的步伐开拓东南亚旅游市场,建立西南、华南和东南亚环形旅游圈,以适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产业的旅游业的发展[31]。
第六,要切实抓紧跨界民族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的问题,逐步使跨界民族两种生产的发展结构合理,步伐协调。根据申旭、刘稚同志提供的资料的计算,早在1982年,我国西南跨界民族人口的总数就已达2728万余人[32]。10多年来,各民族人口逐步递增,到90年代初,西南跨界民族人口总数已达3790余万人[33],几乎增长了1.39倍,其速度确实惊人。近些年,增长仍在持续,令人注目。显然,这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环境、空间范围、自然条件是极不相称的。跨界民族要发展,改革开放要扩大,人口问题是需要稳妥地解决的大事。要总结近10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学习和借鉴先进民族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措施[34],继续深入地调查研究西南各跨界民族传统的生育文化心理及其发展、演变的现状,研讨、实施行之有效的民族计划生育政策。本文认为,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跨界民族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尤其应当强调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改变落后的民族生育习俗,以兄弟民族计生工作的先进经验,启发、引导跨界民族群众尽快改变早婚、早育、近亲婚配的落后民族习俗和“传宗接代”、“儿女双全”等旧的生育观念,逐步树立民族繁荣、兴旺的标志不是人口数量连年递增,而是人口素质逐步提高,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进步的意识。同时,要加强民族法制的建设,切实贯彻、执行《婚姻法》及边疆民族地区制定的《变通条例》等类法规。当然,关键之一还是要根据跨界民族地区实行责任制以来生产关系发展的现状,加强调查研究,针对民族、地区特点,搞好社会福利、保健工作,以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唯如此,跨界民族人口的控制才可能收到实效,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才有可能。
第七,要抓好培养民族干部这一关键,切实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开拓。跨界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既是跨界民族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关键。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抓紧跨界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在各民族干部队伍的扩大,素质的提高,结构的改善上,要实行特殊的倾斜政策,优先选拔、培训,及时地为其必要的见习、考察创造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和办法,不断拓宽选拔跨界民族干部来源的渠道。此外,要在进一步拓宽和用活政策上下功夫。目前,国务院和西南各省、区及跨界民族各州、县制定的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政策和条例虽然还有待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再补充、完善,但现有的法规和政策已相当优厚,如何在进一步用好、用足、用活现有的法规、政策上,各跨界民族地区大有可以挖掘的潜力。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善于把已有的政策捆起来用。尤其应当着重强调的是,西南大多数跨界民族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目前仍然很低,在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上,不妨将政策再放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