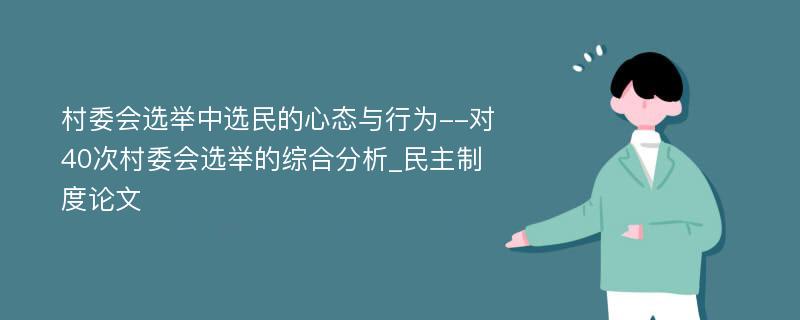
选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心态与行为——对40个村委会选举情况的综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委会论文,选民论文,综合分析论文,心态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举,按其本来面目是民主精神的展现,其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即为选民。自然,没有选民 的参与,选举只能流产;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选民的参与,选举就会是真正民主的选举。 因此,要了解选举的本来面目,还应当深入理解选民的参与行为。本文以1999年在江西省观 察 的40个村作为基本材料,分析选举过程中选民的行为特征。1999年的直选是江西省首次实施 海选,也是该省选民所遭遇的第一次“直选”。对这“突如其来”而又姗姗来迟的民主选举 ,会在选民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在选举中,选民自身的角色是如何扮演的?他们对选举产生 了什么样的影响?显然,这些问题很值得认真研究并回答。一、选民对选举的心态变化
我们知道,在已往村干部从直接任命过渡到“选举”后,也大多是搞“指选”、“派选” ,用农民的话来说,那只是走走过场而已。这种长期的选举实践在选民中所形成的经验,会 怎样影响到他们对1999年选举的看法?在40个样本村,当我们观察员询问选民对即将到来的 选举的看法时,得到了近乎一致性的回答:那还不是“老一套”,“唬弄老百姓而已”,“ 那是乡里玩的新把戏”。当我们进一步解释将可能是更民主的选举时,还是有相当部分选民 表示怀疑。在T县20个样本村,我们在选举前曾对400个选民作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尽 管多数选民(78.8%)希望实行真正民主的选举(注:实际上在1998年前,曾有多位学人就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意愿作过调查,均表明:大多 数农民希望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但相信将会真正搞民主选举的选民只有31.8%(详见表1、表2)。可见,在选举前,尽管多数选民有对民主选举的强烈诉求,但同时又不 相信上面会“给”他们民主。长期形式化选举对他们的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在各村, 自 选举启动至候选人提名结束,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观”:选民们对选举普遍持较为冷淡 的态度。
表1 今年(1999)村委会将举行选举,你希望那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吗? N=400(选民)
很希望是
不希望是 都是上面定的,希望也没用
无所谓
说不清
未答
78.8%
0.3%4.8%0.8% 5.0%10.5%
表2 今年(1999)村委会将举行选举,你认为那会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吗? N=400(选民)
很可能会 很难会是不可能会 说不清
未答
31.8% 28.8%
6.5%18.0%
15.0%
表1与表2的资料来源:1999年选举前夕对T县400个选民的抽样调查。
然而,在“海选”提名结束后,在40个村中选民的态度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性变化。一种 情况是在提名作假的少数村,选民的态度依然如故:看到“选举真的是这么假”,更加深了 他 们的怀疑与冷漠心态。另一种情况出现在那些提名工作做得较为规范的多数村。在那里,由 于对提名票做到了公开唱票、计票,当选民们看到自己以“试一试”等心理而填写的候选人 也在公布的名单上,并基本上按照得票数来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多数选民立刻意识到这次 选举果然与以前不一样,其热情便被激发起来。选民这种由冷而热的态度变化,在仲村、洲 村等多数村皆有表现。然而,部分由于选民在提名中的“马虎”、随意,使得自己拥护的人 没有足够的票数而未能成为正式候选人,而自己所不拥护的人却依然成为正式候选人。由此 ,在不少村出现了令选民并不满意的结果:一些民望本不高的原村干部继续当选(注:这种干部之所以能继续当选,显然有选举不规范操作方面的原因,但选民自己总结的—
—他们在提名中的“马虎”与随意——也是其重要原因。)。在这些
村观察中,我们听到选民之间议论较多的便是:原来不知道今年(选举)会来真的,要不提名 时 就不会这么马虎,这次是没有办法了,“下次来过”!
在观察村中,选民从怀疑到冷漠,与从怀疑到相信再到表示“下次来过”这两种心态变化 的路径,显然缘于各村选举实践差异的影响。在这里,选民心态的变化似乎反映了他们在选 举中的被动角色。不过,当选民们以各种实际行动介入选举后,其能动的角色就有了充分的 体现。
二、选民的投票取向及其理性程度
投票是选民参与选举的主要活动与参与方式。从各地政府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总结来看, 选民对选举的参与和投票率都是较高的。C、T两县民政局在对1999年村选举的工作总结中, 也 表示它们的投票率分别为94.9%、92.0%。不过,从我们的实地观察看,要较为准确地计算40 个样本村的投票率,实际上很困难,因为多数村有相当部分既未办理手续、也未作登记的“ 委托投票”。更遭的是,有的村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票。另一方面,却对那些亲自来投 票的选民也未作登记。鉴此,我们便未轻信村里上报的投票率。这里,也不对此作专门分析 ,有关弃权的现象我们将在后文做些讨论,这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选民投票的取向问题。
选民投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取向多种多样。我们以为,选民的投票取向大致可分 为四种:“能人取向”、“好人取向”、“政治取向”和“关系取向”(肖唐镖,2001)。所 谓“能人取向”,即选人要突出其能力、本领、魄力这类智力因素,如有治村才能、能带领 大家致富等。所谓“好人取向”,则侧重人选的品格、道德等非智力因素,如办事公正 ,不贪不沾,会为村民说话等等。“关系取向”表明,选民主要从与本人关系之深浅、好坏 的角度来选择村干部,比如地缘关系、宗族血缘关系、非宗族的亲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等。 “政 治取向”即以政治标准(如是党员等)来选择村干部。从笔者在1997和1999年两次组织的问卷 调查看(见表3),“好人取向”者居多,“能人取向”者次之,而“关系取向”和“政治取 向”者最少。这表明:选民的选择取向已趋于理性化,更重视候选人的德行和才干(肖唐镖 ,1999)。(注: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1994:91)与郎友兴(2000)的调查结论也同此。)
表3在投票选举村干部时,你对候选人条件的要求怎样?单位:%
重视哪些 最重视哪一个 最重视哪一个
条件?(1999)
条件?(1999)
条件?(1997)
1、要是党员 25.8
0.5 空项
2、能带领大家致富
77.4
24.137.6
3、要是自己家族的人或亲戚
10.0
0.1 3.3
4、敢代表村民说话
71.0
3.4 8.9
5、敢抵制上面下来的土政策
56.6
1.6 空项
6、要人品好,不贪污 79.3
12.17.0
7、要办事公道
79.5
34.639.3
8、同自己要好
13.5
0
空项
9、无所谓,谁当都一样
34.3
3.8 空项
10、其它 0 13.92.5
11、未答 0 5.9 —
样本数 800800 2085
注:“好人取向”包括:敢代表村民说话;敢抵制上面下来的土政策;人品好,不贪污; 办事公道。“能人取向”指:能带领大家致富。“关系取向”包括:要是自己家族的人或亲 戚;同自己要好。“政治取向”指:要是党员。(肖唐镖,2001)
按一般看法,包含在关系取向中的“宗族取向”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但从笔者对选 民“宗族取向”本身所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肖唐镖,2001):他们之所以有宗族取向,并不 是因为受到了来自宗族的压力,而主要是出自选民个人的自发性选择。在这种选择行为中, 虽有选民系出于对情面、情感的考虑,但多数选民却是出于选“好人”与“能人”的目的。 为什么会投本族、本房人的票?不少选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有本事,人很好”、“他还 没 有变坏”;或是因为希望有好的村干部来帮助自己、治理本村。即使是在具有宗族取向的选 民中,理性选择者也已居多数。可见,多数选民的选择行为是理性的。
三、选民在选举中的参与行为
选民在选举中的参与行为,除了投票外,还有在会议上发表意见、接触、信访以及写大字 报、贿赂与破坏选举等过激和非法行为(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1994:92-93)。从我们 的选举观察看,按参与行为的不同,可将选民分为三种类型,即积极参与型、消极逃避型、 随大流型。这几种参与行为在不同类型的选民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如,作为执政型精英的现 任村干部,他们中的多数还是选举的组织者或工作人员。作为选民,他们大都积极参与选举 。在野型精英选民有两种,一种是被提名参与竞选村干部的在野精英,他们会积极地投入选 举竞选;另一种是没有被提名的在野精英,有的也会积极参与,有的则由于对谁当村干部不 感 兴趣等原因,埋头经营自己的家庭经济,如外出打工、做生意,而对选举事务不感兴趣。其 它普通村民选民是各村选民的主流,占各村选民的大多数,他们在选举中的行为特征最为复 杂,既有积极的参选者,也有消极的弃权者,还有随大流的跟从者。
这里,我们对三种参与类型的选民略作分析。在多数村选举中,我们都能看到“消极逃避 型”与“随大流型”选民。他们在选举中典型的行为特征有:1)逃避选举,不参加投票,即 “弃权”;2)投票选人“随大流”,“人家去我也去”,并跟从别人的选择来选择,“你们 选谁我也选谁”;3)面对在场的村干部等人,出于“自保”等心理,而不愿自主选择,或者 直 接让干部来填写选票,或者违心地填写在场干部的名字,甚至还故意出示给他们看;4)面对 选举操作中的作弊现象,选择的是沉默或仅在私下发牢骚。应当说,这些行为,或者是对 选举的“不参与”,或者是“缺乏质量”的参与。按小V.O.基等西方学者的研究,缺乏参与 和代表,反映了“有效公民权”的缺乏以及“对整个制度的忠诚”的缺乏。而弗郎西斯·威 尔逊、赫伯特·廷斯腾等学者则认为并不如此,他们相信,那是“选民对事情进展方式基本 满意的证据。”(注:转自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1-192页。)那么,在中国农村情况又是如何呢?从我们的观察访谈看,中国农村选民 对选举的不参与或“缺乏质量”的参与,主要不是出于“满意”的考虑,而更多是由于:第 一,对人性与体制的怀疑。有的选民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再怎么选村干部也没有用,“上面 不选,光下面选那有什么用?!”在数个村皆有选民说:“条条蛇都会咬人”。实际上,这是 对人性与现行体制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在这种制度体制下,对谁都不能相信,无论选了谁 都一样,都会变坏。第二,不相信有真选举。有的选民认为选举“总是一场假”,自己的参 与并无意义,因为“选不选一个样,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特别是在那些选举完全被暗箱 操纵的村,选民更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表现出强烈的冷淡和反感。第三,选举无用论。在永 昌、花村等村,有选民就公开议论:村主任又不是“老大”,选了他又对村里事务作不 了主,他也做不了什么事,这样不选“一把手”(村支书)又有什么用?!
以上分析表明,即使是在“消极逃避型”与“随大流型”选民中,并不都是“素质低下” 者 。实际上,在他们的应付、顺从乃至逃避中,我们不难看到农民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技巧。这 与项继权先生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对湖北月村的调查表明,“村民的这种‘反常的’ 和‘不合理’行为,显然并不意味村民不需要选举和民主,而是要求更加普遍的民主选举” (项继权,2001)。正如James Scott所称,农民的不合作与抗拒行为不过是“弱者的权力” ,是一些社会弱者不得不采取的、成本最低的、也是最常用的手段(转自项继权,2001)。当 然,他们的如此行为对于选举质量的提升却助益不大。
令人高兴的是,在多数村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参与者”。除了积极参与投票外,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采取了其它参与行为。在一些村中,面对基层干部在选举中有意或无意的 失误、疏忽或舞弊行为,就有选民公开地站出来,或者公开批评,或者公开争取选举权,或 者自发地对选举过程进行全程监督,或者直接到上级政府上访,更有甚者公开抵制选举。39 个村中有22个(占56.4%)发生了这种选民公开地争取并捍卫自身权利的行为,各种行为的具 体 分布情况详见表4。如在铁村、罗家、曹坊等村,一些未得到选票的选民敢于直接质问上级 :为什么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铁村选民谭可秀和张氏兄弟,罗家村近百名来到选举大会会 场的选民,皆因没有得到选票而找到干部进行理论:“我一家在正式选举时没有得到一张选 票,你们以后也不要来向我要一粒附加粮。”“我们又没有犯法,不知你们是根据什么规定 剥夺我们的选举权。既然我们没有选举权,年底的附加粮你们一粒也甭想拿走。”此时,他 们已将权利与义务对等起来,在没有得到民主权利时,很自然地认为也可以不履行相应的义 务。而在花村、石桥、吴坊等村,面对干部非法操作选举,一些选民敢于公开抵制,甚者将 票箱踩烂。
表4在本村选举中,是否有选民采取了以下公开行动?
N=39(村数)
争取选
向干部提出 自发监 对选举工作 抵制
举权投票的条件 督选举 提出批评
选举
有 17.9% 5.1% 20.5% 46.2%23.1%
没有82.1% 94.9 79.5% 53.8%76.9%
资料来源:肖唐镖,2001
有学者通过追踪村民自治的曲折历程,提出:普通村民的行动是“地方阻力”未能阻止村 民选举进程的主要原因,乡村的合法抵制者让各级政府部门感到了他们的存在(欧博文与李 连江,2001:11-13)。从我们的观察研究看,积极参与者的行为确实是多数村选举能够成功 举行的重要保证。即使是在那些选举操作不规范甚至严重违法的村,积极参与者争取并维护 自身权利的各种行为,对那些习惯将村民看作“顺民”的选举操作者也是十分强烈的震撼。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等因素的影响,选民的维权行为基本上是自发的 个人行为,尚不足以成为强大乡村组织的有力的“谈判对手”,因此,还未能成为推动选举 依法运作的基本力量,像石桥村那样能让选举重来的案例仅此一例。
四、选民在选举中的竞争理念
选举是一个能够透视选民行为理念与行动逻辑的焦点性事件。为此,在观察中,我们还十 分注意了解选民对竞选者的态度,如对当选者、落选者各持何种看法,以观测他们的竞争观 念及其与民主价值的兼容程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选民对当选者的看法。这里以当选者是否为选民所拥护为尺度,将出现 两类情况:一类如当选者正是自己所拥护的人选时,选民一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但是我 们还注意到两个有趣的案例:一个发生在雁门村,当作为村主任候选人之一的张建海来到山 上,制止一些选民乱砍滥伐时,选民当即回应他:“你还没有当主任就这样,如当了主任那 还 了得!”为此而纷纷倒戈,使本有胜算把握的张建海在随后的选举中落败。另一个发生在罗 家村,当选的村干部罗新高本以为“现在我被大家选上,说明大家信任我,以后说话办事也 能硬气些”,但未料到的是,选举后罗新高来到自家叔叔家收取税费时,竟然遭到其叔的斥 骂:“你算什么,还帮他们来收我什么粮……!”这两个性质相近的案例表明:一些选民 对自己的拥护者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即我选你当干部就得为我谋利益,“天下即是我们的了 ” ,即使是为此违反法律、损害公共利益(如乱砍滥伐、不交税费)也在所不惜。在此,公共意 识的贫乏暴露无遗。
另一类是如当选者不是自己所拥护的人选时,尽管多数选民还是会服从,但也有不少的选 民不习惯于服从。有的选民对当选者说:“你又不是我选的,我不听你的。”有的甚至公开 反 对,在洲村,曾军民看到“讨厌”的胡小元当选村主任后,就在现场与胡吵架,还差点打了 起来,此后又组织本村庄的选民在马铃薯基地闹事,甚至鼓动大家另立村委会。在仲村,长 发与新社在发明当选村主任后,便以他在竞选中有贿选行为到乡里上访,并一直拒绝向发明 等人交纳税费。很显然,多数表决规则在这里尚未得到恰当的理解,一些选民还以公平竞争 观 念至上,并以此取代法律规则。
再看对落选者的态度。这也有两种情况:如是自己所拥护的人落选,选民也会一同难受, 对 落选者一般不会有其它的行为。但如果落选者正是自己“讨厌”的对象,那么,就有选 民不仅不能抱以同情,有时还会施以挖苦讽刺、幸灾乐祸。如曹村选民吴保乐看到两名他不 支持的竞选者落选,即幸灾乐祸地冲着一村民大喊:“晚上到我家喝酒去”。这种情况与竞 选者在失败后普遍出现的“跌面子”与失落感是一致的。在选举后,尤其是一些原村干部落 选后,羞于见人,有的甚至躲在家里不出门,如坎下、尺江两村的原村主任落选后就是如此 。在这里,就像一些选民不能理解“服从规则”一样,“体面地下台”、对失败者予以鼓励 、宽容的精神也同样缺乏。
五、结论
没有人会怀疑,民主制度需要有健全的社会基础,而不仅仅需要完备的制度设计。民主选 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游戏,实施这种新的游戏,不仅要有新的规则与程序,还需要有与之相 应的公民文化,包括必要的教育水平、健全的人格及政治文化心理等素质。曾几何时,一些 人总认为中国农民的素质太低,“不适应搞民主”。但也有学者认为:不管农民如何贫困、 缺少教育,他们都知道自身的利益,都要求把握自身的未来;他们也是可以教育的,能够学 习和掌握选举的程序,能够依照法律程序来投票,而非相反(Pastor、谭青山,2001:13)。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村委会选举中,选民们的选择行为实际上已趋于理性化,有越来越多的 选民能积极参与,并敢于公开地争取并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即使是那些对选举活动弃权或 冷漠的选民,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观念与素质所限,倒不如说是由于对选举的失望所致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其实,导致农民对村委会换届选举持有消极心理,主要原因是由于 选举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在选举之后新的村委会工作的问题”(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199 4:93)。因此,提升选举的质量,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选民的素质,而在于到底能“给予” 农民多大程度的民主。
当然,选举及基层民主的改善并不仅仅取决于“给予”,还应当来自选民自身的行动。在 本次观察的样本村选举中,我们已看到了选民的这种值得鼓励的积极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为 选举操作者提供了反思与提高的机会,而且也对选举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但 我们也看到,目前选民的积极行为尚是自发的个人行为,既缺乏自我组织化的准备,也缺乏 可供选民借以自保的制度性保障,因此,除了石桥这样个别的村外,选民的积极行为乃至依 法抗争行为还不足以改变选举的大局,并推动选举的依法运作。然而,只要借以时日,这样 的局面是会到来的。“下次来过!”这句发自选民内心的誓言,已为选举的发展前景做出了 最好的注解。
绝大多数人也相信,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政治斗争一直是以“全赢全输”为支配模式(邹谠 ,1994:243),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是“胜王败寇”的连续剧。很明显,这种“全赢全输”式 的 政治斗争观念是与现代民主政治不相容的。(注: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吴晗与袁方先生的研究就得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这种特征。袁方
先生甚至认为:“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观念里要树立起近代式的民主是非常困难的。”
(详见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76页))从本文研究看,这种传统的政治斗争观念至今 还深深地印刻在一些选民的脑海之中。比如,他们在“自家天下”意识的支配下,缺乏应 有的公共意识与法治意识,并对建立政治信任机制的多数规则不予认同,以致对当选者不予 服从、对落选者不予宽容。这些“传统”,将是对选举发展与基层民主建设的严重制约。
欧博文在一篇新近的论文中,列举了多起村民运用“权利语言”质疑地方政府与官员在选 举中的不法行为、反对非法或不民主的选举的案例,并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村民的要求 是进入地方政治,很少要求更广泛的结社、表达以及未经许可的参与和政治权利;也很少怀 疑现存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更不用说怀疑高层不负责任领导颁布法律和政策权利。因此, “在这一点上,中国村民最好被看作是处于臣民和公民之间的位置上”(欧博文,2001:13- 15)。从本文研究看,他的这种总体判断是有道理的。但还应当注意的是,村民本身是一个 分层的多元群体,他们的政治文化也是多元的、分化的。在选举实践中,不仅能看到公民文 化、顺民文化与臣民文化的外在化行为,而且还能看到“暴民文化”在一些选民身上的留存 ,它突出地表现在对当选者或落选者的非理性行为上。这也表明: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的发 展尚须长期的努力。但随着乡村民主、乡村政治发展的持续实践,
农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并非不可能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