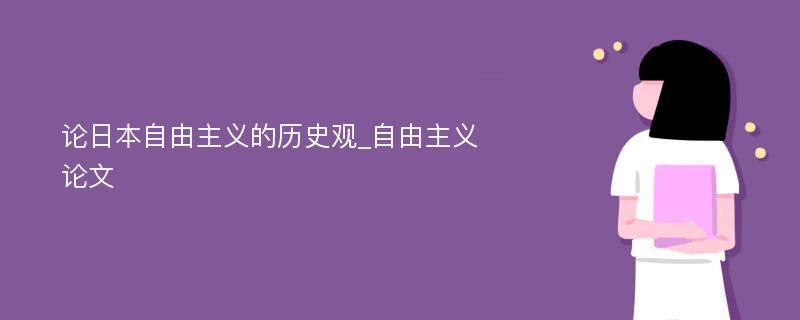
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经对我们的世界给予重大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而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中,我们的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冷战局面结束的今天,人们关注的热点是多极化世界中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如何面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新问题。虽然人类社会并不会忘记过去的战争苦难,并不会忘记发动战争的责任,但是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那次战争中的战胜国以及战败国)的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战争的教训已经进行了总结,战争的责任和是非曲直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日本社会突然又出现了一股有悖于当代潮流的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特别的思潮,即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
一 自由主义史观的产生和发展
自由主义史观的创始人是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的教授藤冈信胜。他从1994年4月起在面向日本初、高中和小学老师而且影响力相当大的杂志——《社会科教育》上连续发表批评日本近现代史教育的文章,指责日本的近现代史教育是失败的,培养出来的日本人“缺乏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视野狭窄,自我封闭”。他认为这是战后占领军对日本实施的“使日本人始终怀有罪恶感的作战计划”的结果,是“抹杀日本人的国家意识的洗脑计划”执行后的结果。他认为战后日本的近现代历史是综合了三个“敌意”而写的历史,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日本的敌意,即“共产国际史观”,这种历史观把明治维新看作是半封建性的被扭曲了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基础上造成了天皇的专制统治,而这一天皇制必须粉碎;第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敌意,认为战争是日本为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而发动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正义一方必须予以惩治,这就是“东京审判史观”;第三种敌意来自中国和朝鲜,即要求日本进行反省的“谢罪外交史观”。他强调说:综合了三种敌意的历史观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近现代史都描写成漆黑一团”,“给历史教育以极大影响”。他呼吁把日本明治以来的历史作为光辉的历史进行宣扬,从日俄战争开始,就要把战争描写为日本的自卫战争。基于这一认识,他强调必须对日本近现代史的教育进行改革,必须成立改革历史教育的研究者的团体。为了表明这一团体的学术观点上的创新和独立,他将这一团体称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自称是源于战争中和战后以石桥湛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是那一自由主义在历史认识上的发展,即“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完全从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改革历史教育,以达到多样化的目的”。与建立研究会的同时,他创办了名为《近现代史的教育改革》的刊物。
“自由主义史观”的产生和该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50年之际掀起的否认侵略战争责任和攻击历史教科书的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后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逆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掀起阴风浊浪,最近的恶浪发生于战后50周年来临之前的1993年。当时,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就以前的战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在他之后上任的村山富市首相也提出了“对过去进行反省”的路线,准备在1995年通过反省战争,维护和平的“不战决议”。应当说,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有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的言论和举措,但是来自右翼势力的强烈的反对和抵抗则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动荡。
就在细川发表上述言论后不久的1993年8月,日本自民党内的部分国会议员就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反对细川首相对于战争的认识,表示要建立“正确”的关于战争的历史史观。他们认为日本当代的历史教科书是导致错误的战争史观的根源,所以呼吁为改正历史教科书的记述进行“新的战斗”。历史研究委员会事务局长、参议员板垣正(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次子)曾说:“即将迎来终战50周年,围绕着一起战争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问题重新突出出来……这使人们再一次深刻地感到,不仅政治家,而且日本人本身的历史认识正处于严重的危险状况。同时,人们也看到了战后占领政策的影响力和以倾向左翼为基础的教育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但是,无论从那个角度出发,我们都必须指出:这种教育是错误的,因为它不能给下一代青年和儿童带来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和生为日本人的喜悦。更何况它是片面地断定日本有罪,并把自虐式的历史认识强加于人。”可见,日本的右翼政治家也把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委员会明确提出:因为自民党冲在第一线容易引起误解,所以要让学者出面,而给予资金和其他方面的资助。在这样策略下,由“历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19人就历史诸问题进行了讲演,并将讲演稿汇总出版了反映日本右翼关于战争历史问题总认识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藤冈信胜声称“自由主义史观”不站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立场上,然而,在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批评上,“自由主义史观”同日本的右翼政治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藤冈信胜在《社会科教育》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呼吁改造近现代历史的教育,也是同日本右翼政治家的活动相呼应的。1995年7月,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由藤冈信胜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决定创立名为《近现代历史的教育改革》的杂志。“自由主义史观”的活动在1996年达到高潮。
1996年6月28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对历史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同意从第二年起使用7个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在那些教科书中,不同程度地记载了“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罪行。自民党中的右派议员立即进行批判,并且成立了“关于教科书问题研究委员会”。《产经新闻》公然刊登了对原法务大臣奥野诚亮的专访,宣称“从军慰安妇”是商业行为,不存在强制问题。同时,该系统的《星期一评论》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员上杉千年致日本文部省大臣的公开信,要求从中学的教科书中删除关于“从军慰安妇”的记载。接着,《产经新闻》又连续发表文章,对南京大屠杀问题进行发难,称大屠杀是虚构的,接着攻击刊登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历史教科书“简直是站在别国的利益上讲话”,“缺少实证和研究的态度与平衡感”,是有害的“反日教科书”。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在这次攻击教科书的浪潮中是主要的力量,藤冈在读了教科书后发表意见说,全部7册教科书的文字给人以一种十分暗淡的情绪影响,我认为必须让有识之士迅速了解这一情况。于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联络日本知识界中政治态度右倾的作家、医生、演员、学者以及一些企业家,在1997年1月组织了“编写新教科书会”,把对教科书的攻击推向高潮。这个组织把承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历史教科书称为“战后历史教育的大罪”,称这样的教科书“贯穿了彻底的反日史观,彻底地否定了日本”。在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编写新教科书会”的鼓动和影响下,日本国内有4个县的议会和24个市町村的议会通过了将有关侵略事实的记述从教科书中删除的决议,用藤冈的话来说就是“掀起了巨大的反对教科书的‘龙卷风’”。
尽管“自由主义史观”一再标榜自己并不是鼓吹战争的军国主义,不是炫耀日本优越的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对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发难的基本阵地则是在日本以政治态度右倾著称“产经”系统的《产经新闻》、《正论》,还有《诸君》、《周间新潮》、《文艺春秋》、《新潮45》、《VOICE》、《SAPIO》等舆论工具,而“产经”系统的报刊是最主要的。这些报刊把藤冈等自由主义史观论者捧为“时代的宠儿”,为他们提供阵地。《产经新闻》从1996年起开辟了名为“教科书不教历史”的专栏,用一年的时间连续刊载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员撰写的攻击现行教科书的文章。
二 自由主义史观与反历史的“大东亚战争史观”
自由主义史观是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历史观的一种表现。
战后日本社会关于从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战败为止的历史认识有许多表现形式,但是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将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简单地归纳为两类,即所谓“只说日本罪恶的历史观”和“不说日本坏的历史观”。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将他们所说的“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和“谢罪外交史观”称为前者的代表,而将“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列举为后者的代表。他们认为这两类史观都是片面的,而主张应当“从日本当时的政策能不能避免那一场战争的角度出发,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暂且不分析这种分类方法是否科学,仅从表面上看,自由主义史观宣称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他们把明确支持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只说日本罪恶的历史观”指责为“自虐史观”、“黑暗史观”、“反日史观”,并且进行猛烈的攻击,而对于“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却从未提出过批评,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大东亚战争史观”是指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指导者们所宣扬的战争观,那一战争观的基本点是:从20世纪起,日本就为了保护自己的条约所给予的权利而被迫进行“自卫”的战争;日俄战争是针对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的反应;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是阻止苏联的“共产主义在东亚的传播”;从袭击珍珠港开始的太平洋战争则是针对欧美殖民侵略的代表亚洲人民利益的“自卫”。总之,那些战争都是为了日本的生存而进行的,目的是在亚洲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取代欧美的殖民地统治。这种战争观无论使用多么华丽的词藻包装,都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把日本推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的主张,是日本右翼宣扬“国粹主义”的“皇国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在战后初期随着对东条英机等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大东亚战争史观”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严厉的批判,日本的学术界一般不再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名称概括那一阶段的历史。
但是,右翼势力同与侵略战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人是不可能认帐的,他们坚持“大东亚战争史观”,通过各种方式为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战后不久,这种翻案活动就开始了。1953年,即战争结束刚刚8年,当时担任吉田茂内阁文部省大臣的冈野清豪在国会回答质询时就说:“我不准备评价大东亚战争的善恶,但是日本以世界各国为对手打了四年仗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日本人的优秀。”6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否认战争责任的舆论更加强烈。对日本战时外交起过重要作用的神川彦松在《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中公开说:“只强调战争责任,会把日本人都培养成只有劣等感的民族,因此必须修改对战争的评价。”1964年,日本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的一次浪潮,重新提出把“大东亚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那些人不仅原封不动地使用“大东亚战争”的概念,而且坚决不承认“战败”,使用“终战”一词表示战争的结束。近年,自民党右翼系统的各种组织,如“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历史研究委员会”等都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支持者,而《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则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新的形势下的翻版。
正因为“大东亚战争史观”是“皇国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日本社会有很恶劣的名声,所以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一再强调同“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差别。然而将其主张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
第一,“自由主义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都是站在当年的战争指导者的立场上,鼓吹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观。《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的主要撰稿人中村粲说:“日俄战争既是一场拯救亚洲的战争,同时也是日本的自卫战争。如果对俄罗斯听之任之,下一个受害的就该轮到日本了。所以这完全是日本的自卫战争。”而藤冈则认为战争是:“为防止日本沦为殖民地的伟大的保卫祖国之战,鼓舞了新兴的明治国家的精英及民众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把他们的智力与精力奉献给了战争。”
第二,自由主义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对战后历史教育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以相当大的力量攻击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称“历史教科书关于近现代史部分的记述变得越来越糟”,“处于令人非常忧虑的状态之中”;说历史教育被日本的教育工会所统治,宣传的是“东京审判史观”;称要从根本上改变“东京审判史观”的影响,必须从改变历史教科书开始。
第三,“自由主义史观”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都是要从否认具体的犯罪事实出发达到从根本上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目的。近年,他们共同否认的战争犯罪有“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的问题、“南京大屠杀”中的被害人数问题、是否存在“三光”政策的问题等等。例如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奥野诚亮认为那是在“女性自由意志下的商业行为”,慰安妇就是允许公娼存在的时代的妓女;藤冈也认为“在军队里设慰安所同在文部省里设食堂是一样的,都是民营的机构,没有问题”。板垣正认为“从军慰安妇不是被军人用绳子绑着的”,藤冈则称“没有证明慰安妇被强制的正式资料”。
第四,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识的右翼人士并不否认他们对“自由主义史观”论者的欣赏。“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会长奥野诚亮看了藤冈的文章后说:“还是有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讲话的学者”,“要是没有他们,日本就会成为充满自虐精神的国家而灭亡了。教育如果不能培养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对于将来是留下了祸根。”他明确地说:“藤冈先生说的话,也是我经常说的,我们的感受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在实际上也无法回避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至“皇国史观”的一致性。1996年9月5日,藤冈应自民党参议院议员的政策研究会邀请作讲演,有人问到藤冈:“在教育中强调日本人的自豪感,难道没有导致回到‘皇国史观’的危险吗?”藤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战后正因为总是顾虑被批评为‘皇国史观’,所以才是畏畏缩缩。”显然,他在这里对“皇国史观”也没有否定。
第五,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同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人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如撰写《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19个人中,有6人也是藤冈信胜的《近现代历史的教育改革》杂志的撰稿人。
三 自由主义史观与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
自由主义史观的产生与日本战后在历史教育上的反省有密切关系。
战后日本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是相当不充分的。造成这一问题的客观原因是冷战开始后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变化。
冷战期间,美国把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作为基本战略目标,改削弱日本为扶植日本,最终免除了日本天皇对于发动战争应负的责任。但是,天皇制在战前和战争中都是对政治和社会起统治作用、对日本人的国民精神起统辖作用的社会体制。既然对战争应负最高责任的战争指导者都被免除战争责任,那么作为日本人的整体,就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和对侵略和加害负责的必要。而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东京审判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对美国的伤害始终被作为追究的重点,而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暴行以及使数千万人受害的历史责任,则被置于次要的位置,由于天皇责任的被免除而更被忽略而束之高阁。战后签订旧金山讲和条约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由于美国要利用日本作为在亚洲的战略基地,压制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朝鲜对日本的战争赔偿的要求,使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责任没有条件得以追究。谴责侵略战争,追究日本的侵略责任的力量被视为“反日本”和“共产主义的间谍”而受到压制和迫害。
主观原因则是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的顽固维护旧体制和战争观的右派政治家的强大的势力。战后,这一势力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全部被褫夺公职的只有21万人,其中职业军人就占75%,而在其他的25%中也有军人,实际上仅军人就占80%。而当时的官僚、企业家很少有被褫夺公职的。像在战争期间极力进行政治动员的日本大政翼赞会的成员,当时是相当大而且相当起作用的机构,而在战后被追究的人只有其154万人的16.5%。
那些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责任的日本政治家为逃避责任,一方面竭力宣扬所谓“战争责任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的论调,一方面竭力宣扬日本在战争中的被害:美国飞机轰炸东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战争中衣食不足等等。他们竭力培养日本国民的受害意识,不愿意让日本人了解侵略战争对中国和亚洲各国造成的灾难,从而为否认侵略战争责任制造理论根据和社会基础。
日本国民对于侵略战争的责任的认识就是这样被引上了歧路。
针对被引上歧路的战争责任认识,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从历史教育入手促使日本人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战后关于教科书问题的诉讼是这一斗争的典型体现。
家永三郎就是日本有识之士的典型代表。他在战后一直强调自己对于侵略战争的“无作为”的责任。他认为日本人只知道自己的被害而不知道加害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他对自己未能制止战争而感到惭愧。他一再表示:“现在想起来,我作为社会一员,不能只因没有赞美战争而聊以自慰,应当对没有阻止战争而忏悔。”“我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没有接到征兵的命令,但内地同战场一样,在我的身边就曾落下过燃烧弹,几乎丧命。能够在战后活下来是幸运的,今后的生命为正义而献身是决不后悔的。”
针对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问题认识的偏向,家永三郎先生坚持编写真实反映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努力向日本的青年一代说明侵略战争的真相。1952年,当时担任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家永三郎先生为日本的中学编写了一部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并于1953年开始发行。家永先生根据战后揭露出来的许多确凿的历史事实,在他的著作中批判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性战争。然而就是从那一年起,所谓的《旧金山和约》签订,在那以后,日本国内政治逐渐右倾化,开始明目张胆地否认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对教科书的审查也越来越严厉。1958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对教科书的严格审查的标准,之后又多次修订,一次比一次严厉。按照这一标准对于日本历史教科书审查的结果,1958年当年就有33%的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而家永三郎先生编写的教科书在1963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理由是“正确性与内容的选择上有明显的缺欠”,“事实的取舍、选择方面欠妥”,“记述往往流于评论,语气和表达不符合教科书的方式”,“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的反省”,“与日本的教科书的目标相去甚远”等等。
为了教科书的发行,家永先生不得不进行修改,在1964年重新提出申请。这一次又被审定有293处不合格必须修改的地方。家永先生感到气愤,而且许多被要求修改的地方是直接涉及日本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而这正是家永先生认为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而且文部省的审查已经违背了日本宪法关于保障表现自由,保障学问自由和保障教育自由的原则。于是在1965年6月12日,家永先生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了诉讼,又在1967年6月23日以文部省为对象提出第二次诉讼。在这以后,针对日本政府对教科书审定的力度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家永三郎先生于1984年1月9日又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第三次诉讼。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学者同日本政府之间的诉讼过程。
教科书的三次诉讼是分别独自进行的,第一次诉讼经最高法院在1993年3月16日作出了家永败诉的判决。第二次诉讼在1975年12月20日经东京高等法院的审理本来是判为家永胜诉的,但被最高法院驳回重新审理,结果在1982年4月8日废除原判,后改判家永败诉。第三次诉讼提出后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1989年10月3日的一审和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都作出了家永部分胜诉的判决。1997年8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对第三次诉讼作出最后的判决,认定教科书关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日本军队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记述上是合适的,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违背宪法,并判定给予家永三郎40万日元赔偿金。
尽管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仍判定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制度合乎日本宪法,否决了家永先生关于审定教科书制度违宪的指控,但是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日本进步力量呼吁日本社会正确认识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责任问题的努力获得了明显的效果,许多日本人通过这一诉讼事件已经认识到“历史教育是为了让一代一代的人正确地认识日本,对于日本应当反省的地方要冷静地总结,对过去问题的分析应尽量客观”。(注:[日]森川金寿:《教科书与裁判》,岩波书店1991年12月版,第157页。)《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在日本的年轻一代几乎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战争的背景下,诉讼这件事本身就有重大的意义,这不是以诉讼的胜负所能评价的。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同日本围绕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诉讼的争论显然有直接的关系。
四 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国际原因
如果说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国内原因的话,那么,国际形态的发展以及对于形势发展的判断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对自由主义史观论者起了重要影响的国际形势变化都发生在90年代。
以藤冈信胜为例,他自称自己原来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说在他的战后意识中有两个支柱,即“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幻想”和“一国和平主义的幻想”。但是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幻想在进入70年代后由于读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而开始动摇,到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发生了变化后,“自己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幻想才得以清除了”。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胜利”这一“世界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形态判断下,过去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也应随之变化。他的理由是:过去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认识是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那么建立在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也好,共产国际史观也好,甚至与此相关的东京审判史观,都应当受到批判,原来对于战争责任的肯定就要转为否定,原来对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目的相信就要转为怀疑和否认,这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的转向。
藤冈的这一表白应当说是反映了他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员的基本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的确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遇到的挫折有密切的联系。其实这一问题并不新鲜,如果对日本战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发展过程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在历史上发生过十分相似的现象。战后初期,日本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对战前的“皇国史观”以及超现实的历史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在理论与实证统一的基础上又与丸山政治学相结合,形成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统一,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史研究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但是,在50年代初,共产国际内部发生分裂,接着在1956年又有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些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件对日本战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以“皇国史观”为背景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向战后兴起的科学的人民的历史观进行反扑,使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有良心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时处于停滞。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与当时的情况十分相似。
与上一个问题相关,对日本的国际作用认识的混乱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另一个国际形势方面的原因。
近年来,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调日本在国际上的贡献的思潮,这是因为日本负担了战争经费的20%以上,达到130亿美元,并把自卫队的扫雷艇派到了波斯湾,并以此为契机派自卫队参加了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行动(PKO)。本来,日本的这些举动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安和警惕,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但是,有的人在这一形势下头脑发热了,一方面以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多年来为之努力的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已经实现,而抱怨国际社会仍然对日本的国际贡献视而不见,日本没有得到相应的报答,包括没有得到在联合国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和发言权。另一方面,冷战结束特别是海湾战争后,一些日本人认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国防,就等于引诱对方的国家来侵略自己”。集合这两方面的要求,在日本社会出现了要求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求给日本向海外的派兵(PKO)以正当的名义,甚至要求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以达到“名正言顺”地对外派兵的目的的种种活动。这样的要求促使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民族主义情绪恰恰需要自由主义史观的配合。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作用,成为政治大国,应当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经济地位,还需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道义感,还需要有各国的信任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这一方面,能够使日本走上正确道路的决不是自由主义史观。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南京大屠杀论文; 日本教科书事件论文; 史观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产经新闻论文; 历史教科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