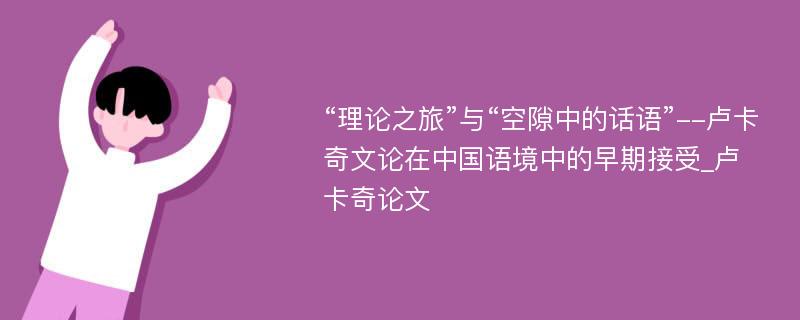
“理论的旅行”与“夹缝中的话语”——卢卡奇文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早期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语境论文,夹缝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1935年《译文》发表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算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下文简称西马文论)在中国已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70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西马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也被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其理论接受旅程的曲折复杂以及现实语境压力下的理论话语呈现形态。卢卡奇在中国语境中的早期接受可称为一次极具特色的“理论的旅行”,并在中国语境的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规导中呈现为“夹缝中的话语”生存形态,这一生存形态是卢卡奇文论在中国早期接受中的宿命,同时也是我们反思西马文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契机。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部分地为国人所知。被卢卡奇称为“马克思的真正的学生”的卢森堡在1919年1月15日牺牲的消息当年年初就刊登在我国《进化》杂志上,而在1921-1922年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还几次举行过相当规模的集会以纪念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①。卢森堡固然算不得西马文论和美学的杰出代表,但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却为中西方学者所公认。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早地进入中国人视野的卢森堡,其主要身份只能是一个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如此,人们对她的关注集中在其革命实践和革命思想方面。具体到西马文论,最早进入中国并且成为中国早期接受主角的应该是著名理论家卢卡奇。
早在1935年,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由中国学者梦十翻译为中文发表在《译文》第2卷第2期上;次年胡风根据日本学者熊泽复六的日译本转译了卢卡奇《小说理论》的一部分,发表在《小说家》杂志上;1940年《论现实主义》由王春江翻译发表在1940年1月的《文艺月报》上;同年,《叙事与描写》由老一代美学家吕荧翻译发表在《七月》杂志上(1946年该文单行本由新新出版社出版),当时作为主编的胡风为之写了“编校后记”,肯定和支持卢卡奇在文学创作与世界观关系问题上的观点;1944年《论文学与人物底智慧风貌》由周行翻译发表在《文艺杂志》第3卷第3期上。此后,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卢卡奇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青年黑格尔》以及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资本积累》、《国民经济学入门》等著作也相继译介出版,但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文革”期间更被贴上“内部教材、供批判使用”的标签,沦为反面的教材和批判的靶子。
对卢卡奇文论的早期接受基本集中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问题是,卢卡奇何以在此时被集中译介?卢卡奇文论中的哪些思考吸引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目光?答案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文化堆积中,然而仍有些微的线索可寻。吕荧在写于1944年的《叙事与描写》的“译者小引”中曾坦言,自己“关于作者卢卡奇,知道得很少”,仅从《国际文学》的后记中知道一些基本情况,而对于卢卡奇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所引起的论争倒是相对了解得比较多②。这一线索意味着,对于上述提问的思考必须把上世纪30-40年代的社会现实和文论语境以及卢卡奇文艺和美学的理论关注点拖进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而稍加深入我们也会赫然发现,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卢卡奇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之间直接发生了复杂的关联,而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使卢卡奇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成为夹缝中的话语。就此而言,对于这一时期卢卡奇的考察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研究西马文论中国早期接受的一份标本。
显而易见,无论对于卢卡奇还是对于中国文论来说,上世纪30-40年代这一时期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对卢卡奇而言,从1930年起一直到1944年,除了侨居德国柏林的三年(1931年到1933年)之外,他在莫斯科苏共马列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度过了11年的时间。11年中,卢卡奇潜心于美学和文论研究,为自己赢得了“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其间也参与了对当时“拉普”运动的批判。而对于上世纪30年代初尚为弱小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来说,来自苏联和日本文艺运动和思潮的影响更为巨大,相比较而言,此时苏联文论更多的是借道日本进入中国的。比如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原则就是转道日本,在中国被接受为“普罗”现实主义的口号。“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原则认为“只有受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才能创造一个具有特殊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③。这一原则在当时的苏联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而“普罗”现实主义这一口号来自日本学者臧元惟人,他在《新写实主义论文集》④中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创作原则,这显然是苏联文艺理论与日本创作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无论如何,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绝对的指导作用这一精神实质不仅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对左翼文学理论建设发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对于作家世界观与文艺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如此这般简单化的理解,在卢卡奇看来是有问题的,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作家必须有一个坚定而生动的世界观”,“没有世界观,就没有作品可言”⑤,同时又指出世界观与作家创作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强调要避免对世界观在创作中的作用问题上抽象的机械理解。这使他在当时斯大林文艺路线影响正盛、宗派主义和左倾势力猖獗的历史时期受到了批判,并在1941年被捕入狱。而恰在此时,卢卡奇的译著进入中国。这样一来,卢卡奇在苏联的遭遇就不能不对其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命运发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其面纱尚未揭开,便堕入被批判的深渊⑥。不容否认,无论是苏联的“拉普”还是源自日本的“普罗”现实主义,他们关于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的阐述,对当时左翼文学创作和文论建设运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为将作家世界观与文艺创作方法混为一谈并将前者视为唯一标准的做法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可以说,卢卡奇在中国的早期接受从一开始颇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他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虽然有助于其文论开始在中国的旅行,然而在那一个凄风冷雨、民族危亡的特定时代,他的理论思考无从获得展开自身的空间,即便是在那些包括胡风在内的极为个别的头脑中情况依然如此。
二
探讨卢卡奇文论在中国的早期接受,胡风是一个不能不谈的人物。这不仅仅因为他较早译介了卢卡奇的理论著作,较早独具只眼地注意到卢卡奇文论之迥异于“普罗”现实主义之处,而且还因为,胡风对于卢卡奇文论的理解以及他个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西马文论在中国的早期接受图景的一个象征。胡风与卢卡奇对话的平台除了上面提到的世界观与文艺创作方法关系问题之外,还有关于典型塑造问题、人的解放与主观精神问题等,此处仅以第一个问题为例进行考察。
在较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左拉与现实主义》中,卢卡奇批判了自然主义文艺倾向,认为对于“辩证的反映论、从而对于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美学理论来说”,强调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别“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⑦。而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的《叙事与描写》的副标题就是“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问题还不仅在于它们(以及与《叙事与描写》同年译介的《论现实主义》)对于自然主义的批判,而更在于卢卡奇在阐述现实主义时所表达的对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而这正是左翼文学创作中所困惑并努力探询的问题。对此,胡风的《叙事与描写》的“编后记”可谓一语中的,针对苏联文艺界在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上对卢卡奇抹杀世界观作用的批评,他写道:“问题也许不在于抹杀了世界观的作用,而是在于怎样解释了世界观的作用,或者说,是在于具体地从文艺史上怎样地理解了世界观的作用罢。”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他高度评价该文“是一篇宝贵的文献”⑧。40余年后,胡风在回忆此事时说:卢卡奇“绝非反对世界观对创作有引导作用,而是具体地说明世界观是怎样在创作中发生作用的,要怎样才能对创作发生积极作用。批评家抓住这一点,不管卢卡奇原文和我的原意,马上断定我是反对正确的世界观对创作有主导作用的”,同时,胡风认为这篇文章“对在创作中进行艰苦追求的作家发生了好的影响”⑨。
面对当时国内外对于卢卡奇众口一词的批评,胡风之所以敢于公开支持卢卡奇的观点,显然是因为他在卢卡奇那里找到了天涯知音。实际上,在胡风的理论话语中,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自始至终是得到肯定的,他也从来没有否定过世界观对于作家主观意愿和创作对象的影响,甚至批评抛弃这个基本立场而奢谈“高度的客观态度”的倾向,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的世界观与正确的创作方法的统一。这在其后的文艺思想中进一步发展为作家与世界观、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统一问题。相对而言,后一重统一更为根本,因为“如果不经过和现实生活相融合这一过程,只是直接地从思想去制造作品,那我们要说,即令他所依据的是正确的思想结论,那作品也是虚伪的东西”⑩。应该说,胡风在现实主义问题上对于卢卡奇的理解和阐发是准确和到位的。
尽管胡风也许是当时少有的读过卢卡奇著作的人,尽管他敏锐地捕捉到卢卡奇文艺思想的火花,并从其理论脉动中感受到知音般的欣喜,但是,对于卢卡奇之于胡风的影响仍旧不应估计过高。二人固然都对现实主义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刻理解,但具体到文艺内部规律的具体把握,二人又判然有别。比如同样是坚持艺术是对于现实的反映,卢卡奇从其“总体性”思想出发,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乃是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对于自己主观的世界图景的无情态度。因此,他推崇和提倡尊重社会存在、排除意识形态干扰的真实反映社会存在的现实主义。当然,强调作家对于社会历史真实的尊重,也绝不等于说作家是镜子式的消极、被动,因为,作家对于社会总体性的真实把握、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揭示以及对于异化现实的关注等等,这些行为本身就标明了作家主观方面的活动,一种尊重客观真实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动。如果说,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在作家与现实的统一中相对侧重于现实的一面,而胡风则显然更看中作家的一面。在胡风看来,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的艺术创作“是一个生活过程,而且是把他从实际生活得来的东西经过最后的血肉考验的、最紧张的生活过程”(11),就是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拥抱、突击、扩张现实对象,并最终通过这种血肉追求而达到主客观的融合,因此,现实主义作家要把“客观的因素变成主观的所有”,又“把主观的所有变成客观的形体”(12)。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主体激活现实主义”(13)。由此可见,即使对像胡风这样接受过卢卡奇著作,而且理解深刻、眼光敏锐的学者来说,卢卡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还是有限的。无论是对于胡风,还是对于卢卡奇在中国的其他接受者来说,这种限度是特定时代及其特定话语语境所造成的。
三
卢卡奇文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早期接受无疑是一次特殊的“理论的旅行”。赛义德认为,“理论的旅行”包含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的环境,使观念得以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14)概而言之,对于理论的引进、接受以及在时空中的变异和改造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新的语境条件——“接纳的条件”或者“抵制的条件”,用赛义德的话来说,“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和容忍”。具体到卢卡奇,这些条件体现为中国语境的历史规定性和逻辑规定性。对于历史规定性,马克思在谈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提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黑格尔则说哲学是把握在精神中的时代,两种说法精当地勾画出理论与现实生活和历史时代的关系;对于逻辑规定性,重视文学功能性的文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论语境以及文论建构其现代性的内在逻辑等方面成为其具体体现。
对于卢卡奇在中国话语中的“理论的旅行”来说,其历史规定性具体体现为与我国政治生活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后者的起伏而潮涨潮落。卢卡奇文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进入我国文艺理论家视野,应该说是源于特定的历史机遇:首先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强势话语成为正处于理论建设时期的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理论资源;其次是卢卡奇在莫斯科的长期停留及其后来引起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正击中了当时文艺理论家所关注的焦点;三是彼时特定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现实主义因其更切近现实而易于成为理论家思考的重点;四是卢卡奇文论本身以现实主义作为理论旗帜也契合了中国文论的需要。正是在上述合力的作用下,卢卡奇文论部分地进入中国理论家视野,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拉开了西马文论在中国“理论的旅行”的序幕。然而,也仅仅是序幕而已。这不仅是因为整体来看,国内早期阶段对于西马文艺和美学的译介和传播无论是在规模还是认识水平上都处于相当低的阶段,谈不上什么深入的研究,而且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新时期以前,这刚刚拉开的序幕又黯然垂下。随着胡风的被批判,卢卡奇也被称为“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15)而受到批判,萨特、布洛赫、梅洛·庞蒂等西马理论家的著作被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面教材,只能内部发行,西马及其文论完全沦为批判的对象,我国对于西马美学、文论的接受和研究就此搁浅。
接受语境的历史规定性与逻辑规定性相辅相成,具体体现了卢卡奇文论在中国的“理论的旅行”的特殊性,注定了卢卡奇伴随着中国文论发展进程的步调而曲折于接受的夹缝之中。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一方面,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我国文论界可谓众声喧哗,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人的文学到无产阶级文学,从文学本质、文学政治性、文学阶级性到文学真实性、文学与世界观等诸问题,派别众多、论争频仍,然而其中逐渐突显的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并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在文学界逐渐发展成为主力”(16)。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强势以及卢卡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标签为其在中国的理论的旅行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卢卡奇40年代初期在苏联的遭遇又使他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中国语境中处于被质疑的位置上。其次是现实主义文论话语。处在“红色的三十年代”的国际背景与30年代社会现实挟裹下的左翼文学运动着力于对于现实主义文论的建构和倡导,并在“文以载道”政教式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下朝着简单化、极端化方向发展,其消极面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部分地得到巩固。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契合了当时中国文论的发展思潮,然而其思考的理性与辩证在其几乎被接受的同时就遭到冷遇。再次是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澄清自身性质和确定自身地位的前提,也是理解和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重要通途,马克思主义文论从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引进和传播到其主导地位的确立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反思,就一直浸润于意识形态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奠定了它在我国文艺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恢复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原初规定,意识形态“是客观的,而且它本身就是武器”,“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也是后者健康发挥职能的先决条件”(17),二者处于辩证关系之中,而这恰构成了卢卡奇文论在中国旅行的特殊性根源之一。
当一种理论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进入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时,它的旅行就意味着与出发点情况迥异的再现过程和制度化过程的开始,意味着理论和观念在错综复杂的移植、流通以及交换过程中探问自身重新立足、萌发、成长的可能性。“夹缝中的话语”是卢卡奇文论在中国早期接受中的宿命,同时也是我们反思西马文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回顾卢卡奇文论在中国的早期接受,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意识形态动机是一回事,而剥离出学理层面的内在规定性则是另一回事,意识形态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解意识形态神秘化的过程。
注释:
①程人乾:《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
②吕荧:《叙事与描写·译者小引》,香港:新新出版社,1944年版,第4页。
③张秋华等编选:《“拉普”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6页。
④[日]臧元惟人著,吴之本译:《新写实主义论文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139页以下。
⑤《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⑥马驰:《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237页。
⑦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270页。
⑧胡风:《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⑨胡风:《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
⑩胡风:《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11)胡风:《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320页。
(12)同上,第105页。
(13)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14)[美]赛义德著,谢少波等译:《赛义德自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15)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
(16)钱中文等著:《自律与他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7)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 (MA:MIT Press,1971) 311-316.
标签:卢卡奇论文; 旅行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胡风论文; 文艺论文; 世界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