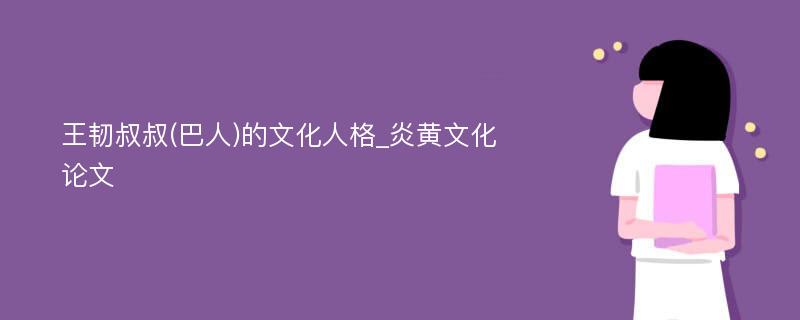
王任叔(巴人)的文化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巴人论文,文化论文,王任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5-0100-05
1901年10月19日,浙江奉化大堰村一户耕读传家的老宅门里生下一个男婴。也许是为抗议此前一个月清朝政府刚刚向西方列强签下让中国全面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表示不愿做封建末世的顺民吧,他没有脉搏,没有呼吸。三天之后,当一个老堕民(“堕民”是浙东世代最受欺凌的特殊族类,一生只能从事别人婚丧嫁娶中最卑微的杂务,年节则演出小戏以求赏赐),抱起这个死婴在山野掩埋之时,才发出第一声哭叫。那充满底气的声音似在向世界宣布:中国虽然多灾多难,但我不愿扭头就走,对义务我要承担,对理想我要追求。这就是王任叔——巴人。
他是唱“挽歌”的诗人、“民间小说家”,文学研究会早期的年轻成员。作为革命者,他是浙东早期的共产党人和跨党的国民党员。他浙东崛起、广州从戎、日本游学、左联实务,他宁汉韬晦、“孤岛”苦斗、南洋流亡、星岛受命。建国后他出任大使,继则是总编辑和研究员——为官为民,不堕其志;四次婚变,五陷囹圄,炼狱人间——真赤子竟成“反革命”。1972年,正当国人被“四人帮”整得或三缄其口或心理变态之时,蓬头跣足的老人却在故乡的山野里喊出了一般人喊不出也不敢喊的两个字:“打鬼!打鬼!”他哪里是什么精神分裂,不,他至死也是位伟大的智者。
他的一生是一部奇书,他把人的思维能量和运作能量推到灿烂的极致。他的文化人格,使他由青年时代嫉恶如仇的“雷雨先生”、青春偶像的“大众情人”,发展到中年时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活鲁迅”、“打鬼的钟(馗)进士”、“端·巴人”(印尼人对哲人智者的尊称)。
他的活动领域由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戏剧、鲁迅研究、编辑出版、翻译、理论批评,而教师、军人、秘密工作、党务、外交、印尼史学……他160来个笔名(是已知中国作家笔名最多的一位)很能说明他涉足范围之广,上千万字的著述,证明他给我们所留下的文化遗产之富。
“巴人”这一名字已包容于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也涵藏着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秘。不管你是研究文学,还是史学、哲学、社会学,你都可以在这个名字之下找到参照之物。正因为如此,这位在生前没有享得“文豪”、“大师”声名的人,在他身后的1986年至1997年,在宁波、丹东连续4次召开全国范围的巴人学术研讨会。研究论文数以百计,研究专著已近十部。随着巴人生前未刊遗著如《冲突》、《莽秀才造反记》、《女工秋菊》、《旅广手记》、《五祖庙》、《点滴集》、《印尼散记》、《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巴人文集》的出版,他的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
二
巴人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情超常广阔,巴人的投入范围与气魄,非一般文人所能望其项背。下面仅就其作为文学家,作一些评估。
巴人是文学研究会诗人之群中被郑振铎称作为“最初在中国唱挽歌的人”。他在1921年就开始了新诗的创作,他手订了一部以《恶魔》冠名的充满了对旧文化旧传统彻底反叛精神的新诗诗集,郑振铎从中选取了一些分期发表在《文学旬刊》上。1923年,巴人出版了《情诗》,这是新诗继《尝试集》(胡适)、《女神》(郭沫若)、《冬夜》(俞平伯)、《蕙的心》(汪静之)之后的早期成果。它前后二十余章,无标题,列编号,各章既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短笺,又是具有整体构思的长诗。1923年发表在《文学周报》上的长诗《从狭的笼中逃出来的囚人》,以250行篇幅塑造了一个至死不向恶势力妥协,宁可投向自由的大海的造反者形象。再加上巴人众多表现自我与现实的冲突,在艺术上常赋予哲理的寓意,这常让人误认为他是创造社的诗人。未刊长诗《洪炉》成稿于1922年,1924年又作修订,计746行,作为叙事长诗,它比1926年朱湘发表的长诗《女娇》要早二三年。它的独特价值在于:不孤立地去表现主人公铁儿个人遭遇及复仇故事,而是从揭露现实上升到反叛现实,从个人复仇上升到了阶级反叛。“阶级反叛”这一体现五四精神向无产阶级革命推进的思想,在郭沫若的《前茅》、蒋光慈的《新马》的若干诗作中有所显示,而巴人的《洪炉》则异常明朗。在艺术上,《洪炉》表现为情节的虚幻化,以人物及诗人的心理时空取代传统的叙写时空。现代化的叙事诗艺,是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楚骚传统在诗人心灵中撞击的火花,它本身意味着中国现代叙事诗的一种成熟(此前,巴人曾翻译过西方短诗在刊物发表),如果《洪炉》及时问世,郭沫若也就不会发出“如今的诗人,可惜还在吃奶”的浩叹了。未刊长篇叙事诗《髑髅哀歌》计480行,从表面层次看,这一部由有爱、美、悲三要素构成的爱情悲剧,它的唯美主义倾向使人想起王尔德的让人肌寒魄冷的《莎乐美》。从更深一层次看,说它是写阶级的对立使穷人的爱之追求破灭亦无不可。而从诗人当时的创作心态来分析,其更深的意蕴在于:以沉重的悲剧意识讴歌对理想至死不渝、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大型史诗《印度尼西亚之歌》系诗人1944年在苏门答腊流亡时创作,1952年他卸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后完成第四稿的宏篇巨制,全诗以两千余行篇幅写一个域外民族的历史、现实与理想,这在中国诗坛尚属独步。
1922年巴人在《文学旬刊》连连发表有诗的意境而不讲究事件与人物的速写式小说。次年,他有三篇小说被收入《小说年鉴》,编者向读者推荐说:“我们的文坛里,向来关于描写乡村生活的只有一位鲁迅,于今又添了这位任叔君。”像许多乡土小说家一样,巴人是受鲁迅乡土小说的影响而开始创作的。鲁迅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1]与鲁迅在文中所涉及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裴文中不同,巴人在创作乡土小说时,没有客居北京,而是生活在浙江乡间。期间,他在镇海、鄞县、慈溪、奉化、宁波教书,作编辑,从事革命活动,并时常遄返大堰故乡。他回忆说:“一到暑假,我就像大赦犯似的,抱着一腔高兴回到乡下去。我的工作是这样开始:一面跟乡里思想相同的朋友,杂谈着一切人生问题;一面却拣着晚上乘凉的时候,跟乡下人谈家常事情——于是我偷偷地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每一个暑假,我总可以记下好多东西……仿佛那些人物,并不是活在这现实社会上,而是活在我的那些草稿本里。”[2]这批大部分收入到《破屋》、《殉》、《乡长先生》中的乡土小说,同当时侨居北京的作家以回忆与乡愁切入生活在距离上就有很大不同,所以1928年文坛上以“民间小说家”来称呼他。他的可贵处在于他不局限在同情农民的立场,而是站在历史运动的潮头上以逐渐显明的阶级意识分析、认识、把握农民,这同他在1922年参加了CY,1925年参加了CP,学习了革命理论并直接参予农民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作品对农民的命运在“哀其不幸”之外,还歌其抗争。大革命失败后,巴人将《唔》、《出路》、《冲突》等小说交给《太阳月刊》时,受到太阳社革命文学者的交口称赞,据孟超回忆,赵冷(王任叔的又一笔名)作品的高质量,使我们非常兴奋[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工作与生活在上海、汉口、南京、宁波,做过教员、秘密工作者、小京官、世界语学者、职业文人,参与并领导过工人运动、民族统战工作、讲习所,还坐过三次大牢。接触过京中要人、上海闻人、外国友人、大小商人,乃至三教九流,七行八作。这反映到他三十年代的都市小说中,有下面几个明显特征:(一)视野开阔,摄取广泛,各类人物一自经过他的镜头,他便能放取睿智的眼光,把握其特异(典型不是一般,也不是个别,而是特殊),评价其价值,于是,互生与并列的人物各以不同的身份、声貌、向我们呼拥而来;(二)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理性与个性交互渗透。巴人在文学论文《典型的写出》中说“典型人物的写出,都还是有赖于个性之社会学发现”,试将巴人的《友谊》与京派作家杨振声的《报复》相对读,就可以感到巴人既不放弃对特殊性的直接感受,又不放弃理性的渗透,由此换来对题材开掘的深与广;(三)艺术手段的多方面选择,审美功能的多方面展现。我们既可看到情节完整结构严谨的作品如《浇香膏的女人》、《保镖黄得胜》,也有展现一幕场景的作品如《雾》、《茶社里》,既有冷静再现生活的《额角运与断眉运》,也有表现情绪流动的《龙厄》、《站在壁角里的人》,既有作者参予评论、抒情的作品如《故居》、《一个发羊癫疯的》,也有用手记的形式表现一种实感的《监房手记》,既有用了现代主义手法乃至荒诞派手法的《六横岛》、《自杀尝试者》,也有以儿童的眼光和语言写革命者受难的《猫的威权》,既有群像式的《女工秋菊》,也有用散文诗形式的《白鹭》。至于他的讽刺小说,如《阿贵流浪记》、《超然先生列传》,《皮包与烟斗》、《沉滓》、《浮渣》、《姜尚公老爷列传》,我们从中可以领略他写实式的、荒诞式的、杂感式的多种讽刺艺术。193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证章》是果戈理式荒诞讽刺的代表作,杨义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道:“假若说晚清有一部《官场现形记》,那么《证章》便是一部‘官场诛心记’……为三十年代讽刺文学不可多得的佳作。”巴人的现实主义精神决定他创作的时代感,由此产生了他的乡土小说、都市小说、讽刺小说。而他战士的斗争实践与学者的修养又使他在“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中创作了《某夫人》、《冲突》、《莽秀才造反记》这样的长篇历史反思小说。与北方义和团相呼应的浙东宁海平洋党起义,就发生在巴人诞生的前一年,事件发生地同巴人的诞生地大堰村仅一山之隔。莽秀才王锡彤领导乡民造反的故事,他自幼耳熟能详。大革命失败后,他同二哥王仲隅在逃避缉捕中走遍宁海、台州的山水、关隘,探访当年王锡彤起义的佚闻遗事。三十年代中期,他有创作“中国的悲剧丛书”系列长篇小说的宏伟构想,而《土地》(《莽秀才造反记》之原名》)却让一生变动不居的作者在40年中起笔了三次。当它的部分章节在《当代》披露后,楼适夷击节叹赏,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黄秋耘则将小说主人公同作者的悲剧性格联系起来。是的,巴人在创造莽秀才王锡彤时,把自己的乃至二哥王仲隅的性格都赋予给他了。翻开卷帙,扑面而来的是浙东的山光水色、乡规俚俗、生活习尚、活灵人物。这部封建末世的浙东百科全书,能让我们了解诸如械斗、诉讼、上坟、求神、祭祖、开贺,如何捐监生、买功名、奉祖庙、聚学田、请龙王、出稻会,如何吃大户、打龙灯,乃至充满野性的聚赌、虐杀、抢亲、野合……在官场、洋场、村场、文场中,作品把握住那一时代,揭示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互的人生状态。秀才王锡彤有仗义疏财、救人危难以及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又有浓重的封建正统观念和世俗思想。为了自己好惹动是非,他曾两次向县衙投案。当反洋的潮流把他裹挟进去时,他性格中鲁莽的一面终于占了上风,竖起了“反教平洋”的大旗,成了一方的头领。这位太平年月里的完人在统领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时,他读书人的缺陷与局限统统暴露出来了,义民们原始的报复狂流在泛滥冲决一番之后,以悲剧结束,而王锡彤亦不知所终。作者的这部生前尚未统稿的长篇小说现在读来有前半部铺排过当的毛病,但主人公造反之前与神秘的林泉长者牛老的哲学探讨,他囚居学宫时与赵举人、曾师爷的辩论和月光之下的内视自省等章节,精微地刻画了各类读书人的哲学观,从深层次探析了主人公的心灵之秘。仅此一端就可使这部获得1986年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的作品不朽。
巴人的剧作最早可追溯到1924年的多幕话剧《烦闷》(与诗友董挚声合作)和独幕剧《阶级》。1925年为声援“五卅”运动,他撰写了《沪上血案记》、《朝鲜亡国一瞥》、《何处去》等剧本或墓表。以上五种有的只存在于报刊的残页,有的亡佚。1940年巴人在“孤岛”上海写成并由香港立即出版了四幕话剧《前夜》,它写的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员们的官邸生活,对形形色色的官僚进行了冷潮热讽。与此同期创作并出版的《两代的爱》的场景只有一个——上海租界区的唐公馆的客厅。剧情展开时间为1939年的仲春至深秋,正是处在上海的“孤岛”时期,它的深意在于表现两代人在两个伟大时代中的不同追求。巴人曾说“戏剧是生活之压缩的表现”,他在半年时间内所写出的这两个剧本,是他半生生活体验的艺术表现。五四时,他是宁波学联的骨干人物,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广州的上层机要工作,“四·一二”后,在他担任宁波地委宣传委员期间曾被捕、坐牢,接受过严峻的考验。他看到过战友的高升、退隐、苦斗,分裂与重组。南京政府的小官僚生活使他对官场看得更加真切。再加他在上海“孤岛”前后所从事的上层社会活动,使他对社会各层面人物有深刻的观察,致使这两个剧本的人物塑造有着独特的价值。以《前夜》中的费娜来说,他是个在大革命时期不能英雄地死去,现在又不能正当地生活,陷于多种矛盾交叉点上的人物,她不同于有反叛精神的家庭妇女繁漪(《雷雨》),也不类于玩世不恭的交际花陈白露(《日出》),性格极其复杂;而《两代的爱》中那出场虽然不多,但左右整个剧情发展的杨达,是个有学问有经验的青年人的导师,他有一种泛爱的精神,爱平民爱一切新生的东西,他又有一种固执的憎恶,恨官僚恨剥削。他对腐朽的事物刻薄、尖利,对青年人调皮幽默,他爱用反话、笑话讲道理,他独具个性而平易近人。费娜、杨达不独在现代剧作中特具风貌,而且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上也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话剧《五祖庙》写的是十九世纪在南洋的五位华工,不堪荷兰殖民者的欺凌,为了众多难胞的尊严,合力杀死大工头而不愿祸及别人,竟各自拿了大工头的肢体去当局自首。这是真人真事,五位英雄牺牲时的年龄加起来才85岁,平均年龄只有17岁。但在苏门答腊,他们被华侨当作祖宗来世代供奉。巴人在创作该剧之前,参加并领导了“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二战结束后他又领导成立了“苏岛华侨民主同盟”,担任印尼华侨总会联合会顾问,并为新成立的印尼革命政府担任咨询。《五祖庙》在编演过程中正逢荷兰以宗主国身份重又踏上印尼国土,反动势力乘机制造华侨与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它在华侨社会广泛演出,并被邀请到印尼游击区演出。当时荷兰军队与印尼革命政府对峙,游击区戒备森严,但华侨团体拿了“端·巴人”的便条,便可自由出入。于此亦可见巴人及其《五祖庙》的威望。《五祖庙》第三场即法场一场,在处理上有很大的难度,如编排不当很容易陷入俗套。作者在表现空间时,将法庭内与法庭外的斗争,同时展现在一个横断面上;在表现时间上,五个被告的审辩各具特色。人物风貌展现得不呆、不滞,互相映比,各具姿彩,非斫轮老手,是莫可措笔的。
现代意义的杂文同古代宽泛意义上的杂文——议论性应用文有着渊源关系,但它具有着鲜明、急切的功利目的,有强烈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是非、爱憎。由于现代社会变革的急遽和斗争的复杂,再加报刊传播媒介的普及,这就造成了现代杂文的繁荣。因为它可以指东骂西,手法可以隐晦曲折,再加上又渗透了传统文化,所以连美国大作家、中国通赛珍珠也表示:中国杂文太特别,实在看不懂。杂文是艺术的内涵文章,当一个读者真看懂了,也就不容易忘记了。巴人认为杂文应该是属于战士的,他在《鲁迅风话旧》一文中说:“如果,这世上不缺乏战士,则总会随兴所至,拿起这杂文的武器来。”在《〈鲁迅风〉发刊词》中说:“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他是鲁迅风杂文的杰出代表,其杂文的特点表现为行文的泼辣与气度的闳放。首先,从创作主体来说,巴人胸中有正气,手中有真理,急切向读者披沥自己的肝胆、见识,以使广大读者在民族危亡时刻站稳立场,故不必藏头露尾、钝刀子割肉。战争时期的中国,陡然加快了生活的节奏,对信息的要求空前高涨。新闻报道承载的是告知信息,文学作品特别是杂文作品承载的是意识信息。人们根据这些信息来调整意识、选择行动、积累知识、丰富精神。巴人的泼辣与闳放的杂文创作,正是与这种社会需要相适应的。其次,巴人杂文的泼辣与闳放也有其个性的依据:幼年在家乡读小学时,教师就选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论说文范》等。读中等师范时,课外爱读《古文辞类纂》、《韩昌黎文集》,走向社会在浙东各地作小学教师时又喜欢汪洋恣肆的《庄子》。再说他又是个“金刚怒目”、“锋芒毕露”[4]的人。抗战前后,他的杂文部分收入在《边鼓集》、《横眉集》、《生活·思索与学习》、《边风录》、《战斗与学习》中。建国后巴人的杂文大致可分下列三类:一是对“老爷气”——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挞伐(如《况钟的笔》)。二是对“君子腔”——教条主义与形上学的抨击(如《略谈生活的公式化》)。三是抉发国家隐藏着的弊端,告诫完善体制。当我们今天重读四五十年前巴人所写的《“多”和“拖”》(批评官员多、办事拖)、《“上得下不得”》(讽刺中国的官员只许“步步高升”,比照外国总统下台后当平民,习俗不以为怪),仍有强烈的针对性。1957年的反右斗争幸没有扩大到他,而两年后的“反右倾”却因这类杂文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以此成为罪名而殉献于自己的审美理想了。
巴人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同他参与发起“左联”并负责“左联”的下属组织——青年学生文艺研究会——任务是辅导并培养青年作家有关。他的《常识以下》、《扪虱谈》、《窄门集》就是三十年代发表在刊物上的理论批评文章的选集。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专著自1924年出版夏丐尊的《文艺论》至1949年以群出版《文学底基础知识》,共有80种,它们大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唯独巴人的《文学读本》自1940年问世以来,连续修订增朴为《文学初步》、《文学论稿》,直至1956年还在修订出版,以应文学青年和高等教育的需要。巴人建造中国文学理论系统的热情还表现在愿自己的理论著作速朽,而寄希望于更完美的理论著作。他的理论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理论建设要紧密联系文学创作的发展和认识发展的实际。巴人与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不同,他不独有“发达的美学感觉”,而且有“发达的思想能力”(普利汉诺夫语)。作为理论批评家,从1922年5月11日在《文学旬刊》发表《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算起,到被剥夺从文权力前夕的1959年8月在某创作座谈会上发表《创作琐谈》为止,活动时间长达47年之久。他在二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针对太阳社、创造社成员的“一切文学,都是宣传”,而提出“文学是一种思想的传染”,三四十年代,他强调时代性、社会效果,而主张“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实践的文学,以及五十年代“笔底下有‘人’”、“没有无个性的典型”等文艺思想,在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建设中,都是可以吸纳的。
三
巴人离开我们已30年了,检点他留下来的思想、文化遗产,我们不难发现所具有的丰厚的现时代价值。这表现在——
爱国忧民。巴人幼年时最狠的骂人语就是“你里通外国”,“五卅”运动中他发动家乡奉化人民集会游行,规模空前。抗战前后,他先参与领导了要求当局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的“入狱运动”,上海“孤岛”时期他是艰苦卓绝的文化战士、爱国青年追随的旗帜。在新加坡、在苏门答腊,他是华人及当地各族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领袖。他对人民,特别是最底层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城乡劳动者,包括浙东的“堕民”、广州的“疍户”,都有着真切的同情与改变他们命运的集体主义行动。关于人口与生态,他的关切也是超前的。他早年的短篇小说《酥碎之岩》,就是写家乡山区因失度开发而引发了泥石流。晚年,他以“被专政”之身回到家乡,看到大堰村人口膨胀、山林破坏、田地锐减,而夙夜忧叹。巴人爱国爱民,可称得进亦忧,退亦忧。
诚信敬业。作为编辑,他接到彝族青年李乔的长篇小说《走厂》是在“八·一三”事件前夕,随着战火的逼进,他自上海的周家嘴,迁到租界区,三变地址后又去香港、去新加坡,层层关卡而后又去苏门答腊,在战乱之中他将一位不相识不知名作者的书稿当作身家性命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日寇在苏岛实行大检举时,他才交托给郁达夫埋藏于地下。1958年,巴人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党委书记,竟然亲自阅读普通来稿,他发现一位署名“浩然”者的书稿《喜鹊登枝》很有基础,便亲自担任它的责任编辑,10天内连写3函,与之平等协商编辑出版事宜,肯定作品的优长的同时,也指出进一步提高的方向。浩然在回忆文章中说:“巴人同志的革命资格很老,可以做高官。巴人同志的艺术造诣极深,可以搞创作。可是,他却心甘情愿在出版社率领一伙编辑,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为他人做嫁衣裳’……”[5]
不懈奋斗。1927年中共奉化县委书记董子兴(挚声)被捕后押至杭州陆军监狱,被杀害后,巴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前去收尸,在装殓时发现衣袋中有日记一册,巴人整理后在上海的革命刊物上发表,以纪念自己的诗友与战友,并鼓励未死者继续奋斗。六七十年代,他被剥夺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权利,于是学习日文、英文,翻译、整理资料,开始了十年研治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进程,直至他被押返故乡,屈辱中的他仍为百万言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与《印度尼西业近代史》而笔耕不辍,直至燃烧完最后一支七分钱一包的大红鹰香烟。其文化人格其道德精神,让山河动容,人神感泣;在中国文学的星空中,可与屈原、司马迁、鲁迅交相辉映。巴人是二十世纪的奇人,他以自己的惨死完成了一部真实的中国的悲剧。正是:
千里汨罗同一哭,
九样辞章未尽才。
[收稿日期]2001-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