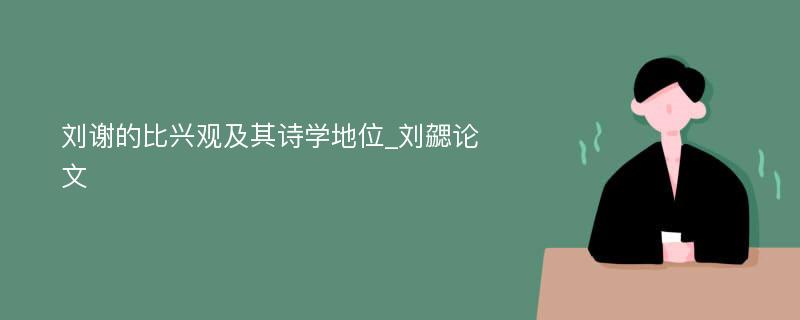
刘勰的比兴观及其诗学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2)04-0111-05
比兴,作为我国传统诗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在其历史的嬗变过程中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因此,理论界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如朱自清先生所感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1]235那么,在刘勰的比兴观里,比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的理论内涵是什么,以及它在我国诗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如果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刘勰的比兴观及其诗学地位不无裨益。
关于刘勰“比兴观”的理论内涵历来存有争论:一是认为比兴是指一种艺术方法,一种认为比兴是一种艺术思维,还有一种认为比兴是一种艺术形象。
如果仅从《文心雕龙》的体系上看,刘勰将比兴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法,而不是一种艺术思维或艺术形象。作者在创作论中把比兴作为一种修辞与章句、丽辞、夸饰、事类等并列放在一起,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或艺术形象放在《神思》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作者把比兴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或艺术形象来讨论,就应该将它放在《神思》篇里,而没有必要单独列出“比兴”一篇。周振甫先生在辨析其“创作论”的体例时指出,《神思》的“赞里”已经论述了创作论的次第,并据此把创作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这五篇即《总术》里的“务先大体”,是剖情析采的根本;《情采》、《熔裁》是剖情析采的结合;第二,物貌指《物色》,《物色》应在《情采》以后;第三,从声律到修辞,包括《声律》、《章句》、《丽辞》、《比兴》、《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加上《养气》来使文思常通,《附会》来“总文理,统首尾”。这部分属于剖情析采的方法。[2]243-244即创作论的体例是按由主到次、由总到分再到总的次序来编排的。由此可见,刘勰对《文心雕龙》体例的编排是深有用意的。
王元化先生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从刘勰承袭汉人体法相兼的视角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比兴仅仅看成是一种艺术手法,“是由于没有辨析《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体例,所以才没有认识到《比兴篇》和《神思篇》之间的有机联系。……倘使我们只从创作论诸篇的并列方面去分析其间的关系,而看不到刘勰以《神思篇》为总纲以笼罩创作论其余诸篇的内在联系,那么就不懂得刘勰的命意所在”[3]188。王先生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艺术手法与艺术思维、艺术形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刘勰比兴观里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但如果就此断定刘勰在“比兴”篇里因为“既把比兴当做艺术方法看待,又把比兴当做由艺术方法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看待,所以才有‘比体’、‘兴体’之称”[3]184,恐怕也不符合作者的原意。
通览《文心雕龙》全篇,无论是对“比”“兴”的界定还是《诗经》和辞赋中大量实例的运用,都表明了比兴的修辞身份。文中“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故诗人之志有二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触物生情所以用‘兴’的手法成立,因为比附事理所以比喻的手法产生。……所以诗人言志的手法有这两种。”[4]325“‘兴’体以立”和“‘比’体云构”中的“体”,是指法而不是体。这一点还可以在“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中得到证明。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时赋和颂首先得到发展,所以比喻手法就风起云涌。“赋”和“颂”是《诗经》“六义”中的两种文体,这一点已是共识。那么这里的“比”只能是为“赋”“颂”服务的修辞手法,而不是一种“体”。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解释这句话。至于作者在这里为什么用“体”而不用“法”,可能如王先生所说是因为延用汉人旧说的缘故。同时,汉人体法相兼之“体”也不同于王先生所谓的“体”。汉人的“体”是指不同内容所形成的文体,而王先生的“体”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艺术形象。另外,作者在论述比兴时明确提出“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比”则有“比义”与“比类”之别,所以“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也就是说,不论是比还是兴,都是一种比喻的修辞手法,只不过“比显而兴隐”罢了。
刘勰在《比兴》篇里把比兴仅仅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与章句、丽辞、夸饰、事类并列在一起,并不等于说其比兴观里就不包含艺术思维和形象。
《诠赋》的“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和《物色》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中仍保留着《诗经》中“兴”的传统用法,即一种由此及彼的艺术思维。这种思维过程在艺术创造中叫联想。依据现代文论的思想,联想可分为类似、接近和对比三种。“比”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类似联想,而“兴”则既可以是类似联想,也可以是接近或对比联想。《诗经》中的“兴”更加突出由此及彼的形象思维过程,如朱熹所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而“他物”与“所咏之物”之间既可以是相似,也可以是相近或相反。关于“他物”与“所咏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黄桂凤在《〈诗经〉比兴的分类》一文中做了很好的总结。[5]29-32
同时,艺术手法与艺术思维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任何一种艺术手法都是在一定的形象思维机制下产生的。在艺术创造中,一种形象思维最终都是要通过具体的语词表达出来,而将这种形象思维固定下来的语词表达就是一种修辞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手法是艺术思维的产物。比训为“附”,所谓“附理者切类以指事”;兴训为“起”,所谓“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附事理就是用打比方来说明事物,托物起兴的就是依照含意隐微的事物来寄托情意,比方也好、寄托也好,都是以此比彼或以此兴彼。
比兴无论是作为艺术手法还是作为艺术思维,《诗经》时代的先民们对此的运用都是不自觉的。他们只是在长期的生活中建立起了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由此及彼的原始形象思维。在“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里,自然万物是有生命的,自然万物对人类来说,既神秘莫测又充满力量;人类对它既感亲切又充满敬畏。人们希望能在她的庇佑下获得安宁和幸福,能与她和谐相处。我国由此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而“比兴”、“比德”说则是其最好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表达。赵沛霖先生认为:“这种渊源于原始宗教生活的联想,由于成千上万次的不断重复而逐级被强化和巩固,并在人们心理上相应地建立起越来越牢固的联系,并终于形成了以习惯性的条件反射为特征的联想,即习惯性联想。”[6]224-228。而这种引起习惯性联想的物象被援引入诗,便出现“他物”“引起所咏之物”的“原始兴象”。《诗经》里大量的物象都是这种“原始兴象”,是这种“习惯性联想”的产物。如用“金锡以喻明德”、用“螟蛉以喻教诲”、用“浣衣以拟心忧”等。无论是由物及情的触景生情,还是由情及物的托物言志,都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艺术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关于《文心雕龙》中刘勰的比兴观所包含的艺术思维,段学俭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比兴篇”与该书的比兴观》中有所论及。但他认为《诗经》中的“兴”“体现着古人一种抽象程度较低的思维方式”,而《文心雕龙》中《比兴》篇以外,“‘兴’字的用例则隐含着汉魏以来的一种新兴的文学艺术观念,即认识到了文艺创作与表达中情感的形象性,代表着古代文学理论中近似于‘形象思维’的初步思想。”[7]11-15而正是这种“抽象程度较低的思维方式”赋予先民们“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而且因为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那些用想象来创造的本人也感到非常惶惑”[8]162,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此,我们认为,既不能局限于《比兴》篇,把比兴仅仅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法,也不能因刘勰比兴观里包含艺术思维而否定其在《比兴》篇中将比兴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而要结合《文心雕龙》全篇来把握其丰富内涵。作者之所以单辟一篇来论述“比兴”,一方面是为了廓清汉人对比兴“体”“法”不分的模糊认识,同时也与其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不无关系。这是刘勰超越于前人的地方。而关于刘勰的比兴观之所以一直有争论,一是因为刘勰本人在不同的篇章里对这一范畴的论述不同,从而影响了我们对其做出清晰的判断;二是可能因为人们习惯于把艺术手法和艺术思维完全割裂开来加以理解,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比与兴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见仁见智。那么,刘勰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王元化先生站在“艺术形象”论的高度上指出:“他在分论比、兴的时候,并没有割裂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仍旧是从艺术形象的整体概念出发的。”[3]163是不是从“艺术形象的整体概念出发的”有待商榷,但作者把比兴看成是辩证统一的,则确定无疑。
首先,从比、兴表意的方式来看,比“显”而兴“隐”,故“‘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简单地讲,就是比是怀着愤怒的感情进行批判,而兴是用委婉的譬喻进行讽刺。作者这里是继承了《诗经》比兴的古老传统,而不是承袭汉人的传统。《诗经》的比是怀着愤怒的感情进行批判,如《硕鼠》、《伐檀》就是最好的例证。到了汉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郑玄注“六义”时认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这正是王元化先生所说的“诗人之比”与“辞人之比”的区别。至于“附理”和“起情”,在这里不能僵化地把它们对立起来进行理解,认为比是表达事理,兴是表达情感。这只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二者互文见义。
其次,从二者表达的意义来看,兴是“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即要传达重要的儒家义理,并且要“发注而后见也”,而比则没有这个义务。它或“比义”或“比类”,“比义”就是以具体的事物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或情感,是以物喻情或理,汉赋中“拟于心”“譬于事”是也;“比类”就是通过甲事物来凸显乙事物同样的特点,使这一特点更加生动形象,是以物喻物,汉赋中“喻于声”“方于貌”是也。所谓传达重要的“儒家义理”实际上是汉儒附会的结果,并不符合《诗经》的原貌。随着“兴”的嬗变这一点也逐渐模糊,更多是侧重表达某种思想或情感,与“比义”之“比”没有多大差别了。
再次,从二者的思维方式上看,兴是“起”、是触景生情,作者的主观情感由客观外物所引发,是由外物到主体的艺术思维过程;比是“附”、是托物言志,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投注到客观外物之上,是由主体到外物的艺术思维过程。叶嘉莹女士曾通过对《关雎》和《硕鼠》的比较来论述“兴”和“比”之间的差异。她说:“‘兴’是一个由物及心的过程,是因为听到或看到外物的景象才引起的一种感动。‘比’则是由心及物,是内心先有一种对剥削者痛恨的恶劣的印象,然后才用作比。”[9]116-121无论是由物及人还是由人及物,都是一种主客体互动的形象思维过程,二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差别。
最后,从刘勰批评汉代辞赋“日用乎‘比’,月望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中,可以看出其褒兴贬比的立场。但这里所贬的是指“喻于声”和“方于貌”的“辞人之比”,而不是“拟于心”和“譬于事”的“诗人之比”;所褒的是具有情感或事理内容的“兴”,而不是汉儒所强调的传达儒家义理的“兴”。从刘勰否定“比”而肯定“兴”的立场中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同时也透露出后世重“兴寄”、“兴象”的消息,这是“比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比兴之所以成为我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是因为它为唐代兴寄、兴象、意象、意境等核心范畴的出现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当然还有其他理论的参与,而刘勰的比兴观是其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丰富我国比兴的理论内涵和孕育意象、意境等范畴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比兴在《诗经》里的运用是古代先民“由此及彼”形象思维的自然反映,使用多了慢慢地就被固定下来,于是便成为一种艺术手法。汉代以后,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诗经》遂被奉为经典,于是汉儒们纷纷加入到“注经”的行列中来。《诗经》“六诗”首见于《周礼》:“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之为本,以六律之为音。”这是后人解释“六诗”的最初蓝本。《诗序》首把“六诗”改为“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但无论是“六诗”还是“六义”都是指“体”而不是“法”。郑玄在注“六义”时说:“风言圣贤治道之教化也。赋之言铺,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谕之也。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容也,诵以美之。”具体解释了六种不同文体所表达的内容和使用方法,其中已经包含了“法”的成分,但他似乎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西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云:“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已意识到其中“法”的成分,但他对“六义”的体、法问题没有作过多阐述。
这种现象一直到刘勰才有了根本改观,他第一次明确地把比兴放在创作论中与章句、丽辞、夸饰、事类等修辞手法并列在一起,使我们真正意识到比兴具有“法”的一面,而不仅仅是“体”,更重要的是,他的比兴观里包含着艺术思维。唐代孔颖达的“三体三用”说、宋代朱熹的“三经三纬”说,都是侧重从“法”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而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艺术思维。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还不及刘勰看得透彻。
同时,这种关于“六义”的解释也有一定的缺陷,那就是它无法说明“六义”的次序问题,也没有将《周礼》中“以六律之为音”这句话考虑进去。“以六律之为音”是说“六义”的划分是以不同的音乐作为分类标准。章炳麟先生在《六诗说》中据此将风、赋、比、兴、雅、颂看成是六种不同的诗体。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朱自清《诗言志辨》和郭绍虞《六义考辨》分别对此加以取舍和发挥。汉代对“六义”基本上是扣住“以六德之为本”这句话来作注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刘勰也没有大的改观,因此才会出现把《关雎》这首清新活泼的爱情诗解释为“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的现象,如此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其中出现细微变化的是,郑玄把比解释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这不符合《诗经》的客观情况,刘勰的“‘比’则畜愤以斥言”则更接近《诗经》的原貌。究其原因可能是汉代文学更多受到屈原的影响,郑玄的解释比较符合屈原作品中“比”。对于“兴”的解释,郑玄和刘勰的《比兴》篇都更接近汉代辞赋的特点,而于《诗经》的原貌有所偏离,比较符合《诗经》原貌的是《文心雕龙》中《比兴》篇以外关于“兴”的论述。
刘勰由汉人作为一种文体的比兴中发现其所包含的艺术手法、艺术思维等丰富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和廓清了汉人“体”“法”不分的模糊认识,同时为唐代意象、意境的出现提供了理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勰的比兴观是我国比兴理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王元化先生极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运用西方文论的思想和方法把比兴作为艺术形象进行立论,观点新颖。刘勰之后有关比兴的大量论述,常常习惯于把比兴放在一起,但论述时往往更注重兴。但无论是比还是兴,不管是显还是隐,都是一种由此及彼的思维活动,强调要有所寄托。由此,作为艺术手法或艺术思维的比兴所创造出的艺术应该包含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一是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由于兴偏重于隐,要求“发注而后见”,所以就构成了比兴的第三个要素:含蓄蕴藉。这三个要素正契合了意象、意境的审美特质。
后世重视“比兴”的诗歌传统主要侧重于“兴”。初唐时期,陈子昂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充实、不注重整体审美形象塑造的弊病,正面提出了“兴寄”。他所谓的“兴寄”既强调作品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又重视诗歌整体审美形象,这样就把作为艺术思维的“兴”赋予了艺术形象的审美内涵,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用来寄托情感和思想的物象应该形象生动、光彩照人,而不应像《诗经》中的物象那么简单、质朴;寄托的情感和思想应丰厚深广,而不应像《诗经》那样浅白狭小。其不足之处是,偏重于诗歌所寄托的社会内容,对审美形象的塑造认识不够。殷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兴象”说。殷燔的“兴象”说,则更侧重于诗歌艺术形象的塑造,并以此来批评六朝过于偏重词藻、声律等艺术形式和技巧。张少康先生指出,“‘兴象’是殷燔首先提出的重要文艺美学概念,它是指诗歌中完整的审美意象,不过,这种审美意象偏重于指主体比较隐蔽的客体形象”,更具有“兴”的特点。“‘兴象’的描绘,正是为了使诗歌的审美意象构成一种耐人寻味、含蓄不尽的境界。”因此可以说,“‘兴象’的超妙是构成诗歌意境的基础。”[10]169
殷燔的“兴象”说已经包含了意境构成的三个基本元素和审美特质。随后,王昌龄提出“意境”论便是顺理成章之事。皎然则把比兴分开来加以论述,他在《诗式》中云:“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这样把比兴人为地割裂开来加以理解似乎不太符合“比兴”的传统,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情与境是不可分离的,境中含情,情由境生,并且在其理论里透露出诗境与禅境合一的美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意境理论。司空图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在强调艺术形象的具体生动和思想内容的深广丰厚之外,更加突出了其含蓄蕴藉的一面,使意境理论有了一个质量的飞跃。至此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将比兴艺术推到一个新阶段,发展到一个新高峰,当属唐诗。”[11]112-115而这一切都发轫于刘勰的比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