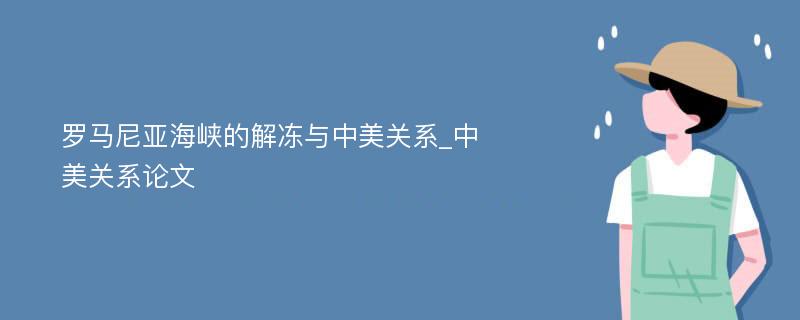
罗马尼亚渠道与中美关系的解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尼亚论文,中美关系论文,渠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敌视与隔绝,双方都曾把对方看作最危险的敌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出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和各自切身利益的考虑,中美两国关系才开始解冻。但由于长期的敌视与隔绝,两国都不得不借助其他国家以建立起最初的对话渠道,其中主要的是巴基斯坦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和法国渠道,此前已经存在,在这时继续发挥作用的是华沙渠道,偶尔使用过的则有挪威等渠道[1](P917)。
战后初期,罗马尼亚和美国的关系较为紧张。匈牙利事件以后,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建设民族共产主义的愿望与美国在东欧推行更灵活的政策的努力不谋而合,两国关系开始逐步改善。由于历史传统和罗马尼亚与苏联矛盾的加剧,罗马尼亚对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比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更积极,步伐更快。而20世纪60年代初罗马尼亚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和罗马尼亚在东欧国家中独特的对外政策,也令美国对罗马尼亚更感兴趣。
罗马尼亚地处巴尔干地区,是苏联—东欧集团的成员国,除了南斯拉夫外,其邻国全是华沙条约成员国。但它却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努力发展与苏联的经贸关系;既与苏联等国始终保持距离,又绝不脱离华沙条约组织;既发展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又公开支持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和立场,罗马尼亚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国际上著名的“诚实的掮客”,在中苏论战中当调停人,在东西方之间“搭桥”,在阿以之间和越美之间作传话人。美国便是看中了罗马尼亚的这个身份,让罗马尼亚成为中美之间最初的对话渠道。
早在罗马尼亚渠道被正式开通之前,美国就已开始通过罗马尼亚向中国转达和解的信息。1967年3月,尼克松以“前副总统”身份对罗马尼亚做了一次私人访问。在与齐奥塞斯库的会谈中,尼克松说要与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他讲此话时,显然不会忽视对话者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罗马尼亚对此心领神会。
3个月后的6月26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访美,与美国总统约翰逊进行了会谈,中美关系是话题之一。几天后,毛雷尔在访越途中秘密访华,向周恩来“转达他不久前访美时总统约翰逊和参议员盖伯赖特关于中美关系的谈话。”[2](P333)。同时,他还劝中国改善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周恩来则重申苏修是“马列主义的叛徒”,并强调“目前没有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由于双方话不投机,访问结束时,罗方提出对访问发一个短消息,中方竟没有同意[2](P329~330)。这就是迄今所知的罗马尼亚在中美之间的第一次传话,似乎是一次失败的传话。
表面上看,中国这时好像对美国、对改善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兴趣。然而,10月尼克松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提出要与中国对话,却马上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不但自己看了,还把它推荐给周恩来等人。[31](P224)这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此时的毛泽东居然会对一个已非国际要人的尼克松的文章感兴趣,这耐人寻味。可能的原因是,除了毛泽东此时仍对国际风云的变幻有超人的敏感外,还不能不考虑到罗马尼亚此前向中国传递的来自美国的有关信息,虽然没有马上收到预期的效果,却开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特别是对尼克松的注意。
1969年中苏关系骤然恶化,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迫切性。但是,双方相互敌视和隔绝已近20年,仅有的一条直接对话渠道——中美华沙会谈又在1969年初因美方的原因而再次中断,而且中国也已因“文化大革命”而几乎与世隔绝。美国只得设法另辟通向中国的对话渠道。选择罗马尼亚作为与中国的对话渠道,与1967年尼克松对罗马尼亚的私人访问有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齐奥塞斯库心里明白,“由于在1967访问布加勒斯特时受到的暴风雨般的欢迎,尼克松觉得欠了罗马尼亚的情”,他希望借尼克松的来访平衡苏联的压力,并推动美国早日给罗以最惠国待遇。
尼克松最初没有接受邀请。但是,当5月27日苏联领导人柯西金告诉他,苏联不会帮助华盛顿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时,恼怒的尼克松力排众议,决定以访问罗马尼亚的方式“拧俄国人的鼻子”[4](P289),做第一个对共产党国家做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4](P290)然而,他提出的访罗日期正好与早已确定的罗共十大的召开时间冲突。但齐奥塞斯库不想失掉这个难得的机会,他立即表示同意,并推迟2天召开罗共十大。促使尼克松接受邀请的另一个原因是,此时,“中国问题一直在他心目中占了很大的位置”。[5](P155)他意识到,“罗马尼亚是通向中国之路。”[4](P290)他想通过此次环球之旅开辟出这条道路。行前,他对基辛格说,让苏联人等着瞧吧,“等到我们完成这一旅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担心我们玩中国牌而发狂了。”[6](P197)
尼克松的罗马尼亚之行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在会谈中,尼克松对齐奥塞斯库说,他希望“罗马尼亚同意充当通向中国的渠道”。齐奥塞斯库表示愿意充当信使,向中国人转达美国的看法,并把中国人的反应告诉美国。[6](P227)在齐奥塞斯库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尼克松又在祝酒词中说:“我们寻求同所有国家的正常关系,不管其国内制度如何。任何国家为了同我们寻求正常关系作出努力,我们也会作出相应的努力。”[5](P179)罗马尼亚渠道由此开通。
9月7日,到河内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葬礼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经停北京时,向周恩来介绍了尼克松最近访罗的情况:尼克松明确地、无保留地表示愿意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周恩来重申,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问题和联合国问题,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谈判。这些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反正我们不欠他们的债,是他们欠我们的债,霸占了我们的台湾[7]。
可以看出,中国这时对于美国要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反应冷淡。与1967年相比,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边界冲突的影响下,中罗关系已大有改善,周恩来对毛雷尔说:“尽管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交换意见是有益的。”[8](P319)然而中国对美国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也包括巴基斯坦渠道)向中国传话不但没有兴趣,甚至似乎还有点反感。原因无非是对美国的诚意和这种方式的效用都持怀疑态度,中国仍倾向于使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级别较低、但两国可以直接对话的渠道,这虽然效率不高,却便于由自己把握。而且美国发现,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条渠道中,中国更愿意接受前者。即便是中罗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也未能使中国偏爱罗马尼亚渠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罗马尼亚渠道仅仅是条“单行道”,即只有信息从美国传过来,却没有相应的信息从中国传过去。
基辛格猜想,中国“可能是担心即使像罗马尼亚这样一个极为独立的国家,也可能受到苏联的渗透。”连他自己也担心罗马尼亚对苏联泄密。他回到华盛顿后,便召见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要巴基斯坦起作用,并建立一条可靠的渠道”。尼克松强调,今后只把希拉利“和我之间的渠道作为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进一步讨论的唯一可靠的接触点”[6](P227)。
尼克松焦急等候渠道那一头的回应,一个月后,他感到,自己亲手建立的三个渠道“所起的作用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快”[5](P161),只好重新求助于中美间早已存在的华沙渠道。他要求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设法与中国外交官直接接触。斯托塞尔费尽心机,终于在3个月后“抓”住一个机会,不顾一切地告诉中国外交官,尼克松总统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出乎美国意料的是,这次中国迅速作出了反应。3天后,中国驻波兰使馆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作客,令美国“大吃一惊”[6](P236)。一下子中美关系“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9]。
中国这次对于美国通过华沙渠道传来的信息反应如此迅速和积极,除了中国这时已做出调整对美政策的决策和更愿意通过现成的华沙官方渠道进行对话这两个主要原因外,罗马尼亚渠道对此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美国在试图恢复华沙渠道的同时,仍继续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频频向中国暗送秋波。虽然没有得到中方的一一回应,却已引起了中方高层的足够重视。11月16日,周恩来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与中国大使张彤谈话一事写信给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8](P334)19日,美国通过罗马尼亚向中国转交了美国著名作家白修德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透露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立场,暗示美国将从台湾撤军。[10]信中同时提出了访华的申请。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米克特为此曾向罗马尼亚政府求助。
当中美之间的这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6](P234)开始一个月后,“突然之间,一切渠道好像都出现了生机”。12月17日,罗马尼亚第一副外长马科韦斯库在华盛顿会见基辛格,“说明了中国对尼克松同齐奥塞斯库的谈话的反应,两人讨论了中国问题。中国人非常有礼貌地听取了谈话,他们说他们有兴趣同西方实行关系正常化。”基辛格分析道:“人民共和国似乎说明了两点:它愿意进行接触,但是不一定通过罗马尼亚这个渠道”,“中国人赋予巴基斯坦渠道以特殊的价值”[6](P239)。
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条秘密渠道中,巴基斯坦渠道明显地更受中美双方的偏爱,作用也更大一些。首先,中国担心使用罗马尼亚渠道可能会带来苏联因素的干扰,中国似乎一直对罗苏关系的状况吃不准,而巴基斯坦就不会让中国有这样的担心。“尽管中罗关系很热,中国却不信任任何东欧的卫星国。北京认为他们都是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包括持鲜明的独立立场的罗马尼亚。”[11]美国原本以为,“中国人宁愿通过共产党中间人同我们打交道”[6](P227),但事实使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人想像得要实际得多。其实,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邻国,人员往来便利,而罗马尼亚远在欧洲,邻国多为华约国家,苏联又是罗马尼亚人来中国的必经之地。最后,“两国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罗马尼亚渠道“太暴露了,风险不可避免地过大,地理位置也太不好了,不适于在最后阶段办理联系事宜”[1](P917)。此后,中美两国虽然继续通过这两个渠道对话,但更多的是使用巴基斯坦渠道。
在1970年的前9个月里,迄今所知的美国惟一一次使用罗马尼亚渠道,是4月下旬基辛格通过罗马尼亚向中国传话,要求冻结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访华的签证申请[12]。6月9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应邀访华,双方主要讨论了中国向罗马尼亚遭受严重水灾的地区提供援助的问题,似乎并没有特意涉及中美关系。
实际上,中国正在酝酿向美国发出一个重大的信号。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在8月再次访华,并在中国国庆节这一天被周恩来特地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成为有史以来惟一享受过如此殊荣的美国人。“这意在向美国表明:中美关系的演变已经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3](P217)可惜,美国没能看出其中的玄妙。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话,不但回答了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多次提出的改换会晤渠道,派遣特使前往北京进行高级会晤的建议,而且提出欢迎尼克松本人来谈判。根据事先的约定,斯诺迟迟没有发表这次会谈的报道。
由于没能理解中国的信号,美国只得继续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向中国传递信息。10月,尼克松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齐奥塞斯库,表示:“我们认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我们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我们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1](P898),并请他转达给中国领导人。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尼克松又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13](P231)。他在祝酒词中,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把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天,为了确保罗马尼亚人领会这个信息,基辛格又遵尼克松之瞩和齐奥塞斯库进行了私下会谈。基辛格重申:“我们很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政治和外交关系。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长期的利益冲突。我们准备建立不受任何外部压力和权威影响的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渠道。”“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想通过你们转告我们什么事情,或你们的大使给我们传递信息,我可以保证,这样的传话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得知。”齐奥塞斯库回答说:“我们将把这次谈话转告中国领导人,如果有什么要传递的消息,我们将像以往一样转告你们。”[14]
11月,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这两条渠道几乎同时把美国的信息传递到中国。罗马尼亚渠道本来有机会在巴基斯坦之前向中国转达口信,因为早在11月12日,罗外贸部长布尔蒂卡就来华访问并会见了周恩来。但可能是齐奥塞斯库认为布尔蒂卡级别较低,不宜参与此事,故还是让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在一周后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时,面交了他致毛泽东的信。勒杜列斯库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和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是十分关切的。尼克松请齐奥塞斯库,如果有可能的话,向你们转告:美国准备通过任何途径,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改善中美关系。美国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科技方面的关系,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周恩来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克松说愿意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恢复会谈,如果他真有解决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谈判。勒杜列斯库说:“如果允许的话,让我这样告诉齐奥塞斯库转告尼克松:你们欢迎尼克松派特使到北京来谈判。”周恩来指出,这不行。这应该是一句完整的话,一定要把前提讲清楚。他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尼克松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15]
得到勒杜列斯库的报告后,齐奥塞斯库即“紧急而秘密地”[5](P465)召驻美国大使博格丹回国,让他把周恩来的口信带给基辛格。1971年1月11日,博格丹向基辛格宣读了周恩来的信件。“这个信息和通过叶海亚传过来的那个信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1](P903)1月29日,基辛格给博格丹以答复,内容和上一年12月16日给巴基斯坦的答复也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信息是口头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的,这表示我们对巴基斯坦渠道更喜爱一些。”[1](P904)3月22日,勒杜列斯库在北京再次会见了周恩来。随后,罗马尼亚人转告美国,周恩来对于同美国对话越来越感兴趣。[16](P524~525)几天后,中国就突然发动了“乒乓外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一下子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终于到了一条道路的终点和另一条道路的起点”[1](P917)。3个月后,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实施了他的“波罗行动”。
在这段半年左右的中美秘密交往的高潮中,罗马尼亚渠道在总体上的作用已明显地逊色于巴基斯坦渠道,但罗马尼亚渠道仍然发挥了某些独特的作用,特别是传递了一些有特殊意义的信息。
首先,周恩来在与勒杜列斯库的会谈中,第一次正式地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访问北京。在这以前,包括对华沙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中国都只表示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北京。而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欢迎尼克松访华,则是在这一个月以后。因而,基辛格称这是个“全新的惊人的提法”[1](P904)。
其次,当博格丹向基辛格当面转达周恩来的上述口信时,基辛格问博格丹,中国的意思是不是要以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来作为同北京建立关系的先决条件。足智多谋的博格丹回答说,虽然他不能随意解释中国方面的意思,但他个人的印象是,“中国总理实际上是建议白宫考虑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折中方式——而不是告诉美国应该做什么。”可以说,罗马尼亚渠道帮助美国理解了在未来的中美高级会谈中,中国对中美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即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塔德·肖尔茨对此评价说:“在这一秘密外交中,罗马尼亚的信息是一个里程碑。”[7](P465~466)
再次,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通过罗马尼亚渠道,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向中国传递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选择这一场合的动机之一,就在于罗马尼亚舞台更容易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从而确保这一信息为中国所知。尼克松的苦心没有白费。1971年3月3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前外相藤山爱一郎时说:中美关系“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引人注目地有所改善”。他已经“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第一次使用中国的正式名称”[8](P441)。
最后,如上所述,从两国元首1970年的白宫会晤开始,美国也开始向罗马尼亚人求教,而且获益匪浅。一名白宫人员后来指出,尼克松从“会见中了解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的想法,比他在早些时候同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的谈话中所了解到的要多一倍。”[7](P463)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克松说这次会晤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13](P231)。如果再加上后来基辛格向博格丹的求教,这时的罗马尼亚渠道就已不再是“单行道”了。
综上所述,在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开通的中美之间的3个秘密渠道中,罗马尼亚渠道虽不是最重要的、作用最大的渠道,却确实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早在1967年就承担了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传话的任务,早于任何其他渠道,“在早些阶段帮了很大的忙”[1](P917)。它和巴基斯坦渠道一起,在1969年帮助恢复了中美间的华沙渠道。在1970年底巴基斯坦已成为中美对话的主渠道之后,仍在中美之间传递了一些重要的口信,促成了美国的“波罗行动”。
罗马尼亚渠道的作用大小主要取决于:(1)中美对改善双边关系的态度及需要。一旦双方都表现出改善关系的迫切愿望并予以实施,就自然要求助于外部渠道。最初的传话是试探性的,罗马尼亚渠道可以适应这种需要。当中美双方已建立起信任,对话变得频繁并准备付诸行动时,巴基斯坦渠道就取而代之。当中美双方已建立起高层接触时,巴基斯坦渠道又让位于中美直接对话的巴黎渠道。(2)苏联因素的影响。苏联因素的加强使中美双方走到了一起,却又使双方在借助罗马尼亚渠道开始对话时顾虑重重,只能更多地使用巴基斯坦渠道。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尴尬。中罗两国因苏联的原因而接近,又因苏联的原因而保持距离。(3)罗美关系与中罗关系。罗马尼亚渠道是在罗美关系迅速发展、对罗马尼亚有着私人感情的尼克松重返美国政坛的背景下建立起来,并在中罗关系达到顶点时发挥作用的。罗马尼亚乐于作为中美和解的渠道,中罗关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如何借助罗马尼亚渠道的问题上,中国更多地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