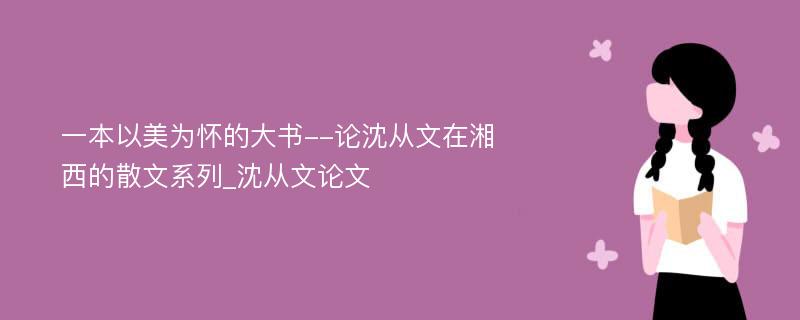
用美和生命孕育的一部大书——论沈从文的湘西散文系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西论文,大书论文,散文论文,生命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系列是其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证了他的这组散文的审美理想、文化意蕴及其在文体意识上的创新,从而得出结论:沈从文的湘西散文是二十年代散文发展最后的又一高峰,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 沈从文 湘西散文 人性 文体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以他那才情横溢、色彩斑驳的小说饮誉文坛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散文创作亦因其对理想和美的渴求,对民族,人生命运的不倦思索和关注以及在语言、风格、文体上的创新面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构成了他创作中的一道奇异景观。当年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刘西渭曾以惊奇的口吻赞叹道:“那个最大的故事,他一直当做背景在烘托的,如今他索性用一本书说他一个尽情,就是这本《湘西》”。[①]虽然50年的时光悄悄流逝,涤荡、湮没了人间无数往事,然而沈从文当年以湘西为背景写作的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等我们今天读来仍是倍感亲切,仿佛在听他讲述一个个娓娓动人的故事:美丽、哀婉而又忧愁。他的这些散文以其独有的审美方式描绘了湘西的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溶入了自己的赤子情怀和对民族命运的不倦叩问,充满了思辨和力量的艺术神韵,构筑了一部奇幻的人生大书,代表了他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招引着我们去捕捉,去研究。
一
沈从文的散文创作集中于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外忧内患、战争频频的苦难岁月,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对当时的时局是颇为忧虑和不满的。他敏锐地感到剧烈的社会变动给中国各地域、各阶层人民带来的冲击和震动,甚至连长期与世隔绝、近乎原始生活状态的故乡湘西也正逐步瓦解着固封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心理结构,为此沈从文的心理情感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这些都在他的这组湘西题材的散文中反映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曾这样描述过自己湘西散文的创作主旨:“这个小册子(指《湘行散记》)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内中写得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②]沈从文面对时代激流的漩涡,在其散文中对湘西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并对民族的历史、现在、未来进行了深层次的严肃思考,客观地再现了中国偏僻地区的历史风貌。
客观地讲,沈从文是毕生尊奉其一再强调的文学家人格独立和文学独立的美学理想的,这就决定了他断然反对把文艺当作政治附庸物的载道文艺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艺术要脱离人生。相反,他却积极评价文艺的批判功能,要求作家深入追寻社会的弊病:“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③]因而当沈从文跋涉、憩息于这块美丽的故土时,他的眼光紧紧盯住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触及到他们的生活、命运及灵魂,时而为他们顽强不息的雄强精神而叹服,时而为他们的保守、自甘堕落而担忧,温情的笔墨下流淌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和无言的哀戚。
湘西属于苗、汉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里本来物产丰富,山岳隐秀,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加之统治者错误的民族歧视政策,导致民族不和,军阀混战,造成了该地区长期的闭塞和落后,《从文自传》便清晰地反映了清末、民初这段时期的社会动荡。这里到处都是野蛮而残酷的杀戮,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统治者经常捕杀苗民,迅即予以处决,每天都达数百人。《清乡所见》、《怀化镇》等文中都详细描写了统治者屠炭生灵、令人发指的暴行,《湘行散记》等篇中也直率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围剿、迫害革命者的不人道行为,确实体现了沈从文对当局者的批判和不合作的态度。联想到沈从文三十年代对国民党捕杀进步人士及文化围剿所持的严正立场,人们有理由认为他在自己的散文中溶进了爱与憎,捍卫了生命及艺术的尊严。
沈从文所处的历史年代,正是中国强权专制制度空前黑暗的时代,“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为其为人”,“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④]严酷的政治现实使昔日的湘西正发生明显的变化,农夫、矿工、水手、寡妇、妓女一个个处于赤贫的生活状态,在社会的最底层拼命挣扎、痛苦地呻吟着,有的失去了原始生命的剽悍和天真,一步步走向堕落。在《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文中,作者精心捕捉到一个镜头:一个老头子水手与乘客讨还价,为一点钱互相谩骂,末了在石上一五一十数着。这同我们在《边城》中看到的翠翠和爷爷的善良、豪爽该是怎样的不同。难怪作者在文章中感慨道:“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着,这人给我的印象真太深了。但这个人在他们弄船人看来,一个又老又狡猾的家伙吧”。马克思曾愤怒谴责资本势力破坏了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使人和人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现金交易,沈从文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但他的这些作品却以艺术的审美方式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湘西的社会现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沈从文还极为关注普通妇女的命运,这是因为中国妇女历来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身上捆绑着四大宗法绳索,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辰溪的煤》中,作者写了一个矿工的天真、可爱的女儿,因被坏人所诱,堕入深渊受辱后自尽身亡,美丽的生命转眼间象一道彩虹,飘散得无影无踪,令人惋惜,然而她的家人都看得很平淡,一切又都如一潭死水。《湘西·凤凰》中更展示了湘西女性受压抑的种种变态行为,她们无法在现实中同相爱的人结合,便在精神的幻觉中同神相恋,最后在人神恋与自我恋情形中消耗其如花生命,衰弱而死。这种原始仪尽管庄严、美丽、然它实则是中国历史上窒息人性、最野蛮、最黑暗的一幕悲剧。沈从文在散文中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若不能在调查和同情以外有一个办法,这种人总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⑤]沈从文透过湘西亘古不变、美丽得让人忧愁的山水看到了正在涌动、变化着的历史潮汐,在二、三十年代的特殊背景下,以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巨大勇气来探究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悲剧和生存、发展的出路,确是难能可贵和令人尊敬的。时至今日仍有少数人淡化沈从文作品的进步因素,说他漠视阶级矛盾,游离于时代焦点之外,这些散文不啻是最好的回答。
二
当然,沈从文不是政治家,他无意也不可能为解决湘西问题寻找到一条正确的政治出路,他心中自有一把理想的标尺,那就是人性,他多年来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⑥]既然巨大的社会变迁给下层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那么沈从文多年所孜孜以求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⑦]也迅速地改变着态势,汇入中国社会艰难行进的合唱当中。沈从文在这组湘西散文中对人性的把握上显然充满了迷惘和困惑,他一方面深深担忧人性美的异化和失落,一方面又从一些人身上看到了人性复归和振兴的希望,恨深爱亦深的矛盾情感一直纠缠着这位湘西水手,面对历史和人生的苍茫与无奈,他一次次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沈从文自从早年离开湘西后,又在一九三三年底和一九三七年两次回到湘西,这虽然不过短短十余年的时间,然而他发现除了青山依旧,河水一仍飞溅、奔流外,他理想中的人性已变得面目全非,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和魅力,未尝不感到深深的失望。尤其在下面一段文字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十六年来竹林里的鸟雀,那分从容处,犹如往日一个样子,水面划船人愚蠢朴质勇敢耐劳处,也还相去不远。但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
——《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沈从文当然无法乐观,文明的侵蚀使得原始蒙昧文化在渐渐解体的同时,童养媳、雇工、卖淫、仇杀等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也正日益显现出来,这使得多年执着钟情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观的沈从文备尝忧伤与痛苦的煎熬。他在晚年的一篇序文中讲到过当年的情感体验:“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⑧]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是憧憬、怀抱着一种纯真和美好的人性观,从湘西走向社会,去读那本人世间深邃无极的大书,幻想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情,用本民族的充满质朴、充满人情、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生活去匡正和改造社会,批判虚伪的都市文明,对民族衰败和道德沦丧满怀忧愤之情。可当他蓦然回首,发现所迷恋的安宁、秀丽、淳朴的“一角小隅”却岌岌可危时,不能不感到惶恐和一种无言的悲伤。他继而在散文中怀着无可奈何的心绪描写了理想王国的轰然倒塌和人性的深度沉沦。在《湘行散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沈从文痛惜地发现曾经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湘西后生竟然“对生存既毫无信仰”,却对名利等发生浓厚兴趣:“这些青年皆患精神上的营养不足,皆成了绵羊。皆怕鬼信神。一句话,完了。”如此严重的精神蜕变迫使沈从文负担起一个过于沉甸的课题:这个民族究竟走向哪里?到底还有没有复兴的希望?如果有,它又在哪里?
沈从文决心继续他的人性探求工作,他是一个有着自己文学信仰和美学观的作家,不甘于看到人性和民族的堕落而放弃对历史所背负的责任,而是希翼人性的完善和复归,以期拯救这个民族的灵魂。他为湘西开出了一剂良药,企图“用作品去燃烧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⑨]从湘西民族中找回那份昔日的光荣与梦想,有时确隐约地感到了某种希望。他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处,面对淙淙的流水和长流千古河水中的沙砾和石子,眺望着蜿蜒连绵的人类历史和苍茫的原始大地,心中难以平静,陡然发现湘西人的生命尊严和崇高:
他们那么忠实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湘西人虽然困苦不堪,然而他们生命中仍不乏坚韧不屈和反抗的火种,他们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也并不逃避生活赋给他们的艰辛和磨难。在走投无路时,他们也能挺身而出,对丑恶势力进行殊死的搏斗,沈从文一再颂扬了他们的这种“划龙船”精神。《箱子岩》一文曾对“划龙船”精神作了很好的解释,他从湘西后生划龙船时个个争先恐后、不与命运屈服的竞技中,感觉到他们不与自然妥协,想出种种办法来支配自然,并在慢慢地改变和创造着历史,并希望他们重新来一股劲,把划龙船的劲头换个方向,来重新安排生活。《五个军官和一个煤矿工人》中着力刻划了一个煤矿工人同统治者抗争,最后跳井自尽的英雄壮举。《虎雏再遇记》里也耐人寻味地安排了一个情节:一个湘西青年被带到都市中接受种种训练,都失败了,只有回到湘西他才重又激起生命的活力。在这种“城市——家乡”的情感模式对立中,沈从文无疑是以一个乡下人的自恋情结来维系自己对生命和人性理想的独特理解的。
毋庸讳言,沈从文寄希望于重振民族理想和人性信仰,要求在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上进行变革,在当时中国社会风云激荡、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局下显然是不合时宜和行不通的,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另外,他企盼的人性理想本身有着明显的偏颇和不足,他竟然错误地认为“生恶性痈疽的人,照旧式治疗方法,可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尽它溃烂,到溃烂净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⑩]这显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守旧心态,他不明白农业文明让位于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必不可缺的一环,人性的变异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或许是难已完全避免的一种现象,他所向往的理想也与都市文化的进程相悖,这就是沈从文的孤独和悲剧所在。但这毕竟不影响他作品中达到高度艺术完美境界所应得到的荣誉,也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人性探求作家所应享有的地位,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就足够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珍视呢?
三
在沈从文的自传体散文《从文自传》刚出版之际,便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不少人把它列为自己当年最喜欢的一种书,他的《湘行散记》和《湘西》也流动着溢人的光彩,是中国现代散文最为成熟的作品之一。这除了内容上的丰富、新奇之外,语言和文体上的创新也是他的这些作品至今仍葆青春魅力的重要原因。
沈从文是很有个性的艺术家,他多年坚持的自由主义文艺观也冲击着陈旧、僵硬的观念:“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11)]鉴于此,他悉心创新,增强文体的自觉意识:“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12)]他的散文已达到相当圆熟的境界,作者也由此获得了“文体作家”、“语言文字的魔术师”的称誉,在现代文学中占据了一个一流的位置。
沈从文散文的语言功力得力于他生活多年的那片故土,也得力于“五四”时代作家和外国作家优秀作品的熏陶。在二十年代创作初期,沈从文的语言并不顺畅,常常文白杂糅,然而经过十年的磨炼,他散文语言的纯熟近乎炉火纯青的地步,散发出沁人的幽香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水手之间的对话简洁、俏皮,寥寥几句便能衬出他们对严酷命运的调侃和不屈:
先生,你着急,是不是?不必为天气发愁。如今落的是雪子,不是刀子。我们弄船人,命里派定了划船,天上纵落刀子也得做事!
沈从文散文的语言也是不拘一格的,常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变化,他有时直接吸收口语,象“把鞋脱了还不睡,便镶到水手身旁去看牌”中的“镶”字,便是当地的方言,用得恰到好处。有时他的语言却又清丽婉转,写得如诗一般,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段深情追忆故土的文字,如烟如缕、令人感到言犹未尽,意味无穷。沈从文的散文有郦道元的凄清冷幽、韩愈的汪洋恣肆,亦有欧阳修的澄澈明净,博采众家于一体,他驾驭文字的功夫是举世公认的。
对文体意识的自觉追求是作家个性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三十年代作家一项重要的收获。中国现代散文脱胎于雷鸣恕吼的“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先驱致力于摧毁封建文学的陈腐观念,一开始尚不能把散文当做一种独立的文体,直到王统照、周作人才把其界定为“美文”,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经过第一代作家的苦心经营,散文的营地终于绽放出蓓蕾,作家的个性也得到了淋漓尽至的发挥,但对散文文体的建设则多有疏忽,导致散文中的议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必然造成其独立审美价值功能的失落。沈从文属于第二代作家,历史的机遇使他完全有可能总结以往经验,恢复散文的审美功能,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创作散文尝试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式,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13)]他的这组湘西散文介乎游记、日记、报告文学和小说之间,在内容上互为表里,用主人公“我”穿插起历史、现在和未来,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翻检时代风云,构成了一篇首尾相连、完整的大散文,但它的许多篇章却又各自独立、互相补充,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主题。例如《一个戴水獭帽子的朋友》侧重于人物形象刻划,象一篇小说,而有时则大段铺叙地方的风土人情,娓娓而谈,给人以丰富地理知识,有些象游记。但大多数时候又抒情与议论并重,不同于一般的山水游记,小小篇幅包容的是一个个重大社会问题。沈从文对众多文体运用自如,这便使几十篇散文在叙事方法和结构上绝不雷同,让人耳目一新。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对文体琢磨最费心力,也可算得上最自觉追求文体意识的一位了。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精神,是继二十年代现代散文发展后的又一高峰,作者细心观察、精心构思,以一支富有才情的手笔绘尽了湘西的世态人情和风云画卷,“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14)]不独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而且在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特定和重要的意义。随着研究视野和学术思想的拓展、解放,随着当代接受者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文化心态的调整,这一点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到,无情的历史终将证明一切。
注释:
①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集〈湘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⑧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③⑨沈从文:《废邮存底、元旦日致〈文艺〉读者》、《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⑤沈从文:《湘西·辰溪的煤》。
⑥⑦ (11)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
⑩沈从文:《湘行散记·箱子岩》。
(12) 沈从文:《从文自传·附记》。
(13)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273·一首诗的讨论》。
(14) 沈从文:《从文自传》。
标签:沈从文论文; 散文论文; 人性论文; 沈从文边城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湘行散记论文; 从文自传论文; 边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