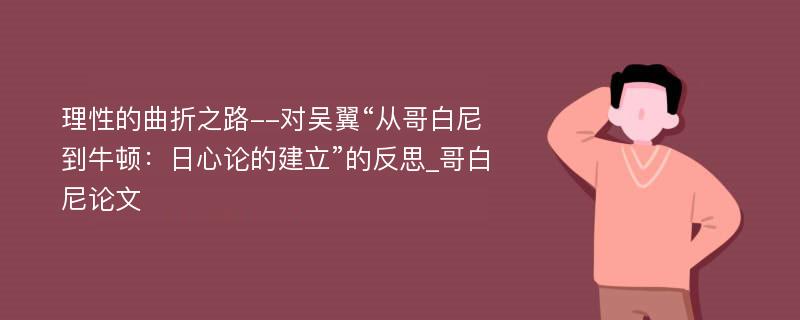
曲折的理性之路——反思吴以义的《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白尼论文,之路论文,学说论文,曲折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以义:《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ISBN:9787208116382。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15)02~0222~10 修回日期:2015-04-04 1 科学史研究的楷模 从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到牛顿(Issac Newton)时代的天文学发展决定性地引导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方向,其过程汇聚了各种社会、文化和认识论因素,最能展现近现代科学实践的一般性特征。它是科学史教科书与科普读物中绕不开的主题。同时,由于这段历史无论是技术细节还是理论发展中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诸多疑问,它一直是科学史专业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教科书与科普读物的优势是通俗易懂,却失之肤浅和简单化。而科学史学术研究常因其专业标准而无法照顾到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雅俗共赏和深入浅出虽是科学史的理想目标,实际做起来却是谈何容易。吴以义先生的近作《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可谓能达到此理想目标的极少数中文研究之一,其宗旨和方法均堪为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楷模。 一方面,本书对当代西方研究成果予以条畅通达的综合性解说。另一方面,又能紧扣原始文献来分析科学家们论证的内在理路,最能探窥其中的委曲隐衷。与此同时,还不忘考察事件发生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巧妙地把科学理论的发展放置在科学家们在实践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因而,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本书可谓内外兼修。而且,行文优雅老道,表述理论内容时清晰严谨,讲述科学家们的奇闻轶事和心理状态时则妙趣横生,使读者恍如阅读说部传奇。在内容上,全书总共7章。第1章讨论了哥白尼时代之前,影响天文学发展的4个重要因素:一是建立在直接经验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自然观;二是在中世纪极为流行的把科学看成为宗教婢女的观点;三是天文学研究中的机械化处理方法对天体运动的模拟、以及这种模拟与数学模型之间的关系;四是以托勒密理论为例展示建构数学模型以预测天体运动的方法。这4个因素合起来,构成了哥白尼进行天文学工作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以及文化宗教方面的背景。第2章讨论了哥白尼理论从《提要》到《运行论》的发展过程,以及之后在欧洲尤其在维滕堡的影响,展示了国外哥白尼研究的最新成果。第3章讨论第谷(Tycho Brahe)的天文学成就。第4章讨论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开普勒的著作一向以晦涩著称。本章以清晰的表述重构了《宇宙的秘密》和《新天文学》两书的论证结构,是目前国内对开普勒理论最成功的研究。本章与第2章堪称全书最精彩的两章。第5章讨论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对日心说的辩护。第6章展示了力学从笛卡尔(Rene Descartes)开始,经过巴斯卡(Blaise Pascal)、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到胡克(Robert Hooke)的发展。第7章解释了牛顿如何用引力概念阐释日心说的运作机制。全书用40万字把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脉络条理清晰地梳理出来,毫无科普读物的简单和肤浅,凸显了作者超强的深入浅出的功力。 当然,无论多么精细的历史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地把握历史的复杂性。所谓“细视大者不尽,大视细者不精”。科学史研究本来就是用有限的篇幅在精与尽的两难中平衡取舍。求“尽”以希展示事件发生的大趋势,求“精”以保证理解事件细节的可信度,这实在是难以两全的要求。本文想讨论吴先生书中所涉及又未被说透的三个问题。讨论过程难免有苛求精尽之嫌,所谓春秋责备贤者。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中世纪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关系;(2)中世纪末期数学的社会地位与自然哲学的关系;(3)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验概念的转变。 2 亚氏自然哲学在中世纪后期的微妙地位 先看第一个问题。吴先生在第一章第一节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及其基于常识之上的经验方法之后,又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介绍了亚氏宇宙论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下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即著名的科学是神学的婢女说。正是自然之书与上帝之书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使得有着异教来源的亚氏自然哲学在经过基督教化之后,在中世纪占领主导地位。而日后日心学说的成长历史也正是对这个自然哲学体系反叛的历史。我对此并无异议。我所想要提出的问题在于,第1章第一、二节的介绍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中世纪的基督教自然哲学家们的确尊崇亚氏的自然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接受亚氏的看法。由于亚氏的异教背景,质疑他的学说在中世纪后期极为正常。而这种质疑也为日心学说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吴先生似乎只强调了尊崇的一面,而对质疑的一面估计不足。 随着12世纪阿拉伯和希腊文献被翻译为拉丁文,亚氏自然哲学在中世纪西欧的大学中获取了主导地位。但亚氏自然哲学中的一些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存在着冲突。尽管许多神学家和艺学师们热烈地钻研并传播亚氏学术,一些保守的神学家开始担心亚氏思想中与基督教教义冲突的地方会引起不利的后果而丧失神学婢女的作用。吴先生举了12世纪后期法国西铎修道院的修士阿兰(Allain)以婢女说的态度推崇希腊文化中理性主义的例子[1]。然而,13世纪之后,在巴黎大学及其周围发生了一系列反对亚氏学术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1277年大谴责”(the condemnation of 1277)[2,3]。 这个谴责质疑了亚氏自然哲学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在亚氏看来,世界是永恒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这与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世界的看法相冲突。①同时,亚氏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一些原则在基督教看来则是对上帝的绝对全能的否定。比如,亚氏认为虚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虚空中物体的下落速度是无穷大,这会造成该物体同时处于两个位置的逻辑矛盾。但在神学家们看来,万能的上帝完全可以创出有广延的虚空,物体在其中可以以一定速度运动。再比如,亚氏的宇宙论认为世界由月下界和月上界组成,月上界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东西,否则月上界之外就会存在虚空。而基督教神学家们则认为上帝只要愿意,就有能力在月下界和月上界之外创造出其他世界。另外,上帝同样有能力使得天体不作匀速圆周运动,而作直线运动。 谴责与质疑无疑会限制亚氏思想在中世纪的继承,因为在自然哲学原则与神学原则冲突的时候,它们会提示自然哲学家们需要使前者服从后者。然而,1277年的大谴责也并非只起到消极作用,它以一种颇为微妙的方式使得自然哲学家们对亚氏思想的继承与利用更为开放与自由。中世纪科学史家爱德华·格兰特(Edward Grant)指出中世纪自然哲学家们即使把亚氏当作的权威,也因为大谴责这类质疑的提醒,并不独断地把他当作不可怀疑的权威。对亚氏理论的偏离被认为是正常的。十六世纪开始的新宇宙论中的许多重要因素其实都缘始于这些偏离[3]。这些偏离鼓励人们对亚氏理论中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反事实的方式(counterfactual)进行想象和思辨。比如,如果恒星天之下的所有物体都被上帝摧毁,那么,月上界的空间是否会出现虚空?在虚空中一个物体是否能够作直线运动?如果上帝创造了其他世界,这些世界是连续存在的还是同时存在的?它们是如何分布在空间中的?它们是同中心的还偏心的?对想象的、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情况所做出的思辨是一种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依赖思想实验而不是直接观察进行研究,是中世纪后期自然哲学与亚氏自然哲学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对亚氏思想的偏离和使用思想实验所进行的思辨为16世纪、17世纪的科学革命提供了实质性的资源[2~6]。 我们不妨看个与本书相关的例子。哥白尼的日心说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地球绕轴做周日运动[1]。这个命题与亚氏的地球是静止的宇宙中心的看法相矛盾。格兰特指出,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对该命题的辩护没有超出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布里丹(John Buridan)和奥雷姆(Nicole Oresme)对相对运动的思想实验所作的讨论[2,4,7]。格兰特让我们看到布里丹和奥雷姆等人对亚氏自然哲学的偏离造成了中世纪自然哲学家们对亚氏思想的开放态度,这是理解日心说建立过程中颇为关键的一点。但由于吴先生仅以婢女说来说明中世纪基督教与亚氏自然哲学的关系,不免忽略了这个关键点。我们来看三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吴先生如果看到这个关键点,就能对相关事件做出颇为不同的解释。 第一个是对托勒密模型的刻画。吴先生从数学天文学凑合现象的特点出发,把托勒密模型看成“是对亚氏原理的具体化和精细化。对于托勒密来说,球形宇宙,地球处在宇宙中心,以及天动地不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套完整的描述”[1]。然而,吴先生的解释未注意到的是,托勒密模型在对亚氏原理具体化和精细化的过程中,为了凑合现象,也偏离了后者。托氏模型中偏心圆和本轮的介入意味着天体可以围绕着不同的中心运转,这超出了亚氏原理所允许的范围。[2]这个偏离是由于数学天文学而非神学的要求。但正是因为在基督教的氛围下,中世纪自然哲学家们无须完全接受亚氏原理,他们可以对这个偏离采取暧昧和宽容态度。在意识到这个偏离之后,少数自然哲学家如罗杰·培根(Roger Bacon)倾向于否定托勒密模型,但在他之后更多人则愿意接受它[3]。他们容忍这个偏离,一方面表示出对亚氏原理的尊重,另一方面允许数学天文学家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凑合现象,并等待日后的技术性变化可以消除亚氏原理和托勒密模型之间的冲突。对偏离亚氏原理的宽容,使得托勒密可以自由地把偏心圆和本轮-均轮模型变为偏心均速点模型,也使得哥白尼在提出日心说模型时,一些同时代的自然哲学家们只把它看成为一个与托勒密模型竞争的新的数学天文模型,而并未看出它在物理学和宇宙论上的颠覆性后果。 第二个例子是吴先生对哥白尼的《提要》的目的的解释。吴先生指出,《提要》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只使用匀速圆周运动而无需偏心均速点的模型。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天体的匀速圆周运动是亚氏宇宙论所要求的,吴先生认定:“哥白尼当时耿耿于怀的,正是要在整个宇宙图景中系统地、彻底地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正是为了把亚里士多德的原则严格地、不变形地贯彻到底,哥白尼认为,托勒密模型必须作重大修正”;“哥白尼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理论家,他所关心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完美要求如何能在天体运行的理论中得到完美的贯彻”[1]。如果在这些表述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和“亚里士多德的完美要求”仅指匀速圆周运动,则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读者在这些表述中读出哥白尼想使自己的模型要比托勒密模型更加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或亚里士多德主义,则是令人怀疑的。我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吴先生自己会认同这种令人怀疑的读法,但吴先生的表述如果不作出更进一步的澄清,的确会引发读者以这种读法来理解吴先生的表述。需要向读者澄清的是,尽管匀速圆周运动的确是亚氏宇宙论所预设的,但对它的采用并不意味着哥白尼比托勒密更加倾向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提要》中围绕着日心说所提出7条假设都可以看作是对亚氏原理的偏离[1]。我们在上面看到,中世纪后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当开放,对亚氏原理辩护和偏离在当时都属司空见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哥白尼的工作是为了帮助亚氏的宇宙论。他不认同托勒密的偏心均速点模型,而试图运用匀速圆周运动或常规运动来建构一个不同的模型,更有可能是因为数学天文学的而非物理学或宇宙论的原因。一旦有机会使用匀速圆周运动来凑合现象,对于一位数学天文学家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 第三个例子是吴先生对第谷发现彗星的解释。吴先生说: ……如果从思想的发展上考察,第谷在这儿发动的是一场革命:通过引进造物主的创造,第谷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上天无始无终的基本假定,上帝打破了永恒。上帝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可以造他想造的东西,而他的大能,绝非是作为受造之物的人所能真正知晓的。([1],179页) 如果我们从格兰特所给出的中世纪科学思想的发展上考察,第谷的这场革命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如造物主的引入,对亚氏永恒宇宙的否定,上帝无尽的难以被人知晓的创造力等,其实从1277年的大谴责就已经开始经常出现于自然哲学家的讨论中。第谷的创见是发现了彗星,并利用这些为人熟知的因素为他对彗星的解释提供了理由。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为自然哲学家们所熟知,第谷对彗星的解释并不那么令人惊讶,只不过出现了一例新证据,支持了自然哲学家们对亚氏宇宙论旧有的质疑而已。 总之,中世纪基督教接受亚氏自然哲学的过程并不是婢女说直接应用的结果,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对亚氏自然哲学的开放态度对日心说的形成与成长至关重要,而吴先生对此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3 数学家们的社会地位与实在论说明 同吴先生商榷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哥白尼日心说产生时外在社会因素对数学与自然哲学之间关系的影响。对于这个关系,吴先生正确地指出,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看来,托勒密和哥白尼的数学天文学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数学天文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凑合现象,即用数学关系来表征天体的空间关系和运动规律,然而,对表征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天体运动的真正原因并不给出说明,对天体的属性和运动的原因给出说明是自然哲学和物理学的任务。鉴于这个区别,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和维滕堡的自然哲学家们对哥白尼日心说给出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日心说模型只是一个计算和预测工具,模型的数学结构并不是宇宙的真正结构,只有自然哲学家或物理学家才有资格来讨论宇宙的结构[1]。 我赞同吴先生对数学和自然哲学之间关系做出的这些观察,我想补充的是,这个关系除了两个研究领域的学科特征的维度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性维度,即数学家和哲学家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这个社会因素也对日心说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科学哲学家嘉丹(N.Jardine)指出,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就是打破数学天文学和自然哲学的区别的过程。如果说奥西安德和维滕堡对哥白尼模型的解释还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个区别,那么,第谷对彗星的报告就是对这个区别的直接打击,而开普勒的研究则即是数学的又是物理的[8]。打破区别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双重革命,一方面在学科的维度上要以实在论而非工具主义或非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不同的天体模型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上,数学家要冲破社会阶层的限制才能去讨论自然哲学或物理学的问题。后一重革命并不比前一重更容易,因为在中世纪后期,数学家的社会地位远低于自然哲学家的社会地位。 最早阐明这个社会性革命的是科学史家韦斯特曼(Robert S.Westman)。他在研究哥白尼理论传播史时发现,数学家的社会身份深刻地影响着传播过程[9]。②哥白尼认为自己的理论可以说服数学家,就像说服雷蒂库斯(Joachim Rheticus)那样。但从1543年到1600年间,接受哥白尼理论的人不到10位。一个原因是当时纯粹的理论数学家并不多。在16世纪欧洲的大学里,数学是艺学院中的初级课程,只学成数学不会找到很好的工作。数学教师的收入要比其他学科的教师的收入低。单纯数学家的工作一般是技术性和工程性的,如编日历、制作计算和测量仪器、丈量土地、制造武器、修筑城堡等。而其他学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数学。最受欢迎的是法律、神学和医学。这些专业都需要在修完艺学院的基础课程后,继续在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中深造才可获得。哥白尼自己就获得法学和医学学位,而开普勒则获得神学学位。实际上,《运行论》出版后50年间关注过哥白尼理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纯粹数学出身的。以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些人为例:奥西安德是神学出身;佩德鲁·拉摩斯(Petrus Ramus)是神学出身;朱利安·斯卡利吉尔(Julian Caeser Scaliger)是医学出身;鲁汶大学的吉玛(Frisius Gemma)是医学教授;维滕堡的马兰克顿(Philip Melanchthon)是全才,兼通法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他的两个关注哥白尼理论的门人瑞因霍德(Erasmus Reinhold)和波瑟(Casper Peucer)都在大学任管理职位,绝无可能仅是数学出身。可以说,数学在当时的社会中被看成是一种为其他学科服务性的基础技能。由于数学在学科上的限制和数学家低微的社会地位,当反对日心说的人声称哥白尼精于数学却疏于物理或自然哲学时,数学天文学家们仅用自身的数学资源难以做出辩驳。因此,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最初50年的传播史中遵循着这样一种式样:反对者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辩护者则集中于赞扬其数学技艺的精湛,尤其是用匀速圆周运动替代偏心均速点的成就。这也就是奥西安德和维滕堡解释的基本策略。 唯一用实在论的方式来解释哥白尼理论的是雷蒂库斯,他也是日心说早期接受者中唯一一个纯粹数学出身的人。他性格叛逆、狂热、对科学无比执着。考埃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把他比作布鲁诺(Giordano Bruno)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1]。他终身从事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只在中年之后才旁骛于少年时就已心仪的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这在哥白尼理论早期传播史中是个异类。按照韦斯特曼的解释,这种与社会常规相违的行为和性格,当是因为雷蒂库斯14岁时父亲被砍头的惨痛经历所引起的心灵创伤所致[12]。正是他与哥白尼用实在论的方式来理解日心说模型的尝试,引发了数学天文学家们以数学的论据涉足自然哲学和物理学领域的艰苦过程。雷蒂库斯晚年曾对门生说,如果自己当年没有去拜访哥白尼,哥白尼的任何著作都不会被人知晓[12]。尽管有狷狂之嫌,却也绝非无稽之谈。 数学天文学家涉足自然哲学和物理学的努力受到了两个事件的帮助。一个是马兰克顿(Philip Melanchthon)在维滕堡的教育改革逐渐被欧洲其他大学借鉴,使得欧洲各大学提高了对数学的重视。在意大利,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对耶稣会罗马学院的课程改革要求自然哲学学位必须把数学当作必修课,并允许数学老师也能像自然哲学老师那样参加讨论课。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数学家们的社会地位,尽管无论受新教影响的维滕堡还是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都无法接受对哥白尼理论的实在论解释。第二个事件则对日心说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宫廷天文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的产生。它使得第谷和受其荫庇的开普勒能够毫无顾忌地以实在论的方式讨论自己的天体模型。 在伽利略以数学家的身份开始其研究生涯时,意大利数学家们的社会和学术地位仍远低于自然哲学家[13]。科学史家比亚乔利(Mario Biagioli)描述了伽利略为了将自己的数学家身份转变为哲学家所做的钻营活动[14]。1588至1610年间,伽利略作为应用数学家在锡耶纳、比萨和帕多瓦大学教授数学、天文学、力学和筑城学。他的工资是自然哲学教授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为了获得额外收入,他担任私人教师,并制作一些数学、天文和军事仪器出售。1610年他把《星际信使》题献给麦迪奇公国的大公考斯莫二世,并把通过望眼镜观测到的木星的四个卫星命名为麦迪奇星。这一趋炎附势的举动改变了他的生涯,使他一跃成为宫廷哲学家和数学家。伽利略对哲学家的身份极为珍视,因为只作为数学家,他无法与经院自然哲学家们进行平等讨论。这个哲学家兼数学家的身份为他以实在论的方式讨论日心说提供了条件。同时,他也要求其他的自然哲学家们以数学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因为自然之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这种态度革命性地改变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数学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的区分,将科学革命引向了成功的轨道,尽管也给伽利略带来了个人悲剧。 4 经验概念的变化 同吴先生商榷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日心说确立史中经验概念变化的一个细节。全书一条重要的线索是经验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中经验的概念也产生了重大改变。吴先生认为,在伽利略的研究方法中,经验受到理性的指导,这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中立的经验概念: 伽利略强调,在对自然的探索中,理性占主导的、主动的地位,而感觉不再是研究的出发点。这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正恰反对,构成了对科学研究的真正的革命。在伽利略看来,亚氏意义上的不带目的的“看”,对于看见的东西兼收并蓄地接受,把感觉当作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可靠的源泉,并不能深入自然的本质,人的认识必须跨越这一障碍……“依照哥白尼的方法,一个人必须否定自己的感觉”。([1],335~336页) 伽利略以理想化的数学模型来说明物理现象的研究方法的确使得伽利略的经验概念与亚氏的经验概念相比更被理论和理性“渗透”。然而,我想指出的是,伽利略的经验概念实际上要比吴先生展示的更为复杂,它一方面是近代科学的经验概念的先导,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脱离亚氏经验概念的局限。 科学史家迪尔(Peter Dear)曾指出,亚氏的经验概念中起码有三个方面被日后的近代科学所取代:第一,经验是可用全称陈述来表达的具有普遍性的事实;第二,经验是一切正常人无须特意搜寻就可感知的事实;第三,经验因其无可争议的确定性相当于数学中的公理,因而可成为自然哲学中演绎论证的前提。而在近代科学中,经验则变为只能用特称陈述表达出来的、在某特定时刻以某种特定方式获取的特殊的经验。科学中所用的经验常常不是普通人轻易就能感受到的,而是观测者必须经过相应的训练,精心矫正自己的感觉之后,通过精密的实验仪器获取的、平常极难观察到的现象。同时,这种经验不具备绝对的确定性,只能在归纳性的推理中作为支持理论的证据,而这种支持是可错的。[15] 经验概念的这种变化对日心说的最终确立也是决定性的。天文学研究传统与亚氏的经验概念最能相互契合。天体运作规律的变化对人来说是细微而漫长的,因而对天象的观察无法建立在个人特殊的经验之上,只能是众多天文学家们长期观测的结果。伽利略对望远镜的使用挑战了这种经验概念。只有少数技能出众的仪器制作者才能制作出合格的望远镜,即使拥有一部合格的望远镜,如不具备足够的学识与能力,也难以看到伽利略所看到的现象。吴先生敏感地意识到望远镜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后果: 的确,日心图景既不是一种归纳的结果,又不是一种演绎的结论;而与之相关的观测,从对象上来说并不是日心体系本身,从手段上说也不是感官所感知的、可以把握的感觉,而是望远镜所提供的间接的信息。([1],316页) 实际上这种间接的信息正如迪尔所分析的,已不是普通人都可拥有的直接的感觉经验,而是通过精密仪器获取的、并需要观察者特殊训练之后才可获得的观测结果。这无疑已经具有近代科学的经验概念的涵义了。当牛顿把日心说安置在他的力学体系中的时候,所有力学现象包括对天象的观测,从本质上来说都变成了以特定仪器获得的特殊经验。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伽利略本人对经验概念与其说是近代科学的,毋宁更加接近亚氏的概念。他对望远镜观测结果的描述并没有记录观测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没有对观测仪器的具体特征的描述。在他看来,所描述的现象“对我们的视觉说来是如此直接和明显,而无需任何推理的帮助”。[15]因此,他的描述更像一组表达普遍性事实的全称陈述,而并非描述特定观测或实验结果的特称陈述。迪尔举出一系列文本证据,表明伽利略有意地强调自己所描述的观测现象是任何人都能够很容易地看出的。反倒是他的论敌耶稣会士夏纳(Christopher Scheiner)在描述自己对太阳黑子的观测时,给出了具体的观测细节,以便证明望远镜中看到的太阳黑子是之前从未观测到的现象。[15] 吴先生认为伽利略之所以在用望远镜观测月球时未能给出具体观测的时间和方位,是因为伽氏的观测不过是“看看”,并未带有明确的哲学或天文学指向研究的目的。[1]这个解释略显肤浅,而迪尔和夏平(Steven Shapin)的解释就更为合理。按照他们的解释,伽利略进行科学讨论的主要对象都是经院科学家。他们无论在经验概念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因此,伽利略不得不把从望远镜中获取的观察结果: 【安】置于按亚里士多德方式解说经验在哲学研究中之适当作用的概念框架内。【他】是这样实现这一点的:通过运用广泛的社交技巧和语言技巧,赋予这类独特经验以确定性的氛围,这种氛围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实践而言是必要的,这包括列举可信的目击者的名字、公开展示中肯的专家意见,以及运用精心设计的促使经验陈述看起来像是无可争议的公理的叙述技巧。([16],81页) 也就是说,望远镜的使用即使带来了革命性的经验,伽利略也不得不在亚氏范式(Aristotelian paradigm)中以特有的方式讨论这个经验并为其革命性的结果辩护。换言之,他的经验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真正抛弃亚氏经验概念的是更具经验主义倾向的胡克、波义耳和牛顿等科学家们。他们在研究力学的各种现象时,使用仪器获取实验数据,而这些数据为他们的力学理论提供了可错的经验支持,而不是像亚氏的经验那样需要成为自然哲学中演绎论证的前提。 总之,本文所探讨的三个问题,即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关系、数学与自然哲学关系的社会性维度,以及经验概念的变化,并不是想说吴先生书中有任何错误,而只是想提醒读者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吴先生认为日心说确立的历史“最终彰显了理性在人类认识世界中的地位”,书中的主要人物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都试图用理性来解释自然现象。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观察。本文无意对其中的理性发展做出全面的讨论,也无法考察全书中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而只想通过两三个例子来提醒读者,在这段历史中理性的发展是复杂和曲折的。不仅理性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研究传统中会有重大的变化,那些一向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因素,如社会、文化、政治和心理等因素也会影响理性的运行,甚至主导理性的发展方向。吴先生当然已注意到这些因素,只不过就像我曾经提到那样,科学史家不免要在精尽之间作出两难抉择。对于日心说确立过程的诸多背景因素,为了避免叙述和讨论时的枝蔓,吴先生必然要做出取舍。本文就是对未被吴先生注意的一些背景因素略作申说,以展示一旦重视这些因素,我们会对相同的历史过程形成更为丰富的理解。 注释: ①吴先生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冲突。他说:“一方面,哲学家对于因果关系的存在性和可认识性反复诘难,另一方面,神学家又断然拒绝亚氏的自在自为无始无终的宇宙。然而当把这两个极端的困难放在一起考察的时候,中世纪的学者发现,他们可以一石二鸟,一举同时解决这两个困难,获得更加高妙更加完美的图景。”([1],23页)吴先生接着解释,这个一石二鸟的解决方式就是婢女说。我在这里想展示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对这个冲突的解决,远比婢女说要来得复杂。 ②韦斯特曼的这篇文章已被更多的学者看作研究科学革命的经典文章。爱丁堡大学的科学史家约翰·亨利(John Henry)在为一部科学革命史文集所写的书评中特别指出,如果是自己编选该文集,将会入选韦斯特曼的这篇文章([10],346页)。标签:哥白尼论文; 伽利略·伽利雷论文; 托勒密论文; 自然哲学论文; 日心说论文; 伽利略望远镜论文; 牛顿论文; 数学文化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论文; 数学论文; 数学家论文; 宇宙论论文; 中世纪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牛顿力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