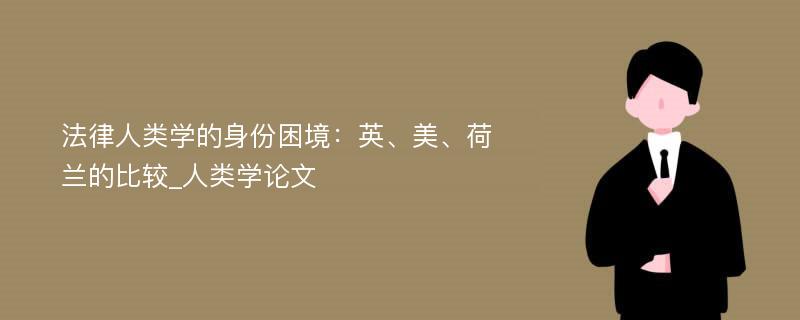
法律人类学的身份困境——英美与荷兰两条路径的对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兰论文,人类学论文,两条论文,英美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法学努力借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背景之下,法律人类学在中国似乎是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但是,当我们环顾海外,此项研究在不同的国家中却有着不同的现状和遭遇。一直为我国学者所引介的、有着百年发展史的英美法律人类学,在20多年前就出现了生存危机。据美国学者克里斯·富勒(Chris Fuller)的观察,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毫不在意地将这个分支领域抛诸脑后,遗忘了那些经典民族志,忽视了新兴作品,不再进行法律研究了”。①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作为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下属协会,政治与法律人类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同样“面临着成员过少的危险”②。
不过,近几年来,安妮·格里菲斯(Anne Griffiths)、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萨利·安格尔·梅丽(Sally Engle Merry)等人所进行的研究,③表明法律人类学的英美进路似乎并未就此终结。但与之相比,荷兰的法律人类学却显得更具活力。目前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法律人类学的国际机构——法律多元研究会(The Commission on Legal Pluralism),便挂靠于荷兰的莱顿大学,由该校范·沃伦霍芬(Van Vollenhoven)研究所的珍妮·尤宾克(Janine Ubink)博士担任执行秘书,其会长则是来自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马丁·巴文克(Maarten Bavinck)教授。除此之外,奈梅亨大学、瓦赫宁根大学在该领域同样有着较强的实力和研究传统。
仔细分析目前比较活跃的几位荷兰学者的知识和职业背景,可以发现他们大多接受的是法学教育,主要供职于法学院,换言之,当代荷兰的法律人类学似乎是法学家的专属领域。那么,法律人类学的兴衰,与研究人员的职业背景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联系?人类学研究法律的进路和作品,在何种情况下会被法学界接受或排斥?什么是法律人类学?它究竟是人类学或法学的分支学科,还是二者的交叉领域?正是基于上述疑问,本文试图通过对英美与荷兰这两条法律人类学研究路径的梳理和对比,来探讨此项研究的定位问题,并以此对当代中国法律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
一、英美路径:人类学的分支领域
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在西方人所发展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这两套知识体系中,法学一直占据后一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直到近代社会科学在19世纪的兴起。④虽然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在学院体制内对法学的地位造成了冲击,但在对法律问题的学术研究上,法学的垄断地位依然不可撼动。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理查德·埃贝尔(Richard Abel)所说,“法律是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对于新手来说有着许多晦涩的词汇”。⑤其他社会科学想要介入到这一领域,必然要充分考虑法学的话语权。而人类学作为19世纪末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在其最初涉足法律问题时,也面临着这种遭遇。
(一)人类学的突破
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历史即“由众多的参加者为占领和确定一个激烈竞争的、但从未明确限定而且松散的实践领域所进行的持续的斗争”。⑥20世纪初,现代人类学各分支领域的创立,也是如法炮制,而对“他者”社会进行了资源切割。研究经济就是经济人类学,研究宗教就是宗教人类学,研究政治就是政治人类学。所以,这些分支领域建立的标志在于研究对象,而并非独特的方法。比如,经济人类学在当时并非指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经济,而是指人类学家研究他者社会的经济。这也决定了它们在创建伊始就属于人类学的分支领域,而并非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
法律人类学也不例外。但是同其他分支领域比较起来,无论是影响还是地位,法律人类学都显得非常尴尬。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和亲属制度研究被并称为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二战之后,心理人类学也发展成了一门分支学科。⑦而法律人类学的学科建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由劳拉·纳德(Laura Nader)等人提出。法律人类学的起步为何艰难?
随着近代西方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全球殖民扩张,进化论的观念为西方法律的自我表述提供了一个时间性的阶序——法律是从非理性、实质理性到形式理性的进化过程。而形式—理性的“法律科学”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独有的标志性特征。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亨利·梅因(Henry J.S.Maine)的法律进化论之中。易言之,在西方法学的视野中,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亲属等社会现象不同,它是高等社会才有的一种制度安排,并不具有普遍性。因而,土著人的“原始社会”根本就没有法律。现代人类学在进行学术资源切割时,充分考虑了法学的意见,并没有理会法律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律人类学的难产。
人类学与法学毕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对象:一个研究土著社会,一个研究西方社会。不过,长达两年的田野实践,与土著居民的朝夕相处,也让一位人类学家开始怀疑西方法学的传统观点。这位人类学家就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没有警察和监狱,为什么人们还要遵守规则?没有法庭和法官,一旦有了纠纷如何解决?”⑧这些问题让身处特罗布里安德群岛的马林诺夫斯基感到非常好奇。因为在他的知识背景中,人们只有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中才会遵守法律。那么,什么是法律呢?除了国家法之外,法律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在此种反思的基础之上,马林诺夫斯基拓宽了法律的定义,承认了土著社会也有其特殊的法律。这就为该领域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标志着现代法律人类学的诞生。
(二)来自法学的帮助
法律的定义是宽泛的,他者社会也有法律,因此人类学可以将法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彰显了法律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合法身份。明确了研究对象,随之必然会面临着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人类学已经突破了法学关于法律的定义,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人类学面对法律毫无经验可言,必需从法学那里寻找灵感,汲取经验。而这一尝试是由霍贝尔(Adamson Hoebel)与卢埃林(Karl Llewellyn)合作完成的。
1930年,霍贝尔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拜在人类学泰斗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弟子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可是当他确定论文选题——美洲平原印第安人的法律制度——之时,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都表示对这一领域并不了解。正当霍贝尔因为找不到一位法律人类学的指导教师而犯愁时,博厄斯把他引荐给了同校法学院的法理学教授卢埃林。⑨霍贝尔的主要困恼在于,如果印第安土著的科曼契人(Comanches)的“法律”就是习惯规范,那么如何研究这些不成文的规范呢?而在卢埃林看来,虽然印第安人缺乏西方社会的成文法,但是同样存在纠纷及惯常的解决方式,而这种纠纷解决的过程与西方的审判程序类似。因此,卢埃林把英美法学中的案例研究方法介绍给了霍贝尔,并以指导教师的身份帮助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也开始了他们长达近30年的合作。⑩
两人最为成功的一次合作,无疑是1941年出版的《夏延人的方式》一书。(11)这次合作被称为法律人类学领域跨学科合作的首次典范。他们将英美法的案例研究,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发展成为个案研究分析方法,成为此后这一领域的标准方法。(12)在很多法学家看来,这部著作也是法学送给人类学的一个礼物。(13)但是从人类学的角度,也可以视为法学对人类学的入侵。
(三)人类学试图自立
20世纪60年代初,哈特(Herbert L.A.Hart)将语义分析哲学引入法理学,标志着英美法学的分析实证倾向日益严重,而人类学在同一时期却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欧陆诠释学哲学的影响,逐渐向人文学科方向转型。这种分歧导致了二者之间唯一的沟通领域——法律人类学的地位愈发尴尬。劳拉·纳德(Laura Nader)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不无担忧地指出,“法律的人类学研究至少在主要的方面,并没有对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产生影响,就像亲属制度和语言研究那样。在《今日人类学》、《当前人类学》、《人类学双年评论》中鲜见法律研究的作品。”(14)作为人类学分支领域的法律人类学,一直使用着法学的研究方法,很难获得主流人类学界的认可。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以纳德为代表的一批美国人类学家,试图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他们把纠纷处理的方式和过程分为“纠纷处理过程”(Processing)和“纠纷过程”(Processes)。(15)前者主要关注产生出结果的大体已经标准化了的程序,仍然是双方当事人分居两边,类似于法官的第三人居中裁断或调解,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出来作证或反驳,纠纷的处理结果主要依赖于习惯法规则。这与英美法中的法庭案例并无二致。与之相比,“纠纷过程”则强调在冲突的程序中审视社会关系,尤其关注于将纠纷纳入公众“竞技场”之前的“怨恨阶段”(Grievance Stage)。(16)纠纷发生之前,双方当事人有着何种关系,这对纠纷有何影响?纠纷发生之后,面临公众之前,双方当事人会运用何种社会资源选择何种解决方式来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纳德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可惜诸如此类的作品凤毛麟角,(17)绝大多数研究仍然只关注于中间的“纠纷阶段”,依旧徘徊于法学式的案例研究之中。
(四)人类学的转向
“人类学是对文化差异的意义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18)“他者”(Other)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法律人类学更是依赖于对他者的研究。但是随着二战之后非洲等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人类学家们已经很难再次踏上这些土地了。人类学的兴趣在于发生了什么,在于如何去描述这些变迁以便于理解其中的意义。他们不太关心新兴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并不试图“达到一个真正的国家法”。(19)因而,传统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对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并无用处。
失去他者,对人类学传统的几大分支领域都造成了影响,但对法律人类学的冲击似乎更为严重。这正是科利尔(Jane Collier)所认为的法律人类学衰落的首要原因:成立得太晚。“法律人类学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提出来,大多数从事这门专业的学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取得学位,而此时人类学的就业大门早已关闭,结果那些取得学位的人再没有机会从事相应的研究。”(20)学科建立不成,自然会阻碍学术研究的进展。这是由现代的学术职业体制所决定的。
总体而言,对于西方人类学家而言,后殖民世界正变得难以接近。早年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比如法律民族志,有助于当局进行殖民统治,因而也获得了相应的赞助和支持。但是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人类学家因为之前与殖民机构的特殊关系,在很多新兴国家都受到了指责。而且,长途旅行也是昂贵的,赞助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开始思考:若要回答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问题,是否真的需要不远万里的长途旅行。所以法律人类学“回家了”。(21)
(五)来自法学的竞争
国家法是法学的研究领域。所以,法律人类学“回家”以后,就另辟蹊径,主要关注于本国的非国家法领域,比如基层司法、公众正义、替代性机制等问题。(22)而这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注意,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琼·维森特(Joan Vincent)的话说,就是“得到了许多法学家的尊重”。(23)但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尊重。大批法学研究者纷纷进入非国家法领域,导致人类学对法律研究的空间进一步受到竞争和压缩。所以,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法律多元研究,“确定无疑是法学界所创造的产物”。(24)而在另外一场法律改革运动——“寻求司法公正和法院的替代性机制”(Justice and Informal Alternatives to Courts)中,“人类学者,除了少数例外,其作用也远不及那些更具权力、更具官方背景的法学家和政府机关”。(25)迟迟找不到自己专属的研究方法,又失去了“他者”这一传统的研究对象,回到西方社会又受到法学的排挤,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人类学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向。
1981年,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作为人类学家受到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在其著名的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演讲中,将遭遇身份危机的法律人类学形象地比喻为“人头马”。(26)“人头马”虽然非人非兽,外形怪异,可毕竟也是一种特征。但是这匹“人头马”到了今天,似乎已经退化为马,或者进化为人。曾经担任过“法律多元研究会”会长的冯·本达-贝克曼(Franz von Benda-Beckmann)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便是“驾驭还是宰杀这匹人头马?”据本达-贝克曼的观察,除了田野调查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之外,如今没有其他明确的身份属性和边界标志来界定法律人类学了,就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在研究对象、理论假设、研究目标上,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出现了较大的重合。(27)
二、荷兰路径:法学院的法律人类学
虽然在英美的学术研究传统中,人类学与法学不断地呈现出限制与突破、控制与摆脱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是法律人类学却始终隶属于人类学。与之相比,同样有着百年发展史的荷兰法律人类学,却一直主要是由法学所推动和发展的。
(一)法学家所创立
科内利斯·范·沃伦霍芬(Cornelis van Vollenhoven)被公认为荷兰法律人类学的创始人。1898年,他凭借着题为《国际法的范围和内容》的论文获得了莱顿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之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成了荷兰殖民事务部长的私人秘书。担任秘书期间,范·沃伦霍芬经常接触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这引起了他对于当地阿达特法(Adat,习惯法)的关注和研究。1901年,他受聘为莱顿大学习惯法教授,主攻印尼阿达特法,并于当年提出了“自治团体”的概念,认为“制裁并非法律的唯一标准,当地人也能形成他们自己的法律”,他也因此被视为阿达特法学派的创始人。(28)
值得注意的是,范·沃伦霍芬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莱顿大学完成的,他一生只到过印尼两次,一次是1907年,一次在1923年。特别是第一次的旅行,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回国之后他就在《误解阿达特法》(29)一书中,讨论了对于阿达特法的带有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和转换问题,关于“阿达特民间法”和“法学家阿达特法”的区别也得以确立。(30)他还早在埃利希(Eugen Ehrlich)和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tvitch)之前就提出了“法律多元”的观念。而且他还多次响应当地人的呼吁,反对印尼的法律统一(认为这会损害传统法律),倡导保护习惯法。(31)阿达特法学派的方法一度被认可为欧洲大陆关于习惯法规范的标准研究方法。1900年到1940年间,荷兰是法律人类学研究最为多产的国家。
(二)法学家的传承
范·沃伦霍芬去世之后,出生于南非的学者大卫·霍勒曼(David Holleman)继承了莱顿大学习惯法教授的职位。霍勒曼曾经担任过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法院首席大法官,对阿达特习惯法非常熟悉,多年的司法实践工作,使他尤为关注殖民当局对于习惯法的政策和态度,强调要给地方性习惯和制度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32)不过,霍勒曼对于荷兰法律人类学的最大贡献,却是培养出了他的儿子——约翰·霍勒曼(Johan Holleman)。出生于1915年的小霍勒曼本来励志成为一名医生,但是高中毕业后与父亲在巴厘岛相处的那一个月改变了他的一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土著人那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是如此有滋有味”。(33)
父亲关于阿达特习惯法的介绍和讲解,使他对法律和民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暑假结束之后,约翰·霍勒曼回到了南非,在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一边学习罗马—荷兰法,一边研究人类学。毕业之后,在南非的祖鲁兰(Zululand)开始了他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并于1952年出版了其首部专著《修纳习惯法》。约翰·霍勒曼之所以被认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除了他将荷兰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从印尼扩展到了非洲,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他身上体现了英美学界对于荷兰的影响。其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英国学者艾萨克·沙佩拉(Isaac Schapera),此人是继马林诺夫斯基之后英美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英美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个案研究方法,在他的著作中同样有所体现。(34)而且,他还参考了英美学界过程范式的研究视角,将“问题个案”拓展为“非严重个案”,强调对于社会惯常状态的研究。(35)
(三)人类学的排挤
作为法学家的约翰·霍勒曼对于英美研究的借鉴,引起了荷兰人类学界的关注。为了法学能和人类学更好地沟通,莱顿大学在1963年任命约翰·霍勒曼担任该校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36)在60年代,关于非洲习惯法的研究一直都是该研究中心的重点,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使莱顿大学的非洲学研究居于欧洲领先水平。但是该中心设立的初衷之一(即促进法学和人类学的合作),却进行得并不顺利。霍勒曼退休之后,法学学者随即丧失了对该研究中心的掌控。
年轻的范·鲁沃罗伊·范·纽瓦尔(van Rouveroy van Nieuwaal)本来有望继承霍勒曼的衣钵,成为新一代荷兰法律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在当时的非洲研究中心,范·纽瓦尔是除了主任霍勒曼之外唯一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在很多方面,他的研究主题都可以视为是对霍勒曼的传承,比如酋邦和国家的互动,习惯法程序的细节处理,问题个案的分析,等等。但是到了加世纪70年代中期,范·纽瓦尔的处境越发尴尬。按照该中心高级研究员维姆·范·宾斯伯根(Wire van Binsbergen)的说法,“他关于法律人类学的博士论文超出了同时代任何一位研究非洲的荷兰学者,而且雄心勃勃、志向远大,但是他的结局却以悲剧收场:一位准备登基坐殿的王子却发现已经没有了王国。”(37)
由于非洲新兴国家积极地进行国家法律的统一,地方性习惯法就逐渐失去了研究的必要性。因而,新的中心主任格里特·格鲁滕休斯(Gerrit Grootenhuis)对部门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整合的过程中,先后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部和政治历史研究部。到了1981年,崭新的非洲研究中心已经容不下分离的、相对较小的法律研究部门了。范·宾斯伯根作为政治历史研究部的掌门人和事件的亲历者,在回忆那段历史时曾表示,因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当时都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中心如何能够继续生存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而没有能够质疑格鲁滕休斯的决定以至于将范·纽瓦尔排挤到了中心的边缘”。(38)当年,中心正式撤销了“法律科”,这也标志着荷兰法律人类学在法学院之外基本没有生存空间了。
(四)国际的法律多元
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受到了人类学的排挤,法国学者诺伯特·罗兰(Norbert Rouland)却将其视为荷兰法律人类学的特点之一,认为“荷兰学派的生命力,部分是由于将法律人类学纳入法学院研究的结果”。(39)由人类学者掌控的非洲研究中心撤销了法律科,法学院则就势在习惯法教席的基础上,创设了范·沃伦霍芬研究所,倡导关于殖民地法、比较法以及习惯法的综合研究。该研究所在扬·米歇尔·奥托(Jan Michiel Otto)、芭芭拉·欧门(Barbara Oomen)、珍妮·尤宾克等学者的推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40)除此之外,阿姆斯特丹大学、奈梅亨大学以及瓦赫宁根大学的法学院也都相继成立各自的研究机构,扩大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规模。
由于荷兰学派的法学背景,这些学者们的身份转换并不存在太多的障碍。而且,他们还利用英美法律人类学危机留下的空间,迅速占领了法律人类学的国际机构——“法律多元研究会”。该研究会在荷兰奈梅亨大学民间法研究所范登·斯廷霍芬(van den Steenhoven)教授的倡议之下,由“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于1978年11月创设,致力于研究和理解法律多元,探讨不同类型的法律,比如国家法、国际法、跨国法、宗教法以及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在相当长时间里,英国学者一直主导着这一协会,但在目前的十名执行委员中,来自荷兰的学者多达三位,美国和英国学者仅各占一席。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会同样也隶属于国际法律科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gal Science),体现了其法学研究的背景。
三、对比:迥异的发展道路,相同的身份困境
通过对荷兰法律人类学发展路径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与英美的法律人类学研究相比,荷兰法律人类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很大程度上一直属于一种法学研究。范·沃伦霍芬早在1901年就赋予了印度尼西亚土著的阿达特以法律的地位,同样的事情,直到18年后才由美国学者罗伊·巴顿(Roy Barton)在菲律宾伊富高人(Ifugao)身上完成;而又过了8年,马林诺夫斯基才出版了那本标志着现代英美法律人类学诞生的法律民族志。此外,范·沃伦霍芬被聘任为习惯法教授,这一职位大概也超出了英美法学院的想象力。所以,荷兰的法律人类学一经建立,就被纳入法学院的体制之内,准确地说,属于法学的分支领域。而且由范·沃伦霍芬的继任者们将其打造成一门分支学科,有专职的教授和讲师,有核心教材,可以授予学位。虽然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向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靠拢的过程中,受到了冷遇和排挤,但这似乎没有影响该学科的发展。
一个是人类学的分支领域,一个是法学院所创建的分支学科;一个曾遭遇生存危机,一个却风生水起,充满活力。而本文开篇提到的几位仍然坚守该研究领域的英美学者,也或多或少地有法学背景,或供职于法学院系,或接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这似乎说明,是否归属于法学,与此项研究的生存现状之间有着某种暗合关系。
但是,归属于法学并不代表实现了与法学的交叉研究。因为从学科沟通的角度来分析,荷兰和英美同样都是失败的。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荷兰的学者们没有像英美同行那样总是纠结于是否要使用法学方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法学家。像霍勒曼和范·纽瓦尔都出身于法律世家,他们的父亲不是法学教授就是职业法官,从小就受到法学知识的熏陶和感染,大学就读的也是法学专业,(41)因而他们不可能排斥法学方法,但同样也不会获得人类学的认可。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例子显示,荷兰法律人类学的学科交叉努力,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言,身份归属并不重要,不管是人类学的分支,还是从属于法学,只要能对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扩展对于法律的理解,就都是一种有意义的研究。但是在学科边界泾渭分明、学术部落固守领地的今天,这种纯粹的研究几无存在的可能。换言之,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身份归属。因为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有着迥然有别的学术准入以及生产规则。在知识市场中,出于对效率和效益的考量,学者们不会冒险也没有必要涉足另一学科的分支领域,但是却乐于在学科的交叉领地一试身手,以期获得双倍的学术市场。这一点,在公认的交叉学科——法律经济学——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42)
那么,法律经济学为何可以实现法学同经济学的交叉?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在1960年发表了包含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被视为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如果我们将其与霍贝尔和卢埃林合著的《夏延人的方式》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相同点在于科斯和霍贝尔均非法学学者,他们都试图研究法律问题;而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霍贝尔仍然采用法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科斯使用的却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经济学的效率观点,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架构与运作方式以及法律与司法制度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科斯的研究方法为法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视角,逐渐获得了法学的认可。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纷纷在法学院及经济学院中开设法律经济学课程,而《耶鲁法学杂志》、《哈佛法律评论》等知名法学刊物也不断地刊登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作品。所以,与法学共建交叉领域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提供一种能为法学接受并认可的研究方法,而并非在于研究者的多样性或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四、关于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反思
究竟什么是法律人类学?相关领域的中国学者需要对此进行反思。虽然在中国法学界中,不乏以人类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法学研究的作品,但作为一项研究的法律人类学,在中国却一直主要是由人类学学者所推动的。时至今日,被国内学界认可为“比较纯粹的法律人类学个案研究的作品”,(43)似乎只有赵旭东的《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44)和朱晓阳的《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45)等少数几部而已,而这两位作者都是人类学家。法学学者不仅贡献甚微,甚至在本世纪初期之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学界对于此项研究的态度颇为冷漠。(46)
由此看来,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发展轨迹与英美路径类似,是人类学主导的一项分支研究。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法学界自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少数民族法制或习惯法为主题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虽然其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相去甚远,(47)但毕竟有着与传统西方法律人类学相似的研究对象——他者的法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又具备着荷兰路径的某些特征。上述两种进路的研究彼此之间并无交集,这也说明了法律人类学在中国同样不具备交叉学科/研究的特征,从事法律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与法学学者之间的交流有限而且不够深入。(48)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英美与荷兰这两条路径百余年来试图沟通人类学与法学、打造交叉学科的努力均未成功,只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法律人类学能有所突破吗?尽管这一目标在短期内很难实现,但至少在促进法学同人类学的交流层面上,就法学界而言,仍然有比较清晰的努力方向。
首先,法学界对人类学研究的关注,必须超越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西南地区各高校因地理位置的便利,一直以来有着研究少数民族的传统。在国家推进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习惯规则与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因此,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就顺理成章地纳入到知识生产的国家规划当中,有充足的科研资金、丰富的从业人员,并且由于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充分尊重,研究人员只需要按照国家法的分类体系从事搜集和整理工作,而不需要考虑二者之间的逻辑融合问题。所以,来自于法学院的从事习惯法的研究者们,并无必要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经验。而人类学者一般也不具备国家法的知识背景,所以很少涉足习惯法的研究领域。因而,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很难能够实现人类学同法学的交叉。
其次,法学学者可以在法律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尝试。实际上,中国法律社会学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忽视人类学理论,甚至还以此作为自己的论说资源,比如苏力对“地方性知识”的使用和宣传,但这并不代表就是人类学式的研究,所以他的《送法下乡》仅被认为是“国内法学院研究中最像人类学的作品”。(49)按照本达-贝克曼的观察,尽管英美路径的法律人类学已经同法律社会学出现了重合,但此项研究仍然坚守着最后的阵地——基于田野调查而写就的民族志。在英美语境中,法律民族志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真正意义上法律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标准。(50)中国也采取此种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前述赵旭东和朱晓阳的作品被认为是纯粹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因而,人类学的研究尝试应该就是一种法律民族志的研究。近年来,可以看到已经有学者呼吁在具体的司法诉讼过程等传统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进行法律民族志的研究。(51)
最后,法学界要对人类学者进行的法律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作出积极的回应。比如,朱晓阳在对“小村故事”的后续关注中,对于城中村的改造与拆迁、滇池的污染与治理、小村的基层选举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52)不仅体现了人类学的视域和关怀,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甚至产生了直接的社会影响。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视为法律人类学拓宽研究领域的一次中国本土化的成功尝试。除此之外,产权、林权、新农村合作社等问题的研究,也为法学学者和人类学学者提供了可以施展其各自特点的合作空间,前者可以充分利用专业的法学知识,与后者形成互补关系,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推进法学同人类学的深入沟通与合作。
*感谢匿名审稿人及责任编辑对本文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由作者承担。
注释:
①Chris Fuller,"Legal Anthropology,Legal Pluralism,and Legal Thought",10 Anthropology Today(1994 ),p.10.
②Annelise Riles,"Representing In-Between:Law,Anthropology,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y",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1994),p.651.
③安妮·格里菲斯的代表作,参见Anne Griffiths,In the Shadow of Marriage:Gender and Justice in an African Commu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而桑托斯和梅丽的代表作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参见[英]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美]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郭星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参见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试论“法律科学”的属性及其研究方法》,《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⑤Richard L.Abel,"A Comparative Theory of Dispute Institutions in Society",8 Law & Society Review(1994),p.305.
⑥[美]西奥多·M.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七卷翻译委员会译,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⑦参见[美]克利尔:《北美社会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与衰落》,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等译,[美]古塔、弗格森主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⑧Simon Roberts,Order and Dispute: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Anthropology,London:Penguin Books,1979,p.12.
⑨See William Twining,"Law and Anthropology:A Case Study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7 Law & Society Review(1993),p.563.
⑩Ibid.
(11)See Karl Llewellyn & E.Adamson Hoebel,The Cheyenne Wa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41.
(12)See Francis G.Snyder,"Anthropology,Dispute Processes,and Law:A Critical Introduction",8 British Journal of Law & Society(1981),p.143.
(13)See William Twining,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3,p.145.
(14)Laura Nader,"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Law",67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65),p.3.
(15)Supra note(12),p.146.
(16)See Laura Nader & Harry F.Todd,eds.,The Disputing Process:Law in Ten Socie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14-15.
(17)See Barbara Yngyesson,Virtuous Citizens,Disruptive Subjects:Order and Complaint in a New England Court,London:Routledge,1993; June Starr,Dispute and Settlement in Rural Turkey:An Ethnography of Law,Leiden:Brill,1978.
(18)Carol J.Greenhouse,"Just in Time:Temporality and the Cultural Legitimating of Law",98 Yale Law Journal(1989),p.1631.
(19)Supra note(14),p.14.
(20)同注⑦,第121页。
(21)See John M.Conley & William M.O'Barr,"Legal Anthropology Comes Home:A Brief History of the Ethnographic Study of Law",27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1993),p.56.
(22)Supra note(12),p.163.
(23)Joan Vincent,Anthropology and Polities:Visions,Traditions,and Trends,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0,p.375.
(24)Simon Roberts,"Against Legal Pluralism:Some Reflec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Enlargement of the Legal Domain",42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1998),p.97.关于法律多元研究中人类学与法学的关系之评价,请参见注(12),p.157;注①;Sally Engle Merry,"Anthropology,Law,and Transnational Processes",21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2),pp.357-379.
(25)Supra note(12),p.149.
(26)参见[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6页。邓正来教授将“Centaur”译为“半人半马”,但笔者以为译为“人头马”更为简练和贴切。
(27)See Franz yon Benda-Beckmann,"Riding or Killing the Centaur? Reflections on the Identities of Legal Anthropology",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in Context(2008),p.102.
(28)See Norbert Rouland,Legal Anthropology,translated by Philippe G.Planel,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4,p.86.
(29)See Cornelis van Vollenhoven,Miskenningen van het adatrecht,Leiden:Brill,1909.
(30)Supra note(27),p.90.
(31)Supra note(28).
(32)See Franz von Benda-Beckmann & Han F.Vermeulen,"Adat Law and Legal Anthropology:In Memoriam Johan Frederik(Hans) Holleman(18 December 1915—28 August 2001):With a Bibliography",46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2001),p.103.
(33)Johan Frederik Holleman,African Interlude,Bellville:Nasionale Boekhandel BPK,1958,pp.7-8.
(34)See Johan Frederik Holleman,Shona Customary Law,With Reference to Kinship,Marriage,the Family and the E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p.35-75.
(35)See Johan Frederik Holleman,"Trouble-cases and Trouble-less Cases in the Study of Customary Law and Legal Reform",7 Law & Society Review(1973),pp.589-607.
(36)Supra note(32),p.104.
(37)Wim M.J.van Binsbergen,ed.,The Dynamics of Power and the Rule of Law:Essays on Africa and Beyond:In Honour of Emile Adriaan B.van Rouveroy van Nieuwaal,Münster:Lit-Verlag,2003,p.13.
(38)Ibid,p.15.
(39)Supra note(28).
(40)近30年来,范·沃伦霍芬研究所的成果颇为丰富,限于篇幅此处不能罗列,具体可以参见范·沃伦霍芬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law.leiden.edu/organisation/metajuridica/vvi/,2013年6月22日访问。
(41)Supar note(32),pp.103-104; note(37),p.10.
(42)Supra note(12),p.142.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请参见该杂志“法律与其他学科关系”系列论文的第一篇——Cento Veljanovski,"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A Critical Introduction",7 British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1980),pp.158-193.
(43)侯猛:《法律和人类学研究:中国经验30年》,《法商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4页。
(44)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45)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76》,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46)参见尤陈俊:《困境及其超越: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法律人类学》,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112页。
(47)参见侯猛:《迈向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法院研究——司法活动中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0期,第57页。
(48)同人类学界交流的法学学者,主要来自于法律社会学和法理学研究领域,那些专门从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者同人类学界其实没有太多的交流。参见朱晓阳、侯猛编:《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5-410页。
(49)同注(47)。
(50)因此,以“法律人类学家”的身份闻名于汉语知识界的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英美学界并没有被视为“法律人类学家”,其原因就在于他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民族志。See Robert M.Hayden,"Review:Rules,Processes,and Interpretations:Geertz,Comaroff,and Roberts",9 American Bar Foundation,Research Journal(1984),p.475.
(51)参见注(47),第57-61页。
(52)参见朱晓阳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uxu3443,2013年5月12日访问。
标签:人类学论文; 法律论文; 法学院论文; 法学教育论文; 政治与法律论文; 习惯法论文; 他者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