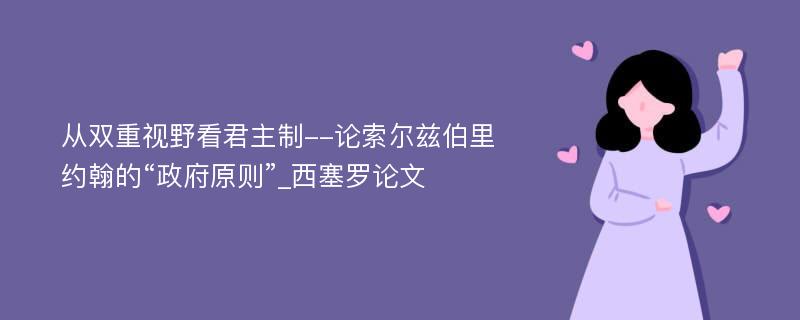
双重视野下的王权——谈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论政府原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权论文,索尔兹伯里论文,约翰论文,视野论文,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的写作犹如一面双面镜,12世纪复兴的古典学术与中世纪神学构成彼此辉映的两面。这位赴法游学凡十余年的英国学者型政治家在教廷和宫廷均历任高职,曾任两届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伯德、贝克特的秘书,英王亨利二世的秘书官,并与教皇尤金三世、阿德里安四世私交甚厚,最终以主教身份葬于法国的沙特尔。 约翰将其对政治的思考熔铸在了《论政府原理》(1159)①一书中,这部著作在12世纪政治思想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伯尔曼认为本书客观地反映了所处时代复杂的政治状况,而非当时流行的乌托邦或程式化的作品,称赞约翰在此意义上堪称“西方政治思想的发端”,②萨拜因认为《论政府原理》是“中世纪的论者试图广泛而系统地研究政治哲学的第一次努力”,是“人们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论著之前唯一的一部政治哲学论著”。③与此相似,是书早先的英译者迪金森也赞之为“西方再度熟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前唯一一部重要的政治论著”。④哈斯金斯亦认为该书是西欧进入中世纪以来“第一次试图超越周边环境,构建一种统一的政治哲学体系的尝试。 国内学界对该书的研究已有初步成绩,⑥但多专注于神学路径的剖解,而忽视了约翰作为12世纪古学复兴代表人物的另一面,因而仍有空白留待填补。 王权是《论政府原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不过,鉴于约翰兼具古典、中世纪学术的知识背景和跨越政、教的双重身份,他的论述也相应地具备了复杂的意蕴。特别是他在王权地位和诛暴君等问题上的谨慎,常被许多注释家理解为自相矛盾。本文认为,约翰的王权观体现了双重视野的交叠,分别是古典时代的共同体和公共义务理念,以及中世纪教会—国家权力格局下的君权神授思想,前者有利于抑制王权,后者有助于伸张王权。约翰的王权观正是古典政治理想在中世纪神学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融合,而二者间的内在张力尤其体现在对诛暴君命题的论述中。故此,笔者试从上述两重视野分别切入,并结合12世纪文艺复兴的学术语境,对《论政府原理》的王权观予以解析。 一、古典共同体理念的重新开掘 哈斯金斯曾提出12世纪文艺复兴的重要概念,其反映在政治理论中,表现为对古典政治传统的重新开掘,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正是他笔下代表该时期学术最高水准的学者之一。⑦在经历中世纪早期的暌隔后,古典拉丁著作被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时期的北方学术以法国为中心,教堂学校是学术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巴黎和沙特尔大教堂学校,在彼得·阿伯拉尔、康切斯的威廉和伯纳德·西尔维斯特等著名学者的调教下,约翰对古典文化的掌握在当时首屈一指。“没有哪位中世纪作家在古典著作阅读的广度和深度上可以与其媲美”,“对西塞罗钻研尤深”。⑧在《论政府原理》中,约翰引用过的罗马作家包括特伦斯、加图、贺拉斯、西塞罗、维吉尔、尤文纳尔、雷纳图斯、克劳迪安、马克罗比乌斯等,⑨涉及西塞罗之处尤其高达16次,约翰的王权论因此打上了鲜明的西塞罗烙印。书中的政治术语大多来自西塞罗,包括指代国家的“共和国”(res publica)一词,虽然该词在当时已不具备西塞罗所谓的混合政体下的共和国古义,但约翰依然采用这一古风式称谓。萨拜因由此认为,“他的理想毋宁说是共和国,亦即res publica的理想;而他所认为的共和国乃是西塞罗所说的这样一种社会,即‘根据一项有关法律和权利的共同协定结合而成的’那种社会。”⑩ 西塞罗的著作经常呈现出将政治学与伦理哲学的考察并陈的风格,似乎是受此影响,约翰对王权的论述也包含政治构想和伦理义务两个方面。 首先,约翰构建了有关国家组成的“政治机体论”思想,即将国家喻为躯体,将国家的各组成部分比作躯体的器官和肢体。(11)国家的头是国王,心即充当元老的贵族,耳、眼、口等器官是地方郡守和法官,地方市政官和士兵是双手,廷臣是协腹,国库司库及其他财务官构成肠胃,双脚则是工匠和农民。(12)政治机体的每一部分都依据所处位置具有相应职能,并统一在躯体的全盘筹划之中。“居下者服从于上,居上者则应为臣下提供所有必需的护佑”,“只有居上者为臣下奉献己力,居下者亦服从上级的合法职权,整个国家才会健康运转,达到安宁和昌盛”。国家的任一部分都很重要,各部分之间和谐互惠。“国家的存在和繁荣需要每个人都满意于其所处地位和事业……个体和全体无不将为公共事业献身作为义务践行……没有人攫夺他人的果实,人人保有一种对所有人的无差别的爱”。(13) 类似思想曾出现于圣保罗、奥古斯丁等人笔下,约翰在巴黎的老师之一,罗伯图斯·普鲁斯可能也曾以这一比喻影响过约翰。(14)但坎宁认为,直接对约翰给予启发的是康切斯的威廉对马克罗比乌斯给西塞罗《西庇阿之梦》所作评注的疏证,以及威廉对柏拉图《蒂迈欧篇》的评注,此外伯纳德·西尔维斯特对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评注和12世纪流行的对罗马法的注解可能也对约翰提出政治机体论有所助益。(15)迪金森也认为,这种视王权来自人民授予,国王应代表共同体利益的观念来自当时的罗马法研究。(16)这表明,约翰的政治机体论主要受益于古罗马政治学,而非中世纪经院哲学。 其次,与这种国家观相适应的是约翰对节制思想和公共义务的标举。约翰信奉斯多葛—西塞罗主义的自然法观念,“文明的生活应当模仿自然而过,我们时常能确认,自然乃是生活的最佳向导”。(17)自然天性决定了人类要过群居生活,在共同体的事业中节制私欲,恪尽职守。西塞罗在《论义务》中赞赏为公共义务献身的公民伦理精神,约翰于1180年去世后将藏书赠予沙特尔教堂学校,清单中便包括《论义务》的抄本,(18)《论政府原理》中亦五次引用《论义务》,足见其对约翰的影响之巨。 约翰还引用了维吉尔《农事诗》中关于蜜蜂的片段:蜜蜂生活在高效的小共同体中里,一切公有,遵守共同法则,分工明确,克己奉公。与蜜蜂一样,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认可真理,培育公共德性才是个人及理性天性的首要护卫。”为了在公与私之间达乎和谐,个体须厉行节制,“所有的德性都来自适度的终止,并居于中道”。(19) 合格的君主应何以为之?约翰对于君主在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先给予认可,他仍以蜂群为喻,假如蜂王不存,蜂群就会私自劫掠蜂蜜,巢穴将毁于一旦。然而君主的权力应有限度,“唯有能够自行设限的权力才安全”,王权的边界即法律和为共同体服务的公共义务。约翰继承了古典政治理论中区分君主和暴君的重要命题,“暴君则无视法律,对人民肆意施加暴力统治。”(20)“为了便宜行事,君主有必要十分富裕,但他必须视财富为人民而非自己的财产”,因为“他并不从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所有臣民。” 公共性是王权特性的重中之重,贵为头颅的君王仍是国家机体的组成部分。王权首先是共同体中的王权,君主应“热爱正义,珍视公平,在任何事上都将他人利益置于私心之上”,“因为他就是公共权力的化身,他从全体民众那里获得力量,为不使权力衰退,他必须保护所有人的安全”。(21)约翰对君主的期待正如克劳迪安对狄奥多西一世的劝诫:“要让公共意志而非个人意愿来引导你自己。”理想中的君王应像图拉真那样,为国开疆拓土的同时却能“以节制之心克服军事荣耀对心灵的鼓噪,对所有人平等相待”。(22) 不过,我们对约翰可以利用的古典资源不能过分乐观。如前所述,约翰是假托普鲁塔克之口提出政治机体论的,在推崇共和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尚未被发现,(23)而人们对古典文化又存在盲目信仰的时代,(24)约翰此举可能是为了给论述增加可信度。这一方面反映出古典政治思想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古典政治著作在12世纪的复兴仍不充分,能够为约翰所利用的思想资源尚且有限。这亦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当古典共同体下的王权理念与中世纪神授王权理念发生龃龉时,约翰选择了调和,因为前者暂时还无法于神学视野之外自立门户。 二、基督教王权神授理念的阐扬 约翰的王权观不仅体现出古典共同体的理论色彩,更是中世纪神学理念的直观反映。从后者来看,王权来自神授,而在王权经由教会转介的具体过程中,又引申出了国王与教会的关系问题。 首先,约翰坚持王权神授的观点。“君主代表公共权力,并且是神权的某种映像。”“君主所能做的任何事都来自上帝,君主的权力从不曾离开上帝,而只是上帝双手的代替,以使万事万物借助君权理解神的正义和仁慈。”对于遵行神旨、执行法律和正义的君主,他的命令即神意的转达,“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25) 其次,约翰谨慎处理了国王与教会的关系,在认可授职权讨论以来教会的理论优势地位的同时,又维护了君主的实际自主权。在论述政治机体时,约翰专门提到灵魂的作用。国家的灵魂显然是教会。虽然不属于躯体,但“正如灵魂拥有对全副身体的统治权,那些‘信仰完人’也理当领导整个国家”。约翰又指出,上帝选择利未人作为祭祀代己立法,教会则继承了利未人的特权,所以“君主的命令若非符合教会法,便是无效的”。(26) 然而,约翰并不打算将教权对王权的优势提高到压倒性地步,因而在阐释王教关系时采用了温和的对双剑论的传统解释。双剑论源于对《路加福音22:38》等圣经经文的注释,经中提到彼得的两把剑,自9世纪以来它们被理解为精神之剑和物质之剑。虽然阿尔昆认为查理曼为平靖内部异端和外部异教徒同时拥有双剑,但在11世纪授职权讨论前,这种理论倾向于暗示世俗和宗教力量的相互合作。到了授职权讨论时期,亨利四世提出双剑分属教宗和国王,它们都来自基督,但相互独立,由此为王权张目,格里高利七世及其支持者则强调双剑同属于身为彼得继承者的教皇。最后,明谷的圣伯纳德提出了互相妥协的通行解释,即基督同时把双剑赐予教宗,精神之剑由教宗保留,物质之剑经教宗中介后交给皇帝,教宗可在信仰事业需要时命令皇帝拔出物质之剑,但自己不能直接使用。(27)双剑论由此发展为双重权威论,它反对把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集中于教会或国王中的任一方。(28) 约翰承认“君主从教会手中接过了剑,尽管我们仍不能说君主独自占有这把染血之剑”,认可“君主在某种程度上是教士意志的执行者”,但因为运用世俗的染血之剑“对教士之手来说是种玷污”,故而实际权力仍保留在君主手中。(29)约翰的意见近似伯纳德,这种理论否认教宗有权直接干预君主的统治,实际上将国家权柄留在了君主手中。约翰期待的毋宁说是教会和世俗政府在各项事务中的二分法,教士可以跻身廷臣之列来影响朝政(如约翰自己),但教会本身则不应直接干涉政治。(30) 约翰既承认君权来自神授和教会转介的渊源,又坚持君主是上帝在国家中的代理人,享有教会无法直接干涉的世俗统治权。但如此一来,来自神授的王权自然便会高踞在共同体之上,这显然与古典政治视野下居于共同体内部的王权观势如冰火,而约翰接下来便面临调和二者的棘手任务。 三、双重视野的调和 中世纪晚期政治思想的发展趋势之一即复兴的古典政治理念与中世纪神学政治理念的调和,虽然《政治学》的重新发现以及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纳入基督教框架的试验使得13世纪广受关注,但这一过程其实在12世纪就已开始,《论政府原理》便是明证。 如果说约翰未能亲见《政治学》的拉丁译本,至少可以认为,约翰对于《政治学》中的某些信条并不陌生。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作为政治动物而天然趋向于组成国家,并且担负公共职责的判断,以及他视国家为共同体的整体论视角在《论政府原理》中都有清晰体现。培育了约翰的12世纪巴黎学界对西塞罗已有相当的研究。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西塞罗为约翰带来了公民义务观念,它强调个体应节制,恪守本职,服从法律,自觉投身于公共事业。 对于约翰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和西塞罗的“法律”、“正义”无疑是至为重要的概念,这几个概念都被约翰成功地置于上帝的引导下。与一个世纪后的阿奎那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被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理解为神意的工具。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被约翰用做证明神的启示的一种方式。”(31)“法律是上帝的馈礼,是公平的外衣,正义的准则,神意的映像”。(32)国王对上帝负责的方式便是为共同体服务,“君主是神的仆人,但他为上帝效劳的方式却在于忠诚地为同样身为上帝仆人的臣民服务”。(33)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就这样被约翰纳入基督教框架,厄尔曼认为约翰吸收了“古代的、罗马的文化因子”,提出了“基督教共和国”的概念。(34)基督教神学观构成了底色,古典政治理念则精巧地附丽其上。 至此,两种视野的调和已完成一半:当在任的是行止合乎法度的君主时,行使神授王权便意味着维护公共福祉,将法律和正义施治于国家;但若在任的是牺牲共同善以满足私欲的暴君,又该如何?按照共同体的法律,诛除滥用公共权力的暴君无可厚非,但惩罚作为上帝映像的神命统治者是否可行?这就引出了《论政府原理》中历来困扰学者们的诛暴君理论,约翰以中世纪诛暴君理论的作者的身份而闻名,虽然并非首创,但他却是首位详细阐述诛暴君合法性的辩护士。(35)当代一些学者对约翰是否赞成诛暴君提出质疑,围绕这一问题曾发生辩论。(36)本文认为约翰的确赞成诛暴,但其理论内部却存在权宜性妥协,这使其表述显得明暗不定。从古典学术与中世纪神学碰撞的角度来看,约翰在诛暴君问题上的依违两可恰好反映了两种视野间的抵牾。 否认约翰赞成诛暴君的理由通常有以下两种:第一,约翰采纳了自奥古斯丁以来广为流传的观点,将暴君的统治视为神的降罚,“当统治者粗暴地对待臣民时,它不仅是在以自己的力量行事,在其背后还有本着善意的神命在对民众施行惩罚或淬炼”。“暴君同样是上帝的执行者……借暴君之力,邪恶得到惩处,良善得到嘉许和淬炼”。(37)阿提拉是责罚堕落的罗马人的上帝之鞭,而上帝为惩罚有罪的英国民众,又让斯蒂芬带来十余年的无政府乱政。 尽管如此,约翰却是将暴君本身的邪恶与其有益效果分离看待的。“暴君之力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然则终究没有比暴政更坏的事了。因为暴政是对上帝所赐之力的滥用,只不过这种邪恶用于许多善举。”约翰以圣经上的扫罗和约拿单父子为例,证明一旦君主所为背离公义,上帝便会“像斩断织布机上的纺线一样断绝君主对王位的继承。”卡里古拉、尼禄、阿提拉都死于非命,斯蒂芬之子尤斯塔斯亦未得善终,“所有这些广见于历史学家们的记载中,里面充斥着暴君的恶行和他们悲惨的下场”。(38)暴政可能在神的计划中充当天惩,但本身仍是邪恶的,暴君仍逃不脱上帝的惩罚。 第二,约翰表达过人皆可能为暴君的观点。“尽管并非人人能领有公国和王国,但人们极少或者说根本不能免于暴政”,凡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都是暴君。(39)这种含混的论述使得一些学者怀疑约翰的出发点并不在于诛除政治上的暴君,对此我们需厘清细节。 首先,约翰主要在七、八两卷表达了这种观点,而《论政府原理》的写作跨越六年,分为三个阶段。在1454年至1456年写完篇首后,约翰于1156年至1157年间因反对亨利二世向英国教会征税而被逐,此时约翰先于中间部分开始写作七、八两卷,着意批判宫廷里的伊壁鸠鲁主义,借哲学著述聊以自慰。(40)约翰可能是出于哲学写作的考虑,才将暴政置于纵欲—节制这一宽泛的古典伦理学命题下予以讨论,遂有了人人都或将成为其管辖事务中的暴君的比喻。 其次,约翰在政治性的公共(public)暴君和象征性的私人(private)暴君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后者即普通大众和神职人员。私人暴君同样要受责罚,“倘或在人类和神的法律下,暴君应当被诛,难道神职人员中的暴君就要被爱戴和尊重了吗?”“设若无法束缚暴君,谄惑、诓骗暴君从来都是被允许的,诛杀暴君也是光荣的”。(41)可见象征性暴君亦不能逃脱惩罚,只不过在法律范围内足以对之予以惩处。就诛暴君这一命题而言,对象特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性暴君。 因此,认为约翰赞成诛暴君的观点可以成立。在古典共同体中,公民不仅要消极地恪尽职守,也应主动地维护公义。“对践踏法律的人,正义理应凭借武装来反对他,对无视公共权力的人,公共权力将严厉制裁他”。(42)在此意义上,尼德曼将第三卷第十五章中约翰的立场阐释为,为共同善而惩处暴君不仅是共同体成员的权力,更是他们的义务。(43) 实际上,使约翰的诛暴君理论略显模糊的并非应否诛除暴君,这一点确无疑义,而是这一公民义务却又同时被约翰视作神意使然的结果。在第八卷第二十一章,约翰先归纳了暴君的结局,神一定会对怙恶不悛的暴君加以惩处,但有时用自己的剑,有时则借用人类的剑。这就产生了推论:诛暴君的决定权无论如何掌握在神的手中,共同体的其他部分不过是践行神意的工具。与第三卷迥然相异,“诛除暴君最有用和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那些受压迫的人应当谦卑地依靠上帝仁慈的保护,向上帝举起手,虔诚地祈祷,祈求加诸自己的鞭打会被解除”。(44)按照这种解释,民众应将诛暴的决定权交付于神,哪怕最终被神拣选行使除暴,也应是由神支配的被动顺从之举。 由此,第三、八卷的冲突转化成了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令人费解的是,约翰在第七卷大谈自由的重要(45)后,又在第八卷强调逆来顺受、依靠神力。假使人毫无自由决定权,那么诛暴君即使在上帝安排下成为可能,对于人又是否有意义?与之相关,权力究竟来源于共同体的赋予抑或神授?其实,在中世纪神学史观中,信仰和政治现实之间没有也无需加以区分,自由意志和人民主权带来的困扰只有现代人方能感受得到。在约翰看来,人民既能自由选举国王,又暗中体现神意的预定;王权既来自共同体,又同时源于神授;人民既可以诛除暴君,又在无意识中充当了神的工具。 归根结底,政治机体所暗喻的世俗国民共同体在12世纪还处在萌芽阶段,“这一唤启仅仅是实验性的”,尚且不能与基督教的国家理念针锋相对。(46)驱使人自愿结合成共同体的自然法也只有寄身于神意秩序下,才恰恰能获得一片安全的自留地。(47)不过,约翰无意间埋下的种子在两个世纪后终于等来破土的环境。《论政府原理》在14—16世纪的多位大陆法学家那里备受青睐,是14世纪法学研究中“被引用和详解最频繁的中世纪哲学家的论著之一”,以彭纳的卢卡斯为代表的法学家继承了约翰的多数政治观点,但在诛暴君问题上却不再消极地求助上帝。(48)较之约翰,罗马法的学者们肯定了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使之能够“为自己立言和行动”,(49)这正是约翰望而止步的地方。在约翰的视野中,无论是共同体中的王权还是神授王权,无论是维护共同体公义的君主还是放纵私欲的暴君,都只是践行神意的工具。正因如此,对立的二者才有可能并存。而当全能的上帝在近代政治思想的舞台上谢幕后,共同体自下而上的主权就不可避免地与依旧自上而下的神权分道扬镳了。 作为中世纪西欧截至12世纪最重要的政治论著,《论政府原理》反映了两种学术视野——复兴的古典学术和正值鼎盛的中世纪神学——的碰撞与融合。《论政府原理》关注的焦点是王权,约翰笔下的王权一方面是政治机体中的头颅,重要却仍受制于国家共同体的法律,另一方面则是权力神授的产物,即使是暴君亦为神旨的执行者,只需向神负责。为弥合二者的裂隙,约翰将维系共同体的法律解释为神意,由此看似矛盾的两种君主形象——共同体中维护公义的君主和代行天裁的神命君主——就此嵌合。虽则如此,两种视野的摩擦依然存在于约翰的诛暴君理论中:作为共同体成员,人民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诛暴,但身为神的子民,人民又只能被动地接受神借暴君给予自己的惩罚,消极地充当神剪除暴君的工具,而不具备自亩抉择的意志,更非王权的最终来源。诚然,约翰选择神学作为理论底色,将古典政治理念置于上帝的统驭下,脚步终究停留在中世纪,但其将古典共同体置于王权神授理论之下的做法,却为复兴伊始的古典政治理念在中世纪找到了安全的栖身之地。 ①全名为《论政府原理:廷臣的轻薄和哲学家的履迹》,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of the Frivolities of Courtiers and the Footprints of Philosopher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ary J.Nederm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②[美]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③[美]萨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 ④John Dickinson,"The Mediaeval Conception of Kingship and Some of Its Limitations,as Developed in the Policraticus of John of Salisbury," Speculum,Vol.1,No.3(Jul.,1926),p.308. ⑤Charles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69. ⑥国内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孟广林:《中古英国神学家约翰的“王权神授”理想》,《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张笑宇:《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世纪渊源》,《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周诗茵:《理想模式与政治现实的互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教会-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孟广林立足于中世纪神学政治语境,对约翰的王权神授和诛暴君思想给予了深入阐释,张笑宇着重于介绍约翰的学说对近代政治的启发,周诗茵强调了约翰在调和教会与国家关系上的努力。 ⑦古典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均在12世纪得到复兴,但后者主要局限于南欧。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以巴黎为学术中心,主要受古典拉丁文化复兴的影响,约翰即为代表人物之一。 ⑧Charles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p.100. ⑨对约翰的古典藏书目录的汇编,参见Clement Webb,John of Salisbury,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71,chap.6。 ⑩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298页。 (11)约翰是在伪造或误用了一份名为《图拉真圣谕》(Instruction of Trajan)的文件后,借“作者”普鲁塔克之口提出这一比喻的,今人已完成证伪,参见H.Liebeschütz,"John of Salisbury and Pseudo-Plutarch,"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Vol.6(1943),p.35。 (12)与res publica一样,约翰又使用已失去实质意义的senate一词指代贵族。参见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66-67,69-126。 (13)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126,10-11. (14)H.Liebeschütz,"John of Salisbury and Pseudo-Plutarch",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Vol.6(1943),p.33.约翰的政治机体论可能从前人论著中得到过启发,但他赋予这一理论以前所未有的丰赡意义,参见Tilman Struve,"the Importance of the Organism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John of Salisbury",in M.Wilks,ed,The World of John of Salisbury,Oxford:B.Blackwell,1984,pp.303-317。 (15)Joseph Canning,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300-1450,London:Routledge,1996,p.112. (16)John Dickinson,"The Mediaeval Conception of Kingship and Some of Its Limitations as Developed in the Policraticus of John of Salisbury",Speculum,Vol.1,No.3(Jul.1926),p.312. (17)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127.这与西塞罗称赞自然法是“生活的向导和责任的导师”相似,见Cicero,Nature of the God,translated by H.Rackha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43。 (18)Charles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p.111. (19)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127,16-17. (20)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206,28,190. (21)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20,63. (22)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223,79. (23)《政治学》进入西欧学术视野始于1260年前后摩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将之译成拉丁文。 (24)对约翰所在的沙特尔学校尤其表现出“对古典著作家的恭顺依赖”,参见R.L.Poole.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Thought and learning,New York:MacMillan,1920,p.102。 (25)《罗马书13:2》,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28-29. (26)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67,41. (27)J.H.Burn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350-14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302-304.[英]厄尔曼著,夏洞奇译:《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131页。 (28)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243页。 (29)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32. (30)Cary J.Nederman and Catherine Campbell,"Priests,Kings,and Tyrants:Spiritual and Temporal Power in John of Salisbury's Policraticus," Speculum,Vol.66,No.3(Jul.,1991),p.589. (31)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282页。 (32)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35,191. (33)John Dickinson,"The Mediaeval Conception of Kingship and Some of Its Limitations as Developed in the Policraticus of John of Salisbury," Speculum,Vol.1,No.3(Jul.,1926),P.314. (34)厄尔曼:《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第116页。 (35)R.L.Poole,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Thought and learning,p.208; C.McIlwain,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New York:McMillan,1932,p.323. (36)认为约翰赞成诛暴君,参见Cary J.Nederman,"A Duty to Kill:John of Salisbury's Theory of Tyrannicide,"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50,No.3(Summer,1988),pp.365-389;反对观点见Jan van Laarhoven,"Thou Shall Not Slay a Tyrant! The So-called Theory of John of Salisbury",in M.Wilks ed.,The World of John of Salisbury,pp.319-341;强调约翰的表述存在矛盾,参见Richard H.and Mary A.Rouse,"John of Salisbury and the Doctrine of Tyrannicide," Speculum,42(October 1967),pp.693-709。 (37)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29,207,201-202. (38)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202,61,205. (39)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202. (40)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introduction,p.xviii. (41)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201,205. (42)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25. (43)Cary J.Nederman,"A Duty to Kill",p.374. (44)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p.209-210. (45)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p.175. (46)[美]沃格林著,叶颖译:《政治观念史稿:中世纪(至阿奎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47)W.Ullmann,Principle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Routledge,1961,p.255. (48)W.Ullmann,"The Influence of John of Salisbury on Medieval Italian Jurist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59,No.235(Sep.,1944),p.388. (49)John Dickinson,"The Mediaeval Conception of Kingship and Some of Its Limitations",p.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