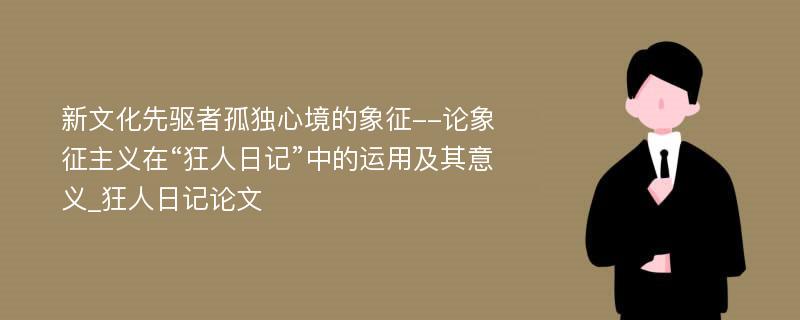
新文化先驱者孤绝心境的象征——论《狂人日记》中象征主义表现法的运用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象征论文,先驱者论文,新文化论文,狂人论文,心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3-0118-05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3.015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坛“独尊现实主义”,而鲁迅在诸多创作方法中选择现实主义为主轴之举也被史家过度阐释、定义,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因此争议不休。 因着《狂人日记》的奠基意义,一些研究者心有不甘,费尽心思为《狂人日记》中所运用的象征主义表现法作美学易容:或削足适履,将《狂人日记》归入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之列,称其“是鲁迅开展他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天才活动的”“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1](P.98)或舍本逐末,冠之以“主要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所用的主要艺术手法则是象征手法”之类的判语。[2]如是作派,与其说是解答问题,倒不如说是在制造问题。 近年来,“独尊现实主义”说竟然又借助某种时机而不断回潮。有鉴于上述误区,本文以《狂人日记》为范本,对鲁迅前期小说中象征主义表现法的运用作一些探讨,借此揭示现代中国小说萌生期鲁迅等新文化先驱者审美视野的开阔品格,以及所选择的创作方法的多元性特征。 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说的唐弢完全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塑形原则分析“狂人”形象,认定“狂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狂人”,“他在没有发疯之前,可能思想倾向比较进步,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满;这样一旦发疯之后,出于这个缘由,当他翻开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便会从字缝里看出‘吃人’两个字来,并且最后作出‘救救孩子’的呼号”。[1](P.103)而王富仁在沿袭、发挥唐弢上述思路时不经意间将观点归谬,称“‘狂人’是在逐渐深入地了解了封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之后得了精神病的,亦即他是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精神病患者。他认识到封建社会充斥着‘人吃人’的现象,认识到封建礼教害死了无数的弱者,后来,他得了精神病,‘吃人’两字便由原来的比喻意义在他头脑中转化为具有实在意义的东西”。[3] “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精神病患者”这一界定印证了此说的悖谬。纯粹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能将“狂人”塑造成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绝不可能使其兼具“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同理,作品中的“大哥”、“母亲”、“医生”、“赵家的狗”等形象,如果不从象征主义意义上去读解,那么,他们合伙吃人不过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妄想、错觉,他们的形象将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迥然有异。如同小说中的“狂人”并非是一个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的典型人物一样,“狂人”所处的环境也并非典型环境。它是抽象的,具有封建性这一共性却缺乏具体性。与《风波》《故乡》《祝福》《离婚》等作品中所塑造的农村典型环境相比,其差异不言而喻。 此外,就细节的真实而言,许多文章所认为的作品中对“迫害狂”患者心理活动的刻画完全是写实的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诚然,鲁迅凭借他的医学知识对“迫害狂”的神经过分纤敏、处处疑神疑鬼作了一定的如实的描写;但作品中“狂人”的心态、思路既有非逻辑的一面,又有相当强的逻辑性。在许多情节、细节上狂人表现出远远超乎精神病患者可能的推理能力、雄辩能力。 对照恩格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界定,《狂人日记》显然不是一部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小说。 持第二说的邵伯周、张硕城等认为,鲁迅主要是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塑造“狂人”形象的,兼用的艺术手法是“象征手法”。他们也认为鲁迅采用象征手法把“狂人”与战士形象统一起来,狂人“只能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并认同《狂人日记》所营造的环境“是一个抽象的象征性的环境”;但他们却讳言象征主义艺术方法,理由是“象征手法的运用,在作品中虽然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但它既不是‘唯美’的,更不是‘神秘’的,所以和象征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和浪漫主义却是相符合或者说是基本上一致的”。[2] 上述研究者近似于掩耳盗铃之举,缘于20世纪80年代初乍暖还寒的特定语境,故不得不委屈“象征主义艺术方法”、将之降格为“象征手法”。其实,退一步说,纵然象征主义定义有其质的规定性,并不等于不能被转换性地运用。笔者比较认同陈涌20世纪70年代末所持的观点:“有些人把《狂人日记》的狂人当作一个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来分析,在那里谈论什么鲁迅创造的‘英雄形象’,就是因为不去区分象征的方法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其实,狂人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鲁迅所假定的抗击旧世界的力量的象征,鲁迅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来创造的。”[4]笔者认为《狂人日记》是一部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手法相调和的作品,并且主要借象征主义表现法使人物、情节、主题显示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在《药》《阿Q正传》《明天》《风波》《长明灯》等运用象征手法的小说中,尽管作者寄寓题名以一定的象征意义、深化了主题思想(如题名“药”、“风波”、“明天”),或赋予人物以象征意味,拓展了人物的内涵(如“阿Q”,《药》中两个悲剧主人公姓氏“华”“夏”);但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诸任务,人们即使不从象征意义上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只会有深度的差异,却不会导致质的变化。这与《狂人日记》显然有区别。 《狂人日记》所运用的象征主义艺术方法不仅是古今中外广义的象征手法的承传与发展,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表现法的吸取与改造。既有研究以切实的论据证明,作品除了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还受到运用象征主义方法创作的安德列耶夫的《红笑》《墙》《谩》、迦尔洵的《红花》等作品的深刻影响。鲁迅在论述安德列耶夫、勃洛克将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一些作品时,曾一再肯定了这种尝试。 象征主义惯用使普通事物变形或升华的方法,曲折地表现隐匿在普通事物背后的理念世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正是凭借自己那超凡的想象力,使“狂人”的感觉能力得以升华,以强化“狂人”与传统社会的内在冲突,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惊世之问,传递了新文化先驱者不无孤绝地反传统的心境。 有别于运用一般象征手法的作品仅仅出现个别词句的象征,《狂人日记》的形象体系具有象征性,它隐喻的是一个系统的世界。 自由联想这一象征主义的主要手法也被鲁迅创造性地运用于《狂人日记》中:医生嘱咐病人“不要乱想。静静地养几天,就好了”,被联想为“养肥了,自然可以多吃”;赵家的狗多看了几眼被联想为“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在象征主义作品中,自由联想得以实现,往往凭借非理性的直觉与幻觉。而鲁迅则巧妙地以“狂人”作为小说的意识中心,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狂人”的感觉本身就是幻觉。这样,自由联想这一象征主义的主要艺术手法就被鲁迅在不违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了。 鲁迅的前期小说对西方象征主义艺术方法采取的是“有所删除”“有所增益”的原则。试与西方象征主义(包括从创作整体上来看不能归入象征派的俄国安德列耶夫、迦尔询的一些以象征主义为主导的作品)的艺术方法作一比较。 由于非理性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衍生了象征主义作品中非理性的艺术特征。他们过分地强调直觉、无意识与本能,往往走向极端。在部分作品中,主观凌驾于客观之上,内心世界游离于外部世界,不仅未能通过表现内心活动反映现实,而且连内心活动本身也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与西方象征主义的非理性恰成对照,清醒的理性始终是鲁迅小说的重要特征。即便在运用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的《狂人日记》中,如同美国学者哈南指出的,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智对象征的把握”。[5]鲁迅对象征主义非理性的特征是有意识地摈弃的,他曾否定安德烈耶夫“理性是虚妄的”论调。鲁迅所重视的是主观对客观的介入,而不是主观超乎客观之上。他在论述安德列耶夫、勃洛克以及望·蔼覃那些“象征写实”的作品时,无一例外地强调不失其现实性、“假中见真”。在《狂人日记》《药》《长明灯》等作品中,鲁迅也描绘某些人物的直觉、无意识与本能,这些感觉活动也是置于非理性状态下的;然而这与西方象征主义作品中的非理性是有区别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非理性的是作者;而在鲁迅的作品中,体现非理性的只是人物,在非理性的人物背后,始终站立着一个有着异常清醒的理性的作者。 在象征主义作品中,象征性形象往往具有多义性、神秘性,没有明确的所指,只是让人隐隐感到某些形而上的意向,扑朔迷离,犹如文字密码。即使在某些作品中象征性形象的指向性较明确,也不过是作为一种符号来使用的。如安德列耶夫的小说《墙》,以“墙”作为象征物,象征吃人的俄国社会;迦尔洵的小说《红花》,以“红花”作为象征物,象征世上一切邪恶势力。象征与象征含义并非是以一定的推理关系为桥梁、以相似的属性为基础而构成的。 在鲁迅前期小说中,象征性形象大都具有相对明确的指向性,读者较容易沿着它的指向性追寻到它的象征含义。这是因为在鲁迅笔下,象征性形象除具有象征含义外,自身也具有实在的具体含义;而且自身的具体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似的属性,有着一定的推理关系。如《长明灯》中一千多年前由梁武帝点起的“长明灯”,本身便是封建神权与君权的产物,在不觉醒的群众眼中,它便成了整个封建传统的象征。《药》中的“药”、《风波》中的“风波”以及其他前期小说中的象征性形象也大都如此构成。唯独《狂人日记》有所不同。在《狂人日记》中,象征性形象自身的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既存在着对立性,又有同一性;既无逻辑性,又有一定的推理关系。 象征派与其他现代派一样,大都是有机形式主义者。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们将形式的重要性强调到极致,认为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离开了形式无所谓内容。这种理论积极的一面,在于促使人们不断地进行艺术形式的创新;其消极的一面,在于某些花样翻新是以牺牲内容为代价的。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鲁迅认为“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6](第6卷,P.22)他吸取了象征主义合理的一面,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狂人日记》便是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他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因为他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他曾说:“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7]当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者不能兼顾时,他“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哪怕因此可能与艺术的距离拉远。在《药》中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并赋予其象征意义,便是艺术形式服从思想内容的典型例子。 鲁迅为何要在《狂人日记》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实践中尝试将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调和;为何不像同时代的某些理论家那样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视为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对立的东西?探索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鲁迅的多元创作方法观。 鲁迅在这一点上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较为接近。卢那察尔斯基肯定“为艺术之一形式的象征主义,严密地说起来是决非和写实主义相对立的。要之,是为了开发写实主义的远的步骤,是较之写实主义更加深刻的理解,也是更加勇敢而合乎顺序的现实”。[8]高尔基说:“《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一种崭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一种精神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地”,“别的戏剧是不能把人从现实中吸引到哲学的概括上面的,——这一点您却做到了。”[9]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 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首先在于更及时地服从思想革命的需要。面对数千年的封建上层建筑,鲁迅的忧愤是那样深广,为了使艺术形式这一外壳拥有尽可能大的思想容量,即卢那察尔斯基所肯定的“开发现实主义”,鲁迅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法——这个“内蕴”远远超出“外象”的方法,以便将作品的主题思想延展得更为深广。无独有偶,苏联诗人勃洛克也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与现实主义的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仅仅两个月便创作了长诗《十二个》,“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首先作出积极反应”。这一创作实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的认识。 其次在于,思想革命这一任务决定了作品不仅应将观念借具体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同时应将具体形象高度抽象化为观念。象征主义表现法有利于浓缩生活、增强作品的概括性。《狂人日记》以它高度抽象的思想性,成为鲁迅前期反传统思想革命小说的“纲”。封建礼教“吃人”这一观念在鲁迅以后的一系列小说中又具体化为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夏瑜、子君等纷纷被“吃”掉的人物形象。又如,在《阿Q正传》中,若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出“阿Q”这一典型,则不尽符合思想革命的需要;他还必须是“国人的魂灵”。于是,“阿Q”这一具体形象不得不高度抽象化为“阿Q主义”的精神特征。在《阿Q正传》中,鲁迅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象征手法调和得如此自如,因此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既富有典型意义又富有象征意义的复杂的艺术形象。 其三在于,思想革命需要作者着力解剖国民的灵魂,并对其进行思想启蒙。象征主义强调表现内心的生活、心理的真实,它的主观性、内向性如果用得恰当,可以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客观性、外向性的补充。鲁迅曾认为勃洛克的象征主义诗作《十二个》“体式在中国很异样,但我以为很能表现着俄国那时(!)的神情”,[6](第7卷,P.301)只要象征主义表现法运用得当,即可反映对象的精神本质。象征主义表现法尤其适于表现特殊人物在特殊状态下的心理。恰如叶芝所说:“当恍惚或疯狂或沉思冥想使灵魂以它为唯一冲动时,灵魂就在许多象征之中周游,并在许多象征之中呈现自己。”[10]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调和这一尝试,为鲁迅以后的创作、也为新文学提供了经验。 《狂人日记》的艺术形式就其为思想革命“呐喊”这一思想意义而言,确实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如同鲁迅自省的那样,作品的艺术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手法的调和尚未如此后的《药》《明天》《长明灯》那样浑然一体,未能完全避免象征主义小说容易出现的思想容量大于艺术形式、观念大于形象的现象。 这一弊端渐次得到了克服。在《药》《明天》《长明灯》等小说中,鲁迅更圆熟地将象征的艺术方法调和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艺术方法中,将象征性形象有机地融化于客观描写中,使象征物与象征含义之间天衣无缝,似象征,又“不失其现实性”。[6](第10卷,P.185)为尝试集合诸种方法的张力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实绩。 收稿日期:2015-03-28标签:狂人日记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艺术论文; 先驱者论文; 文学论文; 新文化论文; 长明灯论文; 风波论文; 明天论文; 阿q正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