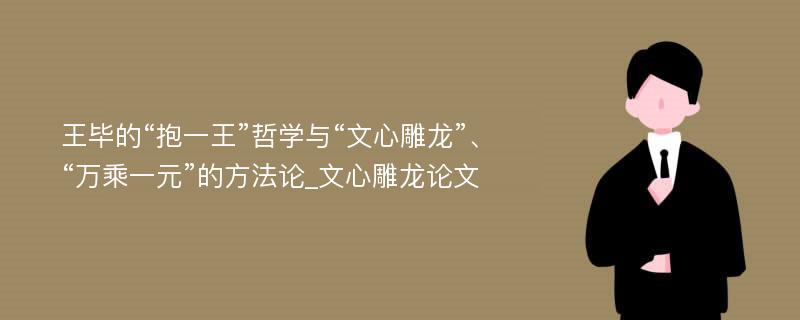
王弼“执一御万”哲学观与《文心雕龙》“乘一总万”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王弼论文,文心雕龙论文,哲学论文,执一御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4)03-0086-05
“乘一总万”是《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贯通于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及批评论的主神经,对全书理论和结构框架都有重大作用,使之体大而不杂乱,思精而不浮泛。但人们对这一思想却鲜少触及,故本文详探它在《文心雕龙》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对它的直接“施事者”王弼“执一御万”、“举本统末”哲学观予以考绎,揭示刘勰对这富有深厚底蕴的思想继承和通变的关系。
一、王弼“执一御万”思想是对前代思想的改造、整合、提升
王弼《周易略例·明彖》:“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执一御万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是体察万物、把握宇宙的钥匙,于汉人总揽人物牢笼象数的方法论是一场革命,但它的形成决非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汲取《周易》、老庄以及孔子思想营养,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结果。
《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邵雍把此创造模式概括为“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犹根之有干,犹干之有枝,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太极”、“一”为世界的本原,“执一”则众理皆存,万物成位,“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系辞上》)无疑《周易》在把握世界本体方面已经有“以少统多”的观念。由太极衍生的八卦,除乾坤二纯卦(父母卦),其余六子卦“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系辞下》)。韩康伯《周易注》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以少者——一阳为主,阴卦以少者——一阴为主。如果抛开阳尊阴卑君子小人的道德标准,阴阳卦的属性完全是以少者的性质所决定,少为多所从,多为少所制。“小成”的八卦如此,大成的六十四卦与万物万理的关系呢?《系辞上》:“八卦而小成,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同上),广大悉备的《周易》正是通过六十四卦以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弥纶万理,以少统多。
我们说,尽管《周易》没有直接揭橥出“以一御多”的概念,但它从林林总总的事物中凸显出“太极”一易理,本身就孕育着“理一分殊”的理致,贯通着“以一御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汉代它依然得以延续,这充分体现在京房“金钱代筮法”上。《项氏家法》有记载:占者掷三枚铜钱,以背面为阳,正面为阴。皆背为老阳,皆面则为老阴,两背一面为少阴,两面一背为少阳。那么面背不同时,则撷取少者,此取爻法与《周易》之阴阳卦的断定法(“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思路相同,所以金钱占筮术是《易》道“以一御多”观的具体实践。但这种思维方式属于弱势文化(注:《论衡·自纪篇》:“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盖文多胜寡,财富愈贫”。“或曰”者代表了汉代“以少驭多”弱势文化,而王充则代表“以多胜寡,繁而不省”的强势文化。),充盈于汉代易学史的是繁琐驳杂的象数学,人们对观照万物“末象”有极大的热情,“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可见一斑。不过森然万象是难以穷尽,且愈理愈棼,因此不免陷入谶纬迷信中不能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弼所开展的扫象阐理《易》学革命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如果说“以一御万”的命题于《周易》尚处于涵融未发状态,那么王弼就自觉地去寻探它的几微,敏锐地把握它的律动。“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周易略例·明彖》)。他明确提出“以一御万”的思想,倡扬义主说,卦主说,以少来驾驭主宰多,以本质来统观现象,以宗主来总摄众庶。
“义主说”指象生于义,应得意忘象。《周易》是假象寓意,非为象而象。王弼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焉……统而举之,乾体皆龙;别而叙之,各随其义。”(《乾·文言》注)象随义而取,对《说卦》列举的112例象,如乾为健,为马,为君等,坤为顺,为牛,为母等,以义为主,不可象汉人拘泥于具体卦象,对号入座而捉襟见肘,“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周易略例·明象》),滋漫出互象、半象等逸象,迷离破碎,故王弼在“随其事义而取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得意忘象”。“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同上)象是意之象,具有象征功能,“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同上)。王弼愤激于汉人胶柱于“象”以致曲意弥缝的解《易》方式,而强调以义(少)来统率象(多),此义主说的实质,是《系辞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精髓的开拓。
“卦主说”是指一爻为一卦之主。一卦六爻唯变所适,表面上互不相涉,实则有一个“宗主”。《明彖》曰:“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至寡治众,主一咸存,故一为众主,众为一臣。六爻但“可举一以明”(同上),其大体有主卦之主,成卦之主,一阴主五阳,一阳主五阴四种。
主卦之主,指居中之爻,或二爻,犹以五爻为多。中爻具备“杂物撰德,辨是与非”(《系辞下》)的气质,举一立主,唯其是荷,“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周易略例·明彖》)。如《革》九五以中正之德信孚他人,以刚猛之气“虎变”,故为革故鼎新之主。其余《乾》九五、《井》九五、《渐》六二等皆为宗主。而“成卦之主”,是卦义因之而起的一爻,它不同于“主卦之主”讲究卦德卦位,而专主卦义。《略例下》:“《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六三在上卦之下,故有“履虎尾”之象,卦义“小心践履”因之而成,故“三为《履》主”(《履·彖传》王注)。《屯》初九、《大畜》上九等成卦之主皆为卦所以然者。
这两大类是“卦主”说的基本条例,都体现了“以一统多”的特点,而作为从前二者分析出来的特例[1]。一阴主五阳、一阳主五阴更为突出。“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明彖》)。卦主皆因六爻中阴阳本身的力量对比而决定,《姤》初六、《同人》六二、《复》初九、《师》九二等十二爻皆因以少制多而为卦主。
“卦主说”主要目的是阐发“六爻之间的主从现象,达到从整体上领会一卦大义的解《易》效果”[1](P177),它与“义主说”一样旨在于“约以存博,简以济众”。二“说”作为批判汉《易》的理论武器,体现了“易简”之理,显示出《周易》蕴涵的“以一御万”观念所达到的高度,但在王弼哲学观中,它不是最高范畴,故应纳入“以无为本”、“举本统末”本体论体系中。《老子》四十章王注:“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三十八章王注:“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论语·阳货》“予欲无言”王注曰:“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举本统末”显然是王弼融通、开掘、发扬《周易》思想的结晶,不可否认也参会了老庄、孔子思想,从而指向了形上的本体论,也切进了形下的方法论,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高标。
王弼《老子指略》曰:“《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2]崇本息末为《老子》哲学的根本。道是世界的本体,摄万殊于一(无)。《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庄子·达生》“通天下一气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崇本”,然而“息末”,灭弃了万物的差异性,致有“齐物”之论(“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说,“外死生,无终始”之谈。王弼显然接受了老庄“崇本”、“守母”的一面,但也没有忽视“全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哉”注),舍弃了“息末”的观点。
王弼“统末”观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孔子博而致一、一以贯之的滋养,《阳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道德的提升是以多学多识为前提的,通过“多”的积累或熏陶,以跃升到“一”的境界(注:后世儒家只执一端,见“博”不见“一”,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而“一”是始终贯通“多”的命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哉!”(《论语·里仁》)。仁道内涵极为丰富,惟有将“忠恕”这一仁道本质浸润于各种道德规范中,才能经受住对道德的操练与考问,“一”才能“多”。“一以贯之”的取向或许是从《易》得到启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睿智的他自能将其中“以一御万”的《易》哲抉择而出,用于建构道德体系,以道(一)隐帅他人文关怀的具体行为(多);也用于体认事物,如他透过《诗》三百篇卷诗行,以一言“思无邪”蔽之,博(多)而能简(一)。可见孔子与摒斥“多”的老庄不同,采取了重“一”更崇博的态度。这样“一以贯之”之道作为内在的向度,为王弼的“举本统末”所接受。他注“吾道以一贯之哉”曰:“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不过,王弼将孔子的“仁道”会通为“无”,《述而》“志于道”王注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而且王弼把举本放在第一位,统末放在第二位,认为举本可不必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韩康伯引王弼解《系辞下》)虽有不同,但“一以贯之”为王弼接受且成为诠释话语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弼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用慧眼透过迷象,挖掘《周易》精髓,并用与此心弦相契的老庄、孔子相互绎释。胡渭《易图明辨》说:“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曾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张善文先生说:“但凡老庄哲理有与《易》理密相沟联旁通者,王弼互为引据参证而阐发精义。”[3]切中肯綮。的确,“举本统末”的思想是对《易》、孔、老三家思想资源整合深化触类旁通而生成的,反过来这独树一帜的理论又显豁了“以一御万”这个命题。
二、《文心雕龙》对“以一御万”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弼作为思想的巨擘,挟裹着玄学之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两汉观念的同时,也使魏晋南北朝广扇玄风,刘勰受其浸染自属必然,其中“乘一总万”、“以少总多”的观点即是受“举本统末”、“以一御万”的影响而产生,不过刘氏自己的贡献也颇显著:将哲学思想改造成文学思维的一个范畴,同时探讨了“一”的“由然”,使“一”的本然有了着落,从而避免了玄而不实的理论缺点。
王弼观照事物时以“无”为本,执本以统末,刘勰接受了“执一御万”的理路,也认为文由“道”所生,文之理(德)亦为“尽稽万物之理”的“道”所生,文学为道(无)所主宰。《文心》首句即标举“文之为德也,大矣”,这言短意长的话给文学定了位:文“为德”而非“为道”。因为“道”为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德”为一物所以生之原理,“德即物之所得于道,而以成其物者”[4]。刘勰的本义是指作为“道”的外在形式,文学尚需“原始”,以期“要终”(文),所以《文心雕龙》开宗明义曰《原道》。刘勰认为外物皆有自然之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而人文之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可见这是从“文”的本体论上演义或发挥举本统末、乘一总万之原则:从“本”上把握文学,把握各种文体以及文学创作。尽管所原之“道”含义与庄子、王弼的不同,但理路别无二致——寻求形上层面的“道”作为依据,以少总多。
为将原道以总文的思想落到实处,刘勰采用了以道为体,以经为用,以道总经,以经总文的方法。《宗经》:“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五经乃“道”之寓体,统而下之,又为群体之原。“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五经之于二十体犹如本源与支流、本根与枝条。《诸子》:“然(诸子)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序志》:“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倡扬宗经师圣之作,而对“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如楚艳汉侈者,则疾呼,“正末归本”(《宗经》),执著地贯彻着举本统末的思想,以使众体各有所宗、所循。
对包括许多品类的文体,刘勰则摄取其共同特征,“一名举之”。《明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以诗(一名)包举三言、六言诗等。《杂文》:“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以杂文(一)总括典诰等16类。《书记》:“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试……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书记一名,所总六类二十四品。《论说》:“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八名区分,一揆宗论。”以“论”一名归总议说等八名。总之刘勰面对“名号多品”的文体,以“情理同致”为准,总括其名而并归一体,运用的方法恰是乘一总万,举要治繁。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不同的文体均有自身之理。刘勰又将“乘一总万”方法推而行之,“若乃论文叙笔……敷理以举统”(《序志》),以“一”(各文体之道)统领、指导“多”(内容、语言、形式等)。《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以雅润清丽为诗歌的范式,其测度诗人、诗篇曰:“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再如《古诗十九首》契合五言清丽标准,被戴上了“五言之冠冕”的桂冠。因“赋”为“诗”之流,故其理亦从诗理中衍生。《诠赋》:“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此立赋之大体也。”丽词雅义为其要义,评骘赋家就有法可依了。班固、扬雄的赋内容合乎儒教,评曰雅赡、深玮;宋玉、司马相如等词采过丽,评曰淫丽、艳,那些执著于繁词丽语而无贵风轨者更为刘勰所诟病,“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刘勰严格地举要以定繁,强调以文体之理为本,以本统末,反对弃本穷末。
平情而论,创作论是全书最精彩、最富创造性的部分,“乘一总万”的理论、方法不但没有被摒弃,却成为很重要的创作原理。文学创作各人异面,但刘勰说“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创作不能任心所欲,应用“术”驾驭群篇。什么术?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这是从写作的总体方面来要求的,针对具体的操作刘勰也有详尽的表述。《附会》:“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整理词语,安排章义,宜抓住全篇纲领,以之为的,使每段之理繁而不背,全篇语言多而不乱,即总纲(道理)以治繁(章义、语言)。对于遣词造句,刘勰提倡“以少总多”。《物色》:“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穷形尽貌,言简意丰,“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反对直白无味,亦不屑“重沓”、“鱼贯”,“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同上)。文辞宜以大道、大体为宗,若以繁词丽句为务则庶几远矣!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在布局谋篇上他也要求以义统篇,以义准章。《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本振末从,据文理体本而谋章篇、构字句,“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意”指字意,如《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熔裁》:“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义”指篇章义,如《征圣》:“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周易》之“义理”。刘勰认为一章所表达的义要总括、穷尽句意字意,章节之间要以全篇的情理为宗,才能开合放收,无往不适。即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文章自会粲然有章,炳彪千古。
《文心雕龙》整个结构框架也贯穿着“乘一总万”的思想。《序志》:“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刘勰效仿《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做法,定《文心》五十篇,前四十九篇为用,阐述他对文学的具体见解;最后《序志》即虚而不用之“一”,谈及写作的目的、方法、态度,特别是创作原则及全书内容,有“以驭群篇”之用,可谓“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韩康伯引王弼语)),乃见刘勰受《易》学思想或以一御万观念影响之大。即便在“叙文论笔”部分,他也没有信马由缰,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通论文体二十篇,纲领明矣”,一以贯之,则条理清晰,杂而不越,使《文心》在各方面均达到精致深刻的程度。
不难看出,在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以及全书结构安排等许多方面,刘勰都运用了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方法,所以在他自上而下建筑的这一金字塔的文论体系中,体大而又眉清目秀,博深但不芜杂玄虚:以道统经,继而以经制式(文体),间或以体总类,然后以体品文或作家,至此这一伟大的工程似乎大功告成——“道”总领一切,各个阶层均有所系所属,但他并未满足,又对文学的基石(作品)进行了开掘。在创作论中,他没有执迷于芸芸众生的个体差异,而是作为共体深入到“文”的内部,“擒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序志》),割情析采,一仍其旧地执行着他深谙的执一御万、以少总多的原则和方法,如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等将构思形诸笔端的部分,要求“乘一总万,举要治繁”,至今仍为不移之论。自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承继王弼思想并有所拓展有关,但若不能体认到他探究“一”的由来——“博而能一”,创新完善举本统末思想的功绩,显然是不全面、不公正的。
《周易》讲“变通”,变而通,凸现物极必反之道;“博通经论”(《梁书、刘勰传》)的刘勰则讲“通变”,通而变,朗显通透方以致变之理,所以在构思过程中突出“博”——博学、博见、博思。《神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事类》:“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博学为附辞会义的先决条件,刘勰称之“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同上),而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是言辞、神思的渊薮,作家平时务必博见、综学,加以取资。但“博”非“驳”,用事取理贵在精约核要,避免杂漫无端,做到博而能一,以一(理)约博。《通变》:“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博览且能总要,才不致偏激浅陋。《神思》:“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博见则治学浅知贫,贯一则拯辞乱才疏,博而能一,必无贫乱之病,有助构思。《文赋》也讲“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强调汲取词藻,虽可取,但辞溺者易逸出“理”的总摄,伤风害骨。缜密的刘勰十分强调“总要”,《论说》:“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谓式矣”,《议对》:“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公孙弘的对策,“简而未博”未尽善尽美,但要约的优点使皇帝将下第改判为第一。简言之,“博”为知识储备阶段,“一”是构思捃理阶段,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后者则是前者的提升结果,这种先后而密切的关系就凝聚在“博而能一”的前“形于言”阶段,成为“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前提。
风格体势论中也能看到“博而能一”的轨迹。体势由文体所决定,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体势,作者应总体势,“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同上)不是偏废,而是以“正”为主,“执正以驭奇”,成“总一之势”,即风格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否则,无论“逐奇而失正”,还是摄正而弃奇,都背离“总一之势”。刘勰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不仅体势重“兼通”,文章的用事也讲“总会”。《史传》:“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博而一,作品单一贫乏之弊亦不复存在。
通观创作论,可以寻绎出刘勰大体把它分为两大阶段:前为构思阶段,后为具体写作阶段。《奏启》:“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与“举要治繁”不同的语序可窥出刘勰“文心”:前者体现着博而能一、治繁到举要的创作心理,后者表现着乘一总万、举要到治繁的创作倾向。因此其创作论表现为博——一——博的模式,内涵丰富,从而弥补了王弼观念“一”、“本”从何而来的理论盲区,也修正了王弼识要不在博求的理论误区。也应指出“博而能一”观很可能掬挹了孔子“博学”而“一以贯之”思想的芳液,自然他的“通而变”才是他文学思想“体大精深”的内因。
任何伟大的能垂范后昆的思想、作品都是方轨前秀的结晶,刘勰的和王弼的也不例外,因此本文深挖“乘一总万”思想渊源,以见其厚重的文化根基,以及刘勰对它的理解:依托着前人雄厚的思想积淀,精心付诸实践,建立起一以贯之且有转化生成功能的理论,并形成与之配套的有序的写作结构体系。一旦梳理出这条主干,我们对《文心》就有了整体上明晰的把握,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不是琐细片面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领会刘勰的思想及《文心雕龙》的文艺观。
收稿日期:2003-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