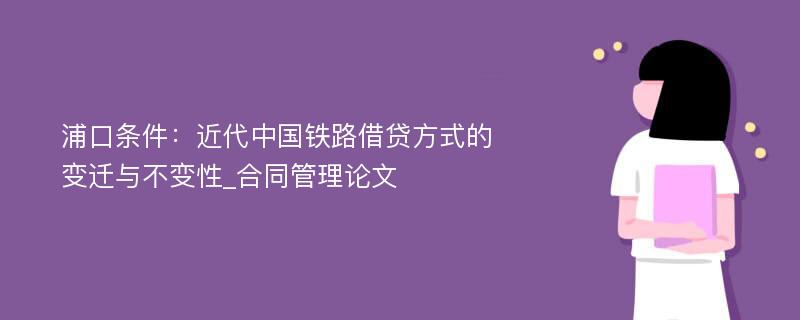
“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浦口论文,近代论文,中国铁路论文,条件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浦口条件”,指1908年1月清政府与英国华中铁路公司(Chinese Central Railways,Ltd)和德国德华银行(Deutschg-Asiatische Bank)签定《津浦铁路借款合同》时所确定的有别于以芦汉铁路借款为典型的“以路作抵”借款模式。马士(H.B.Morse)对其的定义是;“借款并不是以铁路的收入,而是以某几项指定的省库收入为担保的,”并规定“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注:[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97页。)。中国方面虽很少用“浦口条件”这一概念,但两者基本内涵一致,用负责津浦路谈判的张之洞的话来说,这种借款模式即是“让利争权”,改以路作抵为地方税作保,将“造路、借款划分两事”(注:《张之洞致袁世凯、梁敦彦电》,光绪三十五年五月初三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06页。)。为行文简洁,本文借用“浦口条件”的称谓。“浦口条件”与“以路作抵”的最大区别,就是外国债权人不再拥有铁路本身及其进款作为抵押,因而不能直接控制铁路的修筑和经营。在近代中国铁路外债史上,“浦口条件”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的形成和运用与晚清的收回利权运动密切相关。不少研究者予以基本肯定,认为是近代中国借款模式的改善,有利于中国引进外资,发展铁路交通;也有人称这只是一种“骗局”(注:参见许毅主编:《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宓汝成著:《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且在相关的论述中对于“浦口条件”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往往付之阙如。对于这一近代铁路外债特殊形式,笔者不揣浅陋拟作一新的探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一、收回利权与“浦口条件”的形成
1905年初,在收回粤汉铁路的影响下,津镇铁路预定经过地区的绅商也提出“援粤汉之例,废约自办”。他们于1905年6月致电清廷外务部,要求废除1899年与英德银行签订的草合同(注:《留日学生致外务部电》,《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按川汉、粤汉两路办法,筹款自筑,并且初步议订了筹款的方法。此时清政府任命因不久前成功赎回粤汉铁路而官声颇佳的张之洞遥为参与。但是,张之洞和袁世凯均不支持废止津镇铁路借款草约,他们均认为津镇路的国际背景更为复杂,主张不可轻言废约,拒绝了三省绅商的废约要求。袁世凯在给山东绅商要求自办铁路条陈的批复中,虽承认“借款造路,本非善策”,但强调1897年曹州教案条约中已准“德国在山东盖造胶济胶沂铁路两道,俟铁路造至济南后,并可开造由济南往山东界之路”,英德合作投资津镇路已是德国让步的结果,若“津镇果归而曹约具在,仍多棘手,故就山东一省而论,其于曹州教案受害已深,仅争津镇尚属无济”(注:《直督批示东绅请办津镇路事宜》,《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张之洞也认为赎路是得不偿失的,“假如真能废英、德两国借款之约,恐德国一国必将径行独修山东境内之路。执定曹州条约,悍然不顾,硬自兴工,则直、苏两省争回之路甚短,而山东全省路权沦陷外人之手。两相比较,轻重悬殊。”(注:《张之洞至鹿传霖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797页。)但张、袁二人还是利用三省绅民的废约要求,指示具体经手谈判的外务部侍郎梁敦彦与荚德财团讨价还价,做到“让利争权”(注:《张之洞致袁世凯、梁敦彦电》,光绪三十五年五月初三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6页。)。
此时,英国方面主要精力放在广九铁路、沪杭甬铁路和沪宁铁路,因为这些铁路完全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在津镇铁路贷款中英国只占到1/3,更重要的是出面谈判的是有法国资本在内的华中铁路公司。这样,英国政府给予的外交支持是有限的。朱尔典在评估这条铁路的价值时是“犹豫不决的”(注:Frank 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2,P.366.),并称对正在商议苏杭甬铁路兴趣更大,“我们看津镇铁路不甚紧要,着重在苏杭甬铁路”(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57页。)。德国年来就是勉强同意与英国台办此路,它对山东境内自己单独控制的铁路更为关心(注:Frank 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2,P.366.)。英德对津镇铁路的这种态度使得张之洞和袁世凯能在不“轻言废约”的前提下,利用英德之间的矛盾,提出一些具体意见,争取做到修改草约、让利保权。在1907年6月10日,袁世凯即提出:“与外人言三省必欲废约为第一义,与商借款四千万自造为第二义,痛改草约必将前拟之七条办到为第三义。第一义万办不到,而万不可不向外人一言;第二义如能办到极好;第三义必能办到,似亦不能谓之不好”(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5页。)。这里所提的“前拟之七条”是指张之洞在1907年5月间向袁世凯提出的修改草约的七个要点,其核心内容是“华官管事之权宜重”和“存款之权宜操”(注:《张之洞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0页。)。随后,梁敦彦提出“借款须另指三省的款作抵,不能以路作抵”(注:《张之洞致袁世凯、梁敦彦电》,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5页。)。对此,张之洞颇为赞同,称“以他项的款为抵押,此节最重要”(注:《张之洞致袁世凯、梁敦彦电》,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6页。)。对于借款不以路作抵,华中铁路公司代表濮兰德(J.O.P.Bland)不仅没有提出异议,而且还放弃了任命外籍总工程师和会计师的要求,只是要求帐目以英文书写,银行得以随时检查(注:Frank 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2,P.371.)。对于这一方案,德国外交部及驻华公使穆默表示不满,认为英国意在削弱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此时德国的金融市场不景气,加上德华银行此时正在谋取粤汉路的投资权,对于此有利于中国的条件只有暂予承认。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H.Cordes)曾亲赴汉口面见张之洞,表示“甘心退让,以结好于中国”。最后商定借款办法十五条,其中对中方较有利的条款包括:“借款不能以路作抵押,另指三省之款作抵押”,“英、德两工程师只管造路工程之事,不得干预他事”,放弃享受余利二成之权(注:《张之洞致袁世凯、梁敦彦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7-808页。)。1908年6月,张之洞已经与德华银行和华中铁路公司就合同条款基本达成一致。但德国外交部对此方案没有立即予以批准。迫于外交方面的压力,德华银行“采用了拖延的策略”,迟迟不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华中铁路公司的后台老板汇丰银行对此不满,它威胁德华银行,若不同意签字,则津浦铁路借款协议将要等沪杭甬铁路借款协议达成之后才能重新考虑。这样,德国方面为不致协议落空,很快同意相关的条款(注:Frank H.H.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2,P.372.)。
1908年1月13日,梁敦彦与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英华中铁路公司代表濮兰德,订立了《津浦铁路借款合同》(注:时沪宁铁路将竣工,为与之联结,清政府将津镇铁路的南端由镇江西移至南京对岸的浦口。其路线也相应作了变动,原先只经过直隶、山东和江苏三省,现增加了安徽。)。合同规定,借款额为500万英镑,其中英国占37%,计185万英镑,德国占63%,计315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为30年,93扣。借款由以前以铁路路产及进款担保改为由地方税厘担保,担保的税厘包括:直隶厘金每年关平银120万两,山东厘金每年关平银160万两,江宁厘金局厘金每年关平银90万两,江苏淮安关厘金每年关平银10万两。合同中明确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管理”。但在修筑铁路过程中,清政府在南北两段必须任用银行认可的英国和德国的总工程师。铁路建成后南北两段合并,设一总工程师,在借款未还清前,该总工程师必须任用欧洲人,只是不必得到英德银行的认可。此外,在筑路期间,银行方面有经理购买外国路料之权,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购英德的材料,银行并可由此得到购价5%的佣金。与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德华银行和华中铁路公司在津浦铁路建成后,并不占有管理权,外国银行可以分取余利二成的规定也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一次发行的300万镑中一次性提用20万镑作为“酬劳”(注:《中国外债汇编》,附录,第122-131页。)。
合同签订后,奕劻、袁世凯、张之洞曾上折称此合同“确能于造路、借款划分两事,不特主权、利权均无损失,于原订之草合同多所补救,即凡兴工、用人、购料以及提款、还款各事宜,均操之在己,毫不授人以柄。较之他项路约,实为周密”(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邮传部后也总结说:“津浦之所指抵各项,本属虚名,在彼藉此以安债东之心,在我即藉此可争交换之益。至应还本息,我本无到期不还之意,实无虑因此而受人干涉。”(注:叶公绰:《遐庵汇编》,第1辑,上编,公牍,第79-80页。)连置身局外的盛宣怀也认为,“津镇路约比照沪宁路约,便益甚多”(注:《密陈苏杭甬原约案详确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愚斋存稿》,卷14,第7页。)。山东、直隶、江苏三省绅商对借款与筑路分为两事,“均无异词”(注:《奇哉直东苏绅商之争路》,《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3期,1907年8月3日。)。此后,对“浦口条件”的称誉也是屡见不鲜,1909年,郑孝胥在日记中称此为“最优之合同也”(注: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29页。)。对于“浦口条件”,外人也普遍认为它削弱了外国对中国铁路的控制,它使得铁路借款模式“更接近于中国想完全控制自己铁路的目标”(注:Frank 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2,P370.)。“浦口条件”在原则上已取消了英德在草约中所确定的对铁路联合管理的原则,甚至认为“债款已没有凭借抵押”。所谓捐税抵押并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债款的控制权实际在中国人手里。”(注:A,G,Coons,The Foreign Public Debt of China,1930,P34.)
在1905年后收回路权的过程中,社会舆论虽将目标定在绝对地排拒铁路外债,但是在他们看来铁路外债并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令中国丧失利权更重要的是以路作抵这种借款模式。在收回利权中,人们开始对芦汉铁路借款进行反思。他们认为芦汉的症结是“所筑之路与材料供担保,并管理行车事家亦概付之外人,虽我国亦派有行车监督,不过徒有虚名,位置一官吏,开支一薪水而己,其实权皆授予与外人而莫敢顾问,是无异于允外人在其殖民地筑路也,”芦汉借款的后果是严重的,招致列强纷纷效仿之:“自芦汉借款契约宣布后,各国群知可借筑路以握有实权也。英法德美遂相继要求路权,路线所至之地即某国势力所及之地,该借款重要之条件即债务者不能如期履行契约偿还借款,债权者为保护权利得以充分之方法自由处分。是各国争欲借款迫我筑路,明则谓助我交通机关之发达,以兴商务,阴则逆料我之财政竭蹶,如期不能偿还,可实行管理以遂瓜分之策。”(注:《论铁路国有主义与民有主义之得失》,《东方杂志》,第4年第7期。)以路作抵的实质是一种特殊抵押,又称准抵押,以权利为抵押标而设立的抵押权,权利标主要指次于是所有权的不动产物权,包括财务管理权、经营管理权。芦汉等铁路外债的实际效果是:在难以预知是否能如期还本付息的情况下,事先执行了“用于抵押的收入届时不能兑现,抵押品将归债权方支配”的抵押原则,否定了债务人对抵押物的实际所有权。(注:《担保》,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93页。)杨度曾著长文《粤汉铁路议》指出以芦汉为蓝本的粤汉铁路之借款,即是“盖即以铁路及全路产生归美公司所有而已。”以路作抵并没有从法律上赋予债权人所有权,但这种以路作抵使债务人实质上丧失了抵押品的所有权,“本利及各项借款不还清时,不能再行抵押。夫一物权可生无数抵当权,但视之所值之多寡,以为次数之多寡。若头次所抵之债款不能改其所值,则以之再抵、三抵于他人皆可也,不必仅抵一次,亦不必二次、三次仍须抵与第一次之债主也。此非头次债主所能限制者。今此合同载明不能再行抵押,是我欲再抵于他人则不可,若仍向彼借仍以此为抵则可。并我借债之权而限制之,则并头次抵押之名亦有名无实矣。”(注:杨度:《粤汉铁路议》(1905年3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对此,张之洞和袁世凯在津镇铁路借款交涉已经意识到了,而且清政府也认同了这一观点,并渐定为外债政策之一。1910年9月,邮传部在公布的《借款办路说帖》中,总结说:“从前契约失败,约分两端:一日伤权,二日损利。伤权起于抵押……团抵押侵及用人而权更伤,”这是对晚清外债抵押危害的痛定思痛。在随后颁布的《外债条例》中,第一条即是“严禁抵押”,“按以路作抵,路线所至,国权随之,此通论也”。所抵之路若与势力范围“有出入”,则“必起纷扰”;若在势力范围之内,“则自就抑勒”(注:《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中国时事汇录。)。
应该说,此时正趋干高涨的收回利权运动所形成的巨大舆论力量是外国财团不得不放弃一些苛刻条件的重要因素,而“浦口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收回利权的要求。美国人司戴德(W.W.Straight)的一段话可以从反面折射这一趋势:“这些人要求根本改变过去贷款的条件。他们认为‘控制’毁灭了中国的主权,同时他们受了敌对外国利益集团的煽动,……这些官吏的公开目标是要削弱外人对华的压制,且为各省人民所衷心拥护”(注:司戴德:《中国的贷款谈判》,第132页,转引自[美]欧弗莱区著,郭家麟译;《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9页。)。更有人认为这可与收回粤汉路相提并论,因为在这一合同中,英德财团“惟对于事业而贷与资本耳,凡此皆直接收回利权运动之现象也”(注:陈彦彬:《论收回利权之宜有根本解决》,《外交报》,第263期,1909年12月。)。
二、“浦口条件”的虚抵及其实质
考诸史实,“浦口条件”虽使外人不能直接对铁路的建筑和管理进行控制,但它并非是一种能完全挽回利权的引进外资模式。对“浦口条件”的不满当时即有之,这既与当时对外债的排拒有关,也与对外债担保与抵押之间区别的误解有关。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外债排拒倾向导致对任何引进外资形式的否定。他们认为以芦汉铁路借款为蓝本的“以路作抵”的借款,铁路名义为中国所有,实际上完全变成了外国债权人“承办”铁路。津浦路借款改以捐税担保,力图做到中国“自办”,但是由于外国势力的渗入,所谓“自办”只能是自欺欺人。“既不以铁路作抵,自不须牵涉造路。既云用以造路,界限便不分明”(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第515页。)。“且彼当与路政毫无关系之日,尚恃其强权强吾借债,而谓于既有关系之后转能逡巡退让甘居事外,其孰信之”(注:《论苏抗甬铁路借债之不可许》,《东方杂志》,第4年第10期。)。甚至有人认为,借款以盐厘作押,铁路虽“避押款之名,实受两押之祸”(注:《汇报》,第10年,第74号。)。这是在强烈的拒债情绪下对外债担保概念的误解。
从合同的规定来看,以地方税收担保有三个特点,一是指定担保的税收必须有明确的数额,这一数额基本与每年还本付息的数额相等,只有超出抵押额的税收,中国才有支配权。二是如发生不能如期支付还本付息的情况,中国政府有义务将相关各省的其他税收收入交与银行抵付本息。三在借款未还清前,相关税收尽先偿还借款本息,不得同时抵押其他借款。尽管这种担保方式并不违背贷款担保的一些基本原则,但从中国方面而言,这和当初的设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距离。盛宣怀对这种担保理解是虚抵:“政府恐其干预路政,故度支部指项作保,声明邮传部铁路进项无著,始由度支部筹还。凡洋债均系指明或税,或厘,或盐,或粮作为虚保。”(注:《寄程雪帅》,宣统三年五月初三日,《愚斋存稿》,卷77,第20-21页。)梁敦彦也称:“借款既系中国担保,所指亦系虚抵,将来仍由路利清偿,似不必定囿于三省也;请他省协助,亦无不可。”(注:《梁敦彦至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海防档》,戊,铁路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57年版,第524页。)应该说他们通过与“以路作抵”的形式比较,发现用税捐作虚抵可以使中方获得对铁路的实际控制,因而他们强调借款条件中的信用担保,避免因铁路本身抵押而丧失大量的利权。但是张之洞等人仍没有完全分清信用担保与实物抵押的区别,时而称为“作保”,时而称作“作抵”。在致袁世凯、梁敦彦的电中(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张之洞称:“借款不能以路作抵押,另指三省之款作抵押。”而在此后的奏折中又称:“此项的款,只作担保之用,并非实在动拨。”(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第474、477页。)其他人亦复如此。但是,外国债权方则很明确地强调在债款本息不能偿还时,由作为担保物的税捐来偿还。所以,它们要求担保税捐的款额必须与每年要偿还的本息等值。华中铁路公司起初提出借款500万镑,每年作保之款至少须400万两。当英方发现因禁烟土药税已不能作押时,便提出包括用人、行车管理等内容的额外要求。参加谈判的梁敦彦提出为“杜其干权之渐”,还是“能足其数为妙”(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路资料》,第二册,第809页。),这实际是在放弃理想的虚抵模式,而强调偿还的切实性。这种概念上的混乱至少表明他们仍然将担保或抵押与偿还混为一谈,如此则所谓以路作押和以捐税作保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强调的“虚抵”并不虚。邓孝可曾尖锐地讥责盛宣怀的虚抵主张,“盛宣怀能保作抵之物,将来债务不履行时,外人终不实索乎?如仍实索,何以别之曰虚”(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3页。)。正因为如此,外国银行以中国信用不佳为借口,同样也强调担保的切实性。1908年3月,英德财团提出在借款招帖中必须明确写明担保物的数量,因中国方面“向无如各国之官家财政综计表可查”,要求中国政府将“直隶山东两省及南京厘税局与江苏淮安关之光绪三十一、二、三(1905、1906、1907年)三年之均分厘税进款数目”呈交外方(注:《外务部收德使雷克司函》,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海防档》,戊,铁路二,第600页。)。中方对此并无异议,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虽然外国债权人不能直接对这些捐税的征收进行控制,但从直接效果而言,能保证债券获得投资人的信任;从长远效果而言,则可以借此达到使中国政府如期还本付息和间接控制中国财源的双重目的。
由于受拒债观念影响,一些舆论认为“浦口条件”的形成不是缘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的让步,而是表明了中国方面轻易地放弃了废约的要求。所谓“浦口条件”“系补救津镇合同之失败,从事后设法挽回,不得不勉强迁就”(注:《黄侍御瑞麒奏折》,《湘路新志》,第二期,宣统元年十一月十日。)。实际上,袁世凯在交涉之初即称他对绅商要求津镇路废约“实不敢承命。如必不得已,现惟有隐藏废约字面,仍抱定改订合同,另设难题数条,请外部与之试商。……看德、英如何对答,再相机挽回几分利权,以慰三省士庶之望”(注:《袁世凯致张之洞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799页。)。在这一问题上,张之洞与袁世凯的态度是一致的,“不过欲借三省绅民为抵制,庶彼族肯将章程多改,多收回几分利权耳。……辩论、抵制者,措词之空中波澜也。结束者,办到之实事也。”他所讲的“结束”并非指废约,而是改善借款条件。他们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利用商绅的反对,做到“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二是对商办不信任,张之洞明确指出,“盖此路若归绅商自办,十年难成,一无款,二乏人,三各有争心不能划一,四糜费必多。何若听英德代修,指刻期告成之路,招本稳利丰之股,分年集之,一举赎之,岂不至易、至简、至稳、至实哉。”(注:《张之洞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799-801页。)张之洞所以有这种认识,是因为粤汉路收回后并未有预期的效果,“粤汉铁路争回两年,并未多修尺寸之路,可为前鉴。”(注:《张之洞致李嗣香及三省同乡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3页。)他认为“惟废约二字,总须随时留作谈助耳”(注:《致天津袁宫保,京梁崧进生星使》,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张之洞全集》,卷268,电牍99,第11册,第9627页。)。仅仅依靠绅商的废约要求所形成的舆论压力,难以在对外交涉中真正做到挽回利权。这应是“浦口条件”没有使借款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的症结所在。
对于“浦口条件”的核心内容——借款与筑路分为两事,主持谈判的张之洞对之并不完全接受,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徒具虚文之嫌,这倒是“浦口条件”在借款模式中所体现的“不变”之处。在津浦铁路借款交涉之初,张之洞并没有明确要求在筑路方面的“自办”,只是强调路成之后完全自主的管理。他曾对三省京官称“修约”的关键是由英德代造,路成后再由集股收回:“至若废约,即万办不到。且不如改约,英德代造。四年必成,十年赎路。届期已积有余利二千万两内外,三省仅须合筹三千万两,即可将全四季收回。若由自办,则必须筹足五千万。路尚造,集股断不踊跃,十年断不能造成。……。诸君务须详筹熟计,切勿徒徇废约虚名,反无实益也。”(注:《张之洞致李嗣香及三省同乡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3页。)这一观念更体现出了他的“造路不如赎路”的主张。对此,三省京官表示异议,“仍愿抱定原奏自办主意,设法措词,坚持不挠,乃可收回利权。”(注:《三省公所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张之洞全集》,卷267,电牍98,第11册,第9618页。)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后的合同改为所谓借款自办,其核心内容是“北端用德工程师,南端用英工程师,均由中国总办此路之大员自行选取用,此工程师应听中国总办提调、节制、调度”,“英德两工程师,只管造工程之事,不得干预他事。”(注:《致袁世凯、梁敦彦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7页。)
但是,这种对洋工程师的限制并不具备实质性的意义。时任沪宁铁路总管理处中方代表的沈仲礼就称借款与筑路分为两事虽然对于利权“颇多挽回”,但此“亦就表面观耳”。他认为失权的关键之处是外国工程师的特殊地位使其可以大权独揽,而这与铁路合同条文的规定并无必然的联系。因为铁路在修建过程中“一应交涉,何莫非工程之事”,外国工程师的特殊职责“遂使工程司独断专行,全权在握。偶有指驳,既无以发其复,即无以折其心”(注: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即便是借款筑路,用华人工程师是实现真正自办的前提。“非用中国工程司则虽名为自办,而将来必无自办之实权。”(注:留美工学博士胡栋朝:《中国各省铁路办法撮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一年年二月十三日。)所以,“浦口条件”规定由中方承认外方选派总工程师和由外人直接任命总工程师并不具有本质性的区别。英国外交部和汇丰银行对此均不讳言。合同签定后,英国外交部并没有对此有过度反应,称:“没有外国的控制对于贷款是危险的。但是它并没有什么”。阿迪士也曾表示,“我相信,只要有合适的工程师,无论是在铁路建筑过程中还是通车后,对铁路的管理实际上仍可掌握在外国辛迪加手中,这足够有效地保证债券持有人的权利”(注:Frank 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2,P371.)。可见外人对工程师一职的控制功能颇为自信。张之洞也不否认外国工程师的特殊职责,他称“路虽系自办,工仍须包与洋工师,方能合法迅速。若由中国官绅自出心裁,恐必致耽迟缓”(注:《张之洞致鹿传霖、高泽畲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08页。)。所以,当时即有人指责这种所谓自聘总工程师的自欺欺人之处,“总工程师既须由银公司认可,则是银公司所认许者,中国方得用之,银公司所不认许者,中国不得而用之,是中国虽有自聘之名,银公司实操用人之实,而用工程师之权既已在银公司手中,则建造管理之权,其在银公司手中,不在华人手中,已不待辩而自明。”(注:《苏杭甬路约驳议》,墨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二册,时论,第4页。)
津浦铁路合同订立后,对外国工程师的指责仍屡见不鲜。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吕海寰也承认“该路用人既多,虚糜亦巨,日前外间已有烦言”(注:《津浦路奏派邦办之原因》,《申报》,1908年10月2日。)。《申报》曾公开报道津浦铁路上外国工程师和其他管理人员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以示不平。它称津浦路订立合同后聘用洋员71名,其中总工程师一名,年薪高达2500镑,副总工程师一名,年薪1500镑,另加每月津贴费150元(注:《律浦路洋员之薪水》,《申报》,1910年3月23日。)。面对舆论的指责,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只是表现出无奈,称津浦路虽“为自办之路,仍多掣肘,必致浪费巨款,臣殊无两全之策”(注:《吕大臣密陈津浦路为难情形》,《申报》,1908年10月1日。)。所谓没有“两全之策”是指这些洋员一般订有聘用合同,难以解聘。他强调自己虽想做到“审慎用人”,但又不能自主用人。对此,他的解释是:“从前舆论皆以雇用洋员太多,动相诟病,臣等体察情形,订有合同者未便无故撤退,未订合同者即便革除,节省亦复有限。”(注:徐世昌《整饬津浦铁路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奏议二十九,卷29,第4页。)合同订立两年后,时任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在一次召对中对载沣称津浦这种借款筑路模式同样也是“利隐害显,监国甚嘉纳”(注:《专电》,《申报》,1910年10月19日。)。这些诸如外人控制下的浪费、冗员充斥等现象虽不能认为完全是源于“浦口条件”,但作为借款模式而言,它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浦口条件”的运用和弃用
“浦口条件”只是一种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铁路借款模式,它还不足成为中国铁路借款趋于定型的模式。然而,清政府“及津浦铁路之契约成,遂自以为得计,足补沪宁之失,而以后之筑路无不可借外债以成之也。故粤汉、川汉两路遂有借外债之命”(注:邵羲:《论借外债筑路之利害》,《外交报》,第232期,1909年2月。)。社会上也有一部分人附和之,“近来财政家之新识解,则曰借款造路,苟能不以路作押,另以他项动产作抵,而如期付息,既不干预路事,虽多借亦属无伤。”(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97页。)因而所谓“浦口条件”成为清末最后二三年借款筑路中清政府与外国银行交涉的一种蓝本。
在1907-1908年的沪杭甬铁路和1909-1911年的湖广铁路交涉中,外国银行虽然在最终的借款合同基本上执行了“浦口条件”,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外国债权方逐步加强了对铁路的控制,并最终弃用了“浦口条件”。1908年初,清政府外务部面对江浙绅商强烈的拒款要求,不断地与中英公司(The British and Chinese Corp)讨价还价,最终订立了沪杭甬借款合同,并以部借部还的形式获得江浙商办铁路公司的认可。外务部认为江浙绅商之所以能接受外债,主要还是在于借款条件的优惠。“臣部注重路权,其初意援照沪宁合同,至广九,津浦、沪杭甬先后磋商,迭有进步,卒使借款办路,分为两事。……津浦合同未宣布以前,民情疑惧。经电商江浙督抚转饬两省铁路公司公举人来京,阅看档卷,先以不认借款为言,嗣经再三开导,南中土夫亦知商部从前委曲求全之意,与朝廷近日不得已之苦衷,不复再言拒款,乃定一间接办法,邮传部承借外债,转拨两省公司为筑造铁路之用。”在原有草约基础上,删除英人任记帐员,并不以江浙厘税作抵,由关内外铁路余利担保,但是由英人任总工程师,“以上各节,较津浦更为加密”(注:“外务部片”,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邮传部奏议类编》,路政,第176-177页。)。朱尔典也承认1908年初江浙拒款的热度开始下降,部分原因是津浦铁路条件的宽松,借款才得以以“浦口条件”为蓝本完成(注:Chan Lau Kit-ching:Anglo-Chinese Dipolomacy--in the careers of Sir Jordan and Yuan Ahih-Kai,HongKong Universiy Press 1978,P.15.)。但是他认为沪杭甬借款合同的订定并不是借款条件“合理”改善的结果,甚至不是“浦口条件”的正常运用,而是清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之间对抗的果。它“将有深远影响”,对于外国债权方是不利的(注:Chan Lau Kit-ching:Anglo-Chinese Dipolomacy--in the careers of Sir Jordan and Yuan Ahih-Kai,P.15.)。沪杭甬铁路借款最后的谈判结果意味着英国利益的丧失,“英国没有稽查权,铁路百分之百地成为中国的财产。”但面对正在迅猛发展的收回利权运动,朱尔典不得不认为这是英国在当时环境下可以获得的最好结果(注:Chan Lau Kit-ching:Anglo-Chinese Dipolomacy--inthe careers of Sir Jordanand YuanAhih-Kai,P.15.)。
即便如此,对这一借款办祛,江浙绅商中也有人明确表示异议,指责清政府完全以“浦口条件”为依归,放弃对利权的争取。1907年9月,由熙礼尔(E.Hiller)接替濮兰德后,中方代表汪大燮给熙礼尔三种选择,第一是此路由两省筹款赔补中英公司从前费用,议定若干数目,应分若干年摊还。第二是借款只用于杭州至宁波一段的建造,但此路管理权仍由中方掌握。第三即是借款筑路,分为两事,另指的款,作为抵押,“所有办理铁路事宜,概不载入借款合同之内。惟将来归还本息,仍由此路进款项下拨付。”(注:《苏杭甬铁路档》,卷5,第2-3页,转引自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50页。)这样即便提供借款,英方连总工程师一职也无法染指。在朱尔典的劝说下,熙礼尔基本接受了第三种选择,但要求派英籍总工程师(注:Chan Lau Kit-ching:Anglo-Chinese Dipolomacy--in the careers of Sir Jordan and Yuan Ahih-Kai,P.14.)。两省官员对此也较为满意,也劝商绅接受这一方案(注:Chan Lau Kit-ching:Anglo-Chinese Dipolomacy--in the careers of Sir Jordan and Yuan Ahih-Kai,P.14.)。但汪大燮受命出任驻外使节后,继任的中方谈判代表梁敦彦却按照津浦合同底稿与之磋商(注:北京政府交通部编:《中华国有铁路沿革史》(光绪十五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版,台湾国史馆1984年影印版,第396页。)。这一做法当时被报章称为“抹煞英商熙礼尔无督办、无查帐、无工程司管理之借款底稿,而比照津浦三者皆有之覆辙以定约,谓为以利易权,又将谁欺”(注:《旅津绅商废章保律公牍》,宣统二年铅印本,第3页。)。他们的理由是,沪杭甬与津浦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已集有大量股本和筑成了一部分铁路,即便借款,完全可以以此迫使英方降低条件,“借数之多寡,利息之轻重,交镑方法,摊还方法,材料购买,以及监督权,管理权,种种尚可磋磨;若径仿津镇,则以上各问题,毫无余地。”(注: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278页。)连汪大燮也对无原则地仿照“浦口条件”不满,他认为自己在交涉中强调子限制外籍工程师的权力,“其工程师事权,向例分二大宗,一为核定工程用款,一为造路要旨。燮与议时,去其一权,只许核定工程用款”(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80页。)。“惟工师专作保证借款而设,此路造成,借款支讫,则此工师便可辞退。”(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939-940页。)而梁敦彦则以津浦路为模式仍给工程师管理工程之权,此对于削弱工程师的权限无太大作用(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984页。)。
这种不满也是此后江浙铁路公司抵制并驱逐英籍总工程师的原因之一。1911年2月,江浙两路公司股东召开会议,均要求辞退英国总工程师(注:台湾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戊,铁路二,第944页。)。在江浙绅商的压力下,1911年8月,中英双方曾有意废止借款合同(注: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宣统二至三年),第2201页。)。但在清末民初实行铁路国有化的过程中,英国又得以重新加强对铁路的控制。1914年收赎民营浙路时,中英公司强迫中国政府增订契约六条,承允该路总工程师、运输总管、帐务总管各员均须以公司同意之英人充任,后都为沪宁英员兼任(注:《交通史路政编》,第11册,第3735页。)。1916年,又规定如下二项,第一、沪宁车务副总管兼沪杭甬车务总管。第二,添聘洋稽查一员。由是此两路的原订合同等于废纸,外人仍握有极大的管理权,足以控制路政(注:陈晖:《中国铁路利用外资问题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3卷第2号。)。这样与“以路作抵”所形成的外人对铁路的控制难分轩轾,所谓借款、筑路分为两事的“浦口条件”成为过去。
同样,在湖广铁路四国银行团借款中也是这样使“浦口条件”逐步名存实亡。张之洞虽在1905年粤汉铁路赎回问题上态度坚决,但他主要是出于排拒法俄势力南下的目的,他对借款筑路并没有予以否定。当时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就说:“对于取消铁路借款的全部想法,他丝毫不表示同情。”(注:[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1907年中方与英德津镇铁路交涉之时,张之洞曾拟提出按“浦口条件”将津镇铁路借款中的200万镑转借给粤汉铁路:“查鄂境粤汉铁路修造,尚无的款,前与英人商借款项已有眉目。嗣以恐多牵碍,外务部不允,借款迄未成议。然此路关系中国全局,万万不能缓修,而一时猝难筹集巨款。现若以德、英必欲借而三省京官坚不肯借之二百万镑,由津镇转借与鄂,鄂亦以噪声省厘金分认抵款,合同内只言津镇,不说明转借之事,则于津镇路及粤汉路两有裨益。”(注:《致天津袁宫保、京梁嵩生星使》,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四,《张之洞全集》,卷268,电牍99,第11册,第9653-9654页。)袁世凯也认为此举是“自属调停妙策”,”(注:《袁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卷268,电牍99,第11册,第9654页。)此后,张之洞急切向袁世凯称:“鄂省厘金,每年约二百余万两,可抵借二百万镑,此系与英领事商允者,并以附陈。拟恳台端向外部加数言赞成,则全局即日可定。津镇、粤汉,皆受公之赐矣。”(注:《致天津袁宫保》,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张之洞全集》,卷268,电牍99,第11册,第9660页。)但由于外务部不同意,此事只得作罢(注:《齐道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卷268,电牍99,第11册,第9660页。)。
1908年11月,英国中英公司代表濮兰德到达北京,双方就粤汉铁路借款正式进行谈判。张之洞在交涉中提出应按津浦铁路借款条件为标准,“工程师但管分内应办之事,余事皆不得于预”,“凡铁路一切用人、择地、管路、行车等事,均由中国自主”(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第354页。)。但濮兰德一改在津浦路上的容让姿态,完全拒绝张之洞提出的按“浦口条件”交涉的要求,称“借款事如照津浦合同办理,中英公司决不肯办”。但张之洞态度强硬,不愿作出让步(注:《与梁崧生》,宣统元年二月十七日,《张之洞全集》,卷289,书札8,第12册,第10340-10341页。)。对此,外国人认为,中国“最近在从英德那里获得的一笔没有直接监督或留置权的借款的成功鼓励了中国人缔结纯粹的财政借款,不管这些借款日后可能对中国发生的危险。”(注:(美)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2-173页。)在未得到中英公司认可的情况下,张之洞转而与德华银行商洽,并于1909年3月,张之洞与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Heinrch Cordes)签订了中德湖广铁路借款草约。这个草约是按照津浦铁路借款条件确定的,其“大概办法均照津浦合同办理,惟息扣较津浦尤格外公道”(注:《与梁崧生》,宣统元年二月十七日,《张之洞全集》,卷289,书札8,第12册,第10340-10341页。)。然而,中德关于粤汉铁路借款草约签订后,英国方面提出强烈的抗议,张之洞遂很快放弃中德草约,与英方重开谈判。此时,汇丰银行取代中英公司并派熙礼尔与张之洞进行交涉。尽管汇丰银行表示不愿再有华中铁路公司和中英公司在津浦铁路和沪杭甬铁路交涉中的“不幸的经历”(注:Frank 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2,PP.398-399.),希望此次能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但是由于德华银行已提出以“浦口条件”为原则的草约,加上此时两湖地区的拒款运动正趋于高涨,被迫作出让步,1909年6月,由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和汇丰银行组成的三国银行团与中国达成借款草约中,仍是以湖南、湖北两省厘金和部分盐税作保(注:《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3,第40页。)。这与津浦路基本一致,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实系将借款、修路划分两事,于中国主权毫无损失,至折扣之轻,更为中国历来借款所未有”(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75页。)。但汇丰银行对此并不甘心,它曾提出在盐厘担保之外,“将所建的铁路作为平行的抵押”。原因即在于它们“感受了津浦铁路贷款后被欺骗的打击及国会对贷款支出审查的苛刻,同时还有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困难等使它们认为应该确定这样的草合同”(注:司戴德:《中国的贷款谈判》第135页。转引自欧弗莱区著,郭家麟译:《列强对华财政控制》,第149页。)。此建议当时虽没有采用,但最后签订的合同中却赋予债权方广泛的权力:粤汉路用英工程师,川汉路用德工程师;三国公司分别承购材料,英德派遣会计人员稽核铁路用款,铁路盈余存人英德银行;同时三国公司享有支线投资优先权(注:[美]弗雷德里克·裴尔德著,吕浦译:《美国参加中国新银行团的经过》,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2页。)。外国银团显然比此前的津浦路和沪杭甬路获得了更大的控制权。这些在反对借债筑路者看来是极有力的口实,“虽该合同无以路作抵之明文,而银行种种支配干涉特权,实较之明以路作抵者尤足攘吾路权,而制吾死命,则此合同成立,不啻断送该路也”(注: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17页。)。张之洞虽多次称湖广铁路借款比津浦路借款有四大进步,一是折扣从九三降至九五扣,仅此一项就可少损失百万;二是还期短,二十五年还清,三是可多用中国材料,四是在余利方面支付更少。对此当时报刊不屑一顾,讥为“好似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一样”,“真是把我们做小孩子欺哄了”(注:衡云:《敬告乡人》,《湘路警钟》。)。他们强调在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中:“用资购材,既以委之外人,用人经理,复须商之工程师,虽不(以路)抵押而实权所余几何?”(注:《四川留日同乡反对国有铁道意见书》,《时报》,1911年9月24日。)由此可见,国内的拒债派对外国债权人控制中国铁路的担忧,并没有因“浦口条件”的运用而减弱。外国银团同样也对“浦口条件”不满,寻找时机加强对铁路的实际控制。辛亥后湖广铁路的命运就说明了“浦口条件”的原则难以得到持久的运用。1913年因政局动荡,税收减少,英国和其他三国强迫中国将湖广“铁路的财产和材料作为临时的抵押”(注:[美]欧弗莱区著,郭家麟译:《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3页。)。后又订立新约四条,增加铁路财产为担保品,借款全数存放于债权公司,驻路洋查帐员有停付款之权,而且中国政府必须自行雇用洋管帐员及材料总管(注:陈晖:《中国铁路外债合同之史的分析》,《文史杂志》,第4卷第5、6期,1944年9月。)。至此,与沪杭甬一样,湖广铁路也基本上弃用了“浦口条件”。
进入民国初年,因为中国债信低落和国内政局动荡,国内商办铁路公司屈从于铁路国有政策,使得清末拒债运动的主体消失,这对于寻求较为有利的借款条件而言则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而且外国财团对新生的民国在外债条件上更为苛刻。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浦口条件”基本上被外国财团放弃,在1912年陇海铁路借款(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四卷,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1914年的钦渝铁路借款(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储档案史料》,第五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1914年宁湘铁路借款(注:《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五卷,第83页。)、1914年四郑铁路借款(注:《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五卷,第270页。)、1916年的周襄铁路借款(注:《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五卷,第417页。),均是以路作抵。1918年英美的一些金融财团集议成立“共管”中国铁路计划的“国际管理委员会”,在拟订计划的备忘录中,借口中国多数铁路借款的利息支付已经极为困难,不仅要建立由中国交通部和外国债权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而且还强调了在筑路期间要用外国总工程师,行车管理中也应用外籍总经理的原则,认为这“是保证效率的唯一手段”(注:夏良才主编:《近代中国对外关系》(近代史研究专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页。)。对铁路外债抵押问题,外国债权人已不满足铁路本身作抵。1920年4月,在商讨湖广铁路续借款时,美、英、法三国银行团对担保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鉴于中国政府在1913年提出的铁路作为该项借款的附加担保品时就承认原来指定以有关各省税收作为担保已不再生效,同时鉴于目前铁路的状况也不能提供收入来偿还原来的债务,因此显然不能接受以铁路作为此次续借款的满意担保品”(注:《汉粤川铁路督办关赓麟和英、法、美三国银行团代表会谈备忘录》,1920年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因在担保问题上得不到满意答复,银行团不仅拒绝提供续借款,而且提出中国政府应将湖北和湖南两省有关省税交由海关接管(注:《美、英、法三国银行团驻北京代表致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函》,1925年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295页。)。
综上所述,“浦口条件”表面而言只是关于借款抵押方式变化问题,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的要求。然而,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外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基本格局不能得以彻底改变,要求借款条件的部分改善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与中国进行铁路外债交涉中,外国债权人对抵押或担保问题的关注似乎更多在于借款的如期还本付息问题,然而,这并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对于向中国提供贷款修筑铁路,西方政府与银行虽然有不同的动机,但应该明确的是,它们注重的是铁路外债在输出资本和打开市场中的双重作用。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它们认为对铁路的控制比铁路债款的偿还更有价值,这似乎印证了西方金融界的一句名言,“放债而失去债款胜似从不放债”(注:国际清算银行第二任总裁利昂·弗雷泽语,见[美]P·金德尔伯格著,徐子健等译:《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页。)。他们对铁路的控制不仅在铁路的修筑而且在于铁路通车后的管理。对于铁路自身的经济效益,他们并没有寄望外国管理人员的介入而使之获得提高,相反,他们会以中国政局不稳影响铁路效益而要求加强债权人对铁路的控制。这应是理解近代铁路外债的基本出发点。本文虽不能对此进行深入剖析,但可以作为评判“浦口条件”的标准。所谓抵押方式的变化,只是列强对华铁路控制的强弱变化,而不是中外经济关系具有实质性的变动。同时,探讨外国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与铁路发展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作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后者应另当别论。这便是本文所要阐发的主题。
标签:合同管理论文; 中国铁路论文; 抵押合同论文; 铁路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银行借款论文; 张之洞论文; 光绪论文; 银行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