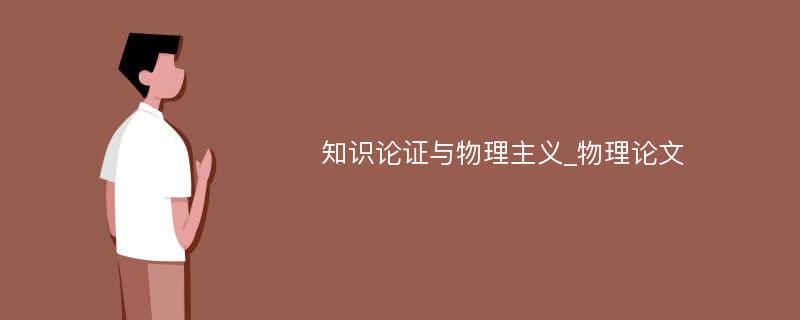
知识论证与物理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理论文,主义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分析哲学中心灵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关于意识的物理主义是否正确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意识的感受特性(qualia)总是由大脑中相应的物理特性或状态所引起的。最通常的例子是疼痛这种意识感受特性是由大脑的C —纤维肿胀这种物理特性所造成的。物理主义声称意识感受特性Q 和其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P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更紧密的“伴随性”(supervenience)关系,具体地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命题来表述:
物理主义的伴随性命题:意识中的感受特性Q 总是伴随着其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P的存在而存在。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一旦大脑物理特性P存在,相应的意识感受特性Q就一定随之而存在。
根据这个物理主义命题,意识的感受特性完全是由其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所必然想像决定的。尽管物理主义的支持者们能给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但是这种理论在直觉上却一时令不少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人们往往觉得尽管在现实世界中大脑物理特性P总是在因果上导致相应的意识感受特性Q的存在,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像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一个人具有大脑物理特性P 但他却感受不到相应的Q。因此在直觉上,P的存在并不能必然地导致Q的存在。
由于物理主义命题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直觉强烈地冲突,许多哲学家都试图将我们的反物理主义直觉发展成严格的哲学论证以便批判甚至驳倒物理主义。杰克逊(Frank Jackson )的知识论证就是少数几个最著名的和有影响力的反物理主义论证之一。① 虽然从杰克逊1982年第一次提出知识论证起,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② 但是人们对这一论证的兴趣和热情却一直不减。不停地有新的讨论文章出现,许多在心灵哲学方面有影响的哲学家都对如何对应这一论证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在2004年由斯图加(Daniel Stoljar)等哲学家编辑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知识论证的论文集。③
本文的目的是对知识论证及其涉及的哲学问题作一个初步的介绍和探讨。下面的第一节中我将先介绍杰克逊著名的关于玛丽的思想实验以及知识论证的论证结构。第二节中我将介绍和讨论对于知识论证的五种类型的反对意见。我将辩论说这些反对意见都不能驳倒知识论证。最后在第三节中我将提出自己对知识论证的分析和诊断。我将讨论这一论证对物理主义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以及这一挑战在相关哲学领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1
知识论证来源于这样一个思想实验:玛丽从出生起就一直被限制在一间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的房间里。在这间房间里通过黑白的书籍和黑白电视,玛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加上她的出色天赋,玛丽最终学会了关于世界的所有的物理知识。她知道了关于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所有的物理事实,包括物理学的、化学的、神经生理学的知识,以及物理世界中一切因果的、关联的(relational)、功能的(functional)事实。
如果物理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的物理事实就必然地决定了所有的关于意识的事实,从而玛丽应该知道关于意识的所有的事实。但是当玛丽有生第一次走出那间黑白的房间,然后有生第一次看到一个熟透的西红柿时,她也有生第一次知道了看到红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意识感受。而这个关于意识的事实在她出房间前她是不知道的,这是她出了房间后才新学到的。因此在走出黑白房间前,玛丽并不知道关于意识的所有事实,尽管她那时已经知道关于世界的所有的物理事实,这就表明了物理主义是错误的。④
在上述关于玛丽的案例中,有两点在直觉上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在离开房间前,作为全能科学家的玛丽知道了关于世界的所有的物理真理,我们可以将这一点称为“完全物理知识宣言”。二是在玛丽离开房间后第一次看见熟透的西红柿时,我们在直觉上强烈地感到玛丽学到了关于意识的新的知识,我们可以将这一点称为“学到新意识知识宣言”。把这两点加起来,我们就得出这个世界中至少有一样知识或真理或事实是非物理的,从而物理主义是错误的。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将知识论证的论证结构表述如下:
第一个论证前提:(在离开黑白房间前)玛丽知道关于其他人的所有物理事实。
第二个论证前提:(在离开黑白房间前)玛丽并不知道关于其他人的所有的事实(因为她在离开后才获知关于他人意识中红色的感受特性的事实)。
结论:存在关于其他人的非物理的事实或真理,物理主义是错误的。
2
在前面提到的2004年出版的关于知识论证的论文专集中,斯图加等编辑们将迄今为止对这一论证的批评总结归纳为五种类型。下面我将逐一地介绍和评论这五种类型的反对意见。
第一种反对意见:玛丽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学到。
丹奈特(Daniel Dennett)强硬地否认玛丽在走出黑白房间后第一次看见熟透的西红柿时学到了任何新的知识。这当然和我们的直觉非常冲突。他把杰克逊的思想实验稍做修改和发挥,假想在玛丽走出黑白房间后,有两个家伙想在玛丽身上搞个恶作剧,他们把几个涂成蓝色的香蕉给玛丽看。因为玛丽知道香蕉是黄色的,他们期待玛丽会指着涂成蓝色的香蕉惊叹道:“哇,原来黄色是这样的呀!”
但是丹奈特断言这两个家伙的恶作剧是不会得逞的。因为玛丽拿着被涂蓝的香蕉看了看后,一定会说:“喂,你们俩搞什么鬼,香蕉是黄色的,怎么你们弄些蓝香蕉来糊弄我?”为什么玛丽能识破这个恶作剧呢?丹奈特说原因很简单,因为玛丽知道所有的物理事实。她知道人看到黄色时的大脑状态P(Y)和人看到蓝色时的大脑状态P(B),所以通过观察她自己或别人在看到那个被涂蓝的香蕉时的大脑状态,玛丽就可以知道那个香蕉是蓝的而不是黄的。丹奈特想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玛丽的确什么都知道,没有人能骗得了她。⑤
那么玛丽真的在走出黑白房间后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学到吗?我们可以争辩说不是这样的。即使在丹奈特改编的故事中,在指出了那两个家伙的恶作剧后,玛丽仍可以这样感叹:“哇,原来看到蓝色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因为玛丽第一次得知看到蓝色的意识感受特性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一事实。
如果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蓝色的大脑物理特性P(B)和其相应的意识感受特性Q(B)是因果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关于黄色的大脑物理特性P(Y)和其相应的意识感受特性Q(Y)也是平行的因果关系,那么玛丽是可以通过她对两个前因的知识来识别两个后果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玛丽不能学到关于两个后果的新的知识。所以说丹奈特改编后的思想实验根本就不能削弱我们关于玛丽走出黑白房间后学到新的知识的直觉,更谈不上支持他关于玛丽什么新东西也学不到的强硬立场。
第二种反对意见:玛丽学到的只是一种能力而不是知识。
在其《经历教会我们什么》一文中,⑥刘易斯(David Lewis )争辩说第一次看见熟透的西红柿的新经历教会玛丽的不是什么新知识而只是一种新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玛丽记住看见红色的意识感受特性究竟是什么样的;这种能力可以使玛丽回忆起关于红色的意识感受特性,即使是在没有看见红色的时候;这种能力可以使玛丽在今后再看见红色时能够识别这是同一种关于红色的经历。
刘易斯强调这种能力只是“知道如何”(knowing how )而不是“知道如此”(knowing that)。“知道如何”是指知道如何具体地做某件事,这是一种身体的技能和状态(如骑自行车、游泳),和作为真的命题(true proposition)的知识并无必然关系。而“知道如此”则是指知道关于一件事的由真的命题所表达的知识,这和我们通常所谓的“课本知识”相似,它是可以通过课堂讲授,读书学习而传播和获取的知识。刘易斯的意思是后者(知道如此)才是由真的命题构成的知识,而前者(知道如何)算不上知识,只是一种身体技能或状态。
因此刘易斯对知识论证的解答应该是这样的:玛丽在走出黑白房间前就知道了关于世界的所有的知识(因为广义的物理学知识就是所有知识),但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玛丽具有各种具体的做事能力,比如识别红色意识感受特性的能力。她出了房间后,通过实践掌握了一种她原来不具有的能力,但这并不表示他学到了任何新的知识,就像其他一个人通过实践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能并不表示她学到了任何新的知识。既然玛丽在出房间后并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那么杰克逊的思想实验并没有展示除了广义的物理学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知识,因此知识论证不能驳倒物理主义。
我们看到刘易斯上述策略的关键点是把知道红色意识感受特性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件事和知道怎样骑自行车、游泳、使用筷子、打高尔夫球等归于同一类,并声称它们只代表一种身体能力,而不是真正的命题构成的知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质疑刘易斯的上述论证手段:知道红色意识感受特性和知道怎样骑自行车、游泳、使用筷子、打高尔夫球等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具有语义学内涵而后者却不具备语义学内涵。我可以在书本上和电视上学到关于骑自行车、游泳、使用筷子、打高尔夫球的所有物理学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我同时学会了怎样识别这些词的指称。也就是说,即使是我自己没有做这些事的能力,我仍然能够识别什么是骑自行车、什么是游泳、什么是使用筷子、什么是打高尔夫球。换句话说,这些作为“知道如何”的范例的能力是没有语义学内涵的,因为没有这种能力,我仍然懂得相关词语的意义,仍然能够正确地指出它们相应的指称。
但是“知道红色意识感受特性”就完全不同了,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红色意识感受特性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按照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实践,这个人就不懂“红色”这个词的意义,在现象世界中他就不能识别“红色”这个词的指称。因此和骑自行车等能力完全不同的是,“知道红色意识感受特性”是有重要的语义学内涵和后果的,正是因为它和“红色”这个词的语义学有关,所以它和包含“红色”这个词的一些语句或命题的真值有关,从而它应该被归为知识一类,而不是能力一类。
我们对刘易斯的论证手法的批评是建立在我们关于“红色”这类词的日常生活的语言实践和直觉上的,刘易斯当然可以否认我们的日常生活直觉,但是这需要他提供进一步的语义学方面的论证。仅仅停留在“知道如何”和“知道如此”这样表层的区别上是不够的。
第三种反对意见:玛丽缺乏的只是一种亲知知识(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
在第一节中我们提到知识论证的论证结构是这样的:(在离开房间前)玛丽知道关于其他人的所有的物理真理。(在离开房间前)玛丽不知道关于其他人的所有的真理。存在关于其他人的非物理的真理,物理主义是错误的。
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在《知道感受特性:回答杰克逊》一文中⑦ 指出:为了使上述的知识论证成为逻辑形式上有效的证明,在两个论证前提中出现的“知道”一词应该是同一种用法。但是丘奇兰德辩论说实际上“知道”一词在两个论证前提中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用法。在第一个前提中,“知道”是指一种对物理学命题知识的掌握,玛丽在感受这些物理学命题知识时大脑会呈现某种特定的状态。而在第二个前提中,“知道”是指对意识感受特性的一种亲知,玛丽在感受这些亲知时大脑会呈现另一种不同的特定状态。因为这两种“知道”的物理基础就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知道”,因此上述知识论证在逻辑形式上不是有效的论证。
作为回应,我们可以询问:即使上述的两个“知道”具有不同的用法,那么两种不同形式的“知道”是否都会导致知识呢?如果是的话,那就意味着在离开房间前,玛丽拥有关于其他人的所有物理知识,但她却不拥有关于其他人的所有知识,因此存在关于其他人的非物理的知识,物理主义仍是错的。
关于这一点,丘奇兰德采取了一种取消主义(eliminativism)的立场。 他指出虽然根据我们的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知道红色意识感受特性”仍可被视为是一种知识,但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陈旧的、科学史前的概念框架是应该被抛弃的,就像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抛弃了许多过去我们民间认为是“知识”的伪知识一样。例如,过去我们民间认为天空是一个不动的圆顶透明的盖子,科学的发展证明这根本就不是知识。
所以丘奇兰德对知识论证的批判总结起来就是:这一论证只是展示了玛丽缺少关于意识感受特性的一种“亲知知识”,但是在科学发展影响下形成的关于意识的新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中,过去沿袭几千年的关于意识的陈旧理论和概念框架将会被废弃不用,从而所谓的“亲知知识”在新框架中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识。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观点,至少科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使我们放弃我们关于意识感受的沿用了几千年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像丘奇兰德这样的哲学家们也许具有某种超前意识,但是他们应该提供进一步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来为他们的极端立场辩护,否则的话,他们的断言只是无根据的猜测。
第四种反对意见:玛丽学到的只是以一种新形式呈现出来的旧事实。
罗耶(Brian Loar) 1997 年的文章《现象状态》对现象概念(phenomenal concept)这一课题作了重要的探讨。⑧罗耶通过对“现象概念”的分析来为物理主义同一论(identity theory)辩护, 从而也从一种新的角度对知识论证进行了反驳。同一论是物理主义中一种比第一节中提到的伴随论更激进的理论。根据同一论,意识的感受特性Q和其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P实际上是同一的,是同一样东西以两种不同方式呈现出来。如果同一论是对的,那么伴随论就一定是对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如果大脑物理特性P存在,而P就是相应的意识感受特性Q的话,那么Q就当然也存在。
罗耶为同一论所作的辩护包括下面几个要点:(1)我们知道酒精这样东西就可以由两种完全独立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是通过相应的现象特性,比如具有某种特定的颜色、气味等等的液体;另一种是通过化学结构CH[,3]CH[,2]OH。(2)类似地,“红色的意识感受特性”这样东西也可以由两种完全独立的方式或概念呈现出来:一种是通过关于意识中特定感受的现象概念Q(red);另一种是通过关于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的物理学概念P(red)。罗耶辩解说尽管Q(red)和P(red)在我们头脑中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概念,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实际上指称同一个特性这样一个物理主义的真理。(3)罗耶进一步分析说关于意识感受特性的现象概念Q(red)是特殊的一类概念,他把这类概念称为识别概念(recognitional concept)。一个识别概念似乎向我们揭示了它的指称的本质,比如“红色感受”这个概念的指称的本质似乎就是我们红色的意识感受性,并没有多余的物理状态或特性包含在这个现象概念中。但是罗耶坚称这只是我们在概念上的幻觉,并不能用来驳倒物理主义同一论。(4)因此罗耶对知识论证的回应是:出了房间后, 当玛丽第一次感觉到红色意识感受特性时,她只是看到一样她早已熟悉的东西,即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红色意识感受特性只是原来那个玛丽所熟知的大脑物理特性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在玛丽面前。总而言之,玛丽没有学到任何新的事实或知识。
我们看到罗耶为他关于“P(red)和Q(red)这两个概念指称同一个特性”这一论断所提供的唯一论证是关于酒精的案例。但是这个案例和关于红色的案例是有本质不同的。上面谈到酒精这样东西的第一种呈现方式,即“酒精是具有特定现象特征的那种物质”,这种呈现方式本身就蕴含了酒精这种物质具有内在的化学结构这层意思,所以当我们后来发现这种化学结构是CH[,3]CH[,2]OH时,我们很自然地把酒精和CH[,3]CH[,2]OH同一化。
但是在关于红色意识感受特性这样东西的第一种呈现方式中,现象概念Q(red)本身并不蕴含红色意识感受特性这样东西具有内在的物理基础这层意思,所以当我们后来发现作为红色意识感受特性的物理基础的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时,我们很自然地不把这两个特性同一化,而是把后者称为前者的物理原因。当然罗耶可以坚持说这两个特性就是同一的,但是失去了像酒精这样的例子的类比支持,他所坚持的也就成了没有道理的、蛮横的同一性了。
第五种反对意见:玛丽并不知道所有的物理事实。
在其《关于“物理”的两种概念》一文中,⑨ 斯图加指出关于“物理”这个词也许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建立在物理学理论上的概念(the theory-based conception), 另一种是建立在(物理)对象上的概念( the object-based conception),我们可以称第一种概念为t-概念,而称第二种概念为o -概念。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把t-概念框架中的所有物理事实称为t-事实,而把o -概念框架中的所有物理事实称为o-事实。
有了这些准备工作后,斯图加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解答知识论证:在离开房间前玛丽知道所有的t-事实,但她并不知道所有的o-事实。离开房间后,玛丽学到了新的事实,即o-事实,但这些仍然是物理事实。因此玛丽离开房间后学到的新的东西并不意味着物理主义是错误的。
斯图加的上述策略的困难在于我们很难说清o-(物理)事实到底是怎么样一种事实,甚至我们并不清楚所谓的o-事实究竟是否存在。以玛丽的情况为例,如果玛丽在看到熟透的西红柿时获得的只是一种关于o-事实的知识,那么似乎这里的o-事实就是指西红柿这个宏观物理对象所具有的红色的特性。但是我们知道红色的特性是西红柿表面的微观物理结构反射光后在我们的意识中形成的视觉感受。所以所谓“西红柿具有的红色特性”是否是一种物理事实就显得非常不清楚。
3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杰克逊关于知识论证的思想实验让人在直觉上印象最深的一点似乎是:当玛丽第一次走出黑白房间看到西红柿时,她确实学到了新的东西。杰克逊宣称那是一种新的知识,并且因为玛丽在房间里已经学会了所有的物理知识,因此这种新知识是一种非物理的知识,从而物理主义是错误的。仔细分析起来上述的五类反对意见实际上都采用了同一种策略,那就是它们都想尽办法“贬低”玛丽出房间后学到的新东西的价值,以便使“玛丽学到新东西”这一现象不会损害到物理主义。
我个人的意见是:在回应知识论证的挑战时,物理主义者根本就不用采取“贬低玛丽学到的新东西的价值”的策略。因为无论玛丽学到的新东西的价值有多高,有多重要,它都不会损伤到物理主义,物理主义完全相容于“玛丽学到新东西”这一现象。让我们回忆一下,物理主义的伴随性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它断言一个意识的感受特性Q和其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P在本体论上有一种必然的关系:那就是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P存在,Q就一定随之而存在。这个命题本身没有说任何关于认识论和知识论上的事。
那么具体到玛丽身上,在黑白房间时,不管玛丽学到了多少关于红色的物理学书本知识,她的大脑都从未呈现P(R)的物理特性,所以她也从未有过。
Q(R)的红色意识感受特性。当她走出房间看到西红柿时,受到特定波长的光线的作用,她的大脑第一次呈现P(R)的特性,而她也第一次经历Q(R)的意识感受特性。这整个过程和物理主义的伴随性命题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因此不管玛丽学到的关于红色意识感受特性Q(R)的新东西的价值有多高,这都不会伤害物理主义。
整个知识论证的关键点是“玛丽走出房间后学到新东西”这一现象,如果我们上面的分析是对的话,那么无论玛丽学到的新东西是多么重要的知识,这都对物理主义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所以说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知识论证变得非常有名,但是作为一个反物理主义论证,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弱的论证。对物理主义的真正挑战在玛丽没出房间前就应该开始了:在黑白房间里,玛丽就经历了黑色和白色的意识感受特征Q(B)和Q(W),她也可以通过仪器观察到她自己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P(B)和P(W)。玛丽当时就可以这样质疑物理主义:如果P(B)必然地导致Q(B),P(W)必然地导致Q(W),那么为什么我从关于P(B)和P(W)的知识在概念上先天地推不出关于Q(B)和Q(W)的知识?
哲学史上,人们一直以为一个命题是必然(necessary )真的当且仅当它是先天(a priori)真的。物理主义的伴随性命题似乎在宣称存在后天(a posteriori)必然真的命题。反物理主义者质疑:这种没有概念上先天性保证的必然性的基础和依据是什么?而物理主义者则反驳说:为什么必然性一定要有概念上的先天性作保证?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目前似乎陷入了僵局,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⑩ 但是关于本体论中的必然性和认识论中的概念先天性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确实是关于物理主义的争论向我们提出的一个形而上学中的深层难题。对这个难题的解答也是解决关于物理主义的争端的关键所在。
另外,我们之所以说物理主义的伴随性命题不是概念上先天真的,是因为在我们现有的日常生活语义学概念框架中,从大脑物理特性P 的概念先天地推不出相应的意识感受特性Q的概念。 但是从上面讨论知识论证的反对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丘奇兰德这样的物理主义哲学家们已经在预言随着科学,特别是脑神经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现有的日常生活语义学概念框架会逐步被更科学的语义学概念框架所取代。结果也许是像“红色意识感受特性”这样的词语在新的框架中会在语义上包含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从而物理主义的命题在新的语义学概念框架中会是概念上先天真的。在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科学的不断发展究竟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实践和用法产生什么样的语义学影响?这也是关于物理主义的辩论向我们提出的语言哲学中的难题。
注释:
① 其他主要的反物理主义论证是:可想像性论证、解释空缺论证、模态论证。关于这些论证,请参看David Chalmers,Philosophy of Mind: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② Frank Jackson,“Epiphenomenal Qualia”,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2,1982,pp.127—136.
③ Peter Ludlow,Yujin Nagasawa,Daniel Stoljar,(eds) ,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Essays on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 and Frank Jackson 's Knowledge Argument,Cambridge,MA:MIT Press,2004.
④ Frank Jackson,“What Mary Didn t Know,”Journal of Philosophy 83,1986,pp.291—295.
⑤ Daniel Dennett,“‘Epiphenomenal’Qualia?” from his Consciousness Explained,New York:Little,Brown,1991,pp.398—406.
⑥ David Lewis,“What Experience Teaches”,from J.Copley-Coltheart,ed,Proceedings of the Russellian Society 13,1988,pp.29—57.
⑦ Paul Churchland,“Knowing Qualia:A Reply to Jackson”,from his A Neuro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9,pp.67—76.
⑧ Brian Loar,“Phenomenal States”,in N.Block,O.Flanagan,and G.Guzeldere,eds,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Philosophical Debat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7,pp.597—608.
⑨ Daniel Stoljar,“Two Conceptions of the Physical,” from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2,2001,pp.253—270.
⑩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参看T.Gendler and J.Hawthorne,eds,Conceivability and Possi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