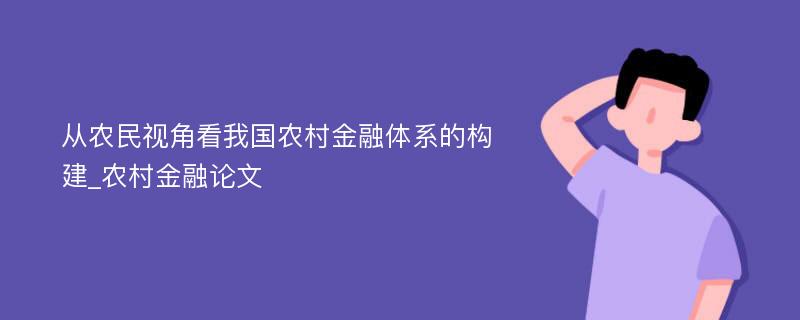
农户视角下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农村金融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742(2007)06-0019-04
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农村金融问题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仅仅分析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足是不够的。本文基于农户(指传统的小农户,排除了那些已实现城镇化或工业化村落的农民)的视角,从中国传统农户的特征出发,分析其金融需求特征及其融资偏好,从而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提出建议。
一、中国传统农户的特征
(一)收入情况
中国农业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匮乏。根据国家环保总局200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9年中国农村住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为0.139公顷,2000年为0.133公顷。据1996年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户均经营0.201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0%,户均经营0.201公顷~0.603公顷的占53%,户均经营0.603公顷~2.01公顷的占15%,户均经营2.01公顷以上的占2%。土地资源的“零细化”导致农业生产规模狭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农户收入水平低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剩的劳动力无法转移,劳动生产率低。中国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因此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产生大量原本可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无产——雇佣’阶层”,即土地人口过密化[1]。根据黄宗智的“拐杖逻辑”,“进城务工收入仅是家庭农场的某种补充”,是农场收入的拐杖[2]。根据农业部经管总站信息统计处对21288农户进行的收入抽样调查,2003年和2004年农户人均外出务工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6.0%和16.1%(表1)。
(二)圈层人际关系网络
中国农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亲缘以及地缘基础上的圈层人际关系网络,以亲缘及地缘关系的远近由家庭向外扩展至宗族、乡里。费孝通将这种社会关系比喻为以中心投入水中石子所形成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薄[3]。
亲缘关系建立在血缘、婚姻基础上,以道德、伦理、宗法等为原则。血缘的亲疏,决定了彼此之间感情的深浅,同时也决定了相互之间权利义务的差异。
地缘关系在长时间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人之间建立起来。人们通过日常的活动,礼尚往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种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是农户人际关系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常由邻里、街坊、村庄一层层向外扩展,越往外关系就越疏远,越往内则越亲近。
表1 2003年2004年农户收入构成
2003年占人均纯收 2004年 占人均纯收
(元) 入百分比(%) (元) 入百分比(%)
家庭经营总收入 1792.0
66.0 1980.1 66.2
工资性收入 842.431.0 909.8 30.4
其中:
外出务工收入434.816.0 481.1 16.1
财产性收入 39.5 1.5 44.1
1.5
转移性收入 40.6 1.5 57.6
1.9
人均纯收入 2714.4
100.02991.6 100.0
数据来源:农业部经管总站信息统计处[4]。
家庭作为处于这种圈层结构最中心的基本单位,是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中国农村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家庭实际上承担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养老、医疗等,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同时家庭甚至一个更大的家族圈子,对于单个小农来说,是一个精神寄托的载体,在家庭或家族圈子中,他们能够寻找到一种归属感,责任感,感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这份精神寄托又使家庭或家族圈子中的成员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5]。在农村,维系人际关系的是亲缘、地缘,人情成为交往准则,维系城市居民关系的社会组织、规则,在农村不存在亦不适用。
(三)生存理性
理论界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理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个以美国经济学家T.W.舒尔茨为代表,认为农户是类似于企业家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激励,农民将点石成金”(舒尔茨)。波普金也指出小农是追求最大生产利益的理性小农,经济行为遵循理性的投资原则。另一个以原苏联经济学家A.V.蔡亚诺夫为代表,他认为小农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消费,不考虑利润的问题。詹姆斯.斯科特则认为农户经济行为遵循“安全第一”、“避免风险”的原则。“由于生活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其后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斯科特)。
具体到中国的农户,自古以来,就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这一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农户的思想及经济行为,并在现在的传统农户家庭中得以延续。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与以蔡亚诺夫为代表的“自给小农学说”,即以满足自身家庭消费为目的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较为相符[6]。由于人多地少以及农业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生存成为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中的农户考虑的首要因素,为回避风险,“保守”成为传统农户的显著特征,他们宁愿赚取可维持全家生存的最低收入,而不愿冒险去获取更大的利益。若根据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则将得出农户非理性的结论。那么农户是否真的就是非理性的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何谓理性。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定义,理性是指决策者在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一个方案。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理性与否与选择性及效用函数密切相关。而效用又取决于决策者的喜好、目标或者说是动机。只要决策者在既定的目标下,在其可选择的范围内,做出使自身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选择,那么该决策者就是理性的。也就是说,理性不是绝对的,理性与否因决策主体不同而异,因目标不同而异。
因此,以经济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来衡量农户行为显然是不可取的。考虑到农户的特殊性,如对土地的依恋,相关的制度性条件的束缚,以及中国传统农户所处的需求层次,经济人标准下的非理性行为——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过多的劳动力造成劳动力生产率低下等均可得到理性解释。这是中国传统农户所特有的理性,是一种“生存理性”[7]。
二、中国传统农户的金融需求及融资偏好
农业本身的脆弱性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等因素,造成中国农户原本就处于低水平的收入更呈现出不稳定性。加之消费的不确定性,如不可预见的大额开支,疾病等,使得中国农户处于收入与消费的双重不确定之中。一旦其中之一发生不利的变化,就极易造成收入不能满足农户维持生存的必要消费的情况发生,即出现生存消费缺口,从而产生融资需求。屈小博、钟学军和霍学喜等(2004)在对陕西渭北地区农户借贷行为进行调查时发现,2000~2002年,70%以上的样本户有资金借贷行为发生。在孔祥智2003年底对陕西、宁夏、四川3省5县的420个农户进行的调查中,也有近70%农户发生过借贷。由此可见,农户借贷较为普遍,农户中存在融资需求。
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生存理性”追求温饱无忧等特点决定了农户由于生产和生活的贷款规模不大,并且以生活性贷款需求为主。根据“生存理性”,农户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他们保守、回避风险,宁愿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弥补资金投入的不足,生产性贷款仅限于购买必需的生产工具、化肥等,而不会冒险借入资金增加投入以获得更大的生产利润。邓学衷和陈天阁(2005)对安徽省6个县农户家庭的问卷调查亦表明农户经常性的资金借贷主要是小规模的(表2)。
表2 安徽6县农户经常性资金借贷情况
借贷数量(元)500
500~ 1 000~ 5 000~ 10 000
以下 1 000 5 000
10 000以上
比例(%) 21 32 29 126
数据来源:邓学衷和陈天阁(2005)[7]
根据何广文(1999)的调查,农户贷款中用于生产性用途的仅占32%,用于婚丧嫁娶的占7.45%,建房占20.5%,人情往来4.35%,临时性生活困难11.8%,其他方面占24.53%。
农户贷款需求的非生产性用途,以及数额小,缺乏有效的抵押或担保等特点使得农户难以甚至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我们知道,金融机构通常必须通过对借款者的信用状况,偿还能力,贷款用途等进行调查,以减轻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降低风险。而我国农户众多,在地域上又高度分散,导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异常严重,也造成要了解农户的信息就必须花费巨额的信息成本,而且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亦无法通过抵押得到缓解。也就是说向农户提供贷款需付出高额的成本。而农户贷款需求的特点,又决定了其低收益性。因此,权衡收益与成本,作为经济人的金融机构选择拒绝向农户贷款是理性的。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资料,2003年,中国农户融资中,13.84%来自银行,18.90%来自农村信用社,65.97%来自民间私人借贷[8]。何广文(1999)的个案调查已表明,农户借贷中来自农业银行的占3.6%,来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占30.63%,民间借贷占到了60.96%。可见,非正规融资在农户融资方式中处于主导地位。
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惜贷、非农化倾向导致了农户不得不以非正规方式融资。其实不然,本文认为,正规金融机构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只是加剧而非导致了农户的非正规融资倾向。也就是说,即使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不存在惜贷、非农化的倾向,非正规金融方式也仍将处于主导地位。这就涉及到农户的融资偏好或者说是融资次序问题。张杰(2003)认为,农户融资的基本逻辑次序是,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寻求非农收入(寻找拐杖),如果家庭预算仍然存在缺口,就去寻求外援融资,外援融资的次序是熟人的无息借贷,国家的官方信贷支持以及前两者不可得情况下的高息借贷。李江(2004)指出农户的融资次序为,内部融资、熟人借贷、自发性融资合作组织、民间私人组织、正规金融组织。即农户对非正规融资的偏好大于正规融资。这与中国农户的特征密切相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的传统农户生活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圈层人际关系网中,与其所处的“熟人社会”紧密相连。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化、社会环境决定了农户非常重视其所处的关系圈,尤其是亲情关系。质量好的关系圈成为农户间有效的风险共担机制。同属于一个关系圈层次上的农户往往对彼此的收入、消费等信息比较了解,信息相对对称,因而能够认同农户所产生的消费缺口并予以资助。对于给予资助的农户而言,这也可以说是对自身遇到风险时从关系圈中获得融资所尽的“义务”。这样就实现了关系圈内互帮互助的风险分担。显然,比起处于农户所在的“熟人社会”之外,背离农业文化且手续繁杂的正规金融组织,有着深厚的文化、道德基础的非正规融资尤其是熟人借贷更能获得农户的青睐。但是当农户的风险无法获得关系圈中其他农户的认同或其他农户亦无力提供融资时,由于正规金融支持的难以获得性,农户极有可能选择高利贷。高利贷与农户的生存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生存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农户必然只关心能否得到贷款以渡过生存危机,而对利率的高低缺乏敏感性。
三、结论及建议
(一)放开民间借贷,并予以适当的引导规范
由上述分析可知,民间借贷或者说是非正规金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特点,并能有效地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对农户的生活以及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对民间借贷持否定态度的人,可能会以民间借贷多为口头协议,不规范,高风险为由,认为必须予以取缔。然而,民间借贷的实际风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对农户而言,实际上相当于在进行一场无限期的博弈。根据博弈论,重复博弈可以产生信用机制。农户无法保证以后都不再有融资需求,为避免受到关系圈内其他农户的惩罚,通常会选择自觉履约。此外,社会地位,希望得到社会赞同,归属感等“面子成本”也降低了违约风险。农户一旦违约,其行为便极易在其所处的“熟人社会”中流传开来,从而使其受到其他农户的鄙视与排斥。也就是说,农户的非经济动机强化了其自履约机制。当然,适当的引导与规范以降低风险仍是必要的。
(二)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
为避免无法获得熟人借贷亦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农户而被迫选择高利贷,国家应加大政策性金融服务农村的力度,降低农户获得国家信贷支持的门槛,使农户不再为了生存而高息借贷,以减轻农村系统性风险对农户生存状态的威胁;因为当发生系统性风险时,农户关系圈的风险分担功能将无法实现。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定位于扶持农村弱势、贫困群体,保障农户的基本利益,满足农户不能由商业性金融满足的金融需求,以维持农村社会稳定。
(三)商业性金融的发展应适时
无论是从农户的融资偏好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商业银行的经济人理性角度出发,当前在传统农区强制性推行商业金融是不可取的。只有当农户的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产生商业性金融需求时,发展商业性金融组织才是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