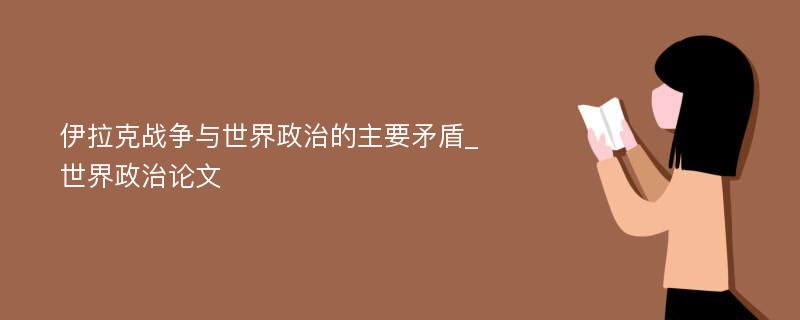
伊拉克战争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政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没有人否认,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超越反恐、具有全球影响的局部性战争。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在战争前后的各种较量表明,冷战结束以来不断演变着的世界战略格局继“9·11”事件后经历了又一次重大冲击。本文不想就格局本身做深入分析,而想对影响世界战略格局更实质性的因素——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冷战后美国战略家对世界主要矛盾的认识
从分析主要矛盾入手观察世界政治,一直是把握时局的关键。因此,随着冷战后美苏两极对立矛盾的突然消失,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们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必须解决一个最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不分国界,但问题的答案则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其中,美国战略家凭借冷战胜利的“王者之气”和以全球为视野的学术传统,率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由于具备超强综合国力,同时受称霸世界的思想影响,美国战略家们在看待世界政治主要矛盾时,往往将美国自身看作矛盾的主体,然后以此为前提寻找美国的对立面。在他们眼里,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自己与美国在建立霸权秩序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之间的矛盾。
日裔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明确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将是自由民主制度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因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影响历史发展的“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注:[美]费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换句话说,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无非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如何巩固并扩展自由民主成果的问题。福山的思想代表了相当一批美国学者的观点,转换成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的语言,便是认为世界从此进入美国独领风骚的“单极时期”。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可被视为“单极论”的始作佣者。(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0/1991.)
然而,无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克劳萨默的“单极论”都没能完全解释冷战后十几年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的巨大活力及广大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发展路线等诸多现象,表明“历史”远未终结;而美国虽实力超群,却并不能在所有重大国家问题上我行我素,也至少说明“单极世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于是乎,另有一批战略家对时局进行了更为谨慎的诊断。其中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人最为引人注目。三人都承认美国的单极优势,但都同时意识到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存在,因此不同意“历史终结”说,也不赞成美国利用单极地位推行单边主义路线。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从“文明冲突”、传统地缘政治和新自由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了关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各不相同的结论。
亨延顿认为,旧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虽然终结,但新的“文明间的冲突”则取而代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将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转为“西方对非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儒教—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对抗。亨廷顿并不否认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但他强调:“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于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在他眼里被简化为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中东世界为主体的“伊斯兰+儒教文明”之间的矛盾。
布热津斯基则更倾向于强调地缘政治的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将围绕美国如何控制欧亚大陆及在此过程中美国与各大力量进行角逐而展开。在这场矛盾冲突中,日、欧盟国是美国借重的力量,中、俄两国则是“潜在的对手”。美国的主要战略就是利用空前绝对的优势地位,团结盟国,将中、俄融进西方体系,完全控制欧亚大陆。(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世界政治矛盾的主体将是美国及盟国为一方,俄罗斯与中国为另一方。(注:Zbigniew Brzezinski,"Living with China","Living with Russia",National Interest,Spring,Summer 2000.)
约瑟夫·奈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言人。他一贯认为,冷战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传统国际关系的主导形式(即主权国家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新内涵。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新的视角看待美国的实力地位及国际格局。他在著名的“三维棋盘论”里指出,美国只是军事层面的超霸,经济层面实际是美、欧、日三足鼎立,而在跨国关系层面,力量则更为分散,可谓多极并存。(注:Joseph S.Nye 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2,p.133.)因此,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新威胁,美国与世界各主要政治力量不必然构成矛盾的对立面。
除了从美国全球战略大视野观察世界政治主要矛盾外,美国另有一大批学者直接从谁是美国的“主要挑战对手”角度审视国际格局,分析主要矛盾,并因此得出了多种不同看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类:(1)美中矛盾是主要矛盾。理由是,中国综合国力最被看好、地缘上与美有现实冲突、意识形态与美相左、反美情绪与日俱增、与西方文明很难相融等,其代表言论是“中国威胁论”,代表作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龙年》等,代表人物则是美国媒体、智库、国会、政府内的所谓“蓝队”成员。(2)美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看法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现实主义战略家头脑里根深蒂固。除了认为俄罗斯是唯一能对美构成现实军事挑战的国家、“帝国雄心”没有泯灭(注:Zbigniew Brzezinski,"Living with Russia",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0.)、占据欧亚大陆主体位置等原因外,更主要的理由是,俄罗斯民族和文化中有中华民族和文化所缺乏的“侵略传统”和“掠夺本性”。正是这一传统,使得当年的苏联共产党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天壤之别”(注:基辛格1999年9月在“21世纪前夕的中美关系”会议上的讲话,法新社华盛顿1999年9月14日电。),也使得俄罗斯的挑战潜力比中国更让人担心。(3)美欧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此最雄辩的论证出自两位学者,一位是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钱,另一位是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前者认为,随着欧洲作为一个联合的政治力量的崛起,美欧联盟终将分裂为北美和欧洲两部分,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分裂成罗马帝国和康斯坦丁堡帝国那样。“尽管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但东、西两个帝国成了死对头”(注:Charles A.Kupchan,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lfred A.Knopf,New York,2002,p.120.),因此,美欧矛盾可能成为今后影响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后者指出,“现在是我们停止假装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拥有一个同样的世界的时候了”。(注: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No.113.对美欧矛盾更全面的论述,参见:Robert Kagan,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Alfred A.Knopf,New York,2003.)美欧矛盾冲突已成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一论调引起了大西洋两岸激烈的论争。
“9·11事件”的发生,在极大程度地撼动美国内外战略的同时,也促使美国战略家们进行适度的战略反思,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新思想。大体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美利坚帝国主义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矛盾,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矛盾都退居其次。(注:James Kurth,"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Current History,December 2002.)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充斥美国报刊杂志,兹不一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倾向可以看出美国思想的实用主义传统。
第二类认为,恐怖主义固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但传统大国威胁仍不容忽视,因此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同时应对恐怖主义与大国挑战这两种威胁。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2001年9月30日出笼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该报告的起草者们一方面谈论恐怖主义的危害,一方面则一再提及所谓“地区强国”的威胁,尤其是到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个“拥有惊人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注: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September 30,2001.也可参见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倡导的军事改革基本根据这一思路。
第三类思想可以说是福山“历史终结论”和克劳萨默“单极论”的深化,即是目前在美国甚嚣尘上的“新帝国主义论”或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该论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美国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又有反恐提供的绝对时机,就看美国领导人敢不敢于“承担责任”,建立“新帝国”。(注:有关美国新帝国的论述很多,最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美国《威尔逊季刊》2002年夏季号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专刊共5 篇文章,见:The Wilson Quarterly,Summer 2002。其他较为重要的论著有:Robert D.Kaplan,Warrior Politics:Why Leadership Demands a Pagan Ethos,Random House,2002;Andrew J.Bacevich,American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02;Se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2.)目前看来,“新帝国”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布什的对外战略。
战略家们对世界矛盾的分析显然影响着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决策,但政府的决策毕竟更讲求平衡性。因此,冷战后出笼的各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力图在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之间、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之间寻找平衡,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划出一条不偏不倚的路线图。不过,在对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把握上,仍可看出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之间的微妙差别。克林顿政府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较深,其对外战略更多是布热津斯基的新地缘政治论、享廷顿的“单极—多极”格局论、约瑟夫·奈重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作用等思想的揉合,强调美国实力的有限性,从相互依存的角度看待大国关系,主张重点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小布什政府则更多受福山、克劳萨默思想及“新帝国主义”论的影响,布什称“20世纪自由与极权主义的伟大斗争,最终以自由力量和国家取得成功的唯一的可持续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注: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2002.),这简直就是福山“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翻版;而他强调“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注:Ibid.)则无异于鼓吹单极论。在克林顿那里,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与大国协调,借助国际机制的重塑,共同应对全球化到来的新挑战,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在布什那里,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整合大国,消灭“失败国家”,缔造美国主宰的“新帝国”。他们的一致性在于,都希望利用美国的实力塑造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长治久安。
二、当今世界政治中两对主要矛盾并存
美国人的观点带有很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与其对立面的矛盾,“美国就是世界”。因此,美国战略家对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分析至少是不全面的。
比较而言,中国学者似乎更能全面地看世界。冷战后,不少学者就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阎学通教授根据国际关系研究“证实的方法”,得出后冷战时期“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称霸与反霸的矛盾”,并进一步得出“中美战略矛盾的尖锐程度超过其他几强与美国的战略矛盾”的基本结论(注:阎学通:“冷战后的延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在中国学者中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时下所谓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关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矛盾等等,说的也就是称霸与反霸的矛盾。这种认识与“一超多强”的格局论,共同构成中国学者对冷战后世界总体形势的流行看法。
“9·11事件”后,中国学者对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认识直接受到一个命题的影响,即,美国当前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反恐还是谋霸?对此大体形成三派意见:一派认为美国现阶段重点是反恐,其他任务都位居其次。主要代表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圈内的所谓“亲美派”。一派认为美国反恐是假,谋霸是真,“反恐只是谋霸的旗号或借口而已”。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圈内的所谓“强硬派”,尤其是军方不少学者对此多表认同。第三派意见则认为美国“反恐是真,谋霸也是真”,“反恐、谋霸两不误”。目前更多的学者似乎认同这一提法。对美国战略走向的不同认识必然也导出对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除相当多的学者依法坚持“称霸与反霸”是世界政治主要矛盾外,也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世界其他基本矛盾如西西矛盾、南北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其他力量中心之间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不能不退居其次。”(注:尹承德:“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在评价上述观点之前,有必要先就“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两个概念作一区分(有人也将世界政治称为广义的国际政治(注: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参阅李兴:“‘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概念辩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2期。),将两个概念等同,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人并不有意识地这么认为,因而作一区分是有必要的)。所谓国际政治,简言之就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国家间的政治;所谓世界政治,即要包含国际政治的同时,“承认民族国家之外其他行为者的重要性”(注:[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著,王玉珍等译:《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页。),是一个比国际政治更大的概念。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
世界政治=国际政治+超国际政治(“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政治)
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全球管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詹姆斯·罗森诺的话说,当今世界是“国家中心体系”与“多中心体系”并存的世界。(注:James N.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A Theory ofChange and Continu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而中国学者时殷弘更有一段形象的比喻,他说,世界政治是国家间政治组成的“平面构造”与全球化塑造的跨国“网状构造”的复合体,是“国家间政治与跨国政治的复杂复合”。(注:时殷弘:“格局·潮流·时代特征”,《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
在这里之所以强调“世界政治”,不仅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在使用这一概念,并在外交实践中身体力行,(注: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中体现的所谓“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民主无国界”、“新干涉主义”等思想,就是从“世界政治”观派生出来的东西。)而且因为全球化加上互联网,使世界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生命共同体”(注:张敏谦:“全球化与美国的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6期。),“国家时空、国际时空向全球时空转变,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内涵、规模和空间全球化,向全球关系、全球政治迈进”(注:俞正梁:“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从而使得世界政治越来越有意义。(注:[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5页。)当然,学界仍在争论。比如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不宜夸大其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影响,甚至认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实质仍是南北对立,南北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矛盾”(注:李存娜:“‘中国: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会议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这里就存在一个对事物量变、质变的把握问题。全球化虽然不是新东西,但诚如约瑟夫·奈所说只是到当代才形成鲜明的特色。(注:[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90页。)托马斯·弗里德曼则用“更远、更快、更便宜、更深入”(注:Thomas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p.7-8.)四个比较级说明当代全球化运行的深远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客观承认全球化及信息化给当代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就会发现当代世界政治的许多问题不是“称霸与反霸”这对矛盾所能涵盖的,它所涵盖的只是“国际政治”而非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而已。(注:对此阎学通教授很明确地指出来,其论证称霸与反霸这对主要矛盾,原本就放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标题下。见:“冷战后的延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而将“美国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视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则显然混淆了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区别。
从世界政治的角度观察问题,可以发现,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中其实一直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国际政治主线。延续的是一战—二战—冷战—后冷战—后后冷战范式,解决的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问题,或谓“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问题。另一条主线则是超越国际政治范畴的“世界基本潮流”主线,包括全球化、多极化、社会政治生活现代化等主要内容(注:参见时殷弘:“格局·潮流·时代特征”,《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其中全球化是核心。延续的是全球化初具规模(一战前后)—全球化深入发展(二战前后)—全球化被人为阻断(冷战时期)—全球化纵深发展(后冷战时期)范式,解决的是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所谓“低级政治”(low politics)问题。
在前一种范式中,矛盾的核心是构筑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战后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冷战后的单极—多极体系,构成了各国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舞台和空间。国家依据实力强弱争夺于己有利的地位,对国际秩序是拥有主控权、主导权还是发言权、参与权,可谓事关重大。美国凭借一超地位试图构建美国主控或主导下的国际秩序,而诸强则尽力争取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国际秩序发言权或参与权。这种秩序之争,很自然演变为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并逐步上升到称霸与反霸之争。称霸与反霸的矛盾因此构成世界政治的一对主要矛盾。
在后一种范式中,矛盾的核心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全球如何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种类之繁多,既涉及国际政治,与国家实力有密切关系,比如全球性经济衰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蔓延等问题;又超越国际政治,在主权国家范围内难以控制,比如金融动荡、毒品交易、跨国犯罪、艾滋病、难民、文化渗透,包括最近在中国及多个国家出现的“非典型肺炎”(SARS)问题,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附着在传统国际政治之上的问题,正如英国学者熊·布思林所说,“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也是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长目标的最佳方式”。(注:[英]熊·布思林:“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全球化既是强者施加给弱者的“枷锁”,也是弱者自强的“倍增器”;全球性问题虽有南北矛盾的原因,但不能全部归咎于南北矛盾。比如,冷战后急速增长的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市民社会、大规模反战运动等现象,更多出现在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恐怖主义虽主要针对美国,但莫斯科人质事件、印尼巴厘岛事件、以巴人肉炸弹事件等等,表明其早已超越“9·11”而成为“人类公害”。(注:对于恐怖主义根源问题的讨论虽尚未得出统一结论,但基本认定是个“综合问题”。参阅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欧洲的疯牛病、美国的碳疽热、日本的手纸危机、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中国的“非典型肺炎”,其影响都超越国界甚至洲界,对全球造成的财产和生命损失甚至超过某些区域性战争。全球化将世界变成地球村,既使各国尽享“通关之便”,也使各国必须联手对付新型威胁。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机构即关注所谓“全球主义”(globalism)和“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问题。到今天,这一问题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因此,当今世界政治的另一类主要矛盾,便是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的矛盾。“9·11”后,这对矛盾突出表现为恐怖与反恐怖、萧条与反萧条、贫困与反贫困、扩散与反扩散等,(注:陆忠伟:“把握世界局势的脉搏,《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第二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当前尤以恐怖与反恐的矛盾最为突出。
区分世界政治与国际政治,指出两对矛盾并存,其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我们不宜继续专注于“国际政治”,将称霸与反霸(单极对多极)这对矛盾无限放大,从而警惕过度,以至忽视对人类影响更大的全球性灾难和问题,错过与美国及其他大国发展合作的历史契机;另一方面,也不宜淡化传统国际政治,过分渲染所谓“低级政治”、“全球公益”(global public goods)及“全球管理”(global governance)等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沉醉于和平与发展的表象,弱化对国家安全应有的重视。认识并重视两对矛盾,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或许有助于对当前世界政治的全面理解。
三、伊拉克战争使两对矛盾空前激化且相互重叠
世界政治两对主要矛盾并存,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同时处于绷紧状态。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是一明一暗,一升一降。冷战结束到“9·11事件”发生前,称霸与反霸的矛盾表现得较为突出,美欧矛盾的发展、中俄关系的加速背后主要是这对矛盾在起作用。布什上台之初大行单边主义,奉行实力政策,使美国与大国的关系骤然紧张,称霸与反霸的较量一度相当激烈;“9·11事件”后,恐怖与反恐这对矛盾迅速跃升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与此相关,扩散与反扩散、萧条与反萧条的矛盾也越发突出。美国为了应对危机,主动调整政策,打出“大国合作”的旗号;大国出于反恐考虑,也积极配合美的行动。一时间,美国与大国之间、大国相互之间出现协调合作的少有局面,称霸与反霸的矛盾相对置后,“反恐联盟”对恐怖主义的矛盾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伊拉克战争前后,“称霸”与“反霸”、“恐怖”与“反恐”这两对矛盾则出现同时并存、相互重叠、空前激化的局面。这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场中东地区既是大国称雄的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滋生地。美国要实现称霸全球的目的,必须从地缘上整合中东,而要完成反恐任务,也必须改造伊斯兰。(注:布什等人的逻辑是,要清除恐怖,必须根除伊斯兰极端势力;而要根除伊斯兰极端势力,必须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中东显然首当其冲。参见: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eport,2002.)因此,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实有同时实现反恐、称霸两大目标的用意。在各主要大国眼中,要防止美国控制全球,中东这块地缘、能源宝地绝对不能听任美国一家主宰(对欧、俄而言,这也是一个周边环境是否稳定的问题);而要保持中东地区的稳定,又确须保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被除根。因此,各国表现出既支持美国在此打恐,又反对美国借机控制中东的两面性。联合国有关对伊武器核查的1441号决议得到全票通过,而对有关美英动武的新决议则遭到坚决抵制,正是各大国矛盾心态的集中体现。
围绕着“倒萨”问题的争论甚至冲突,表面上争的是现实利益(如法国、俄罗斯在伊拉克都有着规模不小的现实经贸利益,同时也担心战争引发国内的民族宗教问题),实际上则是关于今后确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意见分歧。换言之,即将确立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唯我独尊、大事小事全按自己的意思办,还是小事美国可以“自己干”、大事还得大家商量着办。这也就是称霸与反霸的矛盾问题。这一矛盾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也有过白热化的时候(如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其实是对美国冷战后对外继续扩张之势的反弹),但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终究没有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伊拉克战争则使这对矛盾空前激化,欧洲大陆两大传统宿敌法国和德国不仅团结一致,而且还同以前共同的敌人俄罗斯结成“轴心”,联合制衡布什的单边主义,从而形成中、俄、法、德等多强共同对美国的局面。布什谋建“新帝国”的急迫性与大国捍卫既有国际秩序的坚定性,使称霸与反霸的矛盾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多强与美国之间矛盾的焦点不是惩不惩治伊拉克的问题,而是如何惩治的问题。因此,这一矛盾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相反,随着战争进入尾声,法、德、俄与美国的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缓解。这一现象表明,伊拉克战争前后,世界政治中的另一对矛盾——即恐怖与反恐的矛盾——也在发挥重要作用。缺少这对矛盾的制约,称霸与反霸的矛盾必然更加激化,甚至可能失控。
首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有抢占中东地缘、能源优势地位的深层目的,但同时也是出于深入“反恐”的需要。CNN、福克斯新闻等电视节目播放的“自由伊拉克行动”一直都是放在“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这个大的栏目之下,全球反战声浪如此之高而美国却只出现小规模的反战潮,这些都表明,在多数美国人的头脑里,“倒萨”仍是在“反恐”。美国将“极端势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注:"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 New York,June 1,2002.)视为头号安全威胁(这正是布什决定对伊动武的主要理由),也主要是基于“反恐”的考虑。全然否认美国“倒萨”的反恐动机,等于无视“9·11”对美国政治、外交、社会生活造成的深刻打击。
其次,法、德、俄等国此次联合制美,与其说是反美,不如说是反布什的单边行径。1441号决议的全票通过,说明大国在反恐、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中美之间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立场上的相近,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诸强与美国既有反霸与称霸的矛盾,也有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振兴全球经济的共同利益。
最后,“9·11”后恐怖主义迅速向全球蔓延,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中国“非典”引起的全球对非传统安全的更深理解,等等,一方面使各国无法将全部精力用于制美称霸,一方面也迫使各国与美国一起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难题”。从美国方面看,应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摆脱经济萧条,还需要大国广泛的合作。
概言之,伊拉克战争使世界政治两大主要矛盾相互交织,导致大国关系呈现远比以往复杂的面貌:“超”、“强”之间既斗又合,斗而不破,合而不同;“强”、“强”之间既分又合,分而不散,合而不一。由于伊拉克战争没有使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国关系的上述特征仍将持续相当长时期。
四、中国不是矛盾的焦点
不过,对当前两对主要矛盾细加审视,可以发现,中国在两对矛盾中都不是焦点。就恐怖与反恐这对矛盾而言,矛盾的主体分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和美国、俄罗斯、中东、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这是由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运行特点决定的,具体表现在:尽管恐怖主义是全球公害,但就当前的伤害对象看,其主要针对的仍是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以及民族问题尖锐的国家或地区(如俄罗斯、中东、东南亚)。中国尚不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而且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对中国还有所求。同时,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经过多次磨合,中美之间的共识也日益增多;在不扩散问题上,美国更多将焦点锁定少数所谓“失败国家”,而且同样希望中国与美合作,解决这一难题。这一点在当前的朝核问题上体现得最明显。
再就称霸与反霸这对矛盾而言,当前矛盾的双方主要是美国与法、德、俄,或更确切的说是美国与欧洲之间,中国反霸的位置则相对后移。围绕伊拉克战争美欧矛盾的激化固然是这一结论的最好注脚,但更主要的根据则来自冷战后称霸与反霸这对矛盾的发展演变。冷战后相当长时期,美国一直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称霸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几乎所有《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报告》以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将俄、中并称为两大“主要潜在竞争对手”。)克林顿执政八年,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如何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如何确保中国“强而不斗”。(注:参见拙文:“亚太战略棋局中的中美俄”,傅梦孜主编:《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75页;“‘转型国家’与美国的战略”,《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275页。)这一工作被小布什所继承。其结果,美国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目标大体实现。一方面,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逐步走出“冷战阴影”,实现了正常化。科索沃战争使俄罗斯被阻隔在欧洲势力范围之外,阿富汗战争则迫使俄容忍美国势力进驻中亚,如此一来,俄罗斯在全球范围挑战美国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由此换来的是,俄罗斯被接纳为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八国集团)和安全体系(北约20国机制)的成员,从而实现了美俄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俄美关系必然还将存在矛盾摩擦,但其性质已完全不同,是属于正常的大国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经过克林顿时期的“浪漫期”(标志是“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小布什上台之初的“冷对抗期”(标志是小布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也终于在“过热”和“过冷”之间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标志是“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建立),从而实现了双边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中美关系未来依然会继续起伏迭宕,但双边关系的内涵已大为丰富,称霸与反霸不再构成中美关系中凌驾一切的主题。
美欧之间却仍在为关系正常化而斗争。欧洲方面经济军事实力的不对称,限制了其一体化本应带来的政治分量,使其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冷战残留下来的依附关系和小兄弟角色。自己家门口打响的科索沃战争要靠美国来收拾局面,阿富汗战争中本想出一把力却被美国婉言谢绝,欧洲人的尊严和脸面大受屈辱。此次伊拉克战争直接影响法、德地缘、能源、经济、政治等多重利益,美国人依然我行我素,不听劝阻,自然激起“老欧洲”压抑已久情绪的迸发。因此,美欧矛盾看似就事论事,实则是实现关系正常化必经的阶段。称霸与反霸的矛盾当前在美欧盟国之间体现得最突出,也就不足为怪。
此外,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核心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问题。秩序的破坏者和秩序的捍卫者自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在。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客观上已使美国站在了现有秩序的破坏者位置(当然,美国所要破坏的只是对它进行限制的机制和规则);而法、德、俄等国参与现有国际秩序时间更长、卷入更深、获益更多,因此自然成为维护秩序的主力军。相较而言,中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后来者,受美国单边主义冲击的影响要小于欧、俄。因此,中国更像是维护国际秩序的生力军(而非主力军)。这一角色定位客观上也避免中国成为称霸与反霸矛盾的焦点。
在当今世界两大主要政治矛盾中,中国都不是焦点,这正是中国能够拥有并保持“战略机遇期”的又一依据。它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及“三个总体、三个局部”(注:指“9·11”后中国政府对国际总体局势的基本概括,即“国际局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参见:“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7日。)的形势观相互印证,共同决定着中国继续有理由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争取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际环境。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事物的发展变化与矛盾的相互转换,往往变幻莫测;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之间也总是相对的。因此,认识形势的目的,还在于把握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