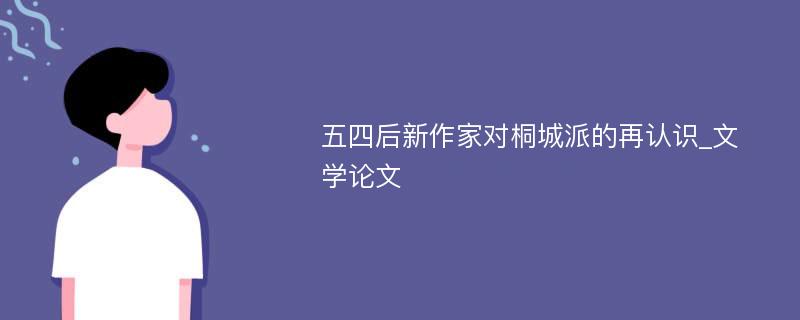
五四之后新文学家对桐城派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再认论文,学家论文,新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人们许多说不尽的话题。中西文化互补,新学旧学的融合,一直为20世纪的学人所津津乐道。中国文学的进化自白话代替文言之后,仍是山重水复。在现代化过程中,不间断地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最后之觉悟。在五四新旧文学争论的硝烟散后,新文学家如何认识五四时期的新与旧、文言与白话之争?如何评价五四时期曾被作为旧文学的代表所攻伐过的桐城派?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这是一个耐人咀嚼、耐人寻味的问题。
1922年,是《申报》创办50周年,胡适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表纪念。既然是谈50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自然要论及桐城派:
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韩愈自曾国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兴,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但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他们有时自命为“卫道”的圣贤,如方东树的攻击汉学,如林纾的攻击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载道”的话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胡适认为桐城古文两个特点,一是通顺清淡,一是勉强应用。评论严复和林纾时认为,“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严复用文言译书,是当时不得已的办法,“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提高译书的身价。”他的有些译文,“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怪不得严译的书风行二十年了。”胡适评林纾道:“林纾译小仲马《茶花女》,用古文叙事写情,也可以算是一种尝试。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殖民地。”胡适论林纾译文的成就道:
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采。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究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得多。
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但由于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能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胡适举周氏兄弟所翻译的《城外小说集》为例,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说明用古文译小说,固然可以做到信、达、雅,但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林纾的失败,并不是他本人的失败,乃是古文自身的毛病。
1935年9月,胡适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作《导言》,再次把桐城派古文的发展、应用问题作为新文学发生的背景予以论述。认为桐城古文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思想成果,向清顺明白的方向发展,其后期又以方、姚、梅、曾为取范对象,以为桐城古文为天下至美,取径虽狭,但切实有用,不眩古,不用典,使得“在那个社会与政治都受绝大震荡的时期,古文应用的方面当然比任何过去时期更多更广了。”胡适认为,近四五十年古文的应用范围:第一是时务策论的文章,种种的“盛世危言”,大都用古文写的:第二是翻译外国的学术著作,“严复的译文全是学桐城古文,有时参用佛经译文的句法,不过他翻译专门术语,往往极求古雅,所以外貌颇有古气”;第三是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最著名的译人林纾也出于吴汝纶的门下,其他用古文译小说的人,也往往是学桐城古文的,或是间接摹仿林纾古文的。”
虽然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适应了19世纪末期骤变的时代需要,“但时代变得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严复式的译书,严复曾在《群己权界论》的“凡例”中自我辩解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艰,且实过长。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当文学的外在形式已束缚内容的阐述,使广大读者不可猝解时,此正是古文穷途末路的表征之一,林纾与周氏兄弟所译小说,也处于同样的困境。
正是在古文处于这样的困境时,白话文运动应运而生。胡适分析五四白话文运动得以形成的几个文化因素:一是我国有一千多年的白话文传统,如禅门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二是全国都处在大同小异的官话区;三是海禁大开,国外有可资比较的成功范例。其次是政治因素:其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笼罩全国文人心理的科举制度现在不能再替古文作无敌的保障;其二是满清帝国的颠覆,中华民国的成立,专制政治的大本营不复存在。胡适引陈独秀的一段话云: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胡适对此话十分赞同,以为“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这也是“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的烟消灰灭”的时代原因。至于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倡导之功,只是把以后可能出现的事提前了二三十年。
胡适对白话文成功因素的分析,也可以用来反观桐城派古文覆灭的原因。桐城派学行程朱,文章韩欧,讲求伦理纲常,文以载道,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在封建政治这张皮之上的,封建政治的垮台,使桐城派自诩为道统、文统传人的优势轰然坍塌;桐城派文自方苞起,便与科举制有不解之缘,士人缘桐城义法而敲开仕途之门。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桐城派文失去往日功利性的诱惑,而不再为人所珍贵。桐城派文在清代盛行,与清政府的提倡保护有关。这种提倡保护一旦失去,其穷途末路也只有林纾之类的赤膊骂阵了,其与世事无补是必然的。相反,白话文由于得到国民的认同,北洋政府教育部定为法定国语后,才逐渐巩固其优势地位。1920年定白话为国语后,甲寅、学衡派与白话文倡导者的争论虽还在继续,但古文的旗帜已无人能使其再张,白话的势力已足可定鼎天下矣。
全面认识桐城派作家及桐城派古文,是新文学家五四以后全面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与新文化、新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写作双簧信的钱玄同、刘半农与写作《人的文学》的周作人,1925年前后关于林纾有过一次小小的争论。林纾死后,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了《林琴南与罗振玉》一文,对林纾的功与过作了简要的评述。文章写道:
林琴南先生死了。五六年前,他卫道卫古文,与《新青年》里的朋友大斗其法,后来他老先生气极了,做了一篇有名的《荆生》把“金心异”的眼镜打破,于是这场战事告终,林先生的名誉也一时扫地了。林先生确是清室孝廉,那篇小说也不免做的有些卑劣,但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
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他所译的百余种小说中当然玉石混淆,有许多是无价值的作品,但世界名著实也不少……“文学革命”以后,人人都有了骂林先生的权利,但有没有像他那样尽力于介绍外国文学,译过几本世界的名著?……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吾师的时候。(注:《语丝》第三期,1924年12月1日。)
此时,身处巴黎攻读文学博士的刘半农见到此文后复信于周作人,以为“你批评林琴南很对。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几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不过他若止于发卫道之牢骚而已,也就罢了,他要借重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注:《刘半农文选·寄周启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钱玄同作《写在半农与启明的信底后面》,对二人的通信内容提出抗议,钱氏绝不同意认林纾为前辈,何况以后辈不可唐突前辈?“实在说来,前辈(尤其是中国现在的前辈)应该多听些后辈教训才对,因为论知识,后辈总比前辈进化些。大概前辈底话总是错的多。一九一九年林纾发表的文章其唐突我辈可谓至矣。”(注:《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25日。)表现出不肯宽恕的态度。
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渊流》,发表了他对中国新文学民族渊源的思考。周氏认为:第一,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实际上是诗言志与文以载道两种文学潮流的交相起伏。诗言志是偶成的文学,称为言志派,文以载道是赋得的文学,称为载道派。第二,中国新文学的思想源头是明末公安派。公安三袁所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对明代复古主义载道文学的反叛,而公安派的创作,清新流丽,不在文章里面摆架子,不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由区分言志与载道,类比晚明与五四出发,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渊流》还涉及到对桐城派的再认识和对文言与白话的再认识问题。周作人认为:晚明三袁文学没有直接与新文学连接的原因,在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阻碍,八股文和桐城派可以看作三袁文学运动的反动。但根据言志、载道相互消长,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的文学发展规律,桐城派出现,又造就了新文学运动。周作人分析桐城派与五四文学的联系与对立道:
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着桐城派纲领,但他又加添了政治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待,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上的文字。曾国藩则将经中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所以,虽则曾国潘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新文学运动固然由于对桐城派的“反动”所起,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所受桐城派中人物潜移默化影响的事实也不可抹煞。新文学不是横空出世的舶来之物,它与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便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被忽视,但决不会不存在。
对于胡适关于文学“向着白话的路子走,才入了正轨,以后即永远如此”及“古文是死文学,白话是活的”两种说法,周作人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首先,中国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言志与载道是此起彼伏,交替消长的。现在虽是白话,虽走着言志的路子,以后也仍然要有变化,虽则未必再变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但必然还会有新的载道文学出现。其次,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因此死活也难分,我们现在使用白话,是因为白话更便于把我们思想和感情表现出来。新文学选择白话是因为时代与思想都在变,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传达出来。
周作人关于新的载道文学产生所发的议论,实际上是指当时已经出现的“革命文学”。1928年1月,周氏在中法大学发表题为《文学的贵族性》的讲演,主张文学家应跳出任何一种阶级。在演讲结束时,似在无意中把当时正流行的革命文学与桐城派作了一下对比:“先前人说到‘文以载道’。夫文而欲载其道,那么便亦近乎宗教上的宣传。桐城派的文,就是根据‘文以载道’的话,而成其为道。”“提倡革命文学的人,想着从那革命文学上引起世人都来革命,是则无异乎以前的旧派人物,以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古书来治国平天下的梦想。”(注:《晨报副刊》1934年12月1日。)
对于周作人把中国传统文学划分为载道与言志的基本看法,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位参与者朱自清有所修正。朱自清写于1947年的《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其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表现“达济天下,穷善其身”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要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或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须要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是风流的标准。朱自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文学或文体的解放开始的,在相当程度上,五四文学革命所确认的语体文学的目标是以外国为标准的,但中国文学传统中语体文学支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周作人所言的公安竟陵派只是这个支流的一段,公安竟陵努力想把支流变为主流,但失败了,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才完成了语体文学革命。
朱自清在《论严肃》一文中,就新文学之载道评论道: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这种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影响”,然而这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注:《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旧文学所载之道,是封建政治之道,新文学所载之道,是人民性之道。旧文学之载道,道尊而文卑;新文学之载道,道文并立,不分主从。载道之形式相近,而道之内容不同。但新文学若“只顾人民性,不顾艺术性”,也会重蹈旧文学“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注:《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的覆辙。
关于桐城派的评价,朱自清在1939年所写的《中国散文的发展》一文曾有专节提及。文章认为:“诗文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诗派比不上的。”“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文章论曾国藩对桐城派的中兴道:“桐城派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宏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选了《经史百家杂抄》,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比姚鼐远大得多。”朱文论桐城派消亡的文体原因及白话文发展的趋向道:
但古文不宜说理,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谓登峰造极。……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会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注:《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桐城古文消亡的自身原因,在于古文创造力的衰竭,古文的形式不再适应事理繁富、世变日亟的社会需要,梁启超“新文体”、五四白话文便应运而生。五四白话文似乎走的是古代言文合一的路,但却是在口语、传统白话的基础上,又吸收“欧化”的语言,所形成的现代白话,它比口语、传统白话更富有表现力,因而也更具有生命力。朱自清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文学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发展过程,是极具启迪意义的。
对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对旧文学的激烈与偏至,新文学家们有着明确的意识,他们认为这种激烈与偏至是一种与文言文、旧文学彻底决绝的策略。茅盾《进一步退两步》一文表述道:“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旧书。”(注:《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明白于此,便可知道鲁迅1925年为青年学生开列书单竟为何写明“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而五四之后的鲁迅、茅盾、郭沫若、胡适、朱自清、郑振铎等人,却又都实际从事于中国古典文学、神话、历史的研究。鲁迅1933年所写的《“感旧”以后》论及新旧文学以为:“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注:《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鲁迅在1930年所写的《〈浮士德与城〉后记》论新旧文化之冲突与承接道:“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注:《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在经历了破字当头的过程之后,新文学家都明确无误地回归到对新旧文化、新旧文学割舍不断联系的理性认识。
“五四”是说不尽的。五四新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而桐城派古文在绵延二百余年之后终归于沉寂。桐城派古文在五四时期是作为旧文学与文言文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学运动攻伐的。桐城派自身艺术创造力的衰竭,其所固守的文化价值及道统、文统观念的不合时宜,其行文拘谨、禁忌繁多的文言文体形式与日益丰富繁杂的时代内容不可协调的矛盾,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王朝的覆灭等桐城派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的变化,都构成了桐城派走向消亡的必然条件。五四新文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促使风烛残年中的桐城派最终走向消亡。五四新文学家运用更自由、更平民化、更富有表现力而经过加工提炼的白话,创造出风格多样、丰富多彩的新体散文,并使新体散文成为五四文学中最具有成绩的门类。而桐城派古文的消亡与新体散文的涌现,也便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道醒目的风景和一次充满思想冲突与文化意蕴的历史性转换。
标签:文学论文; 桐城派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朱自清全集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茶花女论文; 语丝论文; 白话文论文; 古文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