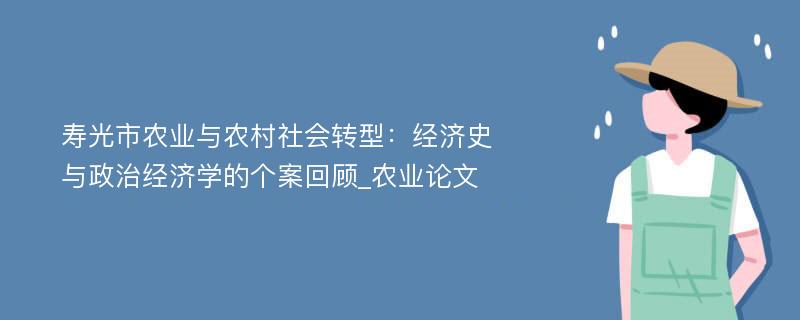
中国寿光市农业和农村社会转型:一个基于个案调查的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寿光市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个案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社会处在急剧转型期,尽管农业与农村从表面上看似乎仍处在小农经济结构的原生形态,但如果超越这表象,人们将发现,与城市化、工业化相联系的中国农村与农业实际上处在巨大的转变之中。在许多地区,农业生产方式远落后于工业生产方式,农村呈萧条状态其实正是工业蓬勃发展、城市急剧膨胀的伴生物。农村的落后状态以及它与城市化相比的滞后程度恰是中国产业政策与城市化政策的必然结果而非原因。
然而也有例外。笔者观察到,河南省南街村、江苏省华西村、山西省大寨村、河北省北戴河集发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集发公司”),还有山东省寿光市,其农业生产形态与组织形态均呈现出不同特点。上述各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已趋一致,农业不仅没有成为落后产业,农村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处在互为正反馈的状态,以至于农业产业链越来越向城市延伸并与工业、金融业、物流业实现了良好对接。
寿光市的农业与农村发展看似独特,其实隐含着一般性。首先,寿光市农业产业化已不局限于“一村一镇”,它是整个区域性的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当多的阶层和组织都卷进了这个历史进程,因之它的“制度故事”相当复杂,需要从历史时序和时间横截面两个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从历史时序看,笔者要追寻“寿光故事”的“制度起源”以及它此后的演变;从横截面来看,笔者有必要把南街村、华西村和大寨村,还有许多仍然处在原生形态的村庄做一个组织与制度方面的比较(对比)研究,从中发现山东省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的“制度特质”,这正是本文的“一个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题中应有之意。
很容易发现,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是渐进性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始终是它的基本制度特征。寿光市农民首先所做的不是制度选择,而是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寿光市才转向制度选择和组织选择,因而寿光市农村制度变迁更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的本质。依托于家庭承包经营制这种小农式的分散经营方式,以家庭为单位,寿光市成功地发展出了以农业为依托的蔬菜产业,并逐渐形成蔬菜生产基地。在市场拉动和技术不断改进的双重作用下,内生出了诸多形式的服务于蔬菜生产的农村货币金融体系。由于寿光市的新型农业能为农民和基层政府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和财政收入,因而政府也就有了把蔬菜产业做大做强的激励。为了满足融资需要,寿光市政府率先实施“确权”政策,使得土地承包权、大棚等变得可抵押,这样,寿光市农业发展就有了质押于土地及其附着物的金融支持①。在寿光市整个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中,政府介入和政策偏好是内生的。经验表明,寿光市农村制度变迁突破了简单的私有逻辑,相反它呈现了更加组织化或合作化的趋势。对比于某些特定地区,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更具一般性。
二、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一个历史演化过程的“比较制度分析”
讨论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有两个基本参照:第一个参照是1979年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第二个参照是寿光市之外的其他农业与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各种形态。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在中国农村,从1979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省小岗村,到江苏省华西村,一直向北到达河南省南街村,再到河北省集发公司,人们都能看到所谓“能人”的身影与作用②。小岗村的“大包干”是由严俊昌带领18户农民通过所谓秘密协议而创设的;河南省南街村则在王宏斌的带领下走了一条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不同的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之路;江苏省华西村显然未采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在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与此种所有制性质相吻合的集体经济组织,尔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齐头并进,逐步发展出农工商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实现了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南街村与华西村有诸多共性,它们都由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脱胎而来,却并未抛弃“公社制”的某些基本特征,这样一来,华西村与南街村就成了公社体制与市场体制的混合体,兼具规模效率与市场配置效率的双重优势。当然,华西村更少意识形态的自我定位,而南街村则更多地把它的成功归于毛泽东式的集体主义力量。
大寨村的带头人是郭凤莲,她的经历很有传奇性。20世纪70年代,她作为大寨“铁姑娘战斗队”的典型成了中共十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因此,她的“政治意识形态基因”与王宏斌、吴仁宝等毫无差异。“文革”后郭凤莲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她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她利用“农业学大寨”积累(起来)的无形资产获得了相应的政治支持和金融支持,通过集体化和市场化的“二元选择”成功地使大寨重新崛起。大寨起步较晚,其原因是它所承载的政治重负使它无法在改革开放之初迅速实现产业和组织转型,作为改革开放前全国农村的制度楷模和学习榜样,大寨面临并必须支付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村庄都绝不可能面临并承受的巨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转换成本(邓宏图,2004;2009)。到了20世纪90年代,郭凤莲集中大寨的人力物力,再次集体化,随之又市场化,结果使大寨成为中国最富的村庄之一。
集发公司的开创者李集周的制度选择亦显独特。事实上,他最开始接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很快意识到,如果以承包制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当地农民将无法利用日益开放的市场获得更多利益。最终,李集周召集并说服二十几户农民把各自拥有用益权的土地集中起来联合经营,一方面从事农业,另一方面从事养殖业和建筑业等生产活动。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基于农地产权集体所有的公司化运作模式。这与小岗村明显不同,与华西村和南街村也不完全一样。
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与上述诸种组织形态的演进相比更是表现出质的差异性。它并没有一开始就组织起来,这与华西村、南街村和集发公司不同,与小岗村十分相像,小农式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是小岗村和寿光市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形态。但是此后,寿光市的演变与小岗村完全不同。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的发展,来源于农业本身的发展潜力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从种植低收益的粮棉作物转变为种植高收益的大棚蔬菜。寿光市农民主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而非外出务工来增加收入。蔬菜属于普通大众型经济作物,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具备一定的蔬菜种植技术。然而,塑料大棚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却是一门学问和技术工作,没有一定的技术体系或者没有相应的种植经验,是不能轻易成功的。寿光市农业产业化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格局,有一段精彩的“制度故事”。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可以为这个故事脚本提供深刻的理论解释③。本文研究的正是寿光市农业产业演化的“制度成因”,因此,要从探索它的“第一推动”开始,这“第一推动”与一个叫王乐义的人有关。
1978年9月,王乐义当选为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当时三元朱村非常落后,王乐义和村民一起在村里的三个埠字岭种植果树,以补充粮食生产之不足,增加收入。1988年腊月,王乐义的堂弟从大连带回1公斤顶花带刺的鲜黄瓜,他见后惊奇不已。冬季还能种出新鲜蔬菜使王乐义陷入沉思:村民如果都能种收反季节蔬菜,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改善城乡居民生活,大大拓展农民的致富空间。次年他前往东北取经,苦学一个月终于掌握了反季节蔬菜种植技术。起初由于所学技术比较简单,冬季只能出产叶菜,王乐义便带着几个乡亲上北京、跑东北,先后调研了6个省(市)的反季节蔬菜生产情况,仔细记录、观察当地的气温特点与蔬菜大棚的结构,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心得笔记。通过借鉴外省(市)的经验,王乐义对原有大棚从方位、墙体、棚顶结构、大棚骨架、覆盖薄膜等处进行技术革新,终于建成了深冬时不需加温的冬暖式蔬菜大棚。
王乐义决定向村民推广这项成熟技术,建成更多实体大棚,使反季节蔬菜种植商业化和产业化。但是,建1个大棚需投入1万余元,对村民来说成本太高,预期风险也大,多数村民无法接受这种产业模式。王乐义只得在全村27名党员中选出17名筹款建棚,开始“产业试错”和“制度试错”过程。1988年8月13日,第一批17个大棚建成;10月18日,第一批黄瓜籽下种;12月24日,第一季黄瓜上市,每个大棚产量平均1 1200公斤,平均产值达30300元,剔除成本尚余2万余元,当地一下子出现了17个双万元户,引起不少轰动。这个结果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其他村民争相效尤。王乐义并不满足,他和其他村民苦学技术,反复摸索,于1992年首次向市场供应无公害蔬菜,至1997年,又大面积生产绿色蔬菜。2001年,三元朱村的300亩大棚被农业部授予国内首批无农药放心菜生产基地,他们生产的蔬菜直供北京多家大型超市④。
王乐义的成功为寿光市农业与农村发展提供了“产业示范”和“技术示范”,其他地区的农民也迅速跟进。以此为逻辑起点,寿光市开始了一场堪称隐性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既来自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又来自非农业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导致的人们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菜、果消费的大幅度上升,导致农业结构转化。这是由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革命。正因此,它更多地体现于产值上的变化,而不是传统模式中那种产量上的变化(黄宗智,2010a)。对寿光市农业和农村而言,以王乐义为代表的寿光农民的历史性贡献在于,通过引进新的种植技术(产业选择)而逐渐用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从而使传统粮棉与新兴蔬果种植产业并存,前者是过密性传统农业(黄宗智,2010b),后者是“劳动、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兴农业;前者的增收空间十分狭小,后者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而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因此,王乐义的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既适应了市场的需要,又迎合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经营制的组织形式,因而易于被寿光市其他农民所模仿、复制和学习,这样一来,王乐义的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就成了寿光市农业产业化的历史逻辑起点。
总结起来,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不同于江苏省华西村、河南省南街村、山西省大寨村,有其更直接的原因:
其一,与其他地区不同,寿光农村并没有开始着手组织选择和制度选择,而是更侧重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即在保持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前提下引进了一种新产业即蔬菜业,而为了更好地促进蔬菜业发展,同时引进并推广了大棚种植技术,这种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根本不同在于它的反季节性。即使在寒冷的冬天,由于大棚可以为蔬菜生长提供足够的温度,因此,许多非冬季生长的蔬菜仍可在冬天上市。这既改变了蔬菜产品的生产结构,又改变了蔬菜产品的成本结构、销售结构并增加了农产品卖方的谈判能力,从而扩大了农民的盈利空间。定价机制要受两方面制约,一是供给,二是需求。反季节蔬菜生产技术激活了潜在需求,潜在需求一旦变成现实需求,又会引导生产方进一步优化其产品生产与销售结构。这样,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也就随之产生了。
其二,表面看起来,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技术简单易学,但需要适当的资金投入和积累相应的人力资本(即经验)。王乐义的企业家能力和村支书的政治地位使他和其他农民很快克服了“金融约束”而获得搭建简易大棚的小额贷款,结果,更多的农民模仿跟进,寿光市的传统农业与蔬菜业就以产业互补的方式获得了共同发展,它既改变了农地的地租结构及其分配,也赋予了农地更高的可抵押性,因此,农村将因新兴农业的出现和农产品价值链的延长而内生出与新兴农业相协调的货币金融体系,这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环境。
其三,不难发现,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技术最先在寿光市推广并不需要特别的制度协调成本,首先,它只是技术和产业选择,并非制度或组织选择,并非制度创新,而仅仅是产业和技术创新。这无疑避免了过早的制度创新可能导致的政治风险,极易得到基层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其次,在此种技术开始推广的20世纪80年代,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市场具有卖方市场特征,农民只要进入新产业即可获得赢利,基层政府自然乐见其成,因此在政策上也极为鼓励此类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此类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无疑将导致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因为消费革命是任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逻辑结果,它会刺激人们选择更合适的农地制度和组织结构,这是一个持续的正反馈过程。
由此可见,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的路径与江苏省华西村、山西省大寨村等诸种路径均有不同,因为它不是以一个组织,不是以一个村落,而是以县为单位的整体演进。它起先是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转向制度选择和组织选择,因而寿光市农村制度变迁更能体现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依托于家庭承包经营制这种小农式的分散经营方式,以家庭为单位,寿光市成功地发展出了附加值更高,盈利空间更大的蔬菜产业,并逐渐形成蔬菜生产基地;进一步,在市场拉动和技术不断改进的双重作用下,内生出了诸多形式的服务于蔬菜生产的农村货币金融体系。政府的政策也非常具有弹性,能适应农民的需要而不断出台鼓励农民把蔬菜产业做大做强的政策措施。于是,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组织呈现出结构化、合作化、规模化的“制度特性”;在此基础上,农业生产体系又顺理成章地向种业、物流业、贸易业渐进性地渗透,并有力地刺激了工商业集群性组织的兴起。这条变迁轨迹有其鲜明的特点:先农业、后工商业,先自发性发展、后政府介入指导,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互动,政府与民间协调,指导性政策与市场的自由选择结合,终于使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顺利转型。
三、需求结构、地权、资本与组织形态选择
笔者调查发现,山东省寿光市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的制度起点与安徽省小岗村及全国大多数地区农村一样,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小农经济为其基本生产方式。但是,起点之后寿光市制度演变的路径与其他地区却大为不同。小岗村及全国多数农村仍停留在传统农业,而寿光市则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究其原因,是因为寿光农民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农产品结构,能够因时、因地选择合适的合同和组织来突破资本(金融)约束和土地约束。
(一)需求结构变化与组织选择
中国经济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不仅导致城市扩张,而且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从传统的8∶1∶1(粮食、肉禽鱼、菜果)向5∶2∶3(粮食、肉类、菜果)转化,如果中低收入者能进一步提高收入,转化的终点将达到4∶3∶3(粮食、肉类、蔬菜)。消费结构变化将导致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型农业和新型小农场出现(黄宗智,2010[a])⑤。黄宗智(2010[b])进一步推断,虽然小规模家庭农场⑥比大型农场更适合中国的新型农业,更多地依赖范围经济效益,但仍需要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在如此背景下,为了把小农场和规模加工与销售整合起来而自发兴起的。
黄宗智(2010[a],2010[b])的分析逻辑和基本结论建立在地权不变、资本可忽略不计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因而才把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仅仅看成小型家庭农场为实现范围经济而必须接受的必要构件。实际上,决定组织(结构)的要素不是单一的,必须对需求结构、地权和资本三要素进行通盘考虑。否则,以单一需求因素为分析基础的理论逻辑就既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龙头企业+农户”的合约结构,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龙头企业+农户”的合约结构被合作经济组织所替代,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会呈现不同的结构形态及其变种。
笔者调查发现,寿光市既出现过“龙头企业+农户”的合约结构,又出现过与蔬菜生产经营过程相关的产前(例如联合采购种子)、产中(例如联合生产)和产后协会(例如联合销售),在基层政府的积极介入下,许多地方还组建过蔬菜贸易市场。随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农业组织又向股份制企业或农村合作社进化;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生产,取得规模效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改进蔬菜品质,建立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经营体系,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提升蔬菜生产的利润空间。随着贸易半径的扩大,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仓储业、物流业也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原来的蔬菜贸易市场也被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平台的农产品交易中心所替代⑦。地方政府也迅速跟进,从制度、政策和技术等方面加强了对各种蔬菜的品质检验。给定技术水平和产业(产品)结构,在不考虑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合约结构和组织形态由地权和资本要素共同决定,亦即由农户和资方的谈判力共同决定。如果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高,即农民谈判力高于资方谈判力,则农民将占有合约结构和各类经济组织更多剩余,所选择的组织性质更倾向于合作社;反之,资本将得到更多剩余比例,所选择的组织性质更倾向于公司。
(二)土地与资本:四个合作社的经验观察
笔者发现,燎原合作社、凯瑞合作社、富昌合作社的发起人或理事长在成立合作社前均拥有各自的企业。燎原合作社理事长拥有生物菌肥厂,凯瑞合作社理事长拥有化工厂,富昌合作社理事长拥有盐厂和化工厂。当笔者询问以上诸合作社的发起资金如何解决时,后二者做出了十分决断的回答,“资金绝无问题”,其原因在于此两合作社理事长在非农产业经营上有充裕的利润。燎原合作社理事长在合作社成立前所从事的产业与农业有关,因而投入合作社的资本数额远不如凯瑞合作社和富昌合作社发起人(理事长)所投资本数额。但是,由于燎原合作社所从事的是现代农业,受到地方政府诸多政策上的支持,当地农村商业银行也在贷款上提供了诸多方便,因此,其发展势头并不差⑧。燎原合作社的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生物菌肥厂,厂长是李春香。2002年,李厂长在原厂的基础上组建果菜生产公司,2003年,为了解决土地规模不足和资金短缺的问题,李春香发动周边农户成立了销售合作社。但是,这类合作社只在销售渠道上合作,农户仍旧以家庭为单位分散作业,无法真正实现土地的规模化利用,也难以真正解决融资难的问题。2007年,李香春说服周边农户以土地入社,把松散型的销售合作社改造成寿光市燎原果菜专业合作社,既可确保土地的规模化利用,也能实现土地的资本化,因为寿光市政府和农村商业银行对合作社有种种政策优惠,每个农户可以自家土地为抵押,每亩可获3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贷款,合作社凭借这个条件一下子可以得到数以千万元计的融资权⑨,资金短缺问题由此缓解不少。鉴于燎原合作社对周边农户的带动以及对当地农业产业化的贡献,2011年,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又额外授信该合作社550万元的自助贷款,合作社可依据生产经营情况自行决定贷款用途。
凯瑞合作社是个统称,包括两类合作社——凯瑞蔬菜合作社和凯瑞土地合作社,分别成立于2011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前者是松散型合作社,农户只在销售上合作;后者是紧密型合作社,社员以土地入股,总计1500亩,合作社则每年以每亩600公斤小麦的平均价⑩支付给社员地租。两个合作社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名目不同,实质也有差异。顾名思义,蔬菜合作社主要经营蔬菜,农户不以土地入社,但所产蔬菜要统一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则以高于市价0.3~0.5元的价格收购农户所种蔬菜,然后转手卖给超市。合作社所得销售利润还要分配给社员(11)。可见,蔬菜合作社社员得到两种收入:一种是把蔬菜买给合作社所得到的价差,二是合作社向超市售卖蔬菜所得利润的分红。由于土地并未入社,这种合作社是松散型的,农民和合作社的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凯瑞土地合作社有其特定逻辑。社员以土地入股,这导致土地的集中使用,可以得到规模效率。合作社发起人(即理事长)一直经营一家化工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合作社的成立使土地与资本的结合有了可能。农户投入合作社的土地共计1500亩,折价220万元,合作社发起人即理事长投入自有资金220万元。这样一来,农户作为整体与理事长各拥有50%的合作社股份。在此基础上,合作社可以土地为抵押从农村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在土地合作社,农户只以土地入社,每年从合作社获得土地租金收入并参与分红,但不参与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愿意接受合作社的雇佣,则每个月可从合作社领取固定工资。这样一来,一些社员就有了二重身份,既是社员,又是工人。
蔬菜合作社专营蔬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强,不确定性大,故采用销售合作的方式;土地合作社主要种植中药材例如丹参、黄芪以及苗木,产品生产的季节性较弱,为了消除不确定性,需要更密切的合作,紧密型的土地合作社就成了不二选择(12)。因此,合作社结构既是农户与合作社讨价还价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所从事的产业属性相关并受后者制约。
富昌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合作社发起人即理事长在合作社成立前拥有盐厂和化工厂,财力雄厚。与农户组建合作社时,投入自有资金5000万元,通过其他途径得到600亩左右流转土地,又从社员手里获得500亩土地的使用权。合作社社员每年生产有机蔬菜约650吨,实现销售收入1000万元。和其他合作社一样,富昌合作社每年以每亩500公斤小麦的平均价格补偿给入社农户,因此,入社农户同样有两笔收入:一笔是作为社员的年终分红收入;另一笔是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地租收入。有意思的是,富昌合作社采用三种合约方式:①反包式的公司加农户合约结构,即合作社与农户双方签订价格合同;②固定租金合同,即某些农户或社员从合作社那里承包“大棚”,每年给合作社上交固定租金;③分成合同,即合作社与农户或社员议定一个分成比例,年终按双方所议比例分红。对合作社所雇工人来说,他们每月只能从合作社领取固定工资。富昌合作社的缔约结构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张五常(Cheung,1968)的分成租佃理论。
比较上述四个合作社的缔约过程可以发现,农民入社始终是一个被动选择,尽管这种被动选择的确改善了其家庭收入状况。具体来说,缔结合作社这类组织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拥有财力的企业,但(这些企业)最后成功地构建了形态各异的合作社,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的确给地方政府、农民还有企业本身带来了可持续的好处,因而具有帕累托效率含义。
(三)地权约束与资本约束及其解决:经验观察与理论解释
黄宗智(2010a)敏锐地发现,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不仅诱致了城镇化,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因此,传统农业必然要被产品附加值高、产业链长的现代农业所代替,这是诸多来自城市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愿意投向农业的最主要原因。然而,他们可能会面临融资问题和如何规模化地利用农村土地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要解决金融约束问题和由农地产权集体属性所导致的制度约束(即土地约束)问题,因此,在组织形态的选择上,合作社比单纯的公司化运作具有更多的制度优越性。
在政治上,如何使数量庞大的农民致富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因此,基层政府无一例外地支持企业或城市资本与农村土地结合。理论上,合作社社员既拥有平等的决策权,又将根据出资额获得相应的分红权,与只获得工资收入的工人在企业内部所处的经济地位具有质的差异性。因此,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比起农业公司在政治上更易被接受,在政策上更易得到关照(优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业的主流制度,任何经济组织要实现资本与地权的结合必然通过三种方式:购买;承租;通过一体化让农民以地权为股而缔结合作经济组织。理论上讲,合作社属于第三种农地与资本结合的实现方式。承租则意味着企业通过向农民交纳地租而获得农地使用权。购买即企业直接从农民手中买断农地产权(13),这在制度和政策上均不可行,因为农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产权)主体。
笔者调查发现,寿光市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均产生了某种“制度变异”。富昌、凯瑞、燎原三个合作社均以承租方式获得农民土地的使用权,每年每亩地价按照600公斤小麦(根据市场情况每两到三年调整一次),所有出让土地使用权给合作社的农户就成了社员,年终参与合作社利润(销售收入剔除各类生产和管理成本等)分红。社员可在合作社内部就业,拿固定工资,也可从事其他活动。实际上,这种合作社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社员的决策权,因为地权之于合作社具有承租的性质。既然社员与合作社具有地权出让与受让的“承租”性质,因而在决策权分配上就会“弱社员而强企业”,这种变异的合作社结构正是作为合作社发起人的企业精心策划的结果,因为企业最渴望得到的是农村土地的使用权。理论上讲,合作社是一种所有成员在经济地位上一律平等的经济组织,国家和银行对此类组织一般总有种种优惠政策和极为便利的贷款(融资)条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地权(使用权)即意味着拥有信贷权。这就是寿光市的合作经济组织实际上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的“变种”的原因之所在。给定农村土地产权的集体属性,企业或城市资本总是倾向于选择合作社而舍弃企业形态,因为前者将给企业或城市资本带来更多的比较制度效率和信贷优势。
例如,燎原合作社就是从企业转型而来的,至今没有放弃“合作社+农户”的合约结构,显然,这种结构是“龙头企业+农户”合约的变种,两者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很明显,选择合作经济组织替代企业组织,可以使作为合作社发起人的企业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也利于企业低成本或零成本地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也使农民更能按照合作社的意图协调行动,减少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使各方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选择“合作社+农户”的合约结构则使各方利益更为清晰,并且减少了各方平等议事的决策成本,因为这种合约结构把社员在合作社内部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减弱了。对凯瑞销售合作社来说,作为发起人的龙头企业对农民的土地和劳动力并无约束力;凯瑞土地合作社则完全不同,发起人首先通过每年每亩计600公斤小麦的价格从农民手中租得土地承包权,然后与这些出让土地的农民缔结合作经济组织,这样,作为发起人的企业既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也获得了以地权为抵押的信贷能力。这是一种基于地权和资本的组织或合约选择。
调查还发现,与上述诸合作社不同,寿光市蔬菜产业集团绝对是个例外。这是一个成立于1998年的民营企业,它在种子培育、高科技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和物流业等方面具有十分雄厚的实力,也得到了外国财团和种业公司的支持。因此,它没有选择合作组织的形态,相反却完全以公司化方式从事农产品的研发、生产、深加工和贸易。它所拥有的1600亩农地全部从农民手中承租而来。这意味着,企业越强大,越不会选择合作经济组织,因为拥有绝对的自由决策权和占有全部剩余是这类企业的首要目标。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地位(拥有商标和多种专利技术等)使其不需要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就可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充分信任。
有必要指出,本文对有关命题的证明基于案例和对案例的逻辑分析(解读),这种做法当然与一般意义上的数学归纳法有一定距离。这种方法是笔者所倡导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一个具体应用,是经济史的“史料实证”(邓宏图,2009)。对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来说,这种方法虽有缺点,但证明的力度已经足够了。
限于特定的研究目的,本文未对各类经济组织作更为细微的分析。对各类经济组织的微观分析十分重要,必须借助合同理论、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才能展开相关研究。本文分析以1979年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起点”,目前来看,这个基础性制度被江苏省华西村、河北省集发公司、河南省南街村“迅速超越”了。表面看起来,家庭承包经营制在任何地区都是等同的,但事实上不同地区总有若干不同因素嵌入其内,从而引发不同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就出现演化路径上的差异性。在华西村,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早的是社队企业;在南街村,制度变革与意识形态偏好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寿光市则不同,它的制度变革是渐进性的,承包经营制始终是它的基本的制度特征。正如黄宗智所说,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会造成消费结构的变化,以此为依托,一场新型的、隐性的农业革命也就开始了。寿光市的“制度故事”有如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活版本”,它首先所做的不是制度选择,而是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重要的是,这两种选择都适应了市场的需要,因此,寿光市的“制度故事”与“市场故事”合二为一,也就具备了一般性的农业与农村社会转型的“典范意义”。
寿光市农村制度变迁突破了简单的“私有化逻辑”,相反它呈现了更加组织化或合作化的趋势,这与三十年来的诸多文献所展现出来的分析逻辑或理论推断(14)多有不同。其基本原因在于,给定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变化,资本和农地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两者的结合与匹配既决定缔约或组织结构,也决定新型农业产业全部潜在剩余的分配比例。笔者调查发现,龙头企业在寿光市诸多形态的合作社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龙头企业需要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来解决资本(金融)约束和地权(制度)约束问题。农地属集体所有,用益权则归之于农民。龙头企业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通过缔结合作社来规避由此产生的制度障碍,加之农地具有信贷可抵押性,用合作社替代先前的龙头企业加农户结构也就顺理成章了。研究表明,当资本十分强大时,龙头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进一步公司化和规模化;当资本占优,但地权对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极为重要时,龙头企业在新缔结的合作社中将拥有更多更大的决策权,分享的合作剩余也比农民多;在农地相比资本更重要时,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民来说将更能体现公平性,农民相对于龙头企业将占得更多合作剩余。当农民所拥有的地权相比资本占据绝对优势时,合作经济组织将不被选择,小农式的散户经营(即最原始的联产承包制)将是最好的制度结构(大量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传统农业地区)。实质上,本文并未从微观层次对上述选择做出更具体的分析(15),但整个分析所揭示的逻辑却是显而易见的。
笔者感谢崔宝敏、曾素娴、韩婷对寿光市农业经济组织部分调查资料的整理,同时感谢寿光市政府办公室对本次调查的全力支持。
①此处描述与判断得自笔者2012年5月对寿光市的调查。据寿光市金融办李主任和潘主任介绍,中央在浙江温州市、丽水市实施的金融改革试点工作中采取的诸多政策,寿光市在自己的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均已率先实行。
②所谓“能人”,是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这是一个熊彼特式的定义。笔者认为,企业家不是外生的,而是依据市场环境变化“诱致”出来的。
③数据来源:《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过万》,中国寿光市网(http://news.sgtv.cc);百度百科词条:“寿光市”,百度百科网(http://baike.baidu.com)。
④此处的“制度故事”乃笔者调查所得。
⑤高原(2010)为黄宗智(2010a,2010b)的论点提供了极好的经验证据。
⑥黄宗智(2010b)认为,小规模家庭农场是以农户为单位,但所经营的农业却是现代农业。笔者认为,黄宗智的这种说法应该是比较理想的说法。
⑦资料来源:寿光市蔬菜指数网(http://www.sgvindex.com)。
⑧许多龙头企业之所以热衷于缔结合作社,是因为通过合作社可获得农村商业银行或其他商业银行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以及其他政策上的好处。
⑨据调查,即使有来自政府和银行的优惠措施,燎原合作社仍感到资金短缺所产生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燎原合作社的业务越做越大,所经营的蔬菜和瓜果种类也越来越多。合作社的急剧发展的确会使其产生对信贷的依赖。
⑩平均价是指计价当年和第二年小麦市价的平均值。
(11)社员从合作社得到的红利按下述公式计算:(超市蔬菜收购价-蔬菜市价)×分红折扣系数×销售量,折扣系数是合作社和农户商定的结果。
(12)从调查可知,该合作社的土地分配是这样的:丹参1000亩,黄芪150亩,苗木(银杏苗)50亩,苹果园、葡萄园共计50亩,大蒜150亩;预留丹参苗用地100亩。
(13)主要表现为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并与农地结合从而实现资本农地化或者农地资本化。
(14)杜润生(2005)对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成因有相当详细的分析。周其仁(2011)、张维迎(2011,2012)、文贯中(2008)、陈志武(2005)、杨小凯(2007)、Coase(1937)、Cheung(1968)声称农地私有化可以解决(农村)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这近乎是经济学浪漫主义的理论诉求,并未得到经验证据的有力支持。张晓山、苑鹏(2009)、姚洋(2008)、温铁军(2005)、李昌平(2009)、贺雪峰(2010,2012)、黄宗智(2010a,2010b)的许多论点则突破了简单的私有化逻辑。
(15)笔者将在另一篇论文里对此展开更为细致的分析。
标签:农业论文; 农民论文; 南街村论文; 农业合作社论文; 农村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三农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农民合作社论文; 蔬菜论文; 种植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