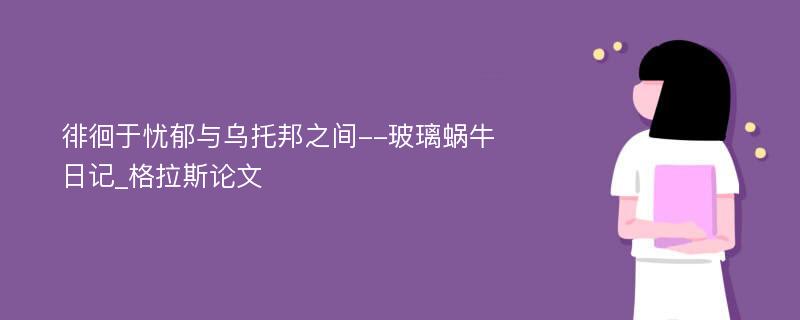
在忧郁与乌托邦之间徘徊——论格拉斯的《蜗牛日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蜗牛论文,忧郁论文,格拉斯论文,日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6-0016-06
在赖以成名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和七十年代后的鸿篇巨制《比目鱼》、《母鼠》之间,格拉斯推出了《蜗牛日记》。这部半自传半虚构的叙事作品不仅在时间意义上“当轴处中”,而且相当集中反映了作家在政治、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观点。书名中的“蜗牛”象征着在“忧郁”与“乌托邦”之间徘徊者的努力,在一定程度可视为既不愿放弃以笔济世的尝试、又对纯粹的“希望原则”提出质疑的格拉斯本人的化身。
在文坛上一举成名之后,格拉斯走出书斋,自称以“公民”身份直接投入了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活,为社民党摇旗呐喊。这一举动与传统上超脱清高的文人形象大相径庭,却符合格拉斯认为文学与政治既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又不能干脆合二为一的观点——他将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喻为其关系若即若离、其距离可近可远的“两个啤酒杯垫”。①在四处奔走、“演讲复演讲”的竞选过程中,格拉斯仿照主要以格言和日记形式进行创作的启蒙主义作家利希滕贝格的做法,在所谓“涂鸦本”中纪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这些随意的断片后来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在1972年的《蜗牛日记》沉淀下来。
格氏作品经常成为“互文性”、“浪漫主义式整体作品”之类研究课题的对象,他一直对固定的体裁归属不以为然,此次同样也未说明《蜗牛日记》是否小说抑或其它。评论界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的长篇小说,亦非文献汇编,也不能称为日记或者自传。但他将这种或那种文学体裁的要素以一种新的、我认为是令人信服的方式糅合在一起,进行了创新。这本书属于当前时代,但有足够的实质内容,可以超越当前时代流传下去。”②
忧郁与乌托邦及其关系便可视为超越时代的实质内容之一。这一主题在《蜗牛日记》本身的二十九章,尤其是在书后所附《论进步中的停顿——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铜版画〈忧郁一〉的变体》的讲演稿中得到了充分的探讨。
《忧郁一》为德国名画家、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之一阿尔布雷特·丢勒(1471-1528年)所作,成于宗教改革的前夜。画上可见一位头戴花环的女子“忧郁”,虽身体强健、背负双翼,却无力飞翔,只是一手持圆规,一手托下巴,目光茫然、心情苦闷地坐着沉思。这一所在既像书斋,又似作坊,周围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刨、尺、圆球、多面体、满是缺口如同锯子的剑等,墙上挂着天平、沙漏、钟,数字魔方阵下行中间的是“1514”即创作该画的年代。一切都显得那么呆滞,另外两个活物——小天使和蜷缩着的狗——也无灵气可言,惟有背景的海天上方有一只蝙蝠,正牵着上书“忧郁”字样的条幅飞翔。
忧郁天使及画上的众多细节分别意味着什么?对此可称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一地散乱的工具仪器都与技术和数学有关,象征着当时的实用知识和世界探索陷入了无解的困境和停顿,理想与现实、无限的追求和有限的可能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忧郁;有的认为,丢勒在画中表现了自己的失望,理性工具、数学方法和测绘技术难以胜任艺术创作的重任;有的在其中发现了画家人文主义的思想和内在自我的写照,求实与探索的智者都不免产生某种孤独感;有的感到“这幅画实在叫人费解”③;《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认为该画“反映了当时先进分子思想上的矛盾”,但这位忧郁的化身和文人学士等新知识阶层的代表“体质健壮,且有羽羿附身,因此也隐有寻求答案的坚强意志”;④有的则一一对号入座:忧郁女子头上的花环和墙上数字魔方阵构成治疗忧郁的手段,背景中的大海象征着土星这颗主管航海的行星,夜行蝙蝠体现的是忧郁,圆规、沙漏等表示几何与时间的计量,彩虹与天体学科学有关,笔和记录本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工具,钟意味着僧侣般的寂寞和孤独,狗本来就在忧郁动物之列,而小天使则是忧郁在童年就已露端倪的思想家的缩影。⑤瓦尔特·本雅明曾联系丢勒的这幅名画讨论“身体与灵魂的忧郁”。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土星与忧郁——自然哲学和医学史研究》⑦,这部名著从各个角度梳理了古希腊古罗马及中世纪文学中的“忧郁”概念,探讨了文学和美术作品中的“土星”题材以及“忧郁”概念在现代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丢勒的铜版画作出了阐释。
格拉斯对忧郁及其与乌托邦的关系的探讨并非超脱的、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而是更多地突出了主观体验和自身观察。他“被一个比一个跳得高的乌托邦紧紧包围着”,又“日复一日地跌入忧郁的纠缠”,因而并不能保持对客观研究而言不可或缺的距离,开始时也无暇请教亚里士多德、费西诺、伯顿 (Burton)、莎士比亚、叔本华、克尔恺郭尔、本雅明、马尔库塞等对忧郁有过论述的大家或者写过忧郁问题专著的帕诺夫斯基/萨克斯尔和沃尔夫·莱佩尼斯(320页)。
使格拉斯如此着迷的“忧郁”形象,在西方已有几千年的研究史。“忧郁”一词初见于医学领域。公元前五世纪产生的气质体液说认为,由脾而生的黑胆汁占优势者属于忧郁型气质。人们不但认为身体和精神交互作用,在古代的哲学思考中,四种体液也分别与宏观宇宙的要素和周期有对应关系。在占星术中主司忧郁的是土星,在西文中以罗马农神“萨图努斯”命名。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费西诺也曾抱怨自己沮丧、绝望、痛苦的情绪与“萨图努斯”的影响有关,但后来他的看法产生了逆转,重提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无论在哲学、政治领域,还是在文艺、美术领域,杰出的人才显然都是忧郁者?⑧哲学家和艺术家身上的忧郁并非纯粹负面的特征,而是呈现出二重性:病态和天才,痛苦和探索,癫狂和创造。
土星对中世纪神学而言主要是灾星,对现存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而言,忧郁者都构成干扰因素。启蒙运动同样严厉抨击忧郁,视之为有悖于理性秩序的左道旁门,“非理性”的忧郁者成了负面价值的载体,因为他们与启蒙运动的目标扦格不入。狂飙突进运动则宣称“诗为人类母语”,反对理性大一统,高扬不拘一格的天才。两位柯尼斯堡学者在此形成了对立:康德提出了著名的启蒙定义,而狂飙突进文学的思想先驱之一哈曼被称为忧郁天才之父,深信越是阴暗,便越是热忱。在启蒙主义者眼里,理性和忧郁犹如光明和黑暗势不两立。但并不顺理成章的是,恰恰在启蒙艺术家和学者中间忧郁者为数众多,恰恰在当初最进步的国家流行着被称为“英国病”的忧郁症。向辉煌未来挺进的途中阴云密布,失望的理想主义者转眼就陷入了忧郁的病态。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的日益卑俗化,作为文化载体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成了忧郁的局外人。艺术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忧郁成了艺术的基调,艺术成了痛苦的产物,成了“社会内的外邦”。这种边缘化过程在第三帝国时代大批文化人背井离乡、亡命天涯时可以说是臻于极致。
《蜗牛日记》中的“我”在旅途中随身带着丢勒铜版画的艺术明信片。画上与土星造物和神话残余同在的是大量杂物,它们大多暗示着处于新时代门槛上运用科学理性获取知识和进行实践的人类活动。然而这些此刻被闲置了。忧郁天使“置身于工具之间无所事事,似乎几何学的计算出了偏差,似乎最新的认识刚蹒跚学步就在疑云中了陷入了停顿,似乎知识被扬弃了,似乎美变得一文不值了,似乎唯独神话才会继续流传。”在格拉斯看来,这幅名作描绘了“人文主义时代反应性忧郁状态”,表现的“不是有霉味的、黑胆汁的忧郁,而是自我把握的、从认识中产生出来的忧郁。”在画中,光明面里握拳的左手和阴暗面中目光呆滞的脸庞以及无力地拿着圆规的右手形成鲜明反差,忧郁天使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渡时代的见证人,一个“至今仍然有效的过渡时代”的见证人。(327-328页)换言之,画的基本框架是“可以转让的”(316页),是允许有变体的。忧郁天使今天随处可见。
比如流水线边上的女工。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忧郁既不是星占学意义上的必然命运,也不是医学意义上的内因性病态。如今忧郁不再为发明者、创造者、艺术家等知识精英所独有,而是成了“雇佣劳动者的阶级特权”(318页),成了以效率为原则、以业绩为标准的现代社会的普遍状态。休闲时间的情况也相去不远,发达国家的“休闲”时间正如马尔库塞而言并非自由时间,⑨忧郁天使在此以“旅游女士”的面目出现,带有流水线特征的“观光”、工业化的休闲方式使她感到腻烦。此外,市郊别墅里百无聊赖的“绿地寡妇”,含哺鼓腹却对消费强迫开始厌倦的女士,也被格拉斯想像为福利社会中忧郁天使的变体。这些女人均可出现在《忧郁》画上,只需替换道具而已:丢勒画上忧郁天使无力地手持圆规,适用这些现代哀女的是工具、相机、成人用品、开罐头刀。头巾或者卷发夹也不妨用来替代忧郁天使头上的花环。最后提及的莱奥·鲍尔和另一位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可以手持镰刀斧头,但在格拉斯笔下却代表了多次劳而无功后对社会公正的理想产生怀疑的失望者,犹如“忧郁天使”暗指的当初对几何学作用产生怀疑的人文主义者。连自称“后期启蒙者”的格拉斯也承认,自己在竞选途中遇见许多“踩着理性这一水车踏轮的忙碌者”,自己也不免失去勇气:“我说话,同时我在沉默。我认定部分目标可以实现,同时我在放弃。我——不少人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为启蒙效劳所得无几,但还是在乏味的论据堆中静守着,被相互矛盾的改革模式包围着,被专家们的论战骚扰着,置身于玻璃罩下:在场又不在场。”(334页)
通过这一幅、严格地说是这一系列《忧郁》画,“我”试图向后代形象地阐明“动中有静,止中有进”的道理,因为丢勒画中所表现的如“停顿中的进步”,“步骤之间的犹疑和停止”,“思之所思,直至唯一肯定的只有怀疑”,“引起厌恶的认识”(329页)等等,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在叙事角度上,一般认为《蜗牛日记》的特点是叙述者之“我”和作家之“我”的距离逐渐消解,以致后者融入前者。“我”无疑带有格拉斯本人的特征,但作为作品中的叙述者,“我”又与虚构人物往来,一如《比目鱼》中的“我”是从古到今九位厨娘的丈夫或情人,《母鼠》中的“我”也是文学形象侏儒奥斯卡的合作者。格拉斯本人以这种方式又逃出了虚构世界。这亦我亦他亦实亦虚的叙事者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在“我”参加竞选活动回到柏林后不断提出问题,这成了“我”阐释政治立场、人生态度、作家使命等等的契机。主要以此教育性的家庭问答为中介,叙事结构的两个层面联系在一起。其一是1969年的德国政坛,从首页上古斯塔夫·海涅曼当选联邦总统开始,到同年勃兰特成为联邦总理为止。穿插其中的历史层面涉及1930年起在格拉斯作品中永远出现的故乡——但泽——发生的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故事。在这虚构世界中有两个人物形成反差。一个是海尔曼·奥特,人称“怀疑博士”。⑩因为他“像用刀叉一般地习惯地用‘怀疑’这个词儿”(23页),以“我怀疑”(32页)为口头禅,所以无论在纳粹时代还是在战后的波兰,他的日子都不好过。这位参议教师帮助被人鄙夷地视为忧郁者的犹太人,熟悉亚里士多德和费西诺的学说,撰写以忧郁为题的论文,象格拉斯一样经常援引利希滕贝格和让·保尔,在叔本华学会任秘书,从自己倾慕的这位哲人那里学会了“在认识前先进行观察,而不像黑格尔那样先有论点再从观察中寻找论据”(52页)。
如果说,奥特对“灰”情有独钟,喜欢这种与他怀疑主义的基本立场匹配的颜色,那么,另一人物奥克斯特则如其妻所云,“不懂什么叫妥协,在他看来一切都是绝对的,非是即否,非黑即白”(256页)。他的特征是有“爬上官位的需求”,有“获准服从的愿望”(234页),并“随时准备把怀疑原则当作奢侈品变卖”(256页)。追随纳粹的同流合污者和学生运动的激进革命家分别能在早年和后来的奥克斯特这个人物形象上发现自己的化身,“两者都是绝对性的见证人,两者都追求毁灭和拯救,两者都只要真理,都急于将真理挤将出来:犹如一次艰难的、难以完成的出恭。”(178页)
这种对立关系也在两种动物意象上体现出来。奥克斯特尊崇的黑格尔“看到拿破仑骑在高头大马上,并在骏马和骑士合成的统一体上看到了一种他称之为世界精神的东西,从此之后它便狂奔起来……”(50页)。奔马意味着革命、单解、整体、速度,意味着一切专制和极权所基于的历史观和国家观。格拉斯认定黑格尔是一切“将国家之权利解释为历史之必然”(53页)的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在《蜗牛日记》中以但泽犹太人惨遭迫害的悲剧说明,整体的、封闭的、似乎自足的思想体系必然导致使个体处于“未成年状态”即“未启蒙”状态的危险。纳粹高唱“向前”;不过这个词是“吹出来的,因而转眼就会瘪下来,需要狂热为气信仰为泵来服侍……”(33页),不但是人们后来在集中营和瓦砾堆里才理解了这一纳粹用词的真正涵义,其实“腮帮子红彤彤地鼓吹以进步为目标”(316页)的学生运动也和驮着其他意识形态的奔马一样,只是“加速了退步”(33页)。
与此相反,奥特乐于收集和观察的蜗牛意味着进步,而这正是因为它主张批判和摸索、坚持怀疑和修正,接受停顿甚至倒退这些社会进步中必然的伴随现象。蜗牛形象在格拉斯以前的作品《我的绿草地》中就出现了(11),它体现了作家从历史上、尤其从亲身体验的纳粹时代意识形态教条化中获得的教训和反乌托邦、反理想主义、反激进主义的立场。“慢”成了“进”的同义词。坚忍不拔的蜗牛以肌肉足慢慢挪动,“原则上落在马后面,在实践中却跑在马前边”。(50页)对始终不能也不愿忘却纳粹罪恶的格拉斯而言,“没有什么比一溜烟地直达目标更让人觉得憋闷的了”(13页),没有什么比确定一个绝对化理想并试图尽快实现更可怕的了。这种历史经验是后代必须记取的,因而《蜗牛日记》中的“我”对孩子说:“我们原则上不拒绝进步,但反对冒进急躁。……我们的财富是持久力。我们决不匆匆忙忙。”叙述时也倾向于曲径通幽,或省略或重复,并不按着严格的线性时序。“要耐心。……请你们别冲着我嚷嚷什么‘快点好不好!’、‘赶紧跳吧!’”(13页)格氏作品特征之一的“昔今未”,即后来在《头脑产物》中明确提出的“过去”、“现今”、“未来”三际合一的时间观与历史观,在此已露端倪。(12)
时常对形形色色的“大跃进”旁敲侧击的格拉斯认同蜗牛——“我是人形的蜗牛。我有向前的欲望,内敛的欲望,蜗居、迟疑、执著的倾向,在情感上我不安、躁动,在这些方面我都有蜗牛相”(72页)——,认同“伯恩斯坦蜗牛”(据说确有这种蜗牛,因其壳呈琥珀色,“伯恩斯坦”在德语中有“琥珀”义(13)),认同伯恩斯坦否定终极目标的观点及其主张的“进化论的、忧郁不决的、阶段交错的、总而言之蜗牛式的过程”(79页)。格拉斯多次自称是“修正主义者”,倡导不断摸索、小步前进,既反对断念和放弃,更拒绝醉迷和狂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蜗牛被视为“忧郁和乌托邦之间的中介”(102页),奥特在蜗牛身上发现了既能克服沮丧又能治疗亢奋的灵药。
格拉斯在《蜗牛日记》最后更是直接探讨了一方面“每天都向乌托邦进发”,另一方面又“倒退到忧郁的暗室”(316页)的极端态度及其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
土星从来就是矛盾的星宿,即使在当代也兼为“忧郁和乌托邦的首领”(316页),实行着“双重统治”。忧郁和乌托邦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成。六十年代末为社会乌托邦而慷慨激昂的大学生很快就一蹶不振,正说明“从好高骛远的革命之巅就可以预计到无可奈何的郁闷之谷”(335页)。基于自己的观察,格拉斯认定忧郁和乌托邦是“雌雄同体”(105页),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对丢勒这样的画家而言完全可以出现在一张双人像上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316页)。这对姐妹“争先恐后地抢话筒”(320页),并不知晓自己的同胞关系。预言伊甸园的乌托邦主义者和主张“大拒绝”的忧郁者都在援引马尔库塞;这位德国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先驱将忧郁和乌托邦联系起来,“从绝望的辩证法中发展出忧郁行为和乌托邦行为的一致性来:大拒绝导致安乐的此在”,(335页)恰恰是绝望的全面否定似乎成了踏进乐土的不二法门。
格拉斯的兴趣所在是这两个“遁点”之间的张力,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的道路,是停顿和进步之间的辩证法。《忧郁一》的画面上可见一把梯子靠在墙上,这或许象征着建设者的高远志向,也可能是暗指一幢房屋尚未竣工,现代读者不由会想起启蒙这项未竟工程(14)。“进步以停顿为回声,忧郁是乌托邦的衬里,摆脱不了的圆木拦住跑步者,忧伤在终点欢迎得胜者……。”(103页)这是进步中的停顿,但对如此频繁的挫折,还有进步的希望吗?格拉斯究竟是“晚期启蒙者”还是“放弃鼓手”?(287页)
《蜗牛日记》将负面人物奥特的家安排在“离布洛赫教授不远”的地方。这与格拉斯对《乌托邦精神》和《希望原则》作者的批判态度是相应的,他在以后问世的《比目鱼》、《母鼠》等作品中也不时地对布洛赫旁敲侧击,呼吁世人告别乌托邦。按词源学来看,近人音义兼顾地译为“乌托邦”的Utopie,表示“乌有乡”,也可解读为“理想国”。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我国的《桃花源记》不乏其例。“乌托邦”也可在与“现实”、“实干”、“科学”等概念对立的意义上使用,表示“不切合实际、不诉诸实践、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空想”。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更多是指一种人类的普遍意向:对“尚未”的更美好状况的希望和期求。在布洛赫看来,世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向未来的各种可能永远开放的过程,而人类总是在期盼达到更完美的状况。他认为历史是乌托邦思想和“客观关联物”即现实的进步可能性相结合的产物,其“希望原则”显然不能与空中楼阁相提并论。但在格拉斯笔下,这位原东德哲人的名字却成了一个简单的符码,它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乌托邦哲学,一种无视人的历史责任的盲目乐观,一种对与日俱增的使忧郁合理化的现象视而不见的天堂许诺。
“我的蜗牛害怕‘天堂’这个字眼。”(177页)格拉斯深信自己的人生经验,认定在所有的天堂许诺那里能期待的只能是灾难。所以面对世人不断提出的“有望还是无望”的问题,他总是倾向于说无,总是对“这种作为终极目标的幸福状态值得追求”打上巨大的问号。在此,同样无需“希望原则”作为奋斗动力,同样认为历史并不依赖于某种意义或目标预设的加缪又能视格拉斯为同道了。这位德国文坛上的西西弗斯并不热衷于勾勒玫瑰色的前景,而是将人生视为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推石上山的过程,即使有成绩也是转瞬即逝,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文学评论家拉达茨称格拉斯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忧郁者”,(15)而不爱听那些“云雀般鸣啭的女高音”(330页)演唱幸福之歌的忧郁者向来就不受欢迎。中世纪时,忧郁常被视为病态,忧郁者因为“懒散”和试图挣脱钦定幸福观的束缚,使得教会和时俗的统治者颇感威胁,尤其当忧郁可能不再为掌握知识和权柄者所独有的时候。启蒙运动更是将忧郁者视为理性秩序的敌人而加以抨击。后来的弗洛伊德也将忧郁视为一种应该治疗的病态反应,隐隐约约地与从神学或道德角度对忧郁者的批判一脉相承。在德国现代历史上,无论右派还是左派,指责忧郁的不乏其人,原因是忧郁者或是无视现存的价值,因而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或是否定乌托邦的目标以及实现乌托邦的手段,成为“介入”、“革命”、为争取政治进步的斗争的绊脚石。
在格拉斯看来,长期以来基本上属于边缘现象和局外人特征的忧郁,在生态灾难、战争威胁、社会矛盾等等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困扰世人的当今成了社会的核心现象。忧郁天使随处可见。在格拉斯的作品里也可以读出忧郁的“全属徒劳”四字。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如此!”的执拗。无论是作为对纳粹罪恶历史的“专业提醒者”,还是作为“以笔抗拒似水流年”的作家,他都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至少不是一个彻底的、完全放弃努力的悲观主义者。《蜗牛日记》里有一段堪称作家自画像的文字,其中说“试图将我定位是毫无意义的”,(80页)因为蜗牛原则就包含不确定性和非连贯性。他怀疑理想主义、唯一真理诉求等“玄思者的骗局”(194页),“害怕那些想劝我皈依的人”(87页),拒斥“绝对性以及类似的紧箍咒”(156页),反对不给个体留下任何空间的极权思维,憧憬某种或许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第三者。任何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不可能在“怀疑博士”或“忧郁天使”那里得到回响,但他笔下的这两个形象实际上并未排除一种积极的可能性:“蜗牛般地不离开路面,触角向着未来探索”(48页),在黑与白之间,在“狂热的天主教徒和虔诚的无神论者”(87页)之间,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在贝恩和萨特之间,在逃避政治和“倾向文学”,在忧郁的断念和乌托邦的狂热之间敏感而谨慎、缓慢而执著地探索。这种探索在格拉斯看来虽然希望渺茫却充满了人生乐趣,犹如加缪所言,“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16)
收稿日期:2006-11-06
注释:
①Guenter Grass:Aus dem Tagebuch einer Schnecke.Neuwied; Darmstadt:Luchterhand 1972,S.313。以下《蜗牛日记》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仅注明页码。
②Kurt Lothar Tank语,见H.L.Arnold(Hg.):Blech getrommelt.Guenter Grass in der Kritik.Goettingen:Steidl 1997,S.127.
③翟宗祝编著:《外国美术史》,安徽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④艾中兴等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180页。
⑤单杰宁:《卡夫卡〈在法律面前〉的“忧郁”思考》,汪榕培等主编:《忧郁的沉思》,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4页。
⑥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起。
⑦Klibansky,Raymond; Panofsky,Erwin:Saxl,Fritz:Saturn und Melancholie.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philosophie und Medizin,der Religion und der Kunst.Suhrkamp 1992.
⑧本雅明提到:“在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经典判断中,天才是在忧郁的概念中与疯癫联系在一起的。如在《问题》的第十三章中所解释的,忧郁综合症理论的影响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见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但根据德国迈耶尔大百科全书所载,这个问题更可能是出自继亚里士多德之后主持吕克昂学园的泰奥弗拉斯多。
⑨参见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⑩德国的“文学沙皇”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的自传《我的一生》中有这样的回忆:1958年“四七社”的聚会上,他讲述了德国占领时期自己在华沙的经历,后来格拉斯在《蜗牛日记》中让“怀疑”讲述了这段经历。后来格拉斯送了他一幅自己创作的版画,还在上面写了:献给我的朋友(“怀疑”)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11)V.Neuhaus:Schreiben gegen die verstreichende Zeit.dtv 1998,S.131.
(12)参见G.Grass:Kopfgeburt oder die Deutschen sterben aus.Luchterhand 1980,S.130以及Davor.In:Theaterspiele.Luchterhand 1970,S.406和Das Treffen in Telgte.Luchterhand 1979,S.7.
(13)参见S.Moser:Guenter Grass.Romane und Erzaehlungen.Berlin:Erich Schmidt 2000,S.98.
(14)Habermans,Juergen:Die Moderne-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Leipzig:Reclam 1992.
(15)Raddatz,Fritz J.:Guenter Grass.Unerbittliche Freunde.Ein Kritiker.Ein Autor.Zuerich,Hamburg:Arche 2002,S.35.
(16)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