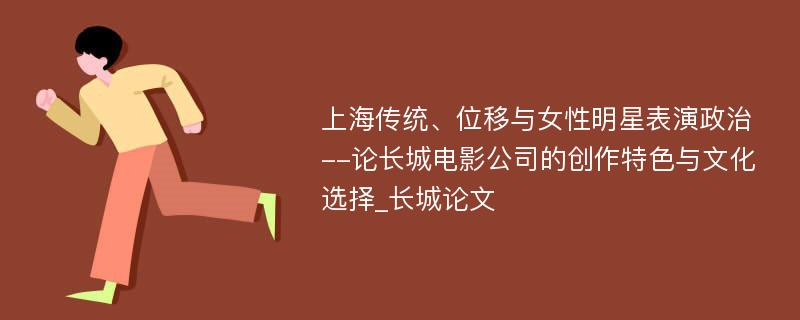
上海传统、流离心绪与女明星的表演政治——略论长城影业公司的创作特色与文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业论文,长城论文,心绪论文,女明星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旧长城”)是战后初期香港最重要的制片厂之一,从1949年7月正式成立到1950年初改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旧长城”共出品了8部影片①,在战后的香港国语电影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在关于战后初期香港国语片的讨论中,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改组后的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即“新长城”),而“旧长城”的历史脉络、创作特色、文化选择,及其在战后香港影坛的过渡性意义,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②
一、长城影业公司的成立及概况
“旧长城”成立于1949年7月,创办人是因与李祖永意见不合而退出“永华”的张善琨。成立之初,“旧长城”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此时恰逢袁仰安由沪来港,两人遂商定合作计划,并经袁仰安介绍,得到航运巨头吕建康的资金支持。“旧长城”由袁仰安担任总经理,但制片、策划仍由张善琨负责。③关于“旧长城”的资本和股权情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法认为“旧长城”系“张善琨与名律师袁仰安合股设立”④,袁仰安之婿沈鉴治的回忆从侧面验证了这一说法,他在回忆录中提及,1950年前后,袁仰安“带来的资金都在长城公司用掉了”。⑤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来自张善琨遗孀童月娟,她坚称“旧长城”是张善琨的独资公司,吕建康对“旧长城”的资金支持,并非直接注资或参股,而是以“胜利”公司的名义向“旧长城”提供每部影片10万港币的借贷。⑥1950年初,改组后的“新长城”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的一则启事验证了这一点,该文称“旧长城”为张善琨独资拥有,其出品影片“均系向‘胜利电影企业公司’借款摄制”⑦。至于“旧长城”的股权情况究竟如何,恐怕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凭借张善琨在电影界的广泛人脉,“旧长城”汇聚了一大批上海的“南来影人”,其中多数是张善琨在“华影”时期的班底,如导演李萍倩、岳枫、马徐维邦,演员周璇、白光、李丽华、王丹凤、龚秋霞、严俊、刘琼、黄河、韩非、王元龙等,技术人员则有摄影师董克毅,美术师万古蟾、万籁鸣等。“旧长城”的片厂位于九龙狮子山麓,厂长沈天荫。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长城片厂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是一家相当现代化的制片厂:“摄影部所用的机器是新近从美国购置来的1949年最新式的Mitchell B.N.C.。录音的设备、洗印的设备,都是现代化的崭新工具。”⑧
外部资金支持、现代化的片厂和大批创作人才的加盟,使“旧长城”成为战后香港最具竞争力的国语制片机构。在张善琨的主持下,“旧长城”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制片计划,创业作为《荡妇心》。根据“旧长城”官方提供的信息,《荡妇心》的筹备工作始于1948年11月,1949年3月中旬开拍,6月底完成,耗时101个工作日;原预算为30万港币,后因增加布景及服装、胶片等方面的额外支出,最终成本逾40万港币。⑨当时,香港国语片的制作成本约为10万—20万港币,在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旧长城”在影片制作上的投入可谓不惜工本、精益求精。
深谙电影经营之道的张善琨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为《荡妇心》的上映制造声势:影片公映前三天,在香港大酒店举行盛大的“创立纪念晚会”,邀请官员、金融界、工商界、新闻界人士及在港电影明星共计五百余人参加⑩;《荡妇心》的首映式更是制造了轰动效应,不仅邀请时任港督葛量洪出席,更动员了白光、胡蝶、李丽华、陈云裳、周璇、王丹凤、龚秋霞、陈娟娟、孙景璐、罗兰等十位女明星剪彩。(11)这一宣传策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荡妇心》一炮打响,“轰动了整个香港,整个广州、澳门、汕头等地亦万人空巷,打破卖座纪录”(12)。携《荡妇心》的余威,“旧长城”的第二部作品《血染海棠红》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东南亚大受欢迎,以至“场场满座,街头巷尾,男男女女,都以‘海棠红’为谈资”(13)。此后,“旧长城”一鼓作气推出《一代妖姬》、《琼楼恨》、《王氏四侠》、《花街》等影片。
总体而言,“旧长城”的制片策略有以下特点:承袭上海传统,制作商业电影,注重影片的娱乐性;影片的题材、类型多样化,既有“教化”色彩浓厚的通俗剧(《荡妇心》),也有感伤的文艺片(《琼楼恨》)以及侠义片(《王氏四侠》)、歌舞片(《彩虹曲》);力求以严谨的制作保证影片的品质——即便是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明星(尤其是白光、周璇等女明星)的票房号召力,赢得市场和观众;高度重视电影的宣传,采取各种手段对出品影片进行推广。
二、流离心绪的银幕呈现
在将上海的电影制作模式带到香港的同时,南来影人还在银幕上展现了自己的流离心绪,这也构成了战后初期香港国语片最为有趣的文化症候。在笔者看来,对银幕上男女性别的不同呈现,便是南来影人流离心绪的重要体现。接下来,笔者拟以《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影片的性别表达为例,并结合女明星白光银幕内外形象的塑造,力图呈现战后初期香港国语片微妙、驳杂的文化特色。
1.在银幕上表演“坏女人”:白光的银幕形象构建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电影运动”中,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经常采用的策略之一,便是借通俗剧的形式在银幕上塑造各种悲苦女性形象。创作者的家国忧思、社会关切,往往透过女性的悲惨遭遇得到曲折的呈现。1945年以后,南迁的上海影人将这一传统带到了香港。在岳枫、朱石麟等辈导演手中,女性的悲惨身世或际遇,成为创作者批判封建门第观念,谴责社会不公,肯定自由、平等的关键。就“旧长城”的作品而言,白光在《荡妇心》、《血染海棠红》及《一代妖姬》等片中饰演的角色无疑颇具代表性。
《荡妇心》以女性的悲惨遭遇作为叙事主线的策略,体现了战后香港国语片与上海传统的密切关联。白光饰演的女主角钱梅英是佃户之女,与地主少爷陈道生(严俊饰)相恋却被拆散,后为生活所迫堕入风尘,终因不堪生活的重负而自认杀人。影片开场,导演以接近“黑色电影”的手法表现女主人公遭受囚禁的情景:伴随着画外女中音深沉的歌声《为了什么》,镜头从监狱的铁栅栏拉开,缓缓摇过空旷的走廊;切至另一个监狱的空镜头,纵深的画面及强烈的明暗对比凸显出监狱空间的幽深和压抑;昏暗的监牢内,铁窗的阴影构成画面的主体部分,景深处狱卒的身影投射在墙上,缓慢横移的长镜头一一展示了囚室中的女犯人;镜头再次横摇,被牢牢锁在铁窗内的梅英出现在画面左侧,特写镜头呈现出她冷漠的表情;牢房内,绝望的梅英颓然倒下。这一场景足以令人想起《神女》(1934,吴永刚导演)结尾处,阮玲玉饰演的少妇因失手打死流氓而身陷囹圄的情景——两部影片的女主角都因环境所迫沦为妓女,都在社会的压迫下苦苦挣扎,最终难逃牢狱之灾。
有研究者指出,与其说《荡妇心》继承了原著《复活》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如说该片延续了上海电影的传统,是“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的余绪”(罗卡语)。梅英被男性抛弃,在狂风暴雨中产下私生子的情节,以及她所遭受的男性的残酷剥削,均突出了编导对女性议题的极大关切。事实上,这一策略被此后的国语片所沿用,并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电懋”等公司的创作中体现出来。有研究者对战后香港国语片的女性塑造进行症候式解读,并指出银幕上那些遭受迫害的悲苦女性,投射的是南来影人的自怜心理:“南来的影人自譬为通俗剧中的女性,一脚踏入财富、堕落及扭曲价值弥漫的社会,毫无抵抗力地成为受害者。”(14)
事实上,类似《荡妇心》中梅英沦为娼妓的情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中屡见不鲜,这再次显示了上海—香港电影双城之间的复杂联系。片中,梅英苦苦等待道生而无果,便独自带着孩子进入城市谋生。伴随画外梅英的独白,镜头在摇过一组叠化的城市景观之后,切至“醉春院”,创作者以一组简洁有力的镜头交待出女主人公堕入烟花柳巷的情景:梅英身着束身旗袍,留着波浪形的烫发,手持香烟,强作欢颜,周旋于各色男人之间。画外幽怨的插曲《叹十声》与以近景及特写镜头为主的画面相得益彰,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女主人公迷人的风情和性诱惑力。白光出色地把握住了梅英少女/妓女的双重个性,精彩地演绎了女主人公的多舛身世和悲惨遭遇,她的表演“洋洋洒洒如水银之倾泻,假便以她过去所主演的社会影片,来衡量这一次的成绩,那么她的飞速进步,已到惊人的程度了”(15)。
值得分析的是,即便梅英的遭遇可以归咎为社会的压迫和男性的不负责任,但她仍旧要为自己的“堕落”付出代价。影片结尾,在法庭审判的一场戏中,律师彦仁(韩非饰)的慷慨陈词令梅英无罪获释,但是她留下一封信独自离去,以赎罪的方式获得新生。更值得玩味的是,梅英在信中要求道生“等孩子懂事后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死了”。这一情节与《神女》的叙事策略如出一辙:“不名誉”的女性在文本中遭到彻底驱逐,由男权主导的社会秩序再次获得确认。
如果说《荡妇心》中的梅英还有清纯、善良的一面,那么《血染海棠红》中的“老九”(白光饰)则被编导加诸各种邪恶品质于一身,几乎成为不折不扣的“蛇蝎妇人”(femme fatale)。以“海棠红”(严俊饰)入狱为分界点,影片分为前后两部分,连接这两部分的,正是白光演唱的插曲《东山青》。在前半部分,“老九”因为不甘心从良后的清贫生活,与姘夫合伙诬陷丈夫“海棠红”。在过渡的部分,导演运用了一组具有强烈对比意味的镜头:镜头摇过被锁在牢房内的“海棠红”;画面渐隐后,切至“老九”在舞厅跳舞的场景,画外响起插曲《东山青》;画面叠化出海棠花、青山、溪水等自然风光;镜头一转,“老九”站在窗后,歌声也由甜蜜转为哀怨——她似乎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悔意;然而画外的歌声停止后,镜头切至室内,“老九”正在与“干爹”(王元龙饰)商量着开设一家妓院。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从来没有一首国语歌舞片中的歌曲是这样明显地独立于剧情以外的”(16)。音乐之超脱于叙事,及其与画面在表意上的错位,一方面凸显了“老九”的邪恶本性,另一方面又令观众为白光饰演的“坏女人”所倾倒。
影片《一代妖姬》改编自意大利歌剧《托斯卡》(Tosca)(17),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白光饰演的京剧名伶“筱香水”一方面延续了她在《荡妇心》及《血染海棠红》中放荡、妖冶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敢爱敢恨、直率干练的特质,她为了营救被逮捕的情人梁燕铭(黄河饰),不惜委身军阀,直至为情人复仇后殉情。影片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白光的明星地位,令她获得“银幕妖姬”的称号。
白光的一系列银幕形象,凸显了战后初期香港国语片对女性的定型化想象:女性角色若非纯洁少女/母亲,便是妓女/荡妇。尽管白光曾表示,希望饰演“善良的女人,像前辈林楚楚一样的贤妻良母的角色”,但是“我的外型,在导演们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人给我机会试一试”(18)。在《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片中,与白光饰演的荡妇、蛇蝎女人、戏子构成鲜明对比的,是龚秋霞饰演的贤妻良母形象。事实上,这种二分式的女性想象殊途同归,全都被用于确认和巩固父权在文本/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2.孱弱的男性与衰颓的父权
战后初期香港影坛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女明星压倒男明星,占据银幕的主导地位。在《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片中,与女性的干练、直爽、狠毒或顽强的生命力比起来,男性角色大都是孱弱、无能,或无力承担男性责任的。《荡妇心》中的陈道生是受到新思想影响的青年,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在梅英面前。然而他做出的承诺——学成归来之后带梅英离开却始终未能兑现。换言之,在文本中,道生是一个缺席者或延宕者,而非女性的拯救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的缺席导致了梅英的“堕落”。在《血染海棠红》中,父权的缺席体现得更加明显。“海棠红”的入狱,意味着他彻底放弃了父亲的责任。影片结尾的一幕相当煽情:“海棠红”越狱出逃,杀死“老九”,为女儿今后的生活扫清障碍,但他在女儿的婚礼上却不敢与女儿相认,唯有老泪纵横。《一代妖姬》中,女性的果敢、机智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同样令男性相形见绌。新、旧“长城”交替之际出品的《花街》,亦是南来影人在银幕上展现流离心绪的作品,男主人公小葫芦(严俊饰)是相声艺人,曾在抗战爆发后逃往大后方,后历经磨难返回花街。在一次为侵略者表演时,他痛斥日军的暴行,随即招致流氓的毒打,但他绝不求饶,妻女则在一旁向日军苦苦哀求。在是非颠倒的乱世,父权代表的正义、坚贞虽遭挫折,却苦苦支撑,绝不向恶势力低头。影片结尾处全家人许愿的场景,则被批评者解读为南来影人试图在香港重建“父亲们的电影”的努力(19)。
笔者认为,战后初期香港影坛上男女形象的巨大反差无疑是极富症候性的,女性的妖冶、放荡和性诱惑力构成了对父权社会的极大威胁,她们在文本中必须受到惩罚(囚禁或放逐)——即便责任不在她们身上;男性尽管羸弱、无能,依然牢牢占据着社会/文本的主导权——一如《荡妇心》中遭受良心谴责的道生坐在审判席上,而占据道德优势的梅英却沦为阶下囚,等待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说,《荡妇心》等影片其实是在文本层面对遭受贬损的父权进行象征性修复的尝试。如果从战后香港影坛独特的文化语境看,两性在银幕上的不同呈现,折射的是父权社会的集体焦虑,亦可视作“南来影人”自怨自艾的流离心绪的投射。
3.历史转折中的女明星:银幕外的白光
如前所述,争取大牌明星是“旧长城”的重要制片策略之一。在张善琨招揽的明星当中,白光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白光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以饰演热情、直率甚或放荡的女性形象而为观众所熟知,与她的明星之路相伴相生的,则是影迷杂志及各类小报有关她的私生活的报道。(20)1949年3月,白光受张善琨之邀赴港,接连主演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多部作品,迅速在战后香港影坛尚不成熟的明星系统中奠定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她标志性的紧身旗袍、波浪形烫发、永不离手的香烟、慵懒的表情、深沉的女中音歌喉,或者一颦一笑间传递出的无限风情,犹如一道耀眼的白光划过香港影坛。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白光四五十年代之交在银幕之外的选择同样值得玩味。1949年3月赴港时,白光曾被媒体指为“逃难”,但白光否认“逃难”说:“纠正人家说我‘逃难’,我怎么也不逃避,新国家,新潮流,新时代,一切新的东西,我都接受!”(21)在《荡妇心》等片中,白光的精彩演出无疑投射了反封建、揭露社会不公、批判性别压迫等相当进步的意识。于是,白光似乎在无意间以自己的银幕上的形象参与到银幕之外关于意识形态的论争之中。1950年,在“旧长城”面临改组的关头,电影明星和其他影人一样,必须做出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外乎三种选择:一是留在改组后的“新长城”,成为左派影人(如龚秋霞、陈娟娟);二是追随张善琨退出“长城”,转向右派阵营(如黄河);三是暂时留在“新长城”,静观其变(如严俊)。白光选择了第二种,她退出“长城”后,继续追随张善琨,为“远东”主演了《雨夜歌声》(1950,李英导演)、《结婚廿四小时》(1950,屠光启导演)等影片。值得注意的是,此间有媒体报道,经张善琨引介,白光与倾向左派的“龙马”签订合约,“每片酬劳为港币三万五千元云”(22),但后来又有消息称,白光与“龙马”解约,转而为“远东”出演《新西厢记》(1951,屠光启导演)。(23)从这个细节不难推测,即便在退出“长城”后,张善琨与左派公司之间也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有往来。1951年,白光赴日本拍摄“新东宝”的《恋之兰灯》,在日本逗留期间,她依旧是香港各大制片公司追逐的对象。有报道称,“永华”正在急切盼白光返港拍片(24),而“邵氏”也在寻求与她合作(25)。随着1953年初“香港自由影人协会”的成立,香港影坛左右对立的局面公开化,白光彻底转向右派阵营。1954年5月,“自由影人协会”第二次组团赴台“观光”,在规模庞大的团员中,白光赫然在列。(26)1956年,白光在“电懋”支持下成立了国光影业公司,并出品了《鲜牡丹》(1956,白光、罗臻导演)、《接财神》(1959)等影片。不久,白光便退出影坛,但她独一无二的“银幕妖姬”形象已然深深镌刻在战后香港影坛及观众心中。
三、左、右夹缝中的文化选择
张善琨一向被视为亲国民党的右派影人,他主导的“旧长城”自然被归入右派公司,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香港影坛,左、右两派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和互动,远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划分所能概括。以今日的观点看,“旧长城”出品的不少影片都颇有进步意识,例如《荡妇心》批判封建门第观念对自由恋爱的阻挠,同情女性遭受的压迫;《一代妖姬》展示革命党人不畏强暴,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正如该片编剧姚克所说,影片批判了反动统治者“不知道革命的原动力是从压迫下产生的;压力益大,革命的力量更大,压迫非但不能消灭革命,反能主张革命的声势”(27);即便是被包装成侠义片的《王氏四侠》,表现的仍是农民奋起反抗豪绅恶霸剥削的故事。事实上,“旧长城”的政治——文化选择并非个案,另一家右派公司——亚洲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同样为此时期香港影坛的复杂性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脚。依罗卡的观察,“亚洲”出品的《长巷》(1956,卜万苍导演)“只要再深入发挥一下,已是出‘进步电影’”,而《半下流社会》(1955,屠光启导演)“乍看之下,与‘左倾’影片并无二致”(28)。
在“旧长城”与左派电影公司的互动中,《小二黑结婚》(1950,顾而已导演)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小二黑结婚》由左派的大光明影业公司摄制,影片改编自赵树理的同名小说,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表现的是“破坏迷信,打倒恶霸,争取婚姻自由,加强努力生产”等内容。在片中饰演小二黑的演员顾也鲁回忆道:“那时长城影片公司的经理看到我们旺盛的创作精力,同时《小二黑结婚》题材新颖……因此愿意拿出一半的拍摄资金,由我们全权制片,将来影片发行时,国外归‘长城’,国内归‘大光明’”(29)。需要说明的是,顾也鲁所说的“长城影片公司”,应当是“旧长城”,而非改组后的“新长城”。1949年9-10月间,张善琨在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台采访时透露了公司下一步的制片计划,其中就有《小二黑结婚》(30),而上文提到过的刊登在1950年初《大公报》上的启事,也证实了该片确是张善琨主导时期的产物。(31)在合作形式上,“旧长城”除了提供资金、负责海外发行之外,还同意向“大光明”外借自己旗下的陈娟娟、孙景璐等演员。一向被指具有反共倾向的张善琨,为何在其主理“旧长城”期间参与《小二黑结婚》的投资?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可能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即拓展内地市场,也可能是受到公司内部左派影人影响的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旧长城”在改组之前,便与左派电影公司有着相当密切的往来,甚至有报道称,两家公司虽然“形式上是各有系统,实质上是完全一致”(32)。这也充分表明,在1949年前后的香港电影界,左与右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微妙的互动。正如罗卡所指出的那样,彼时“‘左倾’似乎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对中国的新生抱有理想或纯为经济利益着想,都得如此”(33)。
除了与左派公司业务上的往来,张善琨也因其在香港影坛的影响力而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据童月娟回忆,1949年下半年,“共产党方面就派来上海电影界的夏衍等几位旧相识,前前后后,好几次来游说我们回内地去担任政协委员”(34)。此时的张善琨或许已经在左与右之间做出选择,他拒绝向左转。
进入20世纪50年代,政治局势的变化为香港国语电影的前景蒙上一层不可预知的阴影:朝鲜战争的爆发,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禁运”,胶片等物资的匮乏令香港电影界处于动荡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香港电影在内地发行放映的控制,令香港电影逐渐丧失最重要的市场;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于1951年颁布法令,禁止左派影人参与制作的影片在台湾发行放映。左派势力的壮大及左派影人的“读书会”等政治活动令“永华”等右派公司感到不安,而亲国民党的右派阵营也在不甘示弱,以各种方式对抗中共的统战,香港影坛左、右两派的对抗和角力日益凸显。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内外交困的“旧长城”迎来了转折点:1950年初,长城影业公司改组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由吕建康注入资金并担任董事长,一同加入的还有《大公报》的费彝民等,“旧长城”的创办者张善琨则黯然退出。于是,改组后的“新长城”发展成为香港最主要的左派电影公司。从表面上看,“旧长城”的改组的直接原因是资金短缺及债务问题。在张善琨的主导下,“旧长城”高成本的制片策略,令创建之初便存在的资金短缺的问题显得更加迫切。1950年初,《琼楼恨》公映后卖座不佳,“营业大不如前,经济周转顿告困难”(35)。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在公司的市场策略上,张善琨和袁仰安产生了分歧:前者主张争取台湾市场,而后者则力主发展内地市场。退出“长城”后,张善琨先是以“远东”的名义出品了多部影片,后于1952年恢复“新华”,并大力寻求与台湾当局的合作,成为右派影人的代表,但这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上海影人南迁的大背景中,“旧长城”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它继承上海电影的传统,尤其是利用通俗剧的形式及对悲苦女性的塑造,集中展现了南来影人的家国想象和流离心绪。在复杂、微妙的政治一文化环境中,“旧长城”小心游于左、右之间,制作了不少表达进步思想意识的影片,为日后“新长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也凸显了其在左、右之争日益加剧背景下的过渡性意义。“旧长城”的崛起和终结,是多种政治—文化力量角力、渗透、影响的结果,其短暂的历程亦是战后初期香港影坛复杂格局的最好见证。
注释:
①这8部影片分别是:《荡妇心》(1949,岳枫导演)、《血染海棠红》(1949,岳枫导演)、《琼楼恨》(1949,马徐维邦导演)、《一代妖姬》(1950,李萍倩导演)、《彩虹曲》(1950,岳枫导演,影片公映时间为1953)、《王氏四侠》(1950,王元龙导演)、《花街》(1950,岳枫导演)、《豪门孽债》(1950,刘琼导演)等。此外,“旧长城”还参与了“大光明”摄制的《小二黑结婚》的投资,并拥有该片在东南亚等地的发行权。
②关于“新长城”的代表性研究,可参见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及银都机构编著:《银都六十(1950-2010)》(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中的相关章节;关于“旧长城”的历史及文化特色,可见钟宝贤:《政治夹缝中的电影业——张善琨与永华、长城及新华》,载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年,及傅葆石:《回眸“花街”:上海“流亡影人”与战后香港电影》,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③《南来香港》(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一),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0年,第32—34页。
④《张善琨退出“长城”》,载《青青电影》,1950年第5期,第5页。
⑤沈鉴治:《旧影话》,载黄爱玲编《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二),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年,第40页。
⑥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年,第91页。
⑦转引自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三):四十年代》,香港:次文化堂出版,1998年,第207—208页。
⑧《香港长城影业公司——中国电影业的新军》,载《光艺电影画报》第16期(1949年8月),无页码。
⑨《〈荡妇心〉小统计》,载《电影圈》,第148期(1949年8月),第2页。
⑩《长城万花筒》,载《光艺电影画报》,第16期(1949年8月),无页码。
(11)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年,第92页。
(12)《长城万花筒》,载《光艺电影画报》,第16期(1949年8月),无页码。
(13)《〈血染海棠红〉彩色画》,载《电影圈,》第150期(1949年10月),第5页。
(14)焦雄屏:《故国北望——一九四九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载其所著《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18页。
(15)黎洱:《荡妇白光的风情画》,载《电影圈》,第149期(1949年9月),第5页。
(16)何思颖:《歌女,村女与曼波女郎》,载香港市政局主办:《国语片与时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1993年,第52页。
(17)另有材料证明,《一代妖姬》改编自20世纪40年代“上海演出之舞台名剧《金小玉》”,详见《白光戏中再串戏》,《青青电影》,1950年第1期,第25页。
(18)黎洱:《荡妇白光的风情画》,载《电影圈》,第149期(1949年9月),第5页。
(19)吴昊:《乱世电影:一九四六——五零年上海南迁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心绪》,载香港市政治局主办:《上海一香港:电影双城》,1994年,第29页。
(20)关于白光早年的成长及生活经历,可参见白光:《白光自传》,香港:鹿鸣书屋,1952年。
(21)文霞:《白光的二个弟弟,一个是解放区,一个在学习中》,载《青青电影》,1950年第6期,第14页。
(22)《白光加入龙马》,载《青青电影》1950年第20期,第5页。
(23)思楼:《白光最近二三事》,载《电影圈》,第168期(1951年4月),第9页。
(24)马美:《白光在日本》,载《电影圈》,第178期(1952年2月),第16页。
(25)《影人影事·张善琨赴日考察》,载《光艺电影画报》,第55期(1952年11月),无页码。
(26)沙荣峰:《沙荣峰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6年,第72页。
(27)姚克:《向历史学习——为〈一代妖姬〉公映而作》,载《光艺电影画报》,第22期(1950年2月),无页码。
(28)罗卡:《传统阴影下的左右分家——对“永华”、“亚洲”的一些观察及其他》,载香港市政局主办:《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年,第13—14页。
(29)顾也鲁:《艺海沧桑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93页。
(30)《张善琨谈中国电影》,载《电影圈》,第150期(1949年10月),第3页。
(31)转引自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三):四十年代》,香港:次文化堂出版,1998年,第207—208页。
(32)萧梁:《小二黑结婚》,载《电影圈》,第154期(1950年2月),第17页。
(33)罗卡:《后记:回顾、反思、怀疑》,载香港市政治局主办:《上海—香港:电影双城》,1994年,第101页。
(34)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年,第93页。
(35)《张善琨退出“长城”》,载《青青电影》,1950年第5期,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