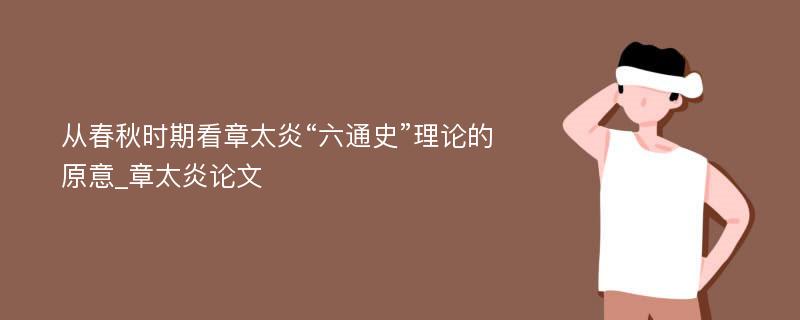
從《春秋》學看章太炎“六經皆史”說的本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本意论文,春秋论文,六經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章太炎于1891年“始分別今古”,標榜“古文經學”與康有爲“今文經學”相抗衡。一開始,他還援引今文經說,相信“孔子改制”和“微言大義”,直到1904年《訄書》重訂本的出版,纔標誌著他真正肅清康氏“今文經學”的影響,確立起“六經皆史”的古學宗旨。① 在重訂本《訄書》的《清儒》篇中,章太炎鮮明反對通經致用、道在六經的“經學”觀念,指出“搏國不在敦古”,想通過六經找到萬世不易之“道”,純屬誇誣之談。他說,所謂“六藝”其本來面目是兼領“天官”的上古史官記録並典藏的“官書”。而研究六經的正確方法應該是“夷六藝爲古史”,從中知“上世社會汙隆之迹”。②
經學消亡,其所述歷史“神話”被否定,經學作爲史料寄身于史學門下。按照中國學術“古今之變”的這一大綫索來看,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說,繼承章學誠、龔自珍而更上一層,對于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轉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義。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後世學者基本上按照這一綫索,將章太炎以“六經皆史”爲要義的“古文經學”進行一分爲二的評說:一方面積極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經見道、通經致用的經學思維,折經入史,將“六經”歷史文獻化,用研究歷史文獻的方法來解經,使儒家六經從神聖寶典下降到了古史資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評其“六經皆史”之說,終未能脫離儒家經學的羈絆,仍爲尊經崇聖的觀念所困,章太炎到底也還是一個“古文經學家”。③ 那些身爲新文化運動疑古思潮之領袖的學人,更是對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說深致不滿,認爲其說不能認清“六經”的真相,不能開闢科學探索中國古史的道路。錢玄同曾說,所謂“六經皆史”這句話是講不通的,即使把“六經”當作史書,其價值也遠在《史記》、《新唐書》之下。④ 另一位太炎弟子朱希祖也說,“六經皆史”很不確當,應該說“六經皆史材”纔對。他認爲先師之意也是要講“六經皆史材”的,只是不願明斥先賢纔没有明言。⑤ 顧頡剛更是批評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說充滿强烈的信古之情,而章太炎本人只是“一個從經師改裝的學者”。⑥
這樣一種對章太炎“六經皆史”說的二分法,其實是把章太炎擺進新文化運動的“先賢祠”中,將其學術思想割裂開來,能爲時代先驅者,則受到尊崇,與潮流對反之論,則目爲落後保守,不暇一哂。這種二分法,往往使我們忽略章太炎“古文經學”形成發展的內在軌迹與自身邏輯,難以平心瞭解其本有的思想意圖,過濾掉其中既不太“現代”又不怎麽“傳統”的思想內容,也難以從中窺見獨特的個性和時代訊息。進一步地說,章太炎的“國學”是中國學術、思想現代轉型中的一個重要形態和階段,他號稱復興“古學”,但其實是對“傳統”的激進改造和重構。對于章太炎的“國學”思想,若僅僅把它當做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事業的先聲和資源,而以“傳統/現代”的二分法框架之,那將是對章太炎的極度簡化。
章太炎的《春秋》、《左傳》學是其“古文經學”的主幹,充分、集中地表達了章氏“六經皆史”說的思想意圖和涵義。如錢玄同所提示,章太炎從早年的《春秋左傳讀》到後來的《春秋左傳叙録》、《劉子政左氏說》,再到晚年的《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其經說“前後見解大异”。⑦ 也就是說,随著章太炎的思想變化和時代變遷,其《春秋》學一直在發生變化,直到1930年代纔形成定論。可見,其《春秋》學也最能表現其“古文經學”形成發展的內在自身的思想軌迹。關于章太炎的《春秋》、《左傳》學,學界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⑧,本文側重的是,追迹章氏《春秋》學的變化發展,並試圖以《春秋》學爲中心,考察其“六經皆史”說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審視的思想內涵。
一、《春秋》“義經而體史”
章太炎于1896年寫成的《春秋左傳讀》,代表了其《春秋》學也是其“古文經學”的第一個階段。
1891年,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問世。爲了證明以《公羊傳》爲主的今文經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康有爲繼承劉逢禄的觀點,力辨《左傳》是劉歆割裂《國語》,依《春秋》以編年而成的“僞作”,其中的“君子曰”、書法凡例皆是劉歆所僞造,劉歆甚至還遍僞群經、竄亂《史記》、假造傳承譜系以實其僞。就在同一年,章太炎“始分別今古”⑨,至1896年,寫成了《春秋左傳讀》,其書雖未曾刊行,卻充分表明章太炎以《春秋》、《左傳》學作爲攻擊“今文經學”、確立“古文經學”的主要學術陣地。⑩
這時,他對《史記孔子世家》所說孔子“因史記作《春秋》”的理解是:孔子創作《春秋》以“立素王之法”。(11) 在1899年發表的《今古文辨義》中,他說:《詩》、《書》、《禮》、《易》多“前聖之成書”,而《春秋》“自爲孔子筆削所成,其旨與先聖不同”。(12) 關于《左傳》的作者左丘明,他采用《漢書·藝文志》、杜預《春秋左傳集解》以左丘明爲史官的說法,還進一步考證說,左丘明爲魯國左史即大史,他以左爲官、以丘爲氏、以明爲名。(13) 他相信孔穎達所引《嚴氏春秋》的說法:左丘明與孔子一起到“周室”觀史,“歸作經傳,共相表裏”。(14)
《春秋左傳讀》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進行文字訓詁;一是搜集戰國至漢初“左氏先師”曾(申)、吳(起)、鐸(椒)、虞(卿)、荀(卿)、賈(誼)、三張(張蒼、張敞、張禹)的有關言論和劉向、歆、賈(逵)、服(虔)舊注,以解釋《左傳》義例和微言。(15) 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章太炎力圖以《左傳》會通于康有爲所云《公羊》大義,論說《左傳》同樣主張“改制革命”、“黜周王魯”、“大一統”、“通三統”乃至“大同”、“遜讓”之微旨。這表明,其時他的“古文經學”基本籠罩在康有爲“今文經學”的陰影之下。(16) 故而,他始終未將《春秋左傳讀》正式刊行。(17)
在1907-1908年,章太炎于《國粹學報》前後刊完《春秋左傳讀叙録》和《劉子政左氏說》,這代表了他《春秋》、《左傳》學的第二階段,也表徵著其“古文經學”的進展。這時,他已于重訂本《訄書》(1902年删革,1904年于日本刊行)中確立了“六經皆史”的古學宗旨,以孔子爲古“良史”,又初步構擬出孔子-左氏-太史公-劉歆的史學譜系。(18) 此後,章太炎反復申說孔子之述作“六經”乃是“存古”之學,其大用在于啓發和維護國人的種族、文化自覺。(19)
但是,在這兩部書中,章太炎對《春秋》的定義是“義經而體史”。(20) 他繼續申說,孔子對于《詩》、《書》、《禮》、《樂》、《易》“但有校訂編次之勞”,而《春秋》則是孔子“自作”,异于“古書”。左丘明既是史官又是孔子弟子,與孔子“偕觀史記,助成一經,造膝密談,自知其義”。(21) 也就是說,只有《左傳》纔真傳了孔子作《春秋》之大義。《春秋左傳讀叙録》原名《〈後證〉砭》,寫于1902年,專門反駁劉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證》卷二《後證》,其中,劉氏論證說《左傳》本非《春秋》之傳,其條例、說經之語、授受系統皆劉歆僞造。同時,章太炎還針對劉逢禄的《箴膏肓評》寫了《駁箴膏肓評》,申明鄭玄對何休的駁斥及其爲《左傳》所作辯解,力争《左傳》書法義例非劉歆僞竄,合于《春秋》本意,合于“禮”。但《駁箴膏肓評》從未刊行,今存手稿。(22)《劉子政左氏說》,主要是就《說苑》、《新序》、《列女傳》中所舉《左氏》事義六七十條,考證古文《左傳》不同于今本的文字、訓詁,尤其是其中的“大義”。在這時,他雖然已不講《公羊》學“黜周王魯”、“革命”、“大同”之說,但還是不能真正擺脫“今文經學”的影響,他仍然相信,孔子在《春秋》中寄托了一套垂訓萬世的“文外微言”,包含在《左傳》的書法義例之中。(23) 他要證明的是,《左傳》中的書法義例能“見之于行事”,深切著明,得孔子真意,遠比《公羊》高明。
章太炎于《駁箴膏肓評·叙》中,駁斥劉逢禄的《左傳》文字甚工而無說經之語的論調,乃是“見淺不見深”。《左傳》中有一條“弑君而稱國稱人,則罪在君”的“經說”,遭到許多清代經學家的責難,而章太炎卻表彰說,此處正是《左傳》的高明深刻處,太史公所謂“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指的正是這一大義,“非知此義,不能治《春秋》”。(24)
據章太炎考證,《左傳》傳世後百餘年,到戰國時代纔有了《穀梁傳》,而《公羊傳》則起于秦末,“若夫公羊所說,或剽竊左氏,而失其真”。(25)《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有這樣一條經文:“冬,仲孫何忌會晋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按照《左傳》的記載,其時,晋國接受周天子的請求,派魏舒、韓不信會合諸侯的大夫,進行增築成周城墙的工程。《左傳》藉當時賢士之言,評論主持其事的晋國大夫魏舒“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26) 又評論主張其事的周朝大夫萇弘“萇叔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27) 章太炎認爲,在這裏,《左傳》要說的《春秋》“大義”是:
大命已去,則支壞無所用;王德未備,則天位不可干。斟酌損益,于是具矣。(28)
也就是說,周朝的衰亡已經不可避免,但在這種情勢下急于篡位,那是亂臣賊子之所爲,而只能以“尊王”的名義盡力使天下維持一定的秩序。這正是孔子《春秋》進行褒貶的基本原則。章太炎說,劉向《說苑·修文》篇闡發的就是這一“大義”。而《公羊傳》于“宣公十六年夏”所說的“新周”之義,即孔子以《春秋》當新王而把周朝當作已經被取代的王(29),其實就是來源于春秋晚期的這一“時論”,而“獎藉篡夫,過爲側詭”,不如《左傳》義遠甚。(30) 另外,章太炎還指出,《穀梁傳》于“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條說,孔父之“父”乃其謐號,孔子不稱其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公羊傳》誤解了《穀梁傳》所謂“故宋”的意思,就發明出“新周”與之對偶。(31) 總之,《公羊傳》所說“黜周王魯”之義其實是風聞《左傳》史事又誤讀《穀梁》之文而恣意妄說。
又如,《春秋經》:“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嘗。”《左傳》解釋其書法曰:“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嘗。書,不害也。”就是說,君主的糧倉遭到火灾,但還繼續舉行嘗祭,並不懼怕這次火灾而以之爲害。而《公羊傳》卻說,《春秋》的書法是譏刺在“御廪”失火之後還照常舉行嘗祭。章太炎評論道,《公羊傳》所說書法大義是“老生常談”,而《左傳》所說書法大義則很“閎深”。他認爲,劉向《說苑·反質》篇關于“魏文侯御廪灾”一則,說的正是《左傳》的書法大義:魏文侯“御廪”受灾,公子成父不吊反賀,他說:“天子藏于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匣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灾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灾,不亦善乎?”“御廪”之灾正是要警戒君主不可大肆聚斂,使之避免更可怕的人禍。章太炎說,戰國初年,《左傳》學主要流傳于魏國,所以,公子成父的諫言是本于《左傳》書法大義的。(32)
此時,他也仍然相信孔子“改制”之說,認爲《左傳》中蕴含著一套“《春秋》家”所自定之“禮”。如,《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晅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解釋其書法大義是:“贈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章太炎認爲,劉向在《說苑·修文》篇中首先引用上述《左傳》之說,接著又根據《公羊傳》和《荀子·大略》篇解釋有關饋贈“賵”和“賻”以助喪的禮制,這說明劉向所說的“禮制”是此三家解釋《春秋》制禮的通義,即天子之“賵”,乘馬六匹,名爲“乘輿”;諸侯之“賵”,乘馬四匹,名爲“乘車”;大夫之“賵”,乘馬三匹,名爲“參輿”;元士、下士之“賵”則不用車輿。接著,章太炎試圖解釋今文經和古文經關于天子之“賵”的禮制爲什麽會出現不同說法的問題。他認爲,按照“宗周舊制”,卿大夫以上所乘車輿皆名爲“大路”,並没有在名稱上分出尊卑等級,這與古文經《毛詩》所說“天子至卿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是相符合的。而真正傳承《春秋》大義的《左傳》不但要記載“宗周舊制”,更是要“損益四代”制定出理想化的禮制,所以,天子之“賵”爲“乘輿”,諸侯之“賵”爲“乘車”的禮制,“非周所有,亦非起于秦漢,乃《春秋》家所定爾”。《左傳》先師賈誼曾說過:“天子之車則曰‘乘輿’,諸侯‘乘輿’則爲僭妄”,章太炎認爲賈誼此說根據的就是《左傳》義例。今文經的孟京《易》說和《公羊傳》有關天子之“賵”的禮制也持同樣的說法。總之,古文經所述“禮制”乃是“宗周舊制”,而今文經所述“禮制”確乎是“《春秋》改制”。只是《公羊傳》只知道“《春秋》改制”,卻不懂得歷史,“不識周時舊章”。而《左傳》則一方面忠實地記録了歷史事實,所謂“事從其舊”,如《左傳》“襄公十九年”記載:“鄭公孫躉卒,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忠實記録了卿大夫以上所乘車輿都叫“大路”的“宗周舊制”;但另一方面,《左傳》又“法從其新”,據以褒貶的“禮制”乃是孔子的“一王大法”,兩方面結合纔是“史官之能事”。(33) 這應該就是章太炎所說“《春秋》義經而體史”的意思。
再如,《春秋》:“隱三年春三月庚戌,天王崩。”劉向在《說苑·修文》篇中首先引用《公羊傳》所說書法大義:“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然後用《左傳》之說又加以解說:“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章太炎認爲,劉向和會《公羊》、《左氏》之說,證明二家關于天子、諸侯殯葬禮制的說法是相通的。章太炎說,《公羊傳》所謂“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意思是,在有朝覲之事或死于外國的情况下,允許諸侯歸葬過期。然而,《白虎通》卻將之解釋爲諸侯即使喪父,一旦聞天子崩,就得放下父親的喪事,趕繁奔天子之喪,並說這是“親親猶尊尊之義”。章太炎指責《白虎通》歪曲了《公羊》“正說”,乃是“佞臣媚子文奸之說”。《公羊》“正說”,應如鄭玄所申、《喪服·四制》所述,必先葬父然後葬君,所謂“資于事父以事君,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接著,章太炎引據《左傳》先師荀子在《禮論》篇中所說:“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認爲這表明《左傳》也同樣主張“諸侯非在斬衰,則無不奔赴王喪”,其“禮”其“義”皆同于《公羊》。爲此,章太炎在《左傳》中找出幾條記載和書法,曲爲之說。(34) 從以上所舉例子可以看出,章太炎爲了證明《春秋》、《左傳》“義經而體史”,《左傳》有一套意旨深微的書法義例,也是極盡牽强附會之能事的。
]904年問世的重訂本《訄書》也還在講《春秋》制禮之說,並對所謂《春秋》“大一統”、“通三統”義有著一番自己的解釋。重訂本《訄書·官統上》說,夏、商信奉“五行”之教,出于《洛書》,所以夏、商的官制之數都以十進位;而周信奉“八卦”之教,出于《河圖》,所以其官制之數以三進位,即《周禮》所謂“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等共爲“三百六十官”。《周禮》是文王、武王、周公父子積思之作,體現了“不尚司天屬神之職,設官在于民事”的精神。在章太炎看來,《荀子·正名》篇所謂“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說的是《春秋》參酌夏、商、周三代而制定一套新的禮制。(35) 按照荀子的說法,孔子《春秋》所定“禮制”,其官制爵名以富有人文理性的《周禮》爲標準。而今文經的《禮記·王制》、《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國》篇也都主張三進位的官制。我們可以看出,章太炎還是相信孔子《春秋》有“通三統”之義,並側重于孔子參酌夏、商、周三代而制禮的核心觀點。章太炎還說,周得天下之後,排斥殷商“眩于神運”的“五行”教,用更具人文理性的“易”教統一天下之志,造就是所謂的“大一統”之義:“是故言‘元年’者,以‘王’爲文王,而摒萁子于海外營部之域,使去亂統。”(36) 章太炎還是認爲“元年春王正月”的書法有著“大一統”的含義,但對之做出了自己的解釋。
二、“孔子誠不制禮”
此後,章太炎關于《春秋》、《左傳》的觀點一直在發生著變化,1910年刊行的《國故論衡·原經》和1914年刊行的《檢論·春秋故言》集中表述了他在1913年前後即“回真向俗”之變時期的《春秋》學新義。
在這時,關于“孔子作《春秋》”,他更傾向于將“作”解釋爲“修”,强調《春秋》以《魯史記》爲本,並藉助了魯國大史左丘明。(37) 還考證說,孔子的“筆削”,有邱明之佐書;而《左傳》的記事和褒貶“皆造膝受意”,所以說《左傳》同時也是仲尼之手筆。(38) 這一說法當然不能證實,但章太炎想要說明的是,《春秋》與《左傳》合成一部史書,二者“丸揉不分”。後人研讀《春秋》應重在“實事”而非“義法”。
他認爲《左傳》中的“五十凡”其實是西周末期史官編年記事之法式而爲孔子所襲取。他考證說,孟子所說“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說明了中國最早的編年國史產生于西周末年,就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記“共和元年”前後,而前此的史書或記大事,或録誓命,如同《尚書》,還不能以事係年——章太炎關于中國史學起源的看法,得到後人廣泛承認。故而,他認爲,所謂《春秋》“經世”,其原意指的不過是紀年而已。那麽,“五十凡”應出自周宣王時的史官之手,而非杜預所說由周公創制。章太炎認爲,列國的史官都是周王朝派下去的,屬于“王官”而非諸侯之臣。春秋時代齊大史董狐和南史氏的奮筆直書,其實是不屈從于諸侯權勢而行使王官之權職。孟子所說“《春秋》,天子之事也”,其本意正在于此,而不是說孔子作《春秋》“立一王大法”。孔子作爲魯國故臣,依大史邱明而修《春秋》,私自使用職掌于史官的修史義例,既有“盗取”又有“侵官”之嫌疑,所以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晋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說:“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9) 如此說來,後人根據孟子這些話認爲孔子創制《春秋》書法義例而寓“素王改制”之微言,完全是個誤解。
章太炎已明確指出,《春秋》不是“制法”之書,不爲後世制法更不爲漢制法。漢朝典章制度因襲秦朝,爲漢制法的是李斯而非孔子,今文學家編造“爲漢立法”是爲了獵取富貴。再說國家法度随歷史而變化,“雖聖人安能豫制之?”晚近今文學家所說孔子爲百世制法,就更不可信了。《春秋》雖記載了治亂盛衰的往事,但其論政,上不如老子、韓非,下猶不及仲長統(40),其經世濟民的大用恰恰在于它是中國最早的編年史書,並創造了中國史學的偉大傳統:
夫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令遷、固得持續其迹,訖于今玆,則耳孫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後民無携志,國有與立,實仲尼、邱明之賜……籍今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國長久,文教浸淫,而故記不傳,無以褒大前哲,然後發憤于寶書,哀思于國命。(41)
他又在《檢論·春秋故言》中指出,《春秋》主要記載五霸事迹,說明孔子具有自覺的民族主義思想:
綜觀《春秋》,樂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姓。雖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故曰“竊比于我老彭”……今以立言不朽,爲中國存種姓,遠殊類,自謂有伯主功,非曰素王也。(42)
章太炎原本相信廖平所說,漢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別主要在于所主禮制的不同,今文經學以《禮記·王制》爲宗主,是孔子“改制”,而古文經學則以《周禮》爲宗主。同時,他又受到“素王改制”的今文家言的牽制,所以,他原以爲,古文經所主禮制乃是“宗周舊制”,而《左傳》記事則從“宗周舊制”,褒貶則從“《春秋》改制”,所以其所言禮制往往不同于《周禮》。而今文經所主“禮制”,其中很大部份確實是孔子“損益四代”的制作。而在《國故論衡·原經》篇中,他完全打破前說,認爲自西周晚期以來,綱紀大亂,典章禮制一直在發生不斷的變化。《左傳》所述禮制是“春秋時制”,所以不合于“成周之典”的《周禮》,但也絕非孔子創制。他在《劉子政左氏說》中曾以爲,天子的車輿乘馬六匹,名爲“乘輿”,這是孔子“損益四代”而自定的禮制,《左傳》正是據此以爲褒貶。這時他卻說,“天子駕六”的禮制,蓋起于春秋之末,是“時王之制”,並非孔子所定。他强調指出“孔子誠不制禮”,《禮記·王制》絕非孔子“制禮”,乃是戰國以後“禮家”的附會之作。(43) 他在同書《明解故下》篇中也論述說,《周禮》是成周之制,而《左氏內外傳》所記述乃周穆王以下發生了“浸移”的典法禮制。今文家不知“周禮”自西周中後期以來屢經變遷,誤把時王新制當作“《春秋》改制”。而且,他進一步打破了廖平以禮制平分今古的說法,正確認識到,在漢代無論今文家還是古文家其內部都有很多“自爲參錯”的流別,出于今文家之後的古文家,往往采用今文經說加以比附,如賈逵等解《左傳》,就說《左傳》同于《公羊》者十有七八;而今文經說又往往有與《周禮》、《左傳》相應者。(44) 章太炎更認識到,漢代古文家的《左傳》學,皆以《公羊》附會《左傳》,依違于今、古文兩說之間,直到杜預的《春秋左傳集解》纔不再雜糅《公羊》、《穀梁》,專就《左傳》解《左傳》,開闢了研究《左傳》的正途。他在1913年的《自述學術次第》中說:“余初治《左氏》,偏重漢師,亦頗傍采《公羊》,以爲元凱(杜預)拘滯,不如劉、賈宏通。數年以來,知釋例必依杜氏。古字古言,則漢師尚焉。其文外微言,當取二劉以上。”(45) 正如蒙文通之所稱讚,章太炎“雖未必專意說經,其于家法之故,實不逮左庵(劉師培),然于《左傳》主杜氏,于費《易》取王弼,以《周官》爲孔子所未見之書,學雖遜于左庵,識實比于六譯(廖平)”。(46)
三、疑古思潮及其對《春秋》、《左傳》的科學研究
20年代,在新文化運動的思潮下,錢玄同和顧頡剛重新提出劉歆僞造古文經之說,唤起晚清今古文之争。但他們並非站在今文經學的立場上攻擊古文經學,而是要將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家法一起打破,將六藝經傳當作迷霧重重的古代史料加以考辨,從而打破儒家世傳之古史系統以開啓科學研究古史的道路。1921年3月間,作爲章太炎弟子後又轉宗今文經學的錢玄同寫信給顧頡剛說,自1917年以來,他終于打破“家法”觀念而發現,作爲對歷史的記載來說,包括《左傳》在內的古文經固然出于僞造,而今文經也很難憑信。(47) 他的這一想法對原本相信章太炎古文經說的顧頡剛產生了醍醐灌頂似的影響。(48) 1923年5月,顧頡剛在《讀書雜誌》上發表著名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第一次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6月,錢玄同發表《答顧頡剛先生書》,除贊同顧頡剛的觀點外,還就孔子與六經的關係以及六經的真相,說出了一大通“驚世駭俗”的看法。他們的通信引發舉世矚目的争論,掀起了“疑古”思潮。錢玄同說,孔子無删述或制作六經之事,《詩》、《書》、《禮》、《易》、《春秋》本是不相關的五部書,大致在戰國之末,由儒家後學配成“六經”。他認爲,《春秋》不過魯國“斷爛朝報”,孟子爲了藉重孔子而硬造出《春秋》大義的說法,一變而爲《公羊傳》。包括董仲舒、何休在內的春秋公羊學雖然不是《春秋》本有,但能自成一派學說。《穀梁傳》則是“文理不通”的學舌。至于《左傳》,他相信康有爲的說法,是劉歆割裂成書于戰國時代的原本《國語》而僞造成書,其中凡例書法以及說經之語皆爲劉歆所增,又把用不著的部份仍留作《國語》。“這部書的信實的價值和《三國演義》差不多;但漢以前最有價值的歷史總不能不推它了”。(49) 1925年3月至9月,錢玄同與顧頡剛又通信討論《春秋》與“三傳”的性質,錢玄同表示,他傾向于相信《春秋》就是一部魯國的“斷爛朝報”,不但没有“微言大義”,且没有組織、體例,是不成東西的史料而已。顧頡剛也持同樣看法,說《春秋》應出于歷世相承的史官之手,絕非孔子著作,只是孔子弟子所讀之書。(50)
錢、顧二人在疑古思潮中重提今古文關于《春秋》學的公案尤其是《左傳》僞造說,引發了撇開經學立場的對《春秋》、《左傳》作者與性質問題的科學化考辨。在整個20年代到30年代初,疑古派和考古派的學者大多傾向于認爲孔子不修《春秋》,而《左傳》即使不是劉歆所僞造,也是出于戰國時代的一部獨立史書,與《春秋》没有直接的關係。1927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左傳真僞考》被胡適介紹到中國,由陸侃如翻譯爲中文出版,在當時學界引起普遍關注。高本漢旨在否定劉歆僞造《左傳》說,他用語法研究的方法,指出《左傳》有著漢朝人所無法僞造的語法系統,也非《論語》、《孟子》中的“魯語”,而與《國語》最爲相近。《左傳》的成書應該在公元前468(《左傳》記事的最後一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間。胡適爲其書作序,也論述了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爲,劉歆僞造《左傳》說是不能被證實的,但《左傳》與孔子《春秋》也本無關係,其成書怎麽也在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後,甚或在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齊”之後(這兩件事都爲《左傳》所預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關于《左氏春秋》一段,經過高本漢的研究證實確係原文,非劉歆所改竄,但司馬遷只認《左氏春秋》爲許多《春秋》的一種,並不曾說是一部《春秋左氏傳》。至于魯君子左丘明,很可能是一種傳說或猜想。至于《左傳》的授受系統,則出于僞造。(51) 胡適還在與錢玄同的討論中指出,現有證據既無法證實也無法否證《春秋》是孔子所作,但似乎可以假定是孔子仿古史書法而作,其底子乃是孔子以前的史官所記録。(52) 他的意見比之錢、顧二人要合理得多。時就讀于清華國學院的衛聚賢于1927年6月刊行的《國學論叢》創刊號上發表《〈左傳〉之研究》,也反駁《左傳》爲劉歆僞造說,但又認爲《左傳》並非春秋時代的魯君子左丘明所作,而是公元前425年(趙襄子死)至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間的晋國人所作,他猜测子夏是《左傳》的作者。(53) 錢穆于1930年6月刊行的《燕京學報》第7期上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痛駁被錢玄同重新抬出來的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充分論證了劉歆僞造說的不合理。(54) 然而,儘管錢文在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胡適、傅斯年皆信從之,但顧頡剛和錢玄同卻還是堅持前說。顧頡剛于1930年6月刊行的《清華學報》第6卷第1期上發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他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左傳》中出現了言之甚詳的“漢爲堯後”的古史系統,來繼續論證劉歆僞造《左傳》說。(55) 1931年和1932年,錢玄同先後發表《〈左氏春秋考證〉書後》和《重論經今古文問題》他除了堅持劉歆割裂《國語》以成《左傳》,還用顧頡剛和傅斯年的研究成果論證原本《國語》的作者是戰國時三晋人,關于《春秋》經,他這時則認爲並非魯國的“斷爛朝報”,而確實是一部“托古改制”的書,以表示其“大一統”與“正名”之理想。只是其“筆削”者絕非孔子。(56)
四、孔子的“史識”
當胡、錢、顧等人繼承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說而至于“六經皆史料”,並以此徹底摧破六經的權威以及儒家綱常的真理性,章太炎卻沿著自己的思想進路于1932年寫成他關于《春秋》、《左傳》學的最後定論《春秋左氏疑義答問》。(57) 與前兩書相比,他終于明確指出,《春秋》“終是史書”(58),《左傳》以“史”傳“經”,所謂《春秋》大義乃是“前聖作史本意”,即孔子良史之“識”。
關于《春秋》的性質以及《春秋》與《左傳》的關係,章太炎這時確認,孔子絕非“作”《春秋》,而是根據原本魯《春秋》有所删改,有意保留了魯《春秋》的原貌——這一觀點得到後來很多學者的認可。删改的原則是,《春秋》所書外事多從赴告,往往失實,而孔子不改,以存“官法”;對經過審核確係有誤的事狀或書法,則“施特筆以定之”。(59) 他又說,孔子與魯大史左丘明一起到“周室”觀看各國《史記》,就是爲了撰成《左傳》“以事實輔翼魯史,而非以剟定魯史之書”。(60)《春秋》經傳“同作具修”,孔子與左丘明“造膝密談”,親授旨意,還參做《左傳》,而《春秋經》之中又有左丘明的“佐書”。(61) 也就是說,《春秋》是《左傳》的大綱,《左傳》是《春秋》的內容,意旨通貫,合成孔子良史之學:“經據魯以守官,傳依周以閱實,苦心作述,正在于斯”。(62) 黄侃爲《春秋左氏疑義答問》作序,專門針對疑古時論說道:
不知孔子有所治定,則云《春秋》不經孔子筆削,純録魯史舊文,而修經之意泯;不知作傳之旨悉本孔子,則經違本事與褒諱挹損之文辭,屈于時君而不得申者,竟無匡救證明之道。(63)
章、黄如此“反潮流”地力證孔子“修”《春秋》而《左傳》和《春秋》根本就是一回事同樣出自孔子,既是爲了維護《春秋》、《左傳》的信史價值,也是爲了保證《春秋》確實有一貫而明確的“大義”,出于聖人孔子,具有不朽的思想價值。(64)
關于《左傳》的義例書法,章太炎重申“五十凡”是西周末年史官書寫歷史之法式,其間也有一些是魯國史官所增。(65) 總之,《春秋》經基本保留了魯史原貌。那麽,很多“書法”被後人賦予“微言大義”,現在就可以得到平實的解釋。如關于“元年春王正月”,以及“王二月”、“王三月”的書法,《公羊傳》及其後學據此發揮“大一統”和“通三統”。章太炎原本相信其說,但在《疑義答問》中,則認識到此說“恐亦附會”,並給予了平實的解釋。所謂“元年春王正月”者,在“史法”上表示紀年的次序;于“國政”則勸喻國君“必慎始也”。所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者,是因爲當時諸侯國所用曆法不一,史官如此書法是爲了統一紀年,使“記事比考不差”。而且,所有這些書法都是魯史舊文,非仲尼新意。(66)《左傳》中還有很多地方用“書”與“不書”來解釋《春秋》書法,不能包括在“凡例”之內。杜預認爲這是“變例”,是“仲尼新意”。章太炎基本認同杜預《左傳釋例》的原則,認爲循之可得孔子“修經之意”:“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异端。實非劉賈許穎所逮。”(67) 于是,他在《春秋左傳疑義答問》中用大量篇幅爲《左傳》的“書”與“不書”等所謂“變例”曲加解釋,以爲能傳孔子《春秋》旨意,牽强附會的地方實在不少。正如李源澄所批評:
《春秋左氏疑義答問》一書……發明甚多,惟左氏說經,不無問题。雖以先生之才之學,终未能使其血脉貫通。(68)
不過,章太炎既否定了孔子“改制”說,那麽,其所謂《春秋》大義主要不是寓于書法義例的“微言”,而是“見之于行事”的良史之識。章太炎說,關于《春秋》大義,同爲良史的太史公所言最爲確當:“《春秋》人事浹,王道備。”而賈誼也明確指出“《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劉向歆父子也明白《春秋》大義其實是“史識”:“謂《春秋》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非專爲懲弑而作。”(69) 章太炎將作爲孔子史識的《春秋》“大義”歸結爲兩個要點,其一:
然則四夷交侵,諸夏失統,奕世以後,必有左衽之禍,欲存國性,獨赖史書,而百國散紀,難令久存,故不得不躬爲采集。使可行遠,此其緣起一也。(70)
這即是說,孔子具有自覺的民族主義史學思想。章太炎在《檢論·春秋故言》中也曾這樣總結孔子《春秋》“本旨”。關于章太炎藉《春秋》大義闡發自己以歷史存“國性”的民族主義思想,前人多有闡發,不再贅論。我認爲,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所謂《春秋》“樂道五霸”的主旨還是一種明察世變、達于時勢的史家智慧,同時,也是一種深具歷史精神的政治原理。他這樣論述孔子修《春秋》之“緣起二”:
王綱絕纽,亂政亟行,必繩以宗周之法,則比屋可誅;欲還就時俗之論,則彝倫攸斁。其唯禀時王之新命,采桓文之伯制,同列國之貫利,見行事之善敗,明禍福之徵兆,然後可施于亂世。關及盛衰。(71)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孔子不是固守舊的“宗周之法”,不是屈從時勢随波逐流,也不是自創一套理想秩序以取代現實,而是以“尊王”爲號召,采取並規範在新形勢下發生變化的禮制,維持“霸政”秩序。《左傳》中“禮也”、“非禮也”的判斷,所根據固然不是“周禮”,但也不是孔子之創制,而是“時王新令”。(72) 孔子不是以“王道”繩“亂世”的理論家、理想主義者,而是一個歷史家和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善于對“時勢”做出準確判斷,把握一定“時勢”下的人心向背,明察現實的可能的歷史走向,然後因勢利導,依據現實提供的條件以求規範現實,于不合理的現實中求得治理的可能方略。章太炎在1935年3月《答李源澄書》中曾論述說:
蓋《春秋》者,以撥亂反正爲職志。周道既衰,微桓文起而匡之,則四夷交侵,中國危矣。故就其時制,以盡國史之務,記其行事得失,以爲法戒之原。孫卿曰有治人無治法。則知聖人不務改制,因其制皆可以爲治也。(73)
無論漢學還是宋學,論《春秋》大義多持孟子之說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自宋代以來,嚴王霸之辨謹義利之別的《春秋》大義更是深入人心。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樂道五霸”的《左傳》纔受到懷疑和貶低。而深通經學的章太炎卻徹底顛覆關于孔子思想的傳統認識,居然論證孔子並不打算發明什麽理想的“王道”,而是因時制宜地尊行“霸道”!在《春秋》學史上,被朱熹視爲“雜學”、“縱橫之學”的蘇軾和蘇轍倒是早就指出《左傳》以“史”傳“經”,最能傳達《春秋》意旨,而不甚重視“書法義例”。他們論孔子《春秋》大義與章太炎有驚人的相似:
春秋之際,王室衰矣,然而周禮猶在,天命未改,雖有湯武,未能取而伐之也。諸侯之亂,捨此何以治之?要之以盟會,威之以征伐,小國恃焉,大國畏焉,猶可以少安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故《春秋》因其禮俗而正其得失,未嘗不予也。(74)
《四庫》館臣稱二蘇之學“究心于經世之學,明于事勢,又長于議論,于治亂興亡披抉明暢”。(75) 可見,章太炎所推尊的孔子及其《春秋》確實是極具政治頭腦的歷史家或富有歷史智慧的政治家。
上述章太炎所論孔子《春秋》大義,與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傾向大有關係。當他尚未與維新派劃清思想界限,並竭力攀附康有爲《公羊》學以論《左傳》的時候,他就著力突出自己政治立場的“歷史”性格並與康有爲的非“歷史”態度相反對。在初刻本《訄書》第一篇《尊荀》中說,孔子《春秋》所作“新法”是根據“周禮”因革損益而成,聖人創制立法的精義就是尊重歷史傳承而漸變:“變不斗絕,故與之莎随以道古”。而康有爲所說的孔聖“改制”,則蔑棄“近古”取法“太古”,想用一套出于理想的法制徹底變革現實,就象墨子想扔掉周代歷史直接回到大禹時代,也象李斯以“法泰皇”爲號而大舉變法,這都是缺乏足够的歷史意識,以爲歷史能够“驟變”。(76)
1906年之後,章太炎經過“轉俗成真”的思想轉變,從佛教唯識學中悟得“虛無”,又由《莊子》悟得“齊物”,開始犀利地批判“公理”、“進化”等現代觀念,正如“上帝”、“天理”之名,同樣都是被現實霸權所假借而禁錮人心的“迷信”。(77) 于是,在他看來,只有歷史傳承形成的“約定俗成”,而不是什麽“普世價值”或“歷史普遍規律”,纔能成爲制定或改革一國政法制度的依據,以及判斷其好壞的標準:
典常法度本無固宜,約定俗成則謂之宜矣。生斯世爲斯民,欲不隨其宜而不可。(78)
在章太炎的思想世界中,存古而明變的史學,有著比興起民族主義更重要的作用和位置。在《國故論衡·原道上》篇中,他曾藉老子之“道”闡發他不問“公理”唯問“歷史”的政治思想。他說,老子是一位明察歷史之變的“徵藏史”,老子所主張的治理之道,就是撇開一切“前識”、“私智”,“不慕往古”,“不師异域”,唯根據歷史積累傳承而來的具體現實,以及一定現實環境下的人民意願,“清問下民以制其中”。而孔子受業于老子,他的思想是繼承老子的。(79) 民國建立之後,章太炎往往根據其所見“大道之原”,反對盡變舊法而照搬歐美現成制度,强調要根據本國政法傳統、風俗民情,來創制中國現代的政治型態。他爲《大共和日報》所撰《發刊詞》,典型地表述了他那以“歷史主義”爲理據的政治“保守主義”:
政治法律,皆依習慣而成,是以聖人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其要在去甚、去泰、去奢。若橫取他國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靈者弗爲。君主立憲,本起于英,其後他國效之,形式雖同,中堅自异;民主立憲,起于法,昌于美,中國當繼起爲第三種。寧能一意刻劃,施不可行之術于域中耶?(80)
五、章太炎“六經皆史”說的本意
在確立“六經皆史”之旨後,章太炎雖然多次申說“素王修史,實與遷、固不殊,惟體例爲善耳”。(81)“《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漢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82) 但他並没有明確指出,孔子删定“六藝”並蕴有“大義”,使“六經”之學得以成立,似乎孔子“述作”六經只是一般的保存整理古代文獻。在重訂本《訄書·清儒》篇中,章太炎强調的是,“六藝”是上古流傳下來的具有濃厚神教色彩的官書,要將之當作歷史文獻來研究,他非但没有明言孔子的删定之功,反而說荀子“隆禮義殺詩書”,使“其言雅馴近人世”。他還說,六經的內容“繁雜抵牾”,孔子“輟其什九,而弗能貫之以櫨間。故曰達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83) 也就是說,孔子並没有通過“六經”建立一個思想體系,不如諸子速甚。而且,他所尊之“史”乃是左丘明的《左傳》、《世本》之學,比之左丘明,孔子的“良史”之稱只是個虛銜而已。(84)“守舊”的劉咸炘曾批評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說過于極端,把六經當作“古史陳賬”,只是“整齊故事”,而與孔子學術無關。他認爲,六經確乎爲“史”,但六經既經孔子訂定,“孔子之學即在經中”。(85)
而我要强調指出的是,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說,其實近乎劉咸炘所云,終以“六經”爲孔子的“良史之學”。“六經”不是“繁雜抵牾”的史料,也不是簡單的“存古”,而是貫穿著孔子的“删定大義”。在1915年所寫《菿漢微言結語》中,他說自己通過專門研究“古文記傳”,而從中探求出孔子的“删定大義”,“由是所見與箋疏瑣碎者殊矣”。(86) 又說,孔子學于老子,深于史學,“故能删《詩》而作《春秋》”。(87)
在新文化運動的疑古思潮中,孔子删定“六經”的傳統觀念遭到質疑乃至否定,更是推翻了孔子“作《春秋》”、“序《易傳》”的神話。學者們基本認爲,“六經”之名之學成于戰國晚期至于漢初的儒家後學,他們爲了尊大其學而托名于孔子。(88) 而章太炎在20、30年代卻一再强調孔子定“六經”之名、立“六經”之學,他說:
孔子之前,《詩》、《書》、《禮》、《樂》已備。學校教授,即此四種……至于《春秋》,國史秘密,非可公布;《易》爲卜筮之書,事异恒常,非當務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贊《周易》、修《春秋》,然後《易》與《春秋》同列六經。以是知六經之名,定于孔子也。(89)
在1922年于上海所作《國學概論》演講中,他這樣講“六經皆史”:
太史公說:“《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引申他底意思,可以說《春秋》是臚列事實,中寓褒貶之意;《易經》卻和近代“社會學”一般,一方面考察古來的事迹,得著些原則,拿這些原則,可以推測現在和將來。簡單說起來,《春秋》是顯明的史,《易經》是蕴著史的精華的。(90)
《春秋》、《易》是“六經”的主幹,而《春秋》經與《左傳》一體相成,是孔子明察世變的史書,《周易》乃是孔子的“歷史哲學”,那麽“六經”究竟是怎樣的“史”,則思過半矣。
在“訂孔”時代,章太炎對儒家乃至孔子的思想評價甚低,不但不能與佛學相比,且遠遜于道家、法家。直到1910年,他仍在《國故論衡·原經》篇中說:“《春秋》言治亂雖繁,識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韓非,下猶不逮仲長統。”(91) 但經過1913年幽禁期間的“回真向俗”之變,他認爲孔子的哲理思想已達到“齊物”的高度,以《春秋》、《周易》爲主幹的孔子之學,大有深意:
間氣相猾,逼于輿臺,去食七日,不起于床,喟然嘆曰:余其未知羑里、匡人之事!夫不學《春秋》,則不能解辨發,削左衽;不學《易》,則終身不能無大過,而悔吝隨之。(92)
如果說康有爲把孔子改裝爲一位神秘的教主,能預言百代,托古改制,章太炎則把孔子塑造成了一位空前絕後的大史家,他由“史”見“道”,而寓“道”于“史”。不過,這樣一來,孔子似乎也突破了“儒家”的範疇,他的歷史智慧傳承于老子而比肩莊子。
“六經”之學是孔子“良史之學”,其中蕴含著孔子由“史”所見之“道”。這是章太炎“古文經學”的一個核心要義。它不但保證了以《毛詩》、《左傳》、《周禮》爲主的古文經傳是“信史”,而且證明其中貫徹著孔子的“史義”,是具有自覺意識的中國種族—文化的起源歷史。與此緊密相關,章太炎的“古文經學”其實就是具有晚清時代思想特徵的一套中國種族-文化起源史,並自認爲可以取代經學中的“神話”而爲“國性”立根基,當然,在科學的疑古、考古派看來它仍然是個“神話”。對此,筆者將另外撰文加以論述。
注釋:
① 參見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爲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迹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重訂本《訄書·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參見侯外廬:《中國近代啓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14頁;周予同:《從顧炎武到章炳麟》,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12、315頁;汪榮祖:《康章合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91頁;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315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1868-1919)》,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189頁;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爲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迹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路新生:《經史互動:章太炎的經學研究及其現代史學意義》,《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④ 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發表于1923年8月5日《讀書雜誌》第12期,收入《錢玄同文集》(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256頁。
⑤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學》,周文玖編:《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48頁。
⑥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收入《古史辨自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3頁。
⑦ 錢玄同:《與顧起潜書》,發表于《制言》第50期,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32~33頁。
⑧ 如張昭軍:《章太炎的春秋、左傳學研究》,《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1期;氏著《儒學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學思想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對儒家經學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1868-1919)》第三章《與清末今古文之争》,主要以章氏《春秋》學爲主綜論其古文經學的基本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侯外廬:《章太炎的科學成就及其對于公羊學派的批判》,也以其《春秋》學思想爲主加以論述,收入章念弛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李學勤:《章太炎論左傳的授受源流》,收入《章太炎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出版社,1996年;洪順隆:《章太炎與左傳》,收入《章太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末岡宏:《章炳麟的經學及其相關思想史的考察——以春秋學爲中心》,《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3集,1991年10月;胡自逢:《太炎先生左傅學》,《第三届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1997年5月;楊向奎:《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論述其《春秋》、《左傳》學,《翻經室學術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羅福惠:《章太炎經學述略》,對其《春秋》、《左傳》學有專門論述,收入《中國近代文化問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房德鄰:《章太炎的經學思想》,也論述其《春秋》、《左傳》學,收入《章太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臺北:理仁書局,1999年。上述研究主要側重于闡發章氏《春秋》、《左傳》學的科學性及民族主義思想,且對章氏《春秋》、《左傳》學的變化發展有欠注意。
⑨ 章太炎:《自定年譜》,《章氏叢書》附録,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
⑩ 章太炎于1933年曾說:“余幼專治《左氏春秋》,謂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語爲有見……方余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餘焰,簧鼓一世,余故專明左氏以斥之。”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收入陳平原等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69頁。
(11) 《春秋左傳讀·隱公篇·立素王之法》,《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2) 《今古文辨義》,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0頁。
(13) 《春秋左傳讀·隱公篇·丘明》,《章太炎全集》(二)。
(14) 《致譚獻書》,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册,30頁。
(15) 《春秋左傳讀叙録·序》,《章太炎全集》(二)。
(16) 參見湯志均:《近代經學與政治》,261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46頁;張勇:《戊戌時期章太炎與康有爲經學思想的歧异》,《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劉巍:《從援今文經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爲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迹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7) 章太炎于1913年所寫《自述學術次第》中說:“所次《左傳讀》,不欲遽以問世者,以滯義猶未更正也。”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8) 參見重訂本《訄書》之《清儒》、《訂孔》、《尊史》、《征七略》諸篇,《章太炎全集》(三)。
(19) 《與人論樸學報書》、《與簡竹居書》,《太炎文録初編·文録》卷二;《答鐵錚》,《太炎文録初編·別録》卷二,《章太炎全集》(四)。
(20) 《春秋左傳讀叙録》,《章太炎全集》(二),845頁。
(21) 同上,829~830頁。
(22) 姜義華:《春秋左傳讀校點說明》,《章太炎全集》(二)卷首。
(23) 章太炎于《1932年7月14日與吳檢齋書》自述研讀經過:“始雖知《公羊》之妄,乃于《左氏》大義,猶宗劉、賈。”于1932年10月6日《與徐哲東論春秋書》說:“其《劉子政左氏說》,先已刻行,亦牽摭《公羊》于心未盡于慊也。”發表于《制言》第17期,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册,924頁。
(24) 《駁箴膏肓評·叙》,《章太炎全集》(二)。
(25) 《春秋左傳讀叙録·後序》,《章太炎全集》(二)。
(2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1518頁。
(27) 同上,1524頁。
(28) 《劉子政左氏說》,《章氏叢書》上册,28頁。
(29) 《春秋公羊傳》于“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灾。”一條說:“成周宣榭灾,何以書?記灾也。外灾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休《解詁》曰:“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宣王)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係宣榭于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灾也。”“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63頁。
(30) 《劉子政左氏說》,《章氏叢書》上册,27~28頁。
(31) 《春秋左傳讀叙録·後序》,《章太炎全集》(二)。
(32) 《劉子政左氏說》,《章氏叢書》上册,9頁。
(33) 《劉子政左氏說》,《章氏叢書》上册,1~4頁。
(34) 《劉子政左氏說》,《章氏叢書》上册,4~7頁。
(35) 《春秋左傳讀·哀公篇·西狩獲麟》條有云:“《荀子正名》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取期……’麟舊謂作《春秋》爲後王法,《荀子》之論乃《左氏》家說,作《春秋》之微言,于茲益信。先商,而周,而禮,則禮非商、周之禮,必爲《春秋》所制之禮也。《公羊》有改制之說,實即《左傳》說也。三統迭建,救僿以忠,是以不言夏而夏即在禮中。《春秋》制禮,參夏、商、周而酌之,故《春秋》正是禮書,語本《荀子》。”《章太炎全集》(二)。
(36) 重訂本《訄書·官統上》,《章太炎全集》(三)。
(37) 《國故論衡》卷中《原經》,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38) 《檢論》卷二《春秋故言》,《章太炎全集》(三)。
(39) 同上。
(40) 《國故論衡》卷中《原經》。
(41) 同上。
(42) 《檢論》卷二《春秋故言》,《章太炎全集》(三)。
(43) 《國故論衡》卷中《原經》。
(44) 《國故論衡》卷中《明解故下》。
(45) 《自述學術次第》,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
(46) 《廖平與近代今文學》,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
(47) 《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僞叢書〉書》,發表于《古史辨》第一册上編,收入《錢玄同文集》(四)。
(48)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49)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發表于1923年6月10日《讀書雜誌》第10期,後載于《古史辨》第一册中編,收入《錢玄同文集》(四)。
(50) 錢玄同、顧頡剛:《〈春秋〉與孔子》,發表于1925年10月《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第1期,後載于《古史辨》第一册下編。收入《錢玄同文集》(四)。
(51) 胡適:《左傳真僞考的提要與批評》,收入《胡適文存三集》,《胡適文集》第4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52) 胡適:《論春秋答錢玄同》,《胡適文存四集》,《胡適文集》第5册。
(53) 衛聚賢:《〈左傳〉之研究》,《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一號,商務印書館。
(54)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收入《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55)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收入《古史辨自序》。
(56)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先後發表于樸社出版的佐氏春秋考證》,北平師範大學《國學叢刊》第1卷2期,載《古史辨》第5册上編;《重論經今古文問題》,其增改本發表于1932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3卷第2號,均收入《錢玄同文集》(四)。
(57) 《1932年6月24日與吳承仕論春秋答問作意書》:“《春秋答問》爲三十年精力所聚之書……獨存此四萬言而已。”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360頁。此書收入《章氏叢書續編》,1933年刊行。
(58) 《1932年6月24日與吳承仕論春秋答問作意書》,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360頁。
(59) 《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卷一,《章氏叢書》下册,1025頁。
(60) 《1932年7月14日與吳檢齋書》,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361頁。
(61) 《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卷一,《章氏叢書》下册,1020頁。
(62) 同上,1026頁。
(63) 黄侃:《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序》,《章氏叢書》下册,1017頁。
(64) 關于《春秋》、《左傳》的作者、性質及其關係,自30年代以來,學界屢有争論,楊向奎的《論左傳的性質及其與國語的關係》、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前言》較有代表性。目前占主流的看法是,孔子很可能曾修訂過《春秋》並用以教學;《左傳》凡例書法以及說經之語並非漢朝人僞造,確係傳經之作,但與孔子無關,其成書大概于戰國中期。也有不少學者認爲,《左傳》很可能非成書于一人一時,並不能排除其始傳者爲左丘明的可能。參見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373~399頁。
(65) 《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卷一,《章氏叢書》上册,1019頁。
(66) 同上,1029頁。
(67) 同上,1023頁。
(68) 李源澄:《章太炎先生學術述要》,林慶彰、蔣秋華編:《李源澄著作集》(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7年,1462頁。
(69) 《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卷一,《章氏叢書》上册,1018頁。
(70) 同上,1019頁。
(71) 同上。
(72) 同上,1027頁。
(73) 《1935年3月2日與李源證書》,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950頁。
(74) 蘇轍:《春秋經解》卷一“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
(75) 《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一《經部·書類一·東坡書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76) 初刻本《訄書·尊荀》,《章太炎全集》(三)。
(77) 參見章太炎《俱分進化論》,《太炎文録初編·别録》卷二;《五無論》、《四惑論》,《太炎文録初編·別録》卷三,《章太炎全集》(四)。
(78) 《代議然否論》,《太炎文急流初編·別録》卷一,《章太炎全集》(四)。
(79) 《國故論衡·原道上》。
(80) 《大共和日報發刊辭》,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册,537頁。
(81) 《與人論樸學報書》,《太炎文録初編·文録》卷二,《章太炎全集》(四)。
(82) 《答鐵錚》,《太炎文録初編·別録》卷二,《章太炎全集》(四)。
(83) 重訂本《訄書·清儒》,《章太炎全集》(三)。
(84) 重訂本《訄書·尊史》,《章太炎全集》(三)。
(85) 劉咸炘:《文史通義識語》卷下《辨惑》,《推十書》第一册,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96年。
(86) 《菿漢微言結語》,《章氏叢書》下册。
(87) 《菿漢微言》,《章氏叢書》下册,952頁。
(88) 參見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26~29頁。
(89) 《1935-1936年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録》,張昭軍編:《章太炎講國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212頁。
(90) 《國學概論》,張昭軍編:《章太炎講國學》,76頁。
(91) 《國故論衡·原經》。
(92) 《檢論》卷三《訂孔下》,《章太炎全集》(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