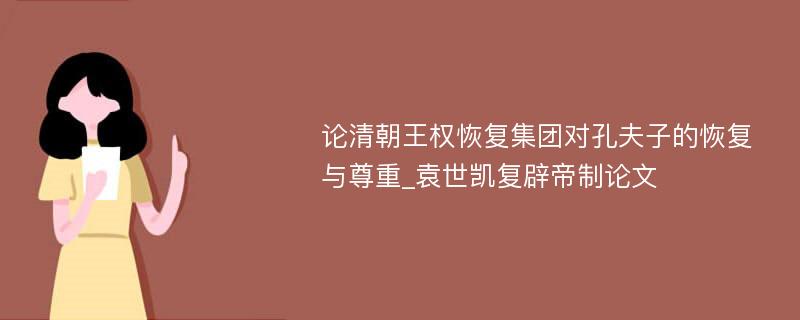
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复辟与尊孔关系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室论文,贵族论文,关系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随着辛亥首义的第一声枪响,宣告了在中国统治267年的清王朝的彻底失败。但是,历史的发展常常是这样:统治者总是不甘心于失败,总是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只要有一线的希望,他们就要付出十倍甚至是百倍的努力,屡败屡战,进行反扑。几乎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时,在亡清皇室贵族顽固派的周围,便迅速结成了一个帝制复辟集团。对此,业师章开沅教授在《辛亥革命史》和《章开沅学术论著选》中从政治变迁的角度曾有精辟的论述,很能从中获得思想的启示。本文试图在文化的层面剖析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复辟与尊孔的关系,揭示其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
一
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被推翻,献身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曾一度陶醉于革命的暂时胜利中,认为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万事大吉了(注: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4-85页。)。岂料辛亥革命后,共和与帝制的较量,如风之乍起,既急迫而又多变;如行人之步入歧途,历经曲折和反复。尽管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但是试图抗拒历史潮流的社会因素还是存在的。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复辟事实说明,辛亥革命能够革亡清朝皇帝的命,却不能革除旧时代人们迷信皇帝、留恋帝制的社会心态。这就是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后,在社会层面上会大量地存在新的与旧的、活的与死的交织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社会现象。新旧斗争的复杂性特征,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所共有的规律性现象。只不过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一特征在民国初年表现得更为强烈、更为明显而已。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巨人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变成了历史的侏儒,他的学生梁启超说老师是“大言不惭之书生”(注:梁启超:《反对复辟电》,《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民国初年康有为彷徨、迷茫、烦躁、愤世嫉俗的情绪,很有代表性。1913年初,康有为认为:“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守法隳斁,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注: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不忍》第2册(民国二年三月)。)接着,他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的文章中,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膝盖跪拜论”:人的肢体,各有所用。腿长膝盖,就是为了跪拜,这是人的天性;民国改跪拜礼为鞠躬,是违反人的天性的。假如膝盖丧失了跪拜的功用,那么,“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注: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不忍》第3册(民国二年四月)。)康有为的这种社会心理与对民国的不满乃至怨恨、对帝制的留恋乃至对于孔子思想的眷恋,决不是无关紧要、不足道论的个别心态。在民国初年,不仅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尊孔为复辟之用,而且其后产生的袁世凯复辟集团、张勋复辟集团在掀起复辟逆流时,他们都举起了孔子的偶像,张扬着破旧不堪的孔子思想的旗帜,妄图以“孔家店”支撑封建王朝的金銮宝殿。
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对于时局的判断,经常不同;哪怕是非常错误、糊涂,甚至是幼稚可笑的看法,也往往不能自知。一方面是拥护革命,欢迎民主共和的人欢畅地说,封建帝制已不合于中国,应该被民主共和所埋葬;民主共和在中国得到确立,有广泛的国民心理基础:
“蓋我国民既懲於甲午庚子以来之失败,又受日俄战役之刺激,就事实上之比较,知专制之终于覆国,立宪之可以兴邦;又以他国已往之事实推测之,则立宪政体之成立,非革命流血不为功。故武汉发难,全国响应。”“今民国成立将一年矣,观共和政治之现状,则其表示吾国民之心理者,尤彰彰焉。”(注:伧父:《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五号(民国元年十一月)。)
另一方面是诋毁民国,做着复辟梦的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可笑的判断:
“革命以来新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新法,不仅不能取悦人心,混乱的秩序依然不能恢复。新的设施尚未见眉目,旧的恶弊仍在困绕着人们。兴一利而生百害,内外施政经营尚不及前清时代。内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乱,生灵涂炭。天下人心已厌共和,讴歌前朝者渐多,复辟帝制的时机似将来临”(注:[日]宗方小太郎:《宣统复辟运动》,1912年12月14日。见《北洋军阀》第三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流产了的宣统复辟闹剧,在人们沉浸在推翻帝制的喜悦中,在亡清王朝皇室贵族顽固派错误判断的支配下,荒诞地上演了。
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他们本是清末亲贵集团中的死硬派。在辛亥革命中,清廷举行“让国御前会议”,他们在会上再三表示暂死反对皇帝逊位,拒绝革命党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坚持反对共和;同时,也反对将大权委于袁世凯。在清王朝土崩瓦解已成定局之际,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仓皇逃离北京,避居在青岛和大连的租界里阴谋策划复辟。溥伟和善耆虽然没有多大实力,但他们凭借日、德帝国主义的支持和他们自己较高的声名地位,居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皇族亲贵中的死硬分子升允(蒙古镶黄旗)、铁良(满州镶白旗)、金梁(满州正白旗)等人被网罗在他们的周围,而且还招罗了一批前清遗老。这些前清遗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因为其中一部分人曾经担任过前清朝廷的太傅、大学士、尚书、部臣、翰林院编修、大学堂监督,还有一部分人曾经在地方担任过总督、巡抚、布政使、提学使。他们在前清出身于进士,居位于高官:在民国初年又摇身一变为“文人学士”,具备了充当封建卫道士的“合法”身份。在这批遗老中,活跃分子有:劳乃宣(前清学部副大臣)、胡思敬(吏部主事)、刘廷琛(学部副大臣)、陈毅(刑部侍郎)、章梫(翰林院编修)、沈曾植(署理安徽巡抚)、郑孝胥(湖南布政使)、李瑞清(江宁提学使)、胡嗣瑗(翰林院编修)、陈三立(吏部主事)等等(注:据章开沅:《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页。)。辛亥革命既击碎了他们的粱园美宅,也击碎了他们的政治信念和文化理念。共和与帝制的冲突就像熊熊烈火一样,在他们的胸中燃烧,升腾。升允在《檄告天下文》中叫嚷:“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胡思敬则以“规复故君”、“奉宣统复位”为职志,以“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思恋故主,每当饭不忘”相激励(注:胡思敬:《退庐笺牍》、《退庐诗集》(甲子刻本)。)。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因此,他们是清王朝覆灭以后的铁杆儿“保皇派”。
他们的政治立场如此反动,有如下因素:一是从个人出身来看,他们在人生历程的很长时间里在科举场上拼搏,深受封建政治、文化的熏陶,长期的旧文化的习染,培育了他们的政治信念与文化理念,很难因新时代的开辟而得到改变;二是从家庭出身来看,他们一般出身于世家大族,家庭环境的熏染,既培养了他们坚定的阶级感情,又培育出浓厚的政治情感,他们对于民主共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视;三是从社会阶层利益来看,辛亥革命使他们由旧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大受益者顷刻变为新时代的最大失利者。巨大的失落感经常地激发他们强烈的社会激愤;只不过这种激愤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罢了,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有害于社会进步的社会心理罢了。这是从总体上分析。
如果进行个案考察,他们在民国初年坚持如此反动的政治立场,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像劳乃宣、胡思敬、刘廷琛等人,在晚清洋务、维新、新政、立宪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站在落后的反动的立场上讲话的,可以说,他们是老牌的顽固守旧分子;像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加入了帝党阵营,对满清皇帝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这种“忠君”的感情并不能随着帝制被推翻而马上消逝,以致于在辛亥革命后他们依然怀着对于亡国之君的无限眷恋,对新时代的到来极端反感,对于民主共和的确立充满敌视。胡思敬曾做一首《咏雪》的七绝,将他的现实感受隐喻于诗意中,十分恶毒。诗云:“茫茫一片无昏暗,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日,朝曦隐隐露西山。”(注:胡思敬:《退庐笺牍》、《退庐诗集》(甲子刻本)。)用旋飘旋溶的雪花比喻和诅咒新生的中华民国,把隐居“西山”的复辟分子比作古代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重见天日”。总之,从追回逝去的王朝,从图谋复辟帝制的立场出发,从对于清朝皇帝的深厚感情出发,封建复辟分子必然诅骂革命是“暴乱”,革命党是“乱党”、“土匪”,诅骂民主共和是“暴民专政”,诅骂进步文化是“异端邪说”。
二
以亡清皇室贵族为核心的复辟集团,他们进行串联、密谋、举事的主要地点集中在上海和青岛。
1912年6月,胡思敬不避劳苦,东行上海,借用寓居上海的遗老们举行名曰“五角会”的聚餐饮酒的形式,在愚园举行了一次有一定规模的遗老聚会。经过事先的串联和准备,各地的复辟分子趋之若鹜,纷至沓来。见诸记载的有:从广州来的梁鼎芬、秦树声、左绍佐、麦孟华;从福州来的陈衍;从苏州来的朱祖谋;从南京来的李瑞清、樊增祥、吴璆、杨钟羲;从广东来的何天柱;从福建来的林开謩、沈瑜庆;从江西来的胡思敬、杨增荦、梅光远、熊亦园;从四川来的胡铁华、胡孝先;从北京来的赵熙、陈曾寿、吴庆坻;以及本来就寓居于上海的郑孝胥、陈三立、沈曾植、李岳瑞等26人。从青岛赶来的刘廷琛因迟到一日,没能参加当天的聚餐会(注:参见章开沅:《章开沅学术论著选》,第541页。)。他们从全国各地赶赴上海,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聚餐饮酒,而是胸怀着共同的政治目的走到一起来。有胡思敬的追忆为证:“今日之乱,古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诸子怆念故物,缅怀旧京,饘于斯,粥于斯,即当歌哭于斯,使四邻闻之,知中国尚有人在也。”(注:胡思敬:《吴中访旧记》,《退庐文集》卷二。)他所谓的“使四邻闻之”,当然不是指使与会者耳闻其音,而是要制造国际影响,赢得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
除了这类的聚会活动外,复辟分子、遗老遗少们的串联、密谋,还借助“诗社”等形式的组织,进行有组织的活动。1912年,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曰“超社”的组织。超社的发起人是沈曾植、瞿鸿禨、陈三立等。超社成员每月必有一聚,饮酒吟诗,抨击时政。他们以亡国之臣自居,抒发亡国之恨。受超社的影响,相继成立了“同抱故国之感”的“淞社”和“逸社”、“希社”等等(注:章梫:《一山存稿》卷十。)。虽然这些诗社的成分比较复杂,但从其组织者来看,大体上是被前清遗老所控制的,因而它们是复辟分子集结密谋的场所,是复辟分子策划“反民复清大业”的政治舞台。
青岛是亡清皇室贵族从事帝制复辟的重要基地。清王朝被推翻后,皇室贵族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有计划有目的地逃亡青岛。在恭亲王溥伟的组织、号召下,前清遗老在青岛的复辟活动与上海遥相呼应。据载,寓居青岛且与恭亲王溥伟有密切联系的亡清贵族、前清遗老有:吴郁生(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北京大学堂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余则达、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胡建枢、李经迈、朱镇琪、徐世光、萧应椿、李家驹、周学熙等人,均与恭亲王密切往来(注:[日]宗方小太郎:《在青岛居住的宗社党主要人物》,1913年7月5日。见《北洋军阀》第3卷,第197页。)。
这些复辟分子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在青岛进行复辟密谋,他们还要加紧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壮大反动声威。1912年,溥伟逃到青岛后,就加紧同德国帝国主义联系,乞求支援复辟。10月,德国皇弟亨利亲王来华访问,在青岛逗留多日,恭亲王溥伟等皇室贵族以及前清遗老与之“往来活跃”。亨利亲王曾当面向溥伟等人允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其时,据观察家分析,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成为许多旧政权拥护者及厌倦新政府的官僚的避难所”。到了张勋复辟时,德国更是在经费与军火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直接地明火执仗地干涉中国内政,这是后话。次年,德人“中国通”魏礼贤积极“协助”寓居青岛的遗老们创设“尊孔文社”,建立“藏书楼”,并特请劳乃宣“主持社事”(注:《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5-256页。)。魏氏在中国活动的七八年,主要和亡清皇室贵族和前清遗老搅和在一起,为他们的复辟活动出谋划策。魏氏除了同劳乃宣建立了“深厚感情”外,还同癸丑复辟、丁巳复辟的骨干分子张勋、升允有密切的联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从中国的唐朝开始,两国历史的发展就有密切关联。在辛亥革命中,有一大批像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那样热心支持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进步人士,“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2页。);辛亥革命后,也有像宫房次郎那样的反动分子,在帝制复辟活动中充当不光彩的角色,为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鼓噪。1912年,宫房次郎以“朝日新闻社”访员的名义,来华活动。宫房氏热心于同前清遗老来往,很快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一方面向劳乃宣自明其志,“笃志孔孟之学,将访求遗老,传述于故国以维纲常也”;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励前清遗老们“匡复旧朝”。民间力量往往是政府行为的基础,也是窥测政府行为动向的依据。在民国初年,日本朝野内外,从首相、公使、驻天津武官到财阀、黑龙会分子纷纷出动,与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财政、军事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善耆、升允等策划的复辟帝制团体“宗社党”,就是中日反动势力聚合的产物(注:参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发源于青岛的帝制复辟运动终于在1912年底和次年初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据当事人陈毅的记载,复辟集团经过“潜楼”密谋(注:“潜楼”是刘廷琛的寓所。),计划在1913年的春天在济南起事。1912年的夏天,溥伟、刘廷琛、陈毅、于式枚,以及分别从山东兖州和天津赶来的王宝田、温肃在青岛的“潜楼”密议:利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统治还不稳固的时机,定于1913年的春天在山东济南依靠张勋的“辫子军”,发动武装复辟。会后,溥伟派王宝田和毓昌进入张勋幕府,专门负责筹划武装起事事宜;另由陈毅和于式枚预先草拟复辟檄文。不过,由于这次阴谋很快被泄露,而檄文也很快被袁世凯得到,济南方面也及时地加强了戒备,所以,这次“癸丑之春举兵济南”的叛乱阴谋迅速流产(注:参见陈毅:《丁巳同难图记》,《郇庐遗文》。)。
在历史上,任何失败的反动派总是不愿意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负隅顽抗。在民国初年,帝制与共和的冲突如同潮起潮落一样在亡清皇室贵族顽固派胸中激荡。复辟分子为了夺回他们已经丧失的政权,为了追回已经逝去的荣华富贵,他们必然地结成复辟帝制集团进行复辟活动,挑战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民国初年的复辟运动,是民主共和作用于清王朝之后的一种反作用力,是已经被革命滚滚洪流破除了神威的封建帝制的老权威向生机勃勃的民主共和的新权威的反扑。在民国初年,帝制与共和的激烈撞击,在政治领域里的表现,就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老权威对于刚刚出场、角色魅力初露的新权威的排异性抗争。政治领域的斗争不能仅仅依靠政治的力量予以解决,除了军事的、经济的等等方面的力量外,文化的力量大概也是政治家们所善于运用的经常发挥作用的一种力量。
三
民主共和的法理依据是:人人平等、主权在民和自由民主。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抗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走出中世纪、步入近代社会无可争议的进步理论。复辟分子们心中当然有数,要在民主共和法理本身做文章,打开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又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必须赋予封建帝制对于民主共和的反弹——复辟运动以正义性,让人们觉得复辟是“护圣”,而不是倒行逆施,从而赢得全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以实现其“恢复祖业”、“光复旧物”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手中惟一的“法宝”只能是:在封建社会里被人民群众所顶礼膜拜的孔子偶像和代表封建统治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子思想。他们善于装扮自己。在应战革命力量的追打中,他们急中生智,把自己打份成维护传统权威、正统思想的不屈的“卫道士”,而不是“落水狗”。他们认为,帝制是中国社会祖传的权威,是生于传统而非外来的权威,人们接受它是合理合法的,是天经地义的,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帝制在中国社会里,从来受到正统思想——孔子思想的支撑和支持,因而其正确性是无可质疑的。这样,他们就给人们一种错觉,好像民主共和反而具有非中国人的特性,是反动的东西,是洪水猛兽,是可怕的怪物。
由此可见,为了给复辟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并击鼓助威,复辟势力必然地抬出孔子偶像和孔子思想。
辛亥革命后,劳乃宣即在《民是报》上发表臭名昭著的《共和正解》。一方面,劳氏采用恫吓术。他诡称中国民智低下,如果推行民主,必然丧失传统的权威,其后果是举国失控,不仅“乱民土寇”要趁机“作乱”,而且列强也会火中取栗,“坐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劳氏采用诡辩术。他诡称君主政体已经体现了“共和”的本意,共和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概念,也是君主政体的应有范畴和题中之意。劳氏有意混淆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迥然有异的法理基础,不惜追本溯源,引经据典,生拉硬扯,将帝制与共和混为一谈。劳氏云:
“宣王即位,共和罢。《索隐》云:‘二相还政宣王,称元年也,’此共和一语所自出也。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故宣王长,共和即罢。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今日东西各国所谓君主立宪绝相似。而不学之流,乃用之为民主之名词,谬矣。夫君主立宪,有君者也;民主立宪,无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恶得引为无君之解哉?”(注:转引自章士钊:《复辟平议》,《甲寅杂志存稿》上册,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版,第191-192页。)
劳氏一方面使出浑身解数,极力维护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以“护圣”和“布道者”的面目出现,播扬孔子思想。1913年,劳乃宣在青岛设立“尊孔文社”,专讲圣人之道。该社的学员,几乎都是前清贵族和旧朝遗老的子弟(注:参见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
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变迁总是有旧的与新的之别。马克斯·韦伯认为,旧的社会是陷在传统的罗网之中的社会;新的社会则是以理性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益满足”。在旧的社会,传统主义盛行,它墨守成规,因袭世传的习俗;在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中,尽管传统主义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但是它还企图将自己强加给新的时代。因此,“超越这种状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注:参见[德]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转引自[美]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显然,在民国初年,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折的时期,要将传统强加给新的时代,就必须突出传统的价值,就必须引导人们尊重和因循传统,这样才能阻止这种转变。民国初年,一直活跃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康有为此时为传统说法,为帝制招魂,很有一股子“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英勇豪迈。他相继发表《共和救国论》、《中华救国论》等文章,讲述中国的帝制传统,论述孔子之道为万世不易的法则。康氏云:“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洽人心。存帝制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民主共和背离传统,不免陷于灾难,“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难;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因此,康有为强调要尊重传统,顺乎传统:
“我中国积数千年之文明,典章法律,远有代序,……自余道揆法守,纪纲礼俗,皆宜民之性,而为立国之本者,不易动摇也”(注: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杂志第1册(民国二年二月)。)。
“传统”既然对于招回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帝制权威有益,“护圣”既然可能焕发已然褪色的帝制灵光,复辟分子们当然会在维护传统与护圣的活动中乐此不疲。沈曾植鼓吹道:“窃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以立者非他,则君臣大义,尊卑上下,定位而已”(注:沈曾植:《复位奏稿》,《近代史资料》1964年第2期。);刘廷琛唱和道:“有君臣而后有上下,有上下而后有礼仪,然归其所在,辨上下,正名分,以其在于大本也”(注:刘廷琛:《致徐世昌书》。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胡思敬、沈曾植还在江西、上海筹建尊孔讲经的“书院”、“学术研究会”。他们要用孔子思想重新引导人们对于传统权威的崇拜,对于封建帝制的迷信。胡思敬曾说:“当光绪将乱之初,一二小人之邪说,可以煽动四方;今日乱极思治,安知一二君子之诚心不可挽回劫运。”(注:胡思敬:《致谢汉川石钦书》,《退庐笺牍》卷四。)他们张扬着孔子的旗帜,拉着历史的回头车,顽强地在复辟之路上艰难地行进;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抬头看一看历史应该或正在前进的方向。
为了壮大声威,蛊惑人心,他们把孔子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又以孔子偶像为号召,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913年春,在前清遗老们的策动下,江苏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典礼,到会的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注:《民立报》1913年3月1日。)。春天祭孔的香火余温尚未散尽,在8月下旬又迎来了更大规模、更为热闹的祭孔活动。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孔教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8月24日下午到9月1日上午,历时七天整。会议的内容十分饱满,但主要的还是祭孔与讲经。这次祭孔大会的盛况,是晚清以至民国所罕见的。据载,“尊亲孔圣,举国同情,赴会者竟异常踊跃”,“与祭者二千余人”,除了孔教会的各省代表外,全国各界也派人参加。此外,还有港澳地区的代表参加行礼,若干外国记者也到会观礼。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次民间组织的行为,其背景还有非常浓重的官方色彩。据衍圣公孔令贻的答谢辞,其中有云:“今幸承各同仁苦心孤诣创立此会,复蒙中央及各省各机关一体赞助,遣派代表惠临鄙邑,以观其成。从此孔教昌明,大同可致。”难怪当时有警察、兵士及民团兵丁近百人维持会场秩序。民间力量加官方色彩,才能造就如此盛典。其时,与会记者也不能不感叹:“自开会至闭会,如期七日,均秩序整然,庄敬而和乐,询难得之事也!”(注:《曲阜孔教大会盛典详誌》,《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九号(民国二年十月)。)在曲阜举行的轰轰烈烈的祭孔盛典中,既有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的支持,又有袁世凯复辟集团的襄助,他们抬着孔子偶像招摇过市,把孔子思想吹得震天价响,既聚合了复辟势力,又扩大了复辟运动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向民主革命力量叫阵示威。总之,1913年祭孔复古运动的主角是谁,其政治身份如何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却是,它在民国初年首次帝制复辟运动中在文化领域里所起的呼应作用,蕴涵着有待发掘的政治文化意义。
在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为着复辟“圣朝”的目的,揭开尊孔复古运动的序幕的时候,他们忘了,无论怎样给孔子偶像上色,也不论怎样吹嘘孔子思想具有无限的“救国”能耐,但“传统”毕竟只是传统。“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在封建社会,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以孔子偶像为化身的封建文化同封建帝制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任何一方的历史命运,都对于对方产生同样的影响。以孔子偶像和孔子思想为封建帝制的权威招魂,为复辟帝制运动提供历史的支撑点和文化的支撑力,虽然可以将复辟帝制的丑剧堂而皇之地说成是“维护中华传统”,甚至是“护圣”,但是“传统”本身在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中,毕竟是“与这种现代社会的风格格格不入的残余之物”(注:[美]E·希尔斯:《论传统》,第12页。),因此,它虽能使社会新陈代谢的局面更加激荡,更加风诡云谲,更加精彩纷呈,但它毕竟不能挽救帝制复辟必然失败的命运。这虽是帝制复辟运动的大不幸,其实也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中以“传统的权威”面目出现的孔子偶像和孔子思想的大不幸,但它实在是历史的大幸!
标签:袁世凯复辟帝制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和元年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中国尊论文; 康有为论文; 国学论文; 沈曾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