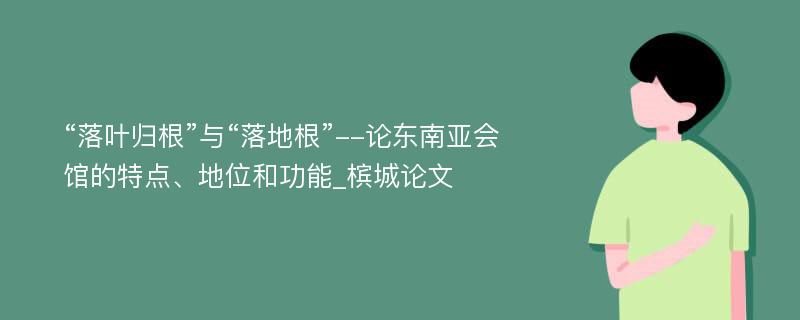
“叶落归根”与“落地生根”——论东南亚客属会馆的特征及其地位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落归根论文,东南亚论文,会馆论文,特征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客属会馆是客籍华侨社团,会员大都是同乡同宗,这是华侨在居住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客籍华侨较早建立会馆、发展会馆文化的国家,本文拟从华侨史上客家人最早建立的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和新加坡的应和会馆这两个具有典型性的会馆为例,来论述客籍会馆存在对中国和所在国所起的积极作用。
上篇:“叶落归根”——客属会馆的华侨时代
一、历史悠久的新、马等地客属会馆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中国形势剧变,清政府腐败无能,与日本、俄国以及英国、法国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大批劳苦群众纷纷出洋谋生,有的被殖民主义者当“猪仔”卖到南洋各国当奴隶,南来的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日益增多,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同乡同宗的组织。嗣后,由于形势发展和人数的日增,便逐渐组成会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客籍会馆发展极为迅速,人数众多。
这些会馆有以国内的县或镇为单位的,如茶阳会馆;有以州、府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如各地的嘉应会馆;有以州、县、府结合的会馆;也有省与省之间由于语系相同而结成的会馆,像广东客家人与福建客家人结成的会馆,如广东嘉应州与福建汀州结成一体的广汀公司;还有县与省之间结成的会馆,如广州、肇庆、惠州结成的会馆等等,这些都属于同乡会馆。另一种是由宗亲结成的会馆,这主要是由聚居在同一国度的同宗人氏,如谢氏、刘氏等等结成的会馆。根据1939年出版的《南洋年鉴》(傅无闷编)记载,清道光年间在马六甲成立的就有永春会馆、林氏西河堂等同乡同族会馆47个,其中不少是客家人的会馆,如茶阳会馆等。这些会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所在国的形势变化,有的寿终正寝,有的与其他会馆合并,有的由于种种原因被所在国禁止等等,也有的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延伸至现在。
槟城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最早建立的客属会馆。1786年8月11日英人莱佛士率兵占领槟城,15年之后即1801年(嘉庆六年辛酉)嘉应客属人士在槟城成立同乡会团体,初名叫“仁和公司”,以后又称“客公司”、“嘉应馆”、“嘉应州公司”、“嘉应会馆”,数名并用,这是一间最悠久的华侨地缘性的组织。“嘉应会馆”之称是1923年定名的,并获当时政府批准〔1〕。
开辟槟城的英国人赖特在1794年写道:“华人在居地中最堪重视,男女老幼凡三千人。他们执业不一,木匠、水泥匠和铁匠都有,也有商贾、店员和种植者。他们雇用小船,遣冒险者往邻近各国去。”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槟城人口仅1万人,最多的为马来人,其次为印度人,再次为华人。这些华人多为南来谋食者,如谢家祠碑所记:“问有谋食远方,以致身留异国,地名槟城……”〔2〕。槟城最早法官狄更斯(DICKTNS)1802年6月在致槟城屿布政使书中对当时槟城社会作了分析,并说:“此间社会上占大多数者为一般仅作小住之过路客商。”〔3〕可见当时华人并未把异域当作定居之地,中国南徙之客家人也是把所在国当作谋生之地,属“侨居”性质。还应该提及的是,在槟城客属人士建立仁和公司前一年,即1800年(嘉庆五年)在槟城华人社会中已建造广福宫。当然,在广福宫内活动的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人氏,也有一些客家人参加,不属于客属侨团。
槟城嘉应会馆之后20年,即1821年,客籍人士在马六甲成立马六甲应和会馆。应和会馆前身为梅州众记公司,由乡贤郑泰松等主持,购入鸡场街三间屋宇为馆宇。此后100多年间,在马来西亚成立了许多嘉应客属会馆,如:安顺会馆(建于1872年)、古晋嘉应五属同乡〔4〕会馆(建于1928年)、霹雳嘉应会馆(建于1900年)、雪兰莪嘉应会馆等。这些会馆均以嘉应五属人士为基础组织的同乡团体,也有以各县为单位建立的会馆,如霹雳蕉岭同乡会、南洋五华同乡总会、金宝梅江公会等,就是以聚居在同一地域的县属乡亲建立的会馆。
新加坡应和会馆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会馆之一,也是客属人士在该国建立的最早的会馆。新加坡开埠于1819年,过了三年即1822年,由刘润德公等发起创建,这是嘉应五属的同乡团体组织。该组织历任会长、副会长均为德高望重之嘉应籍杰出人士,现任会长为新加坡杰出的土木工程师何焕生先生。
新加坡最大的客属会馆为南洋客属总会。1923年春,客属人士汤湘霖等倡议组织客属总会,并积极筹建,在柏城街建造会馆,1928年冬落成,1929年秋南洋客属总会正式成立,胡文虎当选首任会长。经过努力,推动了东南亚各国成立53个客属公会组织,声势浩大,成为东南亚各国客属人士的大本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摆脱英、荷殖民统治相继独立,新加坡也于1965年成立共和国,这样才逐渐与各国客属组织摆脱关系,而变成新加坡客属最高、最权威的领导团体。该团体自成立以来的历届领导人均是客属最杰出人士,如汤湘霖、胡文虎、胡文豹等,皆声望卓著,现任会长为永定人士曾良材,1996年秋由该会主持召开第13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此外,印尼和泰国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客属会馆。例如,印尼苏门答腊岛楠榜的客属公会(建于1894年)、泰国客属总会(建于1929年)等等,在东南亚各地客属会馆有上百个,真称得上星罗棋布,形成一支凝聚客家乡情、推动当地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华侨客属会馆的社会特征
200多年来,东南亚乃至世界客属社团的兴起与发展,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取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是各国华侨历尽艰辛、艰苦创业,以及中国及华侨所在国的支持和关照的结果。为此,研究客属社团(以会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作用与文化现象是亟为需要的。
东南亚客家人的多姿多彩的社团,是中国客家人大批南迁、身处异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情境下的特异社会现象。由于客家人大都聚居粤东山区,山多田少,人口密度大,再加上以前历代政府的腐败无能,苛政猛于虎,使他们难于生存,便结伴陆续南行,而到了新的国度里,当时东南亚各国在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统治下,社会制度、人情风俗和生存方式均与国内有着很大差异,他们谋生不易,立足更难,因此便自发性地组织了同乡会馆,同舟共济,以保护同乡同宗的利益。综观这些团体,都具备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1.对象明确。一般同乡组织都以共同地域和同一客家语言为基本条件,会员具备了这两点才可以加入。例如,跨越省界的广汀公司,即以嘉应五属及大埔、丰顺等与福建省的汀州客籍人士的联合体,既有地缘联在一起的关系又有共同的客家语言。宗亲组织则以同宗与血缘为纽带;行业组织除地缘和语言共同外,还有以同行业为条件的。所以这些社会团体对象都是十分明确的。所谓“亲亲之义,百折而不散”即是共同的思想基础。
2.共同信仰。每个客家同乡社团都有共同的信仰,这是社团凝聚的思想基础。客家同乡组织大都信仰佛教,主张行善积德。慈善团体、公益团体也是以行善为怀、普渡众生为其信仰,木匠行业组织则以鲁班为其祖师爷;航海行业则以天后为其保护神。
3.共同宗旨。这些客家社团宗旨鲜明,并明确记载在章程之中,世代会馆中人均需恪守。新加坡应和会馆“应和”二字即为宗旨。“应”为嘉应之简称,亦可释为“应该”;“和”,即团结,“和为贵”、“和衷共济”。客家会馆组织都有共同遵循的准则,这就是团结乡亲,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会馆组织有着浓重的客家人的特征:团结友爱,患难相助。
4.组织严密。客家同乡会馆都有一整套章程,保证会馆的正常活动和发展。章程从会馆的目标、基金、人员、行业等各方面制订条款,组成董事会和监理会等,以保证会馆宗旨的贯彻执行。对会员中违反条规的也有责罚条款。例如,马来西亚最早的客家人会馆之一的槟城广汀公司,下属有广汀各县会馆为其基本会员,而在公司组织上由各县会馆派出人员参加公司理事会。咸丰十年的公司董事是各府县会馆14名,以及会党5名,基尔特1名,个人4名,共24名〔5〕。这里的基尔特是指影响较大的行业性组织;个人是指捐款、捐屋或捐地给会馆的有功之人。这些董事的活动都是通过章程来约束的。
5.德才兼备,精明能干的领袖人物。客家人尽管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但一般说来重视教育,文化素质较高,而到南洋的客属人士一般说来文化素质就较差了。这些人有的是被卖猪仔而来的苦力,有的是铤而走险的山民,有的是太平天国残兵或会党之人等等。要把这些人凝聚在会馆旗帜下并为之效力是较困难的。因此需要有文化素质较高、有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人物当领袖。广汀会馆章程第七条就明确规定会馆董事要“才德兼备,精明能干”之人充任。这些人士在御外抚内,“排难解纷”中游刃有余,显示出才干与实力。像汤湘霖、胡文虎、胡文豹、刘润德等客家先贤均是有世界性影响的客籍领袖人物。
6.强有力的经济实体。经济是会馆的基础。客家会馆都十分重视发展会馆产业。在建会馆之初,经济匮乏,一般资金来源均是由个人赞助及会员交会费来维持,对捐款每一笔均作记录。例如,香港崇正总会普通会员会费港币10元,每年交年费2元;永远名誉会员缴纳500元;凡交1万元者列为永远名誉会长。购置产业是会馆长久性的经费来源。例如,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在1801年就购置了大伯公街的馆址。新加坡应和会馆先后购置了义山店业以及坐落在直落亚逸街的会馆馆址,70年代还建置了应和大厦等产业,其收入作为会馆活动经费。
三、客属会馆的地位与作用
东南亚客属同乡会馆在世界客属华侨中创建会馆最早,会馆最多,历史悠久,给祖国和华侨居住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
尽管东南亚各客属会馆形态多样,结构形成也不尽相同,会馆宗旨也千差万别,但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凝结乡亲之情,联结祖国与所在国的情谊以及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1.参加居住国的抗暴斗争。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客家人就参与了印尼抗荷和越南抗法斗争,客家将领冯子材的抗法部队中就有许多越南客家华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和马亚西亚以及印尼的客籍华侨中有许多人参加抗日斗争。这些都与客籍会馆的组织和鼓励分不开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印尼爪哇成立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在苏门答腊、棉兰等地都成立了“华侨抗日协会”和“反法西斯同盟会”,客家会馆发动乡亲捐钱捐物,并动员乡亲参加当地抗日斗争〔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客籍华侨又积极参加居住国的争取独立、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为所在国的独立作出应有的贡献。
2.为居住国的经济开发作出贡献。刘果因说过一句极为形象的话:“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客家人世代居住山区,以勤劳吃苦、敢于开拓著称,他们所到之处,披荆斩棘,建设家园。印尼侨领“大唐客长”罗芳伯于1772年来到印尼加里曼丹组织客家人到坤甸采金矿,成立“兰芳公司”,延续了100多年,为开发印尼作出贡献。马来西亚保护神“大伯公”张理,他与丘兆进、马福春三人于1745年乘船飘到马来西亚的海珠屿,便在那里开发土地,死后被人尊为“大伯公”,这些领袖人物组织客家乡亲为开发所在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此外,像印尼的张弼士,马来西亚的叶亚莱等都是客家人的典范。
3.为居住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客家人原本系中原人,文化教育事业较发达。南徙后,他们虽然历尽艰辛,忙于耕种糊口,但对教育却极为重视,宁愿饿肚子也要送子女上学。客家先民来到南洋后,他们感到南来客人日众,教育后代变成当务之急,于是他们率先集资兴学。新加坡应和会馆在会馆总理黄沄辉、汤湘霖等领导下,于1904年率先成立应新学校,据新加坡著名教育家谢戚莱亚博士(D.D.CHELLAH)称:“新加坡之新式学校,最先建立的是应新学校,然后一连串的华文小学相继成立,由一九○六年至一九○九年之间养正、启发、端蒙、道南分别诞生。”〔7〕在此前印尼客籍侨领在巴达维亚的中华会馆创立了第一所新式学校——中华学堂〔8〕。此后,印尼华侨、华人纷纷筹资建校,到1949年已达724所,学生有17万人。华侨会馆办学校,提高了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所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海外华侨不仅办学,而且办报。据记载,东南亚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是新加坡华人薛有礼于1881年创办的《叻报》,1932年停刊。客家人胡文虎是“报业大王”,后迈向“报业巨子”之路,他从1928年创办《星报》以来,以后又陆续创办《星洲日报》、《星槟日报》,并接办新加坡《总汇报》 及曼谷的《星暹日报》、《星暹晚报》等,有力推动东南亚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些文化活动中,客家会馆中人大力推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4.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侨居在国外的客籍先民,对祖国一往情深,关切祖国的命运,情系中华。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客籍华侨在海外为之募捐提供经费据统计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成功,客籍华侨捐款达700—800万港元之多〔9〕。客籍华侨还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梁密庵、谢逸桥、温靖侯、温才生、谢良牧等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东南亚客属会馆也纷纷用各种形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他们抵制日货,印尼华侨、客籍侨领、中华总商会会长丘元荣号召华侨抵制日货,使用国货,东南亚各国华侨纷纷响应。东南亚各国客属会馆还纷纷捐资支持国内抗战。1938年南洋各地成立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赠祖国难民总会”,各地客属会馆亦参加这一运动。据民国二十九年《梅县要览》记载,东南亚部分华侨团体捐资八次约8万元,还捐大米和大批枪枝、药物等。在这时期,客籍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抗战,出现一批奋勇杀敌的热血儿女。
客籍会馆对祖国经济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些华侨根在祖国,在客家山村往往留下父母、妻儿子女,只身闯南洋。客家人有个特点:乡土观念强,上孝下爱。他们赚了点钱便千方百计寄回或托人带回国内,置地购屋、奉老养小。奔走于南洋与祖国之间的“水客”便应运而生。这方面客属会馆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客籍侨领还身体力行,捐资回内地办学办医院和发展实业等。马来亚侨领胡文虎、胡文豹昆仲及印尼侨领张弼士等都对祖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以“实业兴邦”著称的张弼士本世纪初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公司,产品在国际上得了大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在广西、广东等地兴办许多实业,为发展祖国经济呕心沥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东南亚各国的客属会馆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居住国遵纪守法,与居住国的政府和人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开展居住国的经济和建设,为居住国的抵抗外国侵略势力和争取民族独立流血流汗,功不可没。这些也得到居住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但是,这些客属会馆以及客籍华侨,都是以华侨身份参与的。他们的根在故乡,中国是他们的祖国和归宿。他们大都把在异国的事业当作谋生手段,最终还是要“叶落归根”、魂归唐山的。这一时期客属会馆多数冠以“××(国家)客属华侨公会“或“××(国家)客属华侨总会”名称,而他们的居住国也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有时对他们的社团活动乃至经济活动给予诸多限制,有些国家某一时期也会发生排侨事件,有的排侨事件还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这样反而促使这些华侨加深自己的侨居心理,认为自己处境如浮萍,无安定感,从而更加从心理上依赖祖国。而在祖国的亲人又使他们魂牵梦萦,所以当时的客属会馆事实上是中国的客家人在侨居国的民间组织,是维系乡情、排难解忧,维系华侨居住国与祖国民间关系的重要桥梁,他们对居住国和祖国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下篇:“落地生根”——客属会馆的华人时代
一、从华侨到华人:身份与地位的确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般以1945年为年代标志)是客属华侨会馆转向客属华人会馆的标志性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纷纷宣布独立。独立后国家的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积极投入重建家园的建设中去。由于华侨在东南亚国家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经济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研究华侨政策及对策。由于历史原因,以往不少国家的华侨有双重国籍,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大都不主张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他们要求华侨转为单一国籍,主要是加入居住国国籍,采取融化华侨政策,即把华侨归化为其本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也宣布不再实行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而许多华侨由于已在居住国安家乐业,有了自己的房屋、产业和事业等,他们为了生存和自身的发展,纷纷加入居住国国籍,变为居住国的公民,这样大批华侨便融入居住国的民族大家庭之中。马来西亚政府与华侨领袖达成协议规定:“许多民族的华人,将自动地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或者通过申请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在印尼1945年11月1日公布的《印尼共和国宣言》中说:“我们将实行我们的独立政策,我们的国籍方案是使亚洲侨民及欧洲侨民后裔,迅速成为真正的印尼人,成为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我国政府对于华侨和华人的态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访问缅甸时就曾指出:“作为华侨就不是缅甸公民,应该有华侨的态度,侨民应该不参加缅甸的政治活动,只是侨民内部和缅甸人民来往是可以的,但不能参加政治活动。譬如他们的政党、选举、缅甸的一切政治组织,我们都不能参加,这是应该分开的一个界限。”对于选择居住国国籍的华人,他们已经不再是华侨,而是居住国的公民,周恩来明确指出:“凡是在政治上如果我们已经选择了缅甸国籍和成为缅甸公民,就不应该参加华侨团体。作为华侨和作为朋友亲戚要有个界限分清一下,这样大家就相安无事了。”〔10〕
由于东南亚各国的独立后大批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以及中国政府不主张双重国籍,使华侨与华人的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据统计,东南亚客籍华侨、华人大概有410万人,当华侨、华人居住国未独立前,约有123万人加入居住国国籍;当他们所居住国宣布独立后,先后有369万人加入居住国国籍,占华侨总数的90%。在客籍华侨最多的印尼,客籍华侨加入印尼国籍的有110多万人,占客籍华侨的90%以上〔11〕。
由于国籍的变化,大批华侨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他们不再具备中国籍的身份了,告别了以往的祖国,认同了新的祖国。这对他们来说虽然是痛苦的抉择,但由于他们原本就在居住国安身立命,与当地政府和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早已融进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因此在各方面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再加上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对原来华侨社团有着诸多的限制,华侨入籍后这种限制有质的变化,即当地政府不允许已经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社团仍以华侨社团形式存在,限令他们重新按居住国的法令以居住国民社团身份重新注册登记,这样所有客籍社团全都去掉“中国”及“华侨”字样,而改以居住国冠名的客属会馆。由此而由华侨时代转变为华人时代的客属会馆了。
二、亲缘与血缘:华人时代的客属会馆特征与地位
华人时代的客属会馆与华侨时代的客属会馆比较,既有血缘关系,又有着根本性的变化,它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1.“忠”的观念的明显转变。客籍华侨在加入所在国国籍后,立刻从中国公民转变为他国公民。这对有强烈的祖国观念和忠贞观念的原中国公民来说,完成这一转变有着痛苦的心理历程。他们原先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瞬间变成了“他国”,或者可以这样说变成了母国,引起的心理震荡是巨大的。但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离乡背井闯荡异国谋生的客家人,也敢于正视这种严酷的现实,毕竟以往视以“异国他乡”的新的祖国是他们赖于生存之地,有恩于己的国度,客家人对“恩”是不会忘怀的。由于原来效忠的祖国变成了母国,华语变成了母语,“忠”的观念也就作180度的大转移,他们应该也必须效忠于新的祖国。
这样,他们就必须以居住国公民身份来从事各种活动,同时也享受居住国公民的各种待遇。客属会馆的会员在完成国籍上的转变和组织上的转变后,其活动的内容、会馆的宗旨等都必须在效忠新的祖国前提下展开,从而会馆也便起了质的巨变。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华人的传统观念也有根本性转变。以往许多客籍华侨都以在外谋生,赚了钱后荣归故里为自己的夙愿,即在家乡购田置屋,待到年迈力衰时“叶落归根”,返回故里。而加入居住国国籍后,尽管老一代还念念不忘祖屋祖地以及家乡亲人,但由于落籍新的国度,不可能再“叶落归根”,只能“魂归故里”了。也就是说,这些客籍老华人必须从传统观念的“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在新的国度里扎根。而这时期的客籍会馆对会员的这种观念转变起了调节、磨合和促进作用。
2.产业的转变和发展。由于华侨归化为居住国的公民,原来华侨社团的资产也就从“侨产“转为居住国华人社团的资产。也由于华人社团享有居住国公民团体的一切权力与义务,居住国政府给予保护和照顾,使许多华人的会馆产业得以发展。新加坡应和会馆1958年统计有荷兰律双龙义山地皮、会馆馆址、直落亚逸街店面等产业11座,后来除会馆馆址作为文物给予保留外,其余先后为政府征用,政府给予赔偿,该会馆将赔偿金购置地皮建筑楼高19层的应和大厦,出租收益为会馆经费。据了解,客籍华侨归化居住国后,由于各方面努力,会馆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成为会馆的重要经济来源。
3.会馆的文化教育日趋发达。东南亚的各国客属会馆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在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前,会馆办的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异常发达,例如印尼雅加达的巴城中学,新加坡的应新学校等有相当的知名度。各国独立后,由于各国政府的需要,压抑甚至取消华文教育,有的甚至禁止开办华文学校,印尼政府就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华文教育,连华人占大多数而又以华人为政府首脑的新加坡政府也采用压制华文学校的政策。经过多年的严厉措施以后,许多国家发现中国政府影响日大,华文影响也日增,于是有些国家有条件地重新允许办华文学校,在这方面客籍会馆和其他会馆一样积极办学,力促华文教育的发展。客籍会馆还努力发展文化交流,如,举办客家山歌演唱会,邀请梅州汉剧团、山歌剧团访问演出等,南洋客属总会自己组织乐团在国内演出。1995年会长曾良材还带团到西马作亲善交流演出。
4.寻根问祖的活动逐年扩展。老一代华人大都来自中国,他们生活在客家山村,长在客家山村,到南洋落脚后往往还要赡养国内老小,还要购置产业,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根在唐山。当他们遽然改变国籍后,心理失衡,加深了对故国山河、亲朋至友的思念之情。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对祖国籍地的淡薄,更使他们燃起寻根问祖之情,因而各种寻根问祖的旅游团应运而生。这几年海外客籍会馆组团来华祭黄陵,到中原寻根,到梅州、汀州祭祖的客籍人士难于计数。各国的客籍会馆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组织工作。
5.世界性的客属组织迅猛发展。本世纪20年代末,南洋客属总会成立以后,推动了英、荷两属53个客属公会的建立,各国容属总会之间关系密切。但东南亚各国独立后,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与各国客属会馆关系逐渐脱离,各自为政,各自发展。1921年9月香港成立的崇正总会,在美国、加拿大、印尼、印度、澳洲雪梨、南非、毛里求斯等国成立了分会,成为世界性的客家人组织的联合体。1971年9月28口是香港崇正总会成立50周年纪念日,该会特邀世界各地47个客属社团250名代表,大会决定将此次大会定为“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以后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主要城市举办,第12次恳亲大会于1994年在号称“客都”的梅州市举行,第13次大会于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这标志着世界性的宗亲会也在发展,东南亚有些宗亲会组织还组团到中国梅州、汀州及中原寻根。以东南亚各国和香港为主体的客属社团正走向世界性的联合体,这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华人时代会馆社团组织的新走向。
6.捐赠和促进客家地区经济发展的投资。在这方面东南亚华人会馆作了许多组织工作。南洋客属总会名誉会长姚美良先生,就多次组织同乡团体对中国作大量的捐赠活动。他还组织乡亲筹建扬州客家工业城。由于东南亚各国及其他各国华人会馆的努力,对祖居的梅州、汀州等大量捐赠,修桥筑路,办学校,建医院,开工厂,辟农场,作了大量的公益事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东南亚各国客属会馆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程。过去,客属会馆对所在国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客属会馆融入所在国的民族大家庭之中,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对有着血缘关系的母国的联络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东南亚客籍会馆的功绩无疑会载入史册的。
注释:
〔1〕《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第13页。
〔2〕邝国祥:《成立一百五十年的本城嘉应会馆》,原载《光华日刊》民国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3〕载民国卅九年二月十六日《光华日报》。
〔4〕五属指广东省嘉应州所辖之梅县、蕉岭、平远、兴宁、五华这紧邻的纯客家五县。
〔5〕以上材料见今堀博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第3章。
〔6〕〔9〕〔11〕罗英样:《飘洋过海的客家人》,第47~48、51、31页。
〔7〕见新加坡应和会馆16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应和会馆史略》。
〔8〕《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10〕《华侨历史》第1期,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