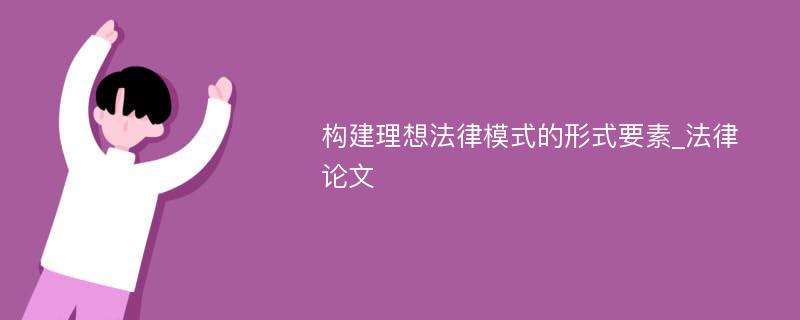
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形式要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件论文,形式论文,理想论文,模式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学论坛
一、引言
一个理想的法律模式之建构,涉及到许多相关的内容,诸如: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需要哪些基本原则?在这些基本原则指导下,又需要具备哪些构成要件?这些构成要件又具体分解为哪些方面?等等。关于前一问题,笔者曾在《理想的法律模式之建构原则》一文中作了一些研究,提出了科学性原则,适时性原则,现代性原则,民主性原则等;①而关于理想的法律模式之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应由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两大部分构成,内容要件反映法律的本质性属性,形式要件则反映法律的许多技术性特征。
关于内容要件,笔者在《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内容要件》一文中作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法律模式的建构,应具备、体现和包含以下基本要素:即民主要素,自由人权要素,公平正义要素,法治要素等等。②本文则着重从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形式要件方面作些探讨,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关于理想的法律模式之构成要件体系。
二、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形式要件
首先,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命题作些说明。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内容要件,是指在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创制中,应包含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体内容和要素,也即法律模式的内容设定和构成要素,并且要将这些抽象的内容要素转化成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条文规定;而本文所欲探讨的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形式要件,则是指为体现诸多实体内容和构成要素,法律模式所应具备的形式上的要求。形式是法律模式的载体。离开形式这一载体,任何法律就不成其为法律。再递进一步,如果没有适当的、合理的形式表现,法律模式也就难以成为理想的模式,那些理想的法律构成内容要件也就无法得到正确的表达和表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分析,在理想的法律模式的建构过程中,内容固然重要,但形式也不可或缺。现代法在其创制过程中,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便是:既要在内容要件上进行有深度有广度的挖掘,又要高度重视其表现形式(即形式要件),寻找最适当、最合理的法律表达(现)形式,完成其法律创制任务。此外,本文所探讨的法律模式,一是指成文法律;二是指成文法律中的理想法律模式。具体理由笔者曾在该课题的前期研究中有所说明。③
按照以上对形式要件的理解,笔者认为,一个理想的法律模式在其建构过程中,应具备以下形式要件:
1.语言的明确性
语言④是文化的重要元素。对于法律而言,语言更是构成其存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元素。语言是法律的载体,是法律的“建筑材料”,是法律能够被创制,得以为世人所知晓的工具。法律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被表达和表现出来。因此,研究法律中的语言,是研究理想法律模式形式要件的首要问题。
法律中的语言,按其内容划分,约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有特定法律意义的语言,如缓刑、假释、故意、过失,等等,这类语言我们将其称为专门法律语言,或称其为法律术语。法律中的这些法律术语,有其特定的法律含义,非经法律学者和教育,一般公众是难解其义的;另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言。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表达,离开社会生活,法律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同样,离开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很难想象一部法律能够存在。倘若一部法律仅由那些专门法律术语组合而成,那无疑犹如一部“天书”,谁也难解其义,难破其谜。因此,日常生活用语是法律中的语言的重要类型,可将法律中的这种语言类型称为日常语言,这些日常语言一般来讲为公众所知晓和理解。但对法律的理解歧义也往往恰好出在这些日常语言上;第三种则是由现代立法所带来的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即法律中的科技语言。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现代法调整范围的扩大,科技领域也直接成为法律调整对象,于是,一些专门的科技语言便成为法律(尤其是科技法律)中的新的语言“品种”。法律中这些科技语言,一般公众难解其义,一般法律工作者若非受过专门科技教育,也不明其义,而只有那些受过专门科技教育的人,才懂得这些语言的含义。比如:维也纳1979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第一条(a)的内容是:“‘核材料’是指:钚,但钚-238同位素含量超过80%者除外;铀-233;同位素235或233浓缩的铀;……”(b)的内容是:“‘同位素235或233浓缩的铀’是指含有铀同位素235或233或两者总含量对同位素238的丰度比大于天然存在的同位素235对同位素238的丰度比的铀;”⑤以上国际公约中谈及到的“钚”、“铀”、“同位素”、“丰度比”等概念(语言),只有受过科技教育的人才能理解其义。
以上三种法律中的语言类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也作了如此的划分。但该辞典将三种语言统称为“法律语言”,并且许多立法学著作、教材也称其为“法律语言”、“立法语言”或“立法文字”等。笔者认为,准确的命题应是“法律中的语言”,而法律语言只是指法律中那些专门的法律术语,它是法律中的语言类型之一种,也是最具法律色彩的一种。离开法律术语,法律便不成其为法律,而可能成为别种属性的事物。《牛津法律大辞典》在“法律语言”辞条中解释道:法律语言部分地是由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词组成,部分地是由日常用语组成的,还有某些科技术语。而那些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词,在日常用语中即使有也很少使用,如预谋、过失、非法侵害等。⑥该辞典在“法律术语”辞条中,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法律经常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按照法学家的意愿形成一种可与医学或工程学的词汇相比的精确的技术词汇,以有助于明确的思维和推理并提高法律效能;二是根据非专业立法者对法律、法律术语及其涵义的无知,有时则按照其意愿使法律为普通人所理解,并根据某些法律部门的需要,使法律以特定专业人员、商人和其他非专业人员所能理解的术语阐述。在较小程度上,法律使用技术术语,如保释、地役权、流通票据。这些术语不是日常用语,因而具有相当精确的涵义。但在很大程度上,法律使用的是日常用语,如协议、疏忽和过错。这些用语产生的含混大多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这些用语不仅具有各种一般的含义,而且具有不同于日常用语的法律上的习惯之意、含蓄之意和言外之意。此外,法律术语如改为通俗文字,则必然会产生某些意思上的曲解。⑦这说明,法律术语是最能体现法律之所以是法律的具代表性的语言类型,最具法律色彩,但它不是唯一的。法律术语须和日常语言、科技语言等组合,才能形成法律。
从形式上讲,语言是法律的载体,是法律的建筑材料,甚而可以认为是法律(形式意义上)的生命。在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J.Gremas)的符号法学中,甚至把语言当作法律性质的中心。⑧因此,一个理想的法律模式在其建构中,就应当高度重视语言这一形式要件,并对其提出较高的要求。这个要求概括地讲,就是语言的明确性。
马克思曾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⑨我们当然明白,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首先是对法律的实体内容要件提出的要求,但也并不排除它同时也是对法律的形式要件提出的要求。“肯定的、明确的”,首先应表现为法律中的语言表达是肯定的,明确的。这一形式要求,是同法律的性质、目的和作用相联系的。
创制法律,颁布法律,其首要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理解和实行。要使法律为人们所理解,首先就应该使法律中的语言具有明确性。若一部法律,其所使用的表达的语言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就难以达到使人们理解的目的,从而给法律的实行带来困难和混乱。因此,历史上许多法学家都对法律语言的确定性给予了很高的重视。例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针对封建时代的法律指出:法律的含混不清是一种弊害,如果法律是用人民难以理解的语言写成的,而且使人民不能判断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的界限,并从属于少数人,那么这种弊害将达到极点。他认为,法律中模糊不清的词句必须修改。⑩18世纪的法学家约翰逊讲到:“法律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法律为每个人规定了行动准则,描述了使他能获得社会支持和保护的行动方式。法律若要成为行动的准则,就须为人们所知;就须是持久稳定的。法律是民权的准绳,但若这一准绳不确定,就决不可能确定所测度的事物的限度。”(11)17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霍布斯也曾提出:主权者应当注意制定良法。但什么是良法呢?……良法就是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12)近代自然法学也提出:“必须用完全符合人的理性和人性的法律来代替旧法律或者对后者进行改造”,并认为新的法律应当是成文形式,内容完备详尽,表达明确和编排合乎逻辑,能使每个公民都能理解和掌握法律。(13)著名的德国比较法学家K·茨威格特、H·克茨著的《比较法总论》一书,在评价《法国民法典》这一具历史价值的法典时讲到:“拿破仑对立法工作的参与多少使《法国民法典》渗入了他那种伟大气魄,而法典的语言也因之而充满力量并激动人心:直截了当而一扫教理式的推断。”“《法国民法典》在世界上的传播得力于它出色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富有弹性及变通灵活的表达,总之,终究也得力于它的质量。”(14)我们从另一本著作中得知,拿破仑当年在立法中要求他的法典既清晰完善,又通俗易晓,象《圣经》一样为人人皆知,使任何个人的评注,任何法官解释都成为多余。效忠法国的法官所奉行的信条是:“我不知道任何民法,我只知道《拿破仑法典》”。当拿破仑得知第一本评注出版时,他惊叫道:“我的法典完了!”(15)
在一些立法学著作中,对法律中语言的明确性进行了一些概括。比如,有一本著作对立法语言的特点和要求概括为:准确、简明、严谨、规范、肯定、朴实;(16)另一本立法学著作将法律的用语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明确易懂,简明扼要,严谨一致。(17)上述著作都指出了法律中语言所应具备的基本要求。法律中的语言以及法律中所采用的文体是一种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书信,以及法律论文的特殊语言和文体形式,它不允许夸张、比喻,忌讳情感色彩,讲求严谨、求实、明确、易懂。经过历史的锤炼,法律中的语言已经成为各种语言文体中最具精确意蕴的文体类型,以致世人对法律形成一种呆板,无生命的印象和误解,法律家被当成没有感情色彩的一类人的代名词。
法律的目的首先在于理解。但由于法律中日常语言的多义性和法律术语的专门性,给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带来困难,这样,对法律的解释便应运而生。按理说,一部法典,解释越少,说明法典中语言的明确性程度越高。但法律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不经解释便非常明确的法律。法典中语言的另一要求是精确性,这就决定了对法典中的语言含义不可能作细微的说明,一般是以高度概括的专用法律术语来表述。这样,在法律颁布时或颁布后,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就成为必要。解释的目的仍在于理解,这种理解不允许多义性和歧义性,而只能以一种为立法者的意肯所认可的含义去理解,以排除其他含义的理解。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解说。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法律生活中,司法实务的操作者——司法者(法官)、辩护者(律师)的大部分工作,是在从事着一种如何理解法律、解释法律以及如何实施法律的工作。法庭上的唇枪舌战,你来我往,一方面是对事实的认定,更重要的则是对如何理解法律而展开激烈的争辩。这都导源于法律中语言的明确与否。由此可见,法律创制中语言的明确性既是公众理解法律的前提,也是司法中实现公正审判的前提。一个不明确的法律表达最易成为随意解释的漏洞和空隙,也可能是产生不公正审判结果的首要因素。
2.法条的具体性
法条的具体性,是建立在语言的明确性基础上的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的第二个重要形式要件。这一形式要件是同法律的作用相连带的。法律是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是一个准绳,这就需要法律明确其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而这一切都需要以具体的法律条文表达出来,才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和遵循,才能达到法律的目的。
一部法典,总是具有一种或多种立法意图和目的,而这些立法意图总是要通过语言、法律条文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说,语言是法律的基本元素,那么,法律条文就是法典的基本单位。法律中的各种具体制度,如二审终审制度、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陪审制度、上诉制度等等,都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法律条文体现出来的。而这些法律条文通过语言形式,将立法者的意图和目的表达了出来,渗入其间。因此,对立法意图的理解,就具体化为对法律条文和条文中语言的理解。正如一位学者提出的:“立法意图是由文字来表达的。由此,社会成员对立法的接受便成了该社会成员对立法文字的解读。他们对立法文字理解的真伪程度直接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实际效用,不被理解的法律是无效的法律,对法律的误解实际上是对真实法律的否定或取代。幻想立法文字能自然而然地再现于社会生活是对人与法律规范关系的误解。”(18)
法条的具体性要求排斥与它对应的另一面——即法条的抽象性。如前所述,法条是一种行为规范和准则,它必须是具体地、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就不能用抽象的语言去表述。一般来讲,抽象语言是学术语言的特点,学术研究有时需要一种高度概括性、宏观性和覆盖性的语言;而法条是一种具体规定,法条不是法律原则。当然,在一部法典中,有的在前面有“序言”内容(如中国现行宪法),有的在前面有“基本原则”内容(如中国民法通则第一章),在上述这些法律结构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较为抽象的语言表述,这是应该允许的。但在涉及人们行为、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中,如果使用抽象语言,那势必造成人们混乱,无所适从,进而导致行为上的混乱,这与法律的要求是相悖的。比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11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条是对“成年人”的法律界定,并对“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了法律确认,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法条中的年龄界线,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标准。如果不作这一具体限定,而采用一抽象概念,人们便无法知晓“成年人”到底是指什么人。又比如,《民法通则》第三章第37条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象诸如此类的法定资格规定,必须详尽、具体,使人们明了要成为“法人”,应该具备哪些法律条件,否则,极易与一般社会组织、团体相混淆。
《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与“法条”相近的“规则”概念时讲到:规则是关于某些事项的法律规定的陈述,通常比学说或原则更加详细和具体。当然,某项陈述是学说还是原则,或者是规则,不同的人常持有不同的意见。……在所有情况下,规则的精确文字表达都非常重要。(19)而对“规范”概念的解释则是:团体成员所接受的行为规则或标准。规范比道德价值或理想更为具体,但不及法律规则具体。(20)以上对“规则”和“规范”的解说,都说明了作为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表现形式的法律条文不同于一般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原则,而是对人们行为及其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因而要求必须具体化、明细化,便于人们掌握、理解、运用和操作。那种抽象的法律条文表述,只会制造混乱,造成司法操作上的各行其事,背离立法初衷。
3.内容的易懂性
法律是用来体现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和目的的一种载体,因而它是一种内容的表达。而这种内容必须为社会公众或法律的接受者所懂得,所明白。仅此要求还不够,还应使法律的内容为社会公众所“易懂”,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法律内容的易懂性,是建立在语言的明确性和法条的具体性之基础上的一个更高的形式要求。
不论是语言的明确性、法条的具体性,还是内容的易懂性,都是同特定社会法律接受者的文化接受力密切相关的。在一个文化素养较高、法律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接受能力相对就高;反之,接受能力就低。而作为法律创制者,就不能不考虑该社会成员的文化接受能力。过多的专门术语,过于晦涩的文字语言表达,常常会使法律接受者如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难以理解。而“不被理解的法律则成为无效力的法律”,法律形同虚设,最终变成同社会公众相脱离的事物,甚至可能成为同公众意志相异化的产物。此外,法律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因此它就须考虑普遍社会成员的接受能力,要选取一个合适的“度”。即它不能仅顾及社会中文化程度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的那一部分人,这样会使法律同大众脱离,变成少数“精神贵族”的接受物;也不能一味地迎合、迁就社会中文化程度较低接受能力较弱的那一部分人,这样只会使该社会法律文化水准越来越低,阻碍法律的不断进步。因为这两部分人都只代表了社会成员中的少数。而占大多数的则是社会中那些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同理,法律是由法学家、立法专家等制定的,但法律并不是专为他们制定的。法律是为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制定的,这就是法律的普遍性所在。因此,法学家、立法专家在制定法律时,要时刻想着全体社会成员这个为法律普遍适用的对象。
同法律内容的易懂性相关的还有如何使用国际通用术语的问题。为了做到内容的易懂性,法律中应禁止使用地方方言和古代用语。但对待外国术语,则情况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对外国术语应惯用。但对由外国术语发展演变的国际通用法律术语,则不能持排斥态度。现代法已不单单是只涉及一国领域,“国内法”概念只具有相对意义,法律已成为国际属性的产物(此处区别于国际法)。任何一个国内法律,都有可能成为涉外事件和行为中的冲突法规范和准据法规范。因此,在国内法的创制中,对于国际通用的法律术语,不能排斥,而要采用、并用。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密切,法律的国际化趋势日显突出,法律创制中对国际通用术语的采用会越来越多。问题在于,在将国际通用法律术语翻译成本国语言时,必须做到精确,达意,不使其产生歧义。《牛津法律大辞典》指出:在(世界各国)现代法律体系中,法律语言中有很大比例的字和词,是来源于拉丁语、法国法语和英语等语系。(21)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许多法律术语,实际上也是从西方继受而来,采用了国际通用法律术语。像法人、自然人、公民、权利、标的等等。
总之,法律内容的易懂性是从法律的目的、功能角度提出的一个必然的要求,而这一要求则是建立在语言的明确性、法条的具体性基础之上,并且还取决于该法所适用的社会成员的文化接受能力。现代立法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既要赶上世界法律文化的发展水平和进程,又要采用为国人所明白易懂的法律表达方式,将法律的诸多内容表现出来。从这一点来讲,立法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立法者所从事的是一种高技艺的工作,这种技艺不同于一般的工业制作技艺,或美学、艺术意义上的技艺,而是一种准确的贯彻立法意图(人民意志)、熟练地驾驽语言、文字,以最精确、合理的形式将法律内容表述出来的技艺。这是需要很高的文化修炼、法律修炼方能达成的。
4.结构的合理性
法律结构,按照立法学通说,分为法律的内容结构和外部结构两大部分。内部结构是指法律规范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外部结构则是指法律的外部表现方式。本文中作为形式要件之一的结构的合理性,则是指这两种结构类型的合理性,侧重于法律的外部结构。
一部法典,本身就是一个结构组合,一个体系。在法律创制中,如何合理安排法律的结构,使其成为层次分明、逻辑合理、前后照应、严谨一致的有机组合和排列搭配,是立法中一个具有较高难度的技术性问题。对于法律的结构,在经历了漫长的法律史实践之后,人们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于法律结构的合理配置已形成一些知识。比如,在法律的名称上,我国所采用的以法律内容的性质和地位相结合的命名法;在法律的制定时间、发布时间、生效时间、发布机关等方面,已采用国际法律惯例;在法律的正文结构方面,人类通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已总结出卷、编、章、节、条、款、项、目等层次结构体系,以及总则、分则、附则、附录等结构内容。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人类的经验合理地配置在法律的创制之中。
法律结构不单单是个法律形式或法律技术问题,它同立法意图密切相关,也同不同时期社会需求相联系。比如,各国宪法中对于公民权利义务的排列位次,反映了各国在此问题上的一种态度;又据报刊披露,我国刑法修改的一个议题是,将公职人员犯罪一章前置,反映了公职犯罪已成为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律结构上的种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社会对某一类问题的关切程度以及其重要性位次变化。
就法律的内部结构而言,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许多法律缺少具体的法律后果或法律责任条款,尤其是在大量的经济法规和行政法规中。法律的最主要体现是致使行为人明确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若法律规范缺少这一重要要素,那就从根本上瓦解了法律的功能。而我国现行立法或者没有明确的责任后果,或者援用其他法律之规定,使许多法律成为弹性很强的条款,难以起到约束和制裁之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法律中用一些抽象的语言表述了法律后果,但又缺乏具体的程序上的保障,使这些法律后果成为无法实现的虚设。因此,一个理想的法律模式,要做到结构的合理性,既要解决法律表现方式的外部结构的合理性,又要使法律规范内部结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实现立法意图。
5.体系的完整性
前述四个形式要件,是就单个的法典、法规提出的形式要件要求。而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只存在一个单个法典或法规。现代社会的法律是成体系的。“法律体系”这一概念较准确地概括了现代社会法律存在的现状和概貌。因此,理想的法律模式还有对法律体系的要求,即体系的完整性。
关于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尤其是关于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我国法学界已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比如,法学家郭道晖先生提出:“在设计立法体系和制订法律文件时,要明确其母子、源流关系,主从关系,使立法体系层次分明,位阶有序,形成一个金字塔似的稳定、有序结构。”(22)并提出立法体系要贯彻结构优化原则:“立法体系不是一大堆法律、法规、规章的简单堆砌,而是由这些基本要素,按一定的门类、源流、主从、平等或不平等的关系,平衡配置,优化组合而成。”(23)而体系的完整性则指:“一要门类齐全;二要成龙配套;三是备而不繁。”(24)
创制一部好的法典,不是一件易事。而要创建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则更加艰难。社会生活在不断变化,法律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适应社会生活,就得不断对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有时可能是结构性的调整,有时则可能是革命性的变革。淘汰旧的,创制新的,法律创制的任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停止。法律的内容在不断变化,法律的形式也在随之变化。虽然相对于内容的变化而言,法律形式的变化可能要缓慢一些,但新的内容总是要寻找到新的更加适合的表现形式。法律的进步无非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以上的探讨只是初步的、粗浅的,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法学界,立法界的努力探索和追寻。
注释:
①详见刘作翔:《理想的法律模式之建构原则》,《法商研究》,1994年第6期。
②详见刘作翔:《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内容要件》,《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③详见刘作翔:《法律的理想》,《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
④在立法学上,有些学者采用“文字”这一概念表述,尤其是在讲述成文法时,这一概念更靠近些。笔者采用“语言”这一概念视同“文字”概念,主要是指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
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增补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⑥⑦(19)(20)(21)《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页,第877页,第790页,第642页,第515页。
⑧见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
⑩(17)见吴大英、任允正著:《比较立法学》,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第233-236页。
(11)鲍斯威尔著:《约翰逊传》(1772年),引自《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7页。
(12)〔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0页。
(13)沈宗灵著:《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14)〔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185页。
(15)(18)参见黎建飞著:《立法学》,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第150页。
(16)见谷安梁主编:《立法学》,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204页。
(22)(23)(24)郭道晖:《建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原则与方略》,《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第37页,第39页,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