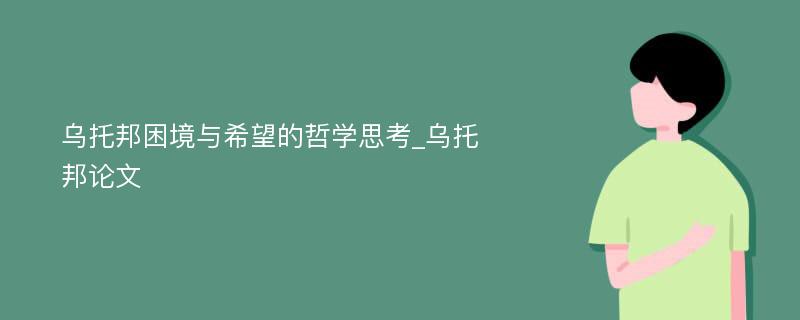
乌托邦的困境与希望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困境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12-0047-06
乌托邦是人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和执着追求,在追求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所凝结的乌托邦精神代表着人类超越当下现实的永不枯竭的批判力量,体现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乌托邦意识匮乏的时代必然使人的精神衰退、灵魂麻木,人们的生活必然处于俗不可耐的欲望满足的简单快感中。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现实化和世俗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越来越空虚和无助,以至于人们都在逃避面对面的内涵丰富的交往世界而退缩到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借助计算机时代的网络技术,“虚似实在”短暂地弥合了人们的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然而这一短暂的弥合并不能消解人们的精神困惑和苦闷,人们也越来越远离自己的生存根基。现代社会中人们非常现实地活着,然而却感觉得很累、很痛苦,大有“不可承受之轻”之感。此时,人们忽然发现,久已远去的乌托邦的理想和浪漫想象,仍然是现代人摆脱不掉的一种古老情结。乌托邦的这种精神不仅仅针对个体而言,同时,它也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继续前进的动力。因此,在现代社会,对乌托邦进行重新反思,不仅关涉我们人类当下的生存,而且与人类的未来密切相关。这里,本文仅从乌托邦的基本规定出发,探讨一下现代性语境下乌托邦的困境,以及乌托邦与人类未来希望的价值关系。
一 何谓“乌托邦”
众所周知,“乌托邦”(utopia)一词是由两个希腊语“ou”(无)和“topos”(场所)构成的,本意表示“无场所”、“没有的地方”,亦即“乌有之乡”。它是由托马斯·莫尔最先开始使用的。但乌托邦观念(也可以说乌托邦思想、乌托邦价值和乌托邦精神)却是由来已久了。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柏拉图就设计了一个现实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的社会模式。他认为,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尽管不可能在现实中得以存在,但它却是应该比现实更加真实可信的,它存在于人的心中。现实只能是对理想社会的粗糙的模拟而已。赫茨勒(J.O.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一书中,把乌托邦的思想追溯到柏拉图之前的希伯来先知那里,认为他们在面对当时不合理的现实时同样能够审时度势,提出重建社会理想的路线,并勾画出一幅完美的未来图景。赫茨勒认为,乌托邦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认为,现实社会是一个并不完全真实的社会,它有必要而且可能进行人自身的改造以符合某种合理的乌托邦社会理念,最终使社会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
但严格地讲,赫茨勒所指出的先知的思想只能说是乌托邦思想的萌芽,还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想,因为乌托邦虽然是人的想象的产物,但它更多的却是人的理性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出现的,而且乌托邦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人自身内在的主体性力量,而不是完全依靠神的力量以神话的方式获得拯救。也就是说,乌托邦思想根源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但又与后者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即使是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它所描述的理想社会依然必须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才可能接近或通达理想的“上帝之城”。
欧洲人发现新大陆这个重大的事件之后,特别是在17世纪进步观念等等启蒙精神的推动下,乌托邦观念不再是指某个世外桃源的、与人的现实无涉的空间概念,而是成为了现实的人可以期待实现的时间范畴。形象地说,乌托邦不再是人幻想的一个“好地方”,而是人希望出现的“好时光”。乌托邦观念的这种转变与人的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人的实践的能动性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乌托邦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生活乐园与人的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近,与人的实践活动也密切相关。这就是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设计美好的社会蓝图、积极尝试的同时,进行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社会试验的原因所在。他们都希望自己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能够最终实现。当然,他们的行动最终失败了,但他们毕竟走出了单纯构想社会蓝图的局限,而积极投身于当时社会的实践活动,这同时说明他们那个时期的乌托邦理论开始贴近和关注现实。但是,即使在近代的社会乌托邦观念发生了由空间向时间的转换,但它仍然根植于近代的西方传统和现代启蒙精神相互融合、碰撞的西方文化中。这种乌托邦设计不但要求构想美好的理想社会,而且也希望通过现实的一定程度的改良或变革来实现这种美好社会的蓝图,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化论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传统的乌托邦观念在逐渐消解,以至于在现代社会中只会出现所谓“乌托邦”的术语,却再也没有其实质内容。根据赫茨勒的说法,它被称之为“拟乌托邦”。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构想不再像传统社会乌托邦思想那样保持与当下现实社会的巨大张力,不再对现实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启迪和警示作用,缺乏丰富的超现实的想象力。他们只是采取了乌托邦的叙述形式或构想模式,但乌托邦的内容却与现实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实现这种所谓的社会理想完全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即使这种“拟乌托邦”的作者本人也承认,他们的乌托邦构想是按照现实的人性来构想和实现的,它与现实社会的差别只在于发生时间上的量的不同而已,而根本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因为在现代的拒斥形上学的文化观念中,在充分理性化、操作化的现代社会中,他们已经“能够认识到试图刻画出一个永恒完美的国家是愚蠢的行为。他们认为社会的改造必须建立在人类本性的现实基础上。”①
正因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念拒绝和排斥乌托邦,从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来看待乌托邦,这必然遮蔽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使人们对乌托邦内涵的理解由“美好的社会理想”变成了“空想”和“不切实际”的代名词。这其中固然有激进的乌托邦社会运动与实践所导致的专制与独裁这一原因,更主要的因素还是现代性对传统社会文化观念的叛逆式怨恨,导致了同黑格尔所说“倒洗澡水连同孩子一同倒掉”的结局。当前,面对全球性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困境,如生态危机、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及其现代社会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的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若从“永不在场”的乌托邦这一独特视角出发,也许能够使我们对现代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能够拓展人类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丰富人类历史的总体性内涵。既然把乌托邦作为审视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一个视角,那么,这里就有必要给乌托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并对乌托邦的内涵做出一定解释。笔者认为,“乌托邦”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它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
具体来说,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应该包括以下具体内涵。首先,它是人的一种价值理想。作为一种双重性的存在,人不仅受到感官所接触到的事物支配,还会受到超验的想象启发,前者是形下的经验层面,后者则是形上的价值理想。其次,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开启了未来广阔的可能性空间。在现实社会中,人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对于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则视之为空想,这就把诸多虽然不可能但对人来说却至关重要的价值排除在外了。因此,人不但需要依靠现实逻辑来维持生存,更需要有超现实的逻辑来展开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为人的存在提供丰富的选择机会。假如人处于不能选择的状态,只能如此的地步,那么,即使人所能够选择的机会再好,人同样也是不自由的。最后,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是人对未来历史的终极性价值诉求。人类的历史是由不同的社会阶段构成的,但作为历史的总体并不是由不同阶段的现实社会简单叠加而成,因为,所有已经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只是历史的过去和现在,至于历史的未来以何种社会形态存在,这往往是由人们超越现实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来开启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对未来历史的展望“首先预设了一个绝对的至善理念或理性本体,然后以为社会历史不过是它们的展开、实现和回归的历程;从它们出发,人类历史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终极境界。”②
二 历史的终结及其现代性神话
“乌托邦”的本意就是指不存在的城邦,在现实中不可能兑现的一种社会状况,正如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完美的人或理想的社会状态那样,乌托邦永远都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其“彼岸”或超验的特征难以消解。传统的以乌托邦为社会理念的历史设计“把人的历史当做神的历史来设计与创造,把人的命运和历史的前途交付人之外的超人的力量或实体,结果为人之有限的和自由的存在与活动设想了完善完满的神的结构”③。此种乌托邦式的历史设计以承认人的历史性为前提,预设了“完善完满的神的结构”,为有限的人规定了超越现实的崇高的价值理想。从本体论上看,这一设计体现了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现实与理想、历史与价值的二元张力,这似乎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如具体分析,它的错误在于,人们在具体操作上误用了乌托邦的价值,只看到人的有限性,却忽视了彼岸的特性。因此,道德性和总体性的乌托邦不可还原于现实,将之强行推之于当下而造成专制与独裁。
形象地说,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处于“天上”的理想与“地上”的理想之间的位置,“天上”的理想是宗教,“地上”的理想就是人的现实的感性生活,包括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衣食住行等等。这决定了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既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又具有超越现实的对未来历史的终极关怀。如果说,传统的乌托邦式的历史设计偏重于“天上”的理想,使人们以无限的热情追求超验的价值理想,结果却陷入僵化和教条,那么,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的历史设计则走向了反面,将“地上”的理想无限制地加以膨胀和外化,使乌托邦的价值彻底成为了虚无,人类历史的地平线消失了。如果说,传统的历史设计误用了乌托邦的价值导致了人类的美好社会的理想的枯萎,那么,现代性的历史设计则看到了乌托邦的彼岸性而将历史的轴心完全转移到“地上”的理想,这种因噎废食而放弃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乌托邦的作法,使人们的精神封闭和满足于当前的现实状况。按照这一逻辑,“历史的终结”将是其必然的结局和不可逃避的命运。就此点而论,苏东解体后,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恰好是现代性神话的逻辑和历史的结果。
按照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一极其悲观的命题,苏东解体后,人类的历史不再是多元的,而是单一的,人类历史的感性形态依然在不断地流动、变化,但是其理念却已经凝固。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的基础的原则和建制不会再有进步了,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现代人再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想象或设计不同于当下现实的另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乌托邦的视野消失了,现实社会的人都成了“最后的人”(last man),人类也就看不到历史的未来走向,进入到了终结的状态。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历史的终结”观却又反映了他对当前历史现实的一种乐观主义态度。因为按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苏东解体后的人类历史将是一帆风顺的,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两极世界的对立和争霸,也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只剩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胜利的凯歌。悲观的历史终结论与盲目乐观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想象在福山这里达到了奇妙的结合。即使如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包含了某种乌托邦的历史观。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及乌托邦与历史总体性这一问题。
历史是什么?如何理解历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人类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历史应该区分为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自然历史是指过去在永恒的自然界中无意识地反复发生的一切,人类无法知道它的起源与终点。人类历史是指因精神而获得意义和连续的现象的演变,是通过人类记忆和继承同人类现在有机地联系起来的过去。相对自然历史而言,人类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一般我们所说的历史都是指人类历史。因为自然历史只是体现“超然存在”的客观存在,它超越人的主观之上,人只能直接感知自然物,体悟自然,却无法感知作为整体的自然。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来看,自然都是人类不可跨越的界限,无论人自身强大到何种程度,人都必须承认自然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和价值论上的自在自为的内在价值。从这个角度说,“自然没有历史”不是对自然力量的削弱,恰恰是肯定了自然的本体论意义,确认了人的有限性和必死性。相反,把自然强行纳入人类历史的发展轨道,否定自然的本体论地位,将自然的价值单纯规定为工具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就由此形成了,人对自然的奴役也就包含在这种逻辑推理中。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反观人类自己、规定人类活动极限的“自然之镜”被打碎了,人被“上手之物”(海德格尔)包裹着,人如何来审视和反思自己,欲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拔地而起,这一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人类历史是真正的历史,它既表现出人的伟大,也映衬出人的渺小。一方面,人类历史体现了“超然存在”的主观存在,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或途径来重现人类已有的历史,并据此来预见人类未来历史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只存在于人和人的创造中,存在于一切与人发生联系的事物中,正如维柯所言,历史是人创造的。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也是一种“超然存在”的客观存在,从人类存在之日起,人类历史就潜藏着“超然存在”的无限可能性。不管人类通过什么理论方法或何种高科技手段,都不可能穷尽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敬畏历史。无论当前或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得多么完善,我们都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对待历史的起源和最终目标,我们也只能在超验或形上的层面去理论假设、思辨构想,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再现历史的起源和科学地预知历史的未来。人类历史的现实生存特性与超然性的对立是诸多西方学者无法规避的一个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也折射了他们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在黑格尔那里,人类历史表现为“绝对精神”的展开、螺旋式的循环发展和实现;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终结取决于绝对理念的完满性的实现。所以,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也暗含着某种强烈的历史终结论。正因为此,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大量吸收黑格尔的思想,并从苏东解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出发,基于西方的单一的“自由、民主”标准,得出了人类历史终结的神话。表面上看,历史终结论完全是基于现实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哲学的反思,但究其实质,它却表现为另一种乌托邦式的历史神话式的预言。难怪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一历史预言遭到了西方学者的反对。历史的事实不断地证明,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的神话,完全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式神话般的呓语。相反,历史既没有终结,人类社会也没有进入到歌舞升平的理想境界。从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及遍及全球范围内的地区冲突,无不在昭示人们,历史的现实仍在按其惯有的脚步,以其超然存在的方式向前行进。人类历史在不断粉碎和嘲笑那些自命不凡的思想家们所做出的乌托邦式的神话及其预言。这就是历史的现实性特征及其超然性特征。那么,历史的超然性是否彻底根除了乌托邦的生存空间呢?我们的回答将是否定的。
三 “永不在场”的乌托邦及其希望之根
乌托邦的源始含义及其本真性即“不在场”(non- presence),这表明它既不存在于空间里的某一点,也不存在于时间内的某一瞬间。“不在场”并不意味着乌托邦就是纯粹的幻想,而是不同于现实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哈贝马斯在谈到乌托邦与幻想之间的区别时指出:“决不能把乌托邦(Utopia)与幻想(illusion)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④ 从这种意义来说,乌托邦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人的本体论的存在方式,因为离开了“不在场”的乌托邦,人只能为现实所左右,成为现实的奴隶,从而成为“物”。没有了形上的“乌托邦”,人类可能坠入世俗的“千年王国”的神话。
20世纪的人们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苏东解体,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难以摆脱乌托邦的某种历史和未来情结。与哈贝马斯相类似,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卫·哈维(D.Harvey)也提出了一种希望的乌托邦,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希望的空间》(2000)一书中。通过对乌托邦的发展和兴衰的历史的追踪研究,在对现代城市环境,特别是美国巴尔的摩市的城市建筑及其空间建构进行了多维度描述的基础上,哈维认为,我们能够运用而且必须运用乌托邦想象的威力来对付表示“没有选择”的所有人。他在《希望的空间》中提出了一个新型的乌托邦思想,即他所谓的“辨证的乌托邦理想”。这一理想是在摈弃了传统乌托邦的空间形式和时间过程这两个乌托邦理想的缺陷和难以克服的弊端后而提出来的。它试图建立一个明确的时空的乌托邦理想。因为在哈维看来,传统的乌托邦思想要么是一种空间形式的乌托邦,要么是一种社会过程式的时间形式的乌托邦。根据爱因斯坦曾说过的空间与时间不能有目的地分开的论述,哈维认为,“乌托邦理想就必须同时包括空间和时间的生产。因此,我称之为“辩证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的探索还在继续。⑤ 通过对现代城市空间和时间发展历史的考察,哈维要求人们重新关注这样的可能性方案,即设计一个与自然更加平等地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他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计划想要发挥作用,那它就必须要考虑到我们人类的特性、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变化的动力。哈维并不认为他所谓的“辩证的乌托邦理想”,也即“时空乌托邦理想”的理想是空洞的设想,反而认为它对现代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作为我们无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的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无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但那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以及那些给予可能性如此一种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在畏缩和小鸡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塑,”⑥
至于辩证的乌托邦理想能否建构,如何建构,哈维认为它并不是建构在空中楼阁之上,相反,“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模糊形式并非很难从我们自己对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所推动的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发掘出来。这样看来,任务就是确定一个替代方案,而不在于描述某个静态的空间形式甚或某个完美的解放进程。这个任务就是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它来源于我们目前的可能性中,但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轨迹。”⑦ 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的附录中为我们勾画出一幅真正的个人乌托邦景象,清晰地阐明了他自己的希望地理学的乌托邦思想,也即他名之的“希望的空间”。借用贝拉米在《回顾》一书中有关乌托邦的描述的话,哈维写到:“当黄金时代来到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希望‘对恐惧、紧张、焦虑、过度操劳和不眠之夜说再见了”。⑧ 这就是哈维辩证乌托邦的理想,即其所谓的未来希望的世界图景。
毫无疑问,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大卫·哈维,在他们看来,乌托邦并不完全是一种空想,而是一种希望,一种人类不灭的未来希望之光。如果人类没有了希望,人类将永远失去方向,并将永远失去自己的存在之根。同时,希望的乌托邦也是一种价值诉求,即人类寄希望于未来的价值追寻。从这一意义上看,现代性的神话无非是现代人过于自信而表现出疯狂的精神病态而已。历史不像运载火箭那样,可以通过人为设定的计算机程序获得预定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诉诸于乌托邦想象,历史未来的终极性视野才会向我们展现和澄明,它使人不会停留在无限历史的任何一个固定点上而将历史的片断永恒化,也不会完全满足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既定现实状况,它始终将目光注视着未来历史更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乌托邦永远不会“在场化”。正因为此,乌托邦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乌托邦的“不在场”并不表示它消极无为,而是更深层意义的“有为”,它不断向现实输送新鲜的“血液”,以防止其“凝固”而堵塞历史向前发展的道路;它只有与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才能确保自身的超越性、终极性、无限性和总体性,才能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起到道德制约和价值制衡的作用。可以说,所有声称“实现了乌托邦”或“拒绝乌托邦”的言论都是历史的短视和意识形态的自欺,其结局都将被历史向前的车轮碾得粉碎。
在当前乌托邦言说极度匮乏的时代,在人们仍沉浸在科技文明的凯旋高歌和消费主义的全球化狂潮中,在现代性已经取得全面性胜利的状态下,在清晰的未来远景与逝去的过去传统一样在历史的绵延中消失的情形下,现代社会背后潜藏的暗流提醒人们,21世纪的人类似乎并不能完全摆脱乌托邦的“纠缠”;乌托邦更应该发挥其摆脱世俗的社会救赎力量,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谋划另一个可能的社会和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想象维度。从这一点看,可以说,乌托邦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必要维度,是摆脱现代性桎梏的一副清醒剂,因为“每一个乌托邦都是对人类可能性的预示,没有这种预示的能力,人类历史上无数的可能性也许至今仍然得不到实现。没有预示未来的乌托邦展现的可能性,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颓废的现在,就会发现不仅在个人而且在整个文化中,人类可能性的自我实现都受到窒息。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世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实之中,无所发展。”⑨ 尽管乌托邦也有其消极性、虚幻性,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性社会理想会使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感到无比沉重,甚至有“欲卸之而后快”之感,但只要使之保持在一定的合理限度内,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就会积极发挥其重塑现实的实践性冲动,并为现实社会提供另一种更加合理的替代性理想社会模式。可以说,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一方面,现代技术理性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开疆扩土,它已经占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通向人类未来总体性的大道上,人类永远离不开乌托邦的想象,或者说,彻底放弃乌托邦就等于阻断了现存历史与未来的终极性社会理想之间的通道,过分执着于乌托邦的“理想”或“空想”,则会使人们脱离现实的大地,重新陷入一种非历史的境地。只有立足于现实的大地而又不乏“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人类才能规避现代性的弊端,实现人自身的完美的发展。
注释:
①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220页。
② 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第42页。
③ 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一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77-78页。
④ 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122-123页。
⑤⑥⑦⑧ D·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77页;第190页;第190-191页;第272页。
⑨ 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