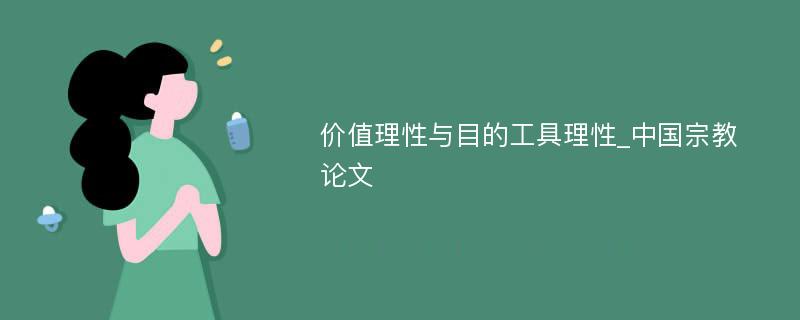
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目的论文,价值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文化中,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是割裂的,因为前者纯属价值判断问题,而后者则是经验实证问题。本文作者从中国大道文化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之相统一出发,论述了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统一性,以及信念道德与责任道德的一致性。作者认为,中国不论是搞市场经济,还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都不能片面地追求目的工具合理性,而必须把价值合理性放在重要地位,努力实现价值与价值判断、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以及信念道德与责任道德的统一与一致。
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研究人的行为时提出的。他所说的价值合理性, 是指由宗教、伦理、道德、审美一类价值意识决定的行为;而他所说的目的工具合理性是指有预期的目的和实现这种目的的工具、手段的一类行为。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是完全对立的、割裂的。因为前者是不可经验实证的,纯属价值判断问题,而后者是可以达到预期目的,是可经验实证的,属于科学理性。韦伯作为倡导“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家,虽然也研究宗教伦理道德一类的价值合理性,但就其整个社会学思想来说,他并不喜欢宗教伦理一类价值合理性及由此产生的信念道德,而是要人们以责任道德实现目的工具合理性。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或知识论哲学为基础的。而这种哲学乃是逐物之学,是不要价值判断的。正如亚当·斯密从经济学领域清除了“道德”及一切价值判断一样,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或知识论的哲学家,也在自己的领域清除掉了形而上学及一切本体论、价值论的学说。前者所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经济事实,后者所剩下的只是物质世界赤裸裸的真理性。韦伯的社会学以这种哲学作为理论基础,把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对立、割裂开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这里并不想详细讨论、研究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倾向性,只想借助他的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理论概念,研究分析一下中国应该如何坚持与西方不同的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因为中国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哲学;特别是贯彻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大道哲学,根本不存在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相割裂的问题。
什么是大道?什么是形而上学的道?过去人们讲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其实,它不过是宇宙万物法则秩序纯粹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诗经》讲“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雅·文王》):“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周颂·维天之命》);《尚书》讲“天叙有典”、“天序有礼”(《皋陶谟》):儒家孔子讲“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子思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道家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15章);庄子讲“天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可观于天”(《知北游》);墨家讲“法于天”(《法仪》),“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尚同下》);以及《易传》讲“仰观象于天,俯察理于地,观鸟兽之父与地之宜”(《系辞下传》)等等,凡此都是讲道为天地万物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天”,在无限的时空意义上,也就是宇宙。携宇宙、傍日月、尽万物而观之,损之又损,抽象了又抽象,使之成为一种纯粹法则的存在,也就是形上之道,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大道本体。因此,不管把大道抽象为有,抽象为无,抽象为无极,抽象为太极,抽象为周行不殆、独立不改的存在,抽象为“寂然不动”的本体,它都是宇宙的法则,都是这种法则的纯粹抽象思维形式;也不管把这种法则的变化说得怎样扑朔迷离、变化莫测、至神至妙,它都不是虚妄的存在,而是像朱子所说的,始终都是真实无妄的实理,是“天理之本然”(《中庸章句》第20章注),或“彻底都是实理”(《正蒙·诚明篇》朱熹注)。实理,就是实有是理,就是真实无妄之理。它作为道,作为本体的存在,作为宇宙法则的纯粹抽象思维形式,虽然不是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家所讲的物的实在,但它也决不是虚假的假设,不是彼岸世界的存在,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灵,不是人格化的上帝,不是神秘的精神实体,不是纯粹主观的终极臆说,而是“物物而不物于物者”(《庄子·山水篇》),是“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庄子·则阳篇》)。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虽然也需要理解与领悟,但它决不是虚妄的价值,不是纯粹的价值设定。它虽然不能以物的实在或经验实在去追求,但它又不是脱离宇宙万物而存在的,而是道体流行随处可以发现的,是可以征之于宇宙万物的。也正因为这样,形而上学的大道才表现为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的统一。讲道为天地母,讲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老子》第25、42章),属本体论;讲道“继之者养,成之者性”(《周易·系辞上传》),属于价值论;讲“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同上),则是属于知识论,而且是最高的知识论,因为道是真知至知的存在。这和西方讲上帝的存在只是属于价值判断问题,与知识无涉,把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相割裂,则是完全不同的。正因为中国的大道哲学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才不存在像韦伯评价西方宗教信仰所说的只有价值合理性,不具有目的工具合理性,也并不是像他所说的只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设定问题,而不具有真实可靠的价值属性。中国形而上学的大道不仅是一个价值肯定、价值判断的存在,而且是一个真实无妄的价值所在;不仅具有价值思维的合理性,而且具有价值实现的目的工具合理性;落实为社会生活,它不仅是一个信念道德问题,还是一个责任道德问题。因此,中国形而上学的大道是价值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是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统一,是信念道德与道德责任的统一,而不是将二者割裂,或像西方哲学那样将它们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价值世界,从而使它们之间不具有真实的价值关系。
正因为大道本体存在与人的行为是一种真实无妄的价值关系,所以中国哲学才要求人在考虑目的工具性行为时,必须与大道本体的价值联系起来,并且把它看成是最高的价值标准,以此去衡量具体的目的工具性行为是否合理。《大学》第一章开宗明义,就是讲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明明德于天,只有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明明德、止于至善,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只是对哲学家的要求,而是对自天子至庶人的普遍要求,是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因为在中国哲学看来,未有本乱而能治天下者,未有本乱而能达到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的。试想,德之不修,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能够和夫妇、正人伦吗?能够使家庭关系和谐美好吗?能够使家庭和睦共处、得到治理吗?一个家庭尚治理不好,乱七八糟,能够治理好国家吗?能够明明德于天下,使天下人皆能明明德吗?自己不诚实又如何能使天下人诚实呢?自己二三其德又如何能使天下的道德清明统一呢?自己不正又如何能正天下呢?自己不能自新,又如何能新天下之民呢?一个不爱他的家庭的人,能够爱他的国家吗?一个不爱他国家的人,能够兼爱天下人民吗?道理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能明明德的人,一个不能自明的人,他是不可能明白天下事理的,也是不能大行于天下而不悖的。在这里,责任道德与信念道德是完全一致的。它决没有为了信念道德故弄玄虚,让人们接受不喜欢的价值;也决没有为责任道德不择手段,以实现某种工具性目的。相反,它要求人们考虑任何目的工具性行为时都要以最高的价值为准则,都要以价值本体考虑不同等级、层次的价值。因此在这里,信念道德就是责任道德,价值思维的合理性就是目的工具行为的合理性;最高的价值本体就是不同等级、层次的价值,或者说就包含着这种价值及其合理性,而决不能将这种价值置于本体价值之外,从盲目的、自私的、与本体价值相悖的方面说明它的合理性或合乎理性。这并不是否定个别的、特殊的价值,而是说这种价值只有符合本体的价值,才是合乎理性的,才不会发生悖谬,因为它是符合普遍价值法则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合理性是这样,企业经营、发财致富的伦理道德合理性亦即如此。企业经营、发财致富按照韦伯的说法,纯属目的工具合理性的行为范围。那么,这种行为要不要符合最高的价值合理性呢?或者说它是不是也要和价值本体联系在一起或遵守最高的天道法则呢?中国大道哲学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因为这类行为同样不能妄行,用《周易》的话讲,只有无妄,才能“元亨、利贞”(《无妄》)。程子伊川解此说:“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可以致大亨矣”,“利贞,法无妄之道,利在贞正,失贞正则妄矣”(《周易程氏传》卷2)。大亨之理,无妄之道,就是天道法则, 就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天道本体而言,就是无妄的价值本体。为什么要遵守天道法则?为什么要贞正价值本体?因为它是化育万物、生生不穷的本源。如果不遵守天道法则,不贞正价值本体,竭泽而渔,就像现代工业化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界生杀掠夺一样,那就堵塞了生化之道,断绝了生生之源。只有遵守天道法则,使阴阳和顺,天地交泰,才能生生不息,有物之美、财之用。故《易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彖上传》)。天地交泰既是成财之道,也是理财的制度方法。只有阴阳和顺、天地交泰,才能万物遂生,财源不竭;只有体验领悟天地之宜而为制度方法,用天时、因地利,才有辅财源不竭之妙用。这种体验、领悟就是明明德,就是有生财之道。而在韦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看来,只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是合理的,哪怕不择手段。中国的大道哲学则不是这样。它最反对为富不仁,最反对以不仁的手段达到致富的目的,因为这是不合乎理性的。仁不仅是爱人、体贴人,也包括仁爱万物、体贴一切生命。如果不明明德,如果失其本而致其末,如果为了富起来使人们相互争夺,甚至竭泽而渔、生杀掠取,那也就会造成财聚而民散,造成整个社会的价值悖谬。如果这样治理国家、经营企业,这样聚敛财富,无异于造盗、蓄盗,实乃自乱其身、自乱其国矣。如果听信只要达到目的就具有合理性的理论,实乃乱国之道也。因为它会使整个国家陷入疯狂和非理性。以利为利,失去价值合理性,反而不利;以义为利,得价值本体之大用,反而得利。这就是本与末、德与财、义与利的辩证法。以此辩证方法治理国家、经营企业、发财致富,才具有普遍的价值合理性,目的工具性行为才是合乎理性的。一切把致富与道德对立起来的说法、看法及其理论与实践,都是和中国大道哲学的伦理道德精神相违背的。
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一个人要想发财致富,要想成为企业家,要想雷行天下,就必须明明德,就必须具大亨之理,行无妄之道,就必须像《易传》所说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彖上传》)。只有道德刚健文明,才能应乎天、行乎时,才能得天道之大用;只有柔得尊位,大中而应,才能生大有;只有坚持刚健而中正,才能大行天下。《易传》这些道理不仅是安身立命的哲学,也是一种致富哲学,一种货币哲学。利在贞正,不贞正则妄,妄则“天命不祐行矣哉!”这个天命不是别的,就是天道法则。法则是中正的,是不准人妄行的。你妄行,它就要纠正你,就要制裁你。即使你一时得意,如果不自觉,如果不能回到理性上来自己纠正自己,那么,法则就要纠正你,制裁你!因为你已经陷入了非理性,已经偏离了大中之道。法则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像无情的法官,像公正的上帝,像无形的纲纪,作为正义的力量来纠正、制裁一切不正义的妄行。老子所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73章)即指此也。即使你可钻社会法律的空子,即使你可以逃过执法人员的眼睛,但 果你妄行,也最终要在商品经济活动中跌交、摔筋头的,甚至遭到惨败的。手段的不合理性最终要导致目的不合理,目的不合理性最终在于不合正理,在于不合天道法则,在于心有邪念,在于不能体验、领悟天道本体的刚中而庸、大亨以正。这就是《周易》所说“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的意思。眚即有病,即错误,即无德。一切妄行,一切过失,一切不正当的非理性行为,皆产生于此。小失于正,则有过,已妄矣;若不改正,继续沿着不正的道路走,继续采取非理性,则妄作凶矣。故曰“天命不保”,或曰“天命不祐行矣哉”。
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人放弃具体的目的工具合理性,并不是要人在管理企业时不精确核算、精密筹划、精心经营,就像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或经营管理方式那样。孔子曾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可知仁者不仅是指事其贤者、友其仁者,不仅是指尊重人才、尊重知识,而且还是包括“器”的工具合理性的内容。器,不仅是指工具、器皿,它包括一切形之者,包括一切事的、物的存在形式,其中也包括组织形式与制度形式。大则宇宙万物、国家政权形式,小则衣物饮食、百姓日用,凡一切形而成之者,都是器,都必须条理之、筹划之、组织之、运行之,然后才能发挥功能,产生妙用,才算善其事、利其器,才算具有目的工具合理性。然条理之、筹划之、组织之、运行之就是道,就是理,就是所以成为器者,就是所以成为宇宙万物、百姓日用者。这就是道不离器、器不离道、器贯之以道的意思。因此,即是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目的工具合理性,也是不能离开恒宇宙、成万物的道的。宋代理学家张栻虽讲“形而上者之道托于器而后行”,但同时也讲“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南轩论语解》卷5)的。这就是说,一切企业管理的深谋远虑、精确核算、 精密筹划、精心经营都是不能离开道的法则的;离开了这个法则的筹划、组织、运行,就会陷入非理性,就会走邪道而陷入目的工具非理性,陷入道德价值悖谬。不管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体制上,存在着多少不合理性,真正的企业家,是应该像孔老夫子所说的“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的。只有至德之人,才能全心;只有全心之人,才能全身;只有全德、全心、全身,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否则陷入不仁,以身试法,也就谈不上求生存、求发展了。这就是《大学》所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第10章)的道理。
还有一点是应该特别说及的,那就是不能把商业的合理性、投机的合理性、技术的合理性等等推广到社会关系中去变为社会生活的合理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品关系、物质关系、技术关系,而还是一种文化关系、意义关系、伦理关系、道德关系。如果把商业活动中的精心算计、精心策划以及投机、技术的合理性等等带入到社会生活中来,你算计我,我算计你,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变成了相互算计的关系了,那也就没有什么伦理道德可言了。故《左传》宣公14年说:“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国家社会为了完成某项具体的工作任务,配备组织各方面的人才,组成功能群体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把整个社会都变成计较个人得失的功能群体、利害群体,也就没有友谊可言了。一切以目的工具为合理性,就等于让整个社会为金钱、为贪欲相互争斗、相互计算,就等于把整个社会的私欲、恶、内心的黑势力、魔鬼统统地都放出来,如此,天下不出乱子才是怪事呢?!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一切以利害为准,一切以目的工具为合理性,及至把整个社会变为功能群体、利害群体、乡党称弟、小人汹汹,皆为市井之人,皆为利害之徒,那么,也就无忠厚老实、高风亮节可言了,也就把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冰冷的现金交易、权力交换之中了。果真如此,中国还谈什么君子之国、礼义之邦呢?
单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不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宗教、哲学、艺术等深层精神生活的价值实现中,更是行不通的。那不言的天地之大美,那不议的四时之明法,那不说的万物之成理,那昭明的天乡其德,那“皇极”的大中之道,那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天地之母,那至神至妙、“寂然不动”的无妄真体,那归乎无始、不累于形迹的无极,那昊昊上天、皇皇上帝、无限光明的神圣境界,那无形的大象,那希声的大音,那雷鸣般的寂静,那万籁俱寂的运作,那山韵、水韵、沙韵、风韵,那忘物、忘我、忘适、忘忘,等等。凡此都不是用目的工具合理性能解决的,不是用技术合理性、科学合理性能解决的,不是用经验实在或逻辑性能解决的。因为它不是逻辑形式,不是经验实在,不是功利目的,不是实体的物的存在,而是非逻辑、非经验实在的存在,是超越一切功利目的存在,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存在,是无始无终、与物俱化的存在,是抽象的法则,是形而上的本体,是价值思维的肯定形式,是凭着理性的直觉所创造的至神至妙境界。对于这种存在,我们只能用心、用灵魂、用道德修养、用理性的直觉,去体验,去领悟,然后才能得之为德,宜之为义;才能知道天地之大美在哪里;四时之明法在哪里,万物之成理在哪里,才能知天乡其德、皇极之道;才能得天地之母,无妄之体;才能领悟天地精神,感知无限光明的神圣境界。这一切都来源灵明之心、道德修养。中国古代先哲以及一切有道德修养的人们,正是凭着这种灵明之心、道德修养获得天地精神、性命之理及伦理道德使命的。中国文化哲学所以深厚博大,中华民族所以刚健文明,其原因也在这里。如果中华民族不能超越经验实在思考天乡其德、大中之道,不能凌空而起思考天地精神、性命之理,只会思考物的实在,离开了物的实在再也不会思考问题了,那也就不是一个深厚博大的民族,而是一个爬行的民族了。
也许有的学者会说,谈价值合理性不必谈目的工具合理性,谈目的工具合理性不必谈价值合理性,二者是不同的价值领域,源于不同的理性之维。自然,物质世界的真理性,目的工具合理性,不是宗教、哲学、艺术的合理性;宗教、哲学、艺术的真理性,也不能完全用物质世界的真理性、目的工具合理性去实证。但是,这不等于说二者完全是割裂的,是彼此互不相关的,或者说是两个互不关心的世界。不是的。这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看一看当今世界价值与价值判断的事实,就会明白。目的合理性,工具的合理性,技术的合理性,科学的合理性,投机的合理性,让转证券的合理性,交换的合理性,一句话,物的实在或经验实在的合理,不仅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领域,而且铺天盖地而来,侵犯着宗教、哲学、艺术的神圣殿堂;特别是物的实在,不仅蒙蔽了人们的眼睛,堵塞了人们的耳朵,而且窒息了人们的灵魂,使他们看不见、听不着、感觉不到一切非物质世界的真理性与价值存在。由于这些合理性被强调到了天经地义的程度,强调到了谁不承认、附和这种合理性,谁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不近人情,以致于使它浩浩荡荡地向整个社会、整个精神领域进军,社会道德让位给了物欲充斥,宗教、哲学的真理性让位给了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艺术的美让位给了感官刺激、色情场面,连光屁股、跳裸体舞也具有了合理性,因为这是最真实的存在。谁不承认这种存在,谁不承认这种存在的合理性,谁就是虚伪——这种价值、价值判断上的咄咄逼人,已使宗教、哲学、艺术的价值理性或价值合理性无路可走。老实说,宗教、哲学、艺术的真理性无意取代物质世界的真理性,无意取代科学合理性、技术合理性,因此价值合理性也无意取代目的工具合理性。然而,物质世界的真理性、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以及目的工具合理性等等,却一点也不谦虚,一点也无自知之明,堂而皇之地侵入了一切领域,占领了一切领域,取代了一切价值合理性,取代了整个宗教、哲学、艺术的真理性,使整个社会陷入了物欲,陷入了浅薄的物质文明。至此还说什么各谈各自的合理性与真理性呢?还怎么使宗教、哲学、艺术的价值理性能对科学、技术、目的、工具合理性表示冷寞和不关心呢?这种发展是整个宗教、哲学、艺术的悲剧,也是时代文化哲学的悲剧!一切非物质世界的真理性都被推翻了,一切神圣的殿堂都被玷污了!至此,又怎么能不使宗教、哲学、艺术家为最高的价值合理性与真理性而斗争呢?只有思考这种合理性与真理性,只有获得大中之道、性命之理,人的思维、存在、追求才有价值合理性,目的工具性行为才有真正的合理性。因为大中之道、性命之理是齐天地、一万物的存在。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存在,是最高、最普遍的法则,是纯粹无妄的真理。它不仅超越物质世界的真理性、目的工具合理性,而且涵盖了这种真理性与合理性,并且向下落实,表现为整个物质世界的真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它是价值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是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统一,是信仰、信念道德与责任道德的统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就在于得此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