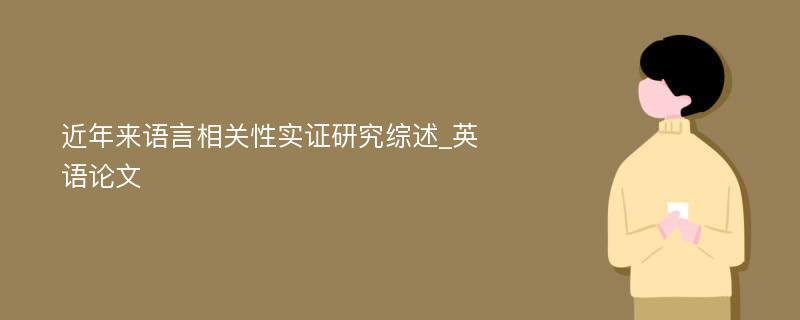
语言相对论近期实证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论论文,近期论文,语言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语言能力是人类具有的共同特征,而语言的种类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面,从显而易见的语音、词汇到细微复杂的语法结构,差异万千。说不同语言的人会不会因为语言的这些差异而以不同的方式观察、分类和记忆相同的经验?或者说,不同的语法范畴对语言使用者相应的思维是否有所影响?
早在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家洪堡特就提出了类似语言相对论的话题。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一种语言的结构会影响使用者的习惯性思维,语言范畴一旦组成连贯的系统,就有可能左右一个人的世界观。这一具体而新颖的提法引起学界极大兴趣,人们遂将这一思想称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根据后人的理解,假说可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强式称作语言决定论,即语言决定思维;弱式叫作语言相对论,即思维相对于语言而存在,语言不同的人,思维也不同。后一种说法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并试图加以检验。
二十世纪中期之后,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普遍主义在解释儿童语言学习中惊人相似之处时所表现出的潜力吸引了整整一代学者的注意,加之六、七十年代人们所做的一系列色彩命名实验研究似乎解决了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争,使后者占了上风,语言相对论在学术界的影响逐渐减弱。八十年代以来,一些讨论和实证研究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理解提出了新的思路,重又引起人们的兴趣。有些研究显示了支持语言相对论的证据(Bloom 1981; Lucy 1992a,b; Imai & Gentner 1993; Slobin 1996; Levinson 2003),而有些研究则提出了质疑(Heider 1972; Mazuka & Friedman 2000)。同时,认知科学发展迅速,尤其是Fauconnier和Turner的心理空间理论、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语言相对论实证研究显示出较强发展势头,研究者们在反事实假设、名词的性、即时思维、名词数标记、空间方位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证据,支持语言相对论。本文将有选择地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作一综述。
2.语法领域的研究
2.1 Slobin的“即时思维”研究
Slobin从“即时思维和说话”(thinking and speaking)的角度来调查人们在形成话语时的思维过程。同思维和语言相比,“即时思维和说话”强调话语形成时的思维过程(1996:71)。他相信,一种语言的强制性语法范畴决定了必须要表达的经验的相应部分。不管语言对人的思维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必定会引导人们注意密藏于语法范畴中的经验范围(dimension)。Slobin和几个国家的研究者合作,比较不同语言的儿童对同样场景的描述,所用材料是Mayer(1969)画册,涉及语言包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希伯莱语。研究的重点是时空和语言的关系。
重点讨论的有两幅画。第一幅画中,一个小男孩骑在一棵大树的树叉上,窥视树干里的洞穴;不远处,一条小狗在攀爬一棵小树,旁边是一个蜂窝。第二幅画中,一只猫头鹰从树洞里窜出,男孩跌落在树下;与此同时,小狗被一大群蜜蜂追击,拼命逃窜。
1)时间描述
英语允许中性体(aspectually neutral)动词和进行体的对比存在, 中性体动词具有默认终止性。前面提到的第二幅图中,男孩“跌落”(fell)就是一个例子。西班牙语允许完成体和非完成体或进行体对比存在。这样,西班牙语可以对持续和非持续状态作语法标记,而英语只能对持续状态作标记。德语和希伯莱语则缺乏这样的体态区别标记,都不能从语法上标记进行或未完成状态。调查表明,德语和希伯莱语受试并不从语法上区别两件事,动词使用了相同的时态,而英语和西班牙语受试则倾向于区分两个事件。下面表格里的实验数据是受试使用相同时态/体描述“跌落”和“奔跑”的百分比(Slobin 1996:80):
在“fall”和“run”从句中使用相同时态/体态的受试比例
学前(3-5岁) 小学生(9岁) 成人
全体
希伯莱语 71 10063 78
德语 54 80 78 71
英语 26 22 33 27
西班牙语 23 18 0 21
有约四分之三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受试在描述中注意到两个事件的体区别,而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德语和希伯莱语受试注意到这种区别。这种现象在叙述实验中一再重复出现,显示了不同类型语言的使用者说话时的思维差异。虽然说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凭借某种非语言知觉知道男孩的“跌落”是终止性完成事件,蜜蜂和小狗的“追逐奔跑”是进行中事件,但他们一般不大可能用语言来表达其语言所难以恰当表达的内容。令人惊奇的是,三岁儿童就已经表现出与其母语相适应的“有选择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问题是,语言表达中缺乏某种范畴是否会有替代补充方法,还是在说话时的思维中予以忽略?Slobin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母语中未能语法化的范畴一般会被忽视,而语法化了的范畴即便是三岁的孩子也都会表达。
2)空间描述
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法范畴的有无,还表现在语法资源在共同语义范围里的分配。从语言表达位置移动的角度看,英语和西班牙语分别代表类型差异的两极。英语以动词表示位移的方式,通过小品词和介词表示方向。如:
The bird flew down from out of the hole in the tree.
(鸟从树洞里飞下来。)
而西班牙语里的位移动词只表示移动方式或方向,不能像英语那样用复合式词组同时表达方式和方向。同英语相比,西班牙语介词只表达很不具体的位置情况,具体细节信息表达需要借助常识来实现。当常识不足时,往往要对相关场景作静态描述,从而使人可以推断出合适的运动路径。比如英语句子:
The boy put the frog down into a jar.
(男孩把青蛙放进罐子。)
西班牙语表达为:
El nino metió la rana en el frasco que había bajo.
(男孩把青蛙放到罐子,罐子在下面。)
这样,西班牙语里的down into 的路径要通过动词和对目标位置的静态描述推断出来。可见,英语倾向于说清楚位移的路径,把最终的位置状态留给人们去推测;而西班牙语倾向于说明位置和方向,把位移路径留给人们去推测。两种语言的这一系统差异决定了说英语的人更注重过程的描述,而说西班牙语的人更注意状态的描述。
在德语里,位移动词一般不表示方向,有丰富的方位小品词和介词,类似英语;希伯莱语有表示位移方向的动词,只有少量介词,与西语同属一类。下表是上述四种语言的儿童描述位移时使用光杆动词的比例(Slobin 1996:85):
使用光杆动词描述向下运动的比例
年龄
3岁
5岁 9岁
英语 4 27
3
德语 1520
西班牙语 6837
54
希伯莱语 6872
45
根据上述研究,Slobin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描述这本画册时的思想体验是不同的。图画本身并不存在某种因素,会导致说英语的人以进行态描述“小狗奔跑”,使西班牙人注意到“跌落在地”是完成体态,使德国人形成对路径的详细描述,或使说希伯莱语的人漠视事件的持续或终结。原因在语言本身。儿童在习得一种语言时受该语言中的一套语法化特征引导,从而在说话时对事件的相应特征加以关注。这些特征就是语法编码的视角。
Slobin(2003)进一步把“即时思维”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语言产出(说、写和手势)和语言输入(听、读和看),总结了对话、口语/书面语陈述、翻译和儿童语言习得等领域的相关调查和研究,得出结论:由于类似英语、德语的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示位移方式的动词,操此类语言者对位移方式的认知是凸显的。
对有特定时序的事件进行序列体验,将物体置于一定位置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其他动物也可以做到这些。但语言要求我们将事件作为“进行”或“完成”状态、将物体作为“静止状态”或“运行终点”范畴化。这样,人们的经验经过语言的过滤而成为语言化事件,每一种语言都是对人的经验世界的主观定向(orientation),这种定向在人们说话时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
Slobin的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从体态角度看,英语和西班牙语同属一类,德语和希伯莱语同属一类;而从空间位移角度看,英语和德语又同属一类,西班牙语和希伯莱语同属一类。看来,区分语言的类型差异要根据特定的语义范围。一种语言表达时间概念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于其表达空间关系的方式。这对洪堡特、沃尔夫的语言-世界观总体概念提出了质疑。其二,Slobin弃用“思维”的说法,部分原因是这些概念会牵扯到“知觉”、“推理”、“习惯性行为”等概念,纠缠不清,而“即时思维和说话”是现时的瞬间过程,具有客观必然性,适于操控分析,可以避开“实验结果是否受文化等因素影响”的质疑。但这种思维显然不同于相对论中讨论的“习惯性思维”,它是转瞬即逝的,还是具有持久影响,尚需要探讨。相对于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即时思维”研究更为谨慎,Slobin的观点因此也较容易为更多的人认可,更适于实证研究(Gentner & Goldin-Meadow 2003)。他的探索促使人们开始审视说话时思维和语言发生联系的具体过程。
2.2 名词的语法性研究
语言把物体名称归类为不同的范畴,语法上的性(grammatical gender)就是其中之一。定冠词、代词可以标记名词性,往往形容词、动词也要变化,与名词的性保持一致。那么,把无生命物当作具有性别的生命物来谈论,是否会使人觉得无生命物也有性?即语言范畴是否影响认知思维?
最近,Boroditsky等人在西班牙语和德语中做了一系列关于名词语法性对归类认知影响的实验(待发表)。实验以非语言的图片形式进行,用英语做指令语。要求受试鉴别男女人像和物体图像的相似性,这些物体名称的语法性在两种语言中正好相反。两组受试均把语法上阴性的物体同女像归为一类,把语法上是阳性的物体归入男像一类。这表明,语言赋予物体的语法性确实影响着人对该物体的思维表征。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西班牙人和德国人根据语法性赋予物体阴性或阳性的品质,比如“钥匙”在德语里是阳性,在西班牙语里则是阴性。德国人往往将其描述为“硬的、重的、粗糙的、金属的、锯齿的、有用的”,而西班牙人则会用“金色的、精巧的、小小的、细小的、可爱的、闪亮的”加以描述。又如,“桥”在德语中为阴性,而在西班牙语里是阳性。德国人将其描述为“美丽、优雅、脆弱、和平、可爱、纤细”,而西班牙人往往把它描述成“高大的、危险的、长长的、强壮的、结实的和高耸的”。
因语言不同而赋予事物名称阴性或阳性,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但一旦习得某种具有语法性的语言,人们在给生活中接触到的物体按照性来归类时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要同语法性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具有任意性(arbitrary )的语法制约了人的认知活动。
3.认知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3.1 名词数标记认知研究
根据Quine(1969),量词语言(classifier languages)同类似英语的非量词语言(注:在汉语和许多其他亚洲语言中,名词计数时往往需要带量词,名词本身无须变化;而英语及许多其他欧洲语言的名词通过词尾屈折变化来体现单复数概念,如horses中的“s”就是复数标记,类似量词的成份较少。)之间在名词语义上有系统差异。 量词语言的名词表示连续的、 无边界(nondiscrete and unbounded)的物质, 而在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里名词表示非连续界限和确定的形状。这反映着本体相对性(ontological relativity):对说量词语言的人来说,物质(material/substance)是凸显的(prominence),对说英语的人来说,物体(bodies)是凸显的。对此,有人持否定态度(Soja et al.1991),有人则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证据(Lucy 1992a,b)。也有证据显示,语言和认知的关系并不像Quine表达的那么简单(Imai & Gentner 1993),需要修正。其中,Lucy的研究比较系统深入。
Lucy(1992a)以名词数标记为切入点,研究了英语和尤卡坦语(Yucatec),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半岛上的一种土著语言。名词的基本数标记方法是使用一个带有数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的词语。这样的分类词是短语中必不可少的,类似汉语的量词(注:关于分类词和量词的关系,可参见刘丹青(2002)和李文丹(1998)。),比如:两只火鸡表达为ka'a-túul'úulum(两个单位的火鸡)。其中的túul就是分类词。
Lucy使用两类特征来对比两种语言名词的数标记:[+/-生命性]和[+/-离散性]。基于语言分析,他推测,两种语言的语法数的标记差异可能对各自使用者的习惯性思维产生影响。对英语使用者来说,可数名词所指物的形状是其数标记的基础,用可数名词指称物体时能引起说话人对其形状的特别注意;而对于说尤卡坦语的人来说,名词指称物构成材料是将其归入某一类词的基础。所有名词就像英语中的物质名词,会引起他们对物质材料的注意。
实验应用了物体分类任务,呈现物质材料和形状的对比。此外,Lucy还用描绘尤卡坦人村落典型生活的图画设计了各种任务活动,包括图画描述、识别、回忆和相似性判断。下表列出了分类任务中的物体(Lucy 1992b:138):
对比形状和材质的分类实验物
参照物 形状物 材质物
1.1sheet of paper
Sheet of plastic
Book
1.2strip of cloth
Strip of paper Shirt
1.3Stick of woodCandle stick
Block of wood
1.4Cardboard boxPlastic boxPiece of cardboard
1.5Length og vine
Length of string
Woven ring of vine
1.6Grains of corn
Beans Tortilla
1.7Half gourd
Half calabash Gourd with opening
1.8Ceramic bowl Metal bowl Ceramic plate
在这一任务活动中,首先给受试看参照物,比如一个陶瓷碗。然后展示后面的供选物,铁碗和陶瓷盘,让其选择哪一个更像参照物。参照物有清晰的形状,由可辨的物质构成;一个供选物有类似的形状但物质构成不同,另一个供选物的构成物质相同,但形状不同。
Lucy发现,多数说英语的受试选择了形状类似参照物的供选物,而多数尤卡坦人选择了构成物质相同的物体。这一结果以及来自其他实验的结果使Lucy相信他的假设得到了证明,即英语和尤卡坦语的数标记影响了思维方式,导致看物体时选择角度不同。操英语者更注意物体形态,而操尤卡坦语者则更关心物体的物质构成。
Lucy & Gaskins(2001)采用更加多样化、控制更严格的实验物,改进了Lucy(1992b)的实验,结果再次验证了后者的结论。此外,他们用同样的实验材料对7岁和9岁两组儿童进行调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物体的分类标准逐渐接近成年人。这与他们的语言逐渐成熟相关。
Lucy的实验方法类似Soja等人的方法,较前人更加合理,尤其是采用了非语言的实验材料,使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推动了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研究。
但他的实验方法也并非无懈可击。Mazuka & Friedman(2000)指出,Lucy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他的实验结果也因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尤卡坦受试的生活极简朴而传统,年龄在18至45岁之间,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文化程度很低;而英语受试则是来自美国高校的本科生,年龄在19至27岁之间,其教育程度甚至超出美国人的平均水平。由于两组受试的教育文化背景差别很大,实验结果可能受到背景差异,尤其是教育水平差异的左右。
根据这个假设,Mazuka和Friedman把尤卡坦语受试换成日语受试,重做了Lucy的实验。他们认为,日语的数标记系统同尤卡坦语很相似,而日语受试和美国英语受试在文化教育背景上又更为相似。实验结果表明,日语受试类似英语受试,也倾向于以形状而不是物质构成材料作为事物分类的依据。这样看来,Lucy的实验结果似乎确实受文化教育因素的影响而不是语言的影响。但Mazuka和Friedman也不否认数标记会产生认知上的影响;在实验材料介于物体和物质之间时,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是存在的。这一点早已为Imai & Gentner(1993)所证明。
其实,语言相对论只是坚持语言能够影响、制约思维,并未排除其他因素,如文化、教育和普遍本体(注:Soja等人(1991)认为,儿童普遍能够感知物质和物体之间的差别,而且这种认识在掌握语言之前就有了,不因语言不同而有差别。)对思维的影响。语言至少是影响、制约思维的因素之一。
此外,Mazuka和Friedman的实验也是有问题的。他们的日语受试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英语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其思维方式是否已受到英语影响也未可知。虽然他们用另外一组在美的日本人做了语言因素排除实验,但那些受试的年龄、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他们是在美日本公司员工的家属,长期生活在日语圈里,如同生活在美国唐人街的许多华人一样, 英语水平并不见得比日本在校大学生高。 而且Mazuka和Friedman把排除组比其他两组更倾向于物质选择的结果解释为,这一组受试和Lucy的尤卡坦语受试一样缺乏正规教育。这更说明该组受试同英语的接触是有限的,所以排除实验的结果并不可信。由此看来,Mazuka和Friedman的实验不足以推翻Lucy的结论。不过,他们的实验的确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比如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可能不像Lucy乃至沃尔夫认为的那样绝对,而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语言和其他因素,如文化、教育等对人的思维产生了综合影响。这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相对论思想。
3.2 空间方位的研究
对于一个物体位置的判断,比如一枝笔,可以从观察者角度看,说“笔在书的左边”。但也有人以绝对方位作参照,说“笔在书的西边”。这些判断方式就是格式塔心理学上所谓的“参照框”(frames of reference)。长久以来, 参照框被认为是人们头脑中的内在概念,植根于神经认知系统。以往多数相关文献认为,在判断物体方位时“自我中心坐标”(egocentric coordinates)具有优先作用。可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表明,参照框在语言、认知和手势领域的运用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异,并且儿童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不同的参照框系统。另外,除了上述“自我中心”(相对)视角、“固定方位”(绝对)视角外,确定物体方位还可以有“物中心”(内在)视角,即以参照物自身的特征为依据。
在观察桌面(相对于宏观地理)物体的空间方位时,英语采用两种不同的参照框(Majid et al.2004)。比如,桌面平放着一把餐叉和一把勺子,叉头指向北,勺头向西垂直对着叉子的中部,观察者面朝北站在桌边。操英语者会说“餐叉在勺子的左边”(相对视角)或“餐叉在勺子旁边”(内在视角),而不会说叉子在勺子的西面。这种绝对参照框在英语中仅用于宏观地理描述。但在一种澳大利亚土著语Guugu Yimithirr中,却只用绝对参照框来描述方位(Haviland 1993)。操这种语言的人甚至会用同样的方法描述身体某一部位上的物体,例如“你的南腿上有一只蚂蚁”。
使用不同参照框的语言需要进行不同的认知测算。内在参照框要求认知系统把参照物分成几个主要部分,如前、后、边等,便于描述参照。相对参照框和内在参照框一样,要求把参照物,即观察者分成几部分,如前、后、左、右,这种划分被投射到空间,即便观察者没有接触描述对象,也可以用前、后、左、右加以描述。绝对参照框要求人们随时随地清楚惯用的固定参照物,为此观察者内心要有一个尺度,时常对背景方位作出判断。那么,为说话需要而进行的空间位置估算是只影响到说话和理解的过程,还是有更深层的认知影响?
Pederson et al.(1998)根据说话者惯用的参照框,区分出绝对、相对和混合参照框语言。在非语言实验活动中,向受事展示桌面上物体空间关系或移动轨迹,然后将受试旋转180°面对另一桌面上的相关空间关系。实验涉及到对物体空间排列、位置移动轨迹的记忆以及空间方位推理。实验结果表明,人们运用了不同的非语言参照框来完成相同的实验任务,而这些参照框同受试相应的语言参照框是一致的。
Li & Gleitman(2002)对这类实验结果提出质疑,认为实验变量控制不足,得出的认知差异可能是环境或文化因素所致。Levinson等人(2002)随即撰文指出,在环境和文化变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语言和非语言表征的相关性仍然存在。使用绝对参照框的语言包括澳大利亚的Guugu Yimithirr语和Arrernte语,纳米比亚的Hai语,墨西哥的Tzeltal语,所罗门的Longgu语和印度尼西亚的Balinese语(见Levinson 2003; Wassmann & Dasen 1998)。这些语言的受试在非语言任务中使用了绝对参照框。使用相对参照框的语言包括荷兰语、日语、墨西哥的Yukatek 语(见Pederson1998; Levinson 2003),这些语言的受试表现出相对认知参照框。上述受试的文化和环境背景差异巨大,从生态环境到生活模式各不相同,但受试在相同实验活动中却表现出类似的认知模式。看来,文化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排除。
近年来跨语言的相关研究表明,语言多样性和认知多样性是一致的,上述研究中空间任务的非语言处理以及伴随话语的无意识手势(Haviland 1998; Kita et al.2001)都证明了这一点。参照框是空间认知中最基本的概念,因语言不同而有异。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为说话需要而进行的空间位置确认有深层的认知影响。
3.3 英汉时空隐喻词研究
英语通常把时间描述成水平延伸的,而汉语除了这样的水平概念外,还用垂直延伸方式来谈论时间。Boroditsky(2001)认为这种差异反映在两种语言使用者对时间的认知方式上。英语主要用表示“前/后(front/back)”概念的词表达事件的先后顺序,如good times ahead,the hardships behind us。这些词和描述水平空间关系的词是一样的,如he took three steps forward,the fox is behind the tree。汉语除了用类似“前/后”这样的空间隐喻词描述时间顺序外,还普遍采用“上/下”垂直空间隐喻,如“上一次”、“下半年”,相当于英语的earlier/later,但英语中这样的用法很少见,更不系统。
Boroditsky的实验对象包括母语分别为英语和汉语的在美大学生,实验用语为英语。先让受试看图画,接受空间关系刺激。图画下面有一个句子描述画中物体的空间关系,包括水平空间关系和垂直空间关系,如The black worm is ahead of the white worm.(黑虫在白虫前面),或The black ball is above the white ball.(黑球在白球上面)。 然后让他们尽快判断关于时间关系的描述是对还是错(true/false)。如,March comes before April.March comes earlier than April.结果,英汉受试在接受水平空间关系刺激后回答before/after(水平关系)问题都比接受垂直刺激后要快;这说明,使用空间隐喻谈论时间对人们的时间思维有即时影响。回答纯粹时间问题earlier/later时, 英语受试接受水平刺激仍然比接受垂直刺激后反应快,而汉语受试表现正好相反。这与两种语言里描述时间的隐喻分别一致,即英语普遍采用水平方向,汉语里垂直方向描述也很普遍。这种情况证明,人们经常使用的隐喻对他们在时间方面的习惯性思维有长久的影响。进一步的实验表明,在美中双语者对时间的垂直思维受习得英语时间早晚的影响,越晚倾向就越强,而与接触英语的时间多少无关。看来,年龄因素不仅影响语言基本技能的习得,而且似乎也影响着语义倾向(biases)的习得。Boroditsky试图从外语习得的角度再次验证隐喻对习惯思维的影响。
但上述实验中,受试习得英语的时间较早,在3至13岁之间,属于双语使用者,他们不能算是典型的外语学习者。13岁以后习得英语的人,情况会怎么样呢?广大外语环境中的学习者又会是什么情况?要真正测试外语是否影响人的思维,还需要在完全习得母语后学习外语的成年人中做实验。
4.结语
上述诸项研究都是对两种或几种语言的某一范畴特征作对比分析,得出假设,然后设计方法加以验证。同沃尔夫的研究相比,这些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它们只是在某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证明(或证伪)相对论假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证据全面证实或否定相对论思想。但他们的具体方法较前人更加合理,实验更加精细,对干扰因素的控制也更严密,如Lucy的非语言刺激物,Mazuka等人的排除性实验等就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改进。在控制实验的变量因素方面,Slobin的“即时思维”研究效果最好。但有得也有失。从语言相对论研究的最终目标来看,这样做的代价似乎太高了。如果说考察语法结构的局部特征有片面性,那么“即时思维”似乎有些偏离了相对论研究的主流,即习惯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显然,仅仅通过一两次的实验研究,即便实验设计较以往更加合理,也难以彻底证明相对论假说。毕竟,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实验不容易设计出来,每一项研究通常只是对人类部分语言的局部考察。Gentner & Goldin-Meadow(2003)指出,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的“僵局”在于其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如果这类研究能够在不同地区、各种语言中广泛展开,每一项涉及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都能够局部证明相对论假说,那么综合结果也许最终能令人信服。
退一步说,即便永远不能证明语言相对论的真伪,这项研究的意义仍然十分深远。正如高一虹(2000)指出的,它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反省本民族中心主义,接受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从而达到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标签:英语论文; 西班牙语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儿童英语论文; 英语思维论文; 复数名词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希伯莱论文; lucy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