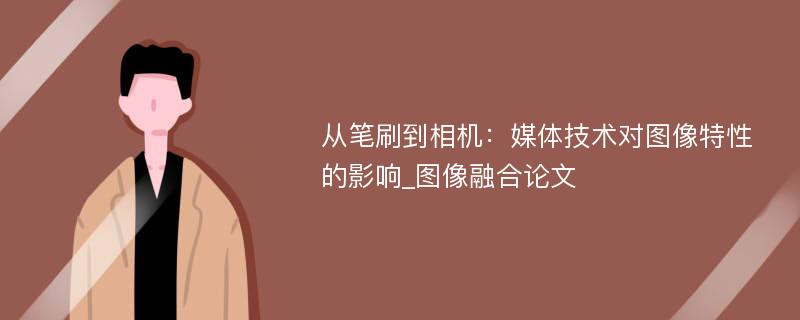
从画笔到照相机:媒介技术对图像特性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画笔论文,照相机论文,媒介论文,图像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 徐沛君 杨斌
一、图像生产历史概览
今天,图像在我们的表意实践中已经不可或缺,且日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然而,古代的图像与现代的图像显然大不相同,其间的分界线大致可以照相机从发明到基本完善的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这也是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从英国发起后陆续完成的时期)为标志,而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这也大致是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分界线。本文的研究即以图像生产在此一时段的转折为对象,远古的由原始工具制作的图腾图像和当代由计算机和数字技术产生的虚拟图像暂略不论。
从古代至现代的图像生产在东西方呈现出一种略显复杂的态势。西方的古希腊以天真的理性眼光和属于农业文明的自然工具开创了手工图像的审美创造和应用于世俗生活的局面。但在中世纪,图像的生产主要被局限在为基督教服务的狭隘神学功利主义的范围之内,直到文艺复兴,古希腊式的审美创造和真实表现世俗情感的图像生产模式才得以恢复。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追求世俗欲望之满足的功利主义和服务于此目的的工具理性主义及其科学思维得到空前发展,谷登堡的印刷术亦在此期间成熟完善,语言和文字思维达到人类思想成就的顶峰,图像的生产和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压抑,而主要以绘画的审美形式由个体的艺术家进行创作,并以一种精英文化的姿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与此同时,图像生产的另一股潮流伴随着1839年达盖尔照相机的发明和16世纪已经诞生的现代印刷机的精度与速度的极大提高而蓬勃涌现,这便是以机械复制为手段的大规模图像生产的方式。这种图像的机器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图像的生产由审美领域全面转入实用的经济发展和日常消费领域,最终以一种大众文化的面貌统治了图像生产的舞台。其间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更具视觉魅力的动态的图像机器——电影和电视摄像机得以诞生,并使电讯传输网络迅速发展和完善,由此而决定性地改变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盛行数个世纪的印刷文字的权威和魅力逐渐被机器生产的各种静态和动态的图像所取代。
在东方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图像的手工生产随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悠久延续而同步绵延,直至20世纪初为止。图像生产在进入王权专制的帝国时代以后,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道德教化所仰赖的伦理形象塑造,而应用于日常用品装饰的图像制作则自发地在民间历久不衰。其间从公元4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了以欣赏为目的的图像生产,并与上述两股潮流同其始终。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遭遇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冲击,以原始工具和技术为基础的农业和手工业渐趋瓦解,图像生产的个体和手工方式也开始面对大规模机械复制方式的挑战,这样的局面自20世纪初始现端倪,在经过几十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历程之后,中国的情形与西方的就基本类似了。
二、图像生产的传统手工技术与现代机器技术之异
在这样一种从古代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图像生产变迁中,我们所观察到的突出现象是媒介技术的巨大改变,即从手工技术到机器技术之差异。对媒介技术进行了较多关注和论述的是麦克卢汉,其基本思想是,将人类从物质和信息传输到具有表意功能的日常用品的任何一种技术发明都看作是一种媒介,其实质就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人的延伸”的意思是,人以各种技术的发明来补足人体天生的功能缺憾,从而增强自己应付外界自然和社会事物的能力,因此“技术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①。
就图像生产来说,首先,基本的差异是不同时代的技术所使用的工具和操作过程之异。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图像生产的基本工具是各种形式的笔——从石锥、石刀、金属刻刀,到用羽毛和兽毛制作的各种或硬或软的笔,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人手的直接延伸形式,是原始的手工技术。人们用它们或刻或绘,在同样是手工技术产品的各种媒材上制作各种形式的图像,其基本的手法就是模拟,即一笔一笔地用手工在媒材上模仿出对象的形象,从而生成对象的另一种媒介形式的存在方式(图像的铸造或蚀刻方式的基础也是手工)。它们或者是石刻,或者是壁画,或者是布的或纸的及其他媒材的图像,其完全以手工模拟的特性则是一致的。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图像生产的主要工具已经由笔变成了照相机以及功能完善的印刷机,图像的生产主要由精确的光学投射和化学反应的技术设备来完成,这样的生产特点是由人的肢体的间接延伸——机器这种在人脑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工具来完成的,其过程再也不需要人的手工性的聚精会神的操作,而是由机器发挥其机械功能,在瞬间按照规定步骤精确地完成。
其次,关键的差异是不同时代技术工具之内在的人的延伸的性质之异。手工模拟技术的工具是以手工凭经验制成的笔(至少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前是如此),且其设计目的就是供人徒手使用,而非以自身的机械功能代人完成操作。因此其根本特征是其使用要调动人的全部感官能力和以过往全部经验为基础的思维能力、情感和想象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以手为核心的操作之中,才能完成预想的任务。笔作为技术工具,在这里就是人的全身心能力的直接延伸,它的使用,就是人的全部感性和理性能力的浑然一体的投入和运用,因此,可以说笔就是手,就是人的全身心的全部能力及其缺憾,它在全力地模仿对象以便尽可能客观地传达其信息的时候,总是无可避免地打上自己的主观的烙印(对信息的无意识增删),更不用说在主动地表现自己的内在情感的时候了。
具有机械复制功能的照相机,在其成熟阶段已经不再是主要凭借经验和手工制成的工具,而是以经过两次科学革命和两次技术革命② 以后日趋成熟的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它自身各部件的构成及其机械功能,都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技术之上的。因此照相机所依赖的技术早已不是人的手以及感性经验所能应付的了,而必须凭借由人脑的机能——理性思维能力才能把握。科学之于经验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完全排除了后者的感性不确定性,而以得出建基于可验证的实验之上的理性思维所产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假说为旨归,由此来保证某种有目的的活动完全控制在确定不移的逻辑轨道之中。由这种科学性所决定,现代技术工具便不再与人的全身心的能力密切相连,而只是作为人的肢体的间接延伸,主要体现为人的大脑及其逻辑思维能力的产物。由此,对于现代技术工具的使用,也就不像传统的手工工具那样,需要人的全身心能力的投入,毋宁说恰恰相反,它基本上都是以限制人的感性能力的自由发挥为原则来保证特定的技术目标的实现的。一旦那些规定程序得到了执行,则确定的客观结果就能够高效率产生,此外人工可以发挥的余地很小。机器的规定程序,亦即人脑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成了图像的机械复制方式的主宰。
三、图像的产出方式和表现对象的选择倾向性
由上述手工和机器技术的差异,首先决定了相应的图像产出方式的不同。因为“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③ 从而使得我们感知世界和作出反应的方式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④ 这种延伸往往是一种感觉的应用比率占据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使我们的感觉及其相应的判断能力产生极大的偏颇,执著于某种单一的模式而最终落入谬误的泥潭。“我们在智商测试中搞出来的那些不恰当的标准真是泛滥成灾。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统一而连续的习惯是智慧的,因而就淘汰了听觉和触觉发达的人”。⑤ 作为人的全部身心能力的直接延伸,使用笔、刀等工具进行模拟的手工技术没有任何可供依凭的现代机器设备,能够让人将特定的工艺过程和操作步骤交托给它,由它替人以科学逻辑的精确性(人脑功能预先运作的产物)加以完成。人所能依靠的只有手、眼、身、心以及以往的全部感性经验,它们还没有经由科学的技术发展过程而固化为某种专业机器的功能,因此,手工的图像生产就必须事事依靠人自身的能力,它必须经由人这个主观中介的劳动过程(主要是手的操作),才能生产出一种形式,将对象的形象或人内心的意象模拟下来。保罗·莱文森说:“即使最不抽象、最栩栩如生的绘画传达的也是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和口语词一样,再现是一种带有个人色彩的、个人神经系统的产物。因此绘画和类似的手工媒介,用巴赞的话说,必然要沾染上主观的罪孽。”⑥ 总之,这里有一个从待再现或表现之物到人,再由人的身心功能到图像产生的转化过程,这个转化的中心环节是人这个血肉生命的存在。而使用机器技术的图像产出方式则与此相当不同,由于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那样的程度,可以将精确复制对象形象所需要的工艺和步骤完全转变为特定的专业机器的功能,因此传统图像生产的那种身心功能即时投入与发挥的生命性过程被压缩和抽象了,现在它只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制作图像)而运用脑力的过程,其结果就是照相机、摄影机和自动印刷机的发明。由此,这些机器作为人的身心功能的抽象和间接延伸,同时也作为人的脑力的逻辑理性能力的直接体现,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图像生产的某种客观存在的一劳永逸的标准化程序,图像的生产不再需要人一次次的全身心生命投入过程,不再需要人这个主体作为中介进行转换,图像的生产这时基本上就是一种机械的复制过程,从对象到图像,只须经过照相机及其相应设备的运作便可简单完成。它不再需要由人来创造主观形式来再现对象的一个转换过程,而形成了一种基本上由物经机器到物的形象的图像生产模式。人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被减弱了,被压缩和抽象了。“因为用来拍照的相机是人设计的产品,但是人在这里的贡献是更加标准化、更加客观化的……一按快门,外部现实反射的光线和胶卷上的化学品就产生化学反应——在这个反应中,是没有象征主义,没有人的解说,没有神经细胞的激化的”。⑦
其次,图像生产由手工向机器的转变,相应地带来了图像表现对象的改变。在手工技术时代,图像所表现的主要是以人的观念和情感为核心的主观之物,而在机器技术时代,图像则主要以外在世界中的事物为表现对象。从原始时代的雷神、太阳神等等无数的众神,到中世纪的基督及其门徒,再到东方农业社会的女史(仕女)、高士乃至梅兰竹菊等等伦理楷模,手工技术的图像生产所钟情的总是这些数量有限的象征某种观念和情感的对象,这不仅是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固定的生活范围和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所导致的结果,同样其时代媒介的技术特性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手工的图像生产作为一种需要专门技巧的劳作,其产品的产出相当费时,而低下的生产效率使得手工媒介材料的生产同样费工费时,因此产量有限的图像制品便弥足珍贵,它们主要都是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国之重器而被使用的,或刻之于碑匾,或绘之于墙壁,或图之于缣帛,以便能长久地宣扬某一社会群体的永恒价值观念,其形象的价值因此也就在于精神内涵的深度,而不在于所提供的外物种类的多少。而机器图像的生产由于其操作便捷性和形象逼真性的特点,满足了人类长期以来精确便捷地复制对象形象的愿望,因此便主要被人们用于记录客观世界,从而尽可能多地将新奇、陌生的对象在意识中据为己有。正如桑塔格所言:“摄影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意在捕捉尽可能多的拍摄对象。绘画却从来没有如此宏大的视界。”⑧ 中世纪以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对人的世俗本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于是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日益强烈,从而形成了一种捕捉世界而不是反省内心的机器图像生产倾向,因此其所表现的对象便不再是有限的观念和情感的象征形式,而是无限多样的外在世界。
四、冷热媒介与手工和机器图像作为语言的审美特性
关于手工和机械复制的艺术作品的差异,本雅明曾做过相当充分的阐述,他大致将其归结为是手的精雕细琢的功夫被眼睛的速度感所取代,照相摄影的机械复制性以其产品的规模和易得性打破了传统艺术品的基于社会等级和文化教育背景所形成的垄断,使得它们更多地为普通大众所拥有和接近,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摄影机制造的图片和影像也创造出人们前所未见的视野和细节,可谓皆大欢喜,但其代价也是惨重的:艺术品与其传统生产方式俱来的独特韵味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惊颤)⑨。显然,本雅明主要从艺术生产的外部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图像生产从手工制作到机械复制的转变过程中,艺术的历史、审美品质的变迁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而对艺术的媒介技术自身的性质及其运作特点则未多加论述。
但从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我们则可以得到另一种阐释。他说:“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高清晰度是充满数据的状态。照片从视觉上说具有高清晰度,卡通画却只有‘低清晰度’,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提供的信息非常之少……大量的信息还得由听话人自己去填补……因此,热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⑩ 显然,相比于手工模拟的图像,机械复制而成的照片是热媒介,因为它以感光胶片上无数的点准确无误地模拟出对象在一个光学聚焦平面上的连续明暗形态,从而将对象的形象逼真的再现出来,因此具有高清晰度。而手工图画则只是凭借人的手操纵的画笔,以数量有限的点、线的勾勒或铺排,将对象的形象模拟出来,因此它必须有所取舍和侧重,则其在单位面积中将对象加以编码的坐标点的数量就非常之少,并且还无法保证这些点的位置完全准确,因而相比之下清晰度就低。但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即由机器加以延伸的单纯视觉,因此虽然照片对眼睛来说是高清晰的,但这种单纯视觉的“充满数据的状态”却导致了感知比率的失衡,使得我们能够很容易因而过分关注形象的细节,而丧失了对形象的整体及其内在气骨和精神品质的注意力,这些看不见的信息正是极端依赖人的情感、想象及其融会于其中的理性等其他感知和判断能力,因此手工图像所擅长的以简约形式象征深远意蕴的艺术性就此而被削弱了。对此,桑塔格从摄影作为一种类似于语言的表达工具的角度分析说:“就某人或某事写出来的东西显然就是一种阐释,手工制作的视觉陈述,例如绘画和素描等,也是如此。拍摄的形象看来却并不像写作那样陈述某事。它是任何人都可以制作或获得的微型现实。”(11) 意即手工图画和机器图像的不同在于前者可以像语言那样阐释现实,并要求人的积极参与和判断,而后者只是消极地复制和展示现实,而无法给出确定的判断。对美国文化从印刷时代走向电视时代呈现出理性退场而感觉和娱乐登台现象深表忧虑的波兹曼,也从类似的角度得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他说:“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12) 他所强调的电视与印刷文化的区别也主要就在这里:机器图像让我们的感官受到刺激和娱乐,但却令我们放弃了融会在文字语言形象之中的理性和思考。
因此,手工图像的低清晰度留给人的正是调动和运用自己全部身心能力的空间,而机器图像所产生的结果则是以充沛的视觉信息淹没人的感官,而令其别种更为重要的能力萎缩乃至废弃,由全面的人而沦为某种“单向度的人”。
五、手工和机器图像的价值观: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手工图像生产因为没有条件对对象的表象进行方便、精确的复制,因此倾向于以简约图像象征性地表达某种内心情感和理念,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象征艺术,它对形的准确性并不特别在意,毋宁说正是通过对形的主动扭曲才达到了对意念的表达效果,像原始部落的面具形象和中国古代的写意水墨画的形象都是如此,中国画论所谓的“离形得似”,“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乃是这种图像生产观念的集中体现,所强调的正是心手一体的运用,而减少对纯粹技术的依赖。也正是这种空灵的图像,使得永恒的精神有了寄寓之所,其低清晰度的信息传达方式也为接受者的相应精神活动留下了空间。因此手工技术珍视不可见的精神、观念的价值及其表现,这也与传统社会低下的物质生产水平、技术条件所决定的重伦理规范和精神信仰,而轻物质生活的特征相适应。
图像的机器生产则与此异趣。因为拥有可以精确、便捷、客观地复制对象形象的机器,因此它特别乐于以排除人工干涉的方式来发掘和精确记录外部世界中的事物,并以其复制形象的客观逼真而自豪。“它完全满足了我们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欲望”。(13)“惟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因为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相簿里一张张照片的魅力就在于此……这不再是传统的家庭画像,而是能够撩拨情思的人生的各个瞬间,它们摆脱了原来的命运,展现在我们面前”。(14) 显然,摄影为人所看重的功能正是其客观而逼真地记录生活的能力,因为自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来,人们的生活逐渐摆脱了传统神学的压抑,而有了追求世俗幸福的权利,其实质就是感官欲望的实际满足,而不再局限于伦理道德的观念性满足的界限之内。于是逼真的机器图像所展现的世俗生活的场景逐步取代了手工图像所象征的理想精神境界,现实生活中可见的东西逐渐取代了原先许多不可见而长久以来被崇奉为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趋势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日渐明显,直至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机器图像所包围。
于是在我们的世界中,思想和图像再也无法分开,因为适合于感官的高清晰的图像就是我们的现实欲望的表征,而几乎不再有抽象的理念存身之地。我们就在图像中思考,就用图像来思考,而不是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可以摆脱巨量图像的困扰而以抽象的语言来思考,因此,我们就是用可见之物来思考可见之物,因为在图像之外别无他物。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情感欲望紧密融合为一体了,再没有抽象永恒不变之美,而只有特定时空之中的特定存在及其特定的情感和欲望之表征。由此,可见的不再是偶然的,无足轻重的,它就是存在、生活本身及其意义、价值本身。那种离开了感性具体的生活的不可见之本质、理念、道、规律等等,都只是一种虚妄之物,是某种权力关系和观念操作之产物。这样一种图像生产实践和观念的转变,正意味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根本特点就是精神生产的商业化、精神享受的消费化以及感官感觉与精神生活的密不可分。可见的才是真实存在和有价值的,可见的本质在现代社会中就是物质的、机械的、机器制作的,而非观念的、灵性的、由人手工创造的。由此我们的感知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被机械化了,我们的生存已经离不开机器,我们作为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机器的了。正如本雅明所说:“电影致力于培养人们那种以熟悉机械为条件的新的统觉和反应,这种机械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日俱增。”(15) 我们已经习惯于以机器的方式来观察世界,我们已经自然而然地认为,世界应该是奇观式的,是对比分明色彩饱和的,是声色俱佳易于理解而不需要花费脑筋的,是冲击力强而极富刺激性的,总之它必须是由机器精巧制作而不是自然自在,并需要由经过教育所获得的后天深湛素养来配合理解的,否则它就是难看见,看不懂,因而是不存在和没有价值的。我们已经是如此依赖机器这根人的间接延伸的拐杖,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已经无法生活,因为它早就成为人的一部分了。
六、小结
媒介作为由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与自然和社会进行交往的工具,最初是与人的血肉之躯紧密相连的,它们就是各种各样的手工技术,其根本的特征就是其使用过程需要人的全部能力直接投入,因此它们同时就是人的全部能力的直接延伸。但经由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刺激,技术已经由人的全部能力的直接延伸而变成主要由人的逻辑理性所制造和主宰的人的间接延伸,此时它们就是各种现代机器。由此,图像的生产方式和表现重点便由媒介的这种技术特性的改变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连带着,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对图像的价值判断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其总体的趋势是从信仰到实用(从超越到功利),从审美到日常生活,从观赏到消费,从贵族精英文化到大众消费文化,如此等等。这是媒介作为技术在人的需要之下发展,同时造成人的文化属性相应改变的逻辑轨迹。人类历史上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曾多次发生这样的媒介技术特性改变,进而导致文化内在属性改变的过程。已有许多先哲对此做过或宏观或特定角度的探讨,而在目前这样一个崇拜效率而又不担保任何确定的逻辑链环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或许还是历史和逻辑能够大致对应的切实的研究。
注释:
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4页。
②刘则渊《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导论》,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2页。
③同①,第33页。
④同①,第37页。
⑤同①,第45页。
⑥⑦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⑧桑塔格《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⑨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
⑩同①,第52页。
(11)同⑧,第14页。
(12)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13)巴赞《电影是什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4)同(13),第7页。
(15)同⑨,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