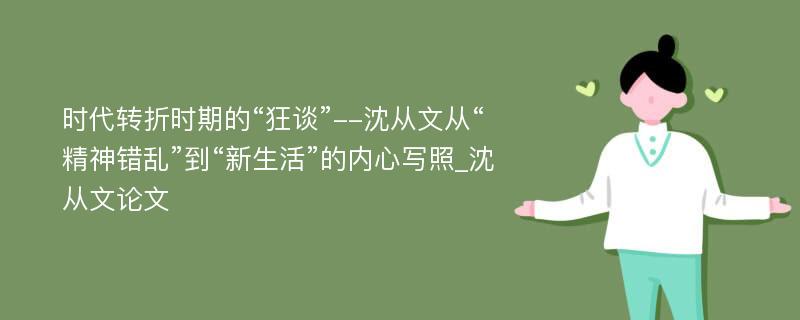
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沈从文从“精神失常”到“新生”的内心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狂言论文,图景论文,呓语论文,新生论文,内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说法适用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转折的人,包括与沈从文同代的很多作家。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裂变,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大多数只能随着这个巨大的、根本性裂变而发生重要的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向。
但是,即使很多人都处在分水岭上,沈从文仍然显得非常特殊。他是以精神的极端痛苦和紧张而孤立在分水岭上的,其孤立的程度,在他觉得是唯一的一个;其极端的程度,竟至于发展到“精神失常”和自杀。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崩溃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情况有扼要说明:“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九月中下旬,病情渐趋缓和。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长诗反映这个过程,以及音乐对于自己的特殊作用。但精神上的康复还待漫长岁月,且时有反复。”①《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在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中说,“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②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这个“恢复”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个“恢复”,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我们先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③“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一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应朋友的邀请前往清华园休息调养,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星期。一月二十九日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④ 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似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⑤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在一九四八年底,沈从文就把对自己命运的预感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这年龄的人必然结果。”⑥ 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⑦ 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悲剧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
然而,到一九四九年,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并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不会顺时应变,可是一切都在顺应趋变。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而此时他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⑧
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又写道,“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⑨
“我不向南行”,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政府派陈雪屏来到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陈雪屏是沈从文旧识,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时的上司,曾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
三月十三日致张兆和堂兄之女、革命干部张以瑛信,说自己“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⑩ 最后一句话又用笔划掉。
二月至三月,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11)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2),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急救;后入精神病院疗养。
三、“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四月六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了长长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之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适。”“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他叹息道,“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他计划自己停止头脑思索,去从事手足劳动,甚至劳役终生。“我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再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作点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这个时候的心境,沈从文用“慈柔”两个字来形容:
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烈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人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隔院留声机放出哭泣声,而旁边放送者却发出笑语,“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13)
沈从文四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已经没有他的课程。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
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在静夜中随手写下一篇文字,题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记录和描述他当时的精神情形。
他从静中第一回听见窗下灶马振翅声,又在全城奇怪的静中似闻远处鼓声连续。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起始疯狂?”紧接着他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一个人“游离”于“一个群”之外的“完全在孤立中”的状态,这是他自“生病”以来最耿耿于怀、反复申说的感受:“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后来又写道:“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新的时代其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
他在极静中想到一些人事,其中主要由三个女性——丁玲、张兆和、翠翠——来展开,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幻想/幻觉。
写字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那是一九三一年,丁玲丈夫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和烈士遗孤回湖南常德,在武昌城头和凌叔华一家人合影。一九三三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沈从文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抗议,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从七月连载至十二月,唤起公众对失踪者的关注。时代变了,丁玲成了新政权的文艺官员和风云人物,当年的遗孤也长成青年——“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照片发呆。”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失去意义,“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就要毁灭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他说到自己的孩子,在回想丁玲的时候也讲到丁玲的儿子韦护和凌叔华的女儿小莹都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在孩子的鼾声中写的,他写道:“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他也早说过,自己“不向南行”,是为了下一代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和成长。
可是他自己呢?“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在最想不清楚自己的时候,在最孤立无告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和风俗人情中的美好形象,沈从文在这样的时刻想到翠翠,我们据此来看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他的家乡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其血肉相连、生死牵记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像。而且,他想到翠翠的时候,用的是将来时态,用的是第二人称,就像在和翠翠说话,在喊着翠翠:“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三三也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又是现实中他对妻子的称呼。从虚构回到现实,“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14)
四、“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吾丧我”;可是沈从文还在“搜寻”,他没有放弃。在“疯狂”中,他差不多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也一直试图着恢复过来。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
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衡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15)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是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丁玲在六月份曾经和何其芳到家中看过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沈从文在信中提到这句话,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他写这封信,向丁玲提出了一个实际要求。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起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6) 这封信别的意思暂且不论,仅就他向丁玲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九月二十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17)
“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如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的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串回复本来。”(18) 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19) 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十月一日完成。
五、“疯狂”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
我们很容易把沈从文的“疯狂”视为外力逼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也很容易为这种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20) 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的,确实难逃其咎。这一罪责,无论怎样追究都不过分;何况我们也并没有怎样仔细清理过其中的缘由。
另一方面,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的缘由。他自己说到于“群”之外“二十年”的“游离”,是“病根”。我们从比较明显的思想征兆来看,至少需要追溯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在昆明写作《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和《绿魇》、《白魇》、《黑魇》、《青色魇》诸篇什的时期;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又发表《新烛虚》(后改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从现实学习》等文章,从而使得这种思想状况延续贯穿了整个四十年代。
沈从文至昆明时期思想上已经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21) 要说“疯”,几乎可以说沈从文那个时候就开始“疯”了:“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22) 原本不长于抽象思考的沈从文,却在这个时期思考起“抽象”的大问题来,而他所说的“抽象”,其实总是与具体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也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搏战不已,“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23) 他的大脑和心灵成为无休止的厮杀的战场,他承受不了,所以“发疯”了。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啮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24)
把这一时期沈从文所表述的内心思想图景——如上述一段文字——和一九四九年“生病”期间的“呓语狂言”相对照,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发现惊人的相似。渴望“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即隐约透露出到一九四九年时已相当明确的“自毁”意识;其时所感受到的在周围人事中的隔绝无援,彻底性也正如后来的体验,如《绿魇》中的情境:“主妇完全不明白我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25) 他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的日记中提到《绿魇》,说,“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已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作人事说明时,那能条理分明?”(26)
“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似乎是说,一九四九年的精神状况与时代转折造成的个人现实处境的岌岌可危紧密关联,而并不仅仅是“抽象”领域里的问题。如果说昆明时期的精神危机和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失常”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疯”,而一九四九年时在“疯”之外,更表现为“狂”,特别是在“生病”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不妨做一点细微的区分:“疯”主要是指思想争斗不休、茫然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而“狂”则是思想意识十分清醒姿态下采取的带有极端性的言行。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这是针对自身的现实处境而产生的“疯狂”。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了来吗?沈从文也有如此的“狂言”: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27)
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效果,也必须给予认真的对待。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的文章里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28)
六、文学
在一九四九年的分水岭上,沈从文得向文学告别了。对沈从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他安身立命的事业,奋斗了近三十年,而且打算终生在这个事业上奋斗下去。只要想想他在“疯狂”时向他小说里的人物翠翠诉说,向翠翠亲人般的诉说,就大致能够体会文学写作对于他至要至亲至密的意义。而且,虽然沈从文早就以独特的风格和非凡的成就确立了文学上的重要地位,但对沈从文自己来说,他的抱负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他仍然怀有文学上的“野心”。
时间倒回去一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叙述当天晚上他和儿子虎虎讨论《湘行散记》,“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其间这么有一段对话——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29)
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未来,是充满了相当自信的。
可是没过多久,他即使在“病”中,也仍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文学的未来一下子破碎了:“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30)
而就在“生病”之前的两个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沈从文还在为文学的自主性而与人辩驳。这次座谈会是在时代的转折关口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其中论及文学与政治“红绿灯”的关系问题: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31)
座谈会后不久,他即认识到这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就想到,不能不搁笔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沈从文在精神病院,读到新时代的文学。“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32)
基本上可以说,在新的时代里,沈从文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作家了。但是,“跛者不忘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常常想到创作,甚至很努力地去尝试着写了一些东西。
更堪玩味的是,在他并未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主要是书信,还有检讨、交待、旧体诗等)里,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文学性。仅以书信而论,按照惯例可以把书信当作广义的散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其实仅仅如此远远不够。完全可以把书信就当作书信,不必去攀附散文,从而进一步认识书信这种写作形式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文学史意义。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照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沈从文书信,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书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得他一九四九年起的大量书信这样一种“潜在”的写作文本集中面世,至少使得那一长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仅就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书信这种典型的“私人性”写作空间,为通常的文学史所忽视,可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
就连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也可以看作是特殊的文学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但是,这样的文学价值却并非沈从文的本意和追求,当他决定放弃自觉的文学事业时,他心中岂止是不甘——“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
七、恢复,新生
沈从文最终从“疯狂”中恢复了过来。恢复过来,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就此加入到“群”中,加入到时代潮流中,顺势而动,与众浮沉?简单点说,是不是一个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狂人”,当他不再“狂”了,就变成了一个泯灭了自我的庸众中的一员?说到“狂人”,我们不妨回头看看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对《狂人日记》的解释。小说前面的文言小序,说“狂人”“所患盖‘迫害狂’之类”,“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33) 病好以后,就到一个地方去做小官了。对此有一个比较为大家认可的解释,就是狂人的反抗失败后,他又回到了他反抗的社会结构中,为这个社会体制所同化。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狂人的“疯狂”是毫无意义的,对社会而言,他的反抗没有作用,完全失败了;对于他自己来说,除了生了一场“病”,也是什么也没有改变,又恢复到正常。这样来看,狂人的“疯狂”其实是白费了。
狂人其实是“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的觉醒是从身在其中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独自觉醒;然而,这是一种“尚未经过将自身客体化的‘觉醒’”,处于脱离现实世界的状态,因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无从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因此需要获得再一次觉醒,回到社会中来。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伊藤虎丸针对鲁迅的狂人形象论述道:“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这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以‘觉醒狂人’的眼光彻底暴露黑暗社会的《狂人日记》这一篇小说,如果从反面看的话,那是一个患被迫害狂的男人被治疗痊愈的过程,也必须看作是作者脱离青年时代,并且获得新的自我的记录。”(34) 从鲁迅个人的精神发展来说,通过《狂人日记》,鲁迅为早年所形成的类似于安特来夫式的封闭的孤独的内面世界,打开了一扇向现实和环境开放的门,因而从此获得的新的自我,就是与环境共生的自我。
对现代主义持有强烈批评意识同时又表现出非凡洞见的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考察到,病态心理的意义是所有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心问题,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穆齐尔(Robert Musil)关于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面对一个简单的选择:一个人或是随波逐流(入境随俗),或是变成一个神经病人。”卢卡契指出,取决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每个时期都给病态心理加上新的重点、不同的意义和艺术功能,如果说自然主义对病态心理的兴趣来自美学需要,企图以此逃避日常生活的沉闷和枯燥的话,穆齐尔的话则表明,病态或精神失常已经成了反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道义上的抗议。鲁迅的狂人也正是以他的狂对他所置身的历史和时代宣战的。然而,卢卡契敏锐地发现,“对于穆齐尔和许多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来说,病态心理成了他们艺术意图的目标及最终目的。但是在他们的意图深处带着一个固有的双重困难,它来自内在的意识形态。首先缺乏明确性。这种由于转入病态心理而表现出来的抗议,只是抽象的姿态;它对现实的否定只是一般的和概括的,没有具体的批判。这一姿态决不会导致任何成效,只是逃遁到空空荡荡的世界里去。”狂人的失败也正可作如是观。卢卡契接着指出,“在穆齐尔的作品中,作为新类型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东西——遁入神经失常作为对社会罪恶的反抗——在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成为不可变更的人类处境。”(35) 就是在这里,鲁迅与卢卡契批判地概括的某种现代主义类型分道扬镳了,他没有让他的狂人坚持他的狂并以此作为空泛的批判之所——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正是逃避现实之所,而是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失败,并且进一步从狂中走出来,走进复杂的现实中,从而与他置身的环境恢复有机的联系。回到现实中,然后才能展开可能产生成效的现实行为。鲁迅轻描淡写地交代的狂人的痊愈,不可不谓是意义重大的新生。
沈从文的恢复,也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生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新生的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
这个新生的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地诞生的,唯其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这样的诗句,不是空话。沈从文的后半生,可为新生证实。他在这个后半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绝不是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所理解的人生取舍,这种哲学,看不到极端痛苦的精神崩毁,看不到从崩毁中极端艰难的新生,当然更看不到这个新生自我平凡朴素外表下的生命的安定、丰富和辉煌。
注释:
①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38页,4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
②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③沈从文:《题〈绿魇〉文旁》,《沈从文全集》第14卷,456页。
④沈从文:《复张兆和》(19490129),《沈从文全集》第19卷,7页。
⑤《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19490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9页,10页。
⑥沈从文:《致季陆》(19481201),《沈从文全集》第18卷,517页。
⑦沈从文:《致吉六》(19481207),《沈从文全集》第18卷,519页。
⑧《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19490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10页。
⑨沈从文:《复张兆和》(19490202),《沈从文全集》第19卷,16页,17页。
⑩沈从文:《致张以瑛》(19490313),《沈从文全集》第19卷,20页,19-20页。
(11)《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编者注释,《沈从文全集》第27卷,37页。
(12)张兆和:《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19490402),《沈从文全集》第19卷,22页。
(13)沈从文:《四月六日》(19490406),《沈从文全集》第19卷,24页,25页,28页,29页。
(14)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第19卷,42页,43页。
(15)沈从文:《致刘子衡》(194907左右),《沈从文全集》第19卷,45页。
(16)沈从文:《致丁玲》(19490908),《沈从文全集》第19卷,48页,49页,51页,52页。
(17)沈从文:《致张兆和》(19490920),《沈从文全集》第19卷,54页。
(18)沈从文:《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沈从文全集》第15卷,213页,214页。
(19)沈从文:《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沈从文全集》第15卷,222页。
(20)1948年3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集中刊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1949年1月沈从文所在的北京大学还贴出了大标语和壁报,同时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文章。
(21)沈从文:《长庚》,《沈从文全集》第12卷,39页。
(22)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43页。
(23)沈从文:《长庚》,《沈从文全集》第12卷,39页。
(24)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第12卷,34页。
(25)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155页。
(26)沈从文:《四月六日》(19490406),《沈从文全集》第19卷,31页。
(27)《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19490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11页。
(28)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晚翠文谈新编》,23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29)沈从文:《致张兆和》(19480730),《沈从文全集》第18卷,505页,504页。
(30)《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19490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11页。
(31)《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纪录》,《沈从文全集》第27卷,290-291页。
(32)沈从文:《四月六日》(19490406),《沈从文全集》第19卷,25页。
(33)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422页。
(34)伊藤虎丸:《〈狂人日记〉——“狂人”康复的记录》,《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148-149页,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5)卢卡契《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148-1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